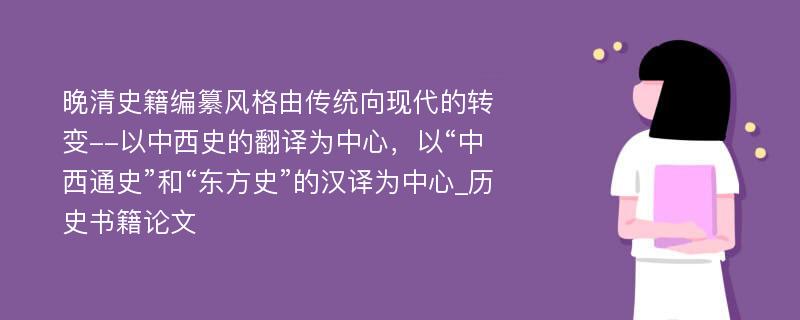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洋论文,通鉴论文,万国论文,支那论文,体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2-0001-10
中国传统历史撰述的题材种类很多,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有一个概括,称主要的不过五种,即编年体、传记体(即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和记言体[1](P266—267)。18世纪时,章学诚已提出改进历史编撰方法的主张,他认为传统史书占统治地位的纪传体,存在着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缺陷,比较可行的史书体例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2](《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国史学在晚清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晚清之际,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传统史书体例均未能完全承担起表述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要求。在传统史书体例中尚能接近新史学理想体裁的,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体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3](P20)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不断出现,传统的史书体例很难适应近代教育教学之需,于是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史体——章节体应运而生。关于近代史书体例的更新,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一书的第七章有过专门讨论,她指出:“随着西方新史学著作传入和影响扩大,中国学者对选用西方史学著作体例和改造旧史体例产生很大兴趣。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时,许多学者借鉴西方新史著的体例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适应新式学堂所用的历史教材多采用以往没有的新型史书体例。这对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更新,成为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4](P303)。
晚清时,西方史学东渐日本和中国,继而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史译著在中国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从史学观念、史书内容到史书表述形式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如《东西史记和合》带来了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历史著述;《四裔编年表》传送了一种中西历史时间对照的年表体;《大英国志》展现了世界史中的国别史;《欧洲史略》则给予一种区域性的“洲史”;《防海新论》展示的是一种西方战争实录体;《泰西新史揽要》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每百年为一周”的“世纪史”。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在此一时期东西史学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其标志性的应属章节体的采纳。这也是诸多论著中所谓的“新型史书体例”。
笔者认为,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且首先由西方传教士将这一史书体例带到中国的,这一点我在《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已有阐述①。然而,从西史汉文系统中的出现,到被中国史书编撰者采纳为编纂中国史书的主要形式,期间有一个过程,亦有诸多构成变化的环节。本文拟通过陈述这个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环节,来说明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如何在晚清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一、晚清最早出现的卷章段结构的译著《万国通鉴》
1869年11月28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tos Sheffield,1841-1913,字锡恩,一作子荣)到达中国,被安排在离北京城东二十余公里的通州传教。1886-1887年,潞河男塾正式改名为潞河中学,学生共计三十名,其中二十六名为住读生,四名走读生,全部都是教徒。谢卫楼自任校长。1892年,该校学生增加到了六十二名,其中有十名据称已有大学程度。他们已经学过了圣经、基督见证、精神哲学、三角、数学、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地质学、自然地理、世界史和中文学科。所有课程都是通过中文教授,为了做到用中文教授,谢卫楼花了很多时间用中文编写或翻译教科书。1893年,该校又一次改组,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附设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校长仍由谢卫楼担任。1904年,潞河书院升格为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谢卫楼仍当校长。谢卫楼用中文为潞河学校编写了许多教科书和译著,如《教会史记》(1896年)、《理财学》(1896年)、《是非要义》(1904年)、《心灵学》(1907年)、《政治源流》(1910年)、《圣教史记》(1914年)等②。反映潞河书院教学状况的《潞河书院名册》中记载,直至1880年,潞河中学的课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四书五经,“兼学鉴书、古文、时文”;二是学习《圣经》新旧约,“考其事迹,究其蕴蓄”;三是“学西国纲鉴、算法与格致各书”③。其中“鉴书”显然就是指“中国史书”;“考其事迹,究其蕴蓄”,其中包含着与《圣经》有关的历史内容;“西国纲鉴”一课显然是指西方历史。为了让潞河男塾的学生有一部合适的世界历史教科书,谢卫楼在讲授“西国纲鉴”一课之余,以浅近的文言编写了一部《万国通鉴》。
谢卫楼参照了马礼逊辞典中将history译为“纲鉴”的思路,将世界历史教材译作《万国通鉴》。这是一部参考了许多西方史书而用浅近文言编就的世界历史教科书。目前所知,该书有好几种版本:(1)有英文版权页和谢卫楼英文自序(English Preface),又有赵如光中文序言刻本,赵如光笔述,最后附有中英文人名、地名对照的索引。该版本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行。英文书名为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In Easy Wen-Li illustrated with Thirteen Large Double-Page Mounted & Colored Maps and in addition an English Index④。(2)仅有赵如光中文序言的版本。后附录“天下六洲图”、“亚细亚”、“欧罗巴洲”、“古希利尼”、“古以大利”等地图十二幅,但无英文版自序和中英人名、地名对照索引。(3)书名题为《万国史论》(又题“历代万国史论”)的戊戌(1898年)中秋杭州石印本。该版卷章段几与上述版本完全相同,只是附图十二幅极为粗糙,同样没有中英文人名、地名索引和英文自序。(4)五卷本,卷首一卷。又,北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清光绪年间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还有上海书局本。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年)有冈千仞训点、四书房发兑的《(订正)万国通鉴》五卷本,该书载有河野通之节译的谢卫楼的英语自序,题为兑设特(即谢卫楼英文名字Devello Zolotos的译音)《万国通鉴英语序》。冈千仞在序中称:“此书成于耶苏教徒,其纪我邦及汉土,极口论驳圣道,特为无谓。唯方今五州普通,各国此书各国讼革,不可不一日讲之。而此书各国理乱兴亡之故,可一览尽其要。其论涉教法,虽属无谓,亦可以观东西风尚之异一至此。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于此书亦云”。(5)福州还出版过该书的节本《(榕腔)万国通鉴》卷一、二,林穆吉译成榕腔、摩嘉立(C.C.Baldwin)修订,福州美华书局1892年出版。该版是以福州方言译出的谢卫楼《万国通史》四卷本中的第一卷和第二卷。
《万国通鉴》几种版本尽管卷数不一,但核心内容大致相同,章节也基本一致,均采取卷、章、段体的结构,四卷本。前有“引”,分为五论:第一论“亚当至洪水后事”,第二论“洪水后生民度日”,第三论“国度律法与分定人之等次”,第四论“古时敬神之道”,第五论“东方人民居亚细亚大洲”。第一卷“东方国度”共四章:第一章“论中国事略”,分二十五段,第一段“上古开国之事:三皇纪略”,第二十五段为“论大清纪略”,下限讨论到1875年。“论中国事略”外附“儒释道三教说略”。第二章“论蒙古事略”,第三章“论日本国事略”,第四章“论印度事略”,基本上是叙述亚洲主要东方国家的历史。第二卷至第四卷为西方历史。第二卷“西方古世代”分八章,第一章“论犹太国事略”,第二章“论伊及国事略”,第三章“论巴比伦和亚述国事略”,第四章“论玛代国和波斯国事略”,第五章“论腓尼基人事略”,第六章“论喀颓基人事略”,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第八章“论罗马国事略”。第三卷“西方中世代”分十五章:第一章“论北方苗人迁移之事”,第二章“论东罗马国又名庇三提尼国事略”,第三章“论回回教事略”,第四章“论喀漏芬及岸朝事略”,第五章“论英国事略”,第六章“论日耳曼国事略(撒可森朝、范叩尼亚朝)”,第七章“论天主教出征(又名圣战事略)”,第八章“论日耳曼国事略(侯很斯他分朝、哈配斯布革朝、鲁森布革朝)”,第九章“论法国事略(喀佩献朝、法勒洼朝)”,第十章“论天主教分门与两次大议会事略”,第十一章“论英国事略(接上五章)”,第十二章“论西班牙国事略”,第十三章“论葡萄牙国事略”,第十四章“论土耳其国事略”,第十五章“论中世代风土人情”。第四卷“西方近世代”,分上、下两部分,共计三十一章。第四卷上,十七章:第一章“论在欧罗巴洲数国事体振兴事略”,第二章“论教会更正事略”,第三章“论西班牙与西班牙之属国事略”,第四章“论法国为道战争事略”,第五章“论英国事略”,第六章“论瑞典哪威莲国事略”,第七章“论自更正起百年之间各等学业振兴事略”,第八章“论在日耳曼国三十年战事”,第九章“论英国改变事略”,第十章“论法国事略”,第十一章“论北亚美利加开国事略”,第十二章“论西班牙王位战事”,第十三章“论欧洲北方数国战事”,第十四章“论布国兴盛事略”,第十五章“论英法为争北亚美利加之地战事”,第十六章“论立美国事略”,第十七章“论从法国所出之文字激动多国人心”。该书第四卷上第一章所谓“欧罗巴洲数国事体振兴”,其实就是在说欧洲文艺复兴。第四卷下,共十四章。第十八章“沦裒兰国被他国分据俄与土交战事略”,第十九章“论法国民变事略(接上卷十章)”,第二十章“论英国事略(接上卷九章)”,第二十一章“论法国事略(接十九章)”,第二十二章“论在以大利之地数处小国合为一统事略”,第二十三章“论日耳曼国复兴事略”,第二十四章“论土耳其国事略(接上卷十四章)”,第二十五章“论俄国事略(接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希利尼脱离土权成为自主事略”,第二十七章“论美国事略(自洼性吞即位直至现今)”,第二十八章“论默希哥事略”,第二十九章“论南亚美利加各国事略”,第三十章“论亚非利加洲事略”,第三十一章论“格物之学术兴起”。附“论耶稣教之风化”。
《万国通鉴》在编纂上显示出如下的特点:首先,该书是晚清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史,这是较之更早的《古今万国纲鉴》和略早的《万国史记》都不曾采用过的。但也并非完全如后来的章节体形式,因此,有论者称该书的“论中国事略”就是采用章节体形式,可以说是章节体中国通史的首创[5](P9),其实并不确切。该书采用卷、章、段的形式,与《万国史记》类似,在每页的天头,都有若干类似内容提要的识语,似乎接近后来的小节标题,我把它称之为“段”。这种以卷统章,章下设小段的方式贯穿全书。因此,称该书最早采用了卷章体或卷章段体则更确切。
其次,《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记述历史演变可以采用不同的“历史时间观念”,有皇帝时间、政治事件时间、文明时间、类型时间和符号系统的时间观念等等。在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中,也有自己的独特表述方法:(1)每个时间单位的开始和终结都是以王朝更替来计算的,历法纪年一般也只是以皇帝在位年代来计算的。这种纪年法是与古代中国的治乱兴衰的易代观念相联系的。(2)采用“世”的分期法。分期划分法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结果,中国很早就有了历史分期的划分,如《韩非子·五蠹》中就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的分期[6](P339);《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将历史演变发挥为“所见之世”、“所闻之世”和“所传闻之世”⑤。但这种断“世”是一种模糊的和笼统的概念,并无确切的时间断限。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如二十四史中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近世”之类的时间分期,并非以前后相续的系列分期的形式,而是以分开的、零散的形式出现的,是没有系统的分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7]。西方的历史分期最初出现是与基督教神学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用以标注历史时间和划分时代的标准是“纪元”或“公历”。这种时间观念代表着基督教思想对西方历史的支配,历史以基督出生为准,划分为纪元前和纪元后两部分,历史也就以神的启示和生命为过程。但这也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概念: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帝国、国家的历史兴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国通鉴》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正是通行于欧洲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不同时期的划分法的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反对历史连续性的观点,特别是反对将他们自身的时代通过文化凋敝、学术凌夷的黑暗的中世纪去衔接古代。作为一种抽象概括来揭示历史演变的具体手段,则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尽管《万国通鉴》没有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历史加以分期,但这种西方历史分期法还是为东方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横向比较提供了时间坐标。
第三,西方史家编写的世界史一般很少叙述东方的历史,即使叙述也多是为了辅助西方历史的展开,如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对东方历史的若干描述,就是为耶稣传记的阐释与基督教历史的撰写作铺垫。《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虽然内容有限,论述肤浅,但将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内去认识。该书采取了统一的纪年法,包括中国历史也在书眉标注了耶稣纪年,并附录了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表明了作者对于一种统一的世界史编写模式的追求。这一方法以后渐渐被中国学者所接受,成了中国学界后来所有“万国史”编写的通行模式。这种模式接续着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写《东西史记和合》的思路,堪称是世界史编撰上的创见。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关于东方历史——中国、蒙古、日本和印度的叙述均没有采用西方历史分期法。中国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历史的编写,从先秦至清光绪年间,从未采用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法,贯穿一线编写模式均为传统中国史书的朝代世系。可能是谢卫楼并非历史学家,特别是对于东方史,如中国史和日本史,基本上是陌生的,而能够参考的那些西方史学读本,对于中国史也缺乏很好的研究和完善的叙述。一般西方史家也多认为,作为分析单元的王朝系统,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带有周期性的波动的因素即使在晚清也并未消失,其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因此,可能谢卫楼在无法对东方世界进行历史分期的情况下,只能于东方与西方采取了不同的书写方法。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属于过去时代的、缺乏近代意识的落后的文化⑥。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对《万国通鉴》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当时传教士撰写的史书中,“很少有这类著作行世,没有一部著作涉及如此广泛的范围”,该书“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有一些经特别装帧在官员中发行”[8](P566)。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9](P641)。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书籍有二十五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著。通史类中仅列入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美国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两种。可见,当时有关世界通史的著述的确不多。1898年,王树柟所撰五卷本《欧洲族类源流略》简述欧洲巴斯革(今译巴斯克)、伊都斯干(今译伊特剌斯坎)、芬、拉伯(今译拉普)、亚利安、斯拉夫、鞑靼等古今民族源起、族属、分支、风俗、分布和迁徙兴亡之迹,略加考释。书中评论欧洲各国政事得失,否定上帝造人及中国人种西来说,并依据进化论,强调弱而愚的旧民族,每不敌强而智的新民族,旧族惟有复兴方能生存发展。提出中国应该亟图自新,以免遭西方列强侵略瓜分。该书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来自《万国通鉴》和《欧洲史略》[10](P263)。
二、影响晚清国人章节体通史编纂的《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
西方史学新的史书体例,首先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19世纪下半期,在日本出现了一批章节体的史学叙事结构的论著,如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的《万国史纲》,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合著《西洋史纲》,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家永丰吉《文明史》等。不少史家还采取章节体撰写东洋史和中国历史,如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田中萃一郎《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等。不少章节体的史著对中国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除上述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外,还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等。
主持东文学社的罗振玉非常关注上述日本学者历史著述,可能是为了给东文学社的学生提供一本适合阅读的中国通史的教材,藤田丰八给罗振玉介绍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因为《支那通史》是那珂通世用汉文撰写的,因此首先出版了该书。那珂通世年轻时曾立志从事英学,二十二岁入福泽谕吉门下,福泽关于亚洲历史停滞论的观点深深影响到那珂通世及其所著的《支那通史》。1886年起,那珂通世致力于《支那通史》的撰述。原计划完成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七卷。卷一为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卷二、卷三、卷四为中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期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期为西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期自五代辽宋至金章宗末年。卷五、卷六、卷七为近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近世史上期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近世史中期自明太祖至清太宗,近世史下期自清世祖至晚清。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九月出版第一卷,十月出版第二卷,十二月(1889年)出版第三卷,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年)出版第四卷。正式出版的四卷本,共五册,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有东京中央堂印本。近世史终未完卷。该书前四卷问世以后深受中日学术界好评。其特点:一是完全用汉文撰写的,因此很快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二是选用史料范围广泛,不仅注意根据中国古书,也兼收西洋人所录;三是体例新颖,简明易解,打破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采用西方章节形式的记述体。上世、中世、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不仅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之意义,而且其实质还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包含着欧洲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理念,而文明的开化程度正是衡量上古、中古与近世这种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志。
《支那通史》首卷为总论和上世史。总论分三章,讨论中国地理概略、人种之别和朝家屡易,阐述中国地理变迁的大势、人种类别和朝代更替的概况。上世史分八篇,讨论自唐虞三代至战国的历史变迁。第一篇唐虞,第二篇三代,第三篇诸侯本末,第四篇春秋,第五、六篇战国,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第八篇先秦诸子。附录“历朝兴亡禅代图”、“三代世系”、“齐晋及七国世系”、“周秦列王在位年数”等。卷二中世史上期分九篇。第一篇秦,第二篇楚汉,第三、四、五篇为前汉,第六、七篇为后汉,第八篇三国,第九篇制度略。附录“秦汉三国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两汉后家多破灭”。卷三中世史中期分九篇。第一篇西晋,第二篇东晋,第三篇南北朝,第四篇隋,第五、六篇唐,第七篇外国事略,第八篇文学宗教,第九篇制度之沿革。卷四中世史下期分六篇。第一篇五代,第二、三、四篇宋朝,第五篇学艺,第六篇制度。附录“五代列国世系”、“宋辽金夏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秩表”以及“地球沿革图”。该书与中国传统史书的重大区别在于,不仅注意对政治、军事事件的描述,还特别注意对文化制度的介绍和分析,如卷一上世史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特别介绍中国的姓、名、氏族、婚嫁制度、宫妾、宦官、丧葬祭祀等,以及阴阳五行之说和先秦诸子的学风与学说。卷三中世史对学制、佛教与道教、基督教在早期中国的传播,以及唐代与西域的交通、唐代的职官、州郡、赋税、选举等制度文化等,卷四对于宋代的儒学、学制科举与党禁、诗文、货币制度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和分析。原书有日本著名学者中村正直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所写的序言,称:“今世所行支那史之简易者,如《十八史略》、《通鉴挈要》,非不良善,但止于纪事实,而不及典章法度,此为可憾。那珂通世氏此书,纪事实而及制度,略古代而详近世,不独采于支那史而兼收洋人所录,简易明白,一览了然。”[11](卷1)
1899年,东文学社还出版了樊炳清根据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一书译出的《东洋史要》。该书原著二卷,出版于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梁启超《东籍月旦》称:“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凡分全史为四期,第一上古期,汉族膨胀时代;第二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第四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繁简得宜,论断有识。”[12](P1376—1386)樊炳清译本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译出距原书初版仅仅一年的时间。该书中文版版权页题名“格致学堂译、东文学社印”。全书分总论、上古期二篇、中古期九篇。总论四章,分别为论本书之大旨、地势、人种、区分时代。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二篇。第一篇“周以前”分三章,讨论太古、尧舜事迹、夏殷兴亡;第二篇“周”分九章:一、周之勃兴与其制度,二、周之盛衰,三、汉族与诸外族关系及周时戎狄跋扈,四、霸者,五、自春秋末至战国初形势,六、诸学兴起,七、秦之勃兴,八、合纵连衡,九、秦之统一。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分九篇。第一篇“秦及西汉初叶”分六章:一、始皇帝政策,二、秦之亡,三、汉楚之征,四、高祖政策,五、自惠帝至景帝间形势,六、武帝之治。第二篇“西汉经略外国”分五章:一、南方诸国与西汉关系,二、古朝鲜与西汉关系,三、匈奴勃兴,四、西域诸国沿革大略,五、匈奴衰微。第三篇“西汉末世及东汉初叶”分三章:一、自武帝至元帝间形势,二、外戚之专权与王莽篡立,三、汉室之再兴与东汉初叶。第四篇“佛教东渐”分四章:一、释迦以前印度状况,二、释迦出世与阿输迦王时代,三、大月氏之勃兴与佛教东渐,四、东汉与西域诸国之关系。第五篇“东汉末世三国及西晋”分四章:一、东汉末运,二、东汉之亡与群雄割据,三、三国鼎立与晋之一统,四、晋室大乱。第六篇“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分七章:一、汉末以来塞外诸侯与汉族关系,二、汉之勃兴与前后两赵兴亡,三、东晋盛衰与前燕前秦之兴亡,四、后魏之兴及南北两朝之分,五、后魏与塞外诸国交涉及后魏之极盛,六、后魏分裂及侯景之乱,七、南北两朝末路与隋之一统。第七篇“隋及唐之初叶”分三章:一、隋之盛率与群雄割据,二、唐之勃兴,三、太宗高宗之治及唐之制度。第八篇“唐经略外国”分九章:一、自汉末至隋初朝鲜,二、隋唐与朝鲜关系及百济高勾丽之亡与新罗之一统,三、突厥勃兴以前西域诸国形势,四、突厥之兴亡及唐与突厥关系,五、吐藩印度之形势及其与唐关系,六、唐兴中央亚细亚关系及大食之兴与波斯之亡,七、唐之管辖属地法,八、唐代东西互市,九、诸外教之东渐与佛教兴隆。第九篇“唐中叶及末世”分七章:一、武韦两氏内乱,二、玄宗之治,三、安禄山之乱,四、唐中叶以后塞外诸国,五、藩镇跋扈,六、宦者专权,七、唐之亡兴与群雄割据。由上述不难看出,该书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章节体,而是一种类似《万国通鉴》的篇章结构。
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总论中强调,所谓东洋史,是以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的一般历史,它与西洋史并列,构成世界史的一半。并指出,按山川形势,亚洲大陆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亚等五个部分。东洋史是以东亚(中国和朝鲜)为主体,阐明其历史沿革,同时对于与东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南亚、中亚的沿革,也不能不略述之。换言之,东洋史是以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为主线,论述兴亡沿革,对于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中国周边东亚、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也要略加述及。而那一时期,大部分日本学者的所谓东洋史的著述,实际上还是一部中国史。作为一部篇章体的历史教科书,《东洋史要》虽然没有正式设节,但每章中所分段落已具有节的形式,初具章节体的雏形。《东洋史要》由东文学社出版推出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销路看好,该书也曾多次重印,以后还有1903年宝庆劝学会舍本。同时,也引发了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其他异译本,如1904年还有泰东同文局的《东洋史课本》、科学书局出版有周同俞译《中等东洋教科书》,1906年有文明书局出版的周国俞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金为译《东洋史要》⑦。可以说,该书在晚清是颇受欢迎的中国史的读本。傅斯年在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指出:“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13](P1225)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以该书为蓝本的就有两湖文高等学堂1903年出版的陈庆年编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在该书序中称赞《东洋史要》,“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⑧。王汎森在《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一文中指出,《东洋史要》不仅采用了“章节体”,同时也开始采用历史分期。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划分中国历史。按照历史时期来划分的编写方法使读者发现只有一姓之变迁不足以为历史时期之标准,并认为如果不分期,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以至后来编写教科书的中国人便有意采取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14](P162—163)。这一点倒与《万国通鉴》既采用历史分期,又采用卷章段的形式不谋而合,从而在汉文史书系统中构成了转变的第二环节。
三、晚清西史、东史章节体新史体的影响
章节体史书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狭隘观念被破除而出现的一种新史书体裁。较之传统史书体例,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一是设编立章分节,较之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条理更为井然,能清晰地展现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次关系,从而打破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格局,有利于来表现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二是顺时按类,因事列目,较之传统史书记事更为简明,能依照时间顺序来陈述通史庞大的历史容量,打破了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循环论,有利于在历史进化论的指导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过程;三是分类分级逐章逐节层层递进,使复杂步变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等内容,在章节顺序之中脉络清晰,更适宜于表述现代史学的系统性。特别有利于逐章逐节进行历史教学,特别是,接近于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纂形式,改变了传统史书不适用于启蒙教育的缺陷。因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在晚清首先被国人用于编写中国通史,并被之后的历史教科书长期沿用。
在晚清章节体史书上,1902-1904年间,夏曾佑编撰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代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后于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编入“大学丛书”。论者多强调该书在近代中国通史的编撰上是首次成功地采用章节体的史书,其诞生后“章节体”一直被沿用,至今流行不衰,或对章节体史书为域外输入的见解表示质疑[15](P258)。有学者指出,夏曾佑编纂《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有感于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的发愤之作⑨,其所编《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如何受那珂通世或桑原骘藏著作的影响,但从该书开端的几节所叙述的种族、该书的分章分节,和他将中国历史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指清代)为近古之世,每个时期下面还划分出若干“时代”来看,虽然在时期或时代上与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的中国史与东洋史不完全一致,但仍不难看出《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留下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周予同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特别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方进化论思想的糅合,“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更应该注意: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就我个人现代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见解的输入。这种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更其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夏氏这部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支那通史》一书相近,而内容精审过之。就体裁说,显然的受了这位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16](P534—536、568注释[41])。
其实,同时代国人受东史影响,注意用章节体编纂中国通史者,并非夏曾佑一人。这期间还有柳诒徵《历代史略》这样一个环节。就在《支那通史》问世后不久,在日本和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续补本,其中国人柳诒徵补辑的《历代史略》特别引人注目。1901年,柳诒徵经同乡好友陈庆年介绍,从缪荃孙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纂。在编译局初期,修改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等两三部书,该年十二月初八(1902年1月17日),“即开始阅读《支那通史》,而逐日修改四五条。从次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起,他开始抄《历代史略》,至于当年九月十六(10月17日)编竟。”同年由江楚编译局出版,初印本柳诒徵没有署名。该书在当时“上海等地书店竞相翻版印售”[17](P198),光绪乙巳(1905年)孟夏,由上海中新书局用有光纸翻印出版,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称自己是“补辑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元明两代,改名《历代史略》”[18](P39)。该书共分六卷,首篇总论,仿效《支那通史》,第一章“地理概略”;第二章改为“历史大旨”。后分上世史(唐虞三代至秦统一)、中世史(秦至五代)、近世史(五代至明末),叙述自上古至明的历史。第一篇第一章“唐虞之国”改为“尧舜”;第二章“数十世开创”改为“三皇五帝之说”;第三章“尧舜事迹”改为“唐虞之地理官爵”,等等。元朝和明朝两卷是柳诒徵根据其他史书内容增辑的,体例仍据《支那通史》而与前者联为一体。中世纪末的五代作为近世史的开端。元朝作为近世史中,内分六篇二十一章,其中关于官制、礼俗、宗教、诗文、释道诸教、学校科举、地理、河渠漕运等都分篇综论,并附有历代世系表、官制沿革表、儒家传授表等,元朝部分增附了“元及诸国世系”,元朝“在位年数及年号”等表。明朝作为近世史下,分六篇二十六章,并录附“明及诸国世系”、“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元明官制沿革表”和“明儒传授表”等。该书顺应晚清日益开放的现实,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周边国家的史地,如卷三第七篇有“外国事略”、卷五第四篇有“西北诸国事略”、卷六第四篇有“东南诸国事略”,详述了突厥、回纥、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状况。第五篇第五章还有“天主教”,所附“中西之交通及历算西学”,介绍了利玛窦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明末的西学传播⑩。以日本《支那通史》为蓝本的这部《历代史略》,打破了中国史著沿袭已久的纪事本末体,改为条理分明的章节体,按朝代顺序编写出了各朝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如生产、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各类专题,篇中有章,因事立节,各相统摄。如果按照整部史书的完成时间,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恐怕较之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早。当年,张舜徽在《柳诒徵传》中就指出:“《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朝末年止,共六卷,每卷各分篇章。全书用流畅浅明的文辞,有条理有系统地叙述了历代事迹。由纲鉴体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体的新形式,这还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它采用了新的编书体式,是对旧纲鉴体例一次大的革命。而这种体例,从清末传到现在,除写作上由文言变为语体,观点上由旧变新外,大体上还是保存这种编写形式。柳诒徵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11)。
笔者借助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无非是想要强调,中国人接受域外新史学的章节体史书编纂体例有一个过程。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史学叙述结构,如1879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以“上古、中古、近古”(《万国史记·凡例》)的时代线索,采用卷节体例。1882年,美国谢卫楼撰写的《万国通鉴》最早采用了卷、章、段合成的新史书体例,以卷、章的形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景进行描述。另外,艾约瑟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更是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较之《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适应性更为广泛的地区史及国别史,而这些卷节体的史学叙事形式较之《万国史记》等更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形式。这种崭新的史书体例,以其纵横贯穿的叙事特点,显示出其既综合通贯,又有分门别类的结构上的优点,较之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更适宜于表述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史学叙事结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能反映纵横交错的政治事件、变动不居的军事战乱,而且能比较系统地阐明历史上相对静态的制度文化与社会规范层面的问题。因此,卷节体与章节体的史学叙事结构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编纂学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了成熟的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和采用历史分期法的东洋史。东文学社译刊的《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往的中国历史读本都是按照朝代的先后,用编年体或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体例编写的。这两种在东文学社使用的历史教科书,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较为完整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采用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相。因此,对中国读书界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较早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章节体的史书形式,而且由于两书的较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学生学习中国史的重要一环。如1905年,十二岁的吴宓在阅读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称自己“获益至多”[19](P55、58)。《支那通史》及其续补和《东洋史要》的各种译本成了清末学界的重要知识资源,如史学家王舟瑶曾指出:“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少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20](P2)因此,他不仅主张参考西方的新史,如“各国历史,极宜究心。就译本言,如《四裔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欧罗巴通史》、《埃及近世史》、《法史揽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外交史》等,皆不可不一读。”也特别强调吸收日本的史书来编写中国历史,指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如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太郎、龙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20](P2-3)20世纪初,夏曾佑在接触东史之前,也接触过西史。1903年,就在他创造章节体史书的过程中,还曾为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作序,并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多采其说。《社会通诠》是一部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史,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种历史形态。同时,夏曾佑还钻研过《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还为中译本校阅删润[21](P80、102),可见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东史,同时也有西史。如果说他编纂中国历史时采用章节体和历史分期主要是参据了东史,那么,西史也是他接受东史新颖形式的一种铺垫。
四、结语
史书体例,是史学家思想观念的体现,对史书体裁、题材体例的认识,实际上包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在史学编撰体例中,何种形式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演变,一直是困扰中国史家的一个问题。从孔子、司马迁、班固到刘知幾、郑樵、袁枢、章学诚等都不断在反省和探索史学叙事结构的合理性。中国的传统史书体裁,反映历史动态变化的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反映历史静态变化的有典志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出现较早,编年体比较适合反映政治史与军事史,纪传体虽然反映历史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但这两种体例的核心还是以帝王的纪年贯穿始终,历史叙事的内容通常都是有关朝代兴亡和社稷安危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主要线索不脱帝王将相的人物线索。即使被写入《史记·陈涉世家》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不是因为他是小人物,而是因为司马迁将其看作是汉代创建者的政治先驱,仍是正统历史观支配下的产物。南宋袁枢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这两种史学叙事结构的缺陷,因此,他“因事命篇”,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开辟了史学编纂的一个新途径。纪事本末体分篇综述,首尾相关,虽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史书,为近代梁启超所推崇,但由于袁枢受到他所依据的基本资料的限制,其历史叙事的结构仍拘泥于历史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世界。尽管如此,袁枢的纪事本末体结构还是成为晚清中国读者能较快接受西方史学叙事结构的本土知识资源。
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了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这一模式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编纂史书的主要形式。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都会列举柳诒徵的《历代史略》、陈庆年的《中国历史》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最应该注意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因为该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受到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大概是来自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的影响(12)。而亦有学者注意到,正是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后,引发改编国史运动,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才开始出现[22](P293)。但这种影响的源流以及发展环节似未完全澄清。笔者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它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周予同所说的在内容和体例上,既采用章节体,又采用历史分期法的史书新体例,在该书已具端倪,只是该书在论述中国事略时仍然采用朝代模式。它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个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章节体史书的积极意义是它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较之善于表现政治史演变的编年体也更能反映所谓“民史”,因为这种体例不再以帝王为中心、以将相臣佐为附庸,将文化制度、社会生活都融合在静态的“志”、“书”中。从这种意义上说,章节体这一灵活的编纂形式,是对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否定。
笔者认为,时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者都过分强调了日本史学论著对晚清新式章节体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晚清史学编纂形式的变化不是一个编纂史上的突变,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万国通鉴》和卷节体《欧洲史略》等历史译著到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诸多环节的渐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基本忽视了早期卷章段体《万国通鉴》等史书在史学叙事结构变化方面的作用。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有卷章段体等史书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卷章段体在中国史家重新思考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为后来以章节体形式编写历史著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可以说,《万国通鉴》是晚清最早出现的卷章段体例的史书,该书为后来章节体在中国史书编纂中成为主流编纂形式作了重要的铺垫。
附记:本文初稿2009年10月17—18日曾提交由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作报告,承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黄兆强教授等批评指正,特此鸣谢!
注释:
①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雷振华编《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汉津协和圣教书局1918年版)、罗伯特·帕特挪(Robert Paterno)《谢卫楼与潞河书院东创建》(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转引自刘广京等编《美国传教士在中国》(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6年英文版,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314页)。
③《潞河书院名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本,转引自吴义雄《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载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9—387页)。
④马金科、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版,第124—125页)将《万国通鉴》的英文书名表注为Universal History,称该书是谢卫楼和赵如光根据美国人Myers(今译迈尔)的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摘译的,所据不详。笔者认为,该推测明显不确,因为《迈尔通史》英文本初版时间在1889年。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0页)。康有为后来在《春秋董氏学》卷2中将公羊“三世”发挥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谢卫楼在《政治源流》(北通州协和书院印字馆1910年版,第146—151页)一书中仍强调“中华二千余年间,于风俗政治文学礼仪,少有改变”。(自序)在十八章“论中国的政治”和第十九章“论清国的政治”中指出:“清国政治多仿照前明”,“清国之行政,惟皇帝之权无限”,“其中之弊窦有不可胜言者”他认为“将来中国之政治日进日新,不难与东西诸强国齐驱并驾也”。可见他确实认为中国在晚清与西方尚未处于相同的时代。
⑦《涵芬楼藏书目录·历史地理部》(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数据系由汪家熔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⑧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陈庆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由两湖文高等学堂初版,后曾多次重印。原书内容至明而止,1912年,经赵玉森增订至清,补充原书未备。学部审定此书,多所订正校勘。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版。1913年4月,已重印9版,1921年10月,重版了15版。第15版为教育部审定。
⑨据陶振誉《日本学人对中国史的研究》一文称,夏曾佑曾经愤慨地说过:“如果因为学术发展的程度还未充分,中国人不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那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是,现在由日本人首先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则确是中国人可羞的一件事”。说明其在撰写时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⑩参见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清光绪乙已(1905年)印行
(11)参见柳曾符、柳佳编《劬学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柳诒徽在《凡例》中直接提到:“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显然不适合中国学生之需,这也是他为什么根据日本人那珂通世所著的《支那通史》稍加删改、编著《历代史略》的原因
(12)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536页、第568页注释[41]);参见邹振环《东文学社及其译刊的〈支那通史〉与〈东洋史要〉》,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7—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