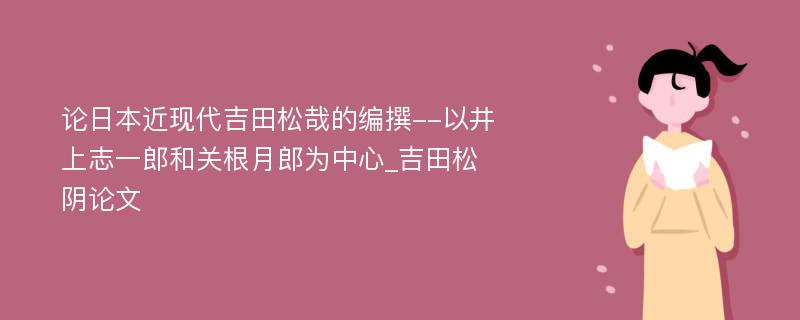
论日本近代时期吉田松阴像的编成——以井上哲次郎和关根悦郎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井上论文,次郎论文,吉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3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8)06-0149-06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志士。19世纪后半期,日本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打开国门后,他为维护日本的独立,积极探索实现政治变革的途径,终被保守专制的幕府处以斩刑。松阴门下涌现出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功臣,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后,吉田松阴愈来愈被迫念刻画为一个“神化”的人物[1]。日本历史学家田中彰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吉田松阴传记作品在250册以上,松阴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狂热尊奉的精神偶像[2]。田中将这些传记所刻画的松阴像的变迁过程总结为:“在与天皇制的关联中,作为体制性意识形态,松阴被渐渐渲染着色。”[3]125他又进一步指出: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奈良本辰也的《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51年)的出版为开端,逐步实现了“没有经过自我批判的松阴像的复活”。这导致“战争责任暧昧不明”,特别是以冈不可止、福本义亮等为代表的传记作者,“在战争时期描写军国主义的松阴像,疯狂地鼓舞战争士气”,在战后重又执笔描写松阴,却“看不到任何自我批评”[3]110-111。其实,田中认为松阴的真实形象被后人歪曲了。他说:“松阴对自己提倡的建立天皇的绝对权威=维新‘革命’,大概是赞同的。但其门下学生们逐渐以藩阀体制的形式强化天皇制,如果松阴能看到这个结果,他难道会漠然置之吗?其门下学生所建立的明治国家体制与松阴的目标日渐背离。”[3]52基于这种认识,田中的指责集中于松阴传记的作者。但问题是:为什么吉田松阴会被选做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典型形象?松阴的思想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其需要?这是本文力图解明的课题。
近代以来论述吉田松阴的视角主要有两个:尊皇主义(即尊奉天皇为绝对权威)和武士道论。田中彰主要考察了前一视角下的松阴像,而且集中于传记作品。在这一方法论之下展开的松阴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够充分。例如,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有1893年的初版与1908年的改订版两种,分析其异同之处可以很好地显示内在于松阴思想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局限性。田中也注意到了两版之间的变化:“在改订版中,初版中的‘革命’这一字眼全部消失了。‘革命’换成了‘改革’。”[3]42变化实际上不止如此,初版中并未提及武士道,改订版中却新设了《松阴与武士道》一章,并把吉田松阴作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来描述,其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著名武士道论者井上哲次郎所编制的“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的影响。有鉴于此,笔者首先以井上的松阴论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展示需要经过怎样的具体操作,才可以编制出符合官方所需的松阴像。然后以关根悦郎的名著《吉田松阴》(白扬社,1937年)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揭示对前一操作过程的抵抗之所以失败的内在原因,即松阴思想实态对松阴像的创作者所施加的制约。在学习田中彰宏观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采取细致考查具体个案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有助于加深理解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近代日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一、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系谱中的松阴像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0月17日,近代日本最大的教育者团体“帝国教育会”在松阴殁后50周年召开纪念大会。在大会之前,松阴神社得到了天皇下赐的祭粢料(供物费用)。此次纪念大会是吉田松阴像被编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田中彰指出,从1893年德富苏峰初版本《吉田松阴》的刊行,到1908年10月其改订版刊行即松阴纪念大会召开前一周左右,是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期。但是当纪念大会召开的时候,“在这次纪念大会的名誉委员中,以政界、财界、学界的名人为首,当时的文化、言论代表者共有204人署名,大会委员有22名。其中可以看到井上哲次郎、德富猪一郎(苏峰——原注)、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名字,他们后来都发表了追颂演说。看到这名士云集如满天星斗的大会,便可以明白吉田松阴已经被作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供奉起来了。”[3]45那么,在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空白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吉田松阴到1908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了呢?田中的书中没有论及。为了考察这一转变,必须分析井上哲次郎的工作。
井上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著名代言人。他对松阴思想的初次全面论述见于其1900年出版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后来盛极一时的武士道热,吉田松阴也还没有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井上主要是把松阴作为日本阳明学派的一员来叙述。关于松阴的著作,井上最看重吉田松阴推崇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楠木正成(1294~1336年)所谓“愿七生人间,以灭国贼”的思想的《七生说》[4]556。井上全文收录了松阴此文,又引用吉田松阴书信中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若不能做些抒发心中郁愤的事情就死了,没有办法成佛。”称赞松阴的“死生之说”是“豪杰的生死观”[4]559。最后又收录了松阴的两首汉诗,并赞道:“如非其决心之强固,学问之素养,不能至于此,自不待言。”[4]560
但是与吉田松阴相比,井上在谈论幕末维新时期的志士对近代日本的精神影响时,对另一位阳明学者西乡隆盛(1827~1877年)有更高的评价。井上认为,虽然西乡在1877年发动反对明治政府的叛乱,带着“逆贼”之名而死,但是,“他由此而得以激发活力,鼓舞士气,进行了实弹演习……如此锻炼得来的胆量和技术,应用于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引者注),无疑是其制胜的一大原因。然则后人岂无所负于南洲(西乡隆盛的号——引者注)乎。然后可知此本来源于其方寸之中所养成的炯炯然一点良知之光也。”[4]553-554在这个时候,井上也还没有开始强调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队的影响,而是推崇阳明学的行动精神,盛赞西乡隆盛的“良知之光”。他如此总结西乡的行动:“充以至诚,其下定决心行动时,生死皆不放在眼里。”[4]552
这些要点,大体和在近代日本大力宣传的所谓松阴精神是一致的。比如德富苏峰说:“松阴一生的画龙点睛,在于至诚二字。”[5]458并以“彼实为学至诚而得至诚也”[5]463一语,结束了其改订版《吉田松阴》的“画龙点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作为近代日本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人物形象,吉田松阴总是以藩主或天皇的具体意志作为判断标准,而西乡隆盛则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判断标准而思考和行动。西乡有著名的“敬天爱人”之说:“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也。人若行之,则以敬天为目的。天者对人对我,皆给予同一之爱,以爱我之心爱人也。”[6]13由此确立了不依赖他人的意志,根据自己的思考而行动的主体性。他主张:“不以人为对象,以天为对象。”[6]13因此,不管是面对藩主、将军,抑或是天皇名义下的明治政府,他都能够完全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自由地决定支持还是反对。岛津久光曾指责他说:“西乡智勇胜过世人,气量宏大且意志坚忍,乃当代豪杰也。虽然,于君臣之大义却甚为失节。服从彼人之壮士,对久光忘却君臣情谊,无礼之举不计其数……既不思数代蒙恩之旧主,其心不顺时则引弓以对朝廷,亦无足怪。”[7]33这实际上表明了西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传统的君臣观念的限制。
与对藩主“失节”、向天皇“引弓”的西乡相反,松阴终生未能超越对藩主或天皇的忠诚。他曾遭遇同藩武士的指责:“义卿(吉田松阴的字——引者注)尊攘,不顾君国。”便满腹委屈地自辩:“勤王诸策,虽过激矣,虽过愤矣,吾之心赤,一毫不负吾公。”[8]361松阴是通过强调自己的意志绝对符合藩主或者天皇的意志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他没有西乡那种叛逆的勇气,因为他没有西乡那种超越性的道德判断标准,无从建立个人的主体性。松阴的主体性被埋没于对藩主或天皇的忠诚之中。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两人对“道”的理解。西乡认为:“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也。然则,虽西洋决无差别”。[6]8与西乡所强调的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相反,松阴则认为日本有独特的“道”,所谓:“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之上,此乃一国之独也。”而欧美等国却“以土地远隔而风气不通之故,人伦之大道亦失其义”[9]272-273。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松阴之所以最终成为“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并非完全由于松阴像制作者的操作和虚构,在其思想之中原本便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所谓松阴像的体制化过程,正是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转变的起点是井上哲次郎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应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在中央幼年学校所作的演讲《谈谈武士道》。在这次演讲中,井上首次开始提倡复活武士道精神,而吉田松阴也初次被塑造成武士道的典型。
井上称德川时代(1603~1867年)著名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年)是“武士道的化身”[10]31。他认为鹿素行由于受到幕府文教政策的限制,不能自由地讲授自己的学问,因此,其门人尽是兵法(即兵学,指军事学)的门人。“但是经过多年以后,终于得到一个有力的门人。不是别人,正是吉田松阴……间接地继承了素行的学问系统的,是吉田松阴。”[10]24井上强调山鹿素行一度湮灭不彰,恰好突出了自己再度发现素行的创造性贡献。但如果素行的武士道无人继承,所谓的传统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正是井上在推出素行的同时,也必须重新推出松阴的理由。而且明治政府中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许多要员都出自吉田松阴门下,于是武士道传统或松阴精神便与近代日本的崛起顺理成章地建立了联系。
井上于1902年出版的《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在论述山鹿素行时,进一步展开了其关于武士道系谱的论述。井上写道:“素行武士道的精神在于《武教小学》,然而该书简约而不涉细目,故与吉田松阴的《武教讲录》并讲始得全。”[11]89但值得注意的是,吉田松阴本来是被井上收入《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的,而阳明学正是倡导古学的素行的抨击对象之一。井上如此不顾自己前后矛盾,为的是构建武士道的传承系谱。实际上,他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论述吉田松阴时根本没有提及武士道,在叙述其师承时强调的是佐久间象山。而在1901年的演讲中,他换了一种说法:“关于西洋的事情,是象山教的,但是松阴处身之精神,全自素行传来。”[10]33赋予松阴以在武士道发展系谱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显然是井上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出版之后才形成的观点。
井上此次演讲中所强调的松阴精神有两个要点。第一点是“死”的问题:“所谓武士,须时时刻刻准备好去死,素行有这样的教导……素行最令我们尊重的地方,在于死节这一点。松阴学之且实行之。”[10]33第二点是“决心”的问题:“武士道最可贵之处在于促发人之决心,使其下定决心,于其所为之处决无所惑,其本在此。”[10]40这两点与前述吉田松阴的“豪杰的生死观”、“决心之强固”恰好可以相互照应。
井上在演讲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不管怎样,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永远发展下去。如武士道者,即此物也。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10]41-42如此,吉田松阴附属于山鹿素行,开始向明治国家体制接近。据说乃木希典读了这次演讲的笔记,非常感动,带着吉田松阴的后人吉田库三拜访了井上[10]187-188。对乃木而言,可以说是由于井上的演讲而重新发现了适应时局需要的吉田松阴像。
在1908年的吉田松阴殁后50年纪念大会上,井上发表了“追颂演说”。到目前为止,井上关于吉田松阴武士道的议论总是附属于他关于山鹿素行武士道的论述,这一次却是以松阴为主题。因为是帝国教育会主办的纪念会,井上便以教育为中心论述松阴精神的这一特征:“松阴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的根基在于其强大的意志。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贯彻到底的真正的意志教育……松阴固然富于感情,但是松阴之强大之处在于意志。”[12]37关于松阴“至诚”与众多强调其动机的纯粹性的学者不同,井上认为这是松阴的意志的表现:“所谓至诚,即以此正确的目的为目的的意志,除此之外别无它物……一个人的意志如果积极地在人类社会中活动,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正确的目标,必然能够感化周围的人。”[12]39井上对松阴“意志”的强调,在内容上是延续了其当初所强调的松阴“决心之强固”。
井上在谈论松阴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素行。他从教育的角度再度确认了两人的传承关系:“松阴之学问自有其所由来之处。松阴之学问乃继承了山鹿素行之学问……在前有山鹿素行、在后有吉田松阴,此二,人实为德川时代意志教育之代表者也。”[12]40-41在这次演讲中,井上开始把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这一武士道的系谱作为独立的学派来把握:“山鹿素行的学问和吉田松阴的学问之间有着系统的关联,这一点不可忘记。其中蕴含着非常强大的精神,把德川时代发展起来的神儒佛以及其他精神,打成一片,形成了日本的学派。故且名之为武士道学派。”[12]46本来分别属于儒学中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的素行和松阴,在此被规定为一个时隔一个半世纪之久却保持了奇妙的继承关系的“日本的学派”。至此,从武士道论的角度把吉田松阴编入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体系的操作大致完成。到1942年5月井上哲次郎为自己监修的《武士道全书》写《武士道总论》时,又如此论述从素行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可称之为皇道的武士道或者神道的武士道,这是文献数量最多的。此亦理所当然,本来武士道就是‘神之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这在本质上是纯日本的东西。”[10]40-41武士道代表者松阴和尊皇主义者松阴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对井上哲次郎的松阴像的编制过程的追溯,与田中彰概论整体的研究相比,是试图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来展示,为了将松阴思想纳入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需要经过怎样的操作。那么,如果要抗拒这一倾向又会如何?可通过分析关根悦郎的名著《吉田松阴》来考察这一问题。
二、关根悦郎:“革命性解读”的尝试及其挫折
关根悦郎的《吉田松阴》一书刊行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内高压统治、对外疯狂侵略的年代。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关根是极少数能够保持学术良心的松阴形象塑造者之一。宫泽诚一曾以此书为据评论道:“的确,吉田松阴的思想中看不到体系性的思考,但和其他的很多志士不同,其中内含着进行那种‘革命’性解读的可能要素。”[13]田中彰也认为关根此书表明了在战争时期“冷静的松阴传的存在”[3]97。但田中也承认关根的尝试并不成功,并引用了远山茂树的评价:“的确是写了一部清新的传记,但是很遗憾,对幕末历史的整个政治过程的把握方法并不具体,结果依然被从前的松阴传所牵引,没有能够贯彻当初的意图。”[3]98但是,关根尝试对松阴进行“革命性解读”的失败,是否仅仅因为研究者自身认识上的不足呢?宫泽认为内在于松阴思想中的进行“‘革命’性解读的可能要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呢?
关根如此强调自己方法论上的独特之处:“对松阴处理方式多数都是将其塞入一定的模式。其做法是把历史人物视为脱离普通人的,脱离一般人的生活的,穿凿附会地塑造出伟人或英雄。”“我的《吉田松阴》是一个打破这种模式的尝试。”[14]2这一研究方法得到田中彰的高度评价。然而,把松阴作为“人”或“普通人”来研究,未必能够避免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田庄三郎的《作为人的吉田松阴》(启文社,1942年)也强调把松阴作为一个“人”来把握:“不是作为志士的松阴或者作为教育家的松阴,本书不如说是用松阴自身的话语编织出作为一个人的松阴的生活。”[15]1但实际上他是认为,过于把吉田松阴偶像化,远离国民大众,反而不利于学习松阴精神,因此,“再现作为国民大众的一员而生活的松阴,是现代史家的任务。”[15]22“松阴精神……必须是配给给一亿国民的生活思想的日常食物。不是在修身伦理的标本箱里落满灰尘的伟人化石,而是朝夕与共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之窗的‘卑贱但真诚’的同路人。”[15]29的确,这样的松阴像才最适合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总动员体制。
那么,关根所刻画的松阴像又有着怎样的特征?非常显著的一点是,关根的松阴传时刻都在有意识地把松阴描述成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然而其议论却时常给人以牵强之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根关于松阴的脱藩行为的评价。在德川时代,武士擅自离开本藩是被严厉禁止的,但是在幕末时期有许多志士为了推动尊王攘夷运动的发展而脱离本藩,四处联络。关根高度评价松阴是“青年志士脱藩之魁”,“在这一点上松阴也是先觉者。”[14]65但松阴脱藩的情形实际上非常特殊。嘉永四年(1851年),在江户游学的松阴与其他藩的武士相约同去日本东北地区游历,为此而向藩政府提交申请书并获得批准。但是由于行政手续上的问题,他未能在约定时间之前拿到通行文书。为了避免被人认为长州藩武士不能遵守诺言,松阴才逃离在江户的长州藩邸。游历归来之后,他主动向藩政府自首待罪。显然,松阴只是为了贯彻封建武士的道德而违背了相关法令而已,和倒幕维新志士的脱藩具有不同的性质。关根也承认松阴的这一行动“是从武士道这种封建道德出发的”,但他依然强调松阴的脱藩体现了“封建体制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14]78。如此,则松阴至多不过是无意中通过此举体现了封建体制的内在矛盾,但并未自觉地认识到此一行为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来谈论作为“先觉者”的松阴,实在难免牵强之感。
关根也谈到了松阴自觉地认识到了的东西,他曾引用松阴的《东北游日记》中有关佐渡金矿的记载,然后评论道:“被资本的魔术映入眼帘的松阴,很快就被其魔力所吸引,不得不修正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封建思想。”[14]69然而,关根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松阴对矿工艰苦作业的记述和慨叹而已,所谓:“其间经多少困苦,费多少财力,兼伤多少人命,呜呼,语之,亦可以寒视金如粪土者之胆。”[14]69仅凭这样的证据,来谈论松阴感受到“资本的魔力”以至于修正了“封建思想”,依然太过牵强。
关于松阴对政治现状的认识,关根曾引用嘉永六年(1853年)松阴给哥哥杉梅太郎的信件,然后评论道:“他通过这次的事件,看透了天下变革之势,实为卓见。而且其变革之势,与从来的单纯的政治变革不同,是更加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其敏锐的头脑中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14]97-98与此处的议论相关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关根就嘉永四年(1851年)松阴的东北游历而发的议论:“松阴所到之处都看到了封建制内部的崩坏、颓废的真实情况,但是从中却未能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洞见。他并未认识到那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在他看来,那是可以通过所谓藩政改革,从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14]74此后直到引用嘉永六年(1853年)松阴的书信,关根中间没有对松阴政治认识的变化做任何说明,而且,在关根所引用的松阴书信中,只能找到“将会有变革”[14]97的字眼,并没有具体谈到变革的内容。尽管如此,关根却直接推论松朋“感觉到了”“更加根本的社会性变革”的到来。
在松阴关于某些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中,例如松阴的农兵论(征用选拔农民用做士兵的主张),关根也从中看出了其先驱性。关根认为:“松阴谈到了封建制度崩溃过程中武士的无能。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农兵论,指示了近代兵制的方向……松阴是此思想的先驱。”[14]207但关根也承认:“农兵制度在建时代就有。”[14]206那么,为何松阴的农兵论“指示了近代兵制的方向”呢?关根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这或许是因为他持有松阴是思想先驱的既成观念,并未感到有必要再做进一步论证。
上述几个例子均属于松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表现,相应的关根的评论也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但在论述松阴临终前的思想状况时,关根终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松阴的思想是从封建意识形态出发,然后发展到了其反对物、否定者。”[14]263松阴在安政五、六年(1858年、1859年)间策划了几次不成功的暗杀等政治阴谋,均遭以周布政之助为代表的长州藩政府的阻碍和破坏。关根认为松阴的“眼中已经无暇考虑长州藩一藩的利害”,而周布却立足于“拥护长州藩的立场”[14]266。关根认为两人对立的根源在于:“松阴的思想和行动既然已经到达了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他一旦行动便会和旧社会秩序产生摩擦。”[14]266实际上,松阴至死都保持着对长州藩及藩主的强烈忠诚,甚至,如同关根所引用的,松阴对破坏其计划的周布政之助也颇有肯定之辞:“亦知周布之爱吾。亦知周布之为英杰。尤知周布之苦心。”[14]289在松阴看来,他自己和周布的对立仅仅是具体政治见解不同而已。
由于关根强烈地倾向于把松阴作为先觉者来强调,反而使其笔下的松阴像渐渐脱离了其时代。比如关根对松阴讨论狱政的《福堂策》评论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强烈的人的解放的精神……具有从封建制度的身份性阶级性限制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14]154实际上,松阴关于其动机说得非常清楚:“近时,洋贼跳梁,势将生事,当此时,勇毅敢死之士,最有用于国。今新下一令,曰:凡隐居之辈(指在狱之士——引者注),不可自暴自弃,一旦有事,可用为先锋。果能立功,秩禄可复其旧。若然,几百人敢死之士,立处可得,此亦可谓国家之一便计。”[16]166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有罪之人,固不可用于平时,然用之于兵战之场,可谓得其用。汉时,七科之谪,发而为兵,其意盖亦如斯。”[16]167松阴不过是出于国防上的目的而主张把平时无用的罪人用作战时的士兵而已。关根却从中读出了把人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但是松阴是否真的否定了封建身份制度呢?关根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投入松阴门下的沟三郎本是商家之子,对松阴说自己想放弃做商人而成为医生,松阴反对,理由是“人各有其身份。去身份而顾其他者,非所宜。”[14]178在此很容易看到松阴对封建身份观念的强烈拘泥。但是在关根的书中,这只是他为了说明松阴和门生之间的亲密感情而详细记述的松阴和沟三郎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实际上,关根最后甚至像其他迎合时局的武士道论者或松阴论者一样,开始以生的名义赞美死亡:“松阴对年少十八岁的和助(原文如此,应指野村和作——引者注)谈论死亡问题时的态度,极尽真挚,而又满溢着人情味。”[14]285关于松阴自身的死的意义,关根论道:“他计划通过死亡而实现理想的飞跃,通过死亡而指示出在封建社会克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道路。”[14]286无论关根的主观愿望如何,他所提供的松阴像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作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松阴像的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把吉田松阴塑造成符合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人物典型,与试图对其思想进行革命性的解释相比,前者相对容易,后者极为困难。然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或者研究者的方法等外在的因素,松阴思想自身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局限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笔者分析认为,井上所塑造的松阴形象并非完全虚构,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需要做出了适当的剪裁,将松阴思想的可能性的一个侧面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相反,当关根试图对松阴思想进行“革命性解读”时,却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行文中布满了牵强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在松阴思想中所内含的这一方面的可能性本身之稀薄。无论是井上还是关根,既然已经把吉田松阴选定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对象”的制约。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地暴露了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近代日本的意识形态政策之间的亲和性。
收稿日期:2008-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