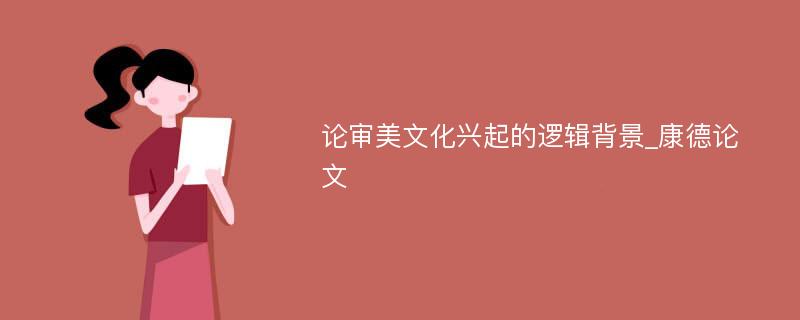
论审美文化学兴起的逻辑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逻辑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3
一
存在本是丰富而又单调的;思维也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的现实形态都是有条件的。只有两者同构互补,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思维和存在才能相互依托,生成它们自身。假如不承认这种同构互补原则的先验性,自明性,任意割裂其本源论层面上的同一性,那就会重演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理性闹剧。如否定人的创造性,把生命看作自然的奴隶;或者反过来将世界当作“我”的表象或任意役使的无机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一种恰到好处的关系结构,它契合或本就是宇宙的内在机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实践和精神探索,由此便可以看作是在两者之间寻求结合的“试错”行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可以把它纳入到这样的序列中来考察,这样做,对于摆脱理论思维的“现象”纠缠,并由此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将不无积极意义。
当然,承认存在的复杂性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态度问题,也不是象非理性主义者那样委身听命于自然,而是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具有“完形效应”的思维结构。以便更好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近代以来的理性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但我们绝难想象出一种能够摆脱理性而又有现实的可能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着要以逻辑的方式来做这种工作。工作的方式一旦明确,我们就不得不先回到康德那里,正是这位德国老人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理性最基本的存在结构和活动原则。我认为,康德哲学至少在两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第一:康德明确地区分了思维和存在的本体差异,物自体的不可知论,遂使一切现象界的经验、思维、真理等全都变成了人自身的事情。这同时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结构的彻底独立,以及拥有了新的研究对象的哲学自身的新生。第二,康德明确区分了主体的两种功能,即对经验界的“构建性”与作用于主体的“调节性”功能。〔1 〕前者可以把杂乱无章的“现象”用理性立法的方式统一起来;而后者只能对人的三种主体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尤其是后一概念的提出,指明了真、美、善之间的本体差异,它们不可能被统而为一,这也就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精神结构。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康德拈出的这个“三分结构”是如此的自明和朴素,它象毕达哥拉斯所追求的“天体音乐”那样无限和谐又无所不包。这是一个万能公式,它在理性和自然、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了一个巨型的交流机制。康德用它在人类最重要的三种心理功能“知—情—意”,以及“科学—美学—伦理学”这三门最重要的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性,籍此达到所谓的“为理性立法”。由康德所建立的理性活动的规则,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哲学家,并使很多人都沉迷于康德式的“三分法”,例如:雅可布逊在语言学上提出的“元音三角”和“辅音三角”;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上提出的“烹饪三角”;我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也研究过“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也提出过“文学认识的三角结构”等等。〔2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哲学家穆蒂莫·艾德勒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他从西方哲学史上选取了64个大观念,经过分门别类,最后发现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两组,即“据以进行判断的真、善、美”和“据以指导行动的自由、平等、正义”〔3〕, 此亦可见真善美在思维结构中的本原意义。此外,还有人的作法是把更多的“思维和存在”之内容安装进康德“先验”地制造的“三分结构”中,这种如简单的归纳法式的操作,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该结构的巨型与自足。如李泽厚,就把康德哲学中较少谈论、而当代人比较关注的语言问题等与之对接起来,形成了“真—描述语言—事实世界”——“美—感觉语言—心理世界”——“善—指令语言—价值世界”这样的新格局。〔4〕
二
一旦当真善美的存在被提升为一个稳定的逻辑结构,它们各自的存在就开始受控于该结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文明的精神结构,之所以限定以文明二字,是要同原始时代的文化结构相区别开来,因为在后者中真善美浑然一体,与文明的精神结构有着无法超越的本体论差异。所以说这个三分结构只对文明时代才有意义。虽然说经康德之手,真善美在文明的精神结构中终于获有了各自的本体论地盘,在理论上有了“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切莫忘记了它们毕竟是三种精神基因,代表着理性能力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显现途径,同时也是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是说它们之间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斗争关系。而人类对精神生活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的强烈需要,则要求它们在“现实化”过程中必须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出场。这也就是说,要以其中的一种理性能力或一种价值观念为主导,其余的为配角,唯此才能构成或表达出人类精神追求和时代步伐的一致性。
关于这个结构的机制原理方面,还应该郑重指出这样两点:其一是它的独断性质。因为它总是一元为主、三元并存,而且我们很难增加或减少这里的“三要素”。前面所讲的这个三元结构所具有的巨大的危害性和自足性就表明了这一点。这里顺便再指出一点,这三个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宇宙物理学家所说的、类似几何学原理所具有的“简单和美”,因此它最有可能揭示了存在的真相。〔5 〕而从相反的方面说,并非没有人试图改变这个结构,例如黑格尔就这样发展过康德,他首先打破了“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的界限,以理性的一元论取代了我们通常所谓的二元论(实际上应该称为三元论,此处暂存而不论)。把三元缩减为一元,并进而把康德哲学中不可知的“道德律令”变成伦理学的对象,把康德美学中“仅仅涉及事物的存在”、“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的“先验感性形式”〔6 〕转而变成有着明确的现实内容和功利目的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这种对三元结构的蛮横态度,虽然顺应了近代社会的需要,但毕竟严重背离了存在自身的规律。
所以有人说几乎20世纪的每一位重要的哲学家,都是以对黑格尔的攻击和发难而出道的。也不仅在思想界,胡塞尔就认为当代生活世界底部所发生的断裂和危机,也就是由于在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祸根、至黑格尔而登峰造极的一元化的理性主义的独断专行造成的。由此可以认为,黑格尔精神的受挫以及近来后现代主义者谈论颇多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与危机,都表明了理性独断论的此路不通。同理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了解到,以善为主导性因素的道德独断论在文明历程中的命运。〔7〕两种独断论是形态不同,但殊途同归, 结果都一样。
这就引出来我们想说的第二点,文明的精神结构不仅在现实中,由社会需要所操纵必然地显现为独断论结构,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地受到整体结构机制的制约。于是当一种独断论结构企图独占人类的精神世界,企图把文明精神结构的三元性完全异化为自己这一元时,它也就面临着颠覆自身的危险。例如:19世纪以来,在以理性独断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飞速发展过程中,当它试图完全从大地上驱逐走宗教、艺术等非理性的存在时,当它用行为科学来规范人的自由,用心理科学来为情感立法,直至要求美学走向科学。于是,在以“真”为中心的精神结构中,“善”、“美”就被异化为“真”的两种变体,两种用以对付“情感”与“意志”这生命中古老的非理性领域的工具。但这种理性扩张的结果,并没有使人获得理性主义所允诺的解放和自由。与此相反的是,由于丧失“情感”,人们变成了“物”;由于丧失“意志”,人则成了“机器”。这是人们更加难以容忍的。且不必说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种种抗议和慷慨陈辞;就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大本营内部,也传出来从理性独断论噩梦中的觉醒的有力声音。例如维特根斯坦就说:“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接触到”。〔8 〕因此他所要做的就不再是传统的用理性来为世界立法,相反却是要为理性立法,确定它的活动规则。这也就是现代哲学史上一再兴起的“回到康德”的大思潮中的一种时代强音。
三
当然也有人试图从根部摆脱这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三元结构,如海德格尔,他力图摆脱二元论的纠葛,以进入到主客未分、一元性的原始经验中去寻找尚未被对象化思维污染、割裂的存在本身,以对理性思维(对象化活动是其本质)的“虢夺”与彻底否定来达到人与世界源初的同一。此时的“真善美”三元素尚未在人类的原始精神结构中生成、独立出来,它们浑然一体,是一个东西,其中既没有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也没有多元的价值关系。所以康德的三分结构在此是无效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直观的“道”,也是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海德格尔则把它叫做“诗”。通过诗意沉思而沉入到人与世界的原始关系中,人也就返归了其本真存在。所谓人与世界的原始关系,也就是朴素的、无功利的、非价值的自然关系,也是从逻辑推论上所能设想的人类最初最原始的存在方式。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思路完全是针对着理性思维的本质而发的,人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拥有理性能力,它一方面表现为“反思”功能,籍此它可以把任何外物都当作自己的对象,通过对象化活动在外物身上实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理性中心论价值观的确立,虽然这种缺乏自明性的伦理学(人道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受到过许多古代智者的批评和抗议,如中国的老庄、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等。但是由于人类生存实践对理性中心论价值观的强烈渴望和无止境的社会需要,它还是被辉煌地建筑起来,并且最终成为人类生活世界中具有自明性的、无须检讨的公理。
海德格尔则紧紧抓住这条公理的可疑之处,重新阐释了他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他说:“对人的本质的一切最高度的人道主义的规定都还不知人的本真的尊严”。〔9〕因此,他声称自己反对这种人道主义, 因为它“把人的人道放得不够高”,它在鼓励人们“与物相刃相靡于是非”(用庄子《齐物论》语),把理性中心论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和人本身时,这也就把人本身变成了理性的工具,成为丧失掉“人的本质自由”的“物”。因此要真正捍卫人性的尊严,就必须彻底放弃全部由理性中心论而产生的价值关系,进而言之,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不是“物”的主体,同时也把“物”当作“物”而不是“人”的对象,这样“存在”才能如其所是或如其本质规定地“存在”(显现自身)。这也就是说只有废除一切社会关系,才能使个体获得其本质自由。因此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人与世界的原始关系乃是一种“无”的关系。一方面,“这个‘无’恰恰是被科学否认并且当作虚无的东西牺牲掉了”;另一方面,“只有以‘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为根据,人的存在才能接近并深入在者”,“亲在意味着:嵌入‘无’中的境界”,“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没有自由”。〔10〕从审美哲学的角度,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海德格尔哲学的深刻和力量,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审美乌托邦。这就决定了它永远都没有“现实化”的可能。试问:谁能够生活、“存在”于“无”之中呢?因此它的全部根据只能是人的想象力。它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倘若我们想要讨论人生的现实问题、文化问题,那恐怕还要回到康德的三分结构中去。由上述分析来看,把康德的三分结构拿来当作我们分析当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背景,应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
这个逻辑背景对我们很重要,真善美的三元结构关系是人类精神结构的现实的真实表达。在这个结构中去探索美学思潮的来胧去脉,比单独在美学范围内讨论它所得结论要客观和开阔得多,并且可以避免那种因“当局者迷”而造成的种种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又比较适中,它比动辄就站在所谓“宇宙论”或“终极意义”的高度又更实在一些,不那么丈二金刚叫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也不那么“高处不胜寒”。质言之,通由这个逻辑背景我们可以直接抵达到现实关系的深处,并且能够对各种现实关系作出最生动和真实的描述。
四
当然,人类精神结构的历史显现,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抛开了尘世存在的偶然关系的“自在自为的存在”,〔11〕它与现实生活有关,更确切地说其直接动力来自现实的需要。因此要正确地利用康德的三分结构,就必须把它的基础建立在马克思的社会需要理论上。关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在这里只着重强调这样两点:其一,需要总是现实的社会的需要,是人的消费活动“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2〕,从相反的或针对美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想象力或幻想所表达的抽象需要就不直接具备社会性,亦即不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所以恩格斯指出,托·摩尔虽早在300年之前就提出了“正义”的要求, 但它作为一种幻想至今仍没有实现〔13〕。这就为人类审美需要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作了最重要的限定,它不可能超出“社会需要”这个规定,那将是缺乏逻辑根据和无效的。其次,马克思多次讲到需要是不断变化的,满足需要的活动和过程中又将“引起新的需要”〔14〕,以及“满足新的需要方式”〔15〕。那么,这些环环相扣的需要之间遵从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都遵从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或“自然的必然性”〔16〕,精神生产自然也不例外。说它“自然”是因为它不是人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我们既不能任意制造它,也不能任意取消它;而说它“必然”是因为归根结底它是由——作为“劳动”的消费环节所产生的——“需要”决定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看作是文明的精神结构变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把精神结构自身的存在方式与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把理论思维同人的实际需要、利益联系起来,这也是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基本思路。〔17〕这也是解决各种精神的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历史上看,这个三元结构先后表现为这样两种现实形态。在文明时代的发轫期,由于原始时代礼乐制度的崩溃,对伦理秩序的需要便成为最强烈的社会需要,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最初的一批思想家(公元前6—前2世纪)大都是文明时代的批评家或不合作者,他们鄙视、“辱骂”文明的现实,高度一致地赞美和歌颂史前时代,把人类蛮荒时代的生活方式当作道德的顶峰。〔18〕对道德和秩序的强烈需求,遂使“善”占据了文明精神结构的首要位置,并使“真”和“美”都从属于它的统治。于是我们看到作为人类理性能力的“知性”不再追求知识和真理而是去转而探求“内心的善”,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的“大学”,它的对象即“德性之知”。同时文学艺术也都成为“载道”、“乐教”的。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与此相类,不过把知识的对象由世俗伦理置换为宗教道德而已。其结果或是把人异化成伦理工具,或是把人异化为神的手段,名号虽异但在人丧失其自由的存在这一紧要处则殊途同归。
正如我们前面讲三元结构原理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善”的独断论也必然要受到整体结构的制约,而且,“真”和“美”这两种理性能力也必然要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于是我们看到,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在中国则有五四运动,它们的旗帜上大写的是“科学”和“民主”,它们要摧毁的堡垒恰是曾一度有恃无恐的宗教神学和封建道德。但我们也不无悲哀地发现,在三分结构中,真正有力量的则是善与真,它们有强大的社会需要作后盾,所以这个现实世界主要是由这两者来操纵的。我们习惯于把知性所揭示出来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当作客观事物的真理;也习惯于把圣哲所揭示的关于生命活动的原则当作永恒的信念。总之它们都被当作某种必然性的表述。而人们对美的需要则远没有这般重要,这也就决定了它永远都只能是一种附属品。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悲剧性命运之所在。虽然为了自我麻痹也尽可能把它寄托希望于无限远的“从前”或“未来”。但从现实的角度看,美的命运就是在真与善之间永恒地摇摆,美就象神话中那双美丽的、充满魔力的红舞鞋,人类一旦招惹上,就会一刻不停地舞动下去。一会儿它扮演“真”的使者;一分儿它又沦为“善”的奴婢。这就是它的逻辑规定,是它自身所无法改变的命运。
尽管从康德开始就为“美”的自主性的建立而积极谋筹,其后的浪漫主义文化运动又试图把它变成人类生活的主旋律,直至提出所谓的“美拯救世界”。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情愿承认这样的事实,它的全部有效性都基于人类想象力这一文化功能之上,而作为人类情感活动的机制的想象力的欲求,远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无论马克思还是中国的儒家,都明确指出人类的基本需要就是食和色;或者说是物质生产于“种”的生产)。倘若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甚至在康德那里,美也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存在。一方面,“在所有人身上这种能力也总是很薄弱的”。〔19〕另一方面,“美在形式”与知识的内容无关(这表明了它与现实没有直接关系);“美是自由的象征”又与“自由界”的存在无关(在康德看来那是由纯粹的伦理原则构成的,这些原则就象人头顶的星辰一样不可改变,甚至人类的知识对它也是无效的,更何况是人类的情感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美的存在范围本就是很有限的,而且限制它的条件也比较多,所谓美的自主性是微茫又稀薄的。因此要研究美的现实问题,就必须把真善美三者结合起来作整体的考察,才能达到其真正的现实性。而我国近年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尤其当作如是观。
五
从逻辑的角度讲,当代审美文化的兴起,可以看作是“美”由“真”向“善”的摇摆和让渡。80年代的美学研究在本质上可以说与“知识”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一种“走向科学的美学”,其中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方法论“热”,当时的美学成果大都与各种新的自然科学方法或社会科学方法相关。美学家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建立一种关于心灵、情感、想象力、艺术的科学体系,由此达到对生命认识的真理性境界。并籍此来彻底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干扰和纠葛,完成对人生的非理性领域的统一大业,从而彻底在人间建立理性的王国。想法固然很好,但却并不“科学”。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三元结构时所指出的那样,“美”和“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这表明采用“知识”的方法来解决“情感”问题,在逻辑上就是行不通的。或者说这就会导致美学自身的异化,丧失自身。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尽管我们前些年的研究中在概念、方法上收获颇丰,但在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取得本质性进步。也许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认识到,有没有一个关于美学的外在的客观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平衡或协调人的身心矛盾,这就使美学逐步放弃了对知识、真理的执著,由此开始了对人自身的生活现状与可能性的探索。于是,思辨让渡于体验,知识中心论让位于生活本身,美学的优先性也让位于现实的第一性,学者所关心的各种抽象问题让位于大众所关心的具体人生话题。至此,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已呈在所不免之势。
当然,除了上述的逻辑背景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也颇值得我们重视。但因它们离本论题较远,所以这里只简单地提一提。首先,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迎合了中国学术界“美善不分”的传统,中国知识者本来就对“纯粹理性”既缺乏学养又缺乏兴趣,因此,他们从主观上就不想把它们划清界限。一种再纯粹的知识,假如它没有实用价值,要它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无论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还是时下极为热闹的后实践美学,都充满着浓厚的伦理学气息。他们所谈的核心问题都是人的生存问题。而我认为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美学问题,倒不如把它划入伦理学的范围更合适。但在我们这个“美善不分”的国度人们却见惯不惊。这种传统也使得人们很容易把美学同文化联系起来,尤其是当他们运用知识手段无法建立起一门有着自身的统一性的审美科学体系之时。因此,他们这样回转过来比整天站在思辨的云头更感到满足,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根。其次,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它还同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代的抬头有关。激进主义者追求的是“真理”,真理意味着“一”,因此这也必然意味着矛盾和斗争,他们认为唯此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保守主义者则根本不相信这种目的论,也惧怕在这种伟大的目的论之下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平静的生活。不是去努力追求一元化的真理,而是把如何认可多元的现实当作自己的课题;不是凝聚意志去改造这世界,而是要尽力想办法去认同此岸,风景这边独好。因此他们也更乐于改变审美与生活的对立,放弃美学的传统话题来降低自身的姿态,以求得与世俗的和解。如果说我们在前面所谈的主要是审美文化学兴起的逻辑背景,那么,这里所讲的就可以看作是它发生的现实机制。
收稿日期:1997-06-05
注释:
〔1〕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劳承万著:《审美的文化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第4—9页
〔3〕艾德勒著,郗庆华译:《六大观念》,三联书店1991 年版第18—20页
〔4〕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页
〔5〕周昌忠:《创造心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6 〕康德著, 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6页
〔7〕拙著:《文明精神结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2—43页
〔8〕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
〔9〕编译组译:《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2页
〔10〕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4—353页
〔1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 卷第121页
〔12〕〔1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94页,第208页,第四卷第94页
〔13〕〔14〕〔15〕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下卷第553页,上卷第718页,下卷第526页
〔17〕《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19〕康德著:编译组译:《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标签:康德论文; 文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三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