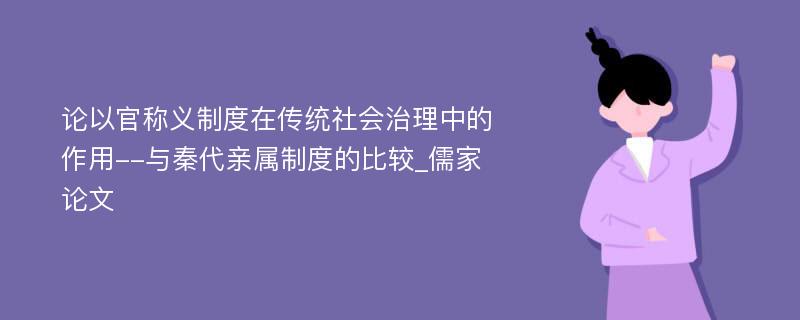
论干名犯义制度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兼与秦律亲属相告规定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名犯义论文,秦律论文,亲属论文,相告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1)04-0077-08
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制度,干名犯义指中国传统社会将亲属间相互告发犯罪,尤其是卑幼告发尊亲属、奴婢告发主人犯罪的行为入罪的规定。干名犯义的罪名本身显示了该罪浓厚的道德色彩:干名犯义,顾名思义,即为触犯名分、教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名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特定化为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伦理规范,法律儒家化使得触犯律法的大多数行为都“干名犯义”,反之,“干名犯义”的行为也往往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以“干名犯义”命名亲属相告的行为并进行惩戒,显示了统治者对于儒家“亲亲相隐”伦理道德的维护。干名犯义制度的演进历程也表明了这一价值选择。
干名犯义的罪名虽然首次出现于元朝①,但是其制度基础却在此前作为法律儒家化顶峰的《唐律疏义》中已经奠定。《唐律·斗讼》第45条“告祖父母父母”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即嫡、继、慈母杀其父,及所养者杀其本生,并听告”,疏义曰:“缘坐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故虽父母听捕告。”第46条“告期亲尊长”规定,“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所犯虽不合论,告之者犹坐。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即非相容隐,被告者论如律。若告谋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诉者听”;疏义曰:“‘其相侵犯’,谓期亲以下,缌麻以上,或侵夺财物,或殴打其身之类,得自理诉。”第47条“告缌麻卑幼”规定,“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诬告重者,期亲减所诬罪二等,大功减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论。即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第49条“部曲奴婢告主”规定,“诸部曲、奴隶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诬告重者,缌麻加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1]。不仅如此,《唐律》还将状告父母、祖父母、期亲尊长的行为列为“不孝”的表现之一,位列十恶,罪在不赦。《宋刑统》除了将“子孙违反教令”融入“告周(期)亲尊长”外,全面地继承了《唐律》的上述规定。明清两代律典则正式以“干名犯义”统摄《唐律·斗讼》第45、46、47、49条的规定②。在清末的法律改革中,干名犯义作为维护纲常名教的制度性规定,成为理法派和礼教派论战的焦点之一。1910年5月15日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依然保留了“干名犯义”的罪名,只是处理部分遵循《大清现行刑律》关于刑罚的称谓,如“……若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虽得实,处十等罚”。但是到了1911年1月25日颁行的《大清新刑律》中,除了第183条对于诬告尊亲属做了相应规定之外③,告祖父母、父母,告期亲尊长或者缌麻卑幼等规定均被删除,干名犯义随着整个法制精神的近代化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干名犯义制度的作用,黄静嘉先生曾以《读例存疑》中论及“干名犯义”条所引之条例仅有三则,且皆非属卑幼告尊长之情形,而推断“本条实际上适用之机会可能不多。是则本条之立法,以经义椽饰宣告及教化意义,抑大于实际之‘效用’”,并推断“礼教派”在礼法之争中未就此坚持并缠斗,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1]。对于干名犯义之“经义椽饰宣告及教化”作用,笔者深表赞同,但是是否仅凭流传下来的案例较少就断言干名犯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效不大,笔者心存疑问。近年来,学者们对于亲属相告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容隐原则本身[2],对干名犯义制度鲜有论及。因此,本文将采用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干名犯义与作为其制度基础的“亲亲相隐”理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干名犯义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且通过与秦律中亲属相告法律的比较,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探求在亲属相告问题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干名犯义与“亲亲相隐”
“亲属得相容隐,又准为首免罪,而告则干名犯义”[3],干名犯义制度与儒家“亲亲相隐”的理念密切相关。追溯“亲亲相隐”的渊源,多推至《论语·子路》的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父子相隐思想在两汉时期经过儒学的阐释与发展,内涵更为丰富,影响也逐渐扩展至政治和法律层面。至唐代,“亲亲相隐”原则被纳入《唐律·名例律》中,做“同居相为隐”条④,成为律法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并为后世的律法所继承。虽然学者们对于“相隐”的含义有所争论[4]:是消极地不告发、不指证还是积极地窝藏、泄露消息乃至帮助逃逸?但是告发则肯定是“不隐”,便是违背了礼法,破坏了人伦,也就是“干名犯义”。干名犯义与“亲亲相隐”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伦理上讲,二者都基于人性;制度上,干名犯义保证了亲亲相隐原则的实施,也赋予了亲亲相隐制度以明确的义务性特征。
首先,维护血缘亲情是人类的本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结构”中,一切法律与道德都要视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远近而加以伸缩,因此,与自己的关系越近,这种本性就体现得越强烈,甚至不惜与国家的权力对抗。“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⑤。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的这则诏书不仅宣告了容隐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也揭示了容隐所体现的人间至情。而约两千年之后的清代薛允升在谈及容隐时依然保有类似的观点:“若不许容隐,则恐有以伤其恩;若不许为首,则恐无以救其亲。首则欲其亲之免罪,本乎亲爱之意而出之也。告则欲其亲之正法,本乎贼害之意而出之也。故既着容隐为首之例,又严干名犯义之法,真天理人情之至也”[5]。允许亲亲相隐,甚至明令禁止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互相告发,回应了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道德诉求,这是“亲亲相隐”与干名犯义制度存续最深层次的基础。
其次,干名犯义是“亲亲相隐”的制度性保障。虽然唐代以降,“亲亲相隐”在律典中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得到了体现,但是从现代法理学的角度而言,“亲亲相隐”的规定本身并没有明确的义务性指向。以《唐律·名例律》“同居相为隐”为例进行分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即捎语消息亦不坐”,容隐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亦不坐”、“皆勿论”,国家不干涉容隐行为,换言之,国家赋予了部曲、奴婢对于主人犯罪的容隐权利。但是同一条文中的另外一句“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对于上述范围的亲属,法律仅仅是说“有罪相为隐”,至于法律后果是什么,条文没有明示,那么当事人究竟是可以“隐”还是必须“隐”?如果是前者,容隐就是权利;如果是后者,容隐就是义务。但是有了干名犯义之条,如果对自己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的罪行没有容隐而是告发,国家就会惩戒此人,此时“有罪相为隐”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强制性,容隐也就成为了一种义务。因此,除非所犯罪行不在容隐之限,同居亲属是没有不“相隐”的自由的。概言之,干名犯义是“亲亲相隐”的保障性规定,但这种保障并不是保护“容隐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而是确保当事人履行容隐的义务。
二、干名犯义与社会治理
干名犯义是“亲亲相隐”实现的制度性保障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干名犯义制度存在的唯一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治理中有着一系列的影响与作用。笔者拟从两个亲属相告的案例展开分析:
案例一:《元史》卷二十八《英宗二》载:驸马许纳之子速怯诉父谋反,母私从人。帝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命速诛之⑥。
案例二:《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师道传》载:种师道字彝叔,河南洛阳人,为熙州推官、权同谷县。县吏有田讼,弥二年不决。师道翻阅案牍,穷日力不竟,然所讼止母及兄而已。乃引吏诘之曰:“母、兄,法可讼乎?汝再期扰乡里足未?”吏叩头服罪[6]。
案例一中,速怯向皇帝告发其父谋反,却被皇帝以“人子事亲,有隐无犯”而诛杀,谋反这样的大罪也让位于了容隐原则,告发尊长的代价可谓大矣。但即使不如这个案例那么极端(依律条,谋反等大罪不在干名犯义之限),一般干名犯义案件违法的成本与受益也明显不成正比例:首先,告发一定范围内亲属的犯罪行为就要接受刑罚甚至付出生命;其次,告发人的告讦行为,将视为本犯的自首行为,这等于为其所告之人开脱罪名、减轻处罚创造了条件⑦;再次,干名犯义仅凭告发行为即可定罪,不需要调查取证审判等一系列繁琐程序,简单易断,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这样的成本收益比例之下,愿意甚或敢于以身试法的人应该不会太多。此外,介于干名犯义案件明了易断,其出现需要上报的疑难案件的概率较小,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该条罪名流传下来的案例较少⑧,同时,也说明了不能完全以流传下的案例较少来否定该律条的实效。
案例二同样也表明了干名犯义案件的简单易断,甚至因为干名犯义行为的存在而使得原告“叩头服罪”,原本争讼的事由失去了继续审判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县官的话,“母、兄,法可讼乎?”以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法律上你可以起诉你的母亲和兄弟吗?”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原因之一就是干名犯义罪的存在。因此,干名犯义罪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剥夺了个人告发亲属犯罪行为的权利。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这种剥夺对于社会治理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消除了卑幼主动借助于国家权力挑战尊长权威的可能性,促进乡规、族约、家法等非国家法适用在解决纠纷时的优先性。
自汉代以降,儒家教义被确立为社会正统的伦理行为和政治生活的准则。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家族内部男性家长享有至高的地位,享有祭祀权、经济权乃至对家族成员的教育惩戒处分权等权威,家族其他成员根据与男性家长的血缘以及婚姻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宗法等级,处于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行为准则,但处理家族内部的基本原则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君是国之家长,“君父”、“臣子”比照父为子纲就成为了“君为臣纲”,由此形成整个国家基本的治理格局。但是这样的格局并不是自然形成并一直会平稳地运行下去,需要礼法的规训与保障,这从反面就说明了卑幼并不都是总是愿意服从尊长,尤其是在尊长侵犯卑幼权益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卑幼告发尊长,卑幼很可能将本应容隐的事项诉诸于国家的正式司法程序,试图以国家的权力否定家族内部尊长的权威,这无异于动摇国家统治的根本。此时姑且不论相关事由诉诸官府的实体结果如何,单单是凭借所谓“干名犯义”之词而将尊长传证到堂,已经被清末礼教派重臣张之洞斥为“滥传滋累”,提升到“坏中国名教之防”、“悖圣贤修齐之教”的高度[7],逞论进行审理、将尊长入罪?所以历代无不将告发尊长,视为乱伦背教的大罪,正所谓“名者,名分之尊;义者,恩义之重。子于父母,孙于祖父母,妻妾于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名分恩义,最尊至重。纵有过恶,义当容隐。乃竟告发其罪,是灭绝伦理矣,故着为干名犯义之首”[8]。
但是禁止告发尊长,已经出现的纠纷或者在普通人之间有可能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干名犯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权衡的结果——在部分行为可能得不到或者更难以受到惩戒与动摇国家统治基础之间,选择了后者。如果出现了前一种情况,那么也是因孝屈法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尽量降低这种代价。首先,干名犯义范围之外的人依然可以告发;其次,某些严重危害国家乃至家族稳定的犯罪不在干名犯义之限,如谋反、谋叛、谋大逆,唐律规定的缘坐之罪(有造畜蛊毒、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等),明律规定的窝藏奸细罪等,《大明律》还规定“嫡母、继母、慈母、所生母,杀其父,若所养父母者杀其所生父母,及被期亲以下尊长侵夺财产,或殴伤其身,应自理诉者,并听告。不在干名犯义之限”等;再次,“尊长虽同,亲疏则异,故干犯之罪有差”[9],干名犯义本身也贯彻着宗法等级的原则,具体表现就是尊长告卑幼,处罚随着服制递减逐渐加重;卑幼告发尊长,处罚随着服制增加而加重。还以《唐律》为例:告祖父母、父母者是死罪,告发期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及丈夫之祖父母,即使罪行确凿,仍然判徒二年;但是对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即使是诬告,也不予追究。这种安排固然是贯彻宗法等级制度的结果,但也意味着宗法等级对于犯罪的处罚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差别对待,亲等越远,干名犯义的惩戒功能就越弱直至与普通人无异,这种差别对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于所谓犯罪行为的放纵。另一方面,干名犯义禁止卑幼向国家告发尊长,并不意味着相关纠纷或者行为不会被处理,相反正是为家法、乡规、族约等非官方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让渡了空间。在中国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既有国家正式的法律与司法程序,也包括家法、乡规、族约等非官方纠纷解决机制。在熟人社会中,这种非官方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事实调查和证据获取等方面可能比正式司法程序更为有效,也更有可能获得为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结果。国家也认可这种非官方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家长、族长对于家族其他成员的管理、教育和惩戒权力就包含了纠纷处理的职能,同时国家依然保有介入纠纷处理的可能性:他人的纠举或者官府的调查都有可能使得案件进入国家的正式司法程序;如果卑幼愿意承担干名犯义的后果,此类纠纷便很可能诉诸于国家的正式司法程序⑨。
三、与秦律中亲属相告规定的比较
此前的讨论,我们将干名犯义的制度渊源追溯至《唐律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干名犯义是一个体现儒家伦理道德的罪名,而《唐律疏义》作为法律儒家化的顶峰和封建立法的典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干名犯义的罪名,却是以后各代相关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考察亲属相告出发,那么早在秦律中就有相关规定。众所周知,秦朝与汉武帝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思想迥异,对比其在亲属相告问题上的不同制度选择,或许能深化我们对于干名犯义制度的理解。
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秦国以及秦朝法律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从中,我们看到了关于亲属间告发犯罪的这样一些规定:父母(主人)擅自对子女(奴婢)施以杀、伤、髡等刑罚,如果子女(奴婢)向官府告发父母(主人),那么就属于“非公室告”,官府将不予受理,如果坚持告发,则告发人获罪,而且告发人获罪之后,其他子女(奴婢)再行告发,官府依然不受理⑩。此外,家罪,待父亲死亡后再向官府告发,则官府不予受理。所谓“家罪”就是父亲杀伤人或者奴婢,以及同居的父子,子杀死或者伤害父亲的奴婢、财产,或者偷盗父亲的财产(11)。
可见,秦律对告发亲属犯罪方面是也有所限制。与干名犯义制度相比,秦律在禁告的主体、罪名乃至规定的详细程度上均有所差异。首先,禁止告发的主体范围较小,仅限于子女和奴婢。这与秦国以及后世秦代的家庭结构相关。在商鞅变法中有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10],这就打破了此前三代同居共财的家庭模式,逐渐形成了夫、妻加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模式,同居亲属的范围被大大缩小。此外,法律并没有否定妻子告发丈夫的权利,“‘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11],表明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不仅不会获罪,而且能够保全自己的陪嫁奴婢和财产。其次,禁止告发的罪名有限,即“非公室告”和“家罪”,这是只限于家庭内部的某些犯罪行为[12],超出了家庭范围,就属于“公室告”,任何人都可以告发,并且适用连坐原则。再次,在法律后果上,多是“勿听”,即使有所惩戒(“告者罪”),也并没有明确惩戒的刑罚种类、期限等。
在进一步解释差异的原因之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奉行法家思想治国方针的秦国为什么会有“非公室告”和“家罪”的规定呢?众所周知,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好利恶害,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与礼法,只能是善用赏罚以暴制暴,因此法家断然反对儒家的“亲亲相隐”思想。“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12)。在具体制度方面,奠定秦国以及后世秦朝法制基础的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度,鼓励告奸,“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13)。通过这些法律,秦朝尽量削弱与减少个体与所在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努力营造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以使得臣民个体直接面对繁密而严厉的国家法律而加强君权。这样的背景之下,“非公室告”和“家罪”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异类。
对此,有学者认为“非公室告”和“家罪”体现了儒家思想在秦律中的影响,也有将“家罪”认为是“父子相隐”思想的初步法律化[13]。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归类。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思想是面对大体相同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不同的、体系化的见解,不能仅凭某个具体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就将其归入儒家或者法家思想的范畴,应该做整体的分析。具体到“非公室告”和“家罪”的问题,它们确立和维护了家长(很多时候是父亲)在家庭内部的权威:父亲(母亲)对于家庭内部的子女、奴婢的财产、人身具有支配权,即使有侵害,受害人也不能告发(14)。但是“非公室告”和“家罪”对于亲属相告的限制是单向的,即只限制子女、奴婢告发家长,家长告发子女、奴婢没有限制,如告发子女不孝(15)。唯一例外的是同居的父子,如果子杀死或者伤害父亲的奴婢、财产或者偷盗父亲的财产,那么在父亲死后,子也不会受到官府的追究。注意,即使是这一例外,子不受追求的条件也是“父死”之后家人再告发——某种程度依然要依附于家长。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家长支配权强调的是对于权力的服从而不是道德。而这也符合法家反对儒家“孝”的立场:“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14],“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11],“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1],法家认为儒家所提倡的贤臣孝子正是国家祸乱、家庭破败的原因所在。此外,这种家长的支配权要受制于君权。如对于“非公室告”和“家罪”,特定成员之外的人是有告发义务的,否则就要被连坐。即使是父亲要杀、刑、髡其子女及奴婢,必须征得官府的同意[11],否则“擅杀子,黥为城旦舂”[11],“擅杀、刑、髡其后子,谳之”[11];对于子女的不孝行为,需要报官府而不能自行处置;夫对于妻没有明显支配权等等。诸多的限制使得君主能够控制家长,这符合法家加强君主权力的一贯主张,同时也进一步解释了秦律中关于亲属相告的规定与干名犯义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
四、“必须告”、“禁止告”还是“可以告”?——法律与道德关系维度的考察
“非公室告”与“家罪”和干名犯义都是处理家庭问题的法律规定。在人类历史上,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即“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15],家庭的存续与人类维护血缘亲情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社会形态的,它们会在社会中形成持久有力的道德诉求。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需要对于这种情感以及维护这种情感最基本的空间——家庭做出调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亲属相告问题上,法律与这种道德诉求之间体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
首先,法律无法长时间的背离、否定根植于人类本性的道德诉求,只有承认这一道德诉求,法律才能获得社会长久的肯定与支持。这正是学者们对于秦律的相关规定是否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争论根源。肯定者认为,虽然秦朝的法律严苛,“诸事皆有法式”,但正是因为法律回应道德诉求的必然性,秦依然为家庭内部秩序让渡了某种自治的空间,使感情得以维护;否定者则将这种让渡解读成加强君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家庭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人口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国家不能取消家庭,对于感情的维护只是这种制度设计的一种副产品。不可否认,对于基本道德诉求的背离(对绝对大多数的犯罪都是“必须告”)导致的严刑峻法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干名犯义则是确认、保障,更是利用了这一道德诉求,根植于传统社会的礼教民情,存续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直至清末民初。
其次,法律为朴素的道德情感划定了明确的行为界限,以刑罚的手段强化(抑或弱化)某种道德立场,但是其效果却并不一定符合法律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维护血缘亲情的道德诉求不可忽视,却并不是制度最后呈现样貌的唯一决定因素。因为法律还要权衡诸如秩序、公平、效率等不同的价值目标。为了加强君权与富国强兵,秦朝甚至可以否定这一道德诉求,在处理亲属相告问题上以连坐告奸(必须告)为一般的制度安排,以“非公示告”与“家罪”(禁止告)为例外;唐代以降,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稳定,设立干名犯义制度(禁止告),让发乎亲情的“亲亲相隐”成为往往以牺牲卑幼权益为代价的一种义务。此外,法律在处理涉及家庭的这样一种道德诉求时有某种天然的局限性,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显然国家需要在家庭自治与必要的社会控制之间保持平衡,并非易事。
再次,道德诉求的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法律回应的方式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农耕社会,人们附着于土地之上安土重迁,世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变化并不明显,孕育了父权制为主导的家族制度,人们维护血缘亲情的意识更为强烈,对不同身份间的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也更为重视和敏感,个人的权利要服膺于宗法秩序的稳定,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维护家庭和血缘亲情多采用令行禁止的方式,干名犯义即为表现之一(禁止告)。清末,传统社会在外来力量之下被迫开始转型,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日益增加,个人逐渐从家族中解放出来,其维护家庭和血缘亲情的道德要求更多地建立在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基础之上。因此,经过清末的礼法之争,维护血缘亲情的道德诉求以拒证特权和藏匿减免罪责的形式(可以告)表现出来,并且延续至民国时期的刑法和诉讼法之中。
余论
历史往往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复杂与精妙,我们对其当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长久存续的制度必定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是看它是否符合了某种理念,而是看它能否与其他制度相匹配,能否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治理的目标相适应。以这样的观念去考察干名犯义制度,我们才不会望文生义,仅仅认为它是一种儒家教义的宣示与点缀。
近年来,学者热议“亲亲相隐”,很大程度上是为将其重新引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张本[16]。笔者赞成顺乎人性维护亲情的立法初衷,但是笔者更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好相关的制度保障这种初衷的实现,正如干名犯义将宗法伦理加诸人情、推动“亲亲相隐”成为一种法律上强制义务,功夫往往在诗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仍处在转型过程中,新旧道德观念存在冲突,而且随着个人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萌发,道德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道德的多元化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法律又该如何回应?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确问题,这大概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2010-11-2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1年3月14日数字出版
注释:
①“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亲属相告,并同自首。诸妻讦夫恶,比同自首原免。凡夫有罪,非恶逆重事,妻得相容隐,而辄告讦其夫者,笞四十七。”参见《元史·卷一百五》。
②“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绞。若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虽得实,杖一百;大功,杖九十;小功,杖八十;缌麻,杖七十。其被告期亲、大功尊长及外祖父母,若妻之父母,并同自首免罪。小功、缌麻尊长,得减本罪三等。若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三等。其告谋反大逆、谋叛、窝藏奸细,及嫡母、继母、慈母、所生母,杀其父,若所养父母者杀其所生父母,及被期亲以下尊长侵夺财产,或殴伤其身,应自理诉者,并听告。不在干名犯义之限。若告卑幼得实,期亲、大功及女婿,亦同自首免罪。小功、缌麻亦得减本罪三等。诬告者,期亲,减所诬罪三等;大功,减二等;小功、缌麻,减一等。若诬告妻及妻诬告妾,亦减所诬罪三等。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佣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诬告者,不减。其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若奴婢以及佣工人者,各勿论。若女婿与妻父母,果有义绝之状,许相告言,各依常人论。”参见怀效峰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大清律例》“干名犯义”律条基本承袭了《大明律》的规定。
③第183条规定:“意图尊亲属受刑事处分、惩戒处分,而为虚伪之告诉、告发、报告者。处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相比较第182条规定“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惩戒处分而为虚伪之告诉、告发、报告者,处二至四等有期徒刑。犯前项之罪,未至确定审判或惩戒而自由者,得免除刑罚”,可以将第183条视为是继承了此前《大清律例》对于诬告行为的规定,只是由于存在尊亲属关系而加重处理,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告发亲属犯罪。参见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印:《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辑),1985年2月版。
④“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泄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引自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注:《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66、467页。
⑤参见《汉书·宣帝记》。
⑥同注释⑤,第65页。
⑦如“(凡)犯罪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自首法(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期,虽捕告,俱同自首例)”,参见《唐律疏义》卷5《名例律》“犯罪未发自首条”);“……其被告期亲、大功尊长及外祖父母,若妻之父母,并同自首免罪。小功、缌麻尊长,得减本罪三等。……若告卑幼得实,期亲、大功及女婿,亦同自首免罪。小功、缌麻亦得减本罪三等。”参见《大明律》“干名犯义条”等。
⑧在清代祝庆祺等所编的《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中,“干名犯义”项下的案例共有37件,其中34件涉嫌诬告,纯粹的干名犯义案件只有两件。所谓纯粹即是因为行使诉权而犯罪,而诬告在历代刑律中都是严惩的犯罪,卑幼诬告尊长虽然在干名犯义中有规定,但是也可以视为因涉伦常而在常人诬告的基础上加重处理,因而笔者认为卑幼诬告尊长不是完全能够体现干名犯义中因行使诉权而获罪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虽然1911年《大清新刑律》中有诬告尊亲属加重处罚的规定,但是笔者依然认为干名犯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⑨如“妻父悔婚另嫁舅婿互相捏告”案([清]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3页)中,身为女婿的钟世芳程控岳父将女儿悔婚另嫁得实,告岳父串通差役计骗等“均事出有因”,后将钟世芳“照申诉不实杖一百”,其岳父“依许嫁女已报婚书,再许他人已成婚律杖八十,酌加枷号一个月”。
⑩即“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编年记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7页。
(11)即“家人之论,父时家罪殴(也),父死而捕(甫)告之,勿听。可(何)谓‘家罪’?‘家罪’者,父杀伤人及奴妾,父死告之,勿治。”,“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同注释⑨,第118、119页。
(12)参见《商君书·禁使》。
(13)同注释(11),第2230页。
(14)除了上述“非公室告”之外,秦律中还有“‘父盗子,不为盗。’令殴(假)父盗殴(假)子,可(何)论”,同注释⑨,第98页。
(15)如“告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往执。令史已爰书:舆劳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无)它坐罪’”,同注释⑨,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