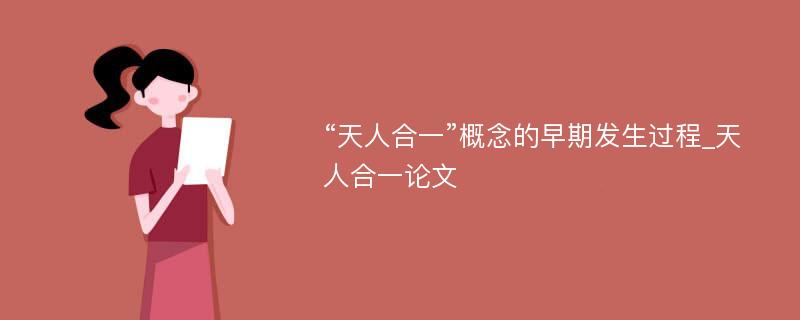
“天人合一”观早期发生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历程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 (2000)05—0078—06
在宇宙的有机系统里,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天和人的关系问题,而他们处理天人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便是“天人合一”。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一书中曾经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论及中国文化时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 今之学者也多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线。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不仅把“天人合一”作为他们基本的宇宙观念,而且将“天人合一”作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理想。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的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2](P6)因此,不了解“天人合一”观, 就不可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精神,深入研究和阐发“天人合一”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目前学界多侧重于对其思想意蕴的探讨及其与西方“主客二分”的比较,而对其发展历程尤其是早期发生历程则少有论及。本文拟对天人合一观的早期发生历程进行初步的探讨和梳理,以期更好地把握“天人合一”思想。
一
要梳理并把握天人合一观,首先必须了解“天”的涵义。“天人合一”之“天”,涵义丰富而复杂,不同的场合各有所指,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天神、自然和天道。“天神”是指有人格意志的主宰意义的天;“自然”是指客观存在的大自然;“天道”是指自然的运行规律。“天”的涵义,大体可以春秋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春秋以前主要指“天神”,春秋以后主要指“自然”或“天道”。相应地,天人合一观也可以春秋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春秋以前属于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春秋以后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
据《国语·楚语下》记载,公元前500年, 楚昭王读到《尚书·周书·吕刑》中“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时,产生疑问,便向大臣观射父询问:“《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的回答是,所谓天地之通并不是指人真的能登天,而是指地上的人类借助于有德能的巫觋与天上的神灵之间的交往。这段记载反映的历史事实是,在原始宗教阶段,神权集体共有,全体氏族成员都有与神灵发生关系的平等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在巫师的帮助下与神灵交往。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贫富的分化,财富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家族和个人,于是普遍求神祈福,并且发展到“夫人(即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程度。这样一来,开始享有特权的氏族贵族不能容忍这种现状,而是要求天上的神灵也与地上的统治关系相适应,于是上帝神的观念也就逐步形成,享有特权的贵族便要求垄断与上帝相通的权利。所以颛顼实行“绝地天通”,表面上要回复到人神不杂的阶段,恢复神灵的威严,实质上不过是垄断天地神人之间的交往手段、垄断神权而已。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在颛顼以前的远古时代,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天地相通、神人杂糅的,人人可以通天,人人可以与神交往。正如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所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3](P13)可以说,“神人交通”,就是中华天人合一观的原始形态。
关于神人交通,我们还可以从神的形象和通天之人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从神话传说和古籍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崇拜活动中所创造的神灵形象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神灵同人的关系是亲和的,先秦典籍谓之“神人以和”(《尚书·舜典》)。“神人以和”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祖先神系列的创造上。首先,这些神灵多具人性善行,多是人类的造福者。伏羲结绳制网,以田猎捕鱼;女娲抟黄土而造人,炼石以补天;神农发明五谷,教人耕稼;黄帝则为人文始祖,兴事创业,神通广大。其次,这些神灵形象独特,多半人半兽,或为人面兽身,或为兽面人身。伏羲“人首蛇身”,女娲“人面蛇身”,神农“人身牛首”,黄帝“日角龙颜”。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是人类自身形象与所崇拜的自然物形象的直接拼版。再次,这些神灵之间也具有着和人类相似的社会血缘关系。据传,伏羲与女娲为兄妹,神农与黄帝为兄弟。除祖先神与人同性亲和以外,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众神也多是和人类具有亲密和谐的关系。如关于太阳的神话,后羿射日,终于获得一日中天、朗朗乾坤、不寒不暑的天人即神人亲和的境界。再如雷神,雷神本狰狞恐怖,意味着天人之际不可掩盖的原始对立状态,然而中华先民却不愿与之发生生死冲突以导致悲剧,而是在雷震之时,焚供献祭于雷神,最终也是以欢乐而告终。在这里,盲目的天与人的原始对立被消解为神与人之间的亲和悦乐的境界,依然一定程度上寄寓着中华先民与这些神灵的交通求和。
我们不仅可以从神人以和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从通天之人看出远古时代的天地神人之间的交通。在“绝地天通”的故事中已经涉及到“巫”的问题,那么巫师是否真的具有通天的功能呢?“绝地天通”的重、黎二人,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属于“昔之传天数者”十四人之列。他们既能将天地通道断绝,则本身必为能通天者。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他们也确是能够上天下地,与日月星辰运行联系在一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同被列入“昔之传天数者”之列的还有一人名为“巫咸”。他是何许人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山海经·海外西经》又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所谓“灵山”之类的各种高山,神话学家袁珂认为都是“天梯”,即上古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天地通道,这完全正确。古人认为山高而为通天的捷径,在古代许多神话传说和古籍中都记载有各种可以上天下地的神山。群巫就在此种神奇的通道上升降上下。注意上述“十巫”之首正是巫咸,因此可以视巫咸为上古时代的巫的象征或代表。据此,通天亦即通神。关于中国上古时代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性质及意义,张光直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4](P4)
总之,在颛顼以前的远古时代,的确是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觋的帮助而与天神交通。但是,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奴隶制度的确立,那些由氏族贵族蜕化而来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开始垄断神权,垄断通天通神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权垄断的同时,王权逐步形成并不断加强,于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提出了所谓天命神权论,宣扬他们的权利是由上帝赋予的,他们自身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称为“下帝”或“王帝”,具有“天之元子”的神性,从而独占了“步于上帝”(《尚书大传》)、“格于皇天”(《尚书·周书·君奭》)的特权。因此,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有能力与上帝、神、天相通。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5](P33)“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的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4](P107)这样一来, 占有通天通神的的手段也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只有占有通天手段的地上君王才能与天交通往来,中华天人合一观便由原始的“神人交通”而过渡到了“天王合一”。所谓“天王合一”,就是天上的上帝神与地上的君王的交通合一。《论语·泰伯》所云“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反映的就是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实际上是说,只有尧是中介,沟通天人。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也曾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十分敏锐、十分准确地意识到了古代“天王合一”的思想观念。
“天王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很长时期,从传说中“绝地天通”的颛顼、帝尧时代,经历夏代、商代,直至西周初年。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初年“天王合一”观念仍相当流行。《尚书》云:“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又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大雅》云:“天监在下,寿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云:“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这些记载都是说明周王是如何承受天命,配享上帝,受民受疆土,为王为后的。当时的人们相信,除周王外,人们不能同天攀亲,只有周王才是天所生,周王是天之子,于是周王之称天子。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天把最高权力赋予了周王。因此,也只有周王才能与天相配,与天相通,沟通天人。
“天王合一”,是天命神权、王权至上思想的根据,其实质是把王权神化。这种思想在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仍然绵延了很长时期,关于天子的神话不断出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王朝承天意以从事”,“王者天之所从也”。在这里君王仍然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对天来讲,王代表人类与天对话,承上启下;对民来讲,王是他们的总领和最高指挥。所以,天下人都要服从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可见,董仲舒此处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心仍然是“天王合一”,要论证的核心仍然是王权主义。宋代程颐所云“君道即天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也是所谓王权主义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西周初年天王合一的思想仍然相当流行,只是说在西周初年“天王合一”是天人关系中的主导思想,而不是说西周初年以后这种思想就成为绝响。同时,也不是说在西周初年就只有天王合一的思想。在西周初年,天王合一的思想在统治集团内部就已开始动摇,他们吸取殷王朝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观念。这种对天命有所怀疑,以民心向背来衡量天命,以主观作为来巩固王权的思想,为以后天人关系问题的探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化,人们心目中的“天”的观念也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诗经》中出现了大量怨天骂天的带有哲理性的诗篇。这些怨天尤人的诗篇既否定了天神上帝的神圣地位,也否定了人间君王的神秘权威,从而也就否定了奴隶主统治者所苦心构造的天命神权思想。这样一来,以神化王权为实质的“天王合一”观念在天人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便逐渐为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所取代。
二
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到春秋时期,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又出现了一股无神论的思潮,对天命神权思想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冲击波。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仅对天神的权威产生怀疑,而且把关注的目光从天(神)转向人(民)。春秋初年,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命题。随后,史嚣发展了季梁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国将兴,听于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言。”(《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嚣把重民还是重神看成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把“听于神”与国亡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神的权威的极大的贬抑,强调神意要以民意为转移,是对人的作用的进一步重视。季梁、史嚣的重民轻神思想,比《诗经》中怨天骂天的思想前进了一步,诗人们虽然痛骂上帝神灵的昏暗不明,但人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而季梁、史嚣却从民神关系的角度来贬低神的作用,在理论上是对有神论的一个批判。由于他们还承认神的存在,所以还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无神论者,但已经动摇了天命神权论的统治地位,对后来无神论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春秋晚年,郑国政治家子产正式提出了“天道”和“人道”这样一对哲学范畴,把天道、人道已经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子产同时还承认天道与人道有一定的联系:“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无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这里潜藏着“人道”应当遵循“天道”的思想。总之,子产既摆脱了天命神权观念中的神秘宗教色彩,又注意到了天人之间存在着客观统一性的内容。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看,子产虽然提出了“天道”与“人道”这对哲学范畴,也初步认识到二者之间既相分又统一的关系,但他的思想还不能算是真正达到了哲学自觉的水准,因为他毕竟没有对这对范畴作出明确的哲学诠释。
真正从哲学的意义上对天道作出明确诠释,并对天道与人道关系作出精辟论述的当属春秋末年的道家始祖老子和越国著名军事家范蠡。范蠡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他一再强调:“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可以成功。”“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国语·越语》)从范蠡对“天道”的涵义以及对天道与人道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天人关系思想已基本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但是,仍然缺乏一定的理论性和深刻性,因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并用于指导战争,多局限在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事物上,概括性不高,并且也缺乏对天命、天神观念的批判。
在中国哲学思想里第一个彻底推倒天命观并提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的思想家应当算是老子。老子提出最高哲学范畴“道”来说明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问题,用“道”来代替传统人格神的“天”,无情地剥夺了天神上帝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资格和权威,使天神上帝失去了往日的神秘和光彩。他认为,天不过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已,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并不是天神创造万物,而只有道才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的始基,道“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只注章号),“先天地生”,“为天地母”(第二十五章);天神并不具有至上性,只有道才具有至上性,道是“象帝之先”(第四章)的,即使天帝真的存在,也是道的晚生后辈,“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第六十章),应当用道来治理天下而不能靠鬼神,鬼神起不了作用。老子又强调,道的作用虽然大,却不具有意志性、目的性和主宰性,它是无私、无争、无求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因此,道与所谓天神有着原则的区别。道不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神,道的作用是让万物自然而无为。道是自然总体的概念,是表述天地万物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的概念,同时道本身就是无限宇宙的不断的生化运动,整个自然界有秩序、有条理、有规律的变化,就是“道之动”的变化。老子的这些论述表明,他扬弃了原始天命观而建立了哲学天道观。
老子的道不仅包括为他所着重论述的天之道,也包括未被他忽视的人之道,因此他在论述道的同时,也论述了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他从天道出发,由天道而人道,由自然而社会,言天必归结到人事,讲人事必本之于天。在老子那里,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既相分离又相统一的二元和合体。他的主要天人观点是:人是自然的产物,从属于“道”的法则,故人道应效法天道,人道以天道为依归;人应效法自然(道),人事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谁能顺任自然而不妄为,谁就能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只有人道效法天道,社会秩序效法自然秩序,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天下大和的理想,达到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真正合一。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也就是说,人要取法天道,自然无为。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七十七章),可见,老子论天人之道的最终目的在于要求人们依据自然规律来改变不合理的违背天道的人道社会,从而实现一个合乎天道的理想社会。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老子的天人思想已经属于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换句话说,中华哲学天人合一观到了老子这里已基本形成。
春秋末年,在哲学天人合一观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的除了老子外,还有儒家创始人孔子。如果说道家的老子是从天道观的正面推倒了原始天命观的权威,从而奠定了哲学天人合一观涵义的宇宙论基础的话,那么可以说儒家的孔子是从人道观的侧面突破了原始天命观的限制,从而奠定了哲学天人合一观涵义的人生论基调。正是由于老子和孔子的合力作用,哲学天人合一观才得以最终战胜神学的天人合一观并在春秋末年正式形成。
孔子的天人观矛盾而复杂,他一方面奠天信命,认为天命具有神秘的主宰力量;另一方面又疑神主仁强调人事和人的主观努力。但总的来说,他的思想中重视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没有从天神那里寻求人道,而是从人自身中寻求人道,从而把人从天神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他虽然承认有意志的“天”和无可抗拒的“命”的存在,但经常离“天”而讲“命”,把“天命”这个哲学概念分开来使用。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基于社会变革和实践经验,孔子开始对“天”的权威丧失信心,天的权威地位在他的心目中已经逐步动摇,因而他把“天”与“命”分开,更多地谈“命”,试图以“命”来补充和取代“天”。而“命”毕竟多少带有客观必然趋势的意味,其神秘性没有天神那么浓厚。其二,他虽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对鬼神采取或回避或怀疑的态度,和敬鬼祭神相比,更重视人事人生。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以下只注《论语》篇名),“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所谓“所重:民、食、丧、祭”(《尧曰》)。其三,他在尊天的同时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享天命以尽人事为准衡。《论语·尧曰》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赞同尧的意见的,即一方面承认尧认让给舜是上天的大命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又要舜好好地把握正道尽人事,否则就会造成天下百姓贫困,那么地位也就完结了。在这里,孔子肯定享有天命是以能否尽力于人事作为衡量标准的。这样,天命的神秘性、天的意志权威也就相对地减弱了,而人事的地位则相对地提高了。《论语·卫录公》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是孔子强调人事作用的明证。其四,他在信命的同时更重视人的主观努力,提出了“仁”学思想。从天人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中蕴含了人的主观自觉精神。何为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就是约束自己,这是内在的心性道德要求;“复礼”就是符合礼制,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复礼”的境界只有通过“克己”的途径才能达到,实践外在礼制只有化作内心欲求才能做到,定义的重心在“克己”。也就是说,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内在的心性修养。孔子在这个定义之后紧接着说“为仁由己”,进一步指出要做一个仁者,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的主观努力。《述而》篇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也是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主观自觉精神在理想追求中的重要作用。由上述四点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确是非常重视人事,重视事在人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正是这种思想在客观上相对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从而使得孔子的天人观能够从人道的侧面突破原始天命神权观的束缚,把人道观、人生观从传统的天人学说中凸显出来。
从孔子的言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重视人道,凸显人生的思想,而且还可以发掘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他的天人合一观同样包孕于其“仁”学思想中。通观《论语》可知,孔子所谓“仁”的涵义主要有二:一是“爱人”,一是“克己复礼”(《颜渊》)。而如何实现“爱人”原则呢?其途径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所谓“忠恕”,就是推己及人,即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样由基于人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相亲相爱的孝悌之情(孔子认为这是人的本质所在,即《学而》篇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出发,通过“忠恕”之道,推及他人,推及社会,推及天地万物,最终达到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内在和谐:“天下归仁”(《颜渊》),万物和合于爱,宇宙之间充满爱。这一过程的完满实现就是“仁”,故程颐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朱熹说:“惟仁然后能与天地万物一体。”(《朱子语类》卷六)可见,孔子所向往的“仁”的境界乃是一个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泯除了人我区别和物我对立,而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这是由“仁者爱人”导出的“天人合一”。而“克己复礼”和“爱人”又是统一的,在孔子看来,不论自己所希望达到的或者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不能离开礼的约束,也就是说,“仁爱”必须符合“克己复礼”的原则。作为外在规范程序的礼,本质上是为了对个体的自由欲望进行必要的节制和约束,以解决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间的各种矛盾,使社会的各种机制和不同个体能够和谐地运转。简要地说,循礼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克己复礼”的境界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一言以蔽之,孔子所追求的“仁”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另外,孔子倡导“知天命”、“知天”,认为只有知天命,才能成为君子,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认为只有“知天”、“则天”才能够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人就“则天”而行。此处之“天命”和“天”,已不能简单归结为宗教神学所谓的上帝的命令和有意志的天,而是具有自然界客观必然性的意味,具有“天道”的意味,孔子是把它作为人事的指导原则。孔子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人事和天道、人性和自然具有统一性,其中也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总而言之,到了老子和孔子这里,哲学天人合一观已正式形成。老子和孔子之后的历代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尽管立场不同、流派各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继续不断地在探讨着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趋向有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不大注意天人双方的对立方面,而特别注意双方的统一方面,他们都承认自然和人、天性和人性、天道和人道是相联相通,和合统一的;他们都认为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办事,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几乎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只不过各家各派在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的具体途径上看法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家儒家和道家就各有所侧重。儒家主张向善求仁,侧重尽人道,泛爱生生,完善人的社会本性;道家主张归真法天,侧重合天道,去私寡欲,完善人的自然本性。但二者又是互补贯通、殊途同归的,都落脚于重视人生,完善本性,珍爱自然,最终达到天人和谐周流的审美境界。正是由于各家各派持续不断地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由老子和孔子所奠基的天人合一思想加以继承、发挥、丰富和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产生至广、至深、至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4—10,修订日期:200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