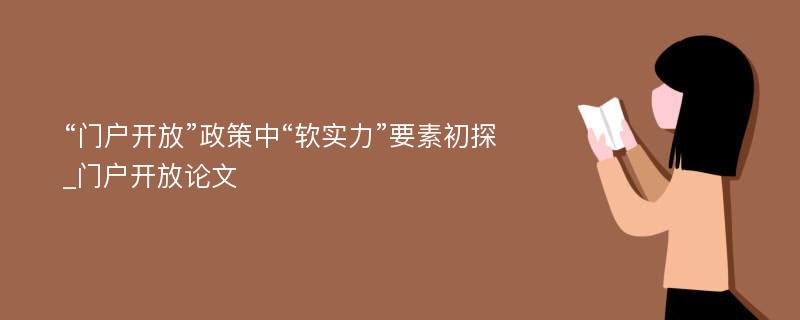
“门户开放”政策“软权力”要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权力论文,政策论文,门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5-0170-09
自1990年美国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提出“软权力”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跨学科、多层面、宽视域的探讨,以至于“软权力”成了当今全球化世界的热门话题。其实,如果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奈的“软权力”理论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早在他提出这个理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国际政治舞台,并且曾长时间地在国际关系包括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过隐性作用,1899年美国在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为一个例证。本文拟根据奈的“软权力”理论,论述这一政策在当时所蕴涵的“软权力”要素,并对这些要素的构成做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在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1899年美国在华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堪称中美学者争议最大的“古老”课题。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这项政策所蕴涵的意义及发挥的作用,而且在于这项政策持续运作所映现的多重属性。
中国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在内涵层面不断深化,在外延层面和实施范围亦不断拓展。20世纪前半期,有学者认为该政策是对中国的“无形之瓜分”,“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1]461。也有学者认为该政策“以超然第三者之地位,谋世界公共之平和”,“实救出中国于瓜分场中”[2]。20世纪后半期,有学者认为该政策“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3]。进入21世纪后,又有学者认为“门户开放不仅是针对中国的应急举措,而且是旨在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帝国的世界性‘大政策’”,其“核心是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体系……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具有无边界外延和开放内涵的新型模式的殖民体系”[4]211。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人们对这项政策的认识程度随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入思考的思想轨迹。
美国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关注,主要立足于中美关系、远东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三个研究视角。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借用了英国“‘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其主要原则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它“起初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在许多场合以政策声明的形式表达于双边条约;华盛顿会议后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但由于美国在30年代奉行无所作为的“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主义”,这项政策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5]304-306丹涅特(Tyler Dennett)从远东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东方的政策:“美国同东方各个民族,同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分别发展,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同亚洲的关系是同样的久远……这个政策并不止限于用在中国。它曾经在1832年宣布于非洲沿海,在1899年以前曾经多次重申于日本和朝鲜。”并指出:“海约翰的特殊贡献,并不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发明……而是外交技术的运用,竟能在实际上既不求诸武力、也不求诸同盟,就使门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6]1、545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和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则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强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远东扩张的传统政策:“在美国政府同远东的全部关系,无论是同中国、日本或朝鲜的关系中,它在十九世纪的目标是开放通商的门户,并务使门户保持开放。”[7]420
中美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既有研究结论,涉及“门户开放”政策的诸多层面。诸如:政策蕴涵的动机、性质与目标,政策实施的途径、方法与范围,政策发挥的作用、功能与效果等。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动机、性质、目标和作用等方面,美国学者除此之外还关注“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途径、方法与范围,并对政策发挥的功能与效果有所触及,但中美学者均未对“门户开放”政策原则的持续性和现实性做深入研究,原因在于人们对这项政策所蕴涵的权力要素、尤其是“软权力”要素缺乏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国际政治学诞生以来,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运用“权力”概念研究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所崇尚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亦译为均势)理论,亦随之被运用于“门户开放”政策研究。其后,中美学者都有从均势角度分析“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例如,中国即有学者认为:“列强在中国的实力均衡和力图维持这种均势为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8]美国学者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亦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成功……有赖于远东局势的完全平衡,如果有一个国家破坏了这个平衡,这个政策就不能够维持了。”[9]1390年代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问世,则为中美学者深入研究“门户开放”政策原则的持续性和现实性提供了更宽阔的理论平台。
约瑟夫·奈起初对“软权力”的定义是:“以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机制——影响别国倾向的能力。”[10]十多年后,他又将“软权力”补充定义为“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拉拢(co-opt),而不是强制他人去做”的能力。[11]5中国学者将他的理论归纳为:(1)“软权力”通过吸引和拉拢,而不是强制或劝说发挥作用。行为国家可以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本身的投射性,使被行为国家产生学习和效仿的愿望,从而实现行为国家的战略目的;(2)“软权力”反映了行为国家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3)“软权力”具有认同性,这种认同可以是对价值和体制的认同,也可以是对国际体系判断的认同。认同性权力有助于一个国家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12]
至此,我们似乎可将“软权力”的基本要素初步归纳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投射性,倡导和建立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以及对价值和体制的认同性。仔细分析“门户开放”政策出台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软权力”的基本要素在这项政策的内涵、外延和实施范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这项政策特殊性反映的内在渊源。
“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与早期实施,主要是顺势利用列强竞相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所形成的交错牵制因素,通过强调国际法的条约权利和主体要素,引导列强在远东达成美国所希望的国际共识。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次年胁迫中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随后侵占旅顺口、大连湾,迫使中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使整个东北三省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在牵制俄德的幌子下,与中国缔约租借威海卫,在渤海湾上形成与俄国对峙;法国亦通过对华照会换文租借广州湾,巩固了在两广、云南三省的地位;英国又以“补偿”为由与中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华南与法国形成对峙;日本则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租让别国,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在竞相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列强还进一步争夺对华贷款和铁路投资权,从而形成其侵略权益向他国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渗透扩张的交错牵制局面。由此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市场利益,而且可能引起列强间严重的利益冲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9月6日指示美国驻法、德、英、俄大使①,令其向驻在国政府提出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三项原则:“第一,在任何可能在华取得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域内,决不妨碍任何根据条约开放的口岸或任何既得权利。第二,对全部所谓‘势力范围’内的这些口岸(自由港除外),中国现行的协定关税适用于所有卸、发货商品,无论其所属国籍,并且那些可征收的关税应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对在这些‘范围’内任何口岸出入的其他国籍船舶所征收的港口费,不高于本国船舶应被征收的港口费;并且不对经由这些‘范围’内建造、控制或经营的铁路所运输的属于他国公民或臣民的货物,征收高于其本国国民同类货物、相等运输距离的运费。”[13]129、129、131、140-141这些原则分别从国际法的角度强调了一项权利、一个机会和一个主体。
首先是强调了鸦片战争后各国在华获得的既有条约权利。照会提出既有条约权利不得因列强在华取得“势力范围”或租借地而被局部中止,应该在这些“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继续保持有效;其次是强调了各国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均沾中国开放新的市场利益的均等机会——该条款以中英《虎门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为滥觞,前者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后者规定:“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14]36、51照会要求列强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按照非歧视的国民待遇原则征收港口费和铁路运费,借以强调各国在中国的这项均等机会;再次是强调了与各国缔结条约的中国政府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照会提议“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除自由港外的条约口岸,所有进出口商品仍按中国现行协定关税纳税,并由中国政府征收,以此强调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主权仍属于中国。当时在华拥有“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英国也持类似主张。海约翰在致美国驻英大使乔特(Joseph H.Choate)的通函中即提到,英国政府为保持中国市场的开放,“急于促使在北京的列强协商行动,支持迫切需要的行政改革,以加强帝国政府并维持涉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的完整”[13]132。这就构成了利于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呼应条件。
由于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回避了列强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对铁路与采矿的专有特权等敏感问题,美国政府得到了列强不同程度的承诺。俄国强调,“关税问题的决定是中国本身的事”,否认对此有“为其本国臣民要求任何排斥其他外国人的特权的意思”[13]141,但避而不谈航运费和铁路运费。德国声明,“不但从一开始就主张,而且实际上在它的中国租借地内对于贸易、航运和商业还最彻底地实行各国绝对平等的待遇”;并称“德国对远东的政策在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的政策”[13]131。法国声称,“希望享有中国全境内各国公民和臣民的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关税、航运费,以及铁路运输费方面”[13]128-129。英国表示赞同美国的政策,但将新近在九龙拓展的土地排除在外。这四国都绝口不提为本国人民在其“势力范围”内谋求开发铁路和矿山资源的专有特权。而日本和意大利则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以同样方式通告列强:它们就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外贸问题对美国提议的接受,被认为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13]142。这就在达成国际共识的基础上,宣告了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原则正式成立,其最初涉及的外延是商业贸易,适用范围专指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
但成立伊始的“门户开放”原则能否实际生效,取决于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列强的赞同与接受;二是中国领土行政的完整和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后者迅即在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冲击下濒临危境。
随着1900年6月20日八国联军宣布准备进京护侨,海约翰于7月3日要求美国驻各国使节向驻在国政府通告:“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在当前情况允许这样做的条件下,应该表明美国的态度。我们坚持1857年所开始的与中国保持和平、促进合法商业,以及根据国际法在治外法权的条约权利下尽一切办法保证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的政策。如果对我国公民发生不法行为,我们决心使肇事者承担最大限度责任。我们将北京的情况视为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里的权力和职责实际上转移到了省级地方当局。只要他们不公然与叛乱者合谋,并运用其权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们即把他们视为中国人民的代表,设法与他们保持和平与友谊。总统的打算是,正如迄今为止所做的,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打通与北京的通讯并解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其他处于危险中的美国人;第二,对在华各地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尽可能的保护;第三,防卫和保护一切合法的美国利益;第四,帮助防止混乱蔓延到帝国的其他省份,并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当然,现在预测达到这一最终结果的方法是太早,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它会给中国带来长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保护根据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给予友邦的一切权利,并为世界保卫与中华帝国全境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15]299这份通函一般被视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也有学者称之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扩大。[7]449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对中国政府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的重申与补充,其内涵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问题。照会明确表示,“1857年所开始的与中国保持和平、促进合法商业,以及根据国际法在治外法权的条约权利下尽一切办法保证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的政策”,是迄至那时为止美国所奉行、并欲继续坚持的对华政策。它将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和正在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了区分。所谓“1857年所开始”的政策,系指由当时的美国公使列威廉(William B.Reed)在1858年6月18日与中国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所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内容是:两国“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第1款);美国在华享受全面最惠国待遇原则(第30款)。[14]80-90、95“门户开放”政策则是保持美国在华享受的最惠国待遇不受损害的政策,基本内容是:美国如何处理与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之间的关系。丹涅特称海约翰1899年的照会是“以蒲安臣的国际协定办法为师承恢复了合作政策”[6]2,而1900年的第二次照会,一定程度上则是美国为保持对华政策而履行《天津条约》第1款义务——“从中善为调处”中外“不公轻藐之事”(只是未“照知”中国政府而已)。
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定性问题。照会认定中国当时只是北京局部呈无政府状态,各省地方当局仍在履行职责,各国并未因此处于对华战争状态;表示美国政府除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解救公使和传教士之外,还要帮助防止混乱蔓延和灾难的再次发生,目的“是要防止宣战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军事行动”,因为“对中国作战就难免要牵涉到领土的永久占领或割让”[6]555。
第三是设法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问题。照会要“寻求一个解决方案”,通过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以保障各国在华享受的条约权利。实际上强调中国领土的完整和行政实体的存在,是中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保障各国在华条约权利的基础。它正反映了丹涅特所述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传统:“美国不但要求门户开放,而且还企求亚洲各国的发展能强大到足以作为它们自己的守门人的程度。”[6]2
第四是贸易“机会均等”原则所适用的地域范围问题。鉴于列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超出其“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照会重申“为世界保卫与中华帝国全境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即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防止列强乘机进一步割占领土,扩大其“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其二是通过强调“机会均等”原则适用于中国全境,顺势淡化、否认列强既有“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专有特权与利益。
基于照会发布的敏感时机和列强在华军事行动的牵制因素,同时照会的口吻亦并非征求列强意见而是通告美国政府的态度,列强当时对此均不便公然提出反对意见,只能相继表示赞同。“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为世界保卫与中华帝国全境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即由此使“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范围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租借地,明确地扩展到中国的全境,而照会所宣称“寻求”的“解决方案”,则具有明显的“倡导和建立国际制度安排”的意思。
由于“门户开放”政策出台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际,并且在20世纪上半期率先运用于中国大陆,中国学者自然认为这是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的侵华政策。但是,如果从经济全球化的宏观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这项政策似不难发现,“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内涵——“机会均等”原则,具有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意义。它既缘起于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以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权学说为渊源;又发轫于西方世界的市场规则,以欧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实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为原型。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权学说,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思想基础,也是美国社会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源头。其集大成之作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表述的天赋人权观:“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与生俱来地被其创造者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其中之一。”[16]A3《独立宣言》首度将欧洲启蒙思想家主张的自由观、平等观和社会契约观归结为人的天赋权利,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建国后,天赋人权观又具体落实为1787年《联邦宪法》规定的限权政府原则,以及美国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个人权利平等观。限权政府原则分别体现于分权制衡的联邦政体和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其中第9条规定:“宪法所列举的确定权利,不应被解释为可以否认或轻视人民保留的其余权利。”[16]A18由此确定了政府权力不得超越宪法和人民天赋权利的施政原则。个人权利平等观被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解释为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就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具有的权利。每一种公民权利都以个人原有的天赋权利为基础,但要享受这种权利光靠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所以他把这种权利存入社会的公股中……并使社会的权利处于优先地位,在他的权利之上。……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资本。”[17]142-143政府则受托负责管理社会权利公股,通过法律和政治程序向股东提供存取资本的“均等机会”。
在美国联邦制社会政体的构建过程中,开国先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论及并倡导过“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各行各业都有不囿于职业的局限抱负坚定的人,他们会因其成就博得不仅来自所属行业的称赞,而且会得到整个社会的称赞。门户应该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18]他所推崇的“门户开放”社会机制不但鼓励各行各业的公民平等竞争、从而使美国社会持续充满活力,而且吸引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渴望自由的移民投奔北美,进而使“美国梦”的魅力经久不衰。英国学者波尔(J.R.Pole)据此认为,汉密尔顿的“这个论断把他置于美国个体主义传统的主流中”[19]140,其内在含义应归类为美国社会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之一——平等。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Patterson)指出:“平等是美国人的另外一个政治理想——这一概念意指所有个人在道义上是平等的,有权受到平等的法律对待。”[20]7法律的宗旨则是保持社会的公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等人进而阐明:“我们美国的传统促使我们认为,公正就是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的均等机会。机会的均等是由公平的法律和政治程序,即以同等方式应用于每一个人的法律和政治程序来保障的。”[21]36从美国历史的渊源来看,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所倡导的“机会均等”原则,恰恰是美国社会文化主流价值观在19世纪末海外扩张过程中的自然反映。
“机会均等”的美国社会机制和主流文化价值观,鼓励不同境遇的社会成员个人奋斗、公平竞争,这是美国在短短两个多世纪内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内在社会动因之一。但“机会均等”只强调竞争的前提和过程,其优胜劣汰的结果又必然会侵害“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原则。这个矛盾集中爆发于工业化完成后的美国社会经济领域,并在当时政府的对外政策选择中得到反映。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美国新兴托拉斯垄断财团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公司、工业巨头、金融财团对中小企业的打压、兼并,破坏了崇尚“机会均等”的传统文化,由此激发了中产阶级领导的经济上反托拉斯、社会上要求新自由的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要求在工业化时代保持平等公正、自由竞争的传统价值观,恢复“机会均等”的社会发展机制,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公众反对在扩张中占有领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从美国外交的政治层面分析,19世纪90年代末出台的“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一项保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阻止列强——尤其是俄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竞相侵犯中国主权的外交努力”[22]728,也是美国政府兼顾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舆论的政策选择。
欧洲国家基于资本主义市场规则,并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实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机会均等”原则由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演变为对外扩张准则,进而逐步吸引列强在帝国主义扩张中达成共识的国际杠杆。所谓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T)是“对已准予的最惠国(MFN)提供同等贸易机会(即关税特许权)的保证。是一种通过使原来的双边协议多边化,在各国之间建立起贸易机会均等的方法。早在17世纪初,试图使贸易机会均等的保证就被作为商务条约的一部分”[23]1300。1641年,荷兰与葡萄牙签订互惠商约,第一次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1654年英国与瑞典签订的条约也规定了最惠国条款。18世纪后,最惠国待遇已经成为欧洲国际贸易、航运优惠的普遍性条款。1778年2月6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率北美使团乘萨拉托加大捷(Saratoga Victory)的有利形势,与法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前者规定两国和平友好,凡双方不拟给予另一方的共同优惠,都不得答应给予其他国家;美法两国在相关区域的贸易、航海和商业税收上,各自赋予对方最惠国待遇。[24]469后者规定“防御联盟主要的和直接的目的,是有效地维护合众国不仅在商务上,而且在政治上的自由、主权和绝对的、无限制的独立”[24]480。美法《同盟条约》奠定了法国介入对英战争、帮助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而美法《友好通商条约》则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肯定了两国的主权平等,其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遂成为美国与欧洲各国贸易交往的起点。
在工业化开始之前,美国经济以商业贸易为基础,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是运用互惠性最惠国待遇条款开辟海外市场;工业化开始之后,美国一方面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仍然运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均沾”国际市场的利益,但在条款的具体运用上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对欧洲国家,美国采用的是从有条件到无条件的平等互惠性最惠国待遇条款。美法《友好通商条约》规定的是有条件互惠性最惠国待遇条款,随后美国亦与英、荷、瑞典、普鲁士签订了类似条款。1850年,美国与瑞士签订的通商条约,首开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先例;②1898年,美法签订特殊互惠条约,瑞士援引1850年商约要求均沾,美国不得不表示同意。其他缔约国也援引此例签约均沾优惠,从而打破了美国运用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惯例。对亚洲国家,美国则采用附有侵犯主权内容的互惠性最惠国待遇条款。1831年,美国与土耳其缔约规定了互惠性最惠国待遇条款,但在条约的英文本上规定,在土耳其境内的美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25]1401844年,美国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一体均沾”了中英《南京条约》的各项特权,享有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美国兵船在中国五口巡查贸易不受中方管辖,以及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民房、土地居住,建教堂、医院等特权;1854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规定美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政府若将此次对于美国未曾准许之事给予其他外国时,当亦对美国予以相同之准许。遇有上述情形时,无须另行谈判,亦不得拖延推诿。”[26]4361858年,美日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更规定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1882年,美国又与朝鲜签订类似条约,取得相同特权。正是借助于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美国与欧洲国家共同打开了亚洲主要国家市场的门户,并使其持续保持开放。
进入帝国主义扩张阶段后,美国为保持在华既有的条约权益,遂向竞相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列强重申最惠国待遇的“机会均等”原则,推行具有普世性的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门户开放”政策。“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其“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27]195,长远目标就是要广泛确立国际条约体系下的贸易开放规则,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的空间。该政策的内涵初步宣示了美国输出“机会均等”社会价值观的理想主义愿景,该政策的外延与实施范围则凸显了美国在华重申“利益均沾”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现实主义需要。
从1899年9月到1900年7月,美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形势,连发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基本阐明了这项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保持各国在华商贸权益的“机会均等”;以及这项政策所适用的范围——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到领土和行政实体保持完整的中国全境。由此与同期在华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的列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堪称美国在远东扩张的特殊政策,其中蕴涵的“软权力”要素值得关注。
首先,“门户开放”政策是以开拓市场为圭臬的新殖民扩张模式与占有领土为目标的旧扩张殖民模式兼容并存的海外扩张战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受第二次工业革命驱动,大国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导致瓜分世界的狂潮。这一进程受两种扩张观念支配:一种是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后重商主义时代的移殖型殖民扩张观念,以攫取土地、实行排他性独占统治为目标,殖民地被视为宗主国垄断下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一种是19世纪中期兴起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开放型商业扩张观念,以保持市场开放、实行机会均等下的自由贸易为圭臬,反对分割领土、损害主权的殖民化“势力范围”破坏市场的完整开放。这两种观念前者被称为旧殖民主义,或“老帝国主义”[28]253;后者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或“自由贸易帝国主义”[29]170。当时正在进行扩张的欧洲列强,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帝国主义大国都在奉行以占有土地为目标的旧殖民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按照实力重新瓜分世界,进而导致欧洲后来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直至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由。只有英美两国开始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步奉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理念。英国早在18世纪70年代即提出了分工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理论,19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全面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甚至为打开西班牙垄断的拉美市场提出过反对封闭型殖民体系的主张。[4]183-184但英国本身是旧殖民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缘由与程度,完全取决于其“世界工场”的地位和竞争优势。英国虽曾向美国倡议联合在华提出“门户开放”原则,却并不愿改变对既有殖民地领土的占有和直接统治,它在中国也与俄、德、法竞相展开争夺,并且将长江流域划为“势力范围”。这种既要维护旧殖民体系的既得权益,又欲谋求新殖民主义开放利益的骑墙投机态度,注定了英国不能令人信服地向在华竞相划分“势力范围”的列强倡导“门户开放”原则。
美国独立后也在北美大陆不断兼并领土、展拓国界,但自19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起,国内就有人倾向于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标的新殖民主义扩张模式。美西战争后,美国社会各界一度围绕菲律宾的占领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共和党政府力主按旧殖民扩张模式直接统治菲律宾,反对派人士则从维护民主、自决原则和传统的立场出发,反对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制度,但不反对将其建成商业基地。随着1899年2月参议院批准《巴黎和约》,美国开始奉行立足于菲律宾群岛开拓远东市场的海外扩张战略。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表达了这一扩张战略的新思路:“随着我们对菲律宾群岛的占有,是美国政治家所不能漠视的商业机会。运用一切合法手段扩大美国贸易是正当的,但我们并不在东方追求特殊优势。我们只为自己要求门户开放,我们亦准备将门户开放给予别人。与这个新的开放自然而又不可避免有关的商业机会,与其说有赖于大规模的领土占有,不如说有赖于一个恰当的商业基础和广泛而均等的权利。”[30]90丹涅特认为,麦金莱的表述将“门户开放”一词在对华政策和对菲律宾政策之间建立起了联系。[6]526笔者认为,这恰恰表明了“门户开放”原则兼容开拓市场与占有领土新旧两种扩张模式的特点,海约翰后来对在华列强发布的“门户开放”照会,正是贯彻麦金莱总统海外扩张战略新思路的第一步。“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否认、但并不阻止或谋求取缔列强兼并领土的旧殖民扩张模式,而是通过重申“机会均等”、“保全领土与行政实体”原则强化内涵,在与列强旧扩张殖民模式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渐次达到保持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中国全境的门户开放,然后向世界各地推进,直至最终达到建立全球市场门户开放机制的目的。
其次,针对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列强而出台的“门户开放”政策,既没有凭借军事实力作后盾,也没有诉诸武力去实施的意愿,是一种非实力型的“柔性”外交政策,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实体起实际保护作用。1898年12月,美国打赢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后,虽在地缘上通过占有菲律宾取得了踏上中国的跳板,但与竞相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欧洲列强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严重不足。打败西班牙只是一场“小而辉煌的战争”,美军人数不过10多万,且大部分用于镇压菲律宾人的起义与反抗,抽不出足够的兵力与在华列强抗衡:当时俄国拥有常备军约75万,法国约60万,德国约50万,而“19世纪90年代末期,大不列颠驻守亚洲的战舰比麦金莱所有的一流战舰还要多”[31]415。美国如欲凭借军事实力迫使列强开放其在华既有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只能“劳而无功地和全体列强相对峙”[6]545。因此,海约翰采取了发布同文照会与列强沟通、寻求达成扩张共识的方式,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在当时即具有与众不同的“柔性”特征。这种与强制力分离的“柔性”,正是列强不同程度赞成、接受美国倡导“门户开放”原则的楔入点:它既为列强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遵循“门户开放”原则提供了自由,也为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实施“门户开放”原则保留了余地。所以,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仅限于以发表声明、与相关国家签署协定的方式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从未试图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原则”[32]7-8。“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需要军事上的强制力,而美国政府实施该政策的“柔性”又规定其仅限于外交努力,结果只能如美国学者所述:“与门户开放政策一样悠久,而且在实践上更加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另一条美国的长期的政策是,美国不会为中国而战。”[32]7-8
再次,“门户开放”政策是基于欧美国家对“机会均等”原则的长期国际认同,依托最惠国待遇条款所赋予各国的在华条约权利,着眼于未来构建国际制度的前瞻性外交政策。以欧洲重商主义和启蒙运动为经济、文化渊源的“机会均等”原则,不但是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打开中国市场门户的核心原则,而且是19世纪90年代末列强竞相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之前保持中国市场门户开放的条约依据。列强对这一原则的国际认同,既体现在要求清政府“一视同仁”地准予其进入中国市场,并通过相互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竞相要求清政府给予更大的开放优惠;又体现在列强之间彼此尊重各自在中国的既有条约权利,不得借向中国索取新的权益破坏各国在华既有利益所达成的国际合作。这种对“机会均等”原则的国际认同,曾由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在19世纪60年代向英、法、俄驻华公使倡导的“合作政策”达成默契:“吾人均承认合作乃必须者,盖由于最惠国条款之故,没有一国能以锐敏之外交行动单独自中国攫取任何独享之特权故也。”[33]304-305但这种建立在美、英、法、俄驻华公使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合作,未能形成明确、稳定的国际制度。虽然丹涅特认为海约翰的政策是师承蒲安臣恢复了与列强的合作,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海约翰的政策是着眼于未来构建国际制度。第一次照会要求:“中国现行的协定关税适用于所有卸、发货商品,无论其所属国籍,并且那些可征收的关税应由中国政府征收”,是在强调给予各国在华既得条约权利的国际法主体;第二次照会宣布:“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保护根据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给予友邦的一切权利,并为世界保卫与中华帝国全境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是在表达从国际法的角度使列强的国际共识制度化的意图。两次照会的立足点是列强长期对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的国际认同,既有平台是最惠国待遇条款所赋予各国的条约权利,最终目标则是要从国际法的角度使这种国际认同上升为国际制度。
总而言之,“门户开放”政策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表达了美国欲均沾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权益的意图,而且该政策诉求的外延与范围亦不乏美国在华倡建国际商贸开放制度的要素。“门户开放”原则的内涵更蕴涵着美国在帝国主义扩张初期传播其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投射性,列强在华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国际认同性,则是这项政策在当时能够顺利推出的国际环境。这项政策既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也没有诉诸武力去实施的意愿,其最初的有限作用主要取决于政策所能调集的各种“软权力”要素。至于这些要素在“门户开放”政策推行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笔者将另行撰文予以分析。
注释:
①给日本和意大利照会的时间分别是同年11月13日和17日。
②条约第8款规定:“对于双方产品之进出口及运送事宜,美利坚合众国与瑞士联邦必须互惠对待,一如对待最惠国、联邦或州。”(Encyclopedia Americana,Vol.7,p.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