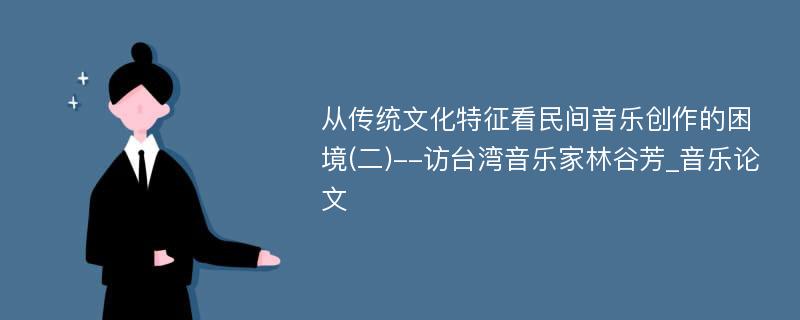
从传统文化的特质看民乐创作之困境(下)——访台湾音乐家林谷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民乐论文,音乐家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于:这就是我想请您谈的第二个问题,即乐队编制问题。前几年贺绿汀先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文章,对大乐队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提倡发展广东音乐、江南丝竹等地方乐种形式的中小型民乐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因为目前国内的民族乐团基本上都是大型管弦乐团的编制。前不久,陈澄雄先生来京时,我也请他就此发表过意见。最近,我们《人民音乐》准备开展这一讨论。
林:我可能是海峡两岸发表反对大乐队意见最多的人,可能也是很遭人讨厌的。因为这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生活问题,即饭碗的问题。
于:陈澄雄先生对此也深有同感,他在理论上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实际上却感到很难行得通。
林:陈澄雄起初也是主张搞大乐队的,他总感到国乐队奏不好,是没有好的训练所致。后来他看了日本音乐集团的演出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认为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中国能不能成立大乐队?我看先不要下一个历史性的断言:一定不能。但是要不要花那么大的精力?这里有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首先大乐队所面临的我们刚才谈的那些问题比小乐队要多得多。即使将来要成立大乐队,也首先要解决小乐队。其次,在美学上,大并不一定比小好。第三,小乐队容易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当然我们不要否定大乐队,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大乐队,只不过我们并不很知道它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小乐队是大乐队的基础,否则大乐队只是一种横向移植,是照搬西方乐队的结果。
我们不要预先划定一个乐队编制,这不符合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西方要呈现形式美学、纯粹结构美学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达到这一旨意的方式。而我们中国是辩证的思维,是现象性的,是随物应性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就要采取什么样的编制。台北国乐团成立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之所以成立80人的国乐团,是为了要有更多排列组合的可能性,而不是要成立一个唯一的80人的乐队。是为了要让作曲家随意运用,是为了使音乐更丰富多采,而不是为了使每一首作品都要80人的编制。这种单一的思维方式是经不住辩证分析的。这种在大乐队问题上的迷失,确确实实导致了许多中国音乐特质的同质化。有些很有特色的乐曲,一进入这样的乐队里,特色就没有了。比如有的流行歌,旋律还是很美的,可是总不能打动人,为什么?首先因为那个爵士鼓,千篇一律的节奏,把感人的深沉都综合掉了。大乐队的作用也类似这样。大乐队并不一定不好,但投资这样大,收益如何?而且很容易出现“大就是美”的迷失,这对我们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负面作用的。
于:大乐队的出现,与作曲家要表现具有深刻哲理性、时代精神等重大题材的需要有关。像《长城随想》这样的题材,显然用中小型乐队是不能胜任的。看来还是大中小乐队并存比较好。您认为呢?
林:大中小并存是绝对的。我们并不是要二选一,而是侧重点在哪里?目前的阶段性在哪里?另外,某些在大陆受到好评的作品,在海外的评价并不高。有的作品受到好评,是因为满足了这里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海外注重的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有个人生命色彩的升华在作品里得到了怎样的体现。有的建筑可以当成民族文化的象征,但你去到那里,并不一定想写出那样的作品,因为你可能想到的是众多生命的丧失。
有的作品大而无当,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大不一定就不好。但大有大的坏处,北京这么大,交通很不方便,恐龙很大,行动很迟钝。大并非比小更进步。大有大的美,小也有小的美。这样发展民乐才会有更多的生路。我们过去过于重视大而忽略小。《二泉映月》用一把二胡来拉,就比大乐队动人。有的大作品10年后就不一定有人听,台湾听众认为,比较起来还是《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更动人。这次来北京看民乐比赛,我看到许多的作品、乐器、编制都很同质化。文化要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而不要建立在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那样会扼杀文化的特色。
现在一些人不相信权威,所以不来参加比赛。民乐界要学会与外界对话,不要关起门来喊“振兴民族文化”。要找到民乐的位置,给它以正确的定位。例如,在作曲上对有些作曲家来说主要是转变角度,传统就成了宝贝,否则就成了累赘。在态度上不要以外国人的审美为外国指挥家听了某人演奏《江河水》之后流泪了,报上就大肆宣传,这有什么!我看要我们中国人听了流泪才算数!
总之,要把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环来对待,进行文化性的思考,建立文化的主体性。民乐界是封闭的,面临社会的变迁时产生很多困难,我们也不要因现实的弱势而否定自己,所以只有找出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找到我们的特质来。两岸分开40多年,这倒可以让我观察在不同环境下文化的不同发展。大陆在改革,但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乱世”,文化人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守住自己的特质,还是化掉自己的特质?释伽牟尼曾经预言,佛教将会灭亡,会灭亡在佛子之手。我看中国音乐就有可能灭亡在搞民乐的人手中,因为特质不见了。
目前谈到民乐的困境,许多人还把民乐的振兴希望寄托在政府的作为上,我认为这是不宜的。政治力量与文化的事务必须有一定的区隔,文化才能乃久乃大。也因此,我个人是台湾唯一拒绝接受到总统府音乐会演奏之邀的人。因为我认为在总统府办音乐会用意再好,也是以政治力量介入艺术。李登辉要听我弹琵琶,可以到我家里来,我总不能用一辈子去换6年,——弹琴是我一辈子的事,而他做总统就只有6年嘛!
于:从大陆和台湾的大、中、小型各类民族器乐作品来看,您认为哪些比较符合您上述的美学观念,而哪些在美学观念上需要调整?
林:两岸在创作水平上,台湾比大陆还有很大距离。原因是,台湾写民乐曲的人,基本上是演奏家出出身的,不是学作曲的。当然,在中国的传统里,演奏家兼作曲家是比较普遍的。而造成台湾民乐创作较差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乐器演奏得并不好,作曲也因此比较差。
现在的民乐,其实是“现代民乐”、“现代国乐”,真正的国乐应该是原汁原味儿的传统音乐,现代民乐、国乐应该只能说是一个新的乐种。而台湾现代国乐的发展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使得现代国乐的发展总是以大陆为它思索和模仿的对象,总是跟着大陆走。大陆又普遍存在着前面我所谈到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而将它们作为落后的象征加以摒弃。我们常常只从两个方面接受传统,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保留了旋律。当然有人对此也有误解,常常把艺术这样一个复杂的表现行为简单化了,好像一提到传统,他就会说:“我们的旋律很优美呀!”请问,哪个人不认为自己国家的旋律是优美的?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旋律是优美的。我们就是要去找出它的特色来。无论是感性的陈述,还是理性的分析,仅仅说“旋律很优美”这样一句空话,说明你对中国音乐还没有真正的反省。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音乐很注意旋律的变化,或中国音乐同绘画、书法一样,有它线形展开的美学特色。旋律固然重要,但还有音色、乐律、调式、乐器之间的配合等等问题。仅从旋律来说,我们也常常忽略了中国发展旋律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中国在旋律上从来不是一字一音的,它留下了一定表现的空间。有的人在旋律下面的配置上又用了许多西方的手法,结果成了西不西、中不中。
除了保留旋律之外,我们的另一项作为是保留了乐器。然而在乐器的配置上,并不发挥它应有的特质,而是用“等量对换”的方法,二胡等同小提琴,竹笛等同长笛,唢呐等同小号……台湾的许多朋友曾对我讲,他觉得民族乐器的许多独奏、小合奏十分迷人,比西洋乐器还迷人,但一听大合奏就让人受不了,感到那么不和谐,那么嘈杂,所有的张力做不出来,等等。彭修文的《月儿高》就改编得很好,因为发挥了每一类民族乐器的特质。而文化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
于:您前面批评了所谓“单线进化论”,在理论上,与其相对的论点是什么?
林:与其相对的是“功能学派”,这是人类学发展到本世纪初所形成的思想。它的意思是,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功能,对于人类生命的功能和对于社会的功能,也就是在人与自然调适的过程中它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从外面看一个民族的风俗时,常常认为它是奇风异俗,但如果你进入到它的文化体系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是理之必然。它之所以如此,是有它的道理,不做这样的选择反而不行,也许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但至少它的演化是有它的道理所在。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我们的文化、艺术,它是一个有机体,你有什么样的美学观,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表现手法,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乐器。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虽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时空在变迁,文化在变迁,但是变化总不能是突然的,如同人的免疫系统一样,它还具有对异体的排他性,你只能慢慢调整。
“单线进化论”产生在19世纪,当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影响。人类学的“单线进化论”在文化学说中出现了,它为欧洲某些人的“我族中心主义”和侵略观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非洲去传教,他并不认为是侵略,他自认为是凭着上帝的旨意去解救你们,因为你们比我们落后呀!西方哲学家之所以能够纵容殖民主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背景。然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了“历史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历史发展中是各有不同的,是分化的,他们以此与“单线进化论”相对抗。他们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虽有共性的一面,但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认识一个事物时,不能只是做横向的类比,还应该纵向追溯它的成因。这就是历史学派的观点。它本身建构的理论并不多,只是一个“破”的学派,即打破单一的思维,让我们懂得文化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单纯,人类的思维也不是那样单一。例如我们见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中美洲玛雅的金字塔,我们不能简单地想,埃及人是如何渡船到玛雅的(当然也有人持这种观点),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它们各自的成因。在历史学派之后的功能学派,主张从功能的角度去研究不同的文化现象。现在民族音乐学开始接受功能论的影响。以功能论的立场,文化就是个有机体,因此,音乐现象就常与哲学观环环相扣。古琴的长度是3尺6寸6分,为什么呢?它表示一年365天有余嘛,它是一个天地的象征,表示大乐与天地同和。人通过琴,融入了天地。
大陆的许多民族乐器越来越金属化,讲得好听一些是音色越来越亮了。原因是我们到农村去演出时,因条件所限,只能在室外演出,丝弦的音量太小。另外,我们太强调昂扬的革命表现,也使得乐器音色愈来愈表面化了。如果以后条件改善了,丝竹乐可以在室内演出了,如果我们思索到自己的文化特质,我们干嘛要用钢弦,要用亮的音色去破坏它原有的美感呢?在听堂里我们可以奏丝竹乐,在广场可以演出吹打乐。一个乐种的形成,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历史原因。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决定坚持哪些,变化哪些。现在一些所谓的乐器改良,我看常常是把“良”改掉了。有些是过时了,有些并不过时,它的存在自有它的道理。
于:您认为哪些乐器是把“良”改掉了?
林:最明显的就是古筝了。古筝到了16弦,它的共鸣箱的共振是最好的。现在到了21弦或26弦,音域虽然扩大了,但高音区和低音区的音色就不能同时照顾到。有人作曲之前总先要问,这件乐器的音域是多少?这是西方的观念。钢琴有七个八度,而琵琶的音在四条弦上所能选择的音比钢琴还多,因为它每个音有多种音色选择的可能性,而我们的作曲家却看不到这一点。我认为音域的问题不是民族乐器改革的主要问题。扩大音域当然是好事,但音域与音色相比,音色更重要。这是乐器存在的根本。古筝的改革,又是加弦,又是转调,但却牺牲了它的音色与韵味,是最失败的例子。此外,笛子加键,把许多特质都丢掉了。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但却丢掉了本质的东西。大陆的乐器的改良不是没有成功的,但多数是失败的。扬琴的改革也有很多问题,没有断音装置,弦越加越多,所有的余音都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忍受。这次比赛有一首扬琴曲《海燕》,可以让我们看到创作的危机!
于:您曾经批评在琵琶的改良中,品加得越来越多。您对琵琶和二胡的改良评价如何?
林:琵琶的品也是越加越多,金属弦那么软,音色那么亮,这都不是琵琶这件乐器本来的结构所给予的,许多原有的特质却发挥不出来了,好在琵琶的传统比较深厚,影响还不大。二胡的改良总的还好,只是有些问题还可以讨论。比如弓子越来越像小提琴的弓子,那么硬。拉《二泉映月》,我是不赞成用如此硬弓的。比如毛笔对宣纸的关系,如同软弓对软弦的关系。用硬弓拉,就如同用钢笔写字了。但现在为了求快,弓子越来越硬。大笛的改良就很成功,既保持了笛子的特质,又具有更加宽广的音色,比曲笛的音色还要浑厚。其实乐器的改良应该是小手术,而不是大手术。前几年,日本音乐集团到台湾演出,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台湾有人竟然向人家夸耀自己把二胡“改良”成四根弦,弓子在外面,如何像小提琴。日本人听后谦虚地说:“对你们的勇气我们深表钦佩,这种改良我们回去再好好研究。不过我们在乐器的改良中,对每一根弦的改变都非常谨慎。”我们听后感到无地自容。
于:大陆音乐界对刘天华的音乐道路存在着不同看法。您对刘天华道路的得与失怎样看?
林:我在刘天华逝世60周年时曾写过纪念他的文章。我认为,要把他的历史地位和他的艺术成就区分开来,当然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的关联,但全搅在一起,就会产生拿刘天华和阿炳比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刘天华所处的历史时代,他那么年轻就过世了,而且做出了那么多的成就,很了不起。但几十年来,我们对刘天华的研究很不够。在那个时代,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么厉害,不少人想用西方音乐去改造中国音乐,而只有少数人,如刘天华能够站在主体位置来接受西方的音乐文化。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这样是十分困难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做到既坚持民族的特质,又不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化的思索上就要比黄自他们困难得多。刘天华只活了短短的37岁,他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的。如果他再活20年,他的创作就可能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十大二胡曲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也充满刘天华个人的风格。他的音乐没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其中用了许多地方音乐很少使用的长弓和慢滑音,反映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索、情感,感情往往也是脆弱的,尽管他写了《光明行》,但它所直接产生出来的泥土般的生命力就不如民间音乐更强,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问题,短短的生命中做出了那么大的成就,很了不起!这就是要给他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肯定他的历史价值。我知道柳尧章先生现在还在上海,90高龄了,现在也没有人去理他。即使他一生只作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它已经成了我国古典音乐的代表作,在历史上也是值得记上一笔的。刘天华的功绩更是这样。他的人格特质就在于他能够站在主体的位置接受西方文化,这是他最突出的一点。对这一点应该是无可质疑的!
刘天华艺术价值的评价,个人兴趣不同,评价也会不同。不满意刘天华作品的人,可能认为风格太单一了,认为胡琴音乐的丰富性体现得不够。刘天华的作品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自怜情绪。听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思乡时经常演奏刘天华的作品。有些文化人主张,音乐作品应该超越传统音乐中文人、士大夫自怜的情怀,而达到更高、更豁达的境界,也因此作为艺术价值的评价。刘天华的作品毕竟有他的局限性的一面。台湾有人讲,一辈子把刘天华的十大名曲拉好了就到头了。这也太没出息了。毕竟,刘天华只活了37岁,连他的晚年都没有活到,自然有他的局限性,在《二泉映月》里听到的东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也就没法听到。那么,练刘天华的东西有没有意义?当然有。像大陆的那种战斗、昂扬的走向,练习刘天华的作品,中和一下是很有好处的。不幸的是,现在却反过来有人拉刘天华的东西也用那种方式。刘天华的作品个人的色彩比较浓,他有他的历史条件嘛!总之,既要看到他的贡献,又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也不同意那种为了今天宣传的需要而片面宣传某一点的做法。对阿炳,我认为不论他的身世如何,他的《二泉映月》无疑是一部经典作品!正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现在流传下来的诗虽然只有两首,但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被人评为“孤篇压倒全唐”。在唐诗的发展史上,他是没有影响和地位的,但仅仅这首长诗却达到了经典的位置,是不朽的。阿炳在艺术发展史上究竟是什么位置?这要看他对后人的影响。也许将来他在艺术发展史上会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位置的人,但这是他的艺术所产生的光辉所给予后人的影响,而不是他在艺术史上直接的开拓。阿炳和刘天华对胡琴的发展从两个不同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二胡的发展上,刘天华所留给我们思索的篇章是会更多一些;在艺术成就上,阿炳是应该更受到肯定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二泉映月》的蕴涵非常丰富,有着十分深刻的个人的特质,却也能深刻感动许多人。《二泉映月》可以说是艺术作品从民间成功走向学院的最好例子。一部作品要在30年内从民间走向知识分子阶层,是很不容易的,而《二泉映月》做到了。其中有内在文化传承的力量在作用着,拉《二泉映月》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像不像阿炳,而是要考虑有没有阿炳的境界。阿炳作为一个民间艺人,他对生命处境的观照比一个文人还要深刻。大陆上有的对阿炳乐曲的解说太无聊,太公式化。公式化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来的。比如说“《大浪淘沙》的最后一段表现了阿炳积极向上的精神”等等,这不符合阿炳的实际思想嘛!最后的快速进行,应该是前面种种感慨一起涌上心头,而最终还是要在低沉中结束,一声感叹嘛!
于:您对现代派音乐怎样看?
林:现代派音乐的基础定位是不满意于古典音乐,总的说它“破”的作用大于“立”的作用。往往写现代音乐的作曲家,他的古典音乐的根底十分深厚,甚至比有些坚持古典音乐的人根底还要深厚。他分析起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来,非常透彻。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陷入了困境。他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他发觉想要超越前人是太困难了;第二,从技术、结构上,他也许感到这条路已经太完美了,作为一个作曲家,他不同于演奏家、演唱家、理论家,他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个性,而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强大的难于冲破的系统。因此,他们就会考虑在古典音乐以外有没有别的系统可以建立。
在现代音乐的各种派别之间,作曲家们往往都彼此虚心学习,注意别人有什么新东西,力求在“破”的同时“立”出新的东西来。现代音乐往往希望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因此现代音乐也都产生在比较开放的国家,现在是信息时代,瞬息万变,作曲家的变化也很快,并不停留在一种手法上,但文化却是需要有一个积淀过程的,作曲家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风格。这也是使我们常常感到现代音乐难以理解,与之存在一定隔膜的原因。台湾作曲家吴丁连先生认为,现代音乐有两大类,一是前卫音乐,其实就是新古典乐派,它不用西方传统的手法,但结构性很强,它是用我们比较陌生的那些元素,但元素之间的逻辑性还很强。另一个是实验音乐,它带有很强的随机性、突破性。前一种音乐,当我们知道了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后,不管你是否欣赏、接受它,起码你能够了解它,因为它结构完整,逻辑严谨。后一种音乐则不同,它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开放性,所谓心灵的积淀是不可能的。有些作品只演一次就完了,只能作为音乐史的现象来探讨。传统音乐可以借助于现代音乐的思维,重新肯定自己的价值。三年前,台湾曾经召开会议,进行所谓“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两极对话”。我发现,我作为传统音乐的传承者、美学研究者,和写现代音乐的人对话,竟然比和搞古典音乐的甚至和民乐界的人对话更容易。现代音乐的作曲家们,他们发现自己所追求的许多东西,在传统音乐里早就有了,例如一些琵琶曲、古琴曲。他们喜欢《十面埋伏》,并非那种千军万马的效果,而是喜欢琵琶那种“无声不可入乐”的手法,他们认为这种手法是非常现代的。
现代音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探索。大学里应该有这样的课程。我们应该鼓励探索,应该有一种宽容的胸怀。在一个社会里给探索留有一定的空间,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不要担心他们会变成社会发展的阻力。他们的特质就是反对阻力,追求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变”,而我们较关心的可能是不变,这两种思维恰是文化发展必须兼顾的。
于:您认为现代音乐的作品如何缩小和听众的距离,如何增加作品的可听性?
林:搞现代音乐的人从来不考虑听众,他只考虑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何具有新意。
于:台湾从事现代音乐的作曲家有哪些代表人物?
林:主要有吴丁连、潘皇龙、温隆信、曾兴魁等等,我不能一一列举了。
于:您对昨晚获奖选手音乐会上的作品评价如何?
林:大阮独奏《松风寒》的韵味很浓,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二胡狂想曲》印象不深,没听出“狂想”,听一次也很难说什么。
于:您对两岸音乐界的音乐评论有什么看法?
林:捧场的文章太多,真正的评论几乎没有。我写了一些评论,吃过我苦头的人可能不少。有的评论非但不是评论,相反是一种误导。要建立好的评论,首先要树立“艺术无亲”的观念,即对艺术的评论不以人际关系的亲疏为转移。佛教讲“佛法无情”,艺术也是一样。第二,对评论的地位、功能要有正确的认识。它对创作、表演究竟起什么作用?评论要能将心比心。好的评论要有两个层次:一是看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将心比心。二是要从他的想法中跳出来,看他这样做在美学上处于什么样的层次。这是美学层次的思考。有一次,张燕拿来香港的一篇评论来找我,说:“人家把我写得那么好,你却把我写得那么糟”“我很直率地说:“这篇评论简直是狗屁文章,胡吹乱捧嘛!我写你音乐会的文章的题目是《优美、流畅之后呢?》就希望你搞了几十年,不要只还拘泥在这个表象的层次。评论就要讲真话,这点一定要坚持。”
于:您对用民族乐队演奏外国交响乐曲的做法有何看法?
林:台湾过去也搞过。作为一种尝试、探索,是可以的。怕的就是“我们也能搞”的心理,这实际是把外国的看得比我们高明。外国人很少讲要向中国乐器学什么,当然这代表着他们的无知,但也包含着他们的自信。我们搞试验,寻求新的音色,这无可非议。可怕的是有的人背后隐含着的自卑心理。火鸡见了孔雀总要“格格”地叫,使劲抖抖尾巴,在孔雀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羽毛,好像在说:“你行我也行!”而孔雀会怎样呢?它无须在火鸡面前证明自己羽毛的美丽。台湾有的搞西洋乐器的人听了那些由子后说:“奏得还真像,民族乐器进步了!”难道像西洋乐器了,就是民族乐器的进步?你像它了,你的进步在哪里?“西方能的我们也能,但我们能的西方却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你不懂得西方。西方不能的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它的乐器在形成的过程中,有它自己完整的哲学背景,我们是不是也能这样来想想自己的乐器?“西方能的我们也能”是一种自卑心态。“我们能的西方不能”,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两者都不好。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点,那就是音乐不应只是专家的事,尽管它需要专家。但音乐家首先要是人,而且要是个文化人。不能离开生命和文化来谈音乐,否则所有的音乐都只能是“术”,而不是“道”,那我们从事音乐的人就太可悲了,所谓“术”,是“道”在现象界出现的手段。中国人过去认为艺术家在“道”与“术”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就在于“道”是“家”而“术”是“匠”。道是体认到艺术与生命、文化乃至宇宙种种关联的,民乐的发展也必须从这里着眼。但我们现在无论在创作还是在表演上,很多人还是在搞“术”而不是在求“道”。
于:谢谢您的谈话。
(以上内容已经被访者审阅)
标签:音乐论文; 刘天华论文; 阿炳论文; 艺术论文; 台湾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作曲家论文; 二泉映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