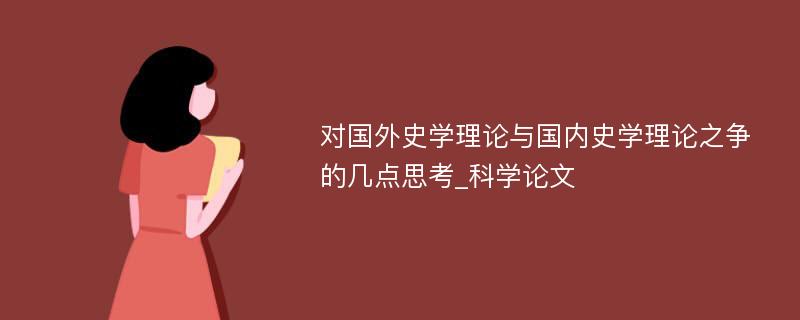
关于外史论与内史论之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外史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外史论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内史论强调科学的自身逻辑,综合史论则力图克服二者的片面性。本文通过对科学的发展历史以及科学的门类结构和学科结构的考察,分析论证了科学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层面,其自身逻辑同社会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
关键词:外史论 内史论 综合史论 小科学 大科学 现代科学
一、综合史论:内外史论之争的结果
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同社会因素的关系,在国外有所谓外史论与内史论之争。1938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科学史著作,书名为《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该书于1971年再版),作者在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外史论的基本观点。外史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同社会条件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解释,试图把科学的发展直接地、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条件。〔1〕第一个系统阐述内史论基本观点的是法国科学史家柯伊列。他在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的研究》一书中力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不能用别的什么来解释,只能以其自身来说明。社会因素是外部因素,它可能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但仅仅是促进或阻碍的影响,而不能影响科学的自身特性、内在结构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向。此后,外史论和内史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双方对推动科学史研究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也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70年代以后,综合史论逐步兴起,新的观点旨在克服外史论和内史论的片面性,它力图证明,科学的发展既有自身固有的逻辑,而这一逻辑又不能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同任何事物一样,科学发展的规律只能由科学自身来说明,但规律的展开又离不开一定条件,科学发展规律得以实现的条件就是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因素。
毫无疑问,综合史论的观点是应该肯定的。笔者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讨论问题,必然会失之偏颇。事实上,科学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层面,同社会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的具体情况。
二、“小科学”时期的外史论
自然科学萌芽于奴隶社会早期,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科学自身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将17世纪及其以前的科学称为“小科学”,19世纪末叶以后的科学称为“大科学”。在这二者之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小科学时期,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社会是第一位的,科学的发展须臾也离不开社会的决定作用。在古代四大文明中心,最初兴起的科学都是以社会为基础又反过来服务于社会的。例如,古埃及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是源于生产的需要,医学则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的需要,至于巴比伦、印度和我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在欧洲,科学在古希腊时期的繁荣和中世纪的黑暗,都无一例外地只能从社会中寻找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四大发明的产生和传播,或者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或者是政治、军事的需要。社会的这种决定作用,不仅作为外部力量影响着科学的兴衰,而且渗入到科学的内部,制约着科学的具体特征和发展方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由于官方的实际需要而组织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偏重于天象的观测记录和相应的历法制定,至于同实际需要关系不大的天体演化规律、宇宙模式等问题,只能被搁置一旁。以实用为重要特征的农学,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重算不重证,缺乏严密逻辑体系的数学,也都是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16、17世纪的欧洲,是小科学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研究时期。英国的贵族之子波义耳用祖上留下的万贯家产,利用简陋的工具和技艺,购买和研制仪器来装备私人实验室,然后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埋头研究。法国马德堡市市长葛里克利用自己的薪水, 拿出4千马克,进行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大气压力的存在。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做的课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研究可以不受或少受社会条件的影响呢?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研究的“随意性”,使得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诱导。首先,作为科学发展相对幼稚的小科学时期,科学研究课题的产生主要地只能来自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其次,作为社会需求的折射,社会舆论的褒奖,社会权威人士的评价等等,也会左右科学家的兴趣。
18、19世纪是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研究的“自由度”逐步降低。由于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难度增加,研究者个人自筹经费,自制仪器日益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科学家不得不设法向社会寻求巨额的研究经费,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把乞求的目光投向资本家。结果,科学家的劳动被纳入了资本的总计划,自由研究变为定向研究,科学家的研究不得不受到资本家利益的影响或受到资助他的财团的利益影响,甚至包括政治的和宗教的影响。
三、“大科学”时期的内史论
19世纪末叶以后,科学的发展进入了大科学时期。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职业活动。科学研究难度进一步增加,所需经费成几何级数增长,原来资本家充当“恩主”的形式已不能适应需要,代之而起的是国家资助以及各种形式的基金会。大科学的研究领域日益向物质世界的纵深发展,科学研究的“投入”“产出”关系和科研效益的可预测性大大降低。在此情况下,研究经费的提供者们只好放弃力所不及的干预,给科学留下更多自由发展的余地。大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高难度、高智力的活动,它的客观内在逻辑强烈地呈现在每一个熟悉它的人的面前。作为社会的人,科学家们越来越不可能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发展某一学科或构建某一理论。科学家进行研究的随意性越来越少,他们只能在科学自身可能的逻辑生长点上进行开拓。这样,大科学同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内在逻辑上升为制约科学的首要因素。社会因素退居为次要的因素。〔2〕
20世纪的科学不再是无结构的几何点,作为人类知识的结晶,它已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组织的知识系统。与此同时,科学实验这一独立的科学实践形式在19世纪末叶以后也得到高度发展和完善。因此,科学可以不再仅仅依赖社会这块土壤才能生长,它有了新的自我增殖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依赖社会需求,单单由自身逻辑的发展而产生新的知识。学科的外部交叉和内部渗透、科学方法的转移和混合、科学概念的推广和畸变、知识单元的蜕变和重组等等,都可以孕育出科学新的逻辑生长点。科学自身逻辑同社会相互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是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如果说,19世纪末以前的科学对生产一般还只能处于滞后地位,那么,在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科学理论已经走在了社会生产的前面。由于科学的超前发展,直接由生产等社会因素产生的课题比重日趋下降,完全由科学自身逻辑所产生的课题愈来占重要地位。本世纪以来,相对论的建立、量子论的建立、现代宇宙学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以及半导体研究、激光研究、核物理研究、超导研究等等,大都是科学家根据科学自身的发展和需要而提出研究纲领的。有人对19世纪末到本世纪60年代全世界自然科学中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过统计,直接来自生产等社会需要的选题只有14%,而由科学自身逻辑导致的选题就占了86%。总之,大科学所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格局:先由科学自身的逻辑衍生出新的理论,再将之应用于社会,推动生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四、现代科学的综合史论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门类结构,这一结构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以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为首要任务,一般地讲,基础科学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比较间接,必须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因而不太容易直接服务于生产等社会活动。基础科学作为探索性最大的科学门类,其研究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它的发展很难完全依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因而不仅研究“成本”高,而且往往很难预料它在何时能够给社会带来何种实际的效益。本世纪30年代,当核物理研究已取得相当进展之时,关于核能的社会利用,卢瑟福仍断言:“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这种途径来取得能量。”〔3〕其他如爱因斯坦、 玻尔等核物理领域的精英也大都持如是看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看法的错误。今天,人们同样很难预测现代宇宙学的研究能给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何种实际效益。基础科学的这一特性,使它同社会保持着一种相对疏远的关系,而在更大程度上沿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发展着。
技术科学是从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的过渡,它同生产等社会因素的关系比基础科学密切,比应用科学疏远。
应用科学同生产领域最为接近。它的研究目的在于,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有关理论通过应用研究,制造出特定的机器,绘制出可供实施的图纸,制订出合适的工艺流程等。应用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最终将科学物化为物质生产力,例如,解决合成材料的分子设计、生物遗传分子的剪裁、电子材料中超微量元素的控制、大规模集成电路中的原子铺设等等问题。人们说,现代条件下的科学正日益成为直接生产力,实际上,真正成为直接生产力的正是应用科学。20世纪以来,正是由于应用科学的直接作用,才出现了生产技术科学化的新趋势,才出现了诸如飞机、导弹、雷达、宇航、电子、仪表等完全科学化了的工业部门。总之,只有应用科学才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现实的效益,也正因如此,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最能引起社会对它的青睐。在当今社会,世界各国的大企业、财团建立起众多以应用科学为主的研究机构,各国政府把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投入应用科学研究,并不厌其详地制定出相关的“投入”“产出”日程表。社会对应用科学如此强烈地关注,使它的特性及其发展不得不主要依赖于社会这一外在因素,应用科学自身内在逻辑的作用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了。
当我们进一步对基础科学的不同学科进行考察时,我们所能看到的科学内在逻辑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各不相同的。一般基础科学是指数学、〔5〕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六大学科。虽然, 每一学科同社会生活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社会作为外部因素对各个学科的作用形式和作用强度却是有所区别的。粗略地讲,社会对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的作用最强,地学次之,天文学和数学相对最弱。关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一方面,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另一方面,它们的研究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地学同前三者基本类似,但程度相对较弱。天文学和数学的情况正好相反。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浩渺的宇宙,除了关于地月系的研究、关于太阳系的研究等少数领域同现实社会有较密切的联系外,其余大都只能作为人类认识的结晶留存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同时,社会至今还很少有能力为天文学的实地考察提供物质条件,即使是相应的模拟实验也十分困难。虽然“阿波罗”登月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但这与天文学研究所能达到的一百多亿光年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天文学的研究主要的只能是观测和想象。因此,社会因素对天文学的作用不能不相对减弱。数学是一门研究客观物质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虽然数学的某些分支在社会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实际应用,但它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只能通过纯粹的理论思维形式才能得到发展。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总要运用社会所能提供的实验手段。数学家们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的定理必须用推理和计算来证明,即使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已被反复验证了的东西也不例外。因此,在六大基础学科中,数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发展必须在最大限度上依靠其内在逻辑的作用。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妨碍我们对数学内部的各个分支作更深层次的探讨。例如,在几何学中,对欧氏几何和解析几何,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看到一些社会因素在其中的投影,而在非欧几何中我们就很难找到这种东西。再如,关于数论,可以称得上是最典型的科学自身逻辑的产物,而运筹学这一比较新的数学分支却较多地留下了社会作用的痕迹。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无论在时间上的持续,还是在空间上的展布,其同社会因素之间都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关于自然科学自身逻辑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任何简单化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1〕也有人认为,外史论是侧重于研究科学的社会史, 侧重于研究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
〔2〕事实上,在大科学时期, 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但是,科学的内因作用则更甚于社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
〔3〕转引自范德清、魏宏森《现代科学技术史》第111页。
〔4〕严格地讲,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