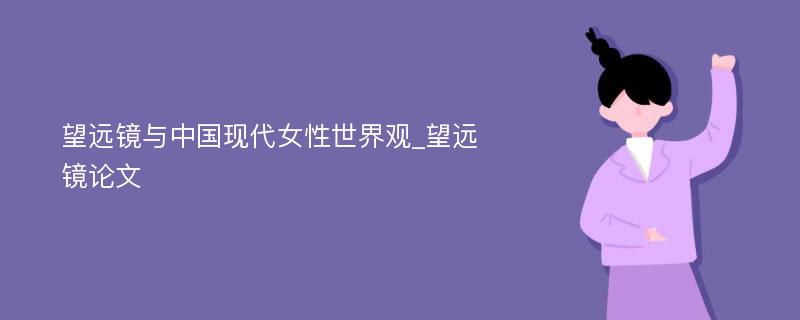
望远镜与中国现代女性的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望远镜论文,中国论文,现代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6-0088-04
望远镜最晚于17世纪初在西方诞生。伽利略用它观察“天堂”,引起了罗马教廷的恐慌。与此同时,望远镜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仅用于天文和军事,而且满足了士大夫对西洋器具的好奇[1],皇宫贵族中的女性,也因此而得见乃至使用望远镜。譬如,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的年谱中便有她儿时玩望远镜的记录。1876年2月,上海优伶“手持千里镜窥探,评骘妍媸”,并引起“妇女勿轻看戏”之劝告[2]。零落的文献记载之外,是隐约可见的媒介意象。周慕桥的画作《视远惟明》描绘了三位女子使用望远镜的有趣场景,1916年出版的二十号《妇女时报》封面上更有女子手持望远镜眺望天际的景观。近代女性眺望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并以一种男性想象的方式流通于大众媒介之中。而现实中的女性也开始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她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是男性参与改造的结果。
一、女性与望远镜的意象
周慕桥(1868—1922)是一位海派画家,被认为是最早表现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广告设计师。他在传统画的基础上揉入了西画的造型与透视,并使用比传统仕女画更丰富的色彩。他的画作《视远惟明》被收入《吴友如画宝》一书中,画中三位女子身处楼阁,穿着长及膝部、袖口阔大的镶边上衣和同样宽松的镶边裤子或裙子——这是清代闺秀的传统装束。其中一位女子欣喜地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另一位女子亦跃跃欲试,二人还在窃窃私语,似乎交流着所看之景。身后立着的另一位女子对此反应平淡,只是低眉望着她们。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责任被限定为“在齐家而不在济世,在阃内而不在阃外”,她们的行动范围和思想自由都受到束缚。两位女子眺望的是家外风景,因进入公共空间而跨越了内外之别;她们的眺望是私密的,没有任何炫耀或展示的成分,自然地流露出面对新景观的兴奋感;她们对待眺望行为的不同态度,隐喻了其时不同女性对于“眺望”的不同态度。
女性借助望远镜眺望的意象第一次出现在近代报刊封面中,或许是1911—1917年出版于上海的《妇女时报》。《妇女时报》是中国第一份商办女性杂志[3],为“通达之闺彦,与夫忧时爱国之女士”[4]创办,以有正书局的财力和经营为后盾,依托《时报》馆的编辑资源,介绍知识,开通风气,主张男女平权,重视市场效益,发行至10余个省市的30多个发行站,发行量一度突破6000册[5]。该刊以彩色仕女画为封面,封面女性的活动和空间多样,出现了一些颇为时尚的道具。在二十号《妇女时报》封面中,一位女子身着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即民国初年中国女性的传统装束[6],额前蓄着刘海,后盘流行的S型髻,发际系一朵蓝色蝴蝶结,透露出少妇的年龄。她伫立江边,手持望远镜,视线所及之处是一个黑色飞行物。同期《妇女时报》刊登了《中国之女飞行家张侠魂女士》的照片两幅(生活照和飞行留影各一幅),“妇女谈话会”一栏刊登署名刘敏智的有关张侠魂的文章,并在“编辑室之谈话”一栏中附张侠魂之姊张昭汉致《妇女时报》社的信。由此可以判断,封面中的黑色飞行物应该是驾机飞行的张侠魂。
得益于“废缠足,兴女学”的热潮,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她们具有迥乎传统女性的智识和眼界。封面中的少妇借助望远镜一睹女飞行者风采,关注女界动态,俨然是现代女性之一员。而根据二十号《妇女时报》刊登的文章和信件可知,驾机飞行的张侠魂也是现代女性的代表。她是维新人士张通典(曾任孙中山秘书)的女儿,是国民政府参谋次长蒋作宾的小姨,后来成为气象学家竺可祯的夫人,当时正在上海神州女学执教。她“素性勇敢,凡事不避艰险。此次服常服(并未易航空之橡皮衣)乘飞机高至十余丈,绕场三周,散采花无数,后欲更进一绕京城,乃风势忽猛,遂堕伤左腿,昏晕二日,现在京汉铁路医院,经德意华日诸名医诊治,创渐平。约一月后,可步履如常矣。是故平淡无足纪,差可洗女界怯懦之习耳”[7]。
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8]47。而在这两幅图画中,既有的旧规则发生了变化。观看者不再是事先设定的男性,被观看者不再是以美貌和欲望为依归的女性,观看目的从对家外世界的好奇和探访发展至实现现代女性对女界新事的探问和参与,观看的结果是她们亲眼目睹了不同于封建女性生活的新世界。特别是《妇女时报》以女性为目标读者,呈现在她们眼中的是女性对女性的观看。至此,画里画外的关系都打破了传统的观看方式,而望远镜成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媒介。
与女性眺望不同,望远镜首次在文学作品中与男性相连,是在戏曲家李渔(1611—1679年)的小说集《十二楼》之《夏宜楼》中①。浙江乡绅詹公的小女娴娴貌美而有才,成为书生瞿吉人利用望远镜登塔远眺所捕获的对象。因未能获得求功名心切的詹公的应允,瞿吉人一面考取功名,一面利用望远镜赢取“神通”之名,获得了娴娴的爱情及詹公的信从。在这里,瞿吉人的眺望对象是詹娴娴,但他眺望的目的并非纯粹的猎艳,而是希望“把他看得明明白白,然后央人去说,便没有错配姻缘之事了”[9]。从这个意义上说,望远镜起到了婚前了解对方的作用,是对盲婚的改良,客观上具有反封建的新意。
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的封面中也出现了望远镜的意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于上海,核心读者群和作者群均为男性。封面多采用花鸟画和仕女画,也刊登过一些国内外女界名人的照片。在1912年第二期封面中,一名男子头戴圆礼帽,身着西装,左手叉腰,右手高举望远镜,向着右上方眺望,视线所及之处是一张法国革命记功碑的照片。与《妇女时报》封面女子有些吃力的眺望不同,这名男子的眺望颇具气势。在辛亥革命初战告捷之时②,这种眺望饱含“向革命致敬”的隐喻,是对暴力获取胜利的讴歌,是对继续革命斗争的鼓励。男性眺望国家和世界,男性读者看到了这种眺望。两性眺望在不同报刊的封面中,呈现出参差错落的呼应关系。
二、现代女性世界观的转变
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女子登高望远本是一个古典意象,近代女性的眺望则与此不同。眺望者不是思念丈夫的闺中女子,而是力挣旧道德束缚的现代女性;眺望的对象不是未归的爱人,而是新奇的大千世界;眺望的目的不是聊慰情绪、排遣寂寞,而是与男子一样了解家外世界;眺望的工具不是一双肉眼,而是同为男性所使用的西洋望远镜。从《夏宜楼》中窥视女性的工具和被女性礼拜的对象,到《视远惟明》中眺望家外风景的神奇媒介,再到《妇女时报》封面中观看女界新事的视觉延伸物,女性对望远镜的利用呈现出显著的进步,女性所做的眺望日益跟上了男性的步伐。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性别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基于性别歧视的男女不平等,核心内容是男尊女卑。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重大变动,传统性别关系才被打开缺口。女性解放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日益受到社会重视而被提了出来。女性的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财产继承权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女性开始获得身体自由和工作自由。在富于强烈政治色彩的被动性中,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和期待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戊戌维新运动赋予传统贤妻良母以“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0]的新内涵,之后又被纳入“女子同为女国民”的新角色[11]。20世纪初,第一个知识女性群体诞生。她们受过新式学校教育,包括在校女学生、职业妇女以及部分受过新式教育的家庭主妇[12],被称为20世纪初女权启蒙中涌现和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③。在她们之前,清末上海租界已有“女界”说:既指一个性别群体,也被视为租界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风气渐变、观念更新的产物,其出现被视为都市开女智的最初成果,为都市女性营造一个共有的性别空间,是女性在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参与面的重要通道[13]。
一方面,在媒体、文本与大众的眼中,现代女性拥有知识和文化,是女性中最先进的一群。她们与进步、文明、自由、爱情、时髦、解放、独立等现代词语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多重想象;另一方面,这些现代女性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思想和行为都烙下过渡时期的矛盾特质,并不具备彻底的、自觉的、革命性的“新”:她们有别于封建传统,迈出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第一步。单士厘随夫东渡扶桑,在四所学校留学,撰写两部旅行记;秋瑾、唐群英等人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留美归国的金雅妹、康爱德等成为第一批职业女医生;康同薇、裘毓芳、陈撷芬等人是第一批女界报人;满族妇女惠兴和慧仙、吕碧城姐妹欣然投身教育界……她们热情接受新式教育,积极投身各种事业,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20世纪初现代女性的代表。近代中国社会的激剧变化,使得女性不再满足于家内空间,不再满足于肉眼式的眺望,她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已不同于传统中国女性了。
三、望远镜与女性视野的变化
画家的观看方法由他在画布或画纸上所涂抹的痕迹重新构成[8]3,《视远惟明》和《妇女时报》的封面反映了画家和编辑的观看方式。绘画、报刊、文学作品中的眺望,都不是女性现实的眺望,大多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女性意识在中国社会萌生,女性的自我意识亦开始苏醒。男性作者敏锐地捕捉并表现这些变化,同时也鼓励这些变化。例如,二十号《妇女时报》的封面虽为画家和编辑所虚构,却也是对张侠魂驾机飞行一事的积极回应和推介。原本是南苑航空学校举行飞机试验,张侠魂因其特殊身份得以参观,进而尝试驾机飞行。对此,《妇女时报》主编包天笑持褒奖态度:“自报纸揭载侠魂女士航空事后,本报认此事与我女界有莫大之关系,乃亟具函昭汉女士,索取造象,顷得复书并赐假摄影,以敬谨印入卷端,爰将来函一并刊入。与刘敏智女士投函所告者,微有不同,因也刊入。幸阅者鉴之。”[15]不仅如此,封面作者更推进了这种赞赏态度,将之表现为引导女界同胞了解、学习这种尝试精神的倾向。
女性与望远镜的意象是男性作者对现代女性群体的一次突出勾勒,在一定程度上是虚拟、超前和想象的。这些女性是他们结合现实并融入想象的产物,甚至代表了当时的某种国族想象,反映了同时代男性所代表的社会共同体对现代女性角色的期待和需要。葛兆光曾经指出,晚清以来的各种政治思潮事实上都是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路向不同,它们都促使民众共同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种迅速飙升的政治力量占据了封建社会旧的权力空间,一切个人的需求统统让位于此,即便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也被要求做一个新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和建构在本质上是为了寻找新的民族国家之途,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目的在于推动国家的现代性进程。20世纪初的第一批女性知识分子,便从“救国”起步,同时开始了“自救”。
这种“自救”,外视为女性视野的改变。她们通过望远镜,形成了更远的视野,不仅在视觉形式上实现了从中式向西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观。技术是其中富于推动力的媒介,时代背景为此创造了根本性前提。望远镜早在明代便传入中国,直到近代女性视野的扩大,女性对技术的内在需要才得以激发,望远镜才成为女性眺望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风气的开化和性别观念的转变是女性视野得以扩大的根本原因。从固步自封的封建帝国发展至“睁眼看世界”的学习者,以男性为主导的近代中国社会在视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循着从技术到科学、从实业到文化、从制度到思想的次序引进西方文化[16]。中国女性解放无论作为口号还是措施,从一开始就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中国现代女性与民族国家紧密纠缠及错综复杂的关系[17],封建性别关系由此得到松动。正是在这种整体视野扩大的背景下,女性的世界观才有条件发生相应的变化。换一个角度说,女性视野的扩大,表现了整个民族视野的扩大。近代中国开始了一场“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18],女性群体的自救工程与之同步。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意即:任何媒介都不外乎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的确,媒介能够帮助人们看到、听到、闻到、触到单凭人力所无法感知到的一切。这种功用对深居闺中的封建社会的女性而言,愈发显得重要。今天,女性借助图书、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拓展她们的感知范围和深度,在更大程度上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回溯历史,对比当下,或许我们更能领悟到媒介与女性世界观之间的微妙关联。
注释:
①“望远镜明际已入中国,但以此器入小说,笠翁算是第一次了。”参见孙楷第.序:李笠翁与《十二楼》.十二楼(亚东图书馆1947出版。)
②《小说月报》第二期的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③文中还列举了陈撷芬、吕碧城、何震、张竹君、康爱德、石美玉等人,作为“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的代表。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