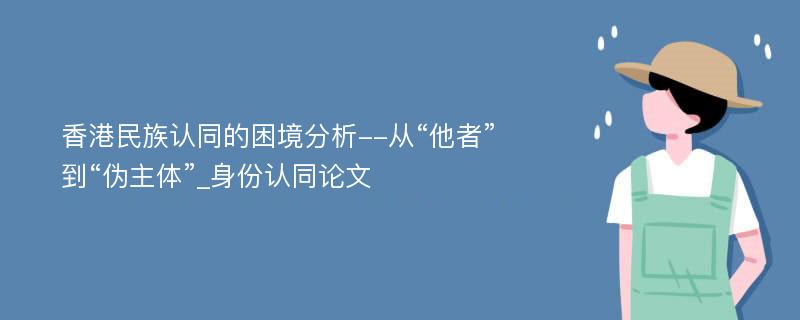
试析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从被言说的“他者”到“伪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困境论文,主体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5)06-0139-05 本土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是香港国家认同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该冲突导致部分港人将“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不认同仅仅是问题表象,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港人自我身份建构话语权的缺失。在香港的殖民历史过程中,殖民主义掌握了书写和言说香港历史、文化和价值的话语权。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由于“去殖民化”效果不佳,西方话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某些层面上继续加强。因此,东西方话语权的争夺就以港人国家认同的问题表现了出来。从精神分析角度看,通过对香港的言说,西方话语制造了一种港人的“伪主体”,导致部分港人以“伪主体”的身份介入到“港陆”对立的映像中来。西方的“自我”借香港的“伪主体”还魂,造就了一种可以将其称之为“自我身份认知的倒错”的精神官能症。 本文试从精神分析学视域出发,对香港本土意识中带有浓郁后殖民主义色彩的主体观念进行精神分析,把握滞碍港人国家认同的主要症候,厘清港人对自我身份误认的根源,寻求港人重建国家认同的可能性。 一、“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殖民逻辑及香港“本土意识”的构建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美籍巴基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通过研究西方殖民者如何将“东方”视作他者性的问题,对殖民主义演变成为后殖民主义的认知根源进行了探究。在萨义德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逐步发现了殖民者最重要的文化统治之术——向殖民地灌输“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殖民国家向殖民地灌输这一逻辑的直接目的在于剥夺殖民地的话语权,使殖民地人民在文化上丧失主体性,从而变成殖民国家的附属品。 2014年底的香港“占中”事件就让我们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实践开始步入深水区,“占中”事件中飘扬的港英旗帜也确证了部分港人身份认知倒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香港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倒错是随着香港殖民历史演进而逐步形成的。为了便于解析,我们以20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崛起为界,将这种倒错了的“精神官能症”的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被言说的他者”阶段和“伪主体”阶段。 所谓“被言说的他者”阶段,是指在港人本土意识形成之前,殖民主义言说和建构出“中国人”即“他者”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殖民者剥夺了港人作为中国人的书写权,通过对香港强行楔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逻辑,塑造港人用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审视中国状况。在这一逻辑下,殖民者成了文明使者的主体和“自我”,中国人(包括香港的中国人)成为野蛮的、被教化的、被审视的客体和“他者”。港英政府通过对这个“他者”的建构,最终间接地将自己建构成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形象。在殖民者的叙事当中,他们自己成为唯一象征性的存在主体,而香港和中国内地则处于边缘并彻底丧失主体性,成为被叙事和被言说的对象。这种二元思维逐步改造港人的头脑,正如法农所说:“殖民主义不满足于把人民紧裹在网中,清除被殖民者头脑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种逻辑的倒错,趋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歪曲它、毁坏它。”[1](P142) 这种二元对立的殖民逻辑在港英时期表现得极为充分,香港人自我言说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本土意识成为被殖民者所建构起来的“他者”的附属品。当然,香港的殖民者并非系统地谋划出这种对立,二元对立是在维护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譬如,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港英政府为了“安抚人心”①,开始重视香港文化教育。港英政府在1967年镇压了港人抗英运动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在将内地视为“他者”的基础上,从文化上建构香港人西化的“自我”。在“自我”与“他者”对立逻辑的统治下,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地位,成为“沉默”的“他者”,他们处于香港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视野之外,没有任何增补、言说和建构自我的契机。西方通过对香港西方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将香港变成了一个西方文化逻辑自我指涉的系统,构造了一个需要摆脱东方前现代化、愚昧、落后,最终建立一个合乎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并实现文化和价值观置换的香港。因此,在本质上,“香港文化”是西方殖民主义投射出来的产物。 香港的主体意识“精神官能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伪主体”阶段。在这一阶段,“自我”和“他者”二元对立的逻辑已经被置入港人意识之中,导致了港人自觉地区分“自我”与“他者”。但这时,“自我”与“他者”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这一阶段,港人不再被殖民者建构为“他者”,港人也不再被视作“他者”(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他者”转变为了英国人以及中国内地人,“自我”则是香港人自己。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事实上,人们是在“他者”(继承下来的条件)为条件下建构“自我”的。法国心理学家拉康通过精神分析学,提出了主体从“他者”的欲望中建构了“自我”的欲望,从而形成伪主体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种伪主体是在语言中被建构,反映的是“他者”的欲望。我们以此来审视香港,就会清楚地看到,以西方殖民者的“他者”逐步缺席为条件,香港的“伪主体”被逐步建构出来。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识的建立阶段,港人迎来了超越二元对立,建立中国人的真正“自我”的契机。表面上看,香港的去殖民是殖民者逐步缺席,成为“他者”,港人开始掌握话语权,可以重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了,但实际上这种重建中国人“自我”的任务并没有实现。在香港,虽然英国殖民统治受到打击,但文化上的殖民没有受到任何削弱,反而逐步演变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继续对香港产生影响。如法农所说的那样,“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结果是把殖民主义的离开对于土著们意味着回到野蛮、堕落、兽性化这一思想插入土著们的头脑里。”[1](P143)经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在一些港人的政治无意识中,“中国”就是一个愚昧、贫穷、野蛮和落后的象征符号,是他们得以“存在”的条件和对立面。由此,殖民历史成为港人获得自我身份认同无法离开的“拐杖”。抛开殖民历史,香港似乎就没有确立自我身份和自身本质,没有书写自身历史的可能。西方文化殖民产生的最严重问题在于殖民文化不但扼杀了本土人民的自我观念,而且让他们丧失了建构真正的自我身份的能力。可见,当香港开始回归祖国,开始寻找“自我”之时,殖民历史和西方文化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了这个工作。因此我们发现,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其实是一种西化的本土意识,其本质是一个“伪自我”,它所建构的主体也是“伪主体”,即臣服于西方的话语霸权,替西方言说的“自我”。 港人从他者(中国人)被抽离出来,建立了所谓的“本土意识”,英国人自然成了“他者”。尤其是在“九七”以后,中英之间完成了香港主权的移交。英国殖民者已经从现实的存在,变成了想象中的存在。但这种想象的他者形象,仍然在以殖民话语的方式存在。这种在场的殖民话语其实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Autre)。大他者指示了一种根本的他在性[3]。香港回归后,香港人头脑中的这种“大他者”就是英国人在殖民时期在香港头脑当中所树立起来的形象,这就是所谓的后殖民状况:虽然殖民者逐步撤离,但殖民地人民在后殖民时代仍然要面对殖民主义的“大他者”。殖民主义的“大他者”不以实体的方式存在,而是依靠象征秩序存在。“大他者”是殖民主义演变成后殖民主义的存在方式。由于对话的存在,使得大他者的欲望成了殖民地的欲望,西方意识形态成了殖民地“真理”性的存在。东西方在文化上的一切差异性都被解读成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低俗与高尚之别。这种认识被贯彻到教育中,培养出了新一代臣服于西方文化的香港人。 港人本土意识,即伪主体意识建立起来以后,内地也成为另一个“他者”,但这个“他者”与香港人想象中的英国人这个“大他者”截然不同。内地的“他者”角色是一个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被视作西方化自我的对立面的“他者”。只不过在第一阶段,香港人还将自己视作是华侨,将自己看做是落后的,需要作出改变的中国人;而在这一阶段,港人开始将自己与内地人相剥离,用前殖民者一样的角度和评判标准将内地视为落后的“他者”。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转折中,将内地看成“他者”的偏见并没有发生逆转。事实上,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政府逐步接管香港,许多港人就对“九七”回归后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焦虑,这种焦虑强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强化了“二元对立”思维。香港回归后,港陆经济地位逐步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创,而内地经济稳步发展,港人对富裕起来的内地民众的排斥心理,这对“本土意识”的建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从而加剧了部分港人“伪主体”的症候,使其进一步丧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 二、“伪主体”的症候——无意识地代人言说 按照拉康的话语政治学,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可以说部分港人是代人言说,是话语的“代理”,而不是真正的话语发起者。出现这种症候是由香港和西方社会所处的话语权力结构决定的。 港人的这种“伪主体”的症候非常明显地表现为港人具有霍米·巴巴所说的“本土的世界主义”意识。在霍米·巴巴看来,在殖民的过程中,被殖民者尽管是殖民的受害者,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殖民者所带来的文化和传统向人们言说。因此,具有悖论性质和讽刺意义的是,被殖民者的视野得到了扩展,被殖民者变成了本土的世界主义者[4]。所谓本土的世界主义,在霍米·巴巴看来,其“精神核心是用少数人的眼光来衡量全球发展。”[5](P11)他认为,殖民者通过向殖民地灌输其价值观,缩小了被殖民者在伦理方面的认知空间,并令他们陷入到对其文化、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误认当中。事实上,香港的本土主义是以尊重西方文化和伦理的权威为前提,香港的世界主义则是以承认西方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意义为前提,而真正属于中国香港本土的东西却被香港的“本土世界主义”者视作了边缘。对于部分港人而言,其本土性就意味着世界性,其所持有的西方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评价尺度具有普适性、客观性和时代性。追求区别于内地的香港本土意识就意味着合乎世界趋势、合乎普世价值。在这里,香港的“伪主体”的症候——无意识地代人言说展露无疑。 在香港,非西方文化长期被边缘化,而西方文化则以主流自居,最终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其他文化为外围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形成的所谓本土文化,其实质是对自己文化的误认——将西方文化看作是主体,就连最为本土的广东文化也因沾染了西方色彩而拥有了所谓“港式”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部分港人才有了越香港就越世界的后殖民观念。 在问题的表层,我们看到港人对自我身份产生的误认,比如“港人优先”的港独组织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与“他者”错位的认知。但这仅仅是“伪主体”和身份倒错症候的表层。从深层次看来,部分港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香港化,而是西方化。这种深层次的症候最明显地表现为部分港人产生了对内地人的自我优势论,“香港人”的身份看做是文明于“中国人”的身份,这种优越感是在殖民历史时期就被建构的,本质上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 三、医治“伪主体”精神症候的路径分析 香港在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港人建立起对“一国”的国家认同,推动香港的“去殖民化”,医治部分港人“伪主体”精神症候。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霸权,导致香港批判性文化难有生存空间。自我主体言说,言说其潜在的欲望、身份、压抑状况,言说其本有的权利,摆脱他者地位,尤其是建立香港底层人诉说自己欲望和权力的空间,争取他们的话语权,成为一个艰巨的政治和伦理任务。因此,应当推动香港建立一个摆脱“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新的协商空间,只有这样的空间建立,才能真正冲破香港文化中的东西方矛盾的疆界,走出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困境。 落实到实践层面,首先,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需要按着“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要求,创造更多的制度环境和机会加强港人与内地的交流,让香港居民参与到国事中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才能建立港人真正的主体意识,将香港人的身份意识由地区居民意识转为中国公民身份意识。譬如民建联所提出的允许港人自愿服兵役问题,如果适时加以推动,将有利于构建“一国两制”下港人的国家认同,有利于促进港人从地区居民向国家公民回归[6]。还有人建议在珠三角地区设立港澳青少年交流培训基地,并安排熟悉外交工作的专家学者不时来港举办讲座,向大专生和中学生讲解国家的对外关系及发展战略;推动港澳与内地青少年的科技交流活动,包括让中小学生参与科技训练营、项目比赛、研讨会及交换生活动等[7]。这些建议均有利于两地青年之间身份之间的相互沟通、认知,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其次,要帮助港人完成真正的自我叙事,找回“真正自我”。特区政府要在文化层面正视殖民历史,澄明殖民历史的本质,从文化和意识层面宣布殖民统治的非法性②,包括对文化符号要顶住压力,积极加以祛除。香港部分民众对所谓的“集体回忆”的留恋,甚至反对遮盖邮筒上印有的殖民地色彩的英国皇家徽号[8],反对祛除耻辱性地名③,恰恰说明仍然残留的殖民时期的文化符号痕迹会造成港人对殖民主义仍然存在的误认。所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不仅要引导民众注重和反思殖民时期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还原港人作为中国人的历史,重新找回港人完整的精神文化史的叙事权利。只有当香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回归以后)修正对公民“象征身份”以及对归属感迷失的认知,才有可能找到和确立真正的“自我”。 再次,在自我救赎层面,香港社会要重新建立“包容”而非排他性“自我”。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和近代不同寻常发展,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相互渗透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殖民与本土文化、商业与非商业文化并存和交融的状况。香港文化的“含混性”或“不明晰性”恰恰证明香港文化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包容品格,让文化之间变得可交流,能够达成共识。香港文化上的多元化得益于其长期以来的宽容环境,而“宽容代表了一种持续”[5](P63)。多种文化在香港的宽容文化环境中彼此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是良性的,这样才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香港的文化。但是香港回归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社会运动频繁,推动香港社会运动的文化和价值缺少了过去的宽容,多了政治上的对立与冲突。究其原因,所谓“普世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还在作祟,混乱了港人的“身份”,撕裂了两地民众的联系和感情。这些显然与香港文化的宽容精神相悖。 总之,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需要引领港人解决第二次遇见“自我”的问题。这个新的“自我”,不再是被殖民者,而是一个融入中国复兴大潮的新主体。当前,香港面临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新机遇。该战略贯穿亚欧非大陆,两端连接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中央政府应当鼓励和推动特区政府以“适度有为”的姿态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努力改善民生。“把握机遇、凝聚共识,团结香港社会各界别、各政团齐心协力,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共同将香港的优势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国家发展,并从中大获裨益。”[9]在这个过程中,要让港人重新熟悉真正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而非西化的带有殖民色彩的“伪自我”:要与那个真实的“自我”对话,从而掌握自我叙事的能力,完成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港人自信心恢复和建立的过程,也是香港真正完成回归的过程。马克思在1843年《致阿尔德诺·卢格》曾说,人心目中追求自由的信心是需要被“唤醒”的,而“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10],当香港真正完成了这一过程,我们才能自豪地说,“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获得了成功。 ①港英政府早期办华人公立学校的意图在1950年3月8日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已有清楚的说明:“政府方面表现出推进教育事业和开办学校的愿望,这是一种手段,意在‘安抚’当地居民,使我们的政府得到人心”。参见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23页。 ②需要注意的是,有人主张“去殖民化”首先应当“去自卑化”,不应当忽视、遗忘殖民史(参见许骥:自卑的去殖民化抹杀不了历史,苹果日报),实际上“去殖民化”不仅不是对殖民史的遗忘,相反是对殖民历史的正视,无法正视其非法性,才是真正的自卑。 ③据统计,香港有一千多个地名、街道名、学校名、建筑物名是以英国殖民者的姓或名命名的。参见华衷:去殖民:香港回归祖国十八年的省思,201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