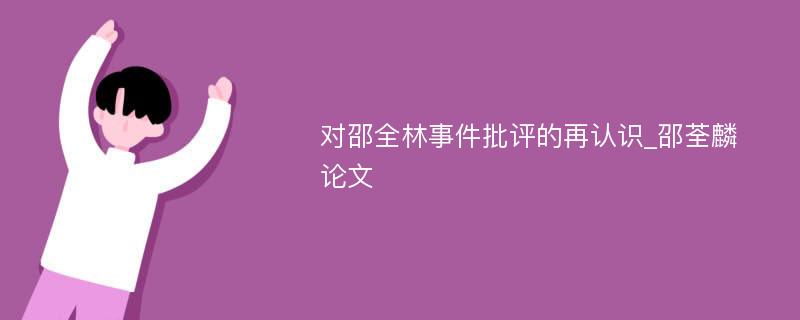
关于批判邵荃麟事件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事件论文,邵荃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1964年10月我们在纳闷的期待中收到了《文艺报》8、9期的合订本。打开看时,一篇大型的批判文章跃入眼前,文章的署名是《文艺报》编辑部。看样子和势头,它比不久前张光年批判丘赫莱依的长文《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1]还要庄重严肃。冠之以编辑部的名义,它标明组织和群体的意向,昭示着问题值得全社会的注意。文章的名字叫作《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又要批判谁呢?我们急忙搜索。原来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一个大人物,仅次于周扬、林默涵的实权派。
一
对于邵荃麟这个名字,作为普通的文艺爱好者,我们说生不生、说熟不熟。说“生”,是因为没见识过他有影响的作品,说“熟”是因为多少接触过他的评论文字。他不是那种“左”得出奇的人物,谨慎稳重中透露着些许客观的眼光,温和的语态里传递着尽可能与人为善、宽容通达的情怀。在作家协会书记处中能对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一案保持清醒的看法,准备予以纠正的人不多,他可算态度最明朗的一个,后来他还因此被批评为有“温情主义”。他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2]看似批判黄秋耘,实是保他过关。他尽量把这位问题稍稍显眼的人物说成是一个天真的书生、一个善良的人道主义者;其毛病在思想上,需要治病救人的帮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笔者阅读当初的感受,由此而对邵荃麟产生了一些好感。
尽管如此,邵荃麟无法超越时代,从1952年调到作家协会,主持常务到今天,经他手里展开的批判斗争远非一次、两次。他谈不上主谋,如果由他说了算,当代文学的大事例或许另写。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与权力中心保持一致,是他坚定不移的选择。40年代批判胡风时,他不甘寂寞,那篇《论主观问题》至今还留在文艺思潮史上。50年代对胡风的鞑伐,他绝不消极被动。丁玲、冯雪峰的问题摆到桌面后,他虽曾有过犹豫,可转变到强硬的处理,又是很迅速的。反右斗争中,“中国作协一个人数不多的机关里,被打成‘右派’的竟达三十人,受到党纪、行政等处分的还未统计在内”[3](P320)。这种情况总不能说与党组书记无关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作为一个实权派,邵荃麟在建国后历次的重大批判中一直扮演着大将的角色。他怎么会飞蛾扑火,制造一种新的理论来对抗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呢!
二
十七年里的大批判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逆反心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总结出一条规律:越是遭到冷遇的东西准保越具有价值,当我们耐着性子把这篇“懒婆娘裹脚布”式的批判文章读完,果然对批判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对邵荃麟观点的维护。最令笔者不服气的是批判者执行着一种强盗逻辑,即你这么说不对,那么说不对,怎么说都不对。同样的话领袖说对,放在你嘴里说,就是罪过。比如“中间人物”这个概念,它的发明权绝不属于邵荃麟,其荣誉的领受权应当归于毛泽东。“中间状态”或“中间人物”是他确定某些人们思想状况、政治态度的一个术语。这些人对待眼前的事变与那些坚决拥护和坚决反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既不特别拥护,也不特别反对,处于徘徊观望的状态。面对任何一个事变的来临,他们都占据多数。他们是我们教育争取的主要对象,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毛泽东在分析抗日统一战线各阶级、阶层的动态时使用过这个概念,在分析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时也使用过这个概念。把他的全部分析模式抽象出来,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一是指积极先进的一头,一是指消极落后的一头,他们都被归结为少数。中间指介乎它们两者之间的人,说先进不先进,说落后不落后,他们占据多数,并且经过改造,能靠向第一种类型。后来“两头小中间大”就成了我们党在发起每一次运动时划分人群种类、思想动态的固定模式。翻开五六十年代党的文件、领导讲话,可以看到,这个模式比比皆是,连我们这些总被教育的小人物都可以对它倒背如流,何况搞熟了运动的邵荃麟,更会运用自如。
现在我们不妨把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既然“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我党惯用的工作术语和思维操作模型,邵荃麟有何不可使用的呢?要说邵荃麟在“中间人物”的概念里塞进了反动的东西——因袭“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P1477)呢?如何理解列宁小说的“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5](P181)呢?要说“中间人物”不能写,那么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主张呢?他说:“人民也有缺点。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6](P849),“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这个改造过程”,“根据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6](P861)。邵荃麟的话没有超出毛泽东的原意,我们还可以说,这位谨慎的文学家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观点句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运用。那么到了他手里怎么就会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了呢?除非毛泽东的活是捏糖人,说给人看,而从来不准备实行,不但不准备实行,反而当作钓饵,诱人上钩,谁要复述,谁就落入陷阱。我们聪明的批判家也深得其中的奥妙,并自觉地成为陷阱的守望者。然而那样一来,又会过高地抬举了他们,把他们又当成老谋深算的阴谋家、权术家。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起码他们还不具备如此高深的城府。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处于无计可施,捉襟见肘的窘困状况,当此之时只能奉行强盗的逻辑、强权统治的方式;不管对还是错;要打倒你,你说什么都是罪过,就是你不说,也能给你安上罪过。对于他们,世界本来就不存在真理,一切都决定于需要,因此你也需讲道理,争辩邵荃麟讲话的合理性,我们单看一些细小的问题便能明白他们的真相。比如,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哪个形象写得更扎实,朱老忠和严志和哪个人物更贴近生活的原貌呢?只要有一点艺术感觉能力的人都会把答案和后面的人物联在一起,可他们不准提,谁要说出真实的感受,他们就说谁否定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鼓吹资本主义。又如,写萌芽可以造成典型,写普遍存在的东西也可以造成典型,是被千百年创作实践证明的艺术真理,可他们只许立论前者,不许提及后者,谁要同时承认后者,谁就有意诋毁无产阶级先进事物,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死胡同里去”[7]。所以不可小瞧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文质彬彬,其强横霸道的面孔不亚于从荒山野林中窜出的强人,不逊于那条守着上游喝水的狼。面对这种场面,你不能争辩道路是谁开的,我喝的是下游的水,只能把性命交给他,任他宰割。所谓“文人之笔可畏”,其描述的情景大概也应包括此类吧!
三
在文艺批评中,由于观念不同,对于同一文学现象乃至同一艺术描写可能引出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还会形成对作品的歪曲。这种歪曲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只要考虑到观念的差异,我们又是可以给予理解的。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栽赃和陷害。而常常的《文艺报》编辑部——一个实力雄厚的知识群体,在大名鼎鼎的批判家张光年的率领下,干的竟就是这种事:对邵荃麟进行栽赃和陷害,其卑劣的行径令人愤愤难平。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得以全面接触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看后我们大吃一惊,《文艺报》编辑部撰写的批判文章和整理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完全是一片弥天大谎。邵荃麟根本就没提出一个“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他在大连会议上共作了三次讲话,把三次讲话整理到一起,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较为松散,还有相当一些文句连通畅都说不上。这个现象说明,邵荃麟事先并没有准备要抛出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重大理论观点。他的讲话像一般领导讲话那样,只有个大致的框框,多数内容是靠即兴发挥,正因为如此他的好多意见都是一般性的接触而没有展开来集中论述。我们无法把他的讲话称作严密的科学论文,更不应根据一些散漫的谈话去归纳一种系统的理论主张。《文艺报》所批的“中间人物论”纯系它们自己臆造出来,强加给邵荃麟的。事实上邵荃麟在讲话中就没有对中间人物作出什么理论界定和说明。包括《文艺报》进行概括、归纳时也露出了破绽,说邵荃麟谈论“中间人物”时“并没有把界限划分清楚”。邵荃麟三次讲话合计起来不足一万字。而涉及到中间人物的只有两处,文字更少。一处是在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前提下,要求写写中间人物,他说:“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焦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另一处是附和茅盾的提法。强调对中间人物的教育,他说:“茅公提出‘两头上,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8](P403)。从上述文字里,我们难以找到邵荃麟与时代有什么不和谐的、耸人听闻的论点,他不过是沿用一般工作模式,要求我们的作家对我们日常工作的重点给与一定的艺术上的关注;他要求作家们写写中间人物时,没有越过什么限度,把中间人物的描写推到艺术表现的中心地位,他只不过是提醒作家不要忽略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个相当大的生活面。而容许他们进入一定的艺术空间,也符合毛泽东说过的“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邵荃麟甚至没有从理论上来系统地论述写中间人物的政治意义、思想意义及美学意义。要想确立一个新的理论口号而忽略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于一个文艺学家来说,会是可能的吗?所以照我的理解,邵荃麟是为了避免人物描写单一化的倾向,为了对作家的注意力作一下微调,才要求写写中间人物,他无意创造一个新概念。《文艺报》编辑部对他的揭发不但没有力量说明邵荃麟想要提出“中间人物”论,反而从相反的方面戳破了他们自己的诺言。请看这段文字,“1961年3月,邵荃麟同志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论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着重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提倡‘写中间人物’。他说,‘光是题材多样化,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起来’。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催促《文艺报》的同志动笔”。《文艺报》编辑部的揭发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邵荃麟一旦把人物创造问题当作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来思考时,他连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也没提,他的中心论题是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提倡‘写中间人物’”一语纯属《文艺报》的分析、推演及捏造,而不是邵荃麟的原话,他的原话里根本就没有丝毫“中间人物”论的影子。像《文艺报》在批判文章中综合的所谓邵荃麟主张“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我们在邵荃麟讲话原文里同样找不到一点痕迹,它们统统是卑劣的谎言,是张光年自己领人加工出来的“罪恶”理论,然后扣到邵荃麟的头上。
四
同样严重的是他们阉割了邵荃麟讲话的主旨,抽去了他讲话的革命内容而给他捏塑了一个反动的“现实主义深化”论,邵荃麟讲话的真正中心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次会议就是“以此为中心”,围绕它来讨论创作中有关的问题。邵荃麟不赞成回避矛盾、粉饰太平的倾向。根据当时官方的政治形势分析,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批评了农民中间的落后意识,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是“个体经济的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8](P392),而这个矛盾又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作家只有写出这个矛盾及其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才能使“现实主义深化”。整个看来邵荃麟对这个问题谈得较为集中、线条也较为清楚,因此像《文艺报》那样,给他抽释出一个“现实主义深化”论未尝不可。
问题是《文艺报》的抽象完全阉割和抹煞了所谓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的灵魂,污蔑邵荃麟“把我们文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更是抽掉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措词强硬而又阴森可怕。可邵荃麟果真抽掉了什么革命性、共产主义的理想吗?首先应当指出,像邵荃麟这样的共产党人,一辈子追求的就是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这追求已和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你让他反对,他都反对不出来,相反他会很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多年的斗争经验也决定,像他这样谨慎的人不会冒着什么风险提出一套新的政见,一种新的文艺思想。说得刻薄些,以他的眼光和能力来言,他很难炮制出完全属于个人的与时代背道而驰的精深理论。他确实谈过应该描写农民思想转变的艰苦性、复杂性。但是他在什么的前提下论及这个问题的呢?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邵荃麟在通篇讲话中提到“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文字不多,可是强调这个前提的文字却不少。他开篇不久就说“要把人口最多的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一个环节”。往哪里提高呢?他紧接着从大的时局出发确定了提高的方向。他说:“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是解决全民与集体唯一的道路,从集体化走向全民所有,这条道路肯定是正确的。”邵荃麟以此来规定文学的任务,他明确指出:“文学的任务就是要求在这时加强思想教育……。集体与个人的统一,个人与集体意识的解决,这就是灵魂工程师的任务。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文学的根本任务。”他反复强调要让农民“注意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应当背道而驰。”因此他提示作家在具体创作中“首先方向问题上不能动摇,……决不能动摇。”即一定要认识到“人民公社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解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关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写农民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注意“我们不是客观主义的反映矛盾,而是为了围绕教育人民。反映矛盾、克服矛盾,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邵荃麟并非像我们平反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很开放、很大胆地提倡一种无多大限制的“现实主义深化”理论。他有时拘谨,他一再强调,就是写矛盾,也“不是写灰溜溜的”、“不要把写内部矛盾与战斗性对立起来”,包括摄取日常生活题材同样不可忽略“可歌可泣”[8](P394)的东西。笔者作了一下统计,邵荃麟上述思想贯穿全篇。他反来复去地予以申明,唯恐作家们产生误解。因为这个,他的讲话颇有拉猴皮筋的风格或自我缠绕的特点,跟《文艺报》经过筛选、过滤出来的内容指向“反动”的“现实主义深化”论风马牛不相及,后者纯粹是《文艺报》为抛出他而硬栽到他身上的。如此陷害真够惊人的了。过去,我们都把知识分子看作书呆子,从《文艺报》编辑部的批判文章观察,事情可不简单。经过批判洗礼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群体了。他们穿戴着文化人的衣帽,实际早已把它当作演进政治的特殊方式,而且把封建时代权术文化机制纳入学术研究机体内,使它成为支配性的运动轴。由此他们才会玩出栽赃陷害这三十六计之一的伎俩。
五
不止如此,对邵荃麟的批判还有更深的东西。它秘不可宣、无法告人。非经过审慎的考究揭不破其中的奥妙。要探寻批判邵荃麟的真相,我们必须考察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今天我们才知道大连会议承接着北京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邵荃麟吞吞吐吐的讲话来自这两次会议,但远远不如两次会议上一些领导人讲的深。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是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左”的偏向。会议由周扬、夏衍主持召开,周恩来、陈毅作了一系列报告。其中不但涉及到了一般创作问题,如批评了粉饰太平的倾向、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否认形象思维等特殊艺术规律的谬说,而且重新确定了对党对文艺的方针,如为人民服务、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给创作以民主和自由。事后周扬曾亲自参与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张光年完成了《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无庸讳言,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对文艺教条有一定突破,其基本精神有助于改善文艺创作的僵化状态。
现在我们不是为谁评述历史功绩,也不是想帮助谁解脱责任。我们是为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态。他们在顺利的形势下,都想抢头功,而在险恶的形势下,又都想来个金蝉脱壳。他们没有刘少奇那种精神,“文化大革命”一来马上把问题揽过去,情愿自己受处分而不愿让下边人受委屈。当江青等极“左”分子打过来、兴师问罪的时候,他们个个像阉人,谁都不主动承担责任。如果时代需要邵荃麟作出牺牲,他又主动要求作出这种牺牲,那另当别论,邵荃麟当了英雄不会觉得冤屈。然而事情远非如此。邵荃麟懵里懵懂被推了出来,作了无谓的殉葬品。要说他因为同柯庆施、张春桥辩论“只写十三年还是要写一○八年”的问题而获罪,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欺人之谈。当时同他们辩论的还有周扬、林默涵。论职位和权势,他们应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却安然无恙呢?而且邵荃麟的问题并非江青之流发现的,而是中宣部送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告之我们,所谓“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写中间人物”论是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进行整风时有人揭发出来的[3](P463)。如果不是有意掩饰,以为邵荃麟的跟斗栽在辩论上,这个认识太天真了。新侨、广州那么大的会,那么多可被极“左”分子抓住把柄的问题都没有人揭发,怎么偏偏就相中了范围、规模很小的大连会议呢?问题就在宣传部,在主管文艺界的两位部长身上。他们想要抛出孩子喂狼,把狼引得远远的。于是他们请出了张光年、请出《文艺报》,由他们起来揭发。《文艺报》非常卖力,为了保住将帅,也为了保住自己,而把写《题材问题》专论的责任推到邵荃麟身上,他们信口雌黄、大打出手。为置邵荃麟于死地,他们不惜采用强盗的逻辑,任意栽赃陷害。这不但是卑鄙的出卖,而且是典型的嫁祸于人。
邵荃麟是不幸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抓进了监狱,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仅从1967年12月25日到1968年1月25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31次法西斯式的审讯”[9]。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这位共产党人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胃病,而他在临死的日子里不得不吞咽那些橡子面充饥。死时,他的骨灰都没留下一点,孩子们收到的只是他破烂的衣物和笔记本。邵荃麟显然是一冤魂,如果人死后有灵,他是绝不会沉默的。
作者附记:本文是作者所写专著《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的一节,全书即将出版。
[收稿日期]200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