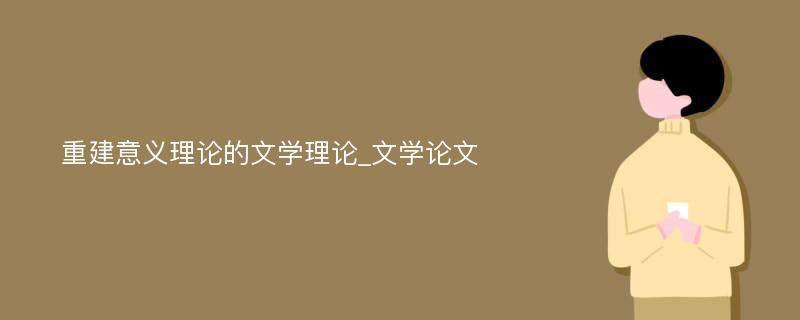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又显出了一股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①。就学科整体而言,这一冲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文论界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向文学理论的返回。可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理论方案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目前相关的讨论尚未真正展开,本文愿行起步之效,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一个方向: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基于如下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具有推进理论认知、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传统等多重根据②。 一、方向感:我们向哪里回归? 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起于文化研究过分否定理论的潮流之后向文学理论的回归③。就像克莱尔·卡勒布鲁克的追问——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对事物冷静理性的打量,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还能留下什么”④?问题是:向哪里回归,或者说回归的方向感在哪里? 西方人的方向感是大体明确的。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回归是要重新回到被文化研究所抛弃了的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宏大主题;在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那里,回归是要回到意识形态批评与自由主义美学的结合;在卡勒布鲁克那里,回归是要使理论之后的理论“具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形式,以便能够在那些理论缺席的地带展开思考”⑤;在布鲁姆、乔纳森·卡勒、辛普森等人那里,回归则是要回到“重申文学的核心地位”⑥。他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恢复,对文学研究来说,其回归指向大约有三项或明或暗的指标:以文学为核心,即便是切入时代政治的宏大主题,也是以文学为扭结核心的关注——这是针对文化研究;全面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成果,抛弃在语言学转向之前思辨美学或认识论的研究模式——这是针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现代英美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积累;向整个社会领域敞开,深度植入后现代以来对现代性危机批判反思的立场和成果——这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此即所谓“理论之后”指向的更晚近的含义。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一种重新向文学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所以,西方人有理论回归的方向感:他们既要追求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为核心的规范性知识积累,又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和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力量。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文学理论在更高程度上创新的努力,其方向感和学术品质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那么我们呢?当然,事实上对于我们,“理论之后”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打通各个领域的福柯或德里达式的大理论,在中国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文化研究也还处在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试验阶段。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大理论之后否弃理论、而后又回归理论这回事。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的重建,其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向感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因而文学理论创新性重建的要求其实更高。原因如下:第一,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从未真正地扎根,我们的理论由于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一直以来的主导范式是反映论、审美主义和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文学理论知识品质的现代性和规范性问题。第二,现代性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与在西方语境下有着迥然不同的针对性,这些针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具有对政治现实和社会正义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一关注显然必须收摄在新的文学理论之中,以保持文论的开放性和照彻现实的能力。第三,中国的文学理论还必须收摄中国文论的悠久传统,使文学理论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因此在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企图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理论方案,除吸取西方人理论回归的几大要求之外,还要有中国独特的理论立场和语境化要求。简言之,要有现代性、开放性和本土性。而这差不多就是那句老话:“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及批评立场,吸收中外文论的经典成果,尔后熔铸创新。 那么,究竟哪一个视野、哪一种理论可以达到这一要求,同时又能够免于余虹所说的“一锅煮”、“大杂烩”的弊端呢⑦?历数种种理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最有可能担此重任。下文分述三个理由。 二、意义论文论的位置 第一个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构成和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 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义事实。所谓“意义事实”,在此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一般的意义事实,文学是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统一体。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话说,“作品的客观意义”包含着“‘总是能再一次’的理想性质”,它既独立于创作者及当初创作时的语境,也不等于阐释者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在理解主观意义以及理解纯粹客观意义之间,有着基于社会世界的独立结构而来的一系列的中间阶段,这个结构包括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共同世界与后人世界。”⑧相对于主观意义的时间化,理解带入了多种时间因素的聚合。一部作品,是该文本在诸世界的关系联络中关联于所有意义理解、意义实现的总和。因此,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性的关联性存在,不仅仅是心理事实(“主观意义”),不可还原为阅读文学或文学写作的意识行为。不管是作家的意向表达,对社会的反映,还是读者的理解,都只是文学作为意义事实的局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文本“带有遗嘱的性质”⑨,文学一创作出来就脱离了写作的原初语境,它“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主体”⑩。写出来的文本像明信片一般散播于社会,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具有通过理解进入历史与文本之符号性持存的双重本性。一方面,文本依靠意义实现即主观的被理解而进入历史,发生着意义的活化、扩容、延异、对文明史的复杂构成和影响;另一方面,写下的文本又是一个客观的、在时间之外的符号书写物,具有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理解阐释而存在的客观意义,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它依然保持原貌并具有“绝对的可读性”。我们今天读到的杜甫的诗并不与唐代有什么不同,它就是那个唐代的杜甫写下的原诗。自杜甫写下之后的任何时代,杜诗都可以其书写物“原诗”的客观意义样态而供人欣赏。书写的客观性使文本成为一个永恒横亘于时间内外、历史内外的心物实体。这便是意义不同于心理经验的特殊性:意义是语言共同体公共和“等待”的意义,只要文本还能被理解,意义就是我们大家的意义。由于文学不是实用产品,如此这般散播的活生生的意义总体就是社会的文学生活。对于这个层面的文学,我们还了解得很少。 第二,作为一种特殊的意义事实,文学是专为意义体验而创造的话语文本。在形形色色的人类活动中,唯有文学将林林总总的人生际遇、命运、情爱、价值等经由想象和语言的创造、提纯、汇聚展示而供人分享。文学是意义体验的专门化。这是作为意义活动的文学区别于其他言语行为的显著特征:其他言语行为的目的实现于“言外”,文学的目的就实现在“言内”。一首诗的价值就是诗带给人意义体验的动人和启示,一部小说的价值就是小说带给我们摄人心魄的领会与沉浸。而这就是文学活动之意义向价值的直接生成:它不外假于其他价值,在文学,意义的体验就是价值。由此就决定了,在文学中“言内”与“言外”具有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结构倾向:言外的意指总是倾向于向自身返回。这就是雅可布森所谓“文学语言的自指性”(11)。体验的需要决定了文学语言总是倾向于自我突出。日常语言以言外的行事效力为目的,文学则倾向于突出意义本身。“它让信息本身——它的具体性、可触知性、可潜沉性等等凸现出来,从而造成涵义的丰富、不定和直接感受的空间。”(12)这一自我突出的倾向体现为文学在文本内部诸结构要素上的一系列特殊性: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雅可布森论“文学语言的诗性功能”、哈维克斯论“诗歌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托多诺夫的“内涵性讲述”、罗兰·巴特的“第二含义系统”、退特的“内涵意义”、布鲁克斯的“反讽诗学”、韦勒克的“语义杂多”、罗曼·茵加登的“拟陈述”、塞尔的“不带欺骗的伪言语行为”、奥曼的“伪述行”、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论等等,所有这些名家所论,实际上都揭示了文学意义不同于日常语言意义的特性,确证了意义体验在文学活动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文学作为意义事实,决定了意义论在文学理论中的根本地位。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不管哪种文学理论,它都应该关注语言生产意义和价值的力量。”“如果要为作为文化产品的文学形成一种理论的话,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关注文学作品是怎样用语言来改变历史、社会和个人生活,也就是说,关注文学作品生产‘意义’和‘价值’的方式。”(13)文学作为意义事实,决定了研究文学的意义机制和构成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的文学论观都仍然着力于对文学外部功能的研究,但是,如果这些研究与探讨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和构成无关,就可以说对文学最切近、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语言学不关心意义的体验价值,但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人对意义的体验和要求;逻辑学不关心意义形态的多样性,但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探索丰富多样的意义形态与人生意义的转换关联。我们无法说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或存在论就是语言论,但它毫无疑问是意义论;我们也无法说现象学文论是语言论,但是它毫无疑问是意义论。我们无法将人类所有的玄思、想象、感觉、直觉、意味、意象、领会、神话、梦想划归于结构语义学、逻辑意义论,但作为语言表达物,它们毫无疑问是意义论的范畴。既然文学是以意义体验为目的,当然就应该以意义体验的有无、动人、精微、深度、生动、充沛、创新等等为有效的意义意识与意义构成。在学术的意义上一个深刻的表达,在文学的意义上可能是空洞,就正如在语法意义上一段晓畅的话语,在诗意品质上可能毫无价值,在逻辑意义上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在文学的意义上可能一无所有。这就表明,普通的实用性语义或逻辑意义并未直接构成文学,文学意义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构成,或者说,文学意义是另一种不同于逻辑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意义形态。在这里,语言的工具性意义与语言的诗性意义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转化关系。要有文学意义,总要有起码的语法意义和逻辑意义,后者是文学意义存在的前提。关键在于,在文学中,话语之“所说”是为了建构意义的体验而存在的,及物的言说反过来是为了建构言内的意义体验。因此,所谓“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就是以意义体验的特殊构成为本位的研究。这就决定了:文学必须要以意义的创造性体验为根据来打破日常语言的工具性宰制;语言的工具意义要反过来成为建构文学意义的手段;作为文学研究的文学意义论不是语文学或逻辑学的意义分析和推演,而是以真实拥有的意义体验为根据的意义确认、阐释和分析。索绪尔说,意义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连接,但是在文学中,这一连接并不意在指向对象,而是通过所指而倾向于向能指、向连接之意义内容自身的体验性返回。胡塞尔说,意义是意识者对感觉质料的意向性统摄,是“被意识者借以被意指的规定内容”(14),但是在文学中,对被规定性内容的了解、认知并不是目的,借此认知而对“含义充实”的诸感觉质料及其意义统摄内涵的吟咏和体验才是目的——可见,把握文学意义需要一种不同于认知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结构语义学的特殊研究。作为专门为意义的吟咏、体验、领悟而存在的话语文本,文学意义的构成因素要比结构主义所说的“文学性”,新批评所说的“复义”、“反讽”广阔得多。在文学,作品中的一切可感性因素——一段传奇、一个笑话、一个隐喻、一片情境,乃至胸襟、意象、想象、观念、人生情绪、蕴藉幽微,乃至对现实的揭示、反映、批判等等——都是意义体验的内容。当它们通过文本独特的话语机制而让读者的注意力焦聚于意义体验,而不是以言行事的时候,就变成了文学。据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同为话语文本,文学的讲述与其他政治、道德、科学、历史的讲述究竟有什么不同,也才可以解释有些及物的讲述为什么同样具有文学性。比如回忆录、游记、历史故事,当它们意义体验的价值凸显并大于实用价值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文学。 由于缺乏对文学意义论强有力的理论奠基,在学科意识上文学理论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一直未能真正确立。许多所谓文学研究实际上离文学事实很远,一些文学学者实际上对文学的意义构成和精神价值漠不关心。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科,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以此为根据,它才可能形成自己可以反复研讨、继承和推进的规范性知识传统。基于文学作为意义事实的本性,确定以文学意义论为研究重心,可以有希望让文学理论真正“面对文学事实”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传统,并沿着揭示文学真相的道路一步步往前推进。 三、文学意义论研究的思想聚合与视野纵深 再看第二个理由:对文学意义相关性的研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打通文学内外的广阔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 不应该有一种理解,认为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就是像结构主义、新批评一样,仅仅是对形式或所谓文学内部“美学肌理”的研究。意义事实的本性注定了文学的特殊性无法构成文学孤立于生活世界的理由:既然是供人体验的意义,就必然包含着人生的解放、激发、肯定、提升、感慨、吟咏、命运感等等的价值内涵。意义的体验性要求决定了文学意义不可能从人生的价值关怀和与生活世界的血肉关联中分离出去。哈贝马斯曾经借毕勒的语言功能图式将意义理论的展开分为三个方面:意向语义学、结构语义学和实用语义学(晚期维特根斯坦)。孤立地看,每一个意义理论视角都抓住了文学意义的某个维度,但是综合地看,实际上“语言表达的意义与(a)语言表达的意图、(b)语言表达的内容,及其(c)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15)。所谓“意义”即是这三重关系的聚合。因此,文学意义论除“言内”的意义形态之外,还必然包括对文学意义的源泉、文学对世界的意义效果以及对文学意义的理解等方面的研究。准确地说,文学意义论的“以文学为本位”并不与“言外”的意义相割裂,而是关注一切意义如何向着“言内”意义的转化、组建和自由创造。文学意义组建的特殊性在于:“言外”在一种独特语态的作用下转化成了“言内”,经由此转换,它既阻断了与言语者实用语境的捆绑性关联,又与言外的世界秘响旁通。通过这种独特的扭结,文学将整个生活世界的意义纳入了专门化的体验性语言通道和程序。 一直以来,各文学本质观的视野综合都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从模仿说、表现论、再现论一直到文化研究,各种理论各取一隅,呈现出各理论视角之间固化、分裂的特征。在这些论观的局部视野下,一个统一的文学事实实际上是分崩离析的。可是从意义论看,诸种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完全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多声部的和声,围绕着文学意义的总体构成而形成文学理论考察的复杂思想谱系。文学是一个以文本为扭结、可以无数次转换为意义经验的社会诸因素的中介联系系统,与此相应,各种考察文学的主义(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实际上是对该规则织物(文本)的意义值的限定性分析和确认。当然,它们所确认的未必都是从文学、从审美出发的意义。它们可能绕开种种问题,但是有一个环节无法绕开:必须断定文学文本的意义值,即必须有关于“文学的意义等于……”的认定。这是文学理论诸种主义的实际效力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诸文学本质论的分布景象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揭示的诸文学理论的视点谱系非常不同。大要而言,种种主义曾经把文学文本的意义值确认为:1.情绪符号(表现说、情感说、直觉说),2.无意识内容(精神分析说),3.意向性内容(现象学),4.意识内容(认识论、心理批评),5.社会意识(镜子说、反映论),6.意识形态(批判理论),7.集体无意识(荣格、文化诗学、人类学),8.独特的语义类型(语义学、语义批评),9.审美意象(意象派、意象批评),10.独特的语义结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11.特殊的精神类型(精神哲学、德国浪漫派哲学),12.审美经验(康德、审美主义者),13.精神的自由创造与意义的延异和散播(解构主义),14.戏剧行为(言语行为理论),15.读者反应(接受美学、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16.意义的政治学(文化研究)等等。其中,每一种主义所给出的意义值实际上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解答,因而也都有它们考察文学意义的视野构成、分析理路和要予以突出的文学意义质性的某个方面。由此,也都构成了我们阐释文学的某种思路。由于活生生的文学是一个在经验状态下混整的意义世界,无论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都意味着对文学意义值的某种断定,不管称这种意义值为“属性”、“特征”、“内容”还是“本质”、“本体”等等。因为说到底,文学无非是一种意义事实而已。当然,这也就决定了各种文学论观实际存在的价值:提供了一种阐释文学意义的路径。除此而外,我不知道关于文学的本质或质性还有什么解答,或者可能有什么其他的解答。 这样,从意义论的视野来看,关于文学研究的诸种主义,其所涉的意义值实际上是在三个层面上解答:心理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这一点与前引哈贝马斯对意义理论的总结高度一致。意义的三重关系与文学理论诸主义对文学意义值的理解高度对应:语言表达的意图对应于心理世界,语言表达的内容对应于社会世界,言语行为的使用方式则对应于读者理解或文化世界。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三个世界的一体性展开共同组成并归属于存在的世界性,它们共同承担着对文学意义的复杂揭示。其中,每一种揭示都是意义内涵的某个面向,而使这些揭示的视野得以成立的原始状态,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对它的现象学解释即解释文学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存在论意蕴”。由此,文学的意义便具有了通向生活世界总体性解码的意涵和通道,文学意义经此纵深挖掘和打量,它与生活世界诸方面的关连和转换便通达明晰起来。所以,意义向来就不仅仅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符号连接或皮尔斯所谓的“解释项”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说,世界不是诸自然事物的外在堆积,而是一个由语言建立的存在之家:因为世界是一个意义展开和充盈的整体。 于是,通过与其他种种主义之间的联系,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意义论背后的视野纵深: 第一,从意义论看,各主义视野之间的打通顺理成章。如前所述,各种主义所涉的意义值是在心理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三个层面上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实际上,历经历史淘汰之后流传下来的几乎每一种主义都切中了文学意义值的某一个层面,因而其分析理路在其所涉的角度看是有效的。比如再现论,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表现论、审美论重新崛起之后,很为一些论者所不齿。可是你看金圣叹用之于明清小说的点评是何等通透有力。每种主义在其所属视角范围内的阐释效力是其他视角无法取代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经久流传的理论视角。 进一步看,各种主义的意义分析只是占了文学意义值的某个维度,它们就像光谱里某一色系的光波值,只是在某个波长范围内有效。比如,属于心理解释的包括无意识、情感、意识、社会意识、意向、意象等,这些解释组成了文学意义心理解释的理论谱系。心理维度的意义论在总体上是意向论的意义观,它揭示意义的心理表达、理解、体验及其形态。我们既不能否认文学的意义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心理内容,也不能说文学的意义就等于心理表达,因为此外它还有道德政治含义、语言规则含义的公共性内容,乃至对人生意义、世界真相的某种揭示等等。除意向论的意义视野外,还有语构论和语用论意义视野的广阔谱系。这样,整全的意义论视野就成为诸主义视野的总和:整合的文学意义论就是打通诸主义的视野之和。它既能收摄各种主义,又能确认每一种主义的适用域和局限性。属值于心理世界的各种文论的差异是解释心理意义的不同层面,一如属值于社会世界的各种文论是揭示社会含义的不同层面,属值于文化世界的各种主义是揭示文化意义的不同层面。 再进一步看,从意义论我们还可看到诸种主义之间究竟如何包容贯通。从心理世界、社会世界到文化世界,不同理论的意义分析视野呈现为不断扩大、贯通、融入的边界延展:再现性的内容必然包含了表现的内容,意识的内容必然包含了无意识的内容,社会世界的内容必然包含了心理世界的意义内容,文化世界的内容则必然包含了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内容等等。心理维度具有理解整个意义谱系结构的奠基作用。最终,说到底,这样的包容含纳具有意义层次整体构成、相互转化的结构自明性:不仅所有这些内容都只是文学意义的不同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于意义而言,只要是社会的,就一定包含了心理的,只要是文化的,就一定包含了社会的,包含了世界整体的意义构成。 第二,由于各主义视野之间的打通,许多关于不同文学理论视角立场之间的纷争也可以自然化解。比如维姆萨特对“意图谬误”(意向批评)、“感受谬误”(感受批评)与文学本体(结构有机体)之间的分野与排除,解释学的意图论(赫斯)和效果论(伽达默尔)之间的纷争,德里达与哈贝马斯、胡塞尔之间的意义真相之争,批判理论与结构主义之争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打量意义而各执一词的结果。事实上意义原本就包含这些层次,是这些不同视角面相的总和。 第三,关键是,正如前文所述,上述种种主义所显示的联系面、所揭示的意义都是综合性文学意义构成的基础,因此反过来,它们所勾连、所揭示的意义恰好显示了文学意义的关联深度:供人体验的文学的意义并不是非现实、非人间性的别种意义,它就是来自生活世界诸领域的意义向人生意义体验性的再创造、再生产。文学与生活世界中的诸意义联络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以一种独特的、专门供人体验的方式,将这些意义提取、凸显、高扬、想象性地再创造出来。此即前文所言,文学是人生意义之体验性聚集的专门化和专题化。所以,文学的审美意义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形式化意义,而是体验性意义向社会、心理、文化意义的纵深的承纳、集结与敞开。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较深入地看到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与上述种种主义之间的区别、联系与转换。这些主义中的大部分对意义值的确认都不是以文学为本位的。因此,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这些意义与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之间的差别转换的研究。先看差别。依据前述,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对文学性、诗性功能、文学叙述、审美特征、诗意特性的描述都是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凸显了文学意义与工具性、实用性意义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明了:如果文学的意义指向是非工具性因而是无用的,那么,人类需要文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本文看来,这是关乎文学精神的根本之问。这一问实际上也是文学语用学研究所面对的难题:我们在逻辑上就无法确认一种无用之用。这也是言语行为理论无法取代文学意义论的根本原因:取消了意义体验,我们就无法确认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言语行为(16)。而直面这一问题,恰恰是文学意义论视角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直接显明了一个生存论事实:人是意义的动物。人之于意义并不像胡塞尔所说,仅仅是“为了求知的需要”,而是人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的生存论需求。钟嵘说,诗“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17)。毫无疑问,人是需要意义体验和照烛的。一如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生的诸多情形、幽微唯有文学才能够“照烛”、“昭告”,爱情、心性、美感、神圣、蕴藉幽微乃至人生的意义感等等:“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8)这种独特的意义建构、揭示及其在体验效果上的感天动地,为文学所独有。文学的根本功用就是人生意义聚集和呈现上的建构性和穿透力。这样一来,差别就显示出来:文学意义是专门为人生提供意义的体验性供养而转化、聚集和创造的意义。就像萨特所说的,文学是人在现实之外为意义的自由体验开出的排排天窗。非文学性意义则是语言的工具性意义,它在文学中意味着为文学性意义奠基、充当意义源泉并通过一种独特的语言机制向后者转变。 显然,文学意义与工具性意义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显明了它们在文学总体意义构成中的作用、关联与转换。在一个整合的文学意义论的视野谱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有效地展开为一系列关于文学内外意义转换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将诸视角之间的转换内在地引向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考察。这些考察包括:1.文本与社会之间的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是文本的意义创新与其所摄入的文本间性、社会世界的意义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影响的焦虑”、“伴随文本”、“模仿论”、“反映论”、“继承与创新”等实际是这一层面的问题展开。2.意义形式与意义要素分析之间的转换,包括形式论与意识形态论、心理学与现象学、文本论与文化研究、存在诗学与新批评等等作为不同意义论的转换融通。3.上述诸层面具体展现在意义形态上各环节的现象学研究:文本符号、意义实现、意义充实、意义状态(价值品相)、意义叙事、意义化、意义政治、意义操纵、意义场域、意义层次(言、象、意、道)、意义机制、意义体验(味、品)、诗意、意向、意趣、言外之意、意义境界等等——就文学研究整体而言,上述各个层面是通向意义构成和形态的研究和阐发的。随着意义论研究的深入,各层次的研究最终必然通向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研究。诸理论将最终走向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意义论并为后者奠基。因此,文学意义论天然地与其他种种主义内在相连,或者说文学意义论视野具有其他理论视野很难具备的对诸理论的收摄、聚合与解释效力。 四、中国文学意义论传统及汉语语感力量的重建 最后,第三个理由:中国古代有极为深厚博大的诗意论传统。诗意论(含“以意论文”)是最了然明白的文学意义论,是地地道道中国本土的原创诗学。由于发之于中国原创,它与汉语的内在质感和思维机制高度融合,具有汉语文论所特有的语感力量。因此,重建文学意义论,可以有效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化,有助于实现中国当代文论汉语语感力量的回复和独特知识品质的重建。 中国上古时代即有极为突出的意义论传统。与古希腊以模仿为核心而关心史诗、哲学和世界的关系不同,意义研究是中国自先秦就得到突破并一直保有的思想传统。这与西方在现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才将意义问题展开为一个普遍性思想领域迥然不同。墨家的名学(名实之辨),法家、黄老的“循名责实”,老庄、易经的“言、象、意、道”之论,儒家的“微言大义”、“诗教”之论、“言近旨远”,纵横家的“飞钳”、“捭阖”之术,几乎所有各家各派都卷入其中的论“辩”之战和在政治外交中广泛出现的以《诗》进言等等,都表明在先秦时代,“言”与“意”的关系考量是诸子百家众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种意义论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早熟的突破,可能与先秦时代士阶层的命运密切相关。春秋战国之际,从社会大动荡中分化出来的士阶层面临着“无以为衣食业”的困境,而以谋略辅佐、聚徒讲学为生存的出路。他们的游说、进言、著书立说和以研习兜售王道论为核心的教学,无不十分突出地面临着一个语言表达意义控制的策略问题,因为他们的言说和研究的企图是以一说动君王。这一潜在的君臣对话意识笼罩了除庄子、杨朱学派而外的先秦诸子、学派、养士和谋士阶层。不管是不是真的面对着某一位王,诸子们的言论、学说都潜藏着一个恒久的听话对象:君王。“王者”、“人主”、“人君”之称在先秦的著作和言谈中大规模出现,表明这一背景意识已经收摄为各家各派思想展开的内在语境。君臣对话的独特语境结构,决定了他们要对各类言谈的意义及其控制技巧展开孜孜不倦的研究,由此形成中国极为发达的对意义表达及其进程高度控制的谋略修辞论传统。不管是“名实之辨”、“循名责实”、“微言大义”、“温柔敦厚”,还是“说难”、“孤愤”、“言近旨远”,或者是占卜解释中的“言象意道”,纵横家的游说之术,后世儒生反复标榜的“赋比兴”,都可以窥见这种独特语境结构关系压力的阴影(19)。比如“赋比兴”在先秦是一种君臣之间以《诗》行谏的言语行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人臣用此六义以讽喻箴刺君上……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君臣间权力格局的巨大压力使进言者不得不乔装改扮,将美刺进言改为唱《诗》,否则就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郑玄疏:“风刺……谓譬谕不斥言……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主文,《诗》辞美刺讽谕。”(20)郑玄的话很好地解释了“讽谕”如何使言谈的意义形态及结构变形。 魏晋之际,中国的意义论思潮发生了从普通意义论向以文学为本位的诗意论的推进转变,对意义表达作为手段的考量此时转变成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追求。至此,先秦深厚的意义论传统终于突变为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意义论。中国文化的智慧形态发生了从王道论背景下的谋智轴心向以人生意义追思为目标的灵性圣智的时代大转型,意义关切从政治语用向审美语用、人生意义追思的突破性转变是这次转型的核心。 这一转变有两个标志:其一,是用“味”来表述对诗文、绘画、音乐的意义效果的把握分析。“味”是领受性的,它意味着理解本身构成了享受。它因此也从直接的理解享受而非功利性价值来评价诗文。这一点到钟嵘就已经十分了然:“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味”是从诵诗者价值体验的角度来讨论意义的。“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21)这里的各种意态都通向“味”并以“味”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或者说“味”就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从心理品质来分析,“味”比认识、评价更主观,它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种体验性的意蕴内涵。但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味”都是中国人评价诗文乐舞画是否具有“诗意”的重要标准。一个文本的意义效果如果“味同嚼蜡”,就不能以“诗”视之,因为它缺乏“诗”的基本意义品质。关键是,从直接审美享受的角度来论诗文的意义,在魏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倾向。经验“味”的活动方式就是自先秦以来古人就津津乐道的“品”。“品评”在魏晋成了一种时尚。诗品、品评人物、品评文章与谈玄论辩、放任自然、书法、绘画等一起成为意趣追求的文化样式。清谈从避祸的手段转变为高谈阔论的聚会方式,玄学从功利之学变为非功利的意义追思,自然从避祸的居所变为“隐逸”,绘画从画像变为“畅神”(宗炳),诗歌从“言志”扩展到“缘情”(陆机),书法从文字书写发展到“意在笔先”(卫夫人)等等。在这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型中,诗文的意义内涵于是从政治语用的意义要求向文学性、审美性的意义要求转变。 其二,批评史论中出现了“以意论诗(文)”的命题。陆机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22)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以“意”来论文之创作。南朝范晔提出文“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23)。曾祖荫认为这“是文意论最早的雏形”(24)。因为在这里,“意”已成为文章创作和表达的核心,而前此(两汉)似乎是“文气”之论占主导。至齐梁,刘勰非常突出地将“意”在文中的地位推到了极高:“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片,其微矣乎!”(25)刘勰甚至提出关于文之意义的特殊性、微妙性的“隐秀”之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26)某种意义上,整个《文心雕龙》的内在逻辑都与以意论文的潜在思绪相关:正因为为文之“意”如此玄妙、深微,有如此重要的承担(“原道”、“宗经”、“征圣”),所以才要有“养气”、“情采”、“神思”、“风骨”等等。紧接着,便是前面提到的钟嵘的“诗味”说在诗意论中的突破。《诗品》开创了一个以意论诗、追思诗意特殊性的典型的中国式文体模型:先有《序》,以揭示诗意独特的“昭告”、揭示之功,将诗意的价值特性追索至“味”,阐述诗意之于人生的意义,并探索如何做才能到达“诗之至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27) 《诗品序》通篇都在讲诗意的特殊性,探讨如何达到这种特殊性的通达道路。在此基础上,钟嵘进而论述各种诗意的质态、品相,为这些品相提供相应的实例,然后,以此为根据,将诗意之论落实到史的具体研究——对前此的诗歌(人)进行等级分类(《诗品》)。钟蝾以意论诗的方式开了后世各种各样的诗品、文品、赋品、画品、字品乃至诗话、词话等融论、品、史为一体的文论文体之先河。自此以后,从唐宋一直到清末,以意论文(诗)、论书、论画、论曲等等在中国文论中有极为广阔的展开,几乎占据了中国文论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中,在先秦作为曲折进言手段的意义考量,比如“赋比兴”、“言近旨远”之类,此时终于演变成了对含蓄蕴藉、余味曲包、不尽之意、味外之旨等等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美学追求。 实际上,中国的诗意论发展到唐代(皎然、司空图),其入思取向的三个角度就已经大致确定下来。它们是:1.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分析诗意的特殊性,分析的重心是诗意构成的复杂性、多重性、微妙性。以言内言外、复意重旨、有限与无限、言与道、虚与实、直接与间接等等关系的探求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具体到诗言上,开此路分析先河的是《文心雕龙·隐秀》。“不尽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是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指标。2.从意义理解的体验性特征来把握诗言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味”。有味无味,味与理、与道德教化、与知识陈说的分野,味之浓淡、深浅、远近、高下,味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味的自然与雕琢等等关系的探求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钟嵘的《诗品》。“品”不仅成为一种活动方式,而且成为中国论古代诗意之有无的基本价值尺度。各种诗品、词品、画品、书品、诗话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著作主体。围绕各“品”的分析、品鉴,如何出诗意、上品级的修炼、养气和技法,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事例和典故成为中国文论体系的独特知识构成。“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是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要求。3.从意义的整体性即意态直观来把握诗言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意义境界。境界之整体与局部、形上与形下、可说与不可说,心境与物境、情思与景物、意味与境界、意象与成境、大境与小境、虚与实、静与动、空与不空、远与近,雄浑、自然、豪放等各种境界之风神品位等等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皎然的《诗式》。浑然成境、“莹彻玲珑”、“境界全出”为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标准。同时,这三种路向又以意态直观为轴心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并互为支撑。 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意义论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诗意论、文意论不管在哪一个路向上的探讨,都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推进和深度。无论是它所开创的思想道路之独特,还是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现代西方的文学意义论所能取代。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心”之言域的分析性演进和高度分化,思想背景上没有对意义内容的反思性分析和确认,观念的语义分析没有成为传统意义论的基础。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真理”的概念,也没有认知、情绪、意义的严格区分。因此,意义论从政治语用向一般意义论的提升、再向审美语用的过渡,都不需要回到对认知意义、逻辑意义的分析作为视角转换的基础。在中国古代,不仅情、志、旨可以为“意”,“趣”、“味”、“韵”、“境”、“入神”等也都是“意”,甚至对于诗而言,它们是比“知”、“识”、“见”等更为重要的“意”。对道家文论或以禅喻诗而言,它们比“知”、“识”、“见”等更接近“诗道”,乃至是“诗道之极”,“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仔细分辨,在不同的语境中,古人所说的“意”主要有三义:1.在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中,“意”是被传达的“旨”(心志、胸怀、情性、意图、意向、情思、意绪等);2.在理解和被理解的关系中,“意”是与符号的言、象、形相区别并笼罩和决定后者的“意”(意义、涵韵、兴寄等);3.在揭示和被揭示的关系中,“意”是通向并显示宇宙内在性的精微之意(深意、玄意、道、不尽之意)。然而此三者在论述中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人主要是在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意态直观中整体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一方法,使中国传统的意义论精神与现象学直观高度契合,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诗意论充满了现象学精神。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28)这段话切中了诗言意义状态的特殊性。叶燮之所以能抓住这些诗意形态的特征并不是源于对象性的逻辑分析,而是源于他对诗歌意义的体验性直观。由于文学意义的审美本性,把握文学的意义特殊性并非逻辑或语法的分析所能奏效,意义体验的反思性直观差不多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真实把握文学意义的唯一方法。对此,中国传统意义论有极为深刻的领会,所谓“诗无达诂”、“说诗者死”即就此而言。而我们看到的许多论述诗意状态的范畴,如“气韵”、“风骨”、“情采”、“隐秀”、“滋味”、“神韵”、“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清丽”、“高古”、“纤侬”、“飘逸”、“言近旨远”、“词约义丰”、“不尽之意”、“韵外之致”等等,无不呈现一种鲜明诉诸审美直观的意义把握,充满了汉语语词“象思维”的质感。 但是,这一极为深厚的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几乎没有体现。中国文论的危机逐渐显现为一种西学东渐的失落:在中西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我们的文学理论丧失了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和内在通达文学事实的能力。由于不是从内在的意义领会去把握,而是概念先行,用从外部移植的理论去肢解作品,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远离了汉语语感原创的血肉,逐步形成通达文学内部的能力、理论原创力和汉语语感力量之三位一体的深重失落。因为缺失意义论视野,古文论中许多基于诗意直观的命题都曾经被文论界斥之为“比附性思维”,很多范畴曾经因为“概念不清晰”而被争执不休,绝大部分富于汉语原创语感的古文论概念被现代文学理论排除在外。如果从对文学意义的现象学直观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这些“不清晰”的概念包含着对文学意义质态某个方面极准确清晰的揭示,而今天我们文论教科书上的那些在形式逻辑上内涵清楚的概念,诸如“形式”、“内容”、“题材”、“本质”、“认识”、“情感”之类,反倒常常言不及义,离文学的意义本相十分遥远。在现代文论中,我们所谓的“科学”和“清晰”,常常是将生硬的逻辑知识论、意义分析硬套到文学意义论上去的不合理要求。文论话语的语感力量是语言直接击中感性直观的能量。一段击中原初直观的话语一定是有语感的,一段有语感的话一定是原创的,而一段有语感的原创的话之于文学的分析把握一定内在于文学意义领会的深处,因为它不是从外在的观念逻辑中截取而来,而是如现象学所言“面对事实本身”,从语言直感的血肉之中迸发而出。就像王国维所说,在丰沛的意义直观中“拈出‘境界’二字”(29)。这就注定了语感力量、理论原创与文学意义领会之反思性直观三者无法拆解的共生关系。在谱系构成上,中国传统文学意义论体现为围绕文意、诗意、言意关系的各个范畴、命题、论断的描摹、洞穿、点评、品鉴、修炼、技法以及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事例和典故所组成的诗话、词话、诗文评而形成的庞大知识传统……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文论对文学意义的巨大关注,甚至可以说,诗意论、以意论文是中国文论的母题。这就注定了文学意义论在传承汉语文论、回复汉语文论语感力量上的独特功效:1.它显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以文学理解为本位创建文学意义论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深厚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具有世界性的理论意义。2.它为古今沟通、中西融合奠定了以意义论为坐标而重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3.它为我们创建中国式、民族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转化材料和巨大的历史依据。 一直以来,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所真正触动的实际上是一个汉语理论言述的语感力量问题。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味的西学概念和学理移植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汉语文论的直感力量。汉语诗学所特有的直观、质感和随处可见的诗意洞穿在扭曲抽象、半生不熟的概念移植中几乎已丧失殆尽。而由此带来的是我们文学理论的原创能力和击中文学事实真相能力的失落。所以,文学理论向意义论的回归与重建,是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依托自己的民族传统而获得独特文化身份的一次历史机遇。由此往前推进,是可以以中国传统诗意论的入思方式和知识基础为本底,融贯近代以来诸文学论观的广阔视野和批判性展开而创建一个新时代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有希望重新获得汉语理论原创的语感力量和对文学事实的深入探究。 ①从文献上看,国内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呼声主要是依据西方“理论之后”的发展趋势而提出来的。比如阎嘉的《“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一川的《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陈太胜的《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王宁的《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的重心不是讨论西方的“理论之后”,而是讨论“理论之后”中国文论怎么办。 ②本文是笔者近年再次撰文正面论述意义论文论的重要性,在行文中我尽力避免与前一篇文章(吴兴明:《视野分析:建立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重复的部分。 ③所谓“理论之后”在理论意向上其实有两种指向,其一是否定理论的,所谓“理论终结”论和“后理论时代”的命名是这一意向的表达。比如尼尔·露西的《理论之死》、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理查·罗蒂的知识语境论(《哲学与自然之境》)一类。其二则是呼唤理论回归的,比如在国内影响很大的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布鲁姆、乔纳森·卡勒等人向文学核心地位的理论回归等。可以说前一种倾向是肯定“大理论”的式微、文化研究的兴起的,而后者则是在文化研究之后向文学理论的回归。两者有融入与联系,但本文这里所谓的“回归”主要是指后者而言,按笔者的理解,这是更晚近一点的倾向。 ④⑤Jane Elliott and Derek Attridge(eds.),Theory After The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 Francis Group,2011,p.64,p.64. ⑥Jonathan Culler,The Literary in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5. ⑦余虹曾经深入剖析过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大一统冲动”:一种“力图用一种主义将所有的主义统一起来,或者干脆将所有的主义一锅煮”的体系化的努力(参见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⑧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6页。 ⑨⑩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第97页。 (11)Terence Hawkes,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London and Methuen:Routledge,1997,p.86. (12)参见吴兴明《视野分析:建立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 (13)J.Hillis Miller,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Taipei: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3,p.9-10. (14)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乌尔苏拉·潘策尔编,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15)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16)文学是否能归结为一种以言行事的行为,是西方当代文学述行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赞同奥斯汀的观点:文学不能归结为一种以言行事的行为(Cf.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04)。 (17)(18)(21)(27)钟嵘:《诗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第3页,第3页,第3页。 (19)参见吴兴明《谋智·知智·圣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7—107页。 (20)《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第271页。 (22)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3)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宋书》列传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24)曾祖荫:《“文以气为主”向“文以意为主”的转化——兼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及其体系的本性》,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5)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6页。 (26)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文心雕龙注》,第632页。《文心雕龙·隐秀》补文的真伪一直有争论,黄侃、范文澜等认为补文是假,詹锳、周汝昌等则力证补文为真。本文对此不持立场,但行文中假设为真。 (28)叶燮:《原诗·内篇》,霍松林等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29)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幼安、周振甫等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