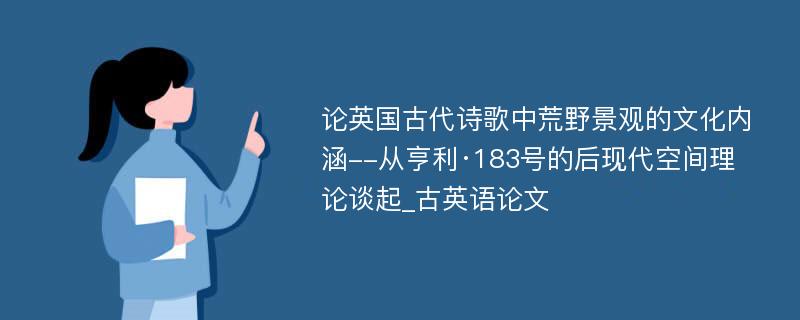
论古英语诗歌中荒野景观的文化内涵——从亨利#183;列斐伏尔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英语论文,后现代论文,荒野论文,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05-0140-07 20世纪末叶出现在人文研究领域内的“空间转向”热潮引发学者们对空间问题进行了多方向深层次解读,空间理论渐渐形成跨学科的立体式发展:涉及建筑、地理、文学、哲学等不同方向①。就文学评论而言,这种综合性的空间视角不仅仅可运用于考察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古代的文本亦大有裨益。正如空间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提到的空间特征不是单一层面,可以从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三个方面来思考其特性[1]11。受这种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启发,古英语文学中的空间讨论可以拓展至社会生产关系、个人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等层面。 文化地理学的引进丰富了空间讨论中对地理景观的理解,现代英语的地理景观(landscape)同源词出现在古英语中为“landscipe”②,意为土地。这一概念发展到现代衍生出极丰富的内涵:包含地面景观与历史文化二位一体的形态。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强调应在文化的视角下解读空间,不再把空间看作是纯粹的客观景观,其实“地理景观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2]27。由此地理景观的社会性被凸显出来。 同时地景这一空间性元素在各类文学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常常以地域、场景、建筑等形式”[3]6出现,特定的地理空间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相对简单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某些地理空间也绝不只是事件发展的场所,它对人物身份的构建具有推进作用。甚至这些地理空间本身就可被当作是一种精神建构而存在,是关于外部环境和社会关系的表征形态。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特征和复杂象征涵义的地理空间。本文借助列斐伏尔有关社会空间和段义孚、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分析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地理景观在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合力作用下所显示出的功能和涵义。 一、文明城墙外的荒野——以史诗《贝奥武甫》为例 置身于都市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常常渴望回归荒野,因为那是喧嚣城市之外的一方世外桃源。但在社会生产力极度落后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人们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不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对未知的自然世界充满了畏惧。他们认为“社会既为个人提供必要的防御同时又是脆弱的,随时会遭遇未知力量的攻击”[4]88。这种恐惧心理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表现为各种怪物栖身于自然荒野,时刻威胁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城邦和蛮荒的自然虽敌对存在,却也紧密相关。文明和荒野的存在本就是相对而言的,“文明创造了荒野”[5]xiii,二者比邻而居,互相影响对方的存在。正是由于早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这种对峙,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社会性方才体现出来。 文明和蛮荒的空间对立在古英语长诗《贝奥武甫》(Beowulf)中尤为显著。这首诗歌具有“时序前后跳动,空间不断变换的非直线式叙事结构”[6]69,但主要叙述事件都集中在一些重要场景下。荒野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叙述空间,它的出现总是和大厅这一重要意象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学者对大厅的意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与之相对的荒野则一直遭遇忽视。实际上人物在荒野中的实践展现了当时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文明易逝的焦虑。 宴会大厅占据了诗歌开始部分的中心地景。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不仅仅为社会关系的发生提供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又和生产力息息相关”[1]85。《贝奥武甫》中的大厅就是这样一个直接体现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地点,反映了当时氏族部落社会的价值观念。诗歌早在第五行就出现了有关大厅的描写,在介绍丹麦王希尔德战胜敌人获取王位时,用的是“夺来酒宴的宝座”(5)③,[7]这样的描述。希尔德过世之后,他的后代统治王国,国力日渐强盛,罗瑟迦继承王位后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成功,因此国王想要在丹麦建立一座蜜酒大厅,“要向老将新兵颁发/上帝赐给他的全部礼物”(71-2)。随后大厅落成,取名“鹿厅”,罗瑟迦国王大摆宴席,招待扈从。由此可见,鹿厅的功用不只是提供宴会的场所,建立这样一座辉煌的建筑,更多象征着国王的统治力和社会的安定。 除了体现日耳曼领主—扈从的社会关系外,鹿厅里的活动也展现出基督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在国王与扈从们一起飨宴时,歌手大赞造物主的伟绩: 上帝全能,创造这世界, 丰饶的平原,环之大洋。 胜利之王,指定了日月, 为芸芸众生,照亮黑暗。(92—95) 这段颂歌表明当时在文明的城邦内基督教教义已经产生影响,人们歌唱上帝的力量,这样歌声环绕、觥筹交错的鹿厅,仿佛一个充满阳光和生命力的伊甸园,是得到上帝恩宠的美丽空间。而大厅围墙之外,却是一片荒芜。 前面提到古英语文学作品中,荒野常设定为怪物的出没地,这一特点在本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第一个敌人葛婪代正式登场时,就和荒野联系在一起:“茫茫荒原,全归他独占/戚戚沼泽,是他的要塞”(103-4)。明亮的大厅和黑暗的荒野间的强烈反差直接激起葛婪代的杀戮之心:它无法忍受文明之地传出的欢声笑语。当夜幕降临时,就从荒野走出,攻击吞食卫士,霸占鹿厅。怪物入侵鹿厅的行为是野蛮对文明的破坏,是对人类生存空间的侵犯,从而迫使武士们晚间不能栖居在大厅内,打破了国王和随从们的联系,稳定的社会空间失去平衡。 随着情节的推进,大厅和荒野不再只是简单的对立,诗人在叙事上巧妙地设计了二者之间相互投射。《贝奥武甫》的叙事主线是主人公和怪物间的三次搏斗,这三次斗妖的地点分别是鹿厅、母妖的巢穴和火龙的洞穴。第一次搏斗发生在鹿厅,第二次搏斗是贝奥武甫率领随从去葛婪代母亲的巢穴中去降妖。此时争斗的性质已悄然生变:人类从第一次的被动防御到这次主动深入无人居住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指出,这场斗争是国王和怪物的领土之争,贝奥武甫旨在清除邪恶力量的行动实质上是在将丹麦王罗瑟迦对空间的控制延伸至怪物们居住的荒野[8]50。这种阐释将文本中建构的空间实践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反映出各部落不断迁徙、争夺土地和空间的情势,也印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一个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 后两次搏斗发生地——洞穴的外部场景描写都充斥着典型的荒野元素,景观非常相似。首先是葛婪代母亲住的地方: 狼群出没的山坡, 狂风扫荡的海岬, 阴险的沼泽小径。 那儿山泉泻下悬崖下的黑雾, 在大地深处泛起洪流;向前不远 再走几英里路,便是那口深潭。(1358-1362) 而火龙盘踞在: 巨石下露出一个阴森森的穹洞, 山溪从水中急急奔出, 湍流夹着滚滚毒焰。(2044-2046)。 两处场景的描写均成功渲染出荒野的危险和神秘,也预示着贝奥武甫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两个洞穴的内部场景还与大厅的意象实现了某种并行。首先大厅一词反复被提及指称母妖居住的潭底洞穴(1513,1545,1557,1570);贝奥武甫也被戏称为“大厅来客”(1545)。而在介绍火龙盘踞的洞穴内景时,和大厅有关的表述也被多次使用(2410,2422)。这种戏仿似的方式巧妙地将两大对立空间并置起来。戏仿是更生动的对比:两类地点皆藏有财富,但性质截然不同。怪物们的洞穴即使储存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不能生产社会关系,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因而在鹿厅里体现国王和武士紧密社会关系的财富在这里只是静止的存在,怪物居住的荒野没有被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范围,是落后的自然空间。 即使荒野是隔绝在文明城墙外的落后空间,二者之间的界限却不稳定牢固。诗歌开始,丹麦王国的鹿厅甫一建成,诗人就指出它在静静等待“战争的火焰、恐怖的焚烧”(83)。而诗进行到后半部分时高特王国的大厅落得被火龙烧毁的结果。这首史诗最后的结尾类似挽歌:英雄死去,大厅被毁,文明社会的根基已然动摇,王朝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荒野是文明对立物,反证着社会空间的存在。 二、人物的内心荒野——以抒情诗《流浪者》为例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其重要著作《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中提到:“荒野不能只是做客观的定义,它既可以用于描写自然也可以是一种精神状态”[9]112。历来文学作品中不乏通过客观景物描写来揭示人物内心的例子,早在古英语抒情诗歌中诗人就已利用蛮荒的外部景观来体现人物内心状况。在此情况下,荒野的地景被晕染上了个人、社会命运的色彩。 《流浪者》(The Wanderer)讲述的是一个失去君主和战友、无依无靠、四处漂泊、寻求新主的武士的故事。诗歌开篇即展现出流浪者身处艰苦的环境,内心更是孤寂: 虽然他,满心凄凉, 仍不得不长期在冰海上 划动双桨流浪,漫漫长途, 一切自有命运掌航。(2—5)④ 冰海旅行确立了诗歌的场景和基调。肖明翰总结过冰海的象征含义:冰海是尘世的象征,冰海航行体现人生,古英语宗教诗篇里经常以“大海上的孤独航程来寓意基督教意义上的人生或人类命运”[10]232。 相比其他抒情诗,《流浪者》有关环境的描写篇幅不长,但每次都是和人物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叙述者在战争中失去主人,“把主人掩埋在大地的黑暗之中”(23)就独自在“冰海的波涛”上流浪,严酷环境呼应了流浪者内心的荒芜和孤寂:他囚禁自我于哀思之中,尽管行动上四处流浪寻找“蜜酒厅”和新主(21—22,25—29),灵魂却被困于冰冷的海上。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分析过大厅是日耳曼物质文明和社会关系的主要象征地:武士在这里接受恩赐,拥有住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在落后的社会中,离开群体独自生活是危险、令人害怕的。在日耳曼英雄文化中,团体(comitatus)有义务去保护个人免受隔绝之痛。了解这样的文化背景,现代读者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流放者的伤痛和悲哀。 外部地景和内心感受互动的最精彩部分出现在诗歌中间关于流浪者梦境的描写:梦中他回到主人身旁,“从宝座上接受赏赐”(45),但是睁眼“看见眼前无垠的海浪,/张开双翅在水中嬉戏的海鸟,/还有严霜、白雪和冰雹飞扬”(47—49)。这样梦中的欢乐立即被眼前的蛮荒景致惊走。这种甜蜜回忆和冷酷现实的对比烘托出流浪者内心的痛苦。寒冷、霜雪、冰雹以及稍后提到的废墟都可以被当作是表现人物内心哀愁情绪的“客观对应物”[10]234。然而在后面的诗行中,流浪者强调自己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因为“没有长年累月的生活磨炼,/谁敢自称智者”(64—65)。真正残酷的考验不是个人失去家园,而是“世界的财富沦为废墟”(74)。这样的感叹和前文《贝奥武甫》中大厅的意象相呼应:文明社会和蛮荒废墟的界限是不稳定的,文明随时可以被摧毁。 细读此诗可以看出流浪者在整首诗中经历了三个层次的焦虑:第一层是海上漂泊时肉体所受的苦难;第二层是离开蜜酒大厅所象征的文明社会,个人精神上被孤寂折磨;第三层已经从流浪者个人的悲哀上升到对整个部落群体社会难逃最终消亡命运的担心。在这三阶段发展过程中,流浪者在荒野之中经受多重试炼,是否能通过此考验,决定他能否真正找到家园。段义孚《恋地情结》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和客观自然环境的情绪连接,“恋地”(Topophilia)是他自创的一个新词。在《流浪者》中主人公对过去的家园——与主人、伙伴欢乐相聚的蜜酒厅怀有深深的眷恋,如今流放在海上,荒芜的景象是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煎熬的真实写照。西方文学各个时期的文本里时常构建起一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尤其在《奥德赛》这种旅行叙事中,家园的空间设定尤为明显:“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11]35。各种古英语诗歌,无论史诗、抒情诗还是圣徒传记都涉及了这一主题,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各族群是由北欧辗转迁徙到不列颠岛定居下来的,家园对他们而言分外重要⑤。 在《流浪者》一诗的结尾,诗人没有止步于对普通家园眷恋的描写,揭示出流浪者寻求的是永恒温暖的庇护之地: 让我们在永恒的幸福中 努力向那方向一步步迈进。 那里生活充满上帝之爱,以及 天堂的快乐。(110—113) 古英语抒情诗中还有很多作品同样展现出地理景观和个人心理层面的联系,比如《航海者》(The Seafarer)和《妇怨》(The Wife's Lament)等。这些诗歌既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日耳曼部落群体生活的依恋,更加突出了他们对尘世的繁荣易逝的担心,所以他们最终的追求都是要获得天恩,通往永恒的天堂之家。“这种渴望不仅根源于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和对天堂的描绘,而且很可能还与剧烈动荡的中世纪社会现实有关”,使得抒情诗人们表达出对“尘世动荡不安、变化无常的生活的否定,而把眼光投向天堂的幸福和永恒”[10]171。 三、通往永恒家园的阈限荒野——以圣徒传记《古德拉克A》为例 《流浪者》中诗人已表达在海上的磨难是远离家园的流浪者获取永恒幸福的必经阶段,荒野的阈限性(liminal)功能在宗教诗歌尤其是圣徒传记里有着更明确的阐释。吴庆军在讨论英国现代小说的空间建构时提出“现代主义作家不再把空间仅仅看作事件展开的场所和舞台,而是一种蕴含身份、宗教和权力等多维社会文化要素的指涉系统”[12]143。其实回看古英语诗歌文本,荒野这一特定空间与居住者的身份构建有着密切关联,空间场所的涵义已经被打上很深的文化和宗教的烙印。以下以圣徒传记《古德拉克A》为例,分析荒野为圣徒构建身份过程中的重要空间。 古德拉克(Guthlac,673?—714)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隐修苦行僧⑥。他出身贵族家庭,年轻时是成功的武士,获得卓越战功,担任首领,后来却忏悔于杀戮的生活,皈依基督教,前往一座荒岛定居,在那里苦修15年,声名远播,吸引众多信徒前往参拜。古英语诗歌《古德拉克A》记载了他在荒野中修行的事迹。 诗歌一开头天使在传递神谕:上帝将在人世间选出一些人赋予他们力量,庇护他们到达永恒的家园。显然这些人就是信仰上帝、意志坚定和品德高尚的圣人:“他们居住在荒废之地,凭借毅力定居于此,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等待通往天堂之路。”(81—83)⑦,[13]这段诗行已经点明:在荒野中经受磨难,获得精神的提升是成为圣徒的必经之路。很快诗人将叙述聚焦于古德拉克由普通修士成长为圣徒的过程。 首先古德拉克被召唤离开热闹的社会,到荒野中去寻找新的住处。这个栖身之所不能随意而定:“这片土地直到上帝显示,才让人们在树林中寻见”(146—148)。这样的地点充满神秘的色彩,普通人无法接近。诗文中并未指明这片荒地的确切位置,但正是这种空间上的不确定性使它区别于人类社会里的真实地景,具有普遍性和隐喻性;虽只寥寥几笔,却勾勒出荒野遥远、神秘、危险的特质。 诚如前文论述,相较文明社会而言,荒野是充满邪恶、危险力量的边缘地带,但是在宗教主题下,这种边缘地却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无论身处沙漠、海洋还是荒山,修行之人可以从艰苦的环境中得到精神的力量,荒野成为更易获得圣意的地点。荒野的这种功能可以追溯到《圣经》之中。例如《旧约》中摩西在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在沙漠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折磨;再如《新约》里施洗者约翰在不毛之地传递教义时所经受的困难。古德拉克在成为圣徒之前,不能逃离外部恶劣生存环境和魔鬼敌人的折磨。在此意义上,古德拉克选择做一名潜心修行的隐士时的身份是含混的,处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betwixt-and-between)的状态:既脱离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家园,还尚未获得天恩进入天堂。荒野就是一个阈限的中间地带,充斥着诱惑和挑战,但却不是一个被动的地点,亦具备对人物发展的促发功能。面对各种危险时,隐士唯有获得“大多数上帝殉道者们拥有的勇敢”(178),通过这个阶段,才能获得个人的救赎,构建起完整的身份。 诗人在《古德拉克A》中对荒野客观的艰苦环境着墨不多,更多表现的是主人公与魔鬼的空间之争。在古德拉克定居这片荒地之前,撒旦的拥趸们被上帝流放,只能“一直游荡在陆地上,疲惫的时候在此休憩”(210—212)。对这些魔鬼来说,此处荒地是欢乐的源泉,所以一旦失去控制权,“他们将遭受永远的悲伤,他们就不能享受在陆地上的停歇之处,失去避难所和家园”(218—222)。古德拉克的到来使得双方产生冲突:都想抢占土地的所有权。在《古德拉克A》近八百行的诗篇里有六百多行都围绕着这场争斗。魔鬼反复对古德拉克进行言语上的攻击和精神上的折磨,古德拉克一直镇定地面对。他清楚自己面临的困境:“荒野之中,是很多逃亡者的居处,这是那些邪恶灵魂的藏匿之处,居住在此的是恶魔”(296—298)。但是他无所畏惧,他有上帝给予的“精神的武器”(175,302),坚信上帝关注着他的行动,因而坚定地为上帝看护领地,驱走恶魔。诗歌中突出战斗意象的写作手法无疑是与当时日耳曼社会的尚武传统有着一定的联系的。这种例子在古英语宗教诗歌中屡见不鲜,很多有关经典宗教主题的古英语诗歌同时融合了日耳曼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古英语诗歌《创世纪》中相比《圣经》里的描述,“对于部族之间的冲突和战斗场面,诗人则浓墨重彩,尽情发挥”[14]81。与普通的世俗争斗不同,宗教诗歌更多是用外界的战斗来概念化内部的精神之争。在讨论诗歌中人物的神圣性时,夏尔马就强调外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联系:“与魔鬼身体上搏斗的进行显示的实际是主人公精神的提升。”[15]185-200霍瓦特认为荒野中古德拉克的住处象征他的心灵,“战争实际就是在他的心中展开”[16]1-28。这些引申解读都共同论证了荒野概念不只囿于物化的外在环境,它与宗教信仰影响下人物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关联。 从广义上看主人公古德拉克和魔鬼们都是流放者,但本质不同。魔鬼作为撒旦的属下,反叛上帝,因而被驱逐出伊甸园,注定永在尘世流浪。与此相对,古德拉克是主动放弃贵族武士的身份,从社会的中心来到边缘,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荣光,与世隔绝、充满危险的荒野成为他寻求荣耀的途径。家园对古德拉克来说是栖居身体更是安放灵魂之处。诸多有关二者空间之争的讨论中,颇具启发的是科恩将土地得失与身份构建联系在一起。“魔鬼失去自己休憩的土地显示他们缺乏一个群体的社会身份”[17]136,它们注定只能在“在空中飘荡”(126),“这些流浪的邪恶魔鬼没有根基,没有家园的基础”[18]131。由此可见,物质存在和精神世界的交互是刻画人物的关键环节,这一文学创作手法在中外古代文学中并不罕见,正如汤琼在比较奥德修斯和孙悟空的漂泊之旅时所总结出的:“自然界中遭遇的艰难险阻象征着人类物质存在的平凡世界和面临的生存环境;外来的诱惑象征着人类风光旖旎的内心世界;而人必须经过双重磨炼才能心智成熟,才能达到生命丰富多彩的境界。”[19]137 中世纪西方文学家和艺术家擅用外部地景的改变来显示人物内心精神的提升[20]1。在《古德拉克A》中,主人公精神境界的提升最终是通过改变外部景观来实现的。诗歌最后,古德拉克坚毅的品行使其获得与魔鬼斗争的胜利,上帝派出使者宣布了他对这片荒地的掌管权力,随即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荒地变成一片盎然绿色,那里鸟语花香、生机勃勃(729—751)。荒野中的住处在“上帝的庇护下经历了一次蜕变”[21]141,流放蛮荒之地可以变为圣意保护下的精神乐园,古德拉克也跨越了阈限,完成了身份的构建:成为上帝忠实的信徒和地域的合法看护者,从而在荒野中建立起一座光明之城,分享天堂的荣光。 《贝奥武甫》、《流浪者》和《古德拉克A》等古英语诗歌中,荒野地景表现为沙漠、沼泽、海洋、荒山等丰富的形式。这些外在的地景承载着多层的象征涵义,涉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化、社会、宗教等方面。荒野既作为一个充满危险的自然空间与人类文明城邦对立存在,但二者的界限并非亘古不变,不安定的社会背景下,蛮荒力量有可能摧毁文明。荒野在基督教教义影响下又传递出积极的意义:它为寻找永恒家园的流放者提供一片中间地带。唯有经历荒野中的一切考验和折磨,才可能跨过阈限,接受圣意通往永恒之地。本文借助现代空间理论开掘荒野地景的涵义旨在为古英语文本的空间研究拓展更广的视角。虽然中世纪的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熟悉的“他者”,但二者不是断裂的存在。古英语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已经通过客观外部景观的描写来揭示个人、社会、命运的交互关系。跟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场景功能在文学创作的长河中逐渐获得多维发展,才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中复杂和精妙的空间建构。 ①具体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空间问题的研究,同样涉及跨学科手段的运用。讨论主要有两大趋向:一类是从考古学出发试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这类研究深受德国地理学家Walter Christaller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NJ:Prentice,1966)中提出Central Place Theory(CPT)理论的影响,将考古的具体发现和社会、经济系统相结合。英国历史地理学家Delia Hooke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定居情况和地景状况等各个方面,其著作有Anglo-Saxon Settlements(New York:Blackwell,1988)和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Leicester: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1998)。另一类是关注文本中的想象空间,考察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文学场景下的体现。Fabienne L.Michelet所著Creation,Migration,and Conquest:Imaginary Geography and Sense of Space in Old English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一书是迄今为止最细致探讨古英语文学作品中空间概念的专著。 ②“Landscipe”一词最早出现在古英语诗歌《创世纪B》中第375—376行:撒旦提到地狱时说道“ic a ne geseah la e ran landscape”("I never have seen a more hostile landscape").Bosworth和Toller在其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词典》(An Anglo-Saxxon Dictionary,Oxford:1898)中将其定义为“一片/块土地”("a tract[or region]of land",p.619)。 ③本文有关《贝奥武甫》的中文译文参照《贝奥武甫》,冯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诗歌行数。同时相关的人物、地点中文译名均参考冯象的译本。 ④本文有关《流浪者》一诗中文译文参照肖明翰的译文,出自他的专著《英国文学传统之形成》(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诗歌行数。 ⑤著名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学者Nicholas Howe的专著Migration and Mythmaking in Anglo-Saxon Engla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探讨。 ⑥现存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本中最早介绍古德拉克的是菲利克斯为其撰写的拉丁语的散文传记,Felix's Life of Saint Guthlac,Ed.and Trans.Bertram Colgra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里面详细记载了古德拉克一生的重要事迹。 ⑦本文有关《古德拉克》一诗中文译文由笔者自己完成,英文版参照Anglo-Saxon Poetry,Bradley,S A J.ed(London:J.M.Dent,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