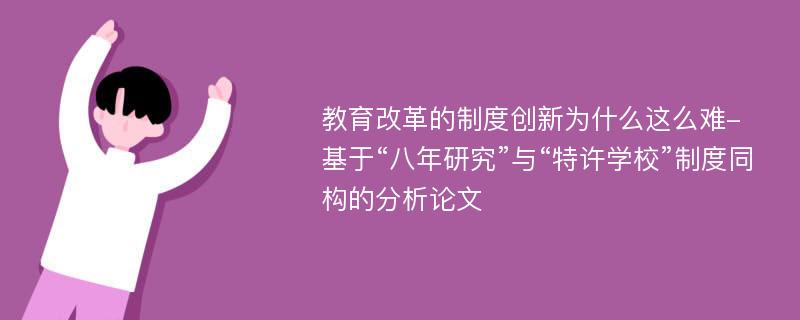
教育学研究
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基于“八年研究”与“特许学校”制度同构的分析
程晋宽 方蒸蒸
[摘 要] 教育改革的过程是对教育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教育的真正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制度的根本改变。作为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公立学校改革也一直与如何实现“学校自由”和“制度创新”相关。从新制度主义“制度同构”的视角看,美国历史上的“八年研究”和目前的“特许学校”改革面临着相似的“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美国“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重大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历史价值和揭示意义,包括如何打破现代主义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为什么在遇到抗拒的制度力量时要妥协,这些有助于为我国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思考。“制度同构”对所有教育改革都是一个难以逃遁的陷阱,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要面对“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模仿性同构”的压力。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应充分考虑制度惯性的压力,突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形成学校改革的合作关系,发挥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
[关键词] “八年研究”;特许学校;制度同构;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40 年来,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何在?为什么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但却难以有教育的制度创新?在全球教育不断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浪潮中,美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往往以其独特的教育改革思想和改革行动,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学校“去标准化”和“去官僚化”的集成化、智能化、泛在互联的教育改革进程,各国教育改革必然要触及到现代学校制度的根本转变,以探索与智能化时代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创新。西方现代学校改革的制度之争一直是与如何实现学校的自治权相关,以打破工业时代形成的公共教育的僵化制度,实现学校治理体系的现代超越。特别具有超越价值的是,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发起的“八年研究”,虽然发生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它对“现代教育制度”做出了超越性的改革,并仍具有当代价值。同样,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特许学校”制度改革,经历了市场化的新制度建设过程,被视为现代教育制度创新的新举措,对现代教育制度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从“制度同构”的视角看,新制度主义的“特许学校”与进步主义的“八年研究”具有历史的相似性,通过对两次重大教育制度改革的制度分析,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困境,也可为我国学校教育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社会历史的借鉴。
一、“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一个教育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
1.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类型的组织会变得与环境中的其他组织日益同构或相似,学校就是这样的现代主义的“制度牢笼”,在其发展演变中具有了“历史相似性”或“历史的轮回”。教育改革中的“制度同构”被教育史学家泰克(Tyack)和库班(Cuban)称为“学校教育的语法(grammar of schooling),意指“组织教学工作的常规学校组织结构和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明显的规律性”与“同质化”,① D. Tyack & L. Cuban,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54. 成为不可逾越的制度藩篱,呈现出惊人相似的“制度历史”。
现代学校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而形成的正规学校教育(formal schooling),也是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巨大抵制力量。梅茨(Metz)认为,建立“真正的新学校”的困难就在于,所谓的“新学校”还是采用那些普通的、寻常的,距离学校传统教学模式和组织结构差别不大的实践或所谓的“制度创新”② M. H. Metz, “Real school: A universal drama amid disparate experience”, in D. Mitchell and M. E. Goertz(eds.) Educational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Yearbook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 London & New York: The Palmer Press, 1990, pp.75-91. 。在这种语境下,所谓的“教育创新”是有限度的,一般只停留在与传统教学模式和学科教学有一定区别的改革实践上,尤其是指教学法的“创新”。公立学校教育改革者积极提倡的教学实践创新方式主要是停留在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上,一般不涉及或触及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因为作为历史存在的现代学校制度,仍然采用着工业时代“流水线式”的年级制度和“车间式”的班级制度,是学校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最大障碍,许多所谓的教育改革都停留在表浅、细枝末节的教学改革上,难以触及根深蒂固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变革。
2.制度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逻辑
学校改革必须对具有合法性逻辑前提的“现代教育制度”提出挑战。梅耶(Meyer)和罗恩(Rowan)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思考的视角,对学校改革的“神话”和“仪式”(myth and ceremony)进行了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解释与分析,认为教育制度中某些正式化和仪式化的力量,往往会对学校改革创新采取“制度同构”的合法性解释。③ J. Meyer & B.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3, 1977, pp.340-363. 对于学校的“制度同构”或“组织同构”,新制度主义往往从“合法性”的角度对学校改革的新思维、新方法进行解释,把“合法性”作为学校改革的首要制度逻辑。学校改革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学校改革要遵循既有的“教育法律制度”,不能超越法律制度与政策规章的规范性限制,还要考虑包括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在萨奇曼(Suchman)看来,学校改革的“合法性”是“一种广义的知觉或假设”,是关于“一个实体的行为是可取的、适当的或适应于某些社会建构体系中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的,④ M. C. 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0(3),1995, pp.571-610. 成为教育改革不可超越的原则或制度逻辑。在学校改革的制度逻辑中,这种“合法性”有很多来源,包括来自政府管理机构的要求,如教育部的规章和政策;或来自于高校的入学要求及其考试形式;还会有来自于父母、学生、教师或劳工联合组织及同行机构的不同意见和利益诉求。对“学校制度”的合法性进行定义与解释,关系到并决定着学校制度自身的存在样式,特别是当这种具有“合法性”逻辑前提的学校制度,成为可获得广泛价值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工具的情况下,学校制度“合法性”的逻辑前提就更加难以撼动。⑤ M. C. 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p.575. 因此,学校改革制度创新的困难就在于,学校改革需要在利益格局的合法制度内进行,不能够挑战具有“合法性”前提的现代学校制度。
3.制度是组织交互作用的规则
新制度主义认为,学校组织内部的交互作用还会产生并加强共同的组织规范和教育实践,这种组织交互作用的规则在学校教育这一特定领域已经常态化,成为不可颠覆的“学校教育的语法”,现代学校“年级组织”的时间序列结构与“班级组织”的空间形态结构,对师生的互动行为起到了规训的作用,已经成为实行制度化教育的学校机构的标准配置,所有的“现代学校”都是以“年级”的时间序列和“班级”的空间形态进行着类似的教学工作,年级制度和班级制度成为现代学校组织交互作用的基本规则,是现代学校的深层制度规训。
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保时捷停在一起,似乎这应该是我所经历过最为热闹、令人热血沸腾的一次“家庭聚会”了。虽然没有什么丰盛的大餐或者醇厚的美酒,但不过是听着这些水平对置6缸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轰鸣,我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的确,这个特殊的家族令人魂牵梦绕,而在我看来,更令人感觉无法割舍的却是这个家族一脉相承的性能理念、哲学以及渴望。
“特许学校”对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压力,已经不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十校实验”改革的时候了,它所面对的制度压力更大、且更加多元,诸如大学入学要求、进行标准化测试、国家问责体系、无所不在的父母、学生和教师对学校的“真正期望”等,都成为学校教育改革最常见的障碍和抗拒性力量。不论是“八年研究”的实验,还是“特许学校”的改革,可以说,所有学校改革的核心困境都是学校如何“寻求组织‘合法性’的过程,以调整它们自身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构相适应”③ R.T. Ogawa, R. Crain, M. Loomis & T. Ball, “CHAT-IT: Toward conceptualizing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formal organizations”,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7, 2008, pp.83-95. 。如果“学校创新”被定义为是对教学实践的传统模式进行根本的修订或改造,那么即使教育组织拥有再多的创新自由,可以进行颠覆性的革新,而来自官僚部门和父母对学校教育“总体产出”的要求,特别是对学校测试分数的要求,都会抑制学校进行创新性的教学实践。
明显,作为历史存在的制度、作为合法性的制度、以及作为组织交互作用规则的制度,在教育改革与学校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当外界因素与内部动力进一步交互作用时,尤其是在面临学校改革创新的不确定性或学校危机的时刻,就创造了朝向“制度同构”和采取“平衡化”策略的进一步改革压力,学校改革的创新就面对着“制度同构”的困境。美国的“特许学校”教育改革运动和“八年研究”的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实验都显示,这种“制度同构”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政府和大学,也来自父母、学生、同行机构甚至教师的期待,仅仅试图去消除强制性的阻止教育改革的因素,而忽视其他相关制度性因素的改革,会使得学校改革制度创新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学校的真正改革必然要触及如何打破旧教育制度的体制,超越“现代学校制度”的合法限制,重构教育组织交互作用的规则。
二、“八年研究”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初次挑战:历史的批判与反思
“八年研究”(Eight-Year Study)亦称“三十校实验”,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PEA)1933-1940 年间在中等教育方面开展的一项学校调查活动和教育制度改革。PEA在“八年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挑战“现代学校制度”的创举,如支持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给教师更多教育自由、推行更加民主的课堂和支持学校进行社会变革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主义学校和课堂中,教师们强调更多的是教学民主,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注重进行教学探索和实验。践行这些教育哲学理念的“八年研究”,不仅着眼于现代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八年研究”是在致力于改变传统学分制学院的入学制度要求,以推动对公立和私立学校学生选拔制度的改革。参加实验的30所学校在高校招生中有特殊的选拔制度保障,进而激发了这些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实践。正如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困境,特别是普通高中多样化创新发展的困境,其背后是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桎梏,导致基础教育学校的创新发展异常的艰难,“高考工厂”盛行;只有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的解锁,义务教育学校的创新发展以及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特色发展和个性发展才有了“制度创新”的条件和基础。
1.“八年研究”的改革背景与改革目标
“八年研究”为了实现这些学校制度改革目标的方式也同样很直接,它选择一些美国高中及其毕业生,暂时地从通常的大学入学科目考试和单元要求的考查中脱离出来,通过校长推荐和根据学生学习记录的学业表现,决定其是否能够进入大学学习。被挑选参加实验的高中不仅要“足够出色”,而且要“具有良好的资金支持,教职员工富有改革热情”。可见,PEA在“八年研究”中对参加实验的30所学校实施了“规范性同构”和“强制性同构”的学校制度改革,要求“实验学校”按照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原则进行学校重构,并强迫它们为经济水平低的高中也承担起“模仿性同构”的责任,成为其它学校改革的样板。“八年研究”的学校改革实验是在美国民主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观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制度改革实践,是对“现代学校制度”进行挑战的初次尝试。
“八年研究”发现,美国中学教育“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核心的目的”,“不能使学生作为美国公民衷心感激他们继承的传统”① W. M. Aikin, The Story of the Eight-year Stud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p.2. 。艾金(Aikin)指出,美国中学的全部教育活动都应该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化身,任何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都不应偏离而应保持和促进美国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进步主义和杜威思想的推崇者都试图推翻“狭隘地强调测试成绩和学术科目”的一些大学和为之做准备的中学,正如我国当前的“衡水中学”模式和“毛坦厂中学”模式,其制度的根源也在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这种大学入学考试的制度“绑架”了中学的课程与教学。PEA致力于建立中学与大学的新型制度关系,允许和鼓励对中学的制度重构,通过探究和实验发现高等教育制度如何更有效地为年轻人服务② C. Kridel & R. Bullough, Stories of the Eight-year Study: Reexamin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 3. 。
对所提出的GOF策略的跳数增加和递交率减少问题给出了理论分析.在描述 fX(x)和 fY(y)水平给出一跳进度的概率密度函数.给出第一个一跳进度,通过fZ|X(z)获得Lane1的第二个一跳进度的条件概率密度函数.为了比较,分析了与GF的GOF相同的度量,即跳数和递交率的变化.
“八年研究”是美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进行的具有明确思想基础、严密实验组织构架的教育革新性实验。“八年研究”的初衷旨在对进步主义学校毕业生和传统学校毕业生在大学的学习情况作对比研究,以了解与分析两种不同类型学校的课程、教法的优劣,以论证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对于大学学习是否必不可少,以及进步主义学校的课程、教法是否同样能为学生升入大学做好准备。
2.“八年研究”对教学与核心课程制度的改革实践
然而在实际的课程改革中,很多学校选择的是只对现有课程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对现有的、分科的课程结构较少以“核心课程”的综合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改变。明显,核心课程体系的改革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推进措施,也没有“规范性同构”的压力,包括来自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所提出的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和实施教学的规范压力。因此在实验学校课程体系改革的现实中,很多学科专家只是为他们所教授课程选择了不同的教学内容,而课程体系本身从制度根源上仍保持着现状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八年研究”的这种情形在我国21世纪以来的“新课程改革”中也是存在的,“新课程改革”所主张的“三维教学目标”,在实际的教学中也由于高考制度的存在,而仅仅关注传统的单一“学科知识”教学目标。
教学与课程改革是参加实验的中学最大的改革核心。PEA主张进行“功能教学”,强调教学的核心不在于传授给学生“满意的结果”,而是让学生学会进行“满意地质疑”,因为学生感兴趣的是“真正的、即时的和个人的”问题。如何在学校中建立综合的课程体系,即“核心课程”,是“八年研究”的标志性主张。“核心课程”的主张试图整合孤立的学科领域,给学生“做中学”的机会,采取“主题教学”的模式,将“真实的社会问题”带到学校场域中进行思考与讨论。科里德(Kridel)和布洛(Bullough)对“八年研究”的核心课程的改革原则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希望“超越现存的学科障碍,兼容并包不同观点,鼓励从事不同的实践活动,包括进行合作规划、学习和教学。”④ C. Kridel & R. Bullough, Stories of the Eight-year Study: Reexamin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 p.150.
在“八年研究”的教育改革实验中,参与实验的中学共有三十所学校,涉及的大学有三百多所,这些实验学校根据大学招生部门的要求,并按照PEA的设想进行教学结构改革和全面的教育革新。这项教育改革实验尤其注重推进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做中学”,“教育完整的儿童”(educating the whole child),“培育创造性表达”,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以及进行学生主导式的教学。这项教育改革实验希望能够证明它们有能力教育学生在民主社会上成为有用的人、过有意义的生活,而非由于大学教育的选拔制度使学生的发展受阻而妥协。③ C. Kridel & R. Bullough, Stories of the Eight-year Study: Reexamin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 p. 30. 这些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方针和原则虽然是很宽泛的,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其中关于“教育是达成民主理想”的内容是具有灵魂性的学校改革主张,是能够确保实验学校不被强迫采用任何流于形式的改革议程,而是要采取民主的学校改革实践方式。因此,“民主立场”正是选择实验学校的基本价值依据,参加实验的学校也以实施“民主的教育”和“民主的教学”作为学校改革的内在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
在泛雅平台中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结合多媒体”教学模式,过渡到“MOOC—学生自主学习—开放式自学方式”的模式。将学生转移为教学中心的指导思想,通过平台实施“学+做”模式。通过“精讲多练”的形式调动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且强化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即上课实验合并在富媒体教学中同步进行,增加基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自主教学。[4]
美国教育历史学家泰克和库班对美国密西西比州、丹佛市等地的实验学校进行了大量的学校调查研究,发现关于真实世界的“主题教学”模式对学生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在丹佛的实验学校中,尽管学校支持“整合性教学”和“核心课程设计”,注重进行创新性改革实践,学校改革持续了十年以上,历经了几任学校负责人的更替,但教师和学校员工普遍感到精疲力竭,学校改革的努力最后却付之东流① D. Tyack & L. Cuban,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 p.101. 。科里德和布洛则考察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课程整合”改革,与丹佛学校课程改革的例子相似,都具有同样的改革艰巨性,不仅需要教师协同工作,还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科专家进行课程体系的重新定位,以及多学科知识之间的交互转化。
转售价格维持是纵向协议的一种特定类型。在该等协议中,上游厂商控制或限制下游厂商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条款和条件),而该等销售通常面对终端消费者。[注]韩伟主编:《OECD竞争政策圆桌论坛报告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根据其所指定的价格标准,大致可分为固定转售价格、最低转售价格和最高转售价格三种形式。最高转售价格维持对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并无损害,故而本文仅对固定转售价格维持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展开分析。[注]张骏:《完善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选择》,《法学》2013年第2期,第90页。
3.“八年研究”实验学校在“制度同构”压力下的妥协
“八年研究”对现代学校制度提出了挑战,从对实验学校学生的追踪研究来看,“八年研究”取得了成功,实验研究本身所要证明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进步主义教育原则在实验学校的实行,既能保证这些中学很好地完成“传统教育”的职责,完成了为大学输送合格人才的任务,又能为学生的多方面个性发展提供动力,而这一切的成就是传统的中学制度所难以达到的目标。
但“现代学校制度”的制度力量是巨大的,参加实验的学校最终没有超越“制度同构”的陷阱,而逐步又回到原来的制度逻辑中。在“八年研究”的教育改革实验中,有人批评“八年研究”随意抛弃了传统科目,只是在为一些特权人士的孩子取得有限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创新教育。PEA的实验研究也发现,来自进步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生的确比来自相同背景的传统学校的学生在大学中要更优秀。尽管“八年研究”的实验已经展示和证明了,传统的课程不是“唯一理智的和安全的教育计划”,但PEA也认识到,即使没有大学入学要求的限制和压力,“三十校实验”的教育改革也是“有缺陷的”,学校改革的创新路径常常被“社会风俗、经费瓶颈、自身惰性和冲突”所限制。② D. Chamberlain, E. Chamberlain, N. E. Drought & W. E. Scott, Did They Succeed in College? The Follow-up Study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Thirty Schools,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1942, pp. xxi-xxii. 进步主义的课程计划和改革创新使教师陷入了一种紧张状态,不仅体现在教师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新技术的掌握方面,也体现在学生自身的多样发展中。虽然这些困境并没有使实验学校的改革出现明显的偏离和屈服,但还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模仿性同构”的压力中,同时学校改革中的“规范性同构”也对实验学校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种教育改革“规范性同构”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实验学校内部的教师和同行的学校教育机构,而是更多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外部压力。
式中:τ 是选定的门限值。另外,正如Chi Y等[17]以及Konar A等[18]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假设,每个传感器节点的输入矢量uk,i 是由随机序列发生器根据不同的随机种子产生的,并且FC已知每个随机种子,从而可以同步复制每个传感器节点的输入矢量uk,i。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各个节点传输给FC的1比特数据{dk,i}来实现对未知参数w0的自适应估计。
拉维奇(Ravitch)认为,“八年研究”的信条是建设“核心课程”制度,其主要目标是以“核心课程”取代具有长期价值的、为成人意识形态服务的传统学科知识,而不再强调学科特有的知识③ D. Ravitch, Left Back: A Century of Battles over School Reform,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p.263-264. 。但很多家长声称他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加传统”的教育。在“八年研究”的实验初期,学校改革的主要阻力是反对把学校分成各自独立的部门和对学分制的轻视,对于这些问题和阻力,学校改革者最初也不甚清晰,三十校也未能做好应对的准备。由于家长的态度和教育实验前景均存在着不确定性,“模仿性同构”与“规范性同构”的力量继续推动着实验学校及其教师朝向“传统课程”的教学实践模式的回归。
虽然“强制性同构”在实验学校的课程改革中也一直保持其影响力,但父母对于非传统教学方法往往持担忧的态度。科里德和布洛的研究发现,家长会反对变化太大的课程。事实上尽管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新的,选择实验学校进行改革实验的目的也昭然若揭,但很多家长仍然担心学校教育中的“非传统方法”是否有效,他们时刻关注着那些不熟悉的“新教法”及其对教育结果的影响,并面对着与传统学校教育进行比较的“模仿”压力。尽管来自大学入学条件的要求,对三十校学生的招生采取了特别的政策和制度,减缓了实验学校的部分压力,但参加“八年研究”的三十所实验学校还是对其学生是否能够升入大学以及在大学层面的表现表示担心,学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始终要面对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外部压力。
“八年研究”的这些学校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今天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包括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21世纪“新课程改革”,以及“核心素养教育”的推进,特别是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特色发展、个性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警醒。在推行教育改革的创新举措时,父母和教师的期望与认识,以及他们所关心的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都会对教育改革的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制度同构”作用。
三、“特许学校”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再次挑战:诺言的诱惑与创新的困境
美国的“特许学校”教育改革运动是继“八年研究”对现代学校制度发动的再次挑战,它以更加猛烈的势力和更大的影响范围在美国各州掀起了“特许”的波澜,它以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希望以具有诱惑性的“特许”诺言和制度创新,打破“现代学校制度”的垄断地位,① 王超、程晋宽:《美国特许学校的运作机制及其效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3 第4 期。 并重建现代学校制度的办学规范与学校标准,改变“死板、机械与僵化”的课堂教学。基于新制度主义而不是进步主义原则的“特许学校”教育改革,相比较“八年研究”而言,明显已经超越了现代主义的思想限制,它不是把教育改革局限在有限学校的改革实验上,而是具有了得天独厚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和学校变革的“后现代转向”的趋势,“特许”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教育改革的想象”,影响范围更广泛,打破了现代学校的制度藩篱,学校已经开始超越“现代教育机构”的边界,不仅要与家庭加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要充分运用学区和学校所不具备的诸多资源,如可以让家长参与制定课程计划,学校的人员配置也不同于现代学校的招募与职业结构,学校注重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或托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但“特许学校”的改革诺言也与“八年研究”一样,难以逃脱“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
就业指导对于高职毕业生具有深远意义,可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努力提高就业竞争能力,教育学生把自身的远大理想和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学生鼓起勇气迎接就业挑战。
1.“特许学校”教育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与诺言
在“特许学校”的教育改革行动理论中,其核心原则是新制度主义,认为如果赋予学校更多的自治权,将会产生更多的教学创新,学校改革者就会主动地通过引进新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以进行学校课程与教学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但在许多“特许学校”中,传统的教学组织结构和教学实践模式还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特许学校内部的资金、组织结构及学校文化,也阻止着学校的教学创新,且其势头和影响力还在继续蔓延;来自多源头的外部压力,通常也会导致特许学校形成更多的“制度同构”,以满足大众教育消费者的预期,以及对同行成功学校的模仿,而不会去冒险采取具有“不确定性”效果的创新性教学实践。
“特许学校”的支持者认为,在市场中不受束缚的学校比受中央官僚体制控制的学校更具有创新性。正如萨拉森(Sarason)所指出的,特许学校是一种有别于公立学校的教育实体,这种教育机构需要教职员工从头开始创建学校的所有方面,包括学校管理体制与机制,学校人事与财政,以为潜在的、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机会,③ S. B. Sarason, Charter Schools: Another Flawed Educational Refor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pp.4-5. 特许学校的教师可以参与课程计划和创建新的学校治理模式。莫斯(Merseth, et al.)等人对几所成功的特许学校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这些学校不仅注重招募教师参与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制定,而且在组织结构、组织体系、组织文化和学校使命等方面也优于其他的学校。④ K. Merseth, K. Cooper & J. Roberts, et al., Inside Urban Charter Schools: Promising Practices Strategies in High-performing Schools,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09, p.18. 但对这些特许学校的研究也发现,组成一所“新”特许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事实上并不都是从零开始的,“新”学校里还有很多隐藏的“旧文化背景”,会对学校的改革与创新产生抵制,学校里所形成的外部压力通常也会抑制“特许学校”创新行动的出现。这种情境与“八年研究”具有相似的“历史重演”,在“八年研究”中,“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先行者被教了些什么,也知道教师会对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更加满意,也知道父母对子女的期望,父母的期望往往是建立在他们自己所推崇的教育方式上的。”① H. H. Giles, S. P. McCutchen & A. P. Zechiel, Exploring the Curriculum: The Work of the Thirty School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rriculum Consulta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p.69. “特许学校”的教育改革也面对类似的压力或者说“制度同构”,甚至在特许学校内部也存在着来自教师、父母对学校制度改革的抵制,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特许学校”的改革者自己也必须面对“特许学校”如何开展创新性管理工作的压力。
胫骨平台时对人体活动膝盖震荡进行缓解的关节面,能够保护膝关节软骨,因为该部位的解剖位置比较特殊,在车祸、外力冲击和跌落时容易出现关节内骨折。现代交通运输也和建筑业发展快速,因此临床中的胫骨平台骨折几率也在增加,为了进行分型和治疗,罗从风等[6]将胫骨平台分为外、内、后侧三柱。如果是复杂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合并三柱损伤患者,临床中双切口双钢板治疗难度较大,无法实现较好的复位效果,所以,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基于国家考试标准与绩效制度的强制性问责措施,实际上是通过“老办法”评价“新举措”的做法,这种情况在“八年研究”中也是同样存在的。在“八年研究”中,就有研究者指出,使用传统的考试方式选拔人才,以及为了进行“八年研究”和满足大学入学的目的,根据档案所记录的表现来推荐人才,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评判学校的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以及来评价一些传统的或非传统的教学改革实践是否有效,都是存在缺陷的。这两种教育评价方式在现实中已被证明都是有问题的,都破坏了对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支持,正如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改革,一方面是用“统一的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是还允许部分优秀学校采取保送推荐制度,这些学校虽然不是“特许学校”,却具有了保送学生升入著名大学的特许条件和资格。这种招生制度对中小学的教学制度创新产生了巨大的限制。
现代学校组织交互作用的规则对学校改革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和限制。迪马乔(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将这种“制度同构”的深层规训或规则分为三种基本形式:(1)规范性同构。规范是一种共享的观念或共享的思维方式,规范性同构的动力源自专业化的压力和职业的共同价值观等,凭借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制定并形成了必须遵守的同业规范;(2)强制性同构。强制性同构的源泉在于政府的规制与社会文化方面的期待,这些制度的力量不仅会将“标准化、规范化”强加在学校组织上,而且学校组织对“制裁的恐惧”也对学校行为产生一种强大约束性力量,同时,正式的外部压力,如政府的监管或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也成为“强制性同构”的外部协同力量;(3)模仿性同构。产生“模仿性同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在面临不确定的环境和问题并要为该问题寻求答案时,组织往往会通过同事间的互动进行模仿性学习,并会根据同一组织场域内其他机构或成员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采取类似的解决问题的方式。① P. J. DiMaggio & W.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2), 1983, pp.147-160. 这些现代学校组织交互作用的规则形成“制度同构”的合力,对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会产生巨大的抵制。
2.特许学校“制度创新”与“制度同构”的双重压力
“特许学校”的制度设计来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哲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弗里德曼认为,现代学校体系的改善,其动力来自于赋予父母选择学校的权利,在学校教育方面推行有竞争的市场行为,将产生更多的创新、更有责任感和更加高效。② D. Groshoff, Uncharted Territory: Market Competition's Constitutional Collision with Entrepreneurial Sex-Segregated Charter School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Law Journal, 2010, pp. 307-308. 这种基于自由市场的“特许学校”制度实践,最初发端于199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学校制度改革创举,在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势头强劲,逐步蔓延到美国各州,成为21世纪以来解决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新出路和新制度,但“特许学校”的制度改革在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后,也同“八年研究”一样存在着“诺言的诱惑”与“制度创新”的困境。
“特许学校”的制度创新与“八年研究”的实验一样,也在教师和父母这两个主要方面显示了对“规范性同构”和“模仿性同构”压力的积极回应。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创新中,有些人会问“特许学校”是否真的能够在学生的培养中提升其创新精神?④ C. M. Hoxby, “Would school choice change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38(4), 2002, pp.846-891. 研究发现,“特许学校”的制度创新,的确产生了一些对“稀缺资格要求”的需求增长,如对数学和科学专业知识及新技术的需求,人们对“特许学校”提供的“特殊教育资源”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但对于这种市场化的“创新需求”与传统的学科知识、学业质量的标准和正式的国家认证之间的关系仍需要重新评估,也就是说,学生“创新精神”的提升一定是特许学校的教学革新产生的效果吗?这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大部分特许学校在小学的课堂教学中主要还是采取“直接教学”的模式和传统的教学指导方式,大家所关注的“特许学校”对合格教师进行自由招聘的事情也是值得怀疑的,很多特许学校并不是真正地实现了这种教师自由招聘。⑤ K. Merseth, K. Cooper & J. Roberts, et al., Inside Urban Charter Schools: Promising Practices Strategies in High-performing Schools, p.47.
富勒(Fuller)分析了美国政治背景中“特许学校”的内部运行,发现父母对传统的教学仍持支持性的态度,反对“特许学校”表面的虚假教学改革,认为那种以“教”与“学”为核心目标的学校改革只是一种“装饰”,学校自治的要求与原则经常是被忽视的,① B. Fuller, “The public square, big or small? Charter schools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in B. Fuller(ed.), Inside Charter School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65. 父母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学校特色”上,如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学校的教育特色。父母对学校的期望是学校是否“适合”孩子而非是否具有“制度创新”。“特许学校”的独特制度设计,以及看起来它们是否是一所“真正的创新型学校”,都不是家长们重点关注的。虽然那些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所预想的“特许学校”的制度创新,制造了一所又一所具有“社会真实性”的学校机构,被统称为“特许学校”,但这种在理论上或理念上强调“由公众选择学校和由公众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特许学校”② J. Meyer & B.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p.343. ,实际上以“制度同构”的方式妨碍了学校进行根本的教学改革创新,更不用说建构一种“新型学校组织”了。这种特许学校的“强制性同构”,伴随着学校绩效责任和教育效果的不确定性,导致“特许学校”的教师也更加青睐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而不是革新性的教学方式,这也是家长们期望他们这样做的;尽管特许学校教师们的最初愿望是在教学中进行教学创新与教学改革,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具有鼓励教学创新的学校结构和学校制度,但都由于“制度同构”的力量而导致“教学创新”异常的艰难。
3.特许学校应对问责举措与国家考核标准的妥协
无论是美国各学区的公立学校,还是特许学校,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教学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学校的日常问责措施上都面临着一个实质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特许学校,基于国家考试标准或测试基础上的问责制度,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强制性制度”压力。当20世纪90年代“特许学校”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想到“标准化测试”会成为衡量现代学校之间的“制度性的强制标准”与“比较的工具”。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使用“普通测试”来比较学校间的差异和质量会带来教育市场的不确定性、紧张关系及更弱的创新。③ S. Davies, L. Quirke & J. Aurini,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Goes to Market: The Challenge of Rapid Growth in Private K-12 Education”, in H.D. Meyer & B. Rowan(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duc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103-122.
就像“八年研究”的三十校改革实验是以进步主义教育原则为依据一样,“特许学校”的拥护者也将其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行动放置在一个类似的、相当直接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中,他们以“特许的自治权”为动力,提供了推动“特许学校”产生教育作用和教育效果的学校创新的实例,以“对公立学校系统施加竞争压力”。然而在经过大致10年左右的教育改革与实验创新后,虽然“特许学校”的数量不断膨胀与蔓延,成为美国一些学区或州的学校改革试点,但特许学校的推广过程已经不再是学校教育改革创新的“实验室”,② P. Teske, M. Schneider, J. Buckley & S. Clark, “Can charter schools change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s?”, in P. Peterson & D.Campbell(eds.) Charters, Vouchers, and Public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0, pp. 188-214. 这种特许学校的流行潮流也同“八年研究”一样难以逃避“制度同构”的困境。
现代学校的考试标准和“问责措施”只是评价传统教学的旧制度主义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特许学校”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强调使用传统的学校评价方式来评价和判断“特许学校”个案的成功或失败。在特许学校个案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将“特许学校”放置于传统的教育评价形式之中,采用国家标准测试的成绩作为评判“特许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依据。这里的制度悖论是显而易见的,“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努力是以实现“解除升学教育目标的桎梏”为价值追求的,但却被传统的方式进行评价。如果“特许学校”由传统模式来评定,人们一定会质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评价是有意义的,特许学校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了开拓性的创新,或者特许学校只是想用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传统教育。测试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强制性同构”的压力,使“特许学校”的教育改革更倾向于寻求与传统做法一致的“制度同构”,这无疑将抑制“特许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实践。
生活世界的观念实质是探讨优良和最幸福的生活的观念。某种程度上,近代思想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向人自身的回归。而幸福本身依寓于世界的生活实践的基础,是人之生活的终极价值和追求,就如边沁所认为的“全人类的最大幸福是伦理和立法之本”的法律终极价值,因此,通过法律中人之形象“幸福人”的建构,可成为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出路,成为沟通法律系统和生活世界的桥梁。
计算知识的教学不能仅仅是由教师的课上讲授来完成,更要通过学生进行系统的计算练习来实现对计算方法的巩固以及计算技能的提高,这样方才可以让学生逐步实现数学素养的提高,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对自身数学知识体系的丰富,从而为后续的数学知识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石。通过将多媒体技术作为数学课堂的辅助工具,能够实现对有限课上教学时间的拓展,从而可以让数学教师能够使教学节奏更加紧凑。具体而言,小学生数学教师在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之下,能够直观地为学生展示更多的计算题和习题,如此将让学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练习机会。
总之,从“制度同构”的视角,我们发现在学校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同构”的压力是所有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挑战。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在推行或者是轻微改变“传统教育制度”的创新实践时,学校都要面对强烈的来自大学入学要求、学校成功的评判依据、教师的专业训练、家长和学生的期待等一系列的“规范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强制性同构”的压力,这些压力是“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共同难题。
四、如何打破教育改革“制度同构”的陷阱:制度创新的机遇与突破
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教育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特别需要以教育制度的创新实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走出一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路径,打破教育改革“制度同构”的陷阱,也不是没有时代的机遇的,在从工业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则迎来了新机遇。200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改革,无论是基于国家政策的“新课程改革”,还是基于生命教育理念的“新基础教育”学校变革,还是联合民间力量的“新教育实验”,以及无数的学校综合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也都面对与“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教育改革相类似的一系列“制度同构”的压力,正如吴康宁教授所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反思性的问题,而更加困难的则是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吴康宁教授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世所罕见,① 吴康宁:《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 年第12 期。 这其实也是世界教育改革必须共同面对的“制度同构”的难题。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面临着两个关乎改革伦理的问题,即改革应该如何既要坚守公立学校机构的公共性质,又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质”。② 《教育研究》编辑部:《2011 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教育研究》2012 年第1 期。 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困难重重,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同构”的压力,美国“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的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具有许多启示,教育改革需要打破“制度同构”的陷阱,抓住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制度创新的新机遇。
1.教育改革应充分考虑社会传统、制度惯性和社会批判施加的压力
“八年研究”对现代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挑战,“特许学校”则是作为传统公立学校的对立面和批判者的形象出现的,对现代学校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特许学校的倡导者对传统公立学校的教育垄断、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漠视学生需求和压抑学生个性等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们也没有提供能够体现“特许学校”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客观的和令人信服的教育改革成果。这样必然会招致传统公立学校的反击和一些中立机构的批评与质疑,从而造就了一个不利于“特许学校”自身发展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环境。③ 黄学军:《美国特许学校政策:论争与走向》,《比较教育研究》2010 年第12 期。 因此,在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包容”的程度,不能全盘推翻教育的传统做法,要采取“渐进式”的教育改革策略;同时,需要关注社会传统、制度惯性和社会批判对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需求。
2.注重学校教学制度创新,突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
“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的改革都强调了学校教学制度的创新,但要推动学校的转型发展还需要超越放权与择校的发展逻辑,④ 程晋宽:《现代学校转型发展的制度逻辑与路径选择》,《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 年第3 期。 注重从最容易、也是最基本的“学校教学制度”的创新做起,以教学制度的创新推动学校的全面转型发展和制度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基于数据的、可穿戴的智能设备,以及体验分享的教学,正在改变着学校的教学制度。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学校具体教学事务创新的直接干预,为智能时代的创意教学提供空间,因为“行政本位型的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社会参与教育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单一”;⑤ 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9 期。 其次,改革学校课堂教学制度,实施供学生和家长选择的智能化课程方案和教学计划,明确学生的数据化、智能化学习定位,积极主动与家长合作推广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提倡教职员工在教学中使用大数据、云算的新教学技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智能化教学目标的设计等;再次,改革传统科目的知识授课方式,实现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学生可以通过按一定学业标准和能力分组的教学方式,而不只是传统的按年龄进行分级教学,以增加智能化教学制度的弹性。
3.建立学校合作文化氛围,形成学校改革合作关系
在“八年研究”中,艾金就认识到,美国高中的突出问题是学校缺少共同的目标及教师各自为政的教学方法。这种作为个体劳动的教学现象是学校组织的基本文化特性。“特许学校”的研究也发现,更强大和更成功的学校办学特色不仅是对外部社会责任的成功回应的结果,而且还包括具有学校内部文化整合的责任意识① R. F. Elmore, School Reform from the Inside Out: Polic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9. 。“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的教育改革都证明了,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学校不仅需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的,建立学校内部合作的学校文化,而且需要形成学校改革的外部合作关系和制度创新的文化环境。这种“基于合作关系建立”的教育改革经验具有借鉴价值,学校改革需要重视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内部与外部及相互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形成。
4.重视社会参与的学校改革,发挥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
学校教育机构如果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并进行创新性的改革实验,其核心参与者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仅教师的教育观念要更新,而且要重视家长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民众的教育改革创新智慧。艾金在对“八年研究”的总结中指出,缺少父母参与的结果一定是父母的误解,及最终对学校改革的责难。“特许学校”虽然享有相对较多的自主管理权力,相比传统公立学校而言,由于没有学区的管理限制,具有教学创新的土壤,但如果要取得学校改革创新的成功,能否有效地吸引学生和家长的社会参与至关重要。② W. M. Aikin, The Story of the Eight-year Study, p.128. 父母的“真正参与”意味着民众对教育质量和结果的保障,他们会以创新的智慧推动学校的创新发展,同时他们也会对社会投入进行监督。正如吉尔斯和哈格里夫斯(Giles& Hargreaves)所指出的:学校“真正成功的改革创新必须是持续的创新,需要通过赋予家长和教育组织以参与的自主权利,学校改革需要采取整体的、灵活的、团结的和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持续的措施”。③ C. Giles & A. Hargreav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ve schools as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during standardized reform”,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vol.42(1), 2006, pp.124-156. 也就是说,进行制度创新的学校改革必须是一所能够充分体现教师和父母自身改变愿望的学校,就这一点来说,学校改革的制度创新之举,应当始终是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的体现。
喵星飞鼠大使哪里肯放弃这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他抖动双翼,向镜心羽衣冲去。壶天晓见状,拼尽全力,再次闪移到敌人面前。而飞鼠大使的翼膜像一把扇向蚊子的巨扇,壶天晓被猛地一下掀翻,狠狠地撞向岩石。
Why i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So Difficult?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of Eight-Year Study and Charter Schools
CHENG Jinkuan, FANG Zhengzhe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reform is the exploratory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modern public schools has been centered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free schooling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eight-year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charter school reform in practice face the similar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f the influential educational reform practices of the eight-year study and charter schoo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istorical values and implications, including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modernis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why to make compromis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resistance of institutional forces. This has led to an explosion of new ideas for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s an inescapable trap for all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should als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compulsory isomorphism, normative isomorphism and imitative isomorphism.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pressure of institutional inertia, highligh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m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school refor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wisdom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eight-year Study; charter school;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程晋宽,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 210097);方蒸蒸,教育学博士,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2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规划项目“创新发展视野下美国高中多样化发展路径研究”(17YJA880013)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程天君)
About the authors: CHENG Jinkuan,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Fellow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FANG Zhengzheng,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Nanjing 210023).
标签:“八年研究”论文; 特许学校论文; 制度同构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论文;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