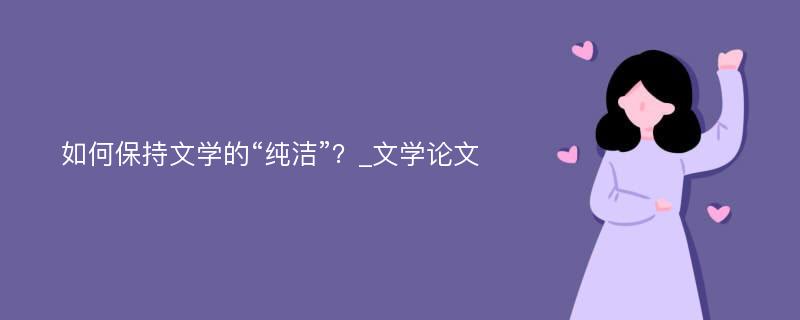
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文学》从今年第三期起接连几期讨论八十年代提出的“纯文学”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对纯文学现状的关注。纯文学在今天备受冷落是不争的事实,众多文学刊物风光不再,面临生存困境,只维持着极少的订数,前几年更有名重一时的《小说》《昆仑》停刊。造成纯文学不景气的原因很多,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而纯文学的创造者们却总是一副怨天尤人的模样,抱怨没有创作自由,抱怨经济浪潮的冲击,抱怨读者层次太低,自己搞的“纯文学”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却往往忽视了从自身找原因;殊不知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作家自己封闭了“纯文学”的接受之门。
“五四”以后把用形象的手段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统称为“纯文学”,表达了人们进行更高级精神活动而挣脱现实政治、物质束缚的欲求。
“纯文学”概念事实上由来已久,至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有相似提法。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很宽泛,还包括了哲学和历史,所以自“五四”以后把用形象的手段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统称为“纯文学”,以与哲学、历史区分开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泛意义的文学等同,这当然也就不似今天的文学有高下纯俗之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纯文学”的意义也有了很大变化,那就是要提升文学的品格、增加文学的艺术含金量,要让文学向着更高、更好、更美的方向发展。“纯文学”成为一个衡量文学艺术价值高下的尺度,表达了人们进行更高级精神活动而挣脱现实政治、物质束缚的欲求,指陈了人们对纯正文学、对高雅文学、对严肃文学的向往,标示着作家努力的向度。以“纯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被重新提出来看,在当时的语境里,它表明在经历了政治粗暴干涉文学、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时代后,作家希望能够自由表达、畅所欲言,希望文学能体现出自己应有的独立品格,而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承载说教的工具。这种用心是对的,也是好的。纯文学截然与那种低俗的不入流的文学、以及那种奴颜婢骨、媚政治之“俗”的文学分流对立,是文学观念获得进步获得解放的表现,它是对文学的重新诠释,表示着一种“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纯文学”被重新提出以后,作家在认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以为文学与现实、时代、百姓贴得近了,文学就又被这些“俗”物玷污了似的。结果,文学创作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作家不再关注“写什么”,而是关注“怎么写”,他们过度地玩弄技巧、卖弄手段,文学在“向内转”、回到本体的同时,成了纯粹形式的东西,变得空洞无物。以纯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代表先锋小说家为例,他们由于现实生活资源的严重匮乏,更津津乐道于叙事和着迷于形式的表演,而放逐了情节,语言成了小说的主体,小说沦为词藻的世界。马原毫不讳言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观察的热情和把握”,“缺乏透视能力和归纳的逻辑能力”,因而更习惯于设计叙事的圈套,把彻头彻尾的“虚构”视若小说创作的至宝。余华则表示,日常经验的真实尺度对他已经失效,他所迷恋的只是“虚伪的形式”,所以在他的许多小说如《现实一种》《古典爱情》中对血腥暴力场面的描写细腻到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叙事者对残暴却表现出惊人的嗜好和冷漠,显然这种叙述是使作者获得快感的动力源。由写诗而转向写小说的孙甘露无比地推崇语言,随意驱驾、拼贴、组合语言,语句不合乎逻辑,晦涩难懂,他的小说《信使之函》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有五十多个关于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定义,小说只不过是华丽语词堆砌的楼厦。先锋作家把文学作为智力的活动,刻意于营造结构的叙事迷宫,小说成为可以随意组装和拆解的智力魔方,格非的《褐色鸟群》无意理顺故事之间的前因后果,而是着迷于通过亦真亦假的叙事,追求真实与梦幻之间含混莫测的效果。在叙述时,先锋作家更注重感觉化,这种感觉往往是想当然、不真实的东西,洪峰《奔丧》中“我”在听到姐姐告诉的父亲死亡的讯息时,竟然无动于衷,倒是对姐姐的一对乳房发生了兴趣;格非《风琴》中,丈夫在目击了妻子遭日本兵的凌辱情形时,居然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奋。尽管这些感觉被作家描写得细致入微,但显然都不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完全是作家凭空杜撰的产物,掩饰不了作者事实上叙事的苍白和想象的贫乏。
时下文学的“贫血”和纵“欲”无度的情形正是作家精神深度被削平后的表现。当文学只剩下“性展示”时,这能不是我们文学的悲哀?
在书写内容上,作家往往对现实视而不见,而是逃遁到历史中去,这并非为的是通过观照历史指涉现实,而是因为“历史”更便于掩盖他们生活经验的匮缺,“历史”更便于他们放纵幻想虚构的野马。一时间,土匪、官绅、妓女、姨太太这些历史的沉滓泛起,在他们粉墨登场纵情表演独角戏时,文学的现实关怀精神荡然无存。即使不进入“历史”,作家也只两眼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门心思写自己的陈芝麻烂谷子,充满了强烈的自怜自恋情结。在全然退回封闭的个人天地后,大肆贩卖纯粹个人的喜乐哀痛,再没的东西可写了,当然只有“身体写作”了,就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一镜在手,专门照自己的隐秘部位。于是我们看到时下小说通篇充斥着触目惊心的与“性”有关的情节:《孙权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为都市里弥漫着的情欲所包围而一天三次手淫;《强暴》中的丈夫与别的女人通奸,妻子由最初被人强奸到后来的主动卖淫;《疼痛与抚摸》中充满着偷情、卖淫甚至女性渴望被强奸的描写;《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则一而再地渲染女主人公的自慰;《关于性,与莎莎谈心》也对性表现了过度的关切,大言不惭地向莎莎发问“告诉我,什么时候你有了性的感觉”之类肉麻的问题;贾平凹这些年的文艺创作,不论是《废都》,还是《白夜》《高老庄》都充斥着对男女性事的描写,这些描写成为其小说叙事的动力,即令晚近的《怀念狼》也要靠痴迷女色的烂头的荤事荤话来维持小说的盎然生机。这种“无性不成文”的情势,实际上是文学精神萎缩、作家叙事资源匮乏的表征。且不说前两年被禁的《上海宝贝》那种无节制地兜售性的低劣读物,即使这两年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尽管有收敛,但还是在展示赤裸裸欲望的层面上不停地滑动,像《四如意》《一天一日》《圈》等就通篇讲述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打情骂俏,男人对女色无休止的追逐,女人因为相貌丑当不了妓女便写小说、甚至写不下去了还要靠性交来体验生活一类的故事。文学作品中的人只剩下了动物性,有欲无爱,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动物还有专门的发情期,人却是男女在一起,便只有性游戏了,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会出现萍水相逢的女人莫名其妙地跑到“我”的床上供“我”享用的情节(《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会有男人们一天到晚寻找艳遇、并相互交换买卖情人追求感官刺激,乃至于有以搜集各种女性阴毛为乐事的恶劣情节(《此人和彼人》)……我们的文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只是肉体的洋洋大观,只是各式常规异态的性交姿势、同性恋多角恋窥淫乱伦自慰的指南?这样的“纯文学”已经抛弃了人文关怀精神,与庸俗文学相差无几。时下文学的“贫血”和纵“欲”无度的情形正是作家精神深度被削平后的表现。文学以消解诗性为代价,总是纠缠于男女的脐下三寸,这既是作家的精神自慰,也是作家对读者的精神亵渎。当文学只剩下“性展示”时,这能不是我们文学的悲哀?当作家在远离社会生活和读者的情形下制造出这些庸俗色情的文字垃圾时,事实上也以作品中散发的恶臭腐朽的气息将读者逐出了看台。
“纯文学”的提出,表明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传声筒”,毋庸置疑,这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文学就可以告别意义,拒绝教益,规避责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曾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的附庸和仆役。事实上,我们知道,文学是不应该从属于政治的,是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但政治总要想方设法渗透入文学中,对文学发号施令——也许就是这种悖论的关系,文学有了反抗外来压力争取自身伸展空间的动力,压力有多大,追求自由的动力就有多大,文学的抗争精神和独立意识就有多强。提防和反抗异质对文学的侵入、政治对文学的强暴的斗争,在二十世纪一直或隐或显地持续着。“纯文学”的提出,表明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传声筒”,毋庸置疑,这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文学就可以告别意义,拒绝教益,规避责任。现在的情形恰恰是,作家们在把洗澡水泼掉的同时,也把婴儿扔掉了。所以即使在那些相对要纯净一些的作品中、肉欲的气息要少一些的作品中,我们还是感到了文学精神的贫困,发现不到文学中存在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这正是拒绝了文学意义和逃避了文学使命的结果。例如,《织网的蜘蛛》以男性的视角不无得意地写到这位“蜘蛛”是怎样织网,猎捕多个女人并同时周旋于这多个女人之间的。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禁困惑,这样的作品意义何在?作者究竟想宣谕什么?《东张西望》《下个世纪见》写的是边缘人一天到晚的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拿王朔在其中一本书序言中的话来做此类作品的评语倒是很恰当的:“它符合我喜欢的那类小说的全部条件: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逮谁灭谁、相当刻薄”。不难发现,文学拒绝了承担,也就失去了分量,放逐了精神,也就失去了内涵,充其量只是一堆轻飘飘软绵绵、无关痛痒的东西,只是一次性的文字消费品罢了。
我们不该忘记,在文革之后,大众对文学的接受热潮曾经持续高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乎每出现一部重要的作品都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和讨论热情。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作家在作品中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积极介入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和阅读热情,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和那个时期的文学相比,我们今天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都不知有了多少倍的提高,文学可表现的范围已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可是读者的反响却远不如八十年代那个令许多人缅怀的文学的黄金时期,这能不令我们深思吗?今天,反腐题材作品能一再激起读者的阅读高潮也正雄辩地说明了读者对文学的热情并不减于当年,同时佐证了文学需要对现实介入、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期待。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要依靠读者的参与、阅读来延续的。千古传诵的诗词曲赋能保持旺盛不衰的生命力,就是依靠不同时期众多读者的代代阅读所达到的。很难相信,仅仅靠文学史家象牙塔内的编撰文学史就可以使一部作品千古不朽——即使真的就存在于那样的史册中,而事实上作品本身乏人问津,那又与干枯的植物标本有什么不同?读者大众的阅读参与才会使一部作品变得完整,并延续丰富它的生命。需要看到,“纯文学”观念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向作家呈示了更高追求目标的同时,又使作家及其文学与一般读者拉开了距离。所以,如何在作家、文学与读者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使作家既能保持作品的艺术水准,又能赢得相当的读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作家如何得享这“齐人之福”的确让人颇费思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作家采取对现实漠视、对自我重视、对读者蔑视的高高在上的创作姿态,一旦文学仅是沉溺于形式的营造,或者在内容上拒绝传递任何现实讯息、拒斥一切“非文学杂质”的侵入,则纯文学势必成为看不懂的文学,纯文学的路只会越来越窄,追随纯文学的读者只会越来越少。一部作品如果不能在广大读者那里产生回响,又怎么能指望它遗传后世?文学的“纯”又靠什么来维持?可喜的是,我们今天许多文学杂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好看”与否来要求小说(且不论这种文学具体的艺术水准如何),就体现了对读者的召唤和重视。今天俗文学也能堂堂正正走进文学史中,也正是文学研究者打破旧有纯文学观念,消弭纯文学、俗文学之间界限的有益尝试。
当某些作家打着“纯”的旗号、把文学变为个人的搔首弄姿、自娱自赏的工具时,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大众的排拒、文学的危机就在所难免。
当某些作家打着“纯”的旗号,把文学变为个人的搔首弄姿、自娱自赏的工具时,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大众的排拒、文学的危机就在所难免。某些作家在具体写作实践中一意孤行地追求个人的高蹈、抛弃放逐了读者时,“纯文学”就成为了一堵墙,一道藩篱,隔离了作家与大众,阻断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联系。而文学要健康地发展,就要拆毁推倒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这座厚厚的“墙”。我们今天讨论纯文学,深层内涵在于探究作家应如何摆正自己与读者的关系。当文学只是作家玩耍的叙事游戏,仅仅成为他们娱乐消遣宣泄情感的工具,或者仅仅成为催人情欲的“春药”时,这与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同样是文学的堕落。文学应该参与到时代的大变动中,感受现实的脉跳,慰抚人的心灵,文学应该裨益于人精神的提升、社会的进步,文学应该是一盏明灯、一簇圣火,照亮人前行的道路,驱散人内心的黑暗。只有这样的强烈关注现实生活、致力于成为人精神支柱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纯”的范本。当读者大众再次被视作“引车卖浆之徒”,被视作平民、贫民时,当文学被自封为贵族的作家操持在手中自说自话浅吟低唱时,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再像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先驱那样振臂高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