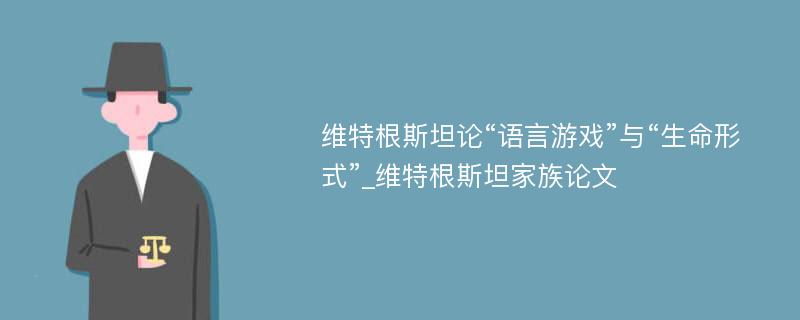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形式论文,语言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两个重要概念“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作者首先述析了维氏提出它们的具体路径,然后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并给出了自己的规定;接着探讨了它们在维氏后期哲学及其整个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作者还特别指出了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更广阔、更深沉的价值——文化意义——它们为价值—文化的相对论多元论提供了根据。
关键词 游戏 语言游戏 生活形式 家族 相似性
1
“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他后期哲学的灵魂。它们分别是作为对他的前期语言观和世界观的批判而提出的。
二十年代末以前,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结构,这个结构是: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它是所有命题的总汇;所有命题最终都可归约为基本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是由简单符号——名字组成的,是名字的一定方式的结合。同样,我们的世界(事实世界,或者说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也具有相应的本质结构: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是所有事实的总汇;所有事实都可归约为基本事实,都是由基本事实复合而成的;基本事实则是由对象构成的,是对象的一定方式的结合。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本质结构上的共同性才使得语言可以描画(描述)世界,命题可以是事实的逻辑图像。而我们的思想活动又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语言的确描画(描述)了世界,命题的确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此维特根斯坦便得出了他的下述语言和世界的本质规定:语言是由所有描述事实的命题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世界是由所有可以为命题所描述的事实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以后,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他以前关于语言和世界的上述看法过于独断,不符合我们的语言和世界的实际。实际上,我们的语言并没有他以前归给它的那种本质结构(逻辑结构):并非所有命题都可归约为基本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并不存在他以前所说的那种以互相独立性为特征的基本命题和作为语言的终极结构元素的名字。同样,我们的世界也不具有他以前归给它的那种本质结构,因为并不存在他以前所说的那种以互相独立性为特征的基本事实和作为世界的终极结构元素的对象。以这种批判为基础,维特根斯坦便最终抛弃了他前期关于语言和世界的本质的规定:语言并不是由所有描述事实的命题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简单)或高级(复杂)、功能各异、彼此间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Sprachspiele)组成的异质类聚物;世界并不是由所有可描述的事实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各样、作用各异但又互为前提、互相交织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en)组成的异质类聚物。那么,维特根斯坦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的呢?
2
为了弄清楚维特根斯坦是如何使用“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的,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他是如何使用“游戏”这个概念的。按一般的理解,游戏这个概念是有着比较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的。它通常指以娱乐为目的、具有对抗性因而也就有输赢(其输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戏参加者的技巧和运气),并且按照确定的规则、在界限清楚的场地(如棋盘、球场、拳击台等等)上进行的有始有终的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规定过于简单化,它并没能囊括游戏一词的日常用法的全部。因为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娱乐为目的;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有对抗性或输赢,而对于有对抗性或输赢的游戏而言,也并非它们的全部的输赢都取决于游戏者的技巧和运气;也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在有限的空间(界限分明的场地)或有限的时间内(有始有终地)进行的;最后,也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按照固定、精确的规则进行的,并非游戏的处处都有明确的规则对其加以限定。因而并不存在人们称为游戏的所有活动所共具的东西。换言之,游戏没有什么本质特征,我们并没有关于游戏的一般概念。〔1〕
不过,尽管在我们称为游戏的那些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本质特征,但它们还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关联在一起,并因之而形成了一个大的(游戏)“家族”。正如一个家族的诸成员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一样,诸游戏之间也有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将这种相似性称为“家族相似性(Familienǎhlichkeit)”。下面我们就看一看他是如何解释这一概念的。设想有一个具有下述谱系的家族:该家族的祖先是A和B,他们的儿女是AB[,1]和AB[,2];而AB[,1]和AB[,2]又分别和C、D结合,他们又有了儿女AB[,1]C[,1]、AB[,1]C[,2]和AB[,2]D[,1]、AB[,2]D[,2];如此类推。AB[,1]和A可能是体格上相似,而AB[,2]和A则可能是面部特征上相似;AB[,1]C[,1]]和AB[,1]则是气质上相似,而AB[,2]D[,1]和AB[,2]则是步态上相似;另外,AB[,1]C[,2]F[,2]虽和AB[,1]C[,2]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与B 便无什么相似之处了;AB[,1]C[,1]E[,1]虽和AB[,1]C[,1]还有相似之处,但和A 却无明显的相似之处了。也就是说,虽在直接相邻的两个成员间(即父子或母子和同父母的兄弟姐妹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而在只具间接的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间则不存在着什么明显的相似了(当然,不排除“返祖现象”)。由此看来,并不存在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所共具的特征。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称为“游戏”的诸多活动便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家族。“我认为‘家族相似性’这个词绝好地刻画了存在于众游戏之间的相似性。因为存在于一个家族的诸成员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体格上的,面部特征上的,眼睛颜色上的,步态上的,气质上的,也是以这样的方式重叠交叉在一起的。——我要说:‘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2〕
由于我们并没有一个关于游戏的一般概念,并不存在什么人们称为游戏的诸多活动间所共具的东西,在它们之间仅存在着家族相似性,所以游戏概念并不是一个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的概念。因而它的外延也是不确定的:一个活动究竟是不是游戏我们并非总能事先就加以确定。“但是,我们的确称很多东西为‘游戏’,称很多东西不是游戏的啊!……——不过,确定所有我们称为游戏的东西与所有其他东西的界限并不很重要。对于我来说,游戏就是我们所听说过的,我们可以列举的那些游戏,而且或许还包括按照类似性而构造出的那些游戏。……因此,我便将处于我们列举游戏时所开列的清单之上的东西称为‘游戏’,同时也把与这些游戏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的东西称为游戏(至于这种相似性的程度需要多大我不能给出更进一步的规定)。此外,我还保留在每种新的情况下就某种活动是否属于游戏而作出决定的权利。”〔3〕
在对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有了一定的把握后我们便可以讨论他的“语言游戏”概念了。自从二十年代末重返哲学舞台后,维特根斯坦便一再地将语言比作游戏(更准确地说,是将“使用一个语言或其部分”比作“玩一种游戏,如下棋”。〔4〕)具体说来, 他是这样做的:将语言的语词比作游戏(如象棋)的元素(棋子),而将游戏的一个步骤(棋子的一个走法)比作一个命题。后来, 他干脆就将“语言”(Sprache) 和“游戏”(Spiel)二词合而为一, 构造出了“语言游戏(Sprachspiel)”这个复合词。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游戏呢? 在《蓝皮书和棕皮书》中,维特根斯坦给出了如下简明的描述:“语言游戏是比我们使用我们的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的符号的方式简单得多的使用符号的方式。它们是这样的语言形式:一个小孩就是经由它们而开始使用语词的。对语言游戏的研究就是对语言的原始形式或者原始语言的研究。”〔5〕在《哲学研究》第2节他给出了这种语言的一个实例:“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语言……:它被用作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的交流手段。A正在用建筑材料建造一幢房子。这里有:方石、柱子、 木板和横梁。B的任务是按照A需要的次序将这些建筑材料依次递给A。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一个由下面四个语词构成的语言:‘方石’、‘柱子’、‘木板’和‘横梁’。A喊出这些语词后,B便将他已经学会听到这个喊声便需将其拿来的那块材料拿给A。”〔 6〕接着,在第7节中,他写道:“在语言(2)”〔这里以及后面所说的“语言(2)”特指《哲学研究》第二节所描述的语言〕的语言实践中,一方喊出某个语词,另一方便按其行事;但在语言课上所发生的则是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命名对象。这就是说,当老师指向一块材料时他便说出指称它的语词。这里,甚至还会有更为简单的训练:学生跟着说老师说过的话。无疑,以上两个过程都是与语言相似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将在语言(2)中所涉及到的语词使用的整个过程看作是孩子们借以学习他们的母语的诸游戏中的一种。我将称这些游戏为‘语言游戏’,而且有时也将原始语言称为语言游戏。人们也可以将建筑材料的命名过程和刚说过的语词的跟说过程称为语言游戏。想一想在围圈跳舞游戏中人们对语词所作的种种使用。我也将由语言和它交织于其中的那些活动所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7〕不难看出, 如此描述的语言游戏概念有如下特征:
(1)语言游戏首先是一种语言,不过是简单的或原始的罢了。
(2)每个语言游戏又都是对语言的一种使用, 而这种使用粗略地讲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语词或命题的说出或写出过程(行为、活动)(这种说出或写出过程既可以是指向他人的也可以是指向自己的)和由这种过程(行为、活动)所引起的(语词或行为)反应或由其所完成的活动,因而每个语言游戏实际上都是由语言表达式和人们借此而完成的或由此而引起的行为(活动)两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3)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 在这样的语言游戏中语言表达式起作用的方式是清楚明白的。
(4)每一个这样的语言游戏都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在下述意义上它们都是完全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存在着(或存在过)这样一个社会(如原始的社会状态中的一个部落),在其中语言(2)是他们的唯一的语言系统,正如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或存在过)这样一个原始部落,在其中只运用原始算术,即类似这样的算术:其中只使用五个数字(1,2,3,4,5), 而对超过五个的东西他们就用“许多个”一词笼统地加以指称。〔8〕
显然,如此描述的语言游戏概念的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综观维特根坦斯的后期著述,我们看到,他对这个概念的实际使用要远比这宽泛、总括。这不仅仅指上面所说的那种原始形式的语言或原始语言(或其部分)和它们的使用所完成或引起的活动的有机整体,而且也指我们现在实际使用的远为丰富和复杂的日常语言或其子部分和它们的使用所完成或所引起的活动的有机整体。因而,它既可大至我们的语言的一切使用,又可小至它的某一个表达式的某种特殊作用。另外,诸语言游戏的功能也是非常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它们既可以描述、报道事实、传达思想,又可用以发布命令、作出假设、提出问题,还可用以抒发感情,……等等。最后,我们称为语言游戏的东西也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生灭灭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说,新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不断地出现而其他类型的语言和语言游戏则逐渐变得过时并被人们遗忘。”〔9〕因而,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千差万别的。 我们不妨“从下面这些例子以及其他的例子中观察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发布命令,并按其行事;按照外观或者按照度量描述一个对象;按照一个描述(草图)制造一个物件;报道一个事件的经过;对一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作出一个假设并对之进行检验;以图表的形式描述一个实验的结果;编一个故事,读这个故事;演一出戏;唱轮舞曲;猜谜;开一个玩笑,讲述这个玩笑;解一道算术应用题;将一篇文章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请求,感谢,咒骂,打招呼,祈祷,等等, 等等”〔10〕。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是否所有语言游戏都是按照固定、 精确的规则进行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我们上面在讨论游戏概念时已看到,尽管所有的游戏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的,但并不是每一个游戏的处处都受到了规则的限定,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按照固定的、精确的规则进行的。对于语言游戏而言情况也是一样。诚然,所有语言游戏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很多语言游戏还是按照固定、精确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包括: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词法和句法规则;关于它们的语义规则;以及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关于它们的使用的一些特殊的约定(语用规则),等等。那么,是不是每一个语言游戏的处处都有明确的规则对其加以限定,是不是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按照固定、精确的规则进行的呢?对此维特根斯坦给予了断然的否定回答:“我要说,语词的应用〔即语言游戏〕并不是处处都受到规则限定。”〔11〕“假设你在看人们打球。当你看过了很多这样的游戏后人们让你写出这种游戏的规则。我们必须承认,就通常的游戏而言,你在一段时间后是能够做到这点的。不过在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和不按规则而只是盲目地进行的游戏之间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过渡的。就我们的语言而言,情况也一样,既存在着经过观察便能清楚地看出其使用规则的语词,也存在着经过观察我们还不能清楚地看出其使用规则的语词。”〔12〕
以上的讨论说明并不存在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游戏的众多的活动所共具的什么东西,换言之,语言游戏无本质,它缺少定义性特征。因而,维特根斯坦断言,真正说来我们根本就不能给出语言游戏概念的定义,而只能通过一系列例子来例示它。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上面引述的他在《哲学研究》第7 节给出的语言游戏规定就不是定义而只是例示式的说明。而且,在他看来,“这种例示法(das Exemplifizieren)并不是在缺少更好的途径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间接的解释方法”〔13〕,而是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解释方法。
不过尽管在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语言游戏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但在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相似性的,而且它们彼此相似的方式是交叉重叠的。正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我们才得以用同一个各称去称呼它们。“我不想给出被我们称为语言〔语言游戏〕的所有东西所共同具有的什么东西,则只想说:并不存在所有这些现象所共具的什么东西,因为它我们才使用同一个语词去称呼它们。不过,在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种亲缘关系或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把它们都称为‘语言’〔语言游戏〕。”〔14〕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游戏间彼此相似的方式和被我们称为游戏的诸活动间彼此相似的方式是相同的。上面我们看到,全是用“家族相似性”来形容诸游戏间的相似性的,因而我们便可以说:语言游戏间所具有的相似性是一种家族相似性。
3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那么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生活形式”概念的呢?正如对“语言游戏”概念一样,他对“生活形式”概念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他也不企图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有关这一概念的定义性特征)。不过,从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中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内涵的,这就是: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因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生活形式”概念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思想行为的总体,又可指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之一部分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社区、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总体或局部。这些或大或小的生活形式的作用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它们又互相影响、互为前提,根本说来,它们是互相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此外,生活形式还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一种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这是由一系列实践活动构成的;其次,任何实践,因而任何生活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都以特定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为前提,因而任何生活形式都构成了人类自然史之一部分;最后,人们的任何概念活动都可在生活形式中找到其最终的根源,都以特定的生活形式为根据,而生活形式本身则是其自己的根据,它不需要其他的根据(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能为它提供根据):人们就是这样生活、这样行事的。“说我们的概念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正确的吗?它们站在它之中。”〔15〕“不得不接受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说就是生活形式。”〔16〕正因为一切概念活动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的,所以人们在概念活动上的一致也就必以生活形式的一致为基础,而不同的生活形式便会引起不同的概念活动。“我要说: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会为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概念提供基础。”〔17〕“因为这里人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这里,不同的概念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事实上,根本说来,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不同的概念才成为可想象的。”〔18〕
4
通过第2、3节的分析和介绍,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这两个概念的引入在他的后期哲学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借助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概念, 维特根斯坦终于认清了我们的语言和我们所居处于其中的世界的“本来面目”:语言并非是由单纯描画或描述事实的命题组成的单一构造物,而是由丰富多采、功能多样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同样,世界也并非是由单纯的事实组成的单一构造物,而是由丰富多采、作用各异的生活形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这也就是说,作为我们的日常语言的基本构成成份的、能够相对独立地表达或传达意义的最小单位的东西不是单个的命题,更不是什么语词或名字,而是语言游戏;同样,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的基本构成成份的、能够相对独立地具有意义(这里特指人生意义)的最小单位的东西不是单个的事实,更不是事物(对象),而是生活形式。
(2)“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作用使维特根斯坦更进一步认识到了语言现象的社会本质:语言归根结蒂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生活现象。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是如何对此进行论证的。
A.语言游戏的诸规则都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
首先,一个语言游戏的任一表达式究竟是语词还是命题;而如果是语词它又属于什么样的词类(是数量词,还是名词、连词等等);如果是命题,它又是什么样的命题(是用以描述、解释什么的陈述句,还是用以下达命令的命令句,抑或是用以提出问题的问句,等等),都最终取决于它在它所处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作用,也即取决于人们在该语言游戏中对它所做的使用。而人们究竟对它作出了什么样的使用则最终又取决于人们所处的语言共同体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因而也就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生活形式。这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19〕
其次,任一表达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是由它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由人们在特定的语言实践中对它所做的使用决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20〕。而人们究竟对它作出了什么样的使用则又最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语言共同体的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因而也就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生活形式。“一个语词的意义真的只是它的用法吗?难道它不是这个用法嵌入生活的方式吗?难道它的用法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吗?”〔21〕这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游戏的语义规则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
最后,一个语言游戏的语用规则很显然也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
B.因为一个语言游戏的所有规则都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所以一个人是否正确地解释了某个语言规则或是否正确地遵守了它便可从它所处的语言游戏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形式的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等看出。因此“遵守规则”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实践,它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是一种人类生活现象。〔22〕
C.既然“遵守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而“遵守规则构成了我们的语言游戏的基础,它们刻画了被我们称为描述〔即语言的使用〕的东西的特征”〔23〕,所以语言游戏也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这里我用‘语言游戏’一语意在强调:讲一种语言是一种活动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24〕“设想一种语言〔语言游戏〕就意味着设想一种生活形式。”〔25〕“属于语言游戏的是整个的文化。”〔26〕
D.由于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所以它必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实践、一种人类生活现象或者说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7〕
(3)“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借以得出他的最终哲学结论的重要契机。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他以前做出的可说和不可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原则上讲,一切都是可说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借我们的语言而言说什么并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借它加以言说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的逻辑结构和我们的思想活动的作用,而是因为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对它做了合乎我们所处的生活形式的习惯、风俗、传统和制度的使用。比如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不可说的神秘体验之域实际上就是可说的,因为我们通常用以言说它的那些语词或命题,如“绝对价值的所在”,“绝对善的寓所”等等,并非如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言不合乎我们所处的生活形式的习惯、风俗、传统和制度。由于可说和不可说的区分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得以作出他的事实世界和神秘之域之分的重要依据和契机,我们甚至可以说二者就是同一个区分的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对前者的抛弃势必引导他抛弃后者。现在他认识到,既不存在什么仅仅由单调乏味、毫无价值可言的事实组成的事实世界,也不存在什么仅仅由体验和价值构成的、处于事实世界之外的作为人生意义终极依托之所的神秘之域。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所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它是由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组成的,而体验和价值就植根于这些生活形式之中。因而,人生意义也就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去寻求,它就在今生今世的生活之中,而不在于以什么方式将自己由经验主体升格为形而上学主体,并沉浸于某种神秘的体验之中。
5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概念不仅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内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从哲学史角度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1)为了解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复杂关系,维特根斯坦引入了“家族相似性”概念。综观他的后期著述,我们看到他不仅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游戏,语言游戏概念,而且也将它应用到其他一般概念之上,并由此得出了如下一般结论:并不存在一般概念所刻画的诸多事物所共同具有的什么本质特征或属性,在它们之间仅存在着这样那样互相交叉重叠的相似性——家族相似性。 “概念词(Begriffscoort)确实表明了归属于它的对象的亲缘关系, 但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是什么性质的相同或者构成成分的相同,它能像链条一样将它的诸成员联系起来,使得其中的每一个都与另一个通过中间环节而互有联系;两个彼此邻近的成员可以有共同的特征,彼此相似,而彼此相距遥远的成员间则不再互有共同之处但还是属于同一个家族”〔28〕。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观点便使他介入了在哲学史上有着悠久历史的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或日一多之争。实在论者认为,一般概念所表示的性质、关系(即共相)正如我们能知觉到的具体事物(殊相、个体)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而在概念论者看来,这些抽象的性质、关系等只在人们的心灵中有其存在;唯名论者则认为世界(包括心灵)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殊相、个体),所谓的一般概念只是一些空洞的、一般性的语词。但在作出上述断言时唯名论者遇到了这样一个理论难题:通常我们都是通过一个一般概念所表示的某种或某些性质来定义由适合于它的那些事物所构成的类的,如对于“狗”这个概念我们通常是这样定义适合于它的事物的类的:一个事物属于狗类当且仅当它具有成为狗所必需的那些属性,但如果如唯名论者所言,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或这些共同的性质,那么我们如何定义适合于一个一般概念的事物的类呢?这时有些唯名论者便转而求助于“相似性”概念了:一个事物属于适合于某个一般概念的事物的类当且仅当它相似于这个一般概念的一个标准的特例。不难发现,唯名论者的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恰好使他们回到了他们所欲反对的实在论者的立场,因为他们这里所说的相似性是以某种同一性(至少是部分同一性)为基础的,因而必包含着某种“共相”。而且不止此,为避免无穷后退的尴尬局面,这种相似性本身还需是某种共相,维特根斯坦在共相问题上的立场显然不同于实在论和概念论,那么它是不是唯名论的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唯名论的,但它与传统的唯名论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虽然他也谈相似性,但他所说的相似性并不是什么全总的、普通的相似性而是某种“家族相似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个事物属于一个一般概念的诸实例所构成的类并不是因为它与该类的其他成员有什么共同的性质或因为它与该类的某个范例有什么相似性(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共同性质或这样的范例、这样的相似性),而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与该类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具有某种或某些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并不一定也存在于其他成员之间。这样,维特根斯坦便很好地解决了唯名论者在否定共相的存在时所遇到的理论难题。
(2)在西方哲学史上, 大哲学家们往往到超越于现实的经验世界(现象世界)之外的领域(如理念世界、本体界)中去寻找人类的概念活动的基础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前期维特根斯坦也没有能够摆脱开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定势的制约,他也设置了一个超越于经验世界的世界——神秘的体验之域,并将它看作是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之所,但三十年代后,他逐渐摆脱了这种传统思想定势的左右,转而到我们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和我们的一切概念活动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3)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还具有如下更为一般的文化意义:它为价值—文化的相对论、多元论提供了根据。价值—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自然事实”〔29〕,正如作为这种差异的基础的生活形式上的差异一样。因此我们切不可站在某种价值—文化的立场上对其他的价值—文化进行任意的贬低和指摘,不能搞“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本身无优劣、高低和对错之分,由此看来曾在我国几度“甚嚣尘上”的以“中西文化之优劣高下”的争论为核心的“文化热”是建立在对文化之真义的误解的基础上的,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结果。
注释:
〔1〕〔2〕〔6〕〔7〕〔8〕〔9〕〔10〕〔11〕〔13〕〔14〕〔16〕〔19〕〔22〕〔24〕〔25〕〔29〕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intersuchungen,herausgegeben von G.E.M Anscome,G.H. VonWright,Rush Rhees.In Ludwig Wittgenstein:Werkausgabe in 8Banden,Band.1 (Suhrkamp,1984),§§66,68,83,100; §67;§ 2;§7;参见§18;§23;§23;§84;§71;§65;p.577;参见§21; 参见§§199,202;§23;§19;§p.578。
〔3〕〔21〕〔22〕〔27〕〔28〕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Grammatik,in Ludwig Wittgenstein:Werkausgabe in 8Bǎnden,Band.4 (Suhrkamp,1984),pp.116—117; p.65; 参见p.94;参见p.66; p.75.
〔4〕〔8〕〔12〕Alice Ambrose (ed.):Wittgens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2—1935,From the Notes of Alice Ambrose andMargaret Macdonald (New Jersey.1979),参见p.47;参见p.101;p.81。
〔5〕〔8〕〔20〕〔27〕Ludwig wittgenstein:The Blue andBrown Books,ed,by Rush Rhees (Oxford,1964),p.17;参见p.17;参见p.81; p.69;参见p.134。
〔15〕Ludwig Wittgenstein:Remarks on Colour (Bemerkungenǖiber die Farben),ed.by G.E.M Anscombe (Oxford,1978),p.57.
〔17〕〔18〕Ludwig Wittgenstein:Zettel,ed.by G.E. 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2nd,ed.(Oxford,1981),§387;§388。
〔22〕〔23〕〔27〕Ludwig Wittgenstein:Bemerkungen ǘber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herausgegeben von G.E.MAnscombe,Rush Rhees,G.H.von Wright,in Ludwig Wittgenstein:Werkausgabe in 8 Bǎnden,Band.6 (Suhrkamp,1984),pp.346,334,331; p.330; pp.346,334,335,351—352.
〔26〕Ludwig Wittgenstein: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Aesthetics,Psychology..and Religious Belief,ed. by CyrilBarrett (Oxford,1983),p.8.
标签:维特根斯坦家族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