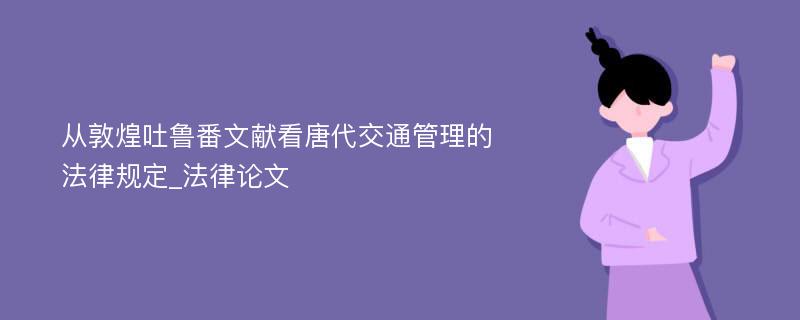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唐代交通管理的法律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敦煌论文,交通管理论文,唐代论文,所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时期,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也涵盖了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十分活跃,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唐代交通管理的论著还不是很多,仅见的有日本学者爱宕元撰写的《关于唐代桥梁和渡津的管理法规》一文[1],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从现存的唐代文献看,唐代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立法还是十分完备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右侧通行”的陆路交通规则,唐律中规定的“上泝避下泝”的海上交通规则, 以及对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审判程序等,都反映出中国古代交通立法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中的某些规定,对于现阶段我国的交通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唐代交通规则的法律规定
据《唐六典》卷6记载:“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分别概述了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的涵义及其法律效力。唐律以“疏议”的形式保存下来,即我国现存最早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唐令已经佚失,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和池田温等人根据现存的古代文献对唐令的部分条文进行了复原,出版了《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唐代另外两种法律形式格和式也已不存,现仅有少量出土文书残卷,如P3078号、S4673号《唐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P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等。令、格、 式法律形式的散佚为人们了解唐代的交通立法带来了诸多不便。笔者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试图对唐代交通管理的法规略作分析,不妥之处,祈求教正。
(一)唐贞观年间“右侧通行”交通规则的创制
唐代是我国交通立法十分发达的时期,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由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右侧通行”的规定,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交通规则。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记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鼟鼟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从上述这条材料来看,马周在贞观年间制定了多项城市交通管理的制度,《新唐书·马周传》中记述的“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交通规则。
(二)维护封建尊卑等级秩序的交通守则
唐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也体现在交通法规之中。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复原的《唐令拾遗·仪制令第十八》规定:“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即使不同品级的官员在路上相遇,唐代令、式中也有规定,“准《仪制令》: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诸官人在路相遇者,四品已下遇正一品,东宫官四品已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
(三)关于交通工具管理的规定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主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车、马、渡船等。在唐代的《车舆令》中,对皇帝大臣以及普通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作了明确规定。唐代法律尤其注重对国有交通工具驿马的保护,《唐律疏议》卷10“增乘驿马”条规定:“诸增乘驿马者,一疋徒一年,一疋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对于使用国有交通工具运送私人物资的行为,唐律规定:“诸乘驿马赍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驿驴减二等。”
为了防止江南地区的民众反抗封建政府,唐代法律还禁止私人拥有和营造战船等战略交通工具,“诸私家不得有战舰等舡”,“诸私家不得有蒙冲等舡”。
(四)实行“上泝避下泝”的水上交通规则
渡船是水上运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关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唐代法律对于渡船质量、行运规则以及运输货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据《唐律疏议》卷27“行船茹船不如法”条记载:“诸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若船筏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以故损失官私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其于湍碛尤难之处,致有损害者,又减二等。监临主司,各减一等。卒遇风浪者,勿论。”在“乘官船违限私载”条中,还对违法超载等行为作了相应处罚:“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唐律对水上通行的交通规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是目前为止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水上通行规则。众所周知,水上通行与陆路不同,船只在水上相遇,回避的空间狭小,若不单独制定交通规则,很容易出现船只碰撞的现象。为此,唐律中专门制定了水上通行的规则:“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
(五)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高速行驶车马
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2],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高速行驶,否则构成犯罪,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很明显,唐律从维护民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限制车马在街巷等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六)为强化社会治安,禁止官民夜间出行
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反抗封建政权,唐代法律严厉禁止官员百姓夜间出行,对于都城的管理尤为严格。《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记载:“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 ”长孙无忌在疏议中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可见,在唐代,如有公私急事出入城门,须有官府发给的公验才允许通行。
(七)实行出行许可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政府为了防止民众逃离土地成为社会上的浮游人口,利用法律手段限制民众出行,凡到外地经商或游览等正常活动,应持有官府发放的有效证件。过所和公验是唐人出行的凭证,类似于现代的通行证。凡官吏民众远行出入关、津,须凭证明其身份的公验、过所通行。唐代的过所通常缮写两份,一份是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申请过所之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要经过主判官、覆审官签名,留作刑部司门司或本州户曹的档案加以保存。唐代公验和过所的申请程序复杂,据《唐六典》卷6“司门郎中”条云:“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在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唐人申请给付的程序。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221号墓出土了《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引之如下[3]:
1 贞观廿二□□□□庭州人米巡职辞:
2 米巡职年叁拾,奴哥多弥施年拾伍
3 婢婆匐年拾贰,駞壹头黄铁勒敦捌岁
4 羊拾五口。
5 州司: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
6 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
7 公验。请裁,谨辞。
8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
9 西州市易,所在烽
10 塞勘放。怀信白。
11 廿一日
在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509号墓中,还发现了《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以及《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等法律文书,这些文书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过所的申请、发放以及过所丢失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73TAM509《开元廿一年正月一二月西州都督府勘问蒋化明失过所事案卷残卷》是一件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丢失过所案件的行政诉讼文书,该文书经过刘俊文先生整理,内容大体如下:京兆府云阳县嗟峨乡人蒋化明,为敦元暕充当脚夫,自凉州向北庭运输。行至金满县,恰逢括户,遂附籍为民。后因饥贫,又为北庭子将郭林驱驴,送和糴米入伊州仓。到西州时驴病死,练用光,过所也不慎丢矢,被郭林派傔人桑思利捉送官司。经法曹司勘问,判付桑思利领蒋化明往北庭。路过酸枣戍,因无过所,又被捕回,交功曹司审讯。从本案件的卷宗来看,既有被告丢失过所的辩词,又有功曹、法曹参军的审问记录,最后是地方主管官员的判决意见和户曹参军为蒋化明补发行牒。整个案件程序复杂有序,说明唐代官府对于通行证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唐代法律对于没有过所、公验而私自出入关津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对于不符合度关手续而发给过所,或冒名申请过所而度关的行为,唐律规定:“各徒一年”。在《白居易集》卷66中收录了一件“得景夜越关,为吏所执。辞云:有追捕”的案例,最后的判决意见是:“设以关防,辨其出入。即慎守而无怠,岂伪游而能过?景勤恪居怀,夙夜奔命:以谓寇攘事切,宜早图之;罔思呵察戒严,不可踰也。”
二、唐代关于道路维护的法律规定
利用道路来运输货物,发展经济;利用道路运送军队和战略物资,这是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构建国家安全防御体系的大事。唐朝也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十分注重利用法律手段对道路进行维护。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交通管理机构。关于陆路交通,为了方便行人及传递信息,唐代实行驿站制度,由兵部下辖的驾部郎中负责,全国总共有1639所驿站,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工部下辖的水部郎中负责道路桥梁的管理,“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都水监下设舟楫署,负责水上交通工具的管理,“舟楫令掌公私舟舩及运漕之事”;“诸津令各掌其津济渡舟梁之事”。道路的修缮等方面的事务由将作监负责,“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4]。
在全国各地方州、县,唐代也建立了相应的道路管理机构。唐朝地方实行州、县二级行政管理体制,州一级的道路管理机构是户曹和士曹,“户曹、司户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士曹、司士参军掌津梁、舟车、宅舍、百工众艺之事”。县级行政机构对道路的维护管理由县令负责,据《唐六典》卷30记载:“籍账、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
唐代交通管理系统虽部门繁多,但封建国家对于交通的立法还是较为完善的。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批敦煌文书,在这些众多文书中,有一件是关于唐代渡津、桥梁管理维护的法规细则《水部式》,该文书的发现为探究唐代道路行政管理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唐代法律严禁私人侵占街道、或将污秽之物排放街道,以及在街道两旁取土等违法行为,对此,《唐律疏议》卷26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防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长孙无忌在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并合禁约,不禁者,与犯罪人同坐。”在此我们看到,唐律不仅规定了对犯罪者本人的处罚措施,也规定了主管官吏的法律责任,如主司不予以禁止,与犯罪者同样治罪。
开元十九年(731)六月,为了维护京城地区的街道安全,唐玄宗颁布了《修整街衢坊市诏》,禁止在街巷及行人通道挖土,诏书内容曰:“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整。比闻取土穿掘,因作秽污坑堑,四方远近,何以瞻瞩?顷虽处分,仍或有违。宜令所司,申明前勅,更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5]
据《唐会要》卷86记载,广德元年(763)八月,针对诸军及诸府在街道两旁开凿种植,侵占道路,造成道路狭窄的情况,唐肃宗颁布诏令:“如闻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衢路隘窄,行李有防。苟徇所资,颇乖法理。宜令诸道路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大历八年(773)七月,唐代宗又下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大历二年(767)五月,唐代宗下令:“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簷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六月,京城右巡抚使上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唐宣宗亲自指示:“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毁拆”。
唐代法律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如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置障碍,也要设有明显标识。据《唐律疏议》卷26记载:“诸施机枪、作坑宑者,杖一百;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有标识者,又减一等。其深山、迥泽及有猛兽犯暴之处,而施作者,听。仍立标识。不立者,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疏议对本条的解释是:“有人施机枪及穿宑,不在山泽拟捕禽兽者,各杖一百。”如非人常行之所,“若立标识,仍有杀伤,此由行人自犯,施机枪、坑宑者不坐”。
为防止雨水冲刷道路,美化道路环境,唐政府曾多次下令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早在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就注重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树,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6]。唐代沿用了前代做法,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殿中侍御史,官职为从七品上,职责颇重,据《唐六典》卷13记载:“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为了便于管理、维修和行人辨认,唐代在交通道路上每隔五里设置一个里程碑,即“里隔柱”。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记述:“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里隔柱类似于现代公路上的里程标识,它的设立对于计算道路里程,辨认道路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唐一代,道路桥梁的营造由国家专门机关将作监负责,据《唐六典》卷23“将作监”条记载:“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等……称为内作;”凡山陵、太庙、都城诸门、诸司官舍、街、桥、道等,称为外作。唐代的道路桥梁和渡津有专职人员管理维护,根据《唐六典》卷7“水部郎中”条的记载,水部郎中负责修缮管理的桥梁共有11座,“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 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茸。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等差”。除水部郎中管理十一座大桥外,还设有另一个管理渡津、舟桥的机构,即都水监下辖的诸律令,《唐六典》卷23“诸津”条载:“诸津:令一人,正九品上;丞一人从九品下。诸律令各掌其津济渡舟梁之事,丞为之贰。”“诸津在京兆、河南界者隶都水监,在外者隶当州界。”
众所周知,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交通运输主要通过陆路和水路来实现。而陆路交通又经常被高山或大江大河所阻断。为了克服陆路交通的障碍,方便行人来往,历史上许多封建政权组织人力物力开山辟岭,打通要道。由于这些地方地势险要,处于战略要冲,封建政府通常派人防守,这也就形成了关。据《唐六典》卷6“司门郎中”条记载,唐代由刑部司门郎中掌管的关“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但是,当陆路交通遇到大江、大河阻隔时,又如何解决呢?毫无疑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架设桥梁。如果在河流流量小、 河面较窄的地方架设桥梁相对容易,但若在河流流量大、河面宽阔的大江大河上架设桥梁又谈何容易!特别是以黄河为代表的流经华北地区的河流,因河水的冲刷而积淀成厚厚的土质松软的河床,不利于打造稳固的桥墩。因此,为了方便运输和行人往来,封建政府往往在河流平缓的地方设立渡口,配备渡船。如连接河西与河北的黄河渡口设有白马津,配有渡船4只,连接越州和杭州的浙江渡,配船只3艘等。
唐代工部管辖众多的道路和桥梁,其又是如何通过何种手段进行维护和管理的呢?这是研究唐代交通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存的唐令逸文中只记载了对道路桥梁维修的时间,如《唐令拾遗补·营缮令第三十一》规定:“凡津梁道路,治以六月。”[7] 但怎样维护, 需要的材料又如何征运,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唐开元年间的《水部式》残卷。式是唐代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水部式》则是一部唐代水行政管理的法规,其中许多内容是涉及桥梁管理的法律规定。通过对《水部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对于道路的管理和维护是非常细致的。
唐代《水部式》残卷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2507。该文书首尾残缺,中部也有个别脱字,共有7纸144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规定,可以说是一部水行政许可法。在《开元水部式》残卷中,还有一少部分条款是涉及全国道路桥梁、渡津以及各地河道运输、海上运输管理的规定。
水部司是唐代六部之一工部下辖的职能部门,其所管理的桥梁主要是规模宏大的建筑,至于较小的桥梁,则由当地行政机关州、县来维护管理;京城内的小桥、街道,由将作监和诸司修造,据《水部式》记载:“皇城内沟渠拥塞停水之处及道损坏,皆令当处诸司修理。其桥,将作修造。十字街侧,令当铺卫士修理。”
水部郎中负责管理维护的桥梁共有11座,桥梁的类型可分为石桥、木桥和浮桥三种类型。
首先,看一下《水部式》中关于石桥的规定。在该残卷第43~45行有如下的记载:
洛水中桥、天津桥等,每令桥南北捉街卫士洒扫。所有穿穴,随即陪填,仍令巡街郎将等检校,勿使非理破损。若水涨,令县家检校。
关于这两座桥的结构,《唐会要》卷86云:“天宝元年二月,广东都天津桥、中桥石脚两眼,以便水势。移斗门自承福东南,抵毓材坊南百步。”可见,这两座桥是由石料构建而成的。由于天津桥人员流量过大,所以派有专人清扫。为了保护石桥, 唐睿宗先天二年八月下令“除命妇以外,余车不得令过”[8]。
《水部式》残卷第105~109行是关于另外两座石桥管理的规定:
京兆府灞桥、河南府永济桥,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检校。仍取当县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灞桥番别五人,永济桥番别二人。
灞桥架设在通往长安城内的灞水之上,关于其结构,根据陕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发掘,已证明其是一座石桥。永济桥位于洛阳西南的寿安境内,亦属于石结构的建筑。
由于石桥质地坚硬,不容易毁损,对于石桥的维护管理也相对容易,官府委派的管理人员主要是残疾或中男,人数很少。
接下来再看一下对木桥的管理。《水部式》残卷第86~92行是关于木桥管理和维护的法律规定:
都水监三津各配守桥丁卅人,于白丁、中男内取灼然便水者充,分为四番上下,仍不在简点及杂徭之限。五月一日以后,九月半以前,不得去家十里。每水大涨,即追赴桥。如能接得公私材木栰等,依令分赏。三津仍各配木匠八人,四番上下。若破坏多,当桥丁匠不足,三桥通役。如又不足,仰本县长官量差役,事了日停。
这里所说的都水监三津,系指都水监所管辖的三座木桥。由于木桥是木质结构,容易腐烂和毁损,需要经常维修,故各桥配给的守桥人丁人数较多,各30人,另外还配有木匠8人,随时维护。
最后,看一下《水部式》中关于浮桥的管理。唐代华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是黄河,由于黄河河宽水深,加之河底多泥沙,在黄河上打造桥梁十分困难,唐代政府在黄河之上建有三座浮桥。《水部式》残卷第67~74行是关于河阳桥和大阳桥管理的规定,第139~141是关于蒲津桥的管理规定,引之如下:
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仍各置竹木匠十人,在水手数内。其河阳桥水手,于河阳县取一百人,余出河清、济源、偃师、汜水、巩、温等县。其大阳桥水手出当州。并于八等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分为四番,并免课役,不在征防、杂抽使役及简点之限。一补以后,非身死遭忧,不得辄替。如不存检校,致有损坏,所由官与下考,水手决卅。
蒲津桥水匠一十五人,虔州大江水赣石险难□□,给水匠十五人,并于本州取白丁便水及解木作□充,分为四番上下,免其课役。
因浮桥与石桥、木桥不同,保护与维修需很多劳动力,故这两座浮桥分别配有水手250人和200人。浮桥的维修需要在水下作业,对于维护人员的要求也格外严格,须“灼然解水者”,一旦被征调为水手,“非身死遭忧,不得辄替”。浮桥所使用的原材料多为竹木,故浮桥配备竹木匠,以便随时维修。
《水部式》残卷第115~134行是关于浮桥材料补给的规定:
河阳桥每年所须竹索,令宣、常、洪三州□丁匠预造。宣洪各大索廿条,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条。脚以官物充,仍差纲部送,量程发遣,使及期限。大阳、蒲津竹桥索,每三年一度,令司竹监给竹,役津家水手造充。其旧索每委所由检复,如斟量牢好,即且用,不得浪有毁换。其供桥杂匠,料须多少,预申所司量配,先取近桥人充,若无巧手,听以次差配,依番追上。若须并使,亦任津司与管匠州相知,量事折番,随须追役。如当年无役,准式征课。
诸浮桥脚船,皆预备半副,自余调度,预备一副,随阙代换。河阳桥船于□、洪二州役丁匠造送。大阳、蒲津桥船,于岚、石、隰、胜、慈等州折丁采木,浮送桥所,役匠造供。若桥所见匠不充,亦申所司量配。自余供桥调度并杂物一事以□,仰以当桥所换不任用物迥易便充,若用不足,即须申省,与桥侧州县相知,量以官物充。每年出入破用,录申所司勾当。其有侧近可采造者,役水手、镇兵、杂匠等造贮,随须给用,必使预为支拟,不得临时阙事。
《水部式》第135~140行规定了河流枯水期时浮桥的拆解办法。北方河流秋冬季节进入枯水和冰冻期,为了保护浮桥设备,需要对浮桥进行拆解更换,故《水部式》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诸置浮桥处,每年十月以后,凌牡开解合,□□抽正解合所须人夫采运榆条造石笼及索等杂使者,皆先役当津水手及所配兵。若不足,兼以镇兵及桥侧州县人夫充。即桥在两州两县□者,亦于两州两县准户均差,仍与津司相知,□须多少,使得济事。役各不得过十日。
以上是关于唐代工部所辖的桥梁、渡津管理维护的具体规定。至于唐代地方州县又是如何对其所辖的道路桥梁进行维护,因文献记载简略,很难窥其全貌。在《白居易集》卷67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为了解唐代地方官员对道路维护的法律责任提供了重要线索:
得洛水暴涨,吹破中桥,往来不通,人诉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犹涨,未可修桥,纵苟施功,水来还破,请待水定。有又有辞。
依据唐代法律,作者对此案件作出的判词是:
大水为灾,中桥其坏。车徒未济,诚有阻于往来;修造从宜,亦相时之可否。顾兹浩浩,阻彼憧憧。人诉川梁不通,壅而成弊;府虑水沴荐至,毁必重劳。苟后患之不图,则前功之尽弃。将思济众,固合俟时。征启塞之文,虽必茸于一日;防坏襄之害,未可应乎七星。无取人辞,请依府见。
第57~61行、第74~77行是关于海上运输管理的法律规定。唐代海上运输也十分发达,但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水部式》残卷中有两条关于海上运输的规定,为我们了解唐代海上运输的法规提供了珍贵资料。
第57~61行是关于海上货船水手选拔的规定:“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不烦更给勋赐,仍折免将役年及正役年课役,兼准屯丁例,每夫一年各帖一丁。其丁取免杂徭人家道稍殷有者,人出二千五百文资助。”
由于海上运输具有特殊性,故第74~77行有关于海师选拔的规定:“安东都里镇防人粮,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海得勋人谙知风水者,置海师贰人,拖师肆人,隶蓬莱镇,令候风调海晏,并运镇粮。同京师上勋官例,年满听选。”
从上述《水部式》中所记录的法律条文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河道运输和海上运输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细致的。
三、从吐鲁番出土文书73TAM509号残卷看唐代交通肇事罪的诉讼审判程序
所谓的交通肇事是指违反国家制定的交通法规而制造事端的行为。由于古代的交通管理规定与现代的交通法规有所不同,所以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处罚和适用的法律程序也各不相同。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交通立法首先是为了保障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人身安全,凡危及封建皇帝人身安全的行为皆属违法行为。唐代交通法规的另一项职能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唐律中的该条法律条文就是为了保障城市内正常的交通秩序而设立的条款。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因此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也很低。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突发性的意外事件,有时难免也会造成交通肇事的情况。唐代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又是按照什么程序进行审判?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值得庆幸的是,在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交通肇事罪的卷宗,为我们了解古代交通肇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编号为73TAM509:8(1)、(2)号《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残卷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文书卷首残缺,结尾完好,中间或有残缺,全部文书共有3纸58行,每行字数约11~12字,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
关于该残卷的书写年代及文书所反映的地点,刘俊文先生曾考证其为唐肃宗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审理的案卷。根据卷中原告诉状所投诉的“县司”,可知该案件由高昌县衙审理。卷中多次出现“元年建末月”,考之史籍,唐肃宗上元二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十一月)为岁首,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至次年建巳月(四月)甲子,始改年号宝应,变寅正,月数皆如其旧。“此卷署‘元年建末月’盖因高昌僻远,信息缓慢,故中原已改元两个月,而其地仍沿用‘元年’纪年和以所建为月数。实际上,此卷之时间当为宝应元年六月。”
吐鲁番出土文书《73TAM509:8(1)、(2)号康失芬行车伤人案残卷》与现存唐人判集《甲乙判》和《龙筋凤髓判》不同,也与敦煌文书P3813号《文明判集残卷》不同,前者是唐代官府依据唐代实体法所进行的实判,后者则是为明法科考生学习国家律令法典所撰写的拟判,因此,《73TAM509: 8(1)、(2)号残卷》所记述的审判活动、刑罚适用原则等也更能反映唐代诉讼审判程序的原貌。
该文书卷首部分已阙,内容不详。其余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中第1至15行记录的是原告法定代理人史拂郍、曹没冒的诉讼内容。为方便阅读,兹抄录如下:
(前缺)
男金儿八岁……
牒:拂郍上件男在张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
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郍牒
追问。舒示。
口一
〈空白〉
元年建未月 日,百姓曹没冒辞。
女想子八岁,……
县司:没冒前件女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快车人将车碾损,腰骨损折,恐性命不存,请乞处分。谨辞。
本案。舒示
口一
辞、牒是唐代司法文书的写作格式,《唐律疏议》卷24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由于本案的原告是未成年人,故该文书记载的是原告法定代理人的姓名,我们推断其为原告的诉辞,即诉讼请求文书。
县是唐代最基层的诉讼审判衙门,唐代的《狱官令》规定:“诸有犯罪,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则徒以上送大理,杖以下当司断之。”[9] 本案发生的地点是唐代西北地区的高昌县,该县也就成为本案件诉讼审判的一审衙门,原告诉辞上记有“县司”二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自第16行至第42行是当地司法官员的问案记录,主要是被告的陈述。本案件的主审官员名舒,根据《唐六典》卷30“京畿及天下诸县令”条记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守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推知舒为高昌县之县令。
第16至33行是主审法官舒对于被告康失芬快车牛行辗伤原告史拂郍男金儿、曹没冒女想子犯罪事实的认定。第34至42行是被告最后的陈述,以及审判人员对本案最终判决所发表的意见。兹抄录如下:
勒嗔奴快车人康失芬,年卅。
问:快车路行,辗损良善,致令困顿,将何以堪?款占损伤不虚,今欲科断,更有何别理?仰答。但失芬快车,力所不逮,遂辗史拂郍等男女,损伤有实。今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情求准法科断。所答不移前款,亦无人抑塞,更无别理。被问,依实谨辩。
元年建未月日。
从上述这段文字看,本案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致使车马不能控制,轧伤了在张游鹤店门前玩耍的两名儿童金儿和想子,致使两人身受重伤。官府在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之后,征求了交通肇事者康失芬的意见,提出了本案的判决意见,责令被告实行保辜。保辜制度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10],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规定。关于保辜制度适用的范围,传统的观点认为仅适用于斗殴所引发的人身伤害,至于保辜制度能否适用于交通肇事案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据《唐律疏议》卷21云:“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唐律疏议》卷21第307条没有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而适用保辜的条款。但在《唐律疏议》卷26第392条规定:“诸于城内巷街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也就是说,在唐代,凡交通肇事而杀伤人,可比照斗杀伤人罪,减一等处罚。《唐律疏议》卷21“保辜”条曾明确规定斗殴罪适用保辜制度,而交通肇事又可比照斗殴罪来处罚,故宝应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也可比照《斗讼律》中的斗杀伤人罪,实行保辜制度。即先保辜五十日,减一等处罚。被告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向法庭提出了保辜,这与唐律的规定并不矛盾。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本案卷宗的记述,唐代保辜的提出是在主审官对伤害人伤害事实认定之后和司法机关判决之前。从“今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这句话分析,保辜制度是伤害人自愿的,并非每个伤害案件都适用保辜。也就是说,如果伤害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被害人进行医治,法官则可依照唐律中的有关法律条文作出判决,而不必适用保辜程序,如本案中主审官舒审问“今欲科断,更有何别理”即是明证。
第43至54行记录的是高昌县勾检官诚对本案的勾检,以及县史上报给高昌县丞、县令有关康失芬保人何伏昏等人保状的牒文。其中第43行以上中缺,但从尾行“简诚白”和后面的“具检如前”一句分析,似为高昌县勾检官诚对本案勾检的结果。据《唐六典》卷30记载,唐代县一级的勾检事务由录事负责,“录事掌受事发辰,勾检稽失”。所谓勾检,即对审判的法律程序进行监督,以保障诉讼程序的合法性。第45行至51行是县吏张奉庭上报给县令舒、县丞曾有关保人何伏昏的保状、勾检官勾检的材料,请求主管官员进行批复。现根据出土文书抄录如下:
靳嗔奴并作人康失芬
右得何伏昏等状,称保上件人在外看养吏拂郍等男女,仰不东西。如一保巳后,忽有东西逃避,及反覆与前状不同,连保之人情愿代罪,仍各请求受重仗廿者。具检如前。请处分。
牒件检如前。谨牒。
建月末 日,吏张奉庭牒
吏是唐代各级官府中的办公人员。这段文字主要记录了保人的职责,即保证伤害人在监外为被害人积极治疗伤病,并保证伤害人不离开本县,否则,连保之人除杖责二十外,还要负连带责任。
第52行至54行是高昌勾检官诚责令车主靳嗔奴及作人通知担保人到衙,并随案卷一同上报至县丞、县令,听候处分的谘报。引录如下:
靳嗔奴并作人责保到。随案引过谘,取处分讫。
牒所由谘。诚白。十九日
“谘”乃“谘报”简称,洪迈在《容斋随笔》卷9“翰苑故事”条云:“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状,但尺纸直书其事,右语云:‘谘报尚书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谓之谘报。”本案中诚与县令、丞同属一个衙门,系下上级的隶属关系,故未用申状。
第55至58行是高昌县最高司法官员舒对本案的批复意见。案卷先报县丞审阅,县丞曾作出“依判谘”后,再呈报给本县最高长官县令舒,由舒作出最终裁定:“放出,勒保辜,仍随牙,余依判”。“放出”,系指将被监禁的被告康失芬释放,唐代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故先行将被告羁押;“勒保辜”,即责令伤害人、保人办理保辜手续。
总之,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73TAM509:8(1)、(2)号康失芬行车伤人案残卷》,使我们看到了唐代地方司法机关对于交通肇事案件所审理的实貌,也使我们对于唐代交通肇事罪的处罚措施有了清楚的了解。首先,唐代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罚可比照斗殴罪的处理办法适用保辜制度,如本案中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即是如此。其次,唐代交通肇事案件对于保辜制度的适用并非伤害案件的必经程序。通过对上述案件的分析,我们看到保辜制度是在伤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行的。若伤害人不同意保辜,则司法官员可依据国家法律进行判决,那么也就不存在保辜的问题。再次,保辜制度是在保证的前提下来实现的。若无保证,保辜也就无从谈起。本案中记有保证人何伏昏等,保证伤害人“将医药看待”被伤害人,并不得随意离开居住地;如发生伤害人反悔或逃亡现象,保证人负连带责任,即“情愿代罪”和“受重杖二十”,这说明保辜制度对保证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复次,唐代交通肇事罪施行保辜制度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先由司法人员对被伤害人作出伤情鉴定,后经伤害人同意、保证人出具保函,由勾检官勾检,再呈报本地区司法长官审阅,最后由该地区最高司法长官县令签署意见同意保辜,然后将伤害人放出,整个诉讼程序都是在严格的监督下来完成的,没有丝毫的法律漏洞,这说明早在唐代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境地。对于交通肇事案件适用保辜制度,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地结合起来,责令伤害人积极地为被伤害人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地降低人身损伤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现阶段对我国的交通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