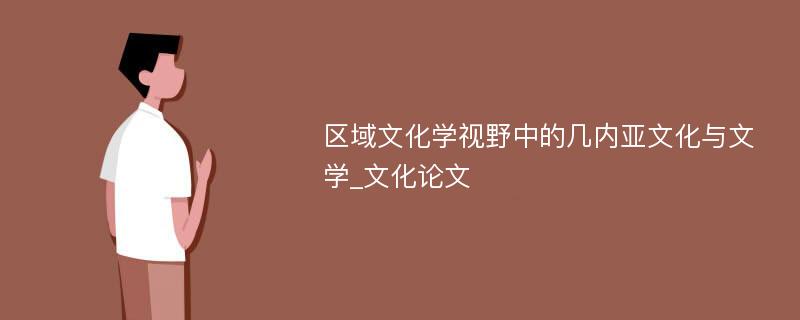
区域文化学观照下的畿辅文化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畿辅论文,文化学论文,文化与论文,区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4-0026-0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4.004 畿辅,又称畿服、畿甸、畿夏、畿疆等,最晚出现于周朝,是建立在周代的“五服”或“九服”之制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制度。所谓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有明确说明,“方千里曰王畿”,其余以“外方五百里”由近及远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五服之说,见之于《尚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颖达注曰:“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又《国语·周语》记载,周称侯﹑甸﹑男﹑采﹑卫为五服。虽“服”的名称略有出入,其意思大致相同,即以王畿为中心,将其四周按一定的空间距离,由近到远,依次划分,形成的若干区域。 纵观千年畿辅文化,是与中国古代的畿辅制度一脉相承的。《说文》对“畿”解释曰: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则曰畿也。先秦典籍中对此多次提到。《周礼·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孙诒让正义:“方千里曰王畿者,谓建王国也……《大司马》云国畿,《大行人》云邦畿,义并同。”又《周礼·夏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贾公彦疏:“云方千里曰国畿者,此据王畿内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国畿为本,向外每五百里加为一畿也。”《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郑玄笺:“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后兆域正天下之经界,言其为政自内及外。”东汉蔡邕《独断》:“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宋代叶廷珪《海录碎事·地下》曰:“天子之畿方千里,象日月径围,故曰日畿,又曰日围。”畿辅是拱卫京师的核心行政区域。 西汉建立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制度。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三辅”。班固《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1](卷五)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后代行政区划虽时有更改,但到唐朝时,仍然习惯上称之为“三辅”。唐朝在汉代“三辅”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京畿制度,将唐长安城周边地区分为京县(赤县)和畿县,京城所管辖的县为赤县,京城的旁邑为畿县,统称京畿。北宋皇佑五年(1053)置京畿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使,以朝廷直辖的开封府为汴京,划拨京东路曹州、京西路陈州、许州、郑州、滑州来属,以拱卫之。后虽屡有废置,行政区划有所改动,但制度基本沿袭。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复置京畿路,以朝廷直辖的开封府来属,同年析京西北路的颍昌府、郑州、河北东路澶州,并置拱州来属;设置四辅制度,以拱州为东辅、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元朝统一天下以后,设立行省制度,设中书省,辖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以及河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南部。明清则设置直隶省,辖境在不同的时期有所改动,但皆以北京为中心,今河北省是其核心区域。 畿辅制起源于商周时期,最晚到周代已经确立,早期管辖范围大约是围绕京师的千里左右。在后世则随着王朝的不同,首都所在地的变化,畿辅辖境各有变化。至元代行省制度确立之后,畿辅往往指的是一省之地,元代称中书省,明清时期则称为直隶。畿辅制度作为我国象征着“大一统”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而正是古代中国这种辐辏似的放射性的统治方式,奠定了畿辅作为皇权统治的核心区域的地位。畿辅地区在历朝历代的核心性、基础性、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畿辅地区是由皇权直接统治的政治格局所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畿辅地区也是皇城的人力、物力、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直接供应与参与者,更是捍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而畿辅地区最大的特征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地域,是随着政治统治中心的确立而确立,统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虽然其具体的地域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于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国而言,畿辅地区形成了一种历史悠久,一脉相承的千年畿辅文化。由于畿辅制度的建立与确立是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虽然畿辅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但畿辅制度给这些地区带来的深远影响却都是大致相同的。 畿辅文化指因古代中国畿辅制度而产生的文化的区域性表现形式。这一文化形态是由各结构要素(如学术、宗教、科举、民族融合、建筑、艺术、风俗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它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代兴所导致的畿辅制度和地域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自秦朝以内史掌内制,建立该制度以来,历代皇权均据自身需要设立相应的畿辅制度,如汉三辅制度,明南北直隶,唐两京畿内制以及清直隶省等。畿辅制度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也呈现出了历时性的变化。这一特殊行政区域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圈,其文化形态独具特性。畿辅文化形态的结构要素因朝代、地域的迁改而有不同的组合,但又有一以贯之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一)政治上的中心性 政治上的中心性是畿辅地区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历朝历代都对畿辅地区十分重视,如汉代设立的三辅制度,唐之京畿制度,宋之京畿路,元之中书省,明之南北直隶,清之直隶。都把畿辅地区从全国的行政区划之中突出出来。这种突出源于对全国统治的全局观。晋代袁宏《后汉纪·和帝纪论》“郊畿固而九服宁,中国实而四夷宾”,几乎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历朝历代都对这一地区实施特殊政策。例如在周代畿辅作为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地,周王对此进行直接控制,无论是税收、徭役,兵役等均予以照顾。汉代,京兆三辅之地官员往往由中央直接任命,且官衔与官俸均高于其他同级别地区,且天下精兵云集于此,以便拱卫。唐代的长安京畿之地同样如此。宋代在东京汴梁周边设置京畿路,元代全国四级地方行政制中,首都所在的腹里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内蒙古部分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以突出其重要性。明之南北二直隶更是显示了明王朝独特的政治历史及其传统。清初之时设直隶,一方面延续了历代对畿辅之地的特殊政策,例如清军一入关首先宣布免除直隶之地的各种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稳定畿辅,后来直隶总督之官衔要高于其他之督抚又成为清之定制。这一切都源于畿辅之地的中心性。这种政治上的中心性主要是由三方面决定的:临近都城的地理位置,与都城紧密的经济联系,拱卫京师的军事意义。当畿辅制度确立之后,这种制度就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语言、交通、赈灾、水利等诸多方面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在国内形成一个直接环绕京师的畿辅文化圈。这一个文化圈一方面具有很深刻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也具有京师文化的特点。这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圈。 (二)交流的广泛性 畿辅之地确立之后由于环绕京师,故其政治活动,军事行动,人员往来,物资交流等必然频繁,这就形成了畿辅地区交流的广泛性。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宗庙会同”“聘问朝贺”等活动,都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呈现出了显著的广泛性。在秦汉郡县制建立之后,这种人员、物质、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性更为广泛。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与确立,天下之士人、学子或科举、或求学、或游历纷纷云集于此,可谓天下英雄毕至。这样就为我国古代的经学、文学、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又为我国的文学、学术、思想等综合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明、清两代,国家重视文化教育,编辑了大量的官修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官方大型著书活动的开展,使学术、文化、文学的交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例如《永乐大典》参与编撰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两万一千六百人。而《四库全书》的直接编撰者达四千三百零三人。参与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朱筠等,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学者,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清代开设的各种修书馆,如通鉴馆、三礼馆、历代实录馆等,对于学术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康熙年间的明史馆,就招揽了南方学者万斯同、万斯大等,他们与畿辅学者王烈有过激烈交锋与辩难。而由畿辅学者朱筠奏请,乾隆下诏编修《四库全书》,则更是一次学术的大融合。南方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都经大兴朱氏兄弟先后引入四库全书馆。而被乾隆皇帝盛赞为“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的畿辅学者纪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过程中畿辅学者与全国各地的学者相互切磋交流,在编书之余,进行诗词酬唱。这种交流与酬唱,无论是对学者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畿辅之地为中国古代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往的平台,这种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学者个人的成长,并推动学术、文学的发展与成熟,这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的交融性 畿辅之地的发展在历史上又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 在中国历史上畿辅之地由于历史的变迁,其地域是不同的,换言之,畿辅具有地域的多变性。但是这种变化却大体上限制在了中国历史上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如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以洛邑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以南京为核心的苏杭地区,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这些区域又往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之地,而畿辅制度的建设使这些区域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呈现出更多的特色。如长安,在秦之时不过是秦之长安君的封邑,而在西汉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地区;又如洛邑及其周边地区最晚在西周时期就被确立为畿辅之地①,这使得河洛地区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后世即使畿辅之地不再设立于此,畿辅制度对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影响也仍然发挥着作用。就学术而言,在以长安三辅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著名的关内学,而在河洛地区形成了泽被中国文化上千年的“洛学”,而金陵一带历来被人们视为“文人之渊薮”,在京津冀地区则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派”的文学与艺术。而区域的多变性也给畿辅制度畿辅文化带来了很多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如上文所叙畿辅制度与陕西的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辅文化。虽然地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但是畿辅之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都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纵观中国历史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延绵不绝的共性,而在和各个地方文化的结合之中又具备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特色。 (四)文化的传承性 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几乎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最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畿辅制度的确立,会对地方文化产生十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被确立为畿辅,那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地位会被大为突出。如长安三辅地区,原来并非全国的统治中心,是由于周天子的权威使之成为了全国政治权利的核心,秦汉对于长安三辅地区的钟爱,使之成为了畿辅之地,这样就把河渭文化上升为三辅文化。十分典型的例子还有河北,虽然河北之地开发较早,但是历史上屡经战乱,一直到明洪武初年河北经济、文化、人口数量,都还远不及其他地区。但是北直隶畿辅之地的确立,使河北一下子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今之河北,古之燕赵,清之畿辅,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这样燕赵文化与畿辅制度相融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会使地方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提升,同时也由于它的政治的核心性、交流的广泛性、多文化的融合性,使之能够在原来的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升华,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创造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生成的文化语言特色,最早多是从水土和风俗立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评论了各地民歌,认为王风“思而不俱”,豳风“乐而不淫”,魏风“大而婉、俭而易”。王充《论衡·率性》记载有谚语:“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憨头”。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语。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顿”。唐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他们提出了语言、风俗和艺术的南北地域性问题。文学艺术的南北地域性主要体现为语言风格、自然风貌和艺术手法上的不同。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不仅阐述了南北自然风貌对文学的影响,还论述了社会环境以及文学交流对南北差异的消融。他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2](P86)概而言之,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和读者的地域性。 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方式和精神系统,除唐代佛学的进入而引起大调整外,其他时间几乎都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意义结构里,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正是文学封闭性的表现方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才会出现不同的语言风格、文化精神和艺术手法,如同一个个文学地域圈,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组成整体的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无论儒家和道家,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荀子·论礼》:“天地合而万物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之神》:“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文化和文学都强调取法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文学的地域性说到底是由文学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所产生,由此带来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所以,文学地域性建立在中国文学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在它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价值哲学。在区域文化与个人的关系上,每一个人都是在区域文化景观中接受雅、俗文化和家庭文化的教育和塑造,建构起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的。这就是《荀子·荣辱篇》所谓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智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儒效篇》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雅俗文化二者是互相蕴含补充的,两者交融于一身,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基本的文化素养,而且这对于个体的人生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的。 众多文学名士生长于畿辅地区,他们深爱这方热土,纷纷使用各种文学样式来加以歌颂。在《诗经》中的王风、豳风、周南等诗篇中,都有古代诗人真诚而热烈的吟唱。据《诗经·国风》地域性而论,畿辅地区的诗歌有《七月》之雅适,有《黍离》之哀叹,有《关雎》之热恋,有《扬之水》之悲壮,有《君子阳阳》之欢愉,有《采葛》之思念,更有《大雅》、《小雅》诗篇中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深情。在先秦时期,畿辅地区的民间诗人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精神文化之园。而在秦汉时期,以长安与洛阳为中心的三辅地区与河洛地区,更是名家辈出,文学佳作迭现。《后汉书·文苑传》就有“三辅多士”之赞美,虽然《文苑传》用“士”一词,但显然是侧重于指当时以儒生自视,后来却被我们看作文学家的三辅文士的。在相关人物中,以班彪、冯衍、梁鸿、杜笃、班固、傅毅、马融等人最为知名,马援、贾逵、苏顺、窦章、曹众、苏章、王隆、赵岐等次之。曾大兴论及汉代文学家的分布,明确指出:“两汉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南阳、陈留、河南、汝南、颍川、安平、北海、齐郡、沛国和会稽等郡国。”[3]并且以此为线索纵论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时代的文学家,从而得出结论,“京畿之地,即首都所在地。凡享国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其京畿之地的文学家数目都很可观。如西汉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时的河南尹,东晋、南朝时的丹阳尹,唐代的京兆府,北宋的开封府,南宋的临安府,元代的大都府、清代的顺天府,都是如此。”[3]故而“历代的京畿地区,除西汉之外,都只是当时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其版图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一,其所拥有的文学家则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3] 元代以来,三代王朝定鼎北方,北京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畿辅地区文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而呈现全新的面貌。其原因大略有如下数端: 其一为移民。明初河北地区由于战乱、灾荒等多种因素,人口较少故而仅官方移民就有八次之多,分别在洪武四年三月、四月,洪武五年七月、八月,洪武十七年夏,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而且移民当中的优秀人才甚多,如根据《永乐实录》永乐皇帝从苏州、浙江等9省简选三千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实畿辅”,不仅促进了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②而且大量的优秀移民的移入对河北地区的人才兴盛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是兴办学校。京畿地区的学校,大多具备优越的教学条件,能延聘到优秀的教师,生源也比较广泛。由京畿地区的学校输送的封建官僚和各类文化人才,不计其数。据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统计,仅明代畿辅地区的书院就有70所,而清代畿辅地区的学校书院建设就更加兴盛,数量达到115所[4](P169~170)。雍正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创建的保定莲池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在晚清时更是享誉全国。另外,乾隆六年成安知县赵元祚创建的文漪书院、道光二十九年昌黎知县王应奎创建的碣阳书院等,均为地方性书院,为当地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教育条件。 三是收藏图书。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重视图书的收藏工作,而京畿地区的图书量,往往居全国之冠。这就为广大文化人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都喜好收藏图书。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如明代直隶开州晁瑮父子和涿州高儒等。而清代畿辅地区的藏书家也甚夥,如清初之大兴孙承泽、宛平王崇简,后又有献县纪昀,大兴朱氏兄弟,大兴翁方纲兄弟,都是著名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及其藏书都促进了本地区的文化与文学的发展。 四是科举考试。京畿子弟参加考试,同外地考生相比,享有近水楼台之便。故而在明清两代科举中,畿辅地区的学者士人甚多,据学者王继平统计,直隶进士多达438人,如果再加上同属于直隶的顺天府的进士216人,两者相加则达到了654人。就其数量而言甚至超越了被人称为“文人渊薮”的江苏(613)人与浙江(608)人[5](P215)。而且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京师完成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此获得晋升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样全国大量的著名知识分子就自然荟萃于畿辅之地,有些学者在京城或为官或侯官或等待科举,都与畿辅地区的学者有所交流。如戴震在入四库馆之前,就广泛地在畿辅各地书院进行讲学,再如章学诚多次科举不中但却先后担任畿辅地区多个书院的主讲。京畿城下科举制度吸引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精英,汇聚于此,这无疑会对畿辅地区的学术与文学都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畿辅地区的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传承、城市的开发都与畿辅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畿辅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绝,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畿辅文化,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相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而畿辅文学又是畿辅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也体现出了千年传承的一致性,畿辅文化与畿辅文学相辅相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注释: ①1963年,陕西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上有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据铭文前面提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当为周成王时所造。铭文释文出自洛阳文物二队《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②参看李国祥《明实录类纂·河北天津卷》,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946-1006页。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汉朝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地域性论文; 东汉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