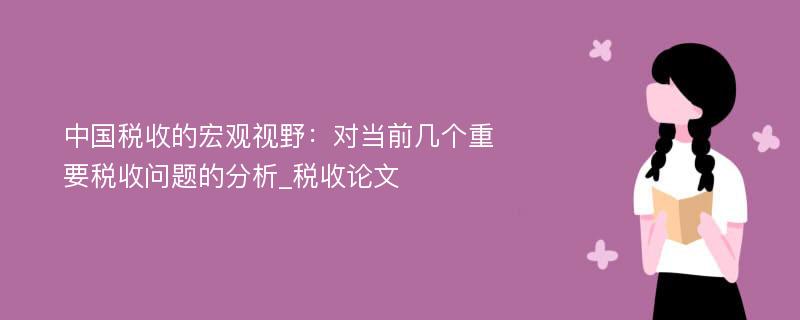
中国税收的宏观视野——关于当前若干重大税收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税收问题,不仅要从微观角度,也要从宏观角度,这是历史与现实一再向我们揭示的道理。许多曾经在微观层面看得不那么清楚、心中不那么有底的事情,只要放眼宏观,便看得清楚了,心中有底了。同时,不少曾经在微观层面论证得非常有理、也十分有力的方案,一旦放眼宏观,便不那么有理、也不那么有力了。甚至有过这样的经历,站在税务部门的立场上,就税收领域的某一问题作局部均衡分析,总是困难重重,疑惑颇多。当脱出部门的局限而伸展至全局,将税收置于宏观层面上作所谓一般均衡分析的时候,便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豁然开朗”或“如梦初醒”几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中国税收就“归位”——提高“税收依存度”
说到底,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在政府的收支体系中,它处在收入的一翼。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中,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税收,也可以是国债,亦可以是收费,还可以是其它别的什么形式。不过,相对而言,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的最佳形式。
税收的形式特征通常概括为“三性”:其一,强制性。它表明,税收系政府依据法律强制征收。纳税人只要有了应纳税的收入,发生了应纳税的行为,就必须按照税法的规定,把该缴的税如数缴上来。所以,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在量上是稳定可靠的;其二,无偿性。它表明,政府征税之后,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向纳税人支付任何代价。所以,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一般是不会有“后顾之忧”的;其三,固定性。它表明,政府系按以法律形式预先确定的征税对象与征税数额之间的数量比例征税。除非变动税法,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前提下,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是不能随意调整的。
国债的形式特征,则为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表明,国债的发行系以认购者自愿承受为基础。认购与否或认购多少,完全听凭其自身意愿而定。所以,政府通过国债所取得的收入,在量上不那么稳定可靠。有偿性表明,政府举债之后,不仅要作为债务到期偿还,而且要依事先约定加付利息。所以,政府通过国债所取得的收入,会因其必需的“后续支出”而给政府带来“后顾之忧”。灵活性表明,国债的发行额度一般没有法律形式的预先规定,而是由政府根据财政收支的状况相机决定。所以,政府通过国债所取得的收入,是可以灵活调节的。
收费是政府以交换或提供直接服务为基础而取得收入的形式。从总体说来,规范化的政府收费有两种:规费(FEE)和使用费(USER CHARGE)。规费系政府部门对公民个人提供特定服务或实施特定行政管理所收取的工本费和手续费。它的收取,一要限定在政府部门提供或实施的特定服务或行政管理的领域内,而不能扩大到一般领域。二要限定在工本费和手续费的额度内,而不能以此牟利;使用费系政府对公共设施的使用者按一定标准收取的费用。它的收取,一须以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为依托,而不能扩大到所有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二要体现收益原则,谁使用谁交费,不使用不交费。三要实行基金化管理,其收入只能用于公共设施的维修与建设。四是收取标准不能高于提供公共设施的平均单位成本。所以,无论规费还是使用费,能够带给政府的收入,在数额上,不会是大量的;在使用上,也是要受限制的。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政府收入,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用于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政府支出的性质,自然决定和制约着与其对应的政府收入的性质。
伴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我们已经将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公共财政。并且,正在加快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步伐。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才必须涉足。由此决定的政府支出事项分别是: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调节收入分配和实施宏观调控。这些支出事项,具有一个共同性质:通常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几乎没有产出。换言之,政府花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领域事项的钱,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
将收入与支出两翼的特征和性质联系起来并加以权衡,不难认定:税收,只有税收,才是政府部门运转的基础和生命线。税收,必须作为政府收入体系中的“主力”队员而居于主导地位。至于其它的政府收入形式如国债和收费,只能作为“替补”或“陪练”队员而担负起拾遗补缺的职责。
由此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如果比照“国债依存度”——国债收入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把税收收入占整个政府支出的比重数字称作“税收依存度”,那么,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提高这个依存度,实在是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收入体系的必然选择。
转眼看一下当前中国政府收入格局的现状,就会发现,尽管税收收入已经占到规范性的政府预算收入的绝大比重(2000年为93.3%),但是,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使用的“政府财政收入统计方法”(GFS)为口径,将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加进来,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并不大。根据陈小平(2001)的测算,2000年中国政府收入为26314.87亿元,相当于预算收入的1.97倍。照此计算,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仅为47.9%。
进一步看,IMF的统计方法所计入的,并非是当前中国政府收入的全部。倘若在此基础上,将政府通过收费、集资、罚款或摊派等途径取得的各种非规范性收入再加进来,税收占整个政府收入的比重,就更是偏低了。
结论1:中国税收要“归位”——提高“税收依存度”,让税收真正成为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
从税负水平提高看实现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规范化的重要性
税收负担,牵动千家万户,事关国计民生,历来被视为税收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
通常用一国的税收收入占其当年GDP的比重数字——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该国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状况的尺子。由于它所揭示的是一国总体上的税收负担状况,而非某一企业或家庭个别承受的税收负担状况,故亦可称作宏观税负或宏观税负水平。
就一般意义的税收负担而言,2000年,中国的税收收入总额为12660亿元,当年的GDP为89415.12亿元,两者之比,税收负担为14.16%。这样的税负水平,同各国的平均水平比起来1,决不能算是高的。不过,一旦透过数字的表象而深入到它的实质内容,便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问题出在“分子”而非“分母”上。我们所计入的税收收入,只是政府按照税收制度的规定,由税务部门通过税收渠道征收的那一部分政府收入。除此之外,在当前的中国,政府还使用别的形式、通过别的渠道取得收入。其中,属于规范性的、纳入预算的收入有:企业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以及其他杂项收入;介于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未纳入预算但可比较精确的统计的收入有: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纯系制度外、且无法加以精确统计的收入,则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收入,等等。如果将上述四个层次的这些收入统统相加,中国政府收入的总量,起码要以税收收入的倍数计算。
仍以2000年的数字(陈小平)测算,能够统计到的前三个层次的中国政府收入总计为26314.87亿元,占到GDP的29.43%。在此基础上,以第四个层次——制度外收入——占GDP的5%计算2,则加入制度外收入之后的整个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3%。这个负担水平,是单纯的税收负担数字的2.43倍。
不过,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或者,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政府收入层次的划分,税收负担和非税负担的区别,只是政府部门内部的事情。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公共部门或社会管理部门的政府,究竟从整个GDP的分配中拿走了多少?企业和居民,又究竟有多少收入交给了政府?或者,整个GDP的分配格局最终是怎样的?
用涵盖前述四个层次的政府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作为尺子,再来讨论中国现时的“总体税收负担”,可以认定:当前中国的总体税收负担远远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税收负担。
结论2:衡量当前中国的税收负担,要同时使用“一般意义的税收负担”和“总体税收负担”两把尺子。
一般意义的税收负担并不高,总体税收负担却不轻。如此复杂的局面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的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不规范。如果以是否纳入预算作为判定规范性与否的标准,那么,前两个层次的政府收入便是规范性的,后两个层次的政府收入则是非规范性的。正是由于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和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同时并存,而且,相比之下,在数额上,后者又大于前者,1998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才将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入格局描绘为“费大于税”,并由此启动了“费改税”的改革。
其实,“费改税”的着眼点,并不是要将所有的“费”统统改为“税”,而是以此为契机,实现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规范化。只有那些具有税收性质或名为“费”实为“税”的政府收费项目,才有必要纳入税收的轨道。对那些本来即属于收费范畴或名与实均为“费”的政府收费项目,则要按照收费的办法加以规范。而对于那些纯属“乱收费”的政府收费项目,则是要坚决取消掉的。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改革以来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在中国的兴起并蔓延开来,其初始的原因,并非是人们对“费”的偏爱超过了“税”,而是规范性的税收渠道不畅。在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政府支出留有较大缺口的背景下,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手段去另外找钱——自立收费项目,便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正所谓“税不足,费来补”。然而,收费之门的打开,非但没有缓解税收运行中的困难,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收费上。甚至于,在尝到了收费甜头、有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种收入来源可以依赖之后,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对“费”的偏爱超过了“税”。于是,“费挤税”的事情——以收费项目的扩大及其规模的增加冲击税基,以擅定减免税条款、鼓励企业偷逃税款的手段截留中央税收等现象发生了。“重费轻税”加上“费挤税”,事情演化下来,便是“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形成。
注意到“费改税”的动因所在以及“税”“费”之间的历史渊源,再来回顾一下1998年以来我们在强化税收征管和“费改税”道路上所走过的历程,其宏观层面上的经济效应也就不难看清楚了。
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已经带来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继1998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实现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目标之后,从1999年起,税收似乎走上了快车道。当年的增收额近1500亿元,增幅为16.2%,从而全国税收收入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的大关。2000年,增收的额度又达到了2348亿元,增幅为22.8%。刚刚过去的2001年,增收势头仍旧居高不下。全年增收额为2511亿元,增幅为19.8%。由此,全国税收收入规模又进一步迈上了15172亿元的台阶。
“费改税”则还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费改税”重头戏的养路费改燃油税的方案,至今还处在论证阶段。农村的税费改革,仍在安徽等少数省份试点。有所突破的,只有从2001年起,原收取的“车辆购置费”改成了“车辆购置税”。
一“快”一“慢”、“快”“慢”不等。两项工作未能同步,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未能随规范性政府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减下来,其结果,企业和居民承受的“税收总体负担”以及整个GDP的分配格局因此而朝什么方向变化,是不言而喻的。
结论3:随着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和“费改税”进程的相对迟缓,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税收总体负担”已经有所加重,GDP分配天平上的砝码越来越向政府一方倾斜。
再深一层看,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大到一个国家的整体税制设计,小至整体税制中某一单个税种的税制安排,总是以取得既定规模的税收收入为基本着眼点的。由于现实生活中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永远不会达到100%,故在设计税制时,无论是税基的选择,还是税率的安排,都要“宽打窄用”——将实际征收率的因素放入其中,将税率定的宽一些,把税率搞的高一点。税基、税率和实际征收率三个因素的乘积,便是我们要通过某一税种或整个税制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所以,税基和税率的乘积,只是理论上或名义上的税负水平。实际的税负水平,则要放入实际征收率的因素之后,从三个因素的乘积中去判断。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带来实际税负水平的升降。这便意味着,即使未采取任何扩大税基或提高税率等旨在提高理论或名义税负水平的行动,随着税收征管状况的改善,也会使实际税负水平相应上升。
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无论税基还是税率,都是根据当时税收征管状况所能达到的税收实际征收率而确定的。从那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们的税收征管状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如果当时的税收实际征收率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现行税制,特别是其中的税基和税率,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结论4:同1994年的情况相比,就“一般意义的税收负担”而论,当前中国的实际税负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