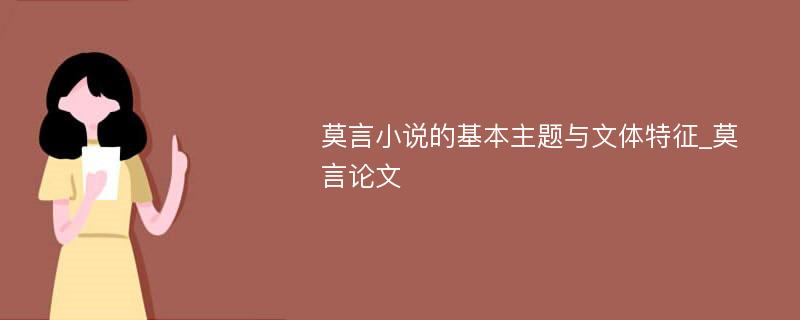
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特征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众多的汉语写作者当中,莫言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既不同于王朔的那种“胡同串子”式的京腔,又不同于苏童、叶兆言等人的那种清雅柔曼的江南话,也不像马原那样一副硬朗有力而雄辩的东北腔,更不像格非、孙甘露等人那样使用一套带欧化倾向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语言,甚至与他的同乡张炜的语言也迥然不同。张炜的山东话带有几分官味儿: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沉闷冗长,令人敬而远之。莫言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农民在说话。例如,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一开头就让我们听一位生产队长的训话。这种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歪七歪八、半通不通的官方辞令:领袖语录、上级指示、报刊社论的言辞,等等,以显示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但是,这种夹生的官腔、杂凑的语言,真正暴露了说话人的农民本性,非但不能令人生畏,反倒叫人觉得好笑。而莫言正是擅长于模拟这一类人的腔调和语体。
与此农民化的语体相一致,莫言小说在取材上大多来自农村生活。即使是描写战争(这通常被认为是莫言作品的另一大题材类型),写的也是农民式的战争,如小说“红高粱系列”中所描写的那样。农村的事物也常是他笔下的表现对象。首先是农作物,如高粱(“红高粱系列”)、红萝卜(《透明的红萝卜》)、棉花(《白棉花》)、蒜薹(《天堂蒜薹之歌》),等等,还有农家的家畜、牲口(如马、羊、驴、骆驼、狗)等动物。此外,农事活动,如修水库(《透明的红萝卜》)、磨面(《石磨》)、摇水浇菜(《爱情故事》)、修公路(《筑路》)等,也总是其作品中使人物活动得以展开的主要事件。这种种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经验世界里最为基本的感性材料,从而给莫言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农民化”的印记。
但是,莫言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谓的“乡土文学”作家。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固然也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但这种意义上的农村乃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都市、军营、知识界,等等)而言,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在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并一律带上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他们有的以描写乡间的风土人情见长(如刘绍棠),有的以描写乡间的日常生活情状见长(如汪曾祺),还有的则显得较为深刻一些,他们以描写特定背景下的乡间生活的变迁及其对乡间心理状态的影响为主(如高晓声、贾平凹)。这些作家总是努力追求自己笔下的乡间的独特性,无论在风情、民俗方面,还是在人物和语体方面。然而,这些特色表现得越突出,作品的普遍性意义却显得越薄弱。特定区域的乡土特色过于强烈的色彩,掩盖了作品应有的更为深刻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这样,朝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规律的反向发展。重新理解民族文化,重新发现民族性与普遍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寻找民族日常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和意义,这些便成了莫言一AI写作作者的重要任务。
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的,这个空间即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代(T.Hardy )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W.Faulkner)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G. G. Marquez)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 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在这个方面,与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中,只有刘恒的部分作品与之比较接近。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性爱、暴力、死亡……这种主题学上的转变,一方面与“寻根派”文学对人性的探索有关(莫言在最初亦曾被视作“寻根派”之一分子);另一方面,它又比“寻根派”更加关注生命的物质形态(比如人的肉体需要和人性的生命力状况等),而不是文化的观念形态(诸如善、恶、文化原型或象征物之类)。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如果将中国农村仅仅理解成一个悲惨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人往往只是这么看,以便自己高居于农民之上,并垂怜于他们。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这正是乡间文化的复杂性所在。中国乡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种苦难与快乐的奇特的混合物。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运动”对此特性有所发现,但“寻根派”作家无法理解这一特性奇妙之处,因为他们往往抱定某种僵死的文化理论模式和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而不能容忍乡民在苦难与快乐相混杂的泥淖之中生存的现状。“寻根派”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冲突模式(野蛮/文明,古老/现代……)对乡间文化作出生硬的评审,在“蒙昧”、“荒蛮”、“落后”等简单标签的掩盖下,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意义化为乌有。
莫言的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化寻根运动”的痕迹。不过,莫言的意义在于,他没有简单地追随“文明冲突”模式,而是卸去了种种遮蔽在农村文化上的观念外衣,将农民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暴露出来了。《红高粱家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抗战题材的故事。这类题材倘若从文化层面上加以处理,则极容易变成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相冲突的寓言,如“文化寻根派”的电影《黄土地》那样。但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更重要的是描写了北方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
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家族》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
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于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家族》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历史观念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正如他在作品中将那些野生的红高粱酝酿成高梁酒。这一由物质向精神的转换,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莫言笔下的另一类形象——妇女,同样也表现出对生命强力的赞美。如《红高梁家族》中的奶奶、二奶奶,《食草家族》中的二姑,《姑妈的宝刀》中的孙家姑妈,等等,这些女性尽管命运多蹇,但她们都有着大胆泼辣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精神,而且,还有着健壮的体格和旺盛的生殖力。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在她们身上,显示了生命力的生产性的一面。这种富于生产力的母性形象,在《丰乳肥臀》中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作者将“大地式”的旺盛的生殖力和广博的母爱赋予了那位饱经苦难的母亲。而在另一处,母亲的形象则发生了衰变。在《欢乐》中,齐文栋的母亲是一位衰朽的、丧失了生育力的母亲。作者特别地描绘了这位老年妇女的颓败的身体:因生育过度、生存的艰辛和时间的侵蚀而变得不堪的身体。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母亲,成为少年齐文栋惟一的保护者。在这个形象中,包含着作者复杂的情感:既有对“大地——母亲”广博的爱的赞颂和感恩,又有对生命力衰颓的追悼。
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生命力主题(无论是其破坏性方面还是其生产性方面),莫言都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肯定性的主题却又是通过父辈形象才得以展开。从《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乃是站在子辈的位置上来追忆父辈的故事。小说的一开头便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这一双重的纪年方式标明了“父”与“子”的历史距离。“父辈”的生活状况以过去时态存在,而“子辈”则只能依靠对过去了的“父辈”的辉煌生命的追忆而苟活。在《红高粱家族》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族系级差:“爷爷”余占鳌——“父亲”豆官——“我”。这一“族系链”,就生命力角度言之,则表现为“力的衰减”。“爷爷”是一位匪气十足、野性蓬勃的英雄,“父亲”则在一定程度上仰仗着“爷爷”的余威。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父亲”带着“爷爷”杀敌的武器,却只是对一群癞皮狗作战,并且,在这场并不体面的战斗中,自己丧失了两枚睾丸中一枚。这也就意味着其生殖力(生命力)的减半。至于“我”,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分子,在作者看来,则是更为内在和更加彻底地被“阉割”了。与“父辈”的生机勃勃的感性生活相对照,现代的“子辈”“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有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回到“红高粱”的隐喻世界之内,作者则是将现代的“子辈”比作劣质、杂芜、缺乏繁殖力的“杂种高粱”。孱弱的不肖之子,在《红高粱家族》中尚且是一个隐匿的形象,而到了《丰乳肥臀》中,则被直接揭露出来。生命力在上官金童那里退化到婴儿状态。
由此可见,“生命力主题”在莫言那里同时还包含一个深的“文明批判”主题。与“寻根派”的一般立场不同,莫言并未以简单的历史主义眼光来看待“文明”进程,没有将“文明”处理为“进步/保守”的单一模式,而是“文明”放到“生命力”的对立面,把它看成是一个“压抑性”的机制,并由此发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
文明的压抑机制和文明与生命力之间的冲突,在莫言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莫言笔下的“小男孩”形象上。十二三岁、倔强、粗野、机敏、沉默寡言、生命力旺盛,而且有时还会恶作剧,这种小男孩子形象在莫言笔下经常出现,形成了一个系列。最早是出现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此外,还有《枯河》中的小虎,《红高粱家族》中的豆官,《遇仙》、《大风》、《猫事荟萃》等作品中的“我”,《酒国》中的少年“金刚钻”、少年余一尺、“小叔叔”、“生鱼鳞皮肤的小子”,以及《丰乳肥臀》中的司马粮,等等。这些小男孩,他们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尚未成熟,他们没有资格享受成人的权利,却必须(像莫言本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孩子一样)首先承受成人世界的生存痛苦,而且,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苦难生活的最大受害者。《猫事荟萃》、《酒国》等作品中对孩子的饥饿感的描写和发育不良的黑孩,均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更大的苦难尚不在于此。莫言在表现“种的退化”观念的同时,更注重文明压抑机制对现实生活的遏制作用,首先即体现在对儿童生命力的遏制。所谓“文明”,对于儿童而言,乃是父辈的、成人的特权。在文明的“进化树”上,儿童似乎是介于动物与人类之间(成人们的确时常称他们为“小畜牲”),是有待进化的“亚人类”,因而必须受到成人的“文明监护”。然而,这一监护首先便意味着压抑和惩戒,甚至是必要的暴力手段,以便对儿童身上残存的“动物性”、“野性”加以驯化。这样,在成人与儿童之间便存在着一个“权力结构”,“父/子”关系表现为“施暴/受暴”关系。在《红高粱家族》这样的历史故事,莫言尚且假想了一种理想的父子关系(余占鳌与豆官之间的带有较多父爱成分的保护性关系),而在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父子关系则呈现一种紧张的对抗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黑孩和《枯河》中的小虎身上,达到了残酷的程度。
另一方面,同样是在这些小男孩们身上,莫言发现了潜伏在脆弱的外部形象之内的顽强的生命力。黑孩在打了多日的摆子之后,变得更加单薄瘦弱了。当他站在成人们出工的队伍中时,生产队长不禁大为惊讶:“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这类小男孩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变成了“小精灵”,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生命意志的顽强。
短篇小说《铁孩》是一篇幻想性的作品。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塑造了两个年龄更小的小男孩。他们生活在五十年代“大炼钢铁”的日子里,饱受了成人荒诞生活所带来的屈辱和饥饿。作者赋予这两个小孩以吃铁的能力。他们吃掉了炼铁的高炉和铁块,吃掉了民兵的枪管。大人们惊恐地把他们认作“铁精”。在这两个男孩儿身上,表现出了儿童对成人的反抗精神。他们以报复的手段来抗拒来自成人世界的强暴。不过,在小说的结尾,这两个反抗的“小精灵”终究未能逃脱成人的惩戒:人们用狡计将他们俩捕获。与这两个小男孩相近的形象还有《酒国》中的那位嘴叼柳叶小刀,身生鱼鳞般皮肤的少年侠客。他的存在,一度引起当局的惶恐不安。
黑孩同样也显示着反抗的意志,只不过他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抗:他沉默。这个“被后娘打傻了”的小男孩始终一言不发,与外部世界的聒噪和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黑孩的沉默意味着对外部世界(即成人世界)的拒绝:通过拒绝语言,来拒绝成人世界的文明。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决绝态度。从另一方面,则反映文明对生命力的压抑的程度。
尽管外部世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压抑力,但生命本身却有着更为强大的代偿机制。黑孩子用沉默来拒绝与外在的成人世界的交流,拒绝进入成人生活的运作规则之中,作为代偿,他的受压抑的生命意志转向更为内在的发展。最明显的表征之一,即是转向了幻想。幻想,是像黑孩这一类少年最常见的意识状态,黑孩子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这个世界正如他幻想中的红萝卜一样,“金色的,透明”,“晶莹剔透”,是一个丰富、纯净、美丽的梦幻世界。它反衬出外部现实世界的平庸、肮脏、丑陋和残暴。莫言的许多幻想性的作品,如《翱翔》、《梦境与杂种》、《怀抱鲜花的女人》,以及《丰乳肥臀》中的一些段落,都表现了幻想与现实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并借对幻想世界的肯定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受压抑的生命力之代偿功能还表现为感官系统的异常发达。感觉器官的敏锐和反常,是莫言笔下的小男孩的共同的生理特征。少年“金刚钻”有着神奇的嗅觉,黑孩有着超常敏感的听觉和视觉,王十斤(《红耳朵》)长有一对硕大无朋、有灵性、感情丰富、“古今未有过的”红耳朵。有些孩子甚至还有诸如吃铁、飞翔之类的特异功能。孩子们的感官系统较少受到成人文明化意识的干扰,更多地保持着原始的敏锐、丰富和自由的状态,它更直接地向外部物质世界敞开。莫言赋予这些孩子们以夸张的感官,并通过他们的感官感受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
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注意到了莫言小说语言的强烈的感官刺激性。对感官经验的大肆铺张,几乎成了莫言小说叙述风格的标志。在一些作品(如《欢乐》、《爆炸》、《球状闪电》,等)中,对感官经验的自由渲染甚至代替了叙事,而成为小说的核心成分。极度膨胀的感官成了叙事的主角,它使叙事的历时性转化为当下的生命感受,同时,也使由理性的总体化原则构建起来的叙事链断裂为瞬间感官经验的碎片。莫言笔下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感官的王国,一个由瞬间的感官经验碎片拼合起来的物象世界。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支离破碎的感官世界,映现了主体内部的基本状况:那是一个充满着焦灼和渴望的、骚动不安的世界。通过小男孩的形象,通过感性化的经验世界,莫言肯定了人的感官生命和肉体存在,也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生命力。在这里,也寄托了莫言本人对生命的理想:通过感官和肉体的充分解放,达到生命的自由状态。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北国乡村,但那里的生活并非一片宁静。它既有原始的单纯和质朴,又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我们注意到,莫言很少关注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新写实派小说家),而是喜欢描写一些脱离了常轨的生活事件,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荒诞的战争、血腥的杀戮、疯狂的野合、神奇的死亡、隆重的殡葬,《酒国》中的盛宴,《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骚乱,等等。这些事件使日子非常化,如同节日一样。脱离常轨的日子总是令人迷狂,因为它使人们暂时摆脱了制度化的生活的约束,而服从于欲望的宣泄和满足。对这种反常生活场景的描写,赋予莫言的作品以“狂欢化”的风格。
狂欢化的生活与制度化的生活有着迥然不同的逻辑。前者遵循着生命本能的惟乐原则;后者遵循着理性的惟实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生活的文明化的结果,是对惟乐原则的限制和压抑。狂欢化的原则是对既定的生活秩序的破坏和颠倒。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首先即表现在这种破坏和颠倒之上。崇高/卑下、精神/肉体、英雄/非英雄、美好/丑陋、生/死,诸如此类的价值范畴的分界线模糊不清,价值体系中的等级制度被打破,对立的价值范畴在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中共生。在《欢乐》的结尾处,莫言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写作理想:“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个“完整的世界”并不能在制度化的现实中诞生,只能诉诸狂欢化的瞬间。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制度化的文体和话语方式与制度化的生活在表现形式上是极其相似的。它们都要求一个外在的权力意志赋予它们以秩序和价值尺度。从叙事性作品方面看,制度化的叙事话语要求一个外在的总体性的观念构架,借以实现对事件的编织并赋予意义。这一类作品中最典型的是历史故事。一般历史故事的灵魂是“时间”——线性的历时性逻辑,并对这一“时间”观念加以神化。在一个封闭的时间段内,历史话语赋予事件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和秩序。另一方面,历史故事还要求塑造英雄。随着时间的顺延,主人公成长为英雄。英雄是对时间逻辑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是时间的意义的呈现。因而,制度化的话语结构是对现存的世界秩序的内在维护。它肯定了现存的等级制(事物的秩序、人物的价值等级,等等)和价值规范。
在莫言的作品中,时间的链条却显得十分松弛脆弱。即使是一些表面上看属于历史故事的作品,如《红高粱》,叙事的时间链在经常出现断裂。过度膨胀的瞬间感觉迫使时间暂时中止,形成一个膨大区,如少年豆官在高粱地里对浓雾的感受。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如《爆炸》、《球状闪电》等),叙事的时间逻辑干脆让位给感受的空间逻辑,极度膨胀的感觉占据了全部的叙事空间。这些作品在几个瞬间中包含了复杂的时间经验,并且,叙事的话语空间随着感觉的扩散而充分敞开,突如其来的开头和了无结局的结尾是这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现时性的经验片断与历时性的经验片断共生共存,并相互穿插和交织。总之,叙事在时间上的完整性、封闭性和单一向度被打破,由时间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话语秩序也因之而瓦解。
与此相关的是,莫言笔下很少出现所谓“英雄”形象。正如前文所述,莫言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人物。一些较为重要的人物形象也不曾在时间的序列中变得更高大些。余占鳌(《红高粱家族》)始终是一个匪气十足的江湖人物,高级侦察员丁钩儿(《酒国》)的经历则是一个堕落和覆灭的过程,一部理想主义的沉沦史。这便宣告了制度化的时间神话的破灭。
《欢乐》也许更能体现莫言小说的狂欢化的话语规则。整部作品从头至尾记录了一位有精神障碍的中学生——齐文栋的意识活动,下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话语片断——
你的耳朵里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机器声和喇叭声,牛叫马嘶人骂娘等等也混杂在里边;你的鼻子里充斥着脏水沟里的污水味道、煤油汽油润滑油的味道、各种汗的味道和各种屁的味道。小姐出的是香汗,农民出的是臭汗,高等人放的是香屁,低等人放的是臭屁,(“有钱人放了一个屁,鸡蛋黄味鹦哥声;马瘦毛长耷拉鬃,穷人说话不中听。”)臭汗香汗,香屁臭屁,混合成一股五彩缤纷的气流,在你的身前身后头上间下虬龙般蜿蜒。你知道要毁了,蹋蹬了,这是最后的斗争,电灯泡捣蒜,一锤子买卖,发生在公路上的大堵塞,是每个进县赶考的中学生的大厄运。(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在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着多重“声音”,或者说,是多重话语系统:中学生齐文栋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活动、瞬间场景的描述、各种知识话语片断、俚语、俗话、顺口溜、民间歌谣,等等。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在同一平面上展开。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失,被淹没在多重“声音”混响的话语洪流之中。这种混响的“声音”,杂芜的文体,开放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的风格,既是感觉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制度化的话语秩序。
莫言小说狂欢化风格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戏谑”。戏谑的言辞、动作和仪式,是狂欢场面中重要的节目。戏谑,是狂欢的基本逻辑,它构成了制度化生活的权威逻辑的反面。在莫言的小说中,经常能见到一些粗俗的骂人话,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生产队长骂骂咧咧的训话,色情的比喻,如《丰乳肥臀》中对云彩的色情化描写;对性欲的描写,如《模式与原型》中对动物交媾的描写以及由此引发的主人公的性激动;对秽物的描写,如《高粱酒》中往酒缸里撒尿,《红蝗》中食草的乡民的粪便,等等。这类物质主义的描写,通常也正是产生戏谑效果的基本手段。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戏谑就是贬低化和物质化。戏谑化的话语(如骂人话)将意义降落到肉体生活的基底部,而这个基底部,则恰恰是生命的起点和始源。因而,戏谑从某种意义上说,包含着积极的、肯定性的因素,它是对生命的物质形态和生产力的肯定。
戏谑化同时又是一种否定性的美学原则。戏谑化的否定性的一面,主要是通过“戏仿”的方式来体现。在莫言的作品中,经常对那些制度化的文体进行戏谑性模仿。这类文本在《酒国》中出现得最多。《酒国》基本上是一个“戏仿”的本文。故事的主线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李一斗与莫言的通信则是对官样文体和社交辞令的戏仿,而托名李一斗所作的一系列穿插性的短篇小说,则是对现代汉语小说各类文体和主题的戏仿。戏仿以一种与母本相似的形态出现,却赋予它一个否定性的本质。戏仿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动摇的美学原则和价值核心沦为空虚,并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权威结构所赖以建立的话语基础。因而,可以说,戏仿的文本包含着至少是双重的声音和价值立场,它使文本的意义空间获得了开放性,将意义从制度化文本的单一、封闭、僵硬的话语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这一角度看,戏仿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策略,它同时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价值原则。
无论如何,莫言小说的狂欢化的话语风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这个世界就像乡村、像大地、像季节轮换、像播种与收获,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
(本文受上海市高等学校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