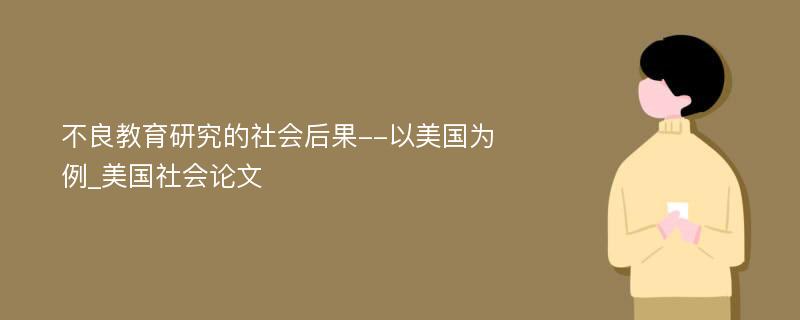
不良教育研究的社会后果:以美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后果论文,不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4)03-0017-05
一、美国公共教育由于研究遭到的责难
众所周知,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遭到了许多责难与攻击。这些责难与攻击有来自全国委员会的、大众媒介的、专业团体的,也有来自个人的。(注:1950年前后,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联邦政府将教育视作赢得美苏军备竞赛、保持美国科技领先的重要手段。这时的美国公众也开始要求学校教育提供比较高水平的教育来提高自身素质和生存能力。但人们似乎发觉现存的学校教育质量低下,问题众多。史密斯的《狂热地教学》(1949)、贝尔的《教育中的危机》(1949)、林德的《公立学校的大话》(1953)、贝斯特的《教育的废墟》(1953)、史密斯的《萎缩的心智》(1954)等著述都强调了美国公立学校的盲目性和没有效率。1957年前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更引发了美国政府及民众对学校教育的批评与指责。)这些攻击有学校教育内部自发产生的,也有社会外部推动产生的,还有政治领域的介入产生的。
自从1966年“科尔曼报告”(注:科尔曼报告的名称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该报告认为,教育中有五种类型的不平等:社会投入不平等、学校种族构成不平等、学校特点不平等、学校对相同能力和背景的个人产生的教育效果不平等、学校对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个人产生的教育效果不平等。)出台以来,教育研究者们便开始通过实证研究来收集大量的资料,以此考察学校教育的局限性,而不是去发掘学校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潜力。加纳·迈雷戴尔(Gunnar Myrdal)指出,社会研究的方向及结论“通常来自主宰我们社会生活的政治利益”。[1]因而,人们发现教育研究者们总是蜂涌而至去创造统计资料和统计数据,以此来揭示公立学校教育不是处于“贫血”状态,就是处于“残废”状态了,甚至更加危言耸听地抛出“我们所有的公共教育系统正趋于土崩瓦解!”的口号。[2]对于许多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统计资料似乎标志着公共学校教育已处于瘫痪状态。迈雷昂·里伯曼(Myron Lieberman)的研究甚至走得更远,他把199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定名为《公共教育:一具死尸》(Public Education:An Autopsy)。对公共教育作出这样一个死亡诊断的做法,正如迈雷戴尔所认为的那样,文化背景和政治形势常常会诱使研究者们采取投机性的做法,使其研究结论与政治或文化偏好相吻合,从而形成自己选择的研究方法,打造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模式和理论,创设为观察而观察的方式,然后提供与政治、文化合拍的研究结论。迈雷戴尔认为这是研究工作中的制度偏见,更为甚者,这是人为制造的计算机般的研究程序。[3]
近年来反映在美国《教育研究者》杂志上的一些研究文章,基本上是建立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端基础上的。比如说1994年4月和5月该杂志刊登的《金钱重要吗:不同的学校投入对学生产生结果的影响的元分析研究》和《金钱在一些地方重要:对赫奇斯、莱恩和格林沃德的回应》两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对教育中定性与定量研究之争端的解决,杜威早在1929年在其《教育科学的资源》一书中主张:所有的良好研究必须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定性观念基础上的,当调查的问题缺乏普遍的意义时,无论怎样细腻的统计措施都是毫无科学价值的。当然,对于非统计性的研究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无论你做得怎样精彩,也难以显现出什么科学价值来。
二、对社会科学研究要承担社会责任之伟大传统的抛弃
撇开把社会研究人为地分为定性与定量两大阵营的问题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似乎抛弃了迈雷戴尔所谓的“社会科学的伟大传统”:即社会科学家对公共教育承担着直接和间接的责任。[4]社会科学家们不仅把自己对公众教育的责任扔得一干二净,而且还把研究关注点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的局限性上面。比如说克里斯托夫·詹克斯1972年出版的《不平等:对美国家庭与学校教育影响的再评价》,引发了许多关于“非学校影响”的研究。詹克斯的研究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认可,尼克松总统的学校财政委员会也使用詹克斯的著述来为其有关处境不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观点辩护。詹克斯在《不平等》中有这样的观点:就学校财政而言,我们极有可能已经开支过大,事实上,学校的财务开支好像对学校成就并没有根本的影响。有人认为詹克斯的这个发现是众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5]有谁能够想象得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居然进行这样的研究:大学教育并不会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变,因此,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也许太多了。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大学教育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是积极而巨大的,因而政府应该保证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拨款。[6]
就像迈雷戴尔对“非学校影响”研究所期望的那样,他评价说“圣经中所讲的‘他寻找,他便找到’是真理;如果科学家寻求还不存在的东西,他将会发现它的。只要实验证据不充足,他就会使用逻辑来扭曲事实”。[7]在寻找不存在的研究问题这个问题上,一位幽默大师曾警告说,你不能通过拍摄鸭嘴兽没有在下蛋,便以此去证明它不下蛋。难怪,在非学校影响的研究中,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变量无法自圆其说,研究者们还是要把其作为对学校影响的对立面提出来,他们通过找不到证据的方式来证明所研究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金钱重要吗”一文中,提出金钱重要吗?去问你的亲戚、家人、邻居、银行家、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吧!可就是没有提去问问五角大楼里的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詹克斯的《不平等》问世之后,过了22年后的1994年,人们依然还在对中小学教育中金钱是否重要的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个研究问世的时候,还有研究表明(即前面提到的“金钱在一些地方重要”一文),资源投入与教育结果两者是呈正相关的,这对每一个老师和家长来说,已是不争的常识了。然而,当缩减教育开支成为一项政治政策时,研究者们便只有努力去寻求机会为自己获取资助了,只有通过摧毁传统智慧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了。
根据迈雷戴尔的看法,为收集和解释资料而使用的繁琐统计方法通常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产生偏见。他认为,教育研究者需要首先提出价值前提假设,然后对研究进行实践意义的相关性检验,这个实践意义是指教育能否有助于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许多标榜为弱势群体代言人的研究者,很快就认可了探讨学校教育的局限性而不是其潜力这一类研究及其相应的公共政策。许多教育研究者也是在选择研究手段而不是在选择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问题,尽力去设置条件证明其研究前提,或者是着手去测量最容易测量的方面。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对这样的科学家实在没有一点忍耐心,他们拿一块木头,寻找最薄弱的地方,然后在这些最容易钻孔的地方钻上许多孔。”[8]
对于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社会意义的关系,发现其没有联系比找到其有联系要容易得多。一些研究者运用一系列繁琐的没有必要的统计方法、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式和一大堆晦涩难懂的术语,让他人对其研究产生一种科学客观性的印象,去掩饰虚假的判断和本来就有问题的前提假设。这其实是在使问题变得模棱两可,掩盖研究者思想观念的贫乏,是在为普通大众与一些钻牛角尖的专家们之间制造一个理解的屏障。用迈雷戴尔的话说就是“虽然社会科学的伟大传统是尽可能清楚而简洁地表达理由,可在近几十年里,社会科学家们倾向运用一些不必要的繁琐手段和陌生的术语来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一来就削弱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相互理解的能力,有些时候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了”。[9]这种情形在所谓的定性研究中也并不少见。迈雷戴尔注意到了模棱两可的技术语言变成了大量高度抽象的思维训练工具。反倒是,一些能够直截了当、简明扼要、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观点的研究者却遭来了同行们怀疑或鄙视的眼光。有些学者由于没有使用晦涩的术语和语句、繁琐的方法,便被人怀疑其理论研究水平和抽象思维水平不高,理论思维方法不够高级,甚至被嗤之以鼻为还没有入学术之门,而且同行们还拒绝接受其阐述的观点。
三、带着政治目标的教育研究报告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1991年由基础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每个学术科目的年级标准。据基础教育委员会所讲,这个标准是由各个学科的国家专业委员会根据国家课程大纲拟订出来的,它“代表了目前这个领域中的最高智慧水平”。[10]现在来看看这个标准中提出的在2000年时四年级学生需要达到的标准吧:“流利地表达和顺畅地撰写观察和实验报告”(恐怕1991年的四年级学生在2000年时,仍需要呆在四年级,力争达到这个标准)。请问,到底有多少学术人士能够“流利地表达和顺畅地撰写观察和实验报告”?更不用说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其实,这样的国家标准无非是一种政治目标的反映。1990年布什政府里的美国教育目标小组制订颁布了“美国教育六大目标”,[11]其中的一条规定:到2000年,美国所有的儿童都要对上学作好准备。后来的克林顿政府把目标定在为学生测试制定国家标准。1993年9月8日,当时的教育部长举行了“美国成人脱盲”(Adult Literacy in America)的新闻发布会。“美国成人脱盲”是由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为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所作的调研报告。当时,美国三大网站的晚间新闻里便出现了大多数美国成人不能阅读的“惊天动地”新闻条目。1993年9月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标题为“研究表明美国有一半的成人不能阅读或者不会计算”的“悲惨故事”。事实上,这种秋风扫落叶似的断言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一些大众媒体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对其大加渲染,以求达到刺激读者感官的效果。而且,这个研究报告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在学术界也没有受到挑战,并且还被学界接受了。这个研究报告事实上是10年前对学校教育进行毁灭性攻击的一个报告的继续,即1983年由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其中列举了危机的证据:学生学业成绩的国际排名由10年前(20世纪70年代)名列前茅而落至倒数一、二名;约有2,300万人是半文盲,17岁人中半文盲高达13%,少数民族青年中则高达40%;中学生标准化测试成绩竟然低于前苏联卫星上天时的水平;一半以上的天才学生所测得的能力与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不相称……[12]其实,2001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公布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的教育改革蓝图及其随后(2002年1月28日)签署的“2001年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意味着美国的公共教育并没有让每一个儿童受到满意的一流教育。因而只有由政府出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此法案中的“绩效责任”、更多的家长和学生选择等规定无疑其政治意义大于教育意义。
我们再回头看看前面有关文盲和脱盲的问题。事实上,到底什么样子算是文盲和脱盲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的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把脱盲(或有文化)界定为“可以使用印刷的书面信息来对社会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发展个人的知识潜能”。[13]撇开这个定义的模糊性不谈,恐怕许多人宁愿声称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发展了自己的知识潜能,而不会自觉自愿去做那个可能是证明自己无能的冗长测试。“美国成人脱盲”报告者声称此报告是以全国13,000个成人(16岁及以上)和27,000户居民的代表性样本为基础的。但美国的一些研究者对本报告持高度的质疑。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样本中的移民比例远远超过了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且这些移民从未在美国上过学。另一事实是,这个样本中的弱势群体(即上学年限、考试成绩和经济条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占的比例特别大。更为甚者,样本中1/10的男性是关押犯或服刑犯人,他们谈得上“在为社会发挥作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发展了个人的知识潜能”吗?而美国的服刑犯人还不到全国男性人口的0.8%。这个“科学”研究中的取样超过了正常情况的1200%。报告认为,考试分数与学校教育年限呈显著正相关。在27,000户居民的测试中,测试成绩为低水平的占25%,几乎1/5的被试视力有问题,在普通灯光条件下不能很好阅读印刷材料,更不用说还要在一个陌生人的监控下限时做完测试了。而且1/4的被试中,有的身体不便,有的精神有问题,有的健康有问题,这种情况对于他(她)们完成一个正式(有人监视和限时)的测试来讲,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再说,这个报告并没有交待在调查中到底有多少人拒绝接受这样的测试。其实,那些工作、学习非常忙的人肯定是不太可能参加这样的测试的。由此看来,这个调查研究的设计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有问题的调查研究能够得出值得信赖的结论吗?事实上,许多测试类的调查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有问题嫌疑。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教育研究者在内,之所以运用一些复杂而且繁琐的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模拟结构程序来产生一大堆数据信息及其分析图表,无非是想借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术声望。他们是想以研究方法的新奇、复杂、“科学”取胜,而并不是想以对研究结论的人文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去承担伟大责任。
四、教育研究理应追求实践性与普适性
在研究专业领域多如牛毛而且日新月异的现时代里,意味着人们虽然学得越来越多了,但却知道得越来越少。这种现象通常被人们称之为“知识爆炸”。结果,我们便忽略了知识的综合性。综合知识有助于我们去对所学知识进行概括和运用,从而用来解决有社会意义的实践问题。今天,包括师范学院在内的高等学校,都必须为践行改善社会之使命而进行研究和提高专业实践水平。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研究并没有为社会目的服务,而不过是在为奠定学术声望装点门面,有时甚至是在损害民主与平等,在损伤一些行业人士的声望和信心。由此看来,处于第一线的老师应该能够对教育研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通过最可靠、最可行的证据去维护自己工作的价值并去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按道理说,学校教育实践者们(教师)能够比其他人更为有效地检验教育研究结论的实践性和普适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说,我国目前来自专业研究人员的有关新课程、新课标、新理念方面的研究文章不计其数,可一线老师几乎是没有质疑地照收不误,甚至是盲目抛弃自己本来就有效的做法去效仿研究文章的提议。
又如,《美国教育研究杂志》1992年春季刊登了一篇由简·汉纳威(Jane Hannaway)撰写的题为《对高级技能、工作设计及动机的分析与建议》(Higher-Order Skills,Job Design and Incentives:An Analysis and proposal)的文章,该文对于在课堂中如何培养高级思维和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的论述得并不充分。汉纳威教授是个教育组织行为理论家,她是从行为决策理论和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并没有把其作为课程问题。结果,她作为组织理论家,提出了一个“奇思妙计”:主张把学校教师分成两类,一类教师专门教基本技能从而确保学生至少掌握了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另一类教师专门教高级思维和解决问题。她认为这样的分法不仅可以保证比较高的教育质量,而且在为不同学生服务方面将体现得更加公正合理。试想想,在同一个学校里,把教师分成这样两类,谁有资格说他就是专门教高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况且技能与思维的二元论在教学实践中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研究的出发点可能是有些荒谬的。
在教育领域里,我们已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和实践基础,如果我们的教育研究和学校实践对其视而不见,那就只可能随着社会政治潮流去作无序地、无望地流浪。我们的教育研究要想成为良性的研究,就需要作好经得起教育实践检验的准备,就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不是把支流作主流。
综上所述,不良的教育研究是对学校教育成效没有尊重而对其大加指责、对从教者提出过高的责任负担、对教育之精神意义和社会意义评价太不充分、并且把研究的社会责任抛在脑后的研究,是通过繁琐研究方法来寻求研究之科学性外观的研究。不良教育研究的后果在于盲目跟政治之风,哗众取宠、自欺欺人,打击人们的精神士气,摧毁人们对追求美好生活和教育理想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