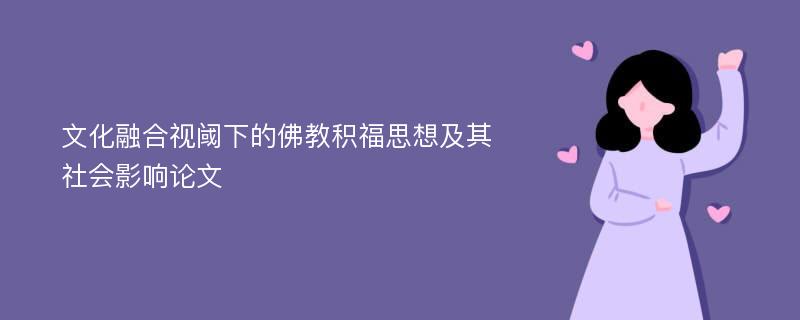
文化融合视阈下的佛教积福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雷火剑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 积福是佛教信众践行佛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佛教积福思想的自主性、普惠性、自受性和虔诚性特点,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积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积福观念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不仅扩大了福报对象的范围、推动了积福主体的人本化和积福方式的简易化,而且增进了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 佛教 积福思想 文化融合
福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诗经·小雅》中较早出现了关于积福的观念:“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周礼》有“六祝”的记载,分别是:顺丰年、求永贞、祈福祥、弭兵灾、远罪疾、逆时雨宁丰旱。《韩非子·解老》说:“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由此可见,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积福观念,包含了个人与家族的平安长寿、富贵康健等内容。积福,在中国古人看来,是“索求于上神,降福与去灾耳。”[1]
为了验证破坏准则的准确性,选取Ehab F. El-Salakawy所做的试验共涉及6个板柱节点试件,运用2.2中的承载力公式进行计算分析,以验证其准确性。
一、佛教初传时期的积福观念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此时中国传统积福观念有了新的发展。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讲,“福者,備也,从示,‘畐’声”。《礼记·郊特牲》说:“富者福也。”《释名·释言语》也说:“福,富也。”东汉桓谭在《新论·辩惑第十三》中也讲:“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在汉代人看来,福、富相通,涉及广泛,包括了顺丰年、求永贞、弭兵灾、远罪疾等与利益关联的内容,并且求取积福的方式多样,有树立祠祀,陈设墓葬,修炼方术,或者巫觋占卜等。贾谊曾说:“人心以为鬼神能与于厉害,是故具牺牲俎豆粢盛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2]。这类观点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汉代人对积福的认识。汉代社会普遍认为人的魂魄可以长存,肉身也可以通过神仙方术等手段得以永生。同时,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像佛教一样的地狱观念,人对死后归属黄泉、幽都等世界是抱有怀疑和焦虑的。这种焦虑寄托在信仰上,并通过当时的墓葬情况反映出来。
汉代中央政府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个人内心的问题,为宗教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此时代背景下,佛教传入恰好填补了汉代人的“信仰空洞”,如康僧会与孙皓诘问:“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3]佛教的初期定位,就在于帮助人们解决与生死、善恶、福罪等困惑。正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核心教义的四谛、八正道等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反倒是善恶报应、灵魂转生等很快为社会接受。这类佛教思想与上述信仰焦虑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祈福的一类形式。
汉代神仙方术,往往通过符咒、治病、祈福、禳灾等方式去灾求福,当时佛教为了迎合信徒需要,也使用占验、卜卦、看病等方术弘扬教义。像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疏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4]。当时佛教借用传统宗教的某些概念,立“浮屠”之祠以求福,这也是帝王垄断的一项特权。三国时,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熟课读佛,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道者听受道……每浴佛,多设酒饭”[5]。可见,当时人们诵经拜佛,未必都是真信仰,像笮融这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慧皎曾批评说:“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皈戒,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6]。由此可见,不以佛教戒律为皈依,所以说“道风讹替”,而在形式上又“设复斋忏,事法祠祀”,正是因为当时社会把佛教理解成“祠祀”的一种,达到祈福的目的。佛教原本认为解脱生死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多数人更在意死后境遇的好坏,也更愿意相信佛教教义对轮回世界的解释,并不关注“涅槃”、“解脱”等佛教核心教义。曾有人引证尚俭的言论来诘难佛教最为典型的积福方式——“布施”。牟子认为按佛教教义布施行善,表面是“不孝不仁”,其实是一种“见其大不拘小”的做法。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期,佛教教义与传统道德伦理之间的龃龉,以及当时人们对佛教积福的片面认识。因此,在初传时期,佛教的积福思想在古人头脑里,更多的是一种关乎“追寻一己之福”的宗教信仰实践,其实质是对本土原有文化传统的一种回归。
二、佛教积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积福观的区别
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区别,佛教积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积福观还是实现了思想的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大量大乘佛教经典流入并被翻译,教义不断被阐释、完善。佛教也因宣扬三世果报和净土世界,迎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理需要,在各地迅速传播开来。此时,佛教社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信仰形式也发生改变,并直接影响了后来隋唐佛教的发展。
(2)由于锅炉汽包水位系统特征在实际工业过程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故该项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对其它工业过程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该种方法对改善实际过程控制系统的控制性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是在实践操作上,佛教与中国传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印度佛教讲,修三福业——世间福业、世出福业、平等福业都应以至诚心布施供养而获得。这是破除人的贪悭心,无所执着的供养功德。而传统积福则要求祭祀者内心保持一种“祭如在”的状态,是抱有种种目的,有所待的一种行为。
三是受报的主体相异。在中国传统伦理看来,积福的实体未必是行为者本身,还要惠及子孙、宗族。而佛教主张自受自报,无有他人代受。《佛本行集经》说:“因业报应,非虚空受,但是众生造善恶业,随业因缘而受是报”。这种业因不会随世界成、住、坏、空的流转而消逝,所以《十住毗婆沙论》中有佛偈:“大海诸名山,丘陵树林木,地水火风等,日月诸星宿,若至劫烧时,皆尽无有余,业于无量劫,常在而不失”。任你本领再大如佛陀一般,也逃不开业报的降临。这一区别反映了佛教对个人解脱、觉悟的重视,而传统积福观则是放低了个人,将积福放在家族血亲等社会伦理关系当中去考虑。
三、佛教积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积福观的融合
一是善恶报应论不同。传统积福观认为人的报应将由上天赏善罚淫,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佛教则归为自身的“业力”,万法唯识,一切善恶业皆起于自心,一切果报亦当自受,自身的福报是自己言行引发,是内在的承担主体。佛教业报论的实质,在于说明命运掌握在众生自己手中,高扬舍我其谁、敢于担当的理想人格。
从整体来看,佛教顺应历史趋势,从三方面实现了与中国传统积福观的融合发展:一是因果报应思想,二是慈悲济世思想,三是福田思想。在公元四至六世纪的佛教造像、写经提识、发愿文、忏悔文等活动当中,就体现上述三点特征。如池田温在《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中谈到,“信仰者的写经愿望,第一是为自己及血缘的父母、祖先的祈福禳灾;第二是把这种良好的愿望推及广大众生;第三是祈愿国祚无穷,把信仰解脱与政治希望绑定在一起。在三种形式的需求当中,由积福而带来的心理满足,实际上仍未脱离祈求福业目的,但是这种行为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血亲以外的人群(慈悲济世思想)。同时,抄经行为本身也是对佛教福田思想、因果报应思想的内在认同。像后来的盂兰盆节、超荐祖先亡灵等活动,其重孝敬亲与出家修行行为并未割裂,反而以积福的形式得以体现。另外,从两晋、南北朝的佛教石刻碑记内容来看,各少数民族确实也因佛教信仰而聚邑、结社”[7]。这些行为使得佛教客观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也缓和了社会上下层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融合中,佛教的积福思想就跟“原先积善造殃的传统善恶报应观思想接榫了,也很容易产生一种以某种代价来换取佛教拯救的思路。不止是抄写佛经,造像建寺、行忏发悔等行为的目的也可与此对照。同时,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和根据佛典的附会说法,促成了佛教末法史观思潮的产生”[8],从而刺激了信众希求净土,向往安乐世界的愿望。而佛教净土法门以福慧资粮为基础,又多以念佛、造像、行善为功德,也广泛地推动了社会积福活动的开展。
四、佛教积福思想的社会影响
(一)福报对象的扩大化
在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强调积福主体方的利益,而忽视积福对所奉求客体的影响,甚至当神灵“冥顽不灵”的时候,还可能被人所摒弃。但在佛教看来,积福主体和过程涉及的一切生命客体,都会“分有”福报。如《宋高僧传》卷27载,唐咸通智广法师于“光化元年修天王阁。向毕乃循江渎池咒食饲鱼。经夜其鱼二尺已上。万亿许皆浮水面而殒。聊蹑流水救十千鱼生忉利同也”。大鱼因为受咒食的功德,福报成熟自然托生忉利天,而法师亦因护生爱生之心,在道业上得顺缘相助速成正果,这说明积福的主客体双方在过程中得到了各自的解脱。
从玉米种植结构调整模式效益对比调查表看,种植普通玉米亩产500公斤,按市场价1.4元/公斤算,亩产值是700元,去掉亩成本500元,亩效益是200元;通过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以杂粮类谷子生产为例,谷子亩产250公斤,按市场价5元/公斤算,亩产值是1250元去掉亩成本700元,亩效益是550元。比种植普通玉米增收350元,效益可观。目前我县正在大力发展有机谷子,今年全县的种植面积4000亩,转换期收购价16元/公斤,每亩产值4000元,扣除1000元/亩成本,每亩纯收入3000元。种植谷子相对种植普通玉米费时、费工、人工投入较高,但是亩产经济效益高,能够增加农民收入。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古人的积福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根据佛教经典,人在死后,将依所造业力轮回,三世因果真实不虚。又因为善恶因果的“异熟”,行善之人很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报偿,这类看不见的因果观念仍会造成人思想的焦虑。而大乘佛教是以众生的解脱为终极目标,开展积福活动更多是为众生,不单是为个人、家庭、血亲谋福祉。如僧传中建立浴池供大众洗浴,设普福二田、药藏供济贫苦,以及放生池、爱生护生等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儒家“恻隐之心”“推己及人”积极入世的另一种表达。在佛教积福思想的支配下,积福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现世利益。
二是积福的目的相异。传统积福观虽然有灵魂不灭的思想,但并不认为人死后灵魂会根据生前的善恶行为而轮回转生,善恶报应一说大多是直接与个人、家族的利益相关的希求。而佛教的积福是放在相对较高的位置和广阔的范围来讲的,统括了三世因果的时空范围,其目的是个人与众生的最终解脱。
(二)积福主体的人本化
中国传统积福观念仍是在强烈暗示一种标准的社会秩序,以社会、国家、家庭秩序的合理维护获取福报。此外,民间也多认为,通过对神祇的祭祀与供奉来祈求愿望福业的达成。福在此又成为外在于人的神祇或神秘力量的赐予,主观意志顺应了这种力量,就能获得积福。这表明,古代中国人信奉的是一种“他力救赎观”。而佛教认为,积福主要还是修行人往生净土、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六祖慧能的开悟偈讲“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本自圆满的清净自性,功德具足、福报具足,何兴之有。显露自心的无穷能量,以此获得解脱,是典型的“自力救赎观”。佛教徒通过自身长期的修行,以至“无我”、“无作”的境界,一方面在俗谛上肯定了积福在事功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从胜义谛的角度讲缘起性空、当体皆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体现了积福理论的圆融智慧。同时,传统积福观认为福祸相互依存,现在的福可能潜在着未来的祸,是“福祸转换”的观点。这种辩证的福祸观,实际上还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现世伦理,关乎的仍是与利益有关的事物。而佛教不仅是辩证地看待福祸相依的道理,还积极地引导祸向福的转变,最终达到福祸俱亡的境界,是“福祸转消”的观点。这些都使得佛教积福主体呈现人本化特征。
融入语境设想,让学生有更多对话文本的机会。如在《天游峰的扫路人》教学中,针对天游峰的奇特景象,不妨建议学生思考:如果你在游览天游峰的时候,见到了这些扫路人,你想与他们畅谈什么呢?很显然,这样的开放性话题,让学生能够有更多自我对话文本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在主动融入文本中形成更多的深刻感知。很多同学在设想中认为,自己真想与扫路人一起扫路,体验其中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辛。有的同学说,扫路人每日登山不是为了赏风景,而是专门寻找败笔,我们游客应该换位思考,不能再随手乱丢垃圾。有的同学说,阅读了此文,让自己感受到劳动最伟大,只有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才能收到别人的尊重,等等。
(三)积福方式的简易化
布施、六度、抄经、忏法等内容丰富的积福形式,借着大量民间神通感应的事例,迅速在社会各阶层铺开,其简易易行的特点,也适应了普罗大众的需求,从南北朝到隋唐,乃至当下都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将“无形的宗教解脱转化为可见的现实利益,不仅拯救人的精神、灵魂,给人慰藉与期望,而且赐人以现实的福利,解决人当下面临的痛苦”[9],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同时,由于在中国宗教行为都会被纳入社会优先于个人的传统伦理规范,佛教积福观念的动力源泉也在于自觉地服从于这种“规范式伦理”,即以少数人教化千百人,从而造就一种“大同”社会。在此理论涵盖下,佛教的福报许诺已经偏离了纯粹的个人信仰,而参与到社会秩序的整顿、传统道德的维护和伦理规范的重建中。
(四)增进了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协调统一
如果从事功的时间发展及涉及的对象范围考量,佛教积福有一个由个体向大众发展的趋势。这不仅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下的佛教本土化的结果,也是因为佛教徒必须彻底地实践经典理论所开示出的觉悟之路,体现了一条“经典佛教”向“人间佛教”转变的轨迹。在此形势下,积福是一种极具亲和力的宗教传播手段,自然成为了佛教实践其理论的契入点。实际上,这种趋势大致是沿着两条路径分化的,即关乎个体境界的宗教性追求之路和涉及公共群体关系的伦理规范之路。前者是涉及个体性私德的,比如造像、建塔、写经、诵经、供佛等。它们一般由个人的,或者带有个体色彩的宗教行为构成,以个体关怀为目标,一般更多关乎积福者本人的生活祈求、精神寄托和信仰修持等,而无关乎集体人群的福祉。这类积福的目的,基本上仍是与现实的利益或一己之福联系在一起,带有浓重的个性特色。而涉及公共群体关系的伦理规范更多表现为公共福利事业,比如建寺、施药、施粥、浴僧、掘井、济困、修桥、铺路、净财经营等。它们普遍都是以群体性的需要为出发点,既满足了个人的情感需要和宗教实践,又利益了广大众生,使得后者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信众皈依,为佛教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涉及公共福利事业的积福实践也会更加广泛和深入,这对当代福利事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贾谊新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陈寿,裴松之 .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6]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张志云.浅析中国佛教的慈善思想渊源[J].延安大学人文学院学报,2006,(04).
[中图分类号] D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03(2019)03-0063-04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雷火剑,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博士研究生,中共南宁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梁世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