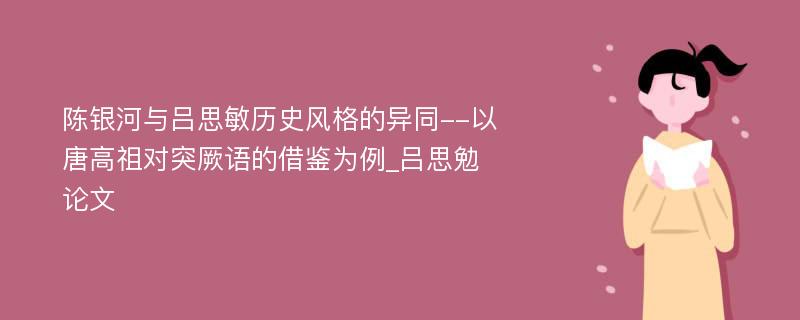
陈寅恪、吕思勉治史风格的异同——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厥论文,异同论文,为例论文,风格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2-0132-09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以下简称“陈文”),最初是在蒋天枢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论著编年目录中看到的①,有关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曾见之于吕思勉的史著,故认为称臣事应是史界的共识,并非悬而存疑的“公案”。然碌碌无暇,未找来陈文细读,更未将陈、吕著述勘对比较。后读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下文简称“余文”),说陈寅恪此文,一望而知是针对解放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发,“陈先生本与人为善之意,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余英时为证明他的推断,提出两条理由:(一)陈寅恪关于此事之考证早己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文称“陈书”)。陈文之要旨实已全见于此。然陈寅恪竟在1951年特撰一文,郑重发挥此旨结之以“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的激励之语,其借古讽今之意十分明显。(二)借突厥以指苏俄,已见于陈寅恪1945年所写《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议感赋一诗》,说:“通过这首诗便能彻底了解《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一文的命意所在了。”②因读了余文,遂引起我读陈文、陈书,探究余文所谓“命意”的兴趣,又由“命意”进而略说陈、吕两位大家的治史风格。所论是否得当,敬请学界同人指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1941年写成于香港,1943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易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③该书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节,引《旧唐书·李靖传》叙高祖称臣突厥事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按:突厥可汗),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授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以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④
细读陈书的这段文字,实是陈寅恪的叙史,而非考史。换言之,陈寅恪并未说高祖称臣突厥的史实为他的新考证。查阅吕思勉的史著,最早记叙此事的是他的《白话本国史》,此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⑤,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有销路的一部书,严耕望说这部书是他所读的第一部中国通史,30年代中期他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对当时历史教学有相当大的影响。⑥然而《白话本国史》所述,也是叙史而非考史。20世纪上半期出版的一些中国史著述,对此事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如1922年出版的王桐龄《中国史》⑦,1932年出版的李泰棻《中国史纲》⑧,1934年出版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⑨,同年出版的章嵌《中华通史》⑩,1940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11),1944年出版的廖凤林《中国通史要略》(12),1946年出版的蓝文徵《隋唐五代史》等(13)。其中,邓、章二书,是“大学丛书”;钱、廖、蓝三书,是部定大学用书,都是当年流行较广的史著。
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按旧史家之观念,实在有损脸面,固常有忌讳或语焉不详。然按现代史家的眼光,则其之所以重要,乃关涉唐初的对外形势。因此,不仅在专业的史著,即便是中学历史科教书也都有涉及。如吕思勉撰写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1924年版)、《高级中学教科书》(1934年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年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5年版)等,(14)对此都有清晰而简要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吕著《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原是学生高考复习用书,体例上以问答形式列出中国史上348个问题,其中第138题问“唐初之武功如何”?答案涉及北方的突厥、铁勒,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东北的奚、契丹、室韦,西南的吐蕃等,也记及高祖称臣突厥事。其所述的主要内容,与陈书及吕著其他史书基本相同。《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出版后颇受学生欢迎,曾一再重印,至1937年出版改订本第五版,1943年有成都(蓉)商务印书馆的订正版的《复习丛书本国史》,在“问唐初之武功如何”一节,以括号方式注有“湘五、成都、山西”六字。其他题目也有类似的注文,如“问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如何”题后注有“赣二十二年、北平、粤”。“问郑和使西洋之事如何”题后的注文是“赣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等。所谓“赣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即表示1934年江西历史考试用到此题,1932年浙江历史考试用到此题。上文提到的“湘五”自是指民国五年湖南的历史考题,可见“唐初之武功如何”及高祖称臣突厥事,大约在湖南、成都、山西等地历史考试中有所涉及,至少在当年已成为部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内容。
清末民初的通俗史家蔡东藩,在1916-1926年间撰写了一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其中《唐史演义》的第十五回“偃武修文君臣论治,易和为战将帅扬镳”,也记有高祖称臣突厥事。(15)这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出版之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到1935年,蔡氏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加上他与许廑父合著的《民国通俗演义》,总计44册,全部改印,成为一部风行全国、销行数量很大的历史通俗书。(16)
以上是高祖称臣突厥一事,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史界、历史教学界、历史通俗读物中的流传情况。其实,高祖向突厥称臣一事,大约在贞观三年后的《国史》、《实录》之类的文献中已有肯定性的记载(17),故后来的史著多有叙述或评述。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九》内,就有肯定性的记叙。范祖禹的《唐鉴》(下文简称“范书”)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此事都有专门的评述。《唐鉴》卷一云:“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18)《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七)”云: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入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国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挟,机有可乘,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19)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下文简称“王书”)卷九十二《新唐书》二十四,就有一条题为“高祖称臣于突厥”的札记,王氏云:“盖高祖起事之时,依仗突厥,屈礼称臣,乃其实也。”(20)王书在晚清乃至民国年代很受学界推崇,读过此书的学者,自不在少数。
《资治通鉴》、《唐鉴》、《读通鉴论》和《十七史商榷》等,都是较常见的史学著述,记有此事的史著一定还有不少。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推断: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早先也非隐晦不明,经过20世纪诸多史著、教科书,乃至历史通俗演义的书写叙述之后,至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此项史实已成为史学界、历史教学界之共认的常识,陈寅恪也未必不知,故陈书、陈文在叙述此事时,并未说这是一桩新考证、新发现。在之前和当时的史学界,也未见有学者对此事提出过质疑或相反的看法。(21)如此说来,陈寅恪在1951年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时云:“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为拈出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似乎不合史界的情实。此时仍说此事是“一重公案”,恐怕只是陈寅恪为撰写此文而拟加的托辞。这似乎可以为余英时的推断(即说陈文的命意是“借古讽今”)提供第三条证据,至少可以为余文及其后续的讨论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22)
就高祖称臣突厥事而言,本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陈文的命意自也不在考证,但此文的样式却是陈寅恪考史的典型,是一篇颇能反映陈寅恪治史风格的考证文章。关于高祖称臣突厥事,陈书的叙述仅用二百五十余字,而陈文则写了六千五百余字。主题虽然相同,但具体史事深入坐实者甚多。陈文较长,此处不能全录,只就笔者的理解,归纳其考证的要点有三:
(一)考证“狼头纛”实如同中国之印绶,是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用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有服从称臣之义。北方群雄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由此证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其,为其附庸。
(二)考证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由太宗主持于内,刘文静执行于外。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刘文静、长孙顺德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
(三)太宗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即太宗与突利用突厥之法,结香火之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23)
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可知陈书、陈文的一些考证片断,早在30年代陈寅恪研读校治新旧《唐书》时,已有眉识式的读史札记。在《编年事辑》1939年内录有陈寅恪校《唐书》时的眉识二条:
(一)案突厥语:大度,事也;毗伽,解也;可汗,天子也。故“大度毗伽可汗”为音译,“解事天子”为意译。当时突厥封号中国特起之酋豪,俱如此例。或者误因可汗天子并称,谓是二种徽号,遂附会木兰诗定位此时作,盖不知此义所致也。
(二)称臣突厥,乃当日崛起群雄所为者,非独唐也。然文静佐命功最多,实太宗之党,裴寂则高祖亲信,时借以胁迫高祖,其才智功勋皆非文静之比也。(24)
这两条眉识,记于1939年,其主要内容后来都写入到陈书和陈文中,可见陈文所云“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并非套话。将上述材料联系比较,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些陈寅恪治史的途径和特色:
其一,学者常谓陈寅恪非常强调历史研究中的新材料,有所谓“预流”一说。但就他个人的史学实践来说,主要下功夫钻研的,恐怕还是普通常见的史籍。他的治史,以精读精校常见史籍为日课,在精读、熟读史籍的同时,写读史札记(眉识),以此为积累进而撰论文、写论著。
其二,陈寅恪考史,印证史实,不嫌重复;列举证据,不嫌繁多。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而为其附庸。此点原无可疑,通常不必再去找证据来再加证明。然陈寅恪则一事一节都不放过,从对“狼头纛”的考证,来证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而为其附庸。又进而考证李唐改旗易帜,树突厥之白旗等史事。
其三,陈寅恪的史事考证,以能坐实史实为最终目标,或也是他考史的最高境界。高祖称臣突厥,谁是主谋,谁是计划的执行者,陈文的考证无一不落到实处。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和《桃花源记旁证》等史著,此种特征也极为突出。
总之,陈寅恪的史事考证,思路上偏好往深度走,好坐实史事,好循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做细节上的大胆推论。所谓精细深入,钩沉发微,尽显史家的真功夫。钱穆说陈寅恪的行文叙事枝节蔓生(25),实与此种考史的风格有关。然就考史而言,引证不嫌重复,证据不嫌繁多,似也当如此。但史事极其复杂,称臣突厥是否必受其封号;受其封号,是否必并受其“狼头纛”,自有多种情形,故陈说“固可通,然非唯一之可能”。(26)与突厥通谋,刘文静是主要执行者,此点史料上有证据;说太宗“实为当时之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则系推论。读者不可径将推论视同于实证。且考证之过于深入求实,偶尔也会有“为求其深反失其真”之误。(27)周勋初曾谓陈寅恪的治史推论较多,“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28)当也与陈寅恪此种治史风格有关。
吕思勉的治史,也以普通常见的史籍为主(29),也是以精读史籍为日课。此点学者多有论述,此处不再展开。然就此点而言,吕、陈两位的治史风格是相似的,这也是前辈史家共有的治史特征。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30)严耕望以“方面广阔”来定位四位大家的治史特征,当是确评。这里所说的广阔,既可指他们治学范围的宽阔,也可指他们视野的广阔。陈寅恪治史自有相当宽阔的视野,上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结论,就是一个例证。而吕思勉的治史,也非常关注时间上的“瞻前顾后”和空间上的“左顾右盼”。我们不妨以《隋唐五代史》第三章第二节“唐初武功一”论高祖向突厥称臣事为例做点分析。全文颇长,这里不能全引,只叙述其大要:
(一)唐初大敌,自为突厥。在叙突厥事前,先交代突厥北面的铁勒,详考其诸部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其中的回纥。因为突厥瓦解后,“遂与之代兴也”。
(二)叙隋末唐初,突厥控弦百万,北方诸族多臣服之,即唐高祖初起时,也称臣以乞援。叙高祖称臣突厥事,引《旧唐书·李靖传》、《突厥传》所载为注。
(三)叙武德七年、九年,突厥入侵,太宗与突厥的两场战争。注引《新唐书·突厥传》所记突厥入寇时,帝与群臣议备边策,及中书侍郎温彦博建议仿“魏为长堑遏匈奴”之法。又引《郑元璹传》记元璹使突厥谓颉利之语,并与宋富弼说契丹之辞作一比。
(四)太宗时,乘突厥饥荒和内乱,将其击破,至此“斥境至大漠矣”。其间又叙突厥饥荒与内乱的大略。
(五)叙突厥来降,如何处置,叙朝臣中有三派不同意见,唐廷最终所采的处置方式及其实施概况。
以上只是撮其要点,文中及其注释,或考人名、地名、部落方位,或考史籍记载的是非异同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31)吕思勉另有一篇《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札记,其要点有四:
(一)引《旧唐书·李靖传》、《新唐书·突厥传》及《通鉴》等所记材料,断言“高祖称臣于突厥不疑”。
(二)引《旧唐书·张俭传》所记“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数句,断言高祖称臣事当在“彼之称敕于诸州”之时。
(三)引《新唐书·突厥传》云:高祖初待突厥用敌国礼,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疑称臣之礼,实至是而始罢,然亦不过用敌国礼。
(四)引《通鉴》所记,称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或高祖未必及此。但唐初确未借突厥兵以为用,高祖之智,虽不及此,群臣之中,必有能为是谋者矣。(32)
此篇札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写于何时不详。原手稿三页,拟于吕思勉自制的方格稿纸,文稿有少数几处修改,吕归入“史事”一类。其末尾,论高祖“既非急于求人,何乃无端屈己”?又云:“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所谓称臣突厥的可耻与否,是否是回应陈文而发?然也可能是针对《旧唐书·李靖传》太宗“耻其雪乎”一句而言。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刊于1952年6月出版的《岭南学报》上,吕思勉是否读过陈寅恪的这篇文章,甚难断言。不过,就所论的几个问题,该札记确可看作是陈文的延伸和补充(如关于称臣起始终止何时等)。总之,该札记的撰写时间,最迟也与《隋唐五代史》的撰写同时。
上述罗列,似也可归纳出吕思勉治史的几点特色:
(一)吕思勉考史叙事的思路偏好往宽度走,这里所说的宽度,有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如叙突厥之前,先叙处于突厥之北的铁勒十五部及其分布;叙唐初太宗与突厥的战事,也都与铁勒诸部的动向相联系。二是时间维度,如温彦博建议仿“魏为长堑遏匈奴”之法,叙元璹谓颉利之语而与宋富弼说契丹之辞作一比等,都是时间上贯通前后隔代的比较。
(二)《读史札记》中的考证,也都是史事细节上的坐实。然而,所考能否确证,吕思勉则比较谨慎。上引札记中关于高祖向突厥称臣细节上的几层考辨,无一写入《隋唐五代史》中。如称臣始于何时、罢于何时等——尤其是称臣之礼罢于何时,今日学者认为当以吕思勉的推断最为近实。(33)然吕都未采入他的《隋唐五代史》。又如对西突厥突利设的“变计绝婚”,是否出于何力之谋划,吕思勉虽有考辨,亦未敢坐实,有关推论仅置于注释之中。学者有谓其“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34),似与此种谨慎态度有关。其实,史事细节上的考实,非有确实的证据不易断;读书越多,越不敢轻易下断言;故此也不足为病。唯近现代学风是偏于精深一路,喜做“仄而专”的研究,故有“博而不精”之嫌。(35)
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并非史界的“一重公案”(36),陈寅恪撰写《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也非全在考求史事真相。此文的“命意”是否如余英时所说,暂且不论。但其治史之目的、宗旨,还是清晰明白的,那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其实,非但陈文如此,就是陈书也是如此。此点,陈寅恪说得很明白: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逐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远学术采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介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戒,兼见其有以异乎跨诬之宣传文字也。(37)
该书还有一节论唐太宗用兵高丽云:
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其一正确之概念也。(38)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求取史事真相,纠正错误历史认识、尤其是要纠正宣传式历史书写,以达到“近真实而供鉴戒”的治史目的和宗旨。所以,“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确是陈寅恪治史的最终目的。
“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实在也是吕思勉治史的特色。《白话本国史》论“高祖称臣突厥”也是以“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为行文的最后归宿。该书云:
唐朝的对外,最重要的还是和北族的关系。突厥启民可汗死后,子始毕可汗立。部众渐强。这时候,又值中国丧乱,边民避乱的,都逃奔突厥。于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数十万。割据北边的人,都称臣于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辞厚礼,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却没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后,待突厥还是很优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骄恣。大抵游牧民族,总是“浅虑”而“贪得无厌”的。而且这种人所处的境遇,足以养成他“勇敢”、“残忍”的性质。所以一种“好战斗”的“冲动”,极其剧烈。并不是一味卑辞厚礼,就可以和他“辑睦邦交”的。而且一时代人的思想,总给这个时代限住,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遗孽,想倚赖北族,北族也把他居为奇货。”这种事情,“齐周”、“周隋”之间,已经行过两次了,已经行之而无效的了。然而隋唐之际,还是如此。……没有一年不入寇,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几次,北边几千里,没一处不被其患。高祖几乎要迁都避他。而唐朝对待他的法子,也还是抄用隋朝的老文章,这个真可谓极天下之奇观了。(39)
吕思勉感慨唐初统治者无视“齐周”、“周隋”已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仍抄袭前代行之而无效的政策。所谓“极天下之奇观”,也意在提示后人警觉清醒。这都是我们读史时当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在上段引文之后,吕思勉又讨论了突厥来降之后朝廷的处置办法及其得失:
太宗初时,想把他处之塞内,化做中国人。(当时魏征主张把他迁之塞外,温彦博主张置诸中国,化做齐民。辩论的话,具见《唐书·突厥传》。太宗是听温彦博的话的。著《唐书》的人,意思颇有点偏袒魏征。然而温彦博的话,实在不错。唐朝到后来,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实行魏征的政策。然而突厥接连反叛了好几次,到默啜,几乎恢复旧时的势力,边患又很紧急,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这件事,颇有关系,可惜原文太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可自取《唐书》—参考。)(40)
关于“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也就是唐朝(历朝)对边事“放任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吕思勉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后人反思总结的大题目。这也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行文至此,有必要将陈、吕两位与范书、王书的评论做点比较。范氏评太宗称臣突厥事,说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而“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王氏则云:“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能和以战耳”,非“中国制夷之上算也”。(41)范、王的史论,自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评说。但两相比较,正可觇史学之变了,也显示了陈、吕两位与传统史学的承继和差别。20世纪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也极重视历史教训的总结,但说法与目的与陈、吕两位又大不相同。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说,“以陈先生所发表的专著和单篇论文而言,几乎全是纯学术性的考据之作,与现实人生似乎毫无交涉”,“然而深一层看,陈先生一生的学术工作可以说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即表面上的考证文章,实质含有深切的现实关怀。陈寅恪治史擅长“考古以证今”,以“古今互相印证”来寄托他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热爱。余英时又说:“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42)撇开“伟大”两字不论,但就此点而言,吕思勉实也与之相类。吕思勉也反对时人死读历史,主张将书本上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他曾说: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43)
吕思勉撰写的断代史、中国通史,也都是纯学术性的专著论文,但内中的有些叙述,也隐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针对着现场的某些问题、某些事态。如1947年出版的《秦汉史》第六章第一节元帝宽弛,说到翼奉上疏迁都事:
时又有翼奉。征待诏,以灾异见问。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共。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蓄。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请徙都成周,定制,与天下更始。此则较诸贡禹,谓惟“宫室已定,亡可奈何,其余尽可减损”者,尤为卓绝矣。迁都正本,元帝虽未能行,然宗庙迭毁及徙南北郊之议,实发自奉,至韦玄成为相遂行之。在当时,亦不能谓非卓然不惑之举也。(44)
翼奉其人其事,一般秦汉史的专著少有提及,而吕思勉特举而叙之,并一再称其见识“卓绝”、“卓然不惑”,盖也隐含着吕思勉自己对现实事态的关切和看法。自民国以来,都城的设置,或南或北,摇摆不定,意见纷呈。直到1945年,仍有某商业社团上书蒋介石请迁都北平之议。按吕的意见,一国之都,当是全国首善之区,具有榜样示范效应。古人言治,首重风化,然观历代之都城,凡“人口愈殷繁,财力愈雄厚之地,即其道德风纪愈坏,京师几成为首恶之地”,故要改弦更张,“旧都邑实不易著手”。(45)理想的都城,应“择一未染旧都市习气的地方”(46)。《秦汉史》叙翼奉事,也就隐含着他对现场的看法和意见。只是这些隐含在学术著作中的现实关怀,读者一般不易体会察觉。正如“陈书”、“陈文”,需经余英时的解读方能探隐发微、彰显其命意一样;吕思勉对翼奉的称赞,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笔者也是在读到了1945年写的《禁奢篇》和1946年写的《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二文,以及他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所拟的以“翼奉迁都”为题的考卷之后(47),才逐渐体会到史事叙述背后的真含义。
深切的现实关怀,“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这是陈、吕两人的共同点。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之处。陈寅恪除了在史学著述中隐含着他热切的现实关怀外,很少写有时论文章,即便是在民国年间,也很少向学界或一般民众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史著之外,另一个能让他倾诉关怀和情感的,那就是吟咏诗章。陈寅恪的诗作,从诗题上往往是看不出诗之本意及所指针的对象。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依其内容给每首诗另起一个标题,这就给我们理解陈诗提供了指引。(48)读《笺释》一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旧体诗,大部分都是受现实社会的某些“刺激”而抒发的“心曲”。陈寅恪隐含在史著中的现实关怀,自不易为读者所体会;他那些旧体诗中的古典与今典、本事与今事,也非经余、胡等人的考释解读,不能为一般读者所读通读懂。所谓“志在刺讥,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陈寅恪在学界内外的形象,俨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其实,陈寅恪不仅关心现场社会,而且还曾有过自己的“大纲细节”。李璜曾撰文,回忆早年他与陈寅恪、陈登恪、曾琦(字慕韩)在康德大街的咖啡馆小聚,畅谈天下国家大事的情形,说陈寅恪在“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49)。这自然是陈寅恪早年的情况,但终其一生,类此的“大纲细节”从未将它写成时论性文章发表(50),这就更加给人造成一种不介入现实问题、不关心现状的纯粹学人的印象。
吕思勉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然而,他更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自称不是“纯儒”,早年向往的是经济之学,稍后(辛亥年间)决定不入政界,专意治史。然不入政界不作官,非谓“不当自效于当世,特谓不当如流俗,以作官为啖饭之途径耳”,且“尝自期,与其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51)观吕思勉一生,既未作官,也未作幕僚,但陈古而鉴今,针砭现场、倡导改革的言论却不少。查他的著述目录,一生所撰的时论性文章,总数约有近百万字,都是刊登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的。涉及的社会问题极多,诸如文官考试、救济米荒、对于群众运动的看法、乡政的改良、货币问题、盐法的改良、田赋征收实物问题、关于平卖的建议、学校食堂的改革、饮食的改良、生活的规范、妇女就业和持家的讨论、邮寄手续的改良、上海路名的恢复等等。(52)总之,上及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下及学校的食堂如何办,脚上的鞋子如何改良,无一不是他关心的事情。只是他的那些渗透着现实关怀的时论文章,常常被他那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所掩盖,以至于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也是一位纯粹学人——吕思勉确实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但他确实也是民国年代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至此,我们回到上文讨论过的主题,做三点小结:(一)诚如余英时所说,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不在考史,因为高祖向突厥称臣事,并非悬而未决的公案。虽然此文考证高祖称臣突厥的许多具体细节,但其“命题”,大约余英时的推断可以成立。需要补充的是,陈文撰写的远因,或许还与抗战胜利后几年时局的刺激有关。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所作所为,陈寅恪一定有所风闻,(53)这岂不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历史重演?(二)就治史风格而言,陈寅恪偏好作纵深的探求,吕思勉喜好作横向的拓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如能将陈、吕两位关于高祖称臣突厥事的叙事合而观之,则对此事可有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就此而言,史学上的精深与博大,本是史学研究上应有的两个蕲向,“合者双美,离者两伤”,史学观念上不应重此轻彼,形同排斥。(三)陈文的命意是“借古讽今”,希望当事者“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吕书叙高祖称臣突厥之事,也旨在检讨历史上对边疆事务的放任主义;两者所虑殊途,所归同一,且有异曲同工之妙。严耕望有“前辈史学四大家”之说(54),就关心现场,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言,这也是四大家的共同特点。(55)只是史学观念的变迁,常会由一种倾向过度地摆致另一种倾向。追求史实的细节,反思历史的教训,本都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不可偏废,也不可分孰重孰轻。称臣突厥自是高祖的权宜之计,然其代价也不可忽视。《旧唐书·刘文静传》云:“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大唐创业起居注》云:“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结果便有武德三年处罗可汗帅兵入太原掠虏三日,守将不敢阻止。而“齐周”、“周隋”间行之无效的老办法,唐朝仍沿袭不改;突厥归降之后,对于边地边患仍抄用着“放任政策”。所谓殷鉴不远,这些陈寅恪、吕思勉为之痛心疾首的历史教训,以及历史上类似的经验,正当为后人深长思之。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非古人或外人独享之专利,而今人能否正确吸取,端赖他能否站正立场,而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李璜在《忆寅恪、登恪兄弟》一文中说: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纪念“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56)。就此点而言,也同样适合对吕思勉的纪念。吕思勉的时论文章,似乎也未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然而,这本是两位大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原不是那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治史者。今日追念他们的为人为学而忽视这一点,虽不能说是买椟还珠,则多少有点论之一偏。
注释:
①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第190—1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8—129页。
④《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9—1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⑤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03、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有关叙述,见本文第三节的引文。
⑥严耕望:《怎样学历史》,第1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⑦王桐龄:《中国史》(第二册),第5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⑧李泰棻:《中国史纲》(第三卷),第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8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⑩章嵌:《中华通史》,第773、78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32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12)廖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中册),第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3)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第104—10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4)《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2月初版),《高级中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初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6月初版)。上述四种,可参见《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190、454、456(注文)、8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蔡东藩:《唐史演义》,第131—13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
(16)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见《唐史演义》,第4页。
(17)贞观三年年底,唐李靖等大破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既然太宗自己已经承认“称臣于突厥”事,那么记载《国史》、《实录》之史官也就可以秉笔直书了。但后来太宗要看《国史》、《实录》,史官不得不有所削改删节,以至于史书所记有所缺略,乃至隐含不显。
(18)范祖禹;《唐鉴》,第12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9)王夫之:《读通鉴论》,第670-6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688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1)李树桐曾在20世纪60—80年代间,连续发表了《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大陆杂志》第26卷第1、2期)、《再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大陆杂志》第37卷第8期)和《三辩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第61卷第4期)三文,不过这都在陈书、陈文发表之后。
(22)2012年6月底,笔者参加了上海大学主办的“民国(1912-1949)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拙文用作大会的提交论文,并在小组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会后,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与余说起一则与此有关的材料。在2010年10月间,王刚教授曾拜访过胡德锟教授(胡先骕之子,北京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闲聊中胡教授说及有关陈寅恪的轶事,胡德锟的父亲胡先骕(江西南昌市新建县人)为陈三立的弟子,其学生陈封怀,为中国植物学研究之先驱,民国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陈封怀是陈寅恪之侄,与寅老也交从甚密。陈封怀曾告知胡先骕,在解放初期“一边倒”的情况下,陈寅恪曾向中共中央写过长文,大致意思是苏联靠不住。不过,此文写了之后是否递送,他不得而知。此则轶事,似可助我们作两点推断:(一)陈寅恪因“一边倒”政策而写过一篇长文的事,曾在他朋友圈子里流传过。(二)陈寅恪对苏联不抱好感。此事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佐证,故不能用为本文讨论的证据,入录于此,或使陈、胡、王诸人转辗之口述不至湮没,亦望学界同好留意搜寻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23)上述三点,参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载《岭南学报》,1951(2)。
(2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1页。
(25)有“冗沓而多枝节……且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芜累枝节,牵缠反复”等言。俱见钱氏1960年5月28日致余英时信。参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素书楼馀沉》,第53卷,第428页。
(26)王荣全:《关于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见《唐史论丛》,第7辑,第22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7)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28)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第207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9)此点严耕望已指出,参见《怎样学历史》,第24—25页。
(30)严耕望:《怎样学历史》,第239—240页。
(3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74—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下同。
(32)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第1074—10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3)王荣全:《关于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见《唐史论丛》,第7辑,第233页。
(34)(35)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16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36)由于陈书、陈文及余文在学界的影响很大,学者说起唐高祖称臣突厥的史事真相,总会首列陈寅恪的研究(见《唐史论丛》,第7辑,第224、234页)。其实,从本文引述的材料来看,对高祖称臣突厥史事的肯定,早在宋明,已有学者做出肯定性的论断。陈寅恪的研究,在于称臣突厥事内的诸多细节,如何时开始称臣,谁是主谋等等。
(37)(38)《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第128、129、141页。
(39)(40)《白话本国史》,第303、304页
(41)《读通鉴论》,第670—671页。
(42)《现代学人与学术》,第186、188、192页。
(43)《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历史研究法》,原刊1941年3月16至19日《中美日报》堡垒第160、161、162、163号,现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4)吕思勉:《秦汉史》,第1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5)《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原刊1946年5月5日《正言报》,现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46、147页。
(46)吕思勉:《禁奢篇》,见《吕思勉诗文丛稿》,第593页。
(47)吕思勉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后考试拟的考题之一,便是论翼奉的迁都主张及其对当今现实的意义。原题云:“翼奉谓汉都长安,其制度已趋奢侈,不足以为治,因欲迁都洛阳,果如其说,则今日之首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而别图营建,甚至各省省会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而增加其效率欤?试以意言之。”或按吕思勉的意见,南京也非首善之地,罔论明清以来的旧都城北京矣。
(48)如写于1938年的“蓝霞一首”,胡文辉新加的诗题是“蓝衣社”;同年另有一首“蒙自南湖”,现加的诗题是“黄河花园口决堤”。写于1939年的“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实是针对“蒋汪分裂”的;1961年“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是针对当时学术界的“厚今薄古”运动。如此之类,举不胜举。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第110、122、144、75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49)李璜《忆寅恪、登恪兄弟》云:“是时寅恪年约三十三岁……但与慕韩相识之后,即时嘱登恪约慕韩与我至寓下或下午五时共同把酒清谈于康德大道街头之咖啡馆中。……寅恪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逆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因甚佩慕韩内除国贼与外抗强权之论。不过,寅恪究系有头脑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的学人,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原刊《大成》第49期。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78—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50)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论著编年目录”,似未有他撰写的时论文章的刊出。
(51)《自述》(即《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见《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3、753页。
(52)如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有:《禁止遏籴以抒农困议》(1911)、《文官考试宜严》(1912)、《国体问题学理上之研究》(1915)、《救济米荒之一策》、《对于群众运动的感想》(1920)、《考试论》(1928)、《乡政改良刍议》(1929)、《所谓铁路附属地者》(1931)、《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货币问题》(1935)、《宦学篇》(1939)、《改良盐法刍议》、《田赋征收实物问题》(1940)、《论禄米之制》(1941)、《关于平卖的一个建议》、《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抗战何以能胜建国何以可成》、《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因整理土地推论到住的问题》、《论外蒙古问题》(1945)、《论美国助我练兵宜缓行》、《学制刍议》、《两种关于延安的书籍》(1946)、《学制刍议续篇》、《如何根治贪污》(1947)等。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有:《禁奢议》(1935)、《吃饭的革命》(1936)、《上海风气》、《向慈善家进一言》(1940)、《肉食与素食》、《蔬食》、《生活的规范》(1941)、《上海人的饮食—辟谷》、《上海人的饮食—烹调》、《妇女就业和持家的讨论》、《上海风气》(1940)、《改良邮寄手续》(1945)、《新生活鉴古》、《吕思勉谈派报问题》(1946)、《再论恢复上海路名刍议》、《治都邑之道》、《寒食》(1947)、《致叶圣陶、周建人建议便利汉字分部书》、《日报版式印数诤议》、《书店印行完全书目议》(1952)、《致〈解放日报〉再议报纸发行书》(1953)等。此外还有文化与教育方面的文章。上述文章,现都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和《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3)参见胡文辉对陈寅恪1945年的“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玄菟”、“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三首诗的笺释。见《陈寅恪诗笺释》,第345—362页。
(54)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第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
(55)相对而言,陈寅恪、吕思勉对现场大多持一种批评态度,而陈垣、钱穆稍有不同。此点须另外撰文讨论。
(56)转引自《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79页。
标签:吕思勉论文; 陈寅恪论文; 隋唐五代史论文; 突厥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论文; 陈文论文; 读通鉴论论文; 李渊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