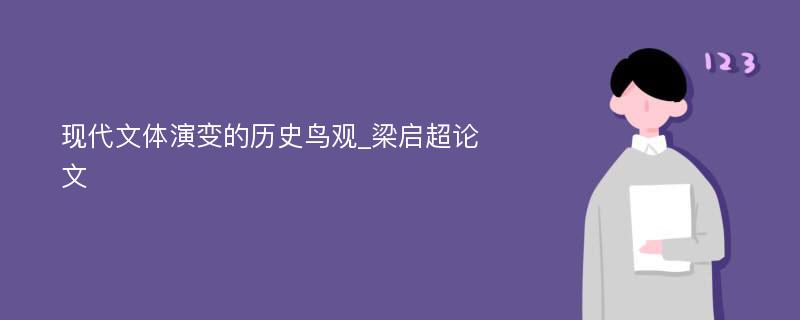
近现代文体演变的历史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文体论文,近现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注:“文体”一词在现代文学中主要有三义:一为作品体式(或称体裁),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章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二为作品的语言形态,如瞿宣颖《文体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三为作家风格或流派特色,如“冰心体”、“语丝体”。本文将文体界定为:由语言形态、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作品的形式审美规范,有时也指由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作品类型。)的建构和演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学告别古典时代逐步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十分薄弱。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想借“鸟瞰”这种粗疏的审视,以引起研究者应有的理论关注。
近代文体变革考察
文体古典形态的终结和现代形态的确立是以近代文体的嬗变为其先导的。这种嬗变虽然未能从整体上推翻古典文学的体式系统,但却在文体意识、文学语言形态和各类文体的内形式规范方面,为现代文体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传统文体意识将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混为一谈,构筑起一个颇具特色的杂文学文体系统。其中,诗歌、散文(文学和非文学散体文章)居于正宗地位;小说(包括戏剧)反而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注:鲁迅《草鞋脚·小引》。)这种状态严重阻碍着文学文体的发展。但到戊戌变法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严复、夏曾佑于1897年揭橥其义,后由梁启超于1902年明确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观念,不仅将小说列入文学文体范畴,而且改变了传统文学文体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一文体意识直接影响了五四现代小说的勃兴,也局部冲击了杂文学文体意识。1903年后,在“西学”影响下,王国维、鲁迅等人又进一步在文体论上提出了“情感说”,以是否表达人的感情,作为界定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标准,从而终结了传统的杂文学文体体系,初建起西方现代型的纯文学文体体系,为“五四”诸文学文体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清场奠基的作用。
改变传统文学的语言形态,也是近代文体改革的主要目标。自龚自珍起,要用“俗语”(即口语)进行创作的思想就已经萌蘖。1886年,黄遵宪又就诗歌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此后,梁启超又进一步依据世界文学进化的历史规律明确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成俗语之文学也。”(注: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伴随理论的呼唤,“俗语”也大规模进入近代报刊。与此同时,自洋务派的郭崇焘、薛福成起,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在理论上提倡并在诗文中大量引入日本和欧美的“新名词”。这样,近代文学的语言变革便沿着两个方向(通俗化和欧化),朝着建立文学语言形态现代化的目标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它还未能彻底推翻古典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却以一种崭新的“白话”形态,为五四现代文体的诞生准备了语体条件。
文体意识和语言形态的变革以及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也引起了各类文体内形式规范的变化。最先的变化是从封建正统文学最牢固的堡垒——诗歌与议论性散文开始的,它的主要演变方向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报章体化(即社会化和通俗化)。正如钱钟书所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日以不文为文,以诗为文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开明书店版第36页。)戊戌政变前后,小说文体的变革被推到前台,并迅速获得较为显著的成就,诗文的变化反倒缓慢下来,这不仅表现在“新小说”数量的突飞猛进,也表现在古典小说情节模式的局部瓦解。戏剧文体的变革最为艰难,但从戊戌政变后开始的旧剧改良到继起的新剧(早期话剧)运动,戏剧文体明显地朝着以说白为主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从各类文体的改革速度、程度到改革的基本走向,都直接影响到五四时期文体改革态势以及各类现代文体的形态面貌。
下面,我们在以上综论的基础上,分别就各种文体作些具体的说明。
先说诗歌。我认为,近代诗体的革新与“五四”新诗文体规范的确立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革新后的近代诗体给“五四”新诗提供了多少足资效仿的艺术样本,而是在于近代(特别是“诗界革命”时期)诗体革新的观念和方法乃至方向对创立“五四”新诗体的启示。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诗界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从观念上来说,近代诗体改革已有了推翻古典诗体规范的崭新意识。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经过一千余年的惨淡经营,逐渐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文体结构系统。宋代以降的诗体改革,都只能是在规唐模宋基础上的局部调节。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这种观念终于在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世界中产生了动摇,谭嗣同于1896年在金陵刊刻的《莽苍苍斋诗·自叙》中说:“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奋而发箧,毕弃之。”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诗界革命”大多数倡导者的心声。继之,南社诗人马君武在著名的《寄南社同人》一诗中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鲜明:“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规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要求诗歌从古典规范中解放出来,“自成模范”,这种思想实际上已成为“五四”诗体革命彻底地除旧布新的先声。
从方法上来说,近代诗体选择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新的改革途径。朱自清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发展时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注:《新诗杂话·真诗》。)五四新诗取法途径的改变,实际上正是肇始于近代。梁启超认为,要改革诗体,“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要达其目的,“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康有为在评论黄遵宪的诗时说:“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注: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他本人也呼唤:“新诗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注:见《康南海先生诗集》。)都说明了这一点,而鲁迅作于1907年的诗论《摩罗诗力说》,号召以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为参照系改造中国传统诗歌的主张,则更可以看作是“五四”新诗取法途径的先声。
崭新的诗体改革意识和取法途径,必然导致崭新的诗体改革方向,这个方向便是:在语言形态上以“俗语”代替文言,在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上以自由化代替格律化。当时,不但改良派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竭力鼓吹“以俗语入诗”,继起的革命派的周实也认为,“讲格律,重声调”“乃文章诗歌之奴隶”。(注:周实《无尽庵诗话·序》。)诗歌创作也呼应了这一理论要求,语言愈来愈通俗化,部分诗歌已打破了五七言的句构形式,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歌体诗”(如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秋瑾的《宝刀歌》等),语言通俗,句式自由,已可看作是向“五四”新诗过渡的一种形式。
总起来说,近代诗体变革虽然仍未冲破古典诗体的整体规范,但在观念、方法和方向上已为“五四”新诗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五四”新诗的倡导者们曾经多次提到了这一点。(注:参见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3卷1号;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同上3卷3号。)可以说,他们正是沿着近代诗体打开的通路,总结了它的历史教训,以更彻底、更科学的姿态继续拓进,才赢来了现代诗体的诞生。
近代小说的文体变革,始于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对小说政教功能的强调,完成于1902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纲领的提出以及此后翻译和创作小说的繁盛。它虽然未能从整体上实现小说文体向现代转化的历史任务,但却在文体观念和文体实践两个层面上以新旧杂糅、良莠并存的过渡形态,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企图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强调其政教功能以达到改良群治目的的主张,固然有其幼稚的一面,但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密切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启示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小说家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谓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创作方向;对此,鲁迅本人就有过明确的说明。(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至于此后黄摩西对古典小说“千篇一律之英雄封拜,儿女团圆”(注:黄摩西《小说小话》,1907《小说林》。)的结构模式,以及众多理论家关于“新小说”语体“雅与俗”的思考或批判等,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倡导者开辟了新思维的道路。
在文体变革的实践上,首先要提到的是外国小说的译介。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至1911 年, 翻译小说多达600多种,为当时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尽管在这股“翻译热”中, 小说家的选择取向囿于以小说改良群治的幼稚观念和中国读者旧的审美趣味,较多地趋向侦探、政治和言情三种类型,但必须以西洋小说改造中国传统小说的实践方向却日渐明确。也正是这一点,给五四时期的小说革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历史启示。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异质”的西洋小说的大量引进,也造成了传统小说文体规范的开始解体和新型小说形态的初建:在语言体式上,初步形成了一种调入方言土语、文言韵话乃至新词语、新文法的崭新的白话文,作为小说的语体形态;在叙述模式上,开始产生对传统规范(顺时空叙述、全知视角、情节中心、叙述和言行描写为主等)的大幅度背离,出现了倒装叙述、限制视角、非情节化倾向和注重心理、细节描写等等。这一切,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在记叙性和议论性两种类型的散文中进行的。记叙性散文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出国人员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当时,这些“介绍”性的散文,在不断走向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如“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如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和《巴黎赛会纪略》等,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等形式,“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这些散文, 在文体规范上已部分冲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为“五四”现代记叙抒情散文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比较起来,近代议论性散文的变革对“五四”散文的影响更大。这种变革,沿着否定“文化载道”和“代圣立言”的共同方向,形成了两个侧重点,一是追求语言体式的“言文合一”。清朝散文原以桐城派古文为正宗,其语言体式不仅高度文言化而且还刻意追求音节和谐,讲求声律,造成了与口语的严重分离。这就不能不与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从近代初始,文坛上就出现了一股反对桐城古文、创立接近口语的“朴实明晓”的新体散文的潮流,而梁启超则是这一潮流中贡献最大的作家。戊戌政变后,他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为适应启蒙宣传的时代要求,取法日本德富苏峰等人善于表现欧西文思的日本报章文体,创立了“新文体”。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给实现议论性散文语体的“言文合一”,启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一是输入本民族有生命力的口语成分,一是输入已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口语一部分的外来词语和语法,以废除文言的语体系统。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新文体”尽管在实际上并未彻底实现议论性散文的口语化,但却为实现这一目标起了重要的清障开路的作用。“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高度评价梁启超“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其原因即在于此。
另一个侧重点是追求议论性散文论述方式的科学化。古典议论性散文发展到明清,其空泛陈腐倾向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过激的言词所指出的:“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1905至1907年革命派与唯心派论战中出现的文章,首次引进西方的形式逻辑,使论述方式具有了现代科学的色彩。此后,章士钊将这种论述方式进一步作了发展,创立了所谓“剥蕉”式文体,即运用归纳和演绎等推理方法,围绕论点层层深入,使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辩力。这些变革,虽然未能彻底脱掉古文的外壳,因而其文章被胡适称为“倾向欧化的古文”,但它对实现“五四”议论性散文向现代转变,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青年》前期作者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和胡适等人的文章,大都受到章氏“剥蕉”文体的影响。
总起来说,近代议论性散文在文体功能、语言体式和论述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已走到了现代的大门前。现代散文首先从议论性散文起步,固然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但议论性散文在近代的变革成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戏剧文体发展的现代进程始于1907年,但在此以前的近代戏剧改良却为其奠定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体观念的更新。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欲借文学之力“改良群治”和“开启民智”的目的,激烈抨击轻视戏剧文学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欲先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注:转引自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11月版。)甚至还有人把小说和戏剧进行对比, 认为“戏剧之效力,影响于社会较小说尤大”。(注:铁《铁瓮烬余》,《小说林》12期。)这些看法虽然过分夸大了戏剧文学的功能和地位,但对引起人们重视文体的改革,并促使其向现代的历史转变,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其次,近代戏剧改良也为实现戏剧文体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启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近代以来,一些戏剧改良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总是打算从旧的戏剧传统里蜕变出新的东西来,结果发现这种努力是很不成功的”,(注: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1954年《戏剧报》第4期。 )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探索取法西洋戏剧以改良中国戏剧的道路。如有人主张,“淘汰而改正”中国古典戏剧的取材,选择“西国近今可惊、可愕、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详其历史,摹其神情,务使须眉活现,千载如生。”(注: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引自《中国五四文学史》第587页。 )有人提倡莎士比亚的悲剧,主张中国剧界“必以悲剧为之”。还有人主张“采用西法”,在剧中增加演说成份。这些主张虽然还未明确提出移植西洋话剧以建构中国戏剧文体,但它把改革途径的视线从传统戏剧引向西方戏剧,其意义却非常重大。
再次,近代戏剧改良也兆示了现代戏剧文体发展的基本方向。戊戌政变前后,汪笑侬、夏月润、潘月樵等“旧的与新的戏子们”,着重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对戏剧的传统规范进行了改革。他们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西洋话剧的形式,在叙述方式上以说白为主,采用生活化的布景,“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代表式的动作了”。(注: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导论》。)这些改革虽然还只是在传统戏剧文体规范的坚冰上划开了一道裂痕,但它却让人们从裂痕中看到了“趋于写实一途”的话剧将成为现代戏剧主要形式的必然趋势。
在以上三个方面所奠定的基础上,从1907年开始,现代戏剧文体的创建终于拉开了帷幕。是年三月,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新派剧影响下成立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上演了曾孝谷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是我国早期话剧第一个完整的剧本。其后,“春阳社”和“新剧同志会”等许多话剧团体也相继在国内成立,演出了许多意译和改编的外国剧本,以及模仿创作的一些话剧。从1907年到新文学运动兴起的这10年间,是现代戏剧文体的开创期,其主要成就有如下两点:
一是逐渐结束以西洋戏剧改造传统戏剧的做法,确立“移植”西方话剧以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形式的文体观念。在现代戏剧运动的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戏剧观念还是以西洋话剧精神来改造传统戏剧。也就是说,改革者并不准备彻底抛弃旧戏的基本形式框架。他们认为,虽然“专取说白传情”的“话剧”已在国内“是处流行”,但“戏以歌唱为之、自应有事”。(注:王梦生《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1915年。)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却认为这类有唱的所谓新戏“止可谓之为过渡戏,不可谓之为新戏,新戏者,固以无唱为原则者也”。(注:李涛痕《论今日之新戏》,《春柳》第1期。)这表明, 人们已注意到将话剧与改良戏剧加以区别,并认为新剧应走“移植”话剧的道路。正是与这种戏剧观念相适应,早期话剧的文体实践越来越深入。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所谓“文明戏”演剧活动的衰落,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人都在努力探索着现代戏剧发展的正确道路,创作了《母》、《新村正》、《燕支井》等较为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结构模式上,已打破了古典戏剧的形式规范,而以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述方式上,程式化的动作和歌唱也全部废除,改为只用对话,语言体式也更加口语化。尽管这时的戏剧还不能完全割断古典戏剧体式的尾巴,但它却日趋话剧化。
现代文体发展态势
近代的文体改革,无论是文体意识、语言形态、还是内部形式规范,都由于改革者主体的思维结构、社会客体诸多因素(政治经济力量、文化条件、读者审美心理等)的时代局限,未能跨入现代的大门;而这种历史情状,也正是五四文体革命崛起的直接原因。
辛亥革命作为旨在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并未实现预想的目标。这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一批具有新的思维素质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得出了要借助新文学的力量进行思想启蒙的结论;而要建立具有现代形态的新文学,则必须破除旧文学的物质外壳——文言。 顺应这一历史要求, 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给旧的“文言分离”的文学形式以全面的否定,并上承梁启超的文学进化论,提出了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胡适的发难很快得到了一些革命文学先驱者的响应。钱玄同在同年三月致陈独秀的信中以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胡适的发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在同年五月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如何创造白话文学语言进行了探讨,并且提出了文章分段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傅斯年在《文学革新申议》和《文言合一草议》等文中也就“言文合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先驱者们“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一致主张,为文体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必要的出发点。
伴随着语言层面的初步变革,各类文体具体规范的除旧布新也就相继开始。因为先驱者们认识到,“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所以,“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注: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号。)
在五四文体革命的风暴中,诗体的革命是先驱者有意率先进行的事业。其原因是,在他们看来,新文学应该是白话文学,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白话化已经施耐庵、关汉卿以来的许多文人的努力,取得了基本胜利,而诗歌却仍然率由旧章,正如胡适所说,“现在只剩下一座诗的壁垒”。因此“还需用全力去抢夺,得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以说是十足的了”。(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9页。)
在这种自觉的理性指导下,胡适于1915年至1916年间就开始思索旧诗体的革新问题,他认为:“诗国革命何时始?更需作诗如作文。”(注:《逼上梁山》,《四十自述》,1933年版。)稍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和《文学改良刍议》等文中,反复阐述了做“白话诗”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先驱者的赞同。钱玄同、刘半农还就新诗的形式规范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2卷6期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次年, 《新青年》又相继发表了刘半农、沈尹默、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60多首新诗。其中,周作人的《小河》被认为“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注:胡适《谈新诗》,1919年10月《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但当时大多数新诗还并未完全脱尽旧诗体的胎气。
“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时代情感推动诗体进一步地解放,新诗创作如潮如涌,这其中,郭沫若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于1917年9 月开始发表后来收入《女神》中的自由体诗,以浪漫主义摧枯拉朽的气势,为奠定新诗体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年10年,胡适发表了《谈新诗》一文,指出,新诗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这一原则为当时绝大多数新诗人所共同遵循。因此,可以说,《谈新诗》的发表标志着新诗形式审美规范的初步确立。
“五四”小说文体规范的更新同近代一样,主要也是在文体观念和文体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文体观念上,陈独秀、鲁迅和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人,批判地继承了梁启超的“文体功能说”,力主“小说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改良社会”。(注: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 )但他们已不再把小说与政治改良直接地联系起来,而是普遍地看到了两者之间还有“人性”、“人的情感”这个中介物;同时,也纠正了梁启超视小说为改良群治的狭隘工具论,赋予了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鲁迅就明确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是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注: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又参见陈独秀《通信》,1917年《新青年》3卷2号。)创造社的一些人,虽然有主张小说无功利的偏颇,但他们却更鲜明地揭示了小说之所以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即在于它是“美的创造”。正是这些更为科学的认识,使“五四”小说文体功能的观念彻底与“文以载道”说划清了界限,从而具有了现代特征,并为小说形式审美规范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前提。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小说的时空观念、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的认识不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也更为科学,从而初步建构起一个与古典小说迥异的现代小说文体理论的体系。
伴随文体观念的更新,在外国小说的规范启示下,现代小说的文体实验也相继开始。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 号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拉开了现代小说诞生的帷幕。这篇小说,以崭新的文体形态使人读后感到“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注:参见《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随后, 不但鲁迅本人的小说“一发而不可收”,而且《新青年》、《晨报》副刊、《新生活》等报刊也陆续发表了汪敬熙、罗家伦、叶绍钧、杨振声、冰心等人的白话小说。
1921年以后,以《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为主阵地,现代小说家逐渐布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以两种主要类型的小说,至1927年初步实现了现代小说文体规范的确立。
作为现代议论性散文第一个宁馨儿的杂文,萌蘖于新文化运动,但它的大面积丰收,却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1918年4月, 《新青年》特辟“随感录”栏目,专刊初级形态的杂文,《每周评论》、《觉悟》、《学灯》等刊物群起响应。据有人统计,“当时有数以百计的进步报刊,多数都为杂文辟出园圃,因而“几年间涌现出的杂文以数万计。”继杂文萌蘖之后,记叙抒情散文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写过这类散文。报告文学的勃兴虽然是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也有大量作家开始实验。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曾追述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造成这种成功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时代的激发,但从文体本身来看,则和新文学作家在近代散文变革成就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散文理论,重建新的散文文体观念具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时期,周作人发表了《美文》,王统照发表了《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发表了《絮语散文》,鲁迅也翻译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这些文章全部或部分地介绍了欧美散文特别是随笔散文的理论。以此为参照,新文学作家从两个方面初建起现代散文观念:一是文学散文观。中国古典散文观,混淆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界限,是一种与韵文、骈文相对的广义散文观,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初期仍未得到彻底改变。但由于欧美散文的介绍,散文终于被视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独立文学类型,确立了散文即美文的新观念。二是随笔散文观。英国随笔是西方近代随笔散文的典型形态,它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功能,结构和抒叙方式不拘一格,灵活自由,语体亲切自然,如同家常絮语。这些文体特征给予新散文家的文体意识以深刻的影响。以近代欧美散文特别是随笔散文为参照系,彻底批判了散文的古典模式,现代散文的文体规范便得到了初步确立。
1917年文学革命爆发后,现代戏剧沿着近代已经开通的道路,进入了文体规范的确立时期。
鉴于近代戏剧变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些激进的新剧倡导者们更高地举起了以西方戏剧为参照彻底否定古典戏剧的革命旗帜。1917 年3月,钱玄同在《新青年》3卷1号发表致陈独秀的信中首先发难,认为“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外国之新戏”“讲究布景,人物登场,语言神气务求与真者酷肖,使观之者几忘为舞台扮演”。钱玄同这些带有根本方向性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倡导者的热烈响应。1918年6月, 《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同年10月又出版“戏剧改良专号”。胡适、傅斯年、欧阳予倩、周作人等人一致主张:彻底废除旧戏体式,“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欧阳予倩还就这一主张发表了更为具体的意见:“剧本文学为中国从来所无,故须为根本的创建。其事宜多翻译外国剧本以为模范,然后试行仿制。不必故为艰深,贵能以浅显之文学,发挥优美之理想。无论其为歌曲、为科白,均以用白话,省去骈俪之句为宜。”(注:《予之戏剧改良观》,1918年10月《新青年》5卷4号。)伴随着上述意见的提出,新文学作家开始大量译介外国近现代作家的剧作和理论。继《新青年》刊出“易卜生专号”之后,《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和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四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和《时事新报》副刊),以及现代第一个戏剧月刊《戏剧》,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全国28种报刊共发表翻译剧本81部,涉及到46位外国剧作家;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泰东书局等出版的外国戏剧集共76种,剧本共151部。借鉴和摹仿外国话剧, 为现代戏剧文体规范的建立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从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所作的现代第一批白话诗起, 在第一个十年里,新诗先后出现了三种基本体式:自由体、新格律体和象征体。稍晚于新诗的是散文。从1918年4 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并发表刘半农等所作的现代较早的白话议论性散文(杂文)起,杂文和小品散文(记叙抒情散文)逐渐成为第一个十年现代散文的基本体式。1918年5月,鲁迅所作的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 此后继续出现了两种主要体式(叙事和抒情)的短篇小说,中长篇白话小说也开始出现。戏剧文学由于受制于生产机制和观众条件充当了各类文体建构阵营的殿军,但从1919年3 月胡适所作的第一部现代话剧《终身大事》问世后,也出现了两种主要体式(叙事和抒情)的独幕剧,多幕剧也开始试作。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是现代文体的创立期,综观这十年的文体进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文体现代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不只表现于文学家们高度重视文体革新和创建的价值,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诗歌、小说等文体的形式规范都力求加以科学的界定和把握。这一点与近代多以如何加强文体宣传教育功能为归宿的探讨迥然不同。这一时期发表的胡适的《谈新诗》、周作人的《论小诗》、郑振铎的《论散文诗》、郁达夫的《小说论》、瞿世英的《小说研究》、沈雁冰的《小说研究ABC》、 周作人的《美文》等文章,都多以西方的文体理论为参照系,对文体的审美规范做了系统、科学的阐述。
其次是文体实践探索的自由。第一个十年是文体从传统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创作机遇的时代。成仿吾表示:“我们要秉我们的天禀,自由不羁地创造些新的形式。”(注:《诗之防御战》,1923年5 月《创造周报》第1期。)胡适说:“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注:《谈新诗》,1919年10月《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这些主张或从探索的态度,或从探索的方向,概括了文体自由的涵义。正因此,这一时期各类现代文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而且,文学家们并不是按图索骥,而是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自由创作,因此造成了许多作品文体界线模糊,边缘文体多有产生的一种青春期状态。
现代文体的创建不是中国文学内在机制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引进一种全新的西方文体规范对中国传统文体进行极端式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虽然由于文学家大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学修养,致使新文体中旧的因素仍有较深的印痕,但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具体操作上经验的缺乏等原因,食洋不化却是这一时期文体建构的主要缺陷,特别是在语言形态上,大量嵌入外文单词和西洋句式,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体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承继创立期的成就与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演变态势。
表现之一是某些文体亚类型的消长兴衰。文体消落最突出的领域是诗歌,1926年前后,不满于初期白话诗过分自由化的倾向,崛起了以新月派同仁为代表的新格律体诗。几乎是同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体诗也出现于诗坛之侧。但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始,象征体便从诗坛陨落。1931年顷,盛极一时的新格律体也消匿于诗坛。与此相反,这一时期许多文体亚类型却勃然而兴。诗歌方面有臧克家为代表的半自由体和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象征体。半自由体是对新格律体的反拨,它反对诗体的完全散文化,也反对过分的整齐律,而是将二者之长加以融合(如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新象征体继承了李金发等人善于用意象进行“暗示性抒情”的叙抒方式,但又不像李诗那样晦涩、朦胧(如戴望舒的《雨巷》)。小说方面除了前一时期还处于萌蘖状态的中长篇体式在这一时期确立并成熟外,还出现了以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所创建的感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散文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3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的勃兴。而戏剧文体方面同样引人注目的则是多幕剧体制的确立和成熟。这一时期的文体消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同社会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剧变有关;也同文体经验的积累和读者审美心理的变化有关;而创作主体及其思维方式的更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表现之二是文体意识的全面自觉和文体规范的成熟与深化。
第一个十年对文体价值、功能和规范的认识主要集中于诗歌和小说,散文则集中于杂文,至于“叙事抒情部类的理论,不象杂文的有鲁迅那样,既是创作大师,又是理论的建立者,所以他在开创期并没有系统的介绍和阐明”。(注: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戏剧文体的研究文章则更为鲜见。这一时期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各种有关小品散文文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兴盛一时,报告文学的文体研究也如异军突起,成绩卓然。(注: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5页。)戏剧文体研究虽然仍不理想,但比起前一时期则有了长足进展,尤其是民众戏剧社的一些理论家,对现代情节剧文体规范的研究,已基本上达到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程度。(注:参见孙庆升《为中国话剧的黎明而呼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伴随着文体意识的全面自觉,文体规范的实践也不断成熟和深化。在第一个十年业已基本成熟的文体都是一些体制简短的样式,如短诗、短篇小说、杂文、独幕话剧等。而这一时期,文体建构普遍向着篇幅较长或规范相对较为复杂的样式深化,因此,长诗、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多幕剧的创作蔚为大观;而且不论长短繁简,大多数现代文体规范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成熟。在语言形态上,作家们普遍从对“白话化”的一般追求上升到对语言审美特性的高层追求。在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上,也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如小说方面,像上一时期鲁迅所批评的“技术是幼稚的”现象已完全绝迹,而代之以茅盾、巴金和老舍等一大批小说家所奏出的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优美乐章。
表现之三是文体形态上食洋不化现象的改进。由于不断深入的唤起民众的现实政治需要,大众审美心理的制约和创作主体对如何利用外来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课题的反思等原因,作家们开始重视并较为自觉地探索文体民族化的问题。民族化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大众化的层面。“左联”对大众化的理论倡导和多次讨论,以及中国诗歌会对诗体大众化的呼唤,加速了文体大众化的进程。在诗歌方面,不少作家主张“技巧不能过于脱离大众”。(注:“文体”一词在现代文学中主要有三义:一为作品体式(或称体裁),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章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二为作品的语言形态,如瞿宣颖《文体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三为作家风格或流派特色,如“冰心体”、“语丝体”。本文将文体界定为:由语言形态、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作品的形式审美规范,有时也指由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作品类型。)因而他们的作品从语体到格式都趋向通俗化,前一时期过分欧化的现象得到很大克服,甚至出现了不少拟民歌体的作品,如蒲风、温流和臧克家的一些诗作。其它文类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叶圣陶和丰子恺的散文以及李健吾的剧作也都既消除了文白杂糅的弊端,也消除了洋味十足的毛病,在文体上变得平易、朴素。
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胜利这10余年间,由于当时国统区(包括“孤岛”地区)和解放区(抗战期间称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种既具有政治差别、也具时代甚至文化差别的地区的划分,现代文体的发展在两条支脉上也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动态趋势。
国统区文体演变的总趋势,依然是沿着五四文体革命开辟的道路,继续以西方文体为参照系,发展着现实需要的各类文体。抗战初始,由于唤起民众投入民族救亡事业的迫切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性质更为鲜明的小型简便的剧作形式充当了各类文体的先锋,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一时十分活跃。与此相似,短诗、朗诵诗、杂文及一向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的小型报告文学也特别兴盛。对于五四以来的新诗家族来说,朗诵诗是一个全新的亚类型。它诞生在抗战初期进步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作者主要有高兰、冯乃超、光未然等。朗诵诗从文体基本形态来看属于自由体,但由于宣传功能的突出和传播方式的特殊,又与一般自由体略有不同。朱自清说:“宣传是朗诵诗的任务,它讽刺、批评、鼓励行动或者工作。它有时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运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语言;这不是文绉绉的拖泥带水的语言,而是沉着痛快的,充满了辣味和火气的语言。这是口语,是对话,是直接向听的人说的。”(注:《论朗诵诗》,《论雅俗共赏》,观察社1948年5月版第37页。)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除上述小型文体形式的勃兴之外,国统区在第三个十年间各类文体的发展态势是很不平衡的。其中,文体成就较大的是诗歌。艾青、田间和崛起于抗战伊始的“七月”诗派的其他诗人,以及40年代后半期被有的人称为新现代派的“九叶诗人”,把“五四”以来的自由体诗推向了新的高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文学期间自由体的规范形态,在小说方面,10年间有许多辉煌之作,除文体规范的圆熟之外,仍有许多创新。散文方面最繁盛的是报告文学,这种繁盛使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戏剧方面除了曹禺、夏衍在一般话剧形式上的继续探索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抗战中期达到鼎盛的历史剧体式,由于实践的充分开展和剧作家的理论探索,使这一体式从语言到结构和叙述方式,都达到了成熟。而解放战争初始发表的《升官图》(陈白尘作)则意味着现代讽刺喜剧文体规范的成熟。
在解放区,第三个十年各类文体的发展脉络相对国统区来说显得比较单纯和清晰,即较为一致地注重传统文人形式和民间形式的利用。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现代文体的基本框架中汲取较多的传统形式,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从总的情况看,前者占主导地位。
第一种情况的突出表现是艾青、田间和柯仲平等人到延安后所创作的一些诗歌,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小说,吴伯箫、杨朔、孙犁等人的散文以及新歌剧《白毛女》等戏剧作品。第二种情况的突出表现有肇始于《王贵与李香香》、终结于《漳河水》的一批民歌体新诗;以《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合著)为代表的新英雄传奇;另外,还有以《逼上梁山》为代表的一批新编历史剧和京剧现代戏。
解放区文体发展的这种向传统(文人和民间)文体的现代意义的复归现象,有其产生的多方面原因。一是解放区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一是解放区文学接受对象(工农兵大众)的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制约,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对作家思维方式的导向则更起了决定的作用。
文体演变的历史启示
回顾30年来现代文体的发展历史,它的兴衰演变规律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是十分丰富的和宝贵的。
其一,现代文体的诞生和演变动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社会进程特别是政治进程的现代化需要不能不是最根本的客体原因。正如瞿秋白所说:“中国的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作新文学。”(注:瞿秋白《〈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序》。)但是短短几年的“五四”文体革命,就基本摧毁了经营几千年的“趋稳定”的古典文体规范,初步建构起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从文学本体(自身)来看,却主要是因为引进了与传统迥然“异质”的西方文体系统的缘故。鲁迅、朱自清等人都反复谈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注: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体本身尚未具备向现代化自然演进的内在机制。而与此相应的主体原因,则是一代具有新的思维素质的文学群体的崛起。当然,作为一种要在中国扎根生长的现代文体系统,它又必然受到传统(文人和民间形式)和被传统长期熏染的民族大众审美接受心理的制约。可以说,现代文体的确立正是以上四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演变动因,也必须从上述发生原因中去寻找。
其二,现代文体确立和演变动因也大体造成了它的流程态势。从总体趋势看,是新一代文学家不断寻找新的形式,以表达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审美感悟和理解。但各类文体的演进过程却并非呈现为连续发展的线性序列,而是一种起伏消长的动态局面;并且,各类文体之间也相互渗透,其发展也存在不平衡性。相对来说,小说、散文强于诗歌、戏剧;长诗、讽刺喜剧和讽刺小说以及悲剧的发展都不够充分,史诗式的文体建构较为少见。这其中的奥秘都可从四种因素中找到答案。
其三,上述两点也大致规定了中国现代文体的总体面貌和形态性质。如果以世界文学格局为参照物,那么中国现代文体的主流形态大致与西方近代文体相一致;在现代主义思潮中诞生的西方现代文体规范,虽然也冲击着中国现代文体,并程度不一地成为某些文体的构成因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代文体的总体面貌。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体是以与西方近代文体相似的格局,结束了它的文体封闭时代,而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正是这一性质的中国现代文体,适应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其四,文体的现代化同时展开为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所谓“欧化”(即“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鲁迅指出,要创造现代中国的文学,必须“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非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注: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文体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在于某些时候二者的偏至。20年代象征体诗的过分欧化是一种偏至,而4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过分迁就民间形式而贬抑外来形式,某些人甚至号召“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则是另一极端的表现。
标签:梁启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体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议论性散文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胡适论文; 刘半农论文; 散文论文; 诗体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