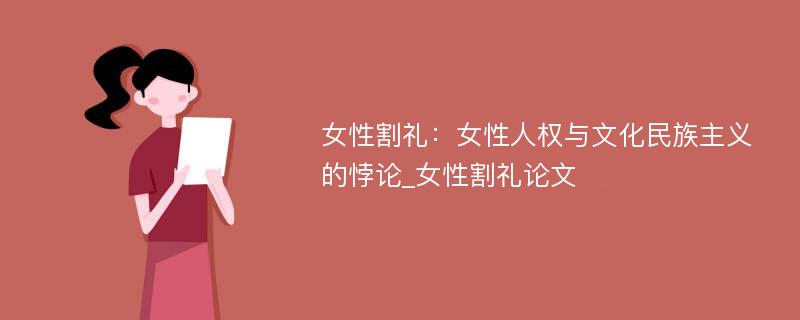
女性割礼:妇女人权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割礼论文,悖论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人权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1-0114-07
女性割礼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至今仍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着,它的分布几乎是全球性的,在非洲大陆,西起塞内加尔、东至索马里横跨整个北非地区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在内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南欧和印度的各穆斯林民族中,都广泛地施行女性割礼。另外,在马来亚群岛、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美洲的秘鲁、巴西以及大洋洲的一些土著居民中,也有此习俗。女性割礼的现象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国家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地较为严重,在美国和欧洲这些有着众多非洲移民的地区也时有发生[1] (P691)。女性割礼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也导致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遵守某种习俗是一个社会的权利,施行女性割礼的民族应有自己的文化自决权,其他社会无权将与之相悖的道德和信念强加于该社会。女性割礼的反对者则强调这种做法对妇女和儿童的身体危害和情感创伤,主张废除这种陋俗。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一个社会的文化自决权和保护个人的身心免遭侵害之间达到平衡关系,是维护一种传统文化重要,还是保障妇女儿童的身心利益更重要?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中,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受侵害的妇女应当从这种带有伤害性的割礼习俗中解脱出来,这也正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女性割礼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cision)亦称为割阴(Clitoridectomy),或称女性生殖器切除术(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简称FGM),是一种以切除女子外阴为特征的成年礼①。实际上,女性割礼包括一系列对生殖器进行的手术,通常有3种形式:即法老式切割术或阴部扣锁术(Infibulation or Pharaonic)、切除术(Excision or Clitoridectomy)和环割术(Circumcision or Sunna)。女性割礼最初是如何产生的,今天已很难考证,据说它起源于古代母系社会的珊德社(Sande),该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为确保妻子间和睦而不争宠,要求入会的女子实行割礼,虽痛苦异常,但得到社会的强大支持。为了安慰受割礼者,其他妇女为她准备食物,并为她唱歌跳舞,力图使她相信现在的痛苦将确保她未来的生育能力。同时,能忍受这种痛苦也标志着她的道德和社会意识的成熟[2] (P25-31)。关于女性割礼的来源,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远古蒙昧时代,非洲各部落只考虑如何繁衍后代,以增强部落的实力,割礼普遍地认为是提高女子生育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另一种说法是各部落间的战争频繁,男子要经常远征,受过割礼的妇女被认为能更有效地保持自身的贞操,从而避免不忠于丈夫的行为。此外,在非洲的许多部族中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即每个人体都具有一阴一阳两个灵魂,对于女子来说,呈阳性的灵魂附在阴蒂上。为了最后明确男女的性别,就必须从女人身上切除多余的东西,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女人,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3] (P25-31)。
女性割礼迄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有人说它起始于古埃及法老时期,从几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就发现,有的女干尸已受过割礼,在金字塔中还有关于割礼的壁画[4] (P387)。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便有行割礼的习俗,他们认为这种习俗有利于健康,使人清洁、卫生,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女人的性欲,可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此种习俗在埃及相当普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希伯来人将它视为一种“信念的标识”时,才开始在中东地区流行起来。历史学家相信,它可能是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时带走的一种观念,割礼也被看作是犹太人超自然的象征,按照严格的犹太教理论来说,犹太民族的女性也应行割礼,《圣经》上就有摩西之妻受割礼的记录,但因一些犹太教学者的反对而没有得到提倡。到公元前5世纪,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在黎巴嫩、叙利亚一带的阿拉伯人中已广泛地存在着女性割礼的做法。虽然女性割礼发生于伊斯兰教起源之前,但它的延续和发展与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盛行割礼的伊斯兰民族,如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企图从《古兰经》里找到根据。据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塔与他的另一位妻子海蒂斗嘴之后,命人割去了海蒂的阴蒂,自此以后割礼就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妇女中盛行开来[5]。
文化人类学家一般者认为女性割礼只会发生在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它是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为了生殖繁衍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其产生根源是基于当时的人们将女性阴蒂与生殖对立起来的扭曲认识。在远古人类的生活中,性与生殖的关系是自然而和谐的,而后才出现了阴蒂崇拜的逆向演化即割去女性阴蒂的做法,这种冷酷的女性割礼在人类性与生殖的关系中奏出了极不和谐的声音[5]。
在盛行割礼的非洲各地,人们把割礼视作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女孩子只有在受过割礼后,才被公认为是部族的正式成员,否则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歧视。19世纪非洲一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这与割礼习俗有直接关系[6] (P99)。至少在非洲有一个关于这种手术起源的假设,那就是认为没有接受过割礼手术的妇女是社会的耻辱。伏尔泰曾经指出:“这种仪式,今天看来猥亵下流,在从前却是神圣的。因此,祭司们把生殖器官的一小部分贡献给创造万物的神,似乎也是很自然、很正当的举动。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对女孩子施行割礼,即割掉一小部分阴唇。这表明,健康和洁净都不能成为这种仪式的理由,因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割礼的女孩肯定可以跟一个行过割礼的女孩同样洁净。既然埃及的祭司们要做这种手术,他们的入教者也应是这样,但久而久之,这种特殊标记就完全归祭司们专有。这只是一种起源于迷信,然后因袭保存下来的古老风俗而已”[7] (P90)。
女性割礼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或为减少女子的性欲以保持贞操;或为迷信这一做法可以促进女子青春期的到来而受到宗教的嘉许。在非洲大陆上,处女格外受到尊崇,那些做过割礼手术的女孩子在婚前不是去挑选婚纱准备嫁妆,而是要到未来的婆婆面前接受检查,看看被缝合的阴部是否原封不动,以此来证明这位少女的贞洁,女子只有在被确认为是处女之后,婚礼方能顺利进行。如果验明新娘已非处女之身,她的命运可就惨了,轻则被休回娘家永远别想嫁人,重则被处以极刑。从实行割礼的不同文化中的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割礼是男性统治下的女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割礼能使女性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找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
二、女性割礼对妇女人权的侵害
女性割礼的本质在于整个或部分切除或烧毁女性的外生殖器,目前此仍在非洲等地流行的做法,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广泛关注。对女性割礼提出批评的人通常举出这样的理由:割礼手术既摧残了女性的性功能,又危害了她们的健康。弗洛伊德早在《处女的禁忌》一文中就已指出,对女孩子的阴蒂及小阴唇的割礼,要比对男童施行的割礼残酷得多,因为后者并不伤害其性能力,而前者对性能力的破坏却严重得多[8] (P241)最可怕的要数“法老割礼”,受这种割礼后的女子必须长久地以固定姿势躺着,直到被切割的大阴唇两侧相互融合、粘连,使伤口愈合在一起完全封闭阴户,阴茎便无法进入阴道完成性交,从而达到维护女子贞操的目的。割礼手术使得阴道闭合,对于女子婚后的性生活非常痛苦。在妇女行将婚配时,不得不把阴户出口处割开一小部分用于性交,此后如果丈夫外出,妻子还可能被迫将阴部再次切割封闭,无穷的苦难又将重新开始。只有到生育前阴部才被完全割开以便分娩,但产期一过,又再次施行手术封闭大部分阴户[9] (P202-203)。上述的锁阴习俗是割礼的一种极端异化现象,在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人(Nubians)、埃塞俄比亚的蒂格赖人(Tigrai)和古拉格人(Gurage)以及非洲的索马里人(Somali)、安哈拉人(Amhara)、吉布提人(Djiboutis)、伊萨人(Issa)、阿法尔人(Afar)等民族或部族的少女中广泛地盛行着[10] (P161)。女孩子们之所以要经受这种巨大痛苦多数是被迫的,不是出于她们自身的意愿,而是出自男人对女子贞节的需要。
女孩子接受割礼的年龄依社区居民和传统习俗的不同而异,有些是在婴儿出生后几天或几周之内施行,有些则到女孩青春期时进行,有些是在妇女首次怀孕后第七个月进行。女子被施以割礼时如受酷刑般痛苦,在这过程中甚至有人当场昏死过去。在南地族中,女子的割礼实际上应该说是“烙礼”,因为那些执行这种仪式的巫婆们是用烧红的火炭将少女的阴核和阴唇烙去的,这种手术非常痛苦,要经过好几个月伤口才可以痊愈,而在执行这种仪式时,又照例不准女孩子们喊痛,因为呻吟会招致不吉[11] (P60-61,P107-108)。尼日利亚的女孩子出生后7日或在7岁时施行割礼,割礼多用刀子、剪子或是剃刀,止血剂为粉末状的咖啡、木炭灰、椰子油等,消毒很不严格,使得伤口很容易受到感染,染上破伤风的情况最多[12] (P101)。
非洲每天仍有6000多名女孩要遭受这样的性残害,全世界每年至少要有200万女童可能成为下一批牺牲品,全球已有1.5亿女性正面临着割礼后的厄运。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绝非只是非洲所独有,一方面,非洲的妇女们想逃离这种极端残忍的女性割礼,欧美的人权主义者也在为承认割礼是非洲妇女的避难理由而努力,另一方面,大批非洲廉价劳工流入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们将女性割礼也带进了工业国。据估计,每年至少有7000名妇女和儿童从那些至少多数女性都要接受割礼的国家移民到美国,在这些移民的故国,接受割礼的女性占有的实际比例是很大的,“在索马里接受FGM的人所占比例将近100%,埃及为97%,埃塞俄比亚超过90%,即使刚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那些家庭中坚持FGM传统习俗的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但这些数字暗示,在美国长大或在美国诞生的许多少女,现在每年都处在FGM的危险之中”[12] (P10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割礼普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欧美的社会活动家正积极为废除这种性摧残而展开斗争,他们的观点是:首先,割礼会给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其次,割礼的确能减弱女性的性欲,但近90%的妇女在接受过割礼后仍有较强的性欲,因此割礼难以达到保持妇女贞操的效果;第三,《古兰经》中并未提到割礼,相反从有些经文看,其对性快感的态度是积极的,因此有些文化禁止妇女享受性快感的做法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第四,关于阴蒂等外生殖器官会造成不育或影响女性特征的看法纯粹是一种偏见,没有任何事实做依据[13]。女性割礼的反对者们早在1979年10月就创建了“国际废除性摧残委员会”,总部设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1982年,该委员会在达喀尔召开了一次关于“妇女和社会”的国际讨论会,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施行割礼手术对少女进行性摧残。迄今埃及、苏丹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已经宣布,切除妇女的性器官为非法行为,但私下里对女孩施行的割礼手术并未因几道禁令的颁布而有所减少。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基金会等机构多次通过决议,对非洲这种残忍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废止女性割礼习俗。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说,割礼对女性身体的直接影响是急性感染、破伤风、邻近器官渗血、由剧痛产生休克以及出血,甚至会导致死亡。
三、实行女性割礼与文化自决权
对于那些盛行女性割礼习俗的民族和部落而言,割礼是女孩成为女人的标志,并且是他们的民族和部落文化及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宗教任务。在非洲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和原始民族中禁止女性割礼的实施,目前仍有相当大的阻力,因为这种对女童施行的割礼手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那些对女性割礼给予支持的人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对妇女进行性约束,割礼通常割去女性的性感觉器官以削弱性欲,甚至使之不能性交,从而达到为新郎保证新娘贞洁的作用;第二,他们迷信地认为,施行割礼可以促使女孩子青春期的早些到来,从而获得旺盛的生育能力,阴蒂等外生殖器官被认为会造成不育或影响女性特征,而女人没有生育能力是奇耻大辱,因此要施行割礼手术;第三,根据宗教信条,妇女要施行割礼,宗教与这种习俗联系最多的是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女性割礼是受《古兰经》的启示,因为伊斯兰教最强调女子的贞操;第四,那些赞成女性割礼的人认为,施行割礼的民族和社会应有文化自主权,外部文化应当尊重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反对这种做法的人(特别是西方人)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是将自己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其后果将会导致非洲部落法和部落组织的解体[14]。
盛行女性割礼的社会迷信着种种不接受割礼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在这些社会里,人们对女性的身体构造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反而认为割礼是古已有之的习俗,每个女人都毫不怀疑地执行着被切割的程序。虽然为割礼手术而支付的费用通常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开支之一,但却被认为是一笔很好的投资,不然女儿们长大后将不能进入婚姻市场,父母也认为,确保女儿有最大可能去找到丈夫是他们的责任。在父权背景下,经济生存问题将给妇女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婚姻被看成是她们经济来源惟一的或基本的手段,即使她们已经认识到了割礼对身心健康的危险,也仍会继续让女儿接受割礼手术[5]。
为了论证女性割礼的合理性,有人摆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过去英美的医生将阴蒂切除术作为治疗女子忧郁症和手淫癖、淫狂、癔病、女子同性爱及癫痫病等的方法之一。美国妇产科医生协会虽然发表了一项声明,反对所有医疗上不必要的女性生殖器修改手术,但是有些医院和医生仍继续为妇女做这类手术。[13] 另有论著提到女性阴唇扩大症是某些种族的特征,如不割礼会影响生育,日常行动也不方便。比如说南非黑人哈顿多特族的女人在生理上便有这种阴唇扩大的特征,又如非洲的班图族和南地族两种黑人,其女子多数也有这种阴唇扩大症,因而当地人有“你的前门口挂着一束烟叶一样累赘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其女子的小阴唇也有反常延长的情况[15] (P121)。据说有人在埃及作过实地调查,发现埃及女子的阴唇部分多数都松弛下垂,形成一大块平扁的肉片,全然掩蔽了阴门口,看起来非常不雅观,“中东民族和黑人女子在成年时要举行割礼的习俗,这虽是宗教仪式,但真正的动机是在割除这种妨碍种族繁殖、极不雅观的东西,这种割礼并不是很多地方都流行,大概只是生理上的需要才会如此”[11] (P60-61)。也有观点认为,女性割礼并非为了宗教上的信仰,也不是为了清洁卫生,而是为了日后性的享受。因为这种割礼手术另有妙处,它能使成年女性的阴道变得狭窄,可以发生刀鞘一样包裹男子性器官的作用,也正是为了男人的此种享受,她们才肯甘受如此的苦痛。有些行过割礼的女性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性技巧,懂得这种技巧的女性遂成为罕见而珍贵的高级娼妓[16] (P179-180)。这种针对女性的割礼习俗,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古代女子的缠足,其最深层最隐晦的含义是直接满足男子的性快感。据说缠足后的女子为保持行走时身体的平衡,两腿及骨盆肌肉经常处于绷紧状态,所以缠足后的女人在性交时由于其阴部肌肉较紧,性交时会给男人如同处女做爱的感觉[17] (P96)。
女性割礼在非洲最为普遍,但多数是在青春期到来前才举行的,有人因此认为女性割礼主要不是为了女性的生理卫生,如果是考虑卫生的话,割礼的时间显然拖得太晚,事实上它更可能代表一种“青春期仪式”。非洲为数众多的部族都把割礼作为女孩子成年仪式的一部分,乍得的图布人女子的成年仪式就是对女孩子做切除阴蒂的手术。割礼的社会功能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实行了割礼的女孩从此成为部落的一员,而割礼手术就是她们向童年诀别的一根界桩,割礼在亲属群体所有成员的心理上都起到了这种作用。[18] (P84)肯尼亚的马赛族几百年来都维持着一种成年礼,即女孩子在第一次月经来潮后要割除阴蒂,否则不准结婚和继承遗产,也不准和他人共舞[19] (P96)。
非洲人对外界否定女子割礼态度的反抗在20世纪20年代初进入了公开化阶段,他们认为女子的成年仪式在他们的社会中有着意义深远的目的,任何突然的废除都将大大地扰乱他们从心理、社会到宗教上的安全感。人类学家发现,那些针对殖民主义和外来强迫势力而展开的文化运动,往往利用本土原有的文化符号体系,构造出本土的民族一体性和象征力量以排斥外来的文化因素。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克在其所著的《从祝福到暴力》中描述了马达加斯加岛马瑞那人(the Merina)当中的割礼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其功能的转移,在将近200年的发展过程中,割礼的象征一直被该族群所保留,但其社会意义则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传统的部落社区时代,割礼的象征十分突出祖先对其后代的保佑和祝福,强调祖先与后世的社会连续性和家族社会的一体化。但在殖民主义时代,为了表示一致对外以显示本土社会的力量,割礼仪式被改造为具有暴力色彩的军事性表演[20] (P203-204)。割礼已经具有许多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义,在面对外来压迫的民族中,诸如马瑞那人之类“隐蔽性”的符号抵抗运动广泛存在。已故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就赞成女性割礼并认为它是非洲古老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必须加以保留。在基库尤人中间则建立了一些独立的学校,其目的是恢复这一习俗,并为那些由于割礼问题而不能进入教会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教育。
四、二元对立语境下妇女的抉择
女性割礼是父权制文化对妇女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特殊的实例,从而为外部世界将国际人权法应用于具体的对妇女的关注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领地。基于它对妇女和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国际社会要求结束这一传统习俗。但另一方面,那些流行女性割礼的本土势力又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习俗和道德准则。这导致了两种互相对立的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实行割礼的民族应有“文化自决”的绝对权利,根据这种观点,即使某种文化传统经常导致死亡,也不能被指责为对人权的侵犯;第二种观点认为某种文化经常伤害或残杀个人,就是对人权的侵犯,应加以制止[14]。对于生活在实行FGM社区里的妇女来说,挑战FGM就等于挑战宗教法规,因为宗教与习俗已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使女性割礼在穆斯林世界中竟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比如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下令禁止女子割礼仪式,此举在穆斯林学者中引起骚动,有人认为这项命令亵渎了伊斯兰教,与他们的教义相抵触,于是就密谋造反。[21] (P33)女性割礼的复杂性加大了解决的难度,把这个问题裹上民族文化的外衣就看不到它的实质。西方社会往往将女性割礼视为一种对妇女人权的侵害,而非西方人也可能视美国妇女的隆胸是女人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做出的与割礼相类似的怪事。那些能够提供教育和向社区传递有关FGM信息和保护未受割礼少女的医务人员往往既要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又要引导人们摆脱正是那种文化传统中带有伤害性的那部分习俗在道德上的制约作用,这使得他们经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巴基斯坦学者法丽达·沙希德指出,其实只要一个地区流行这种风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要遵从这种习俗,而大部分穆斯林社区并不实行FGM,这些社区里的人们对此闻所未闻,当他们听说这居然和伊斯兰教沾着点边儿时,常常大惊失色;另一方面,冈比亚妇女和法律研究小组揭示,让妇女们得知其他穆斯林妇女并不遭受FGM之苦,能大大激励她们冲破思想的禁区,反抗自己社区里的FGM[22]。在美国,那些童年时受过割礼之害的移民妇女现已团结起来,她们积极反对故国同胞中流行的这种传统文化习俗,并且将自己在美国和去非洲劝说人们改变这一传统习俗的工作作为一项事业来奋斗。这些人都是深受割礼之害的非洲女子,现在她们四处宣传自己的痛苦教训,教育人们抛弃此传统习俗,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她们还向人们描述自己接受割礼后肉体上的痛苦:发烧、疼痛、不能享受性生活,有些人甚至因感染而死亡。1998年秋,《沙漠之花》(Wüstenblume)一书风靡欧美,作者沃丽斯·德里(Waris Dirie)详述了自己5岁时遭到性摧残的痛苦经历,这位勇敢的女性通过向世人揭示她痛苦的个人隐私,希望能帮助结束这种残害了太多女性无辜者的野蛮传统。沃丽斯所遭受的是那种最可怕的“法老式割礼”,当她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女人(至少是黑皮肤女子)都经历了这种割礼残害时,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遭遇是不公平的。1997年,她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邀请,成为该组织的女特使到世界各国作反对摧残妇女的宣传。几年来,她的足迹遍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埃及等地,不倦地现身说法以宣传割礼的罪恶,唤起人们的觉醒以废除这种陋习,使非洲千千万万的妇女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23] (P154)。
现在为数不少的非洲妇女正领导着反对割礼的斗争,但她们尽量避免将这种手术说成是对人权的侵犯,并反对用外力来终止这种行为。由于视角的不同,她们与外部文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大家都同意割礼是一项应该废除的行为。非洲妇女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参与的反对割礼的运动带有过分渲染的色彩,她们对此极为反感,并进而认为这是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24] (P201)。弗兰·霍斯肯(Fran Hosken)是西方研究非洲妇女阴核切割术的权威之一,她研究这一风俗的前提是:这种手术是不让妇女在性交时有快感。从这一前提出发,她的结论是在这些盛行阴核切割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的性欲以及生育权被男人控制,父权制通过对性行为的控制在统治妇女,使她们依赖男人[25] (P121)。在1980年的国际妇女大会上,霍斯肯开展的关于割礼的图片展引起了公开的反对,非洲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霍斯肯把阴核切割术作为判断非洲妇女地位的唯一标志的做法缺乏历史的观念,她们反对把阴核切割术这一问题从妇女争取平等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割裂出来单独讨论,更不接受第一世界妇女把这一问题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这种土著文化中男女对立的观点。1985年内罗毕妇女大会上,肯尼亚的伊达·加切卡亚(Edda Gachakia)就指出,许多非洲国家的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在反抗和抵制这些残害妇女的风俗,但她们希望诸如营养、婴儿死亡、文盲、医疗保健措施、技术训练等问题能够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得到与女性阴核切割术同样的曝光度。[26] (P222)在非洲妇女看来,她们面临着许多比反对女性割礼更重要的事情,而外界单纯只关心女性割礼问题显然是偏颇的。一些非洲妇女感到有捍卫本土文化的必要,她们并不像西方妇女那样认为割礼风俗是由于非洲文化落后的原因造成的,相反她们并不把它简单地看成是有害人体的习俗,甚至还认为这是她们民族的特征。
对于像女性割礼这样富于文化挑战性的父权制习俗,应该要以一种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复杂视角来看待。女性割礼习俗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传统已经在非洲大陆上延续了数千年,它早已融注到这些民族的意识深处积淀为一种集体心态和群众信仰。接受女性割礼成为了妇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割礼被认为是女性成熟的标志并由她们的父母自豪地执行着。因此不可能光靠几道政治性禁令就从总体上彻底改变它,来自外部文化的批评与谴责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习俗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反而可能招致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批评。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女性割礼的关注被看成是一种种族与文化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的虚伪表达,而“我们帮助她们”的方法给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们带来许多对殖民主义的痛苦回忆,为了回应殖民主义和西方世界对女性割礼的批评,那些已经致力于在自身文化中寻求解放的非洲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不需要西方拯救者的任何干预。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显示出她们对文化复杂性和跨文化间相互尊重的敏感性认识不同,许多非洲妇女提醒她们的西方对手们要尊重女性割礼背后的悠久传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的不断发展,在这种文化的内部已开始有人意识到割礼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并积极地为女性寻找解放的途径,因为真正的解放者只能是她们自己。一个妇女自主支配其身体的完整性并拒绝接受来自外界的伤害,这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当女性真正地觉醒后,那种剥夺和限制妇女的性权力的男权社会终将结束,女性割礼也应当像中国废除缠足和多妻制一样,最终由受害国家的妇女自己来完成。
注释:
①《美国百科全书》(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对Circumcision有这样的解释:In some tribal societies,female circumcision--the removal of the clitoris and the labia majora--is also part of rites of init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