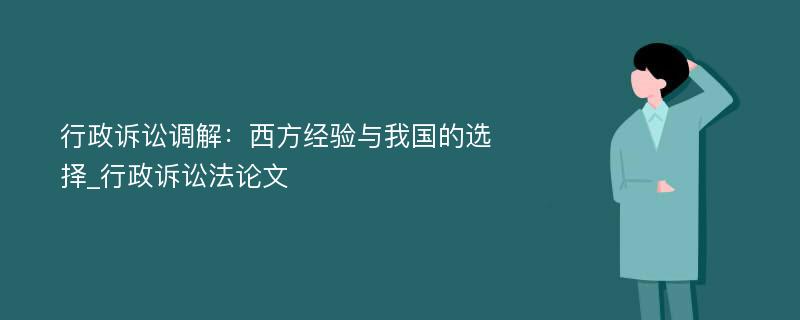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诉讼论文,中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78(2009)03-091-07
过去的30年中,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西方法院,都开始积极地尝试用调解来解决纠纷。而在东方,中国长期以来就以注重把调解和审判相结合而闻名。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法院对于通过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并且各国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①但人们对于法院能否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行政纠纷则有着不小的争议。
一、西方国家有关能否用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争论
在西方,行政法(公法)纠纷能否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一直存有争议,这种争议似乎将仍会存在下去。公法律师们会提出反对,正被审查的行政争议不可能通过调解方式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些学者就认为,公法是最抵触用调解来解决纠纷的一个领域。②一些学者甚至直接主张,公法和司法审查的特性决定了ADR(法院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是不适宜的。③反对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有两点:一是行政案件涉及了一些政府无法妥协的基本原则。当政府执行法律时,即使一定的妥协或让步可能让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但法律规定是不允许政府退让的。而且法律的执行强调统一性,不可能为某些人或事而去变更法律的明确规定。人们很难想象可以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公开的讨价还价;二是在民事调解中,调解双方通常都习惯于将调解的过程和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保密,不对他人公开。这是西方民事调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由于政府与当事人的协议可能会影响第三人甚至是公共利益,所以,政府必须将调解的过程和内容通过适当方式公开,以防止暗箱操作。这也是开放政府(opening government)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为了保守秘密而侵犯其他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这也给行政调解带来困难;如果一切都公开,则政府和相对人之间很可能达不成协议(在中国的行政审判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行政机关对于和相对人之间经调解达成的征地、拆迁的补偿协议经常是严格保密的,原因即在于害怕引发其他行政相对人的攀比效应)。
但是,西方学者、法官和民众也逐渐认识到传统解决公法的纠纷方式存有多种缺陷,如时间冗长、费用昂贵、程序繁琐等。而且用判决这种“赢者通吃”的方式来解决纠纷,通常是把当事人推向对立而不是互谅互让,当事人也失去了对解决纠纷过程的控制,没有机会继续接触并协商出不同解决方案,只能机械地等待法院的裁判。结果就是,不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赢得诉讼,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均被彻底摧毁。这显然不利于行政管理关系的和谐发展。
因此,在调解被成功运用于民事诉讼后,西方的学者和法官们开始讨论:或许调解也可以被用于解决行政纠纷,并论证了调解在解决行政纠纷时的优点: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涉及法律上绝对的合法或违法的事务,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尚存有一些灰色地带。由于立法的局限和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可能存在数种选择。所以,如果说法官可以选择性地裁判,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尝试用调解来解决纠纷呢?
其次,行政机关行使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行政管理中有不少可谈判之处。如果行政机关可以和当事人协商、谈判,法院就应当有权去监督甚至亲自过问这种裁量权的行使,建议双方调解。
再次,调解还有利于法官回避法律与现实的冲突问题。当立法滞后或者无法跟上社会发展时,法官可能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严格依法裁判可能产生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而根据案情作出有利于实现公正的裁判却又可能与法不符。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解就可能让法官避免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
最后,刑法中辩诉交易的实行,也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行政法纠纷。数十年前,由于考虑到刑法涉及一些人权问题(如嫌疑人是否有罪),人们并不接受辩诉交易。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实践却证明辩诉交易比较成功,定罪量刑上的讨价还价并没有危及社会秩序,也未侵犯了罪犯的人权。因此如果说检察官能够与严重的罪犯做交易,那么为什么警官(或法官)却不能和轻微违法者谈判呢?
总而言之,基于以上的一些理由,西方学者们开始强调,即使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适合通过调解来解决,但从整体上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却是不现实的。而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如何能在不危害法治的情况下进行。
二、西方国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的不同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不少西方国家,调解已经被法院用于解决行政法纠纷,但具体的调解方式却各异。以下是几个主要国家的调解实践的简单介绍。
(一)英国
在英国,规范司法审查的民事诉讼法CPR 1.4(2)(e)规定,如果法院认为适当,应鼓励当事人选用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并为使用该程序提供便利。这是英国法院适用调解的法律依据。英国政府也大力促进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行政纠纷。如英国工党在1995年的年会上所发表的《政策宣言》中就明确表示,要大力推广调解在解决行政纠纷中的作用,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是传统的诉讼方式,一手是今天的调解方式。”④宪政部长在2001年宣称,只要可能,涉及政府的纠纷就应通过调解或仲裁来解决。英国政府甚至颁布了一个称为“政府承诺”的文件,强调政府部门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是最后一步棋,任何案件,只要当事人接受,就应考虑使用ADR。⑤
但是,他也承认,仍然有些案件不适宜通过调解等ADR方式来解决,比如那些恶意的违法事件,滥用公权力,涉及人权的一些公法案件,一些缠讼或者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对于一些需要通过裁判来创造一个先例以澄清法律的案件,也不适宜通过调解解决。
但这些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一些涉及基本人权的案件,法官已经开始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比如在2002年上诉法庭的一个案件中,尽管涉及上诉人的居住权问题,法官仍然要求双立必须先行协商解决纠纷。⑥而且对于那些所谓需要先例来澄清法律争点的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论调,有观点就反驳说是否需要先例裁判是法院和法官要考虑的事,而通常当事人只关心纠纷得到解决。总而言之,在英国,行政纠纷的当事人被允许去通过协商解决矛盾,法庭也开始鼓励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但法官自己并不参与调解,而是将案件委托给法院外的独立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人去进行调解。
(二)美国
美国的政府和法院很早就认识到,法院根本就不可能审查所有有关行政决定的诉讼。因此,美国法院发明了一系列的标准来决定哪些案件能够到法院来,比如是否具有可司法审查性、是否成熟、是否穷尽行政救济途径和诉讼理由等等。
但这仍然没有能够阻挡美国政府部门成为大量案件的当事人。1990年,在联邦法院系统所受理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所属各机构是一方当事人的案件占全部诉讼数量的1/4。⑦而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所属的机构大约是联邦法院所受理的三分之一民事案件的当事人。”⑧这给政府和相对人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政府和民众逐渐开始认识到,虽然与政府的纠纷不可避免,但诉讼是可以避免的。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开始强调通过ADR来解决行政纠纷。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协商制定规章法》(也有学者译为《协商立法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和《行政争议解决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这两部法律旨在授权和鼓励联邦行政机关适用调解、协商、仲裁或其他非正式程序,迅速处理行政纠纷以及制定行政规章。正如一位参议员在评价上述两个法律时所指出的,这样的法律将有助于替政府找到更有创造性的办法,避免支付大量的费用,预防因法庭战斗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双方而言都节约时间和金钱,并增强国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ADR工作组,他的目的即在于促进政府更多地通过ADR来解决纠纷。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就是只有大约2%的政府纠纷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来解决的。
(三)法国
法国的法官们已经多次尝试把审前的调解程序整合到法国的行政法院程序中,法国的最高法院也支持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1986年1月6日,法国人修改了规范法国行政法院的法典,在第3条第2款中增加了一项规定,这项规定认可了行政法院扮演的调解角色。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推动调解在行政法院的使用。1998年,专门成立了一个专业小组来讨论法院附属调解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最终的报告中,这个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提供了有关把调解整合到行政审判程序的建议,还包括了一些实施意见、程序以及职业道德方面的建议。但看起来人们很少使用调解。对大多数一审行政法院来说,这个数字是每年一到三件。
(四)德国
在德国,几年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调解项目力图在德国行政法中建立一种调解文化。根据目前的一些调解实例可看出,在行政法院系统,调解已取得一定成功。有趣的是,评论家们同样提醒说,或因案由或当事人的态度,只有少数案件适合调解。德国行政法院处理的案件中,只有10%到25%的案件具备调解的条件。⑨而德国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法官可以协助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规定,被认为是调解的法律依据。但法院没有义务达成调解,只是应向当事人说明是否考虑法律关于调解的规定(《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⑩目前,德国仍在探索和实践“圆桌会议”制度,即在平等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人们仍然担心法官的过度介入,或许并不利于调解。因而,主持圆桌会议的法官不是审理案件的法官,而是其他法官;如果审理案件的法官亲自主持对话,一旦对话失败,就不便继续审理该案件。对大部分法官调解员来说,仅有10%到25%的工作量是用于调解,其他时间还是用于常规的案件工作上。(11)当然,“圆桌会议”方式不是目前的行政审判的通用方法,仅仅是探索,每个法院每年约10件左右。虽然大家都很向往协调解决争议,但是德国至今没有成熟的做法。(12)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也都各具特色。比如在澳大利亚,人们并不去具体规定,哪些行政诉讼案件能调解,哪些不能调解。一些在英国或者美国被认为不适合调解的案件,如涉及公共利益、税收、移民的案件,都成功地被调解。而在荷兰,通过协商和调解来解决纠纷是荷兰人的一个文化传统。统计数字表明在所有的被调解的案件中,75%是民事,25%是行政案件,包括了一些税收案件。(13)荷兰并不存在一个不合适调解的案件分类。
三、西方国家的调解经验
考察西方国家的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我们可以谨慎地总结出以下的几个特点:
首先,西方有关国家的行政诉讼调解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健全的行政法系统是建立在一系列多样化的救济机构和救济程序基础上的。调解被当作是对僵硬、昂贵和耗时的诉讼程序的替代。但值得注意的是,调解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更低廉、更省时,尤其是对经历了一个不成功的调解后又继续进行的诉讼而言。因此,对调解的过高期待或许会影响调解的进行。而且西方有关调解的试验项目的成效仍显不足,除了美国的数据让人兴奋外,英法德的有关数据仍说明调解成功的并不多,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案件去检验行政诉讼中调解的利弊得失。
其次,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实践都表明,调解的运用与法官和法院职员的积极性紧密相关。是否使用调解,调解能否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而不是当事人。法国的实践表明,只要法官愿意调解,他就经常能够成功。因此,行政诉讼调解的发展与行政法官的主观意愿密切相连。要想推动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转变法官(以及整个社会)的观念。
再次,在大多数国家,学者、政府以及法官们都试图定义出哪些案件适宜或者不适宜调解,但所有这些尝试都尚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信息。比如德国和法国在自由裁量权能否调解问题上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在法国行政法体系下,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协商是不可能的,而德国行政法院却认为这个领域对调解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4)国内的研究似乎也是如此,虽然有不少课题研究试图来总结哪些类案件不适宜调解或者适宜调解,但结论都很难完全经得起推敲。(15)
我们认为,或许某些案件不宜通过调解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案件都不能调解。或许从案件的种类上,存在着某些种类案件总体上不适宜调解,但对于具体的个案而言,却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有着相异的案情。因而,我们或许无须煞费苦心地去定义或者找寻出哪些种类行政案件适合或者不适合调解(因为这种努力可能永远不会成功),而是应把这样的权力预留给睿智的法官,由他(她)根据个案的情况和社会因素去决定是否需要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或许是如何对法官的选择权或者命令权进行规制。
四、中国行政诉讼中调解的现状及特殊原因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法纠纷涉及合法性和公共利益,不应允许谈判或妥协,法院只能做出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判断。如果是合法的,法院就应当维持;如果是不合法的,法院就只能撤销。因而,没有可以调解的空间,法官只能判决而不能调解。
但今天人们对调解的观点已经转变。大多数的学者和法官都坚持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16)而唯一的障碍即在于《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已经事实上超越了这个规定,不少案件已经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得到了和解。虽然法院还继续坚持不用调解书来解决纠纷,但法院巧妙地通过由被告改变或者承诺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的方式解决了法律上的障碍。相关的统计数字显示,有1/4到1/3的行政案件是以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方式得到解决的。最高法院显然也支持这种事实上的调解,并于2008年初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但碍于《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存在,仍然只是延续法院建议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原告因此撤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没有调解书的调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有理由相信,《行政诉讼法》在不远的将来修改时,行政诉讼案件可以调解的规定将可能被直接写进法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的原因和理由,显然并不能适用于中国行政诉讼的现状。在法治较发达国家,人们拥护调解,主要是因为法院裁判冗长、昂贵、繁琐。但这样的原因在我国并不突出。
首先,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着行政诉讼案件压力大的问题。不论是案件的总量,还是法院和法官的平均办案数量,都仍然处于法院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2004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平均每个法院仅受理28.7件案件,每个行政法官受理的案件数不足10件。(17)因此,不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法官,还是与我国的民事法官相比,行政法官根本不存在办案数量压力过重的问题。不少法院行政庭法官不得不办理部分民事案件;其次,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也不存在审限过长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期限分别为三个月和两个月,与西方有关国家相比,这样的审理效率是相当高的。如此短的审理期限说明,即使是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也不会显著地降低审理期限。不少的审判实践甚至表明,调解将会延长而不是缩短审理期限;再次,调解在减少诉讼费用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我国的行政诉讼的受理费用十分低廉,其他诉讼费用也不高。基本不存在调解会明显降低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问题。
换言之,西方国家拥护调解的主要理由,诸如诉讼耗时、费力和成本高昂等,在中国并不存在,而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偏好,除了受东方民族和谐思想的影响外,还有着以下独特的理由:
首先,由于我国行政权过于强大,且行政法律规范远未完善,与西方同行相比,我国法官在裁判行政案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远较其西方同行多。“中国的行政诉讼是在法律与政策、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维护政府权威与实现个人权利之间游移的选择性司法。”(18)法官的裁判经常会受到各种法外因素的困扰。法官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和足够的权威,经常处于行政机关和原告的双重压力之下,前者通过行政权来干预司法权,而后者则通过涉诉上访等方式来给法官施加压力。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法官会觉得与其通过裁判来解决案件,不如通过各种手段让当事人接受调解的方案。这对于处于并不强势的法院、法官来说都更为有利。另一个影响法官喜好调解的因素,还在于上级法院改判的压力和本单位内部息诉率的考核机制。
其次,导致行政机关乐于接受调解的原因在于,行政执法水平不高和考核机制的存在。不少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实体上并没有太多的问题,更多的是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或者不当之处。如法院裁判,则只能撤销这样的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出于自身执法的威信和“面子”问题,以及忌惮本系统内部的考核和错案追究机制,通常更乐于作出部分实体上的让步,而取得原告的谅解;原告也经常会基于和行政机关今后的长期合作,也愿意接受行政机关的新方案,见好就收。
再次,由于行政机关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且对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上很少受到真正的控制,因此通过调解和谈判解决行政纠纷的筹码很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损失经常可以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进行补偿;对于大部分相对人而言,只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也并不一定真正在乎法律上的“说法”,而更愿意通过调解来解决。因为暂时的让步或者损失,换来了行政机关的理解、同情或者以后的帮助,对于相对人而言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五、调解的潜在风险及可以采取的几种对策
如上所述,行政诉讼中的法官、原告和被告三者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由去拥抱调解,这或许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因此,在我国这样的特殊国情下,盲目地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表现形式就是: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会越来越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可能成为协调庭;法院和法治的权威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在法治较发达国家,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公民对法治都有着较高的信任度,也都承认法院裁判的终局性,承认法院的权威。但我国的民众及政府官员对法治的信仰度和忠诚度并不高,司法机关也经常只是被视为法治的工具,社会对司法的权威也不太尊重和维护。在这样的情形下,片面地强调调解,最终可能会破坏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减损法院的社会地位和解决纠纷的能力。一个不适当的调解有可能比判决更容易形成不正义的结果。对于法治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向他们提供调解,就好似用一个替代性的解决办法引诱他们。有学者甚至批评认为,在一个国家没有法治的传统或人民的法律权利有限的国度,“向他们提供调解会被视为给了他们一个替代方案的诱饵,却延缓了一个真正公正的司法体系发展的步伐。”(19)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我们还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避免法治受到损害。
首先,要限制法官的权力,以保证调解的自愿性。不少的司法案例已经反映出,行政法官经常会与政府机关一道“压迫”原告通过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如前所述,法官喜欢调解的原因是多重的:对于法官自身而言,调解会让他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避免引发当事人的信访申诉,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尤其是在他意识到他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并不确信、裁判结果并不完全有把握,上级法官可能不同意他的法律见解时更是如此。因此,一些法官热衷于调解而不是裁判,就完全可以理解。但法官对调解的过分热衷很容易引发强迫调解的问题。研究数据已经表明,如果调解建议是由法官主动提起的,那么当事人就很难拒绝,即使是一个不太满意的调解方案,当事人也可能迫于压力而接受。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调解的自愿性,调解的发起和协议的形成过程就必须牢牢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而不是法官的手中。当事人可以随意退出调解程序,并要求及时作出裁判。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强迫当事人调解或者调解中有偏见的法官,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通过赋予当事人对主持调解法官的回避权,或许是目前成本最小、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其次,尽可能实行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的相对分离。我国的法官既从事调解工作,也主持案件的审判。这样的制度既容易导致法官在裁判时的先入为主,也容易为法官与一方当事人的接触提供机会,并进而成为腐败的温床。因此,从长远来看,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的职能分离,应当是一个保证程序正义的选择。这一点的成功经验,不但得到西方法治较发达国家的实践的验证,在我国民事案件的调解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0)
再次,对于当事人之间形成的调解书的合法性,西方法官经常不负责审查。但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机关与公众间的诉讼能力有着较大的差距,公民很可能被迫、被引诱甚至被欺骗达成某种于己不利的调解协议。因此,法官就应当被赋予一个新的职责,即要审查并确保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法官应当有权去否定一个双方当事人都接受的调解方案,以维护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调解书的合法性,应当是法官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对于我国的行政诉讼而言,法院调解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我们也应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事实上的调解合法化。但必须始终坚持调解的自愿和合法性。调解中法官的作用则应当有所限制,法官既要积极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又要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当事人之上,以始终保证当事人的自决权。对于存有偏见、未审已有倾向性结论的法官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法官,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同时,也不宜过分夸大调解的功能,不能忽视法院的依法裁判在维护法治方面的突出意义;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尤为重要。
注释:
①有关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参见耿宝建、赵艳花:《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4期。
②Daniel Stilitz[2004]:ADR and Public Law,Judicial Review,volume 10,issue 3,p.220.
③Sean Wilken[2005]:The ADR in Public Law:a New Hope?,Judicial Review,volume 10,p.214.
④Lord Irvine of Lairg The Lord Chancellor Inaugural Lecture to the Faculty of Mediation and ADR,Wednesday,27 January 1999.载http://www.dca.gov.uk/speeches/1999/27-1-99.htm.
⑤For the pledge text,applic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ee DCA Annual Report 2004/05 Monit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using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载www.dac.gov.uk/civ il/adr/adrrep_0405.pdf.
⑥R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wl) v.Plymouth CC [2001] 1 WLR 803.
⑦See 142 Cong.Rec.S6157(Daily ed.June 12).
⑧参见Jeffrey M.Senger:Federal Dispute Resolution:Using AD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Jossey-Bass Press.p.2.而得出如上结论的依据是美国总检察长执行办公室公布的2001财政年度,政府律师起诉和应诉的案件总数为79854件,而同一年度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所公布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的总数是250907件。参见该页注⑧。由于美国的普通法体制,此处的民事诉讼中相当部分实际上类似于我国的行政诉讼。
⑨参见赵艳花、耿宝建:《行政法纠纷中调解的出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谈》,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⑩最高法院行政庭等编:《中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11)参见赵艳花、耿宝建:《行政法纠纷中调解的出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谈》,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2)最高法院行政庭等编:《中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13)Bert Niemeijer and Machteld Pel(2003):Court-Based Mediation in the Netherlands:Research,Evaluation and Future,p.11.
(14)参见赵艳花、耿宝建:《行政法纠纷中调解的出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谈》,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5)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可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行政诉讼协调问题研究》,2006年度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2007年3月。
(16)反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亦然存在。
(17)《2005年中国法律年鉴》(中文版):中国法律年鉴社2005年版,第159页。
(18)所谓选择性司法,是指法院在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的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则之外的因素,来作出是否受理,如何裁判和怎样执行的决定。很多案件是经由选择性司法被过滤掉了的,以至于完全没有进入司法的流程。选择性司法由于其依据规范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对于法院行为完全无法预期,从而可能形成比没有法律还要糟糕的结局。选择性司法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可能会以司法的名义和权力站在一起,从而彻底消解民众对于法治的信心。参见汪庆华:《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主义的司法》,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
(19)参见Tijdschrift Conflicthantering Special Issue 2006,p.5。
(20)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开展庭前调解,便民利民为民》,载陈明主编:《立案审判实务与创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标签:行政诉讼法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法院调解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法官职业道德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司法调解论文; 行政法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