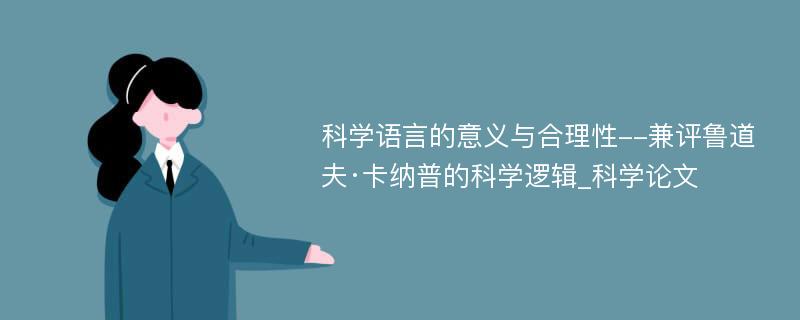
科学语言的意义与科学合理性——卡尔纳普科学逻辑再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卡尔论文,合理性论文,逻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D0
卡尔纳普与石里克一样,把科学知识看成语言系统。石里克说:“逻辑的就是纯粹形式的,……弄清纯粹形式的本质,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这种陈述表达着其中所认识到的实况,而这是可以随便哪种方式、通过随便哪种语言、应用随便哪种任意制定的记号系统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注: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7、8页。)。由于科学知识是陈述系统,就可分析它的逻辑形式,因而可对它进行“合理重建”,在此基础上分析它的合理性。
一、陈述的意义与科学合理性
卡尔纳普把科学方法论同科学陈述的有意义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与形而上学陈述不同,科学陈述是有意义的。他首先把“有意义的”的陈述分为三类:第一类陈述,其真实性是由于它们的形式(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同语反复”),关于实在,它们什么也没有说。逻辑和数学的公式属于这一类。它们本身不是事实的陈述,只用来使这种陈述变换形式。第二类陈述是这些陈述的否定(矛盾),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第三类陈述即所谓“经验陈述”,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要说明经验科学的合理性,就尤其要给出“经验陈述”有意义的标准。对这一问题,他先后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早期的卡尔纳普认为,一个陈述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我们能提出这个陈述的证实方法。设"a"是任意的语词,"s(a)"为按语法规则建立的包含"a"的一个最简单的句子,则"a"有意义(即语词意义)的充要条件可用下面几个表述提示出来,它们说的是同一回事(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8页。):
1.已知a的经验标准。
2.已知规定了"s(a)"可以从一些什么记录句子推出来。
3."s(a)"的真值条件确定了。
4.已知"s(a)"的证实方法。
更明确地说,通过定义把一些语词(谓词)还原为另一些语词即那些不能进一步定义的语词,而这些语词是直接标示“可观察的”事物或性质的词。因此,这些词必须以经验的东西为根据。“这样,就把语言中的每一个词归结为另外一些词,最后归结为发现在所谓‘观察句子’或者‘记录句子’里的词。词就是通过这种归结获得它的意义的”(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6页。)。因此科学理论中的每一个词都通过定义与基本谓词相连。而定义的特征是: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内涵以及外延是相等的。科学语言中有意义的陈述是按一定的句法规则由有意义的词组成。“证实”是最后的:能够最终确定某个句子的真假。演绎方法在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可以使理论中处于顶层的陈述推导出可与记录句子对照的陈述来;另一方面又可根据记录句子对导出的被对照陈述的证实或证伪,依逻辑推论对被定义的陈述作出选择。
但卡尔纳普很快就发现,这种模式将导致现有科学知识都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结论。理由很简单,科学中表现为全称语句的规律,即使它的每个“单一例子被认为是可证实的,这个规律所谈到的数目——例如空一时点是无穷的,所以决不能够被我们的永远是有限数量的观察所穷尽”(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75页。)。对于单称陈述,由于它可做的检验性观察是无穷尽的,因此也是不可最后证实的。所以,"s(a)"不可能从有限的记录句子推出来,演绎方法在第二方面的作用是不成立的。因此,卡尔纳普修改了综合陈述有意义的标准。他提出用对陈述的“确证(或译‘验证’)”来代替“证实”作为陈述有意义的标准。他把对陈述的确证的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对一个陈述的确证还原为对另一个(或一些)陈述的确证,这里依据逻辑推论概念,第二步引入可确证性概念。
一个陈述的确证还原为另一个陈述的确证,是指这样的情况:设K是陈述的有限类,所有由K类陈述合乎逻辑地推出的陈述,其确证可还原为K类陈述的确证。另外还有这种情况:从陈述的有限类K出发,所有借助全概括而由K类中(一些或全部)陈述得来的命题的确证,都可以直接地不完全地还原为对K的确证。
在精确地规定了逻辑结构的语言中,未曾定义的基本谓词是仅仅根据于可观察的东西的,一个把某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某一对象的陈述应被称作观察陈述。如果对一个陈述的确证可以还原为最后一类观察陈述的确证,那么这个陈述就是可确证的。意义标准可以表达为:一个经验(综合)陈述是经验上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属于那种按照精确的句法规则建立起来的,其全部陈述都是可以被确证的语言。
卡尔纳普始终把词和语句的“有意义性”看成是否接受这样的词或句子的前提。陈述的“有意义性”问题可以看成是陈述有无客观基础问题,科学以追求客观性为特征;应完全排除主观性的东西。卡尔纳普找到的客观基础就是“记录句子”或“观察陈述”,运用逻辑推论规则以及确证方法,会把所有的科学陈述、语词固定在客观的基础上,并在这些陈述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科学就是由此获得客观性的。
科学拥有达致客观性的方法,即逻辑方法,因此是合理的。卡尔纳普在此是把科学知识作为陈述系统来说明其客观性、合理性的,即说明单个陈述的可接受性。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可观察陈述以及可还原为观察陈述的陈述的增长,科学发展是连续的、累积的。
卡尔纳普的上述关于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的观点,是以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为前提的:我们选择某些特征作为给一类事物下定义的特征,作为我们对这类事物所使用的名词的“意义”。因此,意义只能是客观的,是关于事物或事物属性的。与心理的捏造不同,卡尔纳普认为,“意义问题同研究某一思想活动可以包括的心理过程是无关的”(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54页。)。此后那些给这类事物下定义的特征就用作决定任何东西是那一类事物,应当用那个名词来指称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就是说用作“标准”。如果任何东西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将对它不使用那个名词。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导致那些标准的改变,因为如果一个事物不符合那些标准,它便不是那一种事物;因此,它就不能够是使该标准失效的一个例子。具体来说,首先给定一个词(或句子)的应用标准(即“它的基本句型、真值条件、证实方法所结成的可推关系”),这标准的规定就使一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个词“意谓着”什么,“如果要这词取得一个确切的意义,就必须起码给定这个应用标准……,意义就暗含在这个标准里;所要做的事只不过是使这个意义显出来而已”(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7页。)。这是制定标准的过程。其次,给定标准以后,我们就只能用该标准判定某个事物(或属性)是否属于该词所指范围。意义是确定的,“精确的”,“所给定的也不能多于这应用标准”,一旦给定了某词的“意义”,就能判别某一事物是否可归于该词之下,它不能是可变的和可修改的。例如知道了“人”这一语词的意义是“两足无毛的动物”,就给提供了“人”这一语词的应用标准。如果有人要问“扒光了毛的鸡是否是人”的时候,有两种回答:它是“人”,这是坚持原有标准;或者退一步说:我们原先认识到的“‘人’的意义”不够精确,它不是“科学的”概念;精确的意义是不变的,科学语言中语词的“意义”是精确的。同时,卡尔纳普还要求,这种“意义”不能是心理的捏造,必须是指“可观察的”性质的。科学的客观性就在其所有陈述都是有“意义的”。合理性表现在所有的科学陈述演绎地与观察陈述或记录句子联系着,并可用确证方法在相互竞争的陈述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
但是,科学实际中却没有具有这样“意义”的语词和陈述。首先,汉森·库恩等人以令人信服的论据表明:任何一个语词(无论是观察名词还是理论名词)的意义与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是分不开的;每个语词的意义受构成它们的基础的范式或高层背景理论所制约,“观察中渗透着理论”,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观察”或“所与”。卡尔纳普无论通过“定义”还是“还原”都不可能使科学获得纯粹的客观性。
其次,科学实际中任何一名词的“意义”不可能是充分精确的以至于永远不变的。例如对于“原子”的认识,开始人们认为它是“不可分的”,曾几何时,“不可分性”成了原子的代名词。但后来发现原子是可分的,人们却并没有以“不可分性”为标准把“可分性”原子排除在科学外,而是改变“原子”的“意义”即应用标准。因此,在实际科学中,“意义”是可变的,可修改的。同时,人们还是认为原来“不可分性”的原子与“可分性的原子”都是在谈论同一种“原子”,只是认为原来没有认识到这种“可分性”而已。所以,“意义”的变化是有连续性的。卡尔纳普据“意义”不变性论点必然把科学描绘成静止的,没有变化的,已完成的。这是脱离科学实际发展的,不能说明科学的变化与进步。在实际的科学发展中,那种完全精确的,意义不变的语词以及科学陈述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给定了一个词的意义标准,就是把这个词精确地应用于这一可观察现象而不是别的对象上;科学的合理性表现在,可以用逻辑的方法(定义,还原等)使所有科学语词都成为有意义的。同时,也有逻辑方法可在相竞争的有意义的陈述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这是卡尔纳普早期科学合理性的主要观点。但是,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意义”——即纯粹客观的、精确的意义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实际发展表明没有不可修改的东西,科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种完成状态,永远处于变化中。科学方法论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这一变化是“合理的”。
早期的(卡尔纳普)意义标准,还有着具体的困难。卡尔纳普后来意识到并加以克服:
第一,用定义或对陈述的确证的可还原性不能说明现实科学中的所有名词与陈述是“有意义”的。
第二,科学一般是表现为理论而不是单个陈述。卡尔纳普发现,科学理论可以设想是用演绎地展开的公理化系统的形式陈述出来的。一个公理化理论,从它的原始词项和原始命题出发,依靠定义和演绎的纯粹形式原理就可以展开。然而,只有获得一种使它同我们的经验现象相关联的经验解释,才能构成一个科学理论。同时,卡尔纳普发现,经常一种解释并不是给予原始词项或原始命题(这是他早期“有意义标准”所要求的),倒反而只给予某一些能用原始词项定义的词项或某一些能从公设演绎出来的句子。不但如此,解释还可以只相当于局部的赋于意义。一切迹象表明:原有的名词或陈述的“有意义标准”必须被改变。
二、理论语言与科学合理性
后期的卡尔纳普注意到,原来的语词及陈述的有意义性标准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许多科学的理论名词不可还原为观察名词;因此,包含这些名词的陈述不能还原为观察陈述。例如物理学中的“长度”,“质量”等度量概念因为它们能把任何非负数的实数都看作是值,并且在逻辑上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可能性的可观察条件都表达出来。另外倾向性谓词,例如“可溶解的”,也是不能下定义的。同时,所谓确证的还原,事实上是以“A真那么B真”的形式(或者说用条件定义)把对陈述B的确证还原为对A的确证。但对于这种形式,如果A假则B就永远得不到确证。所以用还原法仍是行不通的。按照原来的标准,包含这些语词的陈述是不能接受的。另外,科学知识一般是理论的形式而不是单个陈述的集合。因此,卡尔纳普后来又修改了原来的陈述有意义标准。
在此之前,卡尔纳普是把科学语言看作统一的整体,所有陈述都服从统一的意义标准,科学的合理性表现为对单个陈述的合理接受上。到后期,他采取如下步骤克服面临的困难:一是放弃把所有名词定义为观察名词的要求,把标示不可观察的性质的名词称为“理论名词”。二是把理论看成是一个“演算系统”,而不是单个陈述的集合。具体来说,科学语言的语词现在被分为三大类:逻辑词(包括所有纯数学词),观察词或O—词,理论词或T—词(有时称之为“构造”)。相应地,科学语言的语句有三类:
1.逻辑语句,它不包含描述词。
2.观察语句或O—语句,它包含O—词。但无T—词。
3.理论语句或T—语句,它包含T—词,T—语句有两种类型:
a、混合语句,包含O—词和T—词。
b、纯理论语句,仅包含T—词。
这样,整个科学语言便被分为两个部分:观察语言L[,O]和理论语言L[,T](注:R.卡尔纳普著,张华夏译:《科学哲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54页。)。每部分包含整个逻辑(包括数学)。观察语言L[,O]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是“直接标示可观察性质的,是得到完全解释的”,其意义是客观的,精确的,因而是可直接接受的。理论T是理论语言中纯理论语句表述的公设的合取。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理论T在何种情况下被接受才是合理的?
首先须找到一种途径,使理论T能够与观察语言相关。因为理论T中不包含观察名词,且又不能用定义或还原的办法归结到观察语句,按原来“有意义”的标准,它无客观性,对其接受也就无合理性可言,是应被排除的。卡尔纳普找到理论T与观察相连的规则即C规则(对应规则),它是包含O—词与T—词的混合语句。对应规则“通过例如使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上的推导成为可能的办法,把L[,O](观察语言)和L[,T](即理论语言)的某些句子是联系起来”(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48页。)。理论语句借助逻辑演绎规则和对应规则与L[,O]的句子相联系而“间接地”得到“部分解释”。由此卡尔纳普给予理论名词的有意义标准即:一个理论名词M相对于一个给定理论T(包括T—公设或者C—规则或兼而有之)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有一个含有M的语句S[,m],由S[,m]和T的合取便把一个不能单独由T推出的观察语句S[,O]推演出来,简言之,一个理论名词在一个给定的理论中是有意义的,必须是在那一个理论中它的使用对可观察事件的预测方面是有关系的;一个理论句子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合乎句法规则并且它的一切理论名词是有意义的。
这样,科学结构的基础是描述事实的观察陈述的集合L[,O],这个经验基础不属于科学理论系统的内部,却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经验内容。L[,T]及T,对应规则,逻辑演绎规则一起,能够演绎地得出L[,O]中的句子,这一点使L[,T]及T获得经验解释并能做出预测。所有并且只有能够由某一科学理论演绎地推导出来的观察陈述,才是这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根据归纳逻辑规则,可计算出假说的确证度。科学总是朝着提高其确证度即它的逻辑概率的目标前进。观察和逻辑一起就构成了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基础。
卡尔纳普说:
首先,在C—规则被给定之前,L[,T]及公设T和演绎规则是一种未经解释的演算。……我们在构造这演算时是自由的;并不缺乏明晰性,只要那演算的规则是明白地给定的。然后加上了C—规则。其实它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以允许L[,O]的某些句子从L[,T]某些句子推导出来,或倒过来。它们间接地有助于从L[,O]中给定的前提,例如由观察所得结果的报告,推出L[,O]的结论,例如对所观察事件的预测,或有助于在L[,O]中给定的前提的基础上来确定L[,O]中一个结论的概率。既然前提和结论两者属于满足狭隘要求的L[,O],那么就涉及推导程序的结果的有意义性这点来说,就没有理由来反对应用C—规则和应用L[,T](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47~148页。)。
在对应规则给定以前,L[,T](理论语言)及公设T和演绎规则一起构成了一个未经解释的演算,只有理论名词出现在该演算中或者说理论名词出现在该演算公式的变项的论域中,但是它们是没有认识意义的,而是“给人一种心理学上的帮助,使读者把这些表示和一些有用的联想和意象结合起来,而不应把它看作明确指定了L[,T]的部分解释”(注:《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147页。)。因此,这时的理论名词所起的作用与形式语言中的符号一样,是没有内容的;它与公设T所起的作用唯一地使这一演算成为可能。理论公设T也就成了没有事实内容的逻辑公理。事实上卡尔纳普把理论“重建”成了形式逻辑。支持这一论点的另一个证据是:我们不能在该演算中找到综合陈述(因为综合陈述是依赖于事实证据的)。对应规则类似于一阶逻辑中的解释规则:它把理论名词与观察名词连接起来,配给演算的表示式以经验内容的语句集,其功用与解释规则给逻辑符号指定常词一样。因此具有由于语言规定而成为真语句的元语言地位。理论T的客观性、合理性,可接受性就在于:它是经验内容(观察语言)的逻辑形式。或者说是“计算”(说明或预测)L[,O]中的句子的逻辑工具。
对这种模式,我们首先可以提出如下批评:前提是真的,那么所得结论一定是真的,如果结论是错的,那一定是前提为假。但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演算却从真的前提(L[,O]中的句子)可能得出假的结论:结论的真假不是通过检查是否恰当地运用了逻辑推演规则而确定,而是通过观察检验来确定,检验的结果有可能发现这一预测是假的。理论语言的演算虽遵循演绎规则,但却能得到超出前提内容的结论,做出对将来的预测。显然,在现实科学理论中,陈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逻辑关系,而是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亨普尔说:“在任一种情况下,形式化理论就被看做实际上仅仅涉及使公设真的这样一些种类的事物和关系,这种分析对公理化的纯数学理论也许有点道理,——希尔伯脱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化是采用这种分析的——但主张经验科学的一个公理化理论的原始名词必须被了解为表示这样的事物和性质,即公设并且定理对于它们是真的,就根本不合理了;因为按照这种分析,公理化理论的真理性就会先天地有了保证,而没有进行经验研究的任何需要了”(注:转引自江天骥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这种模式与科学发展实际是不相干的。卡尔纳普依其把“意义”作为“应用标准”,把“应用标准”看成固定的、不变的形式,把观察名词的意义(形式)看作是“标示可观察属性和关系”。因此,观察语言是“得到完全解释的”,把理论名词的意义(形式)看作“标示不可观察事件、事件的不可观察属性的”,造成了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的截然地二分,把观察看作理论的语义基础(经验内容),把理论看成“演算”,看作已完成的科学的形式,固定不变地把科学的内容与其形式分离开来,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实际。在实际中科学的形式(理论)是不可能与内容(经验)截然区分开来的。首先,正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观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其中渗透着理论,把“观察语言”看作是科学理论唯一的客观的语义基础是不成立的。其次,在实际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截然二分是行不通的。如普特兰所指出的:仅仅使用观察名词来给理论名词以意义,除了特殊的例子外,看来是不可能的,理论中也使用观察名词,观察陈述可以含理论名词。如奎因所指出的,不可能把逻辑上真的陈述与事实上真的陈述截然区分开来。最后,卡尔纳普要求对“观察语言”(即“经验内容”)的形式化,认为观察语言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其中的语词和陈述的“意义”是固定的、不变的,这种看法也是脱离实际的。观察语言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