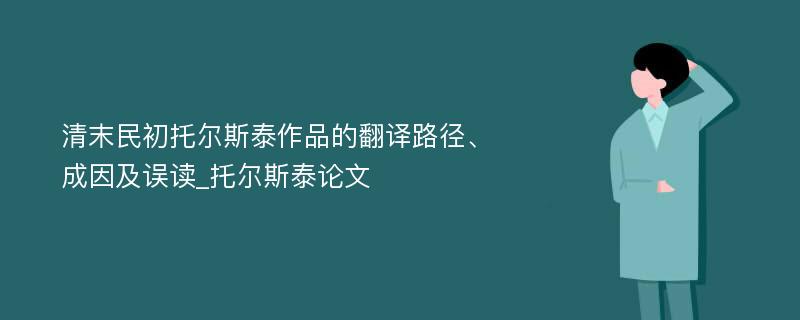
晚清民初时期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路径、原因及其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民初论文,晚清论文,误读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以“五四运动”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为分水岭,晚清民初只是我国大举接受俄国文学的“热身”而已。这个时期我国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大都缺乏系统性,对单个作家进行集中和详尽研究的系列文章更加少见。然而,托尔斯泰则是其中的特例,当时我国对其作品的翻译规模及其专题性研究文章的数量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俄国作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五四前我国研究者共撰写了11篇介绍俄国作家的专题文章,其中有10篇是研究和介绍托尔斯泰的。在我国1919年以前翻译出版的65种俄国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占33种(结集出版或重译作品除外),普希金2种,莱蒙托夫1种,屠格涅夫14种,契诃夫的短篇小说8种,高尔基4种,克雷洛夫3种。以上统计数据表明,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得到了译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拉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火车头”。
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之所以在中国译介俄国文学的发轫期就受到我国学人的高度关注,这与其传奇人生及作品中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容密不可分。此外,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受当时研究条件、译介者学识及其对待俄国文学的态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学者在“热情”译介托尔斯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误读。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既能帮助我们厘清中国译介托尔斯泰作品的背景、路径及其原因,也可以让我们返观晚清民初时期中国学人对俄国文学的期待视野,探讨某些误读的由来。
19世纪末,受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中国有识之士从“学西洋之长技”转向引入西方“政事之书”,希冀从中找到医治中国社会顽疾的良药,俄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开始进入中国。
托尔斯泰的名字在中国首次被提及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上海广学会的《俄国政俗通考》对他进行了介绍,称其“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转引自陈建华 39)。1903年,女作家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称托尔斯泰“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其“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①1904年,福州《福建日日新闻》刊登了寒泉子的文章“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该文主要介绍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并将他与我国的庄子、孔子、许行、伊尹等先哲进行了对比。
此外,王国维的“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1904)、“脱尔斯泰传”(1907),鲁迅的“破恶声论”(1908),陈淑铭的“托尔斯泰百周年纪念”(1908),佚名分别于1911、1914和1919年发表的“俄大文豪托尔斯泰小传”、“托斯道氏之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与革命”,汝非的“托尔斯泰之逃亡”(1915),李大钊分别于1916和1917年发表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和“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太玄的“小学教师托尔斯泰”(1917),凌霜的“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著作”(1917),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得”(1918),顽石的“托尔斯泰之劳动生活”(1918),封斗的“纪念托尔斯泰”(1918),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1919),两极的“托尔斯泰之影”(1919)等都是晚清民国初期在研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
1906年,托尔斯泰的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由德国牧师叶道生和中国的麦梅生(润色)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译,载上海《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该书由香港礼贤会出版,在日本横滨印刷,在中国内地发行。这是托尔斯泰的作品第一次经由英伦来到中国。今天看来,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在中国的影响有限。不过,王炳堃为此书写的序言从中西小说对比的角度肯定了译介托尔斯泰作品的意义。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近日新学家,所以有改良小说之议也。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不啻汗牛充栋。然所译者多英美小说,鲜译俄文”;其实俄国“亦有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读所序之书“觉襟怀顿拓,逸趣横生,诚引人入胜之书。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转引自陈建华 47)。
如果说《托氏宗教小说》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名著的话,一年后,即190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君武从德文转译的《心狱》(《复活》节译)、朱东润所译的《骠骑父子》(《哥萨克》)、林纾试译的《现身说法》(《幼年》等),包括热质在1911年所译《蛾眉之雄》(又名《柔发野外传》)等却都是从托尔斯泰的名作翻译过来的译本,且译著的翻译质量较高。1914年,马君武《心狱》(《复活》第一部)的重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评论家认为,该译本“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就当时的翻译水平来讲,《心狱》是值得肯定的一部译作”(郭延礼 219)。马君武既通外语又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修养,他能自觉地选择《复活》进行翻译,说明当时的翻译者已经具备较高的名著识别能力。这部译作在读者中得到好评,为中国人了解《复活》及托尔斯泰提供了新的参照物。
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托尔斯泰作品翻译方面,林纾也是很有成就的一位。在林纾翻译的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作品所占的比重不大,仅居第四位。不过,他的俄文译作几乎全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共有7部,其中在五四前翻译的就有4部。如果以单个作家的译作来算的话,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林纾所翻译的外国作家中居第一位(莎士比亚6部、小仲马6部、狄更斯5部,司各特3部)。虽然林纾所译托氏作品主要借助陈家麟从英文翻译过来,但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②,得到了刘半农、茅盾、郑振铎和钱钟书等人的高度评价。
1917年《娜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稍后《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刁冰伯爵”(即“两个骠骑兵”)、收录“波子西佛杀妻”(即“克莱采奏鸣曲”)和“玛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的《恨缕情丝》,以及《克里米亚血战录》(即《萨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名作相继被翻译。可以说,在五四之前,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托尔斯泰的大部分作品在中国都有了译本,其中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美华浸会印书局和公民书局等知名出版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能得以如此大规模、系统地翻译和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决定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托尔斯泰一向被认为是世界文坛的“巨人”。亨利·詹姆斯称托尔斯泰为“大象”,他拉着“大篷车”,而车上载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转引自朱宪生 9)。列宁对他和他的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182)。可以说,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价值方面来看,托尔斯泰的作品应该是中国读者了解俄国及其文化的重要载体。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也受到我国文化精英的关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诸如李大钊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俄国文学的特质,即“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③鲁迅甚至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④此外,托尔斯泰对我国孔子、老子、庄子等先哲的学说比较感兴趣,其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张建华在分析中国古典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时写道,“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儒家学说不仅使列夫·托尔斯泰认识了中国文化,上述学说甚至成为他在晚年批判俄国社会黑暗势力、专制制度统治以及东正教会的工具,成为他所提出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思想基础”(145)。因此,托尔斯泰所宣扬的“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博爱”等思想更容易引起我国读者和研究者的共鸣。虽然晚清民初时期某些研究者在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哲人进行横向比较时得出的某些研究结论有待商榷,但它们却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中国读者与托尔斯泰的心理距离,为大众认同其作品并引发好感创造了条件。
其次,这与当时中国接受俄国文学的大背景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维新人士的共识,一些具有“政事之书”性质的西方文学作品搭乘科技书籍的“便车”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而且,他还自称“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并力举翻译外国特别是俄国政治小说用来改良群治。正如智量先生在总结当时的俄国文学译介状况时所说:“俄国文学翻译发轫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是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外来文化进行自觉地、集体地同时又是有选择地认同、接受和吸收活动,它没有恒定的翻译标准和一成不变的翻译原则,在它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需求”(336)。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经历了两千多年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对异族人民的求变愿望特别容易产生共鸣,而对探索改善自己国家的途径又极为关心,因此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热爱人民、追求真善美的大师,自然很快就赢得普遍的热爱”(草婴 7)。
再次,中国大量译介托尔斯泰的作品与其在欧洲的广泛影响有关。我们发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并非通过日语译本转译,而主要借助英语、法语、德语译本进行翻译,这其中除了当时的中国译者关注的最多的是欧美文学这一原因之外,也与托尔斯泰在欧洲的美誉度有很大的关系。托尔斯泰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屠格涅夫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屠格涅夫旅居欧洲期间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让欧洲人领会到俄国文学的魅力,还大力向欧洲读者翻译、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朱宪生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出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时,更是掀起了阵阵‘风暴’,托氏的名声从此便蒸蒸日上,很快被视为欧洲文学的泰斗”(9)。因此,中国学人在译介欧美文学时得以接触到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而将它们翻译介绍到国内。
最后,中国文化精英们对托尔斯泰不遗余力的推崇提升了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影响力。五四运动前,既有茅盾、鲁迅、王国维、太玄、蒋梦麟、陈复光等文化名人高度肯定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也有诸如马君武、林纾等翻译大家译介过他的作品。我们认为,在大力倡导欧洲政治小说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普通读者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还十分陌生的情况下,上述“专业读者”(即社会精英)的译介及其推崇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比如,茅盾在1919年4月撰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认为,俄国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里“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俄国文学“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为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群峰也”;“谓近代文人得荷马之真趣者,惟托尔斯泰,其谁曰不然”(转引自陈建华 63)。对托尔斯泰如此高的评价,无疑会对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热”的形成,对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懂俄语的翻译人才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且那时对俄国作品的翻译大都从英、日、法、德等文字转译,转译本身就为译者理解、阐释原作的意义带来了困难。而且,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者过分追求译作的“中国化”,盲目将译介对象与中国文化“联姻”的做法也很常见。特别是因中国当时社会斗争的需要,我国研究者在介绍俄国文学时,赋予其过多的社会和政治使命。受以上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当时的译介者对俄国文学的误读也在所难免。
寒泉子在对托尔斯泰“抛弃教权教会教仪,排黜骄奢虚伪残酷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文明”,走上“衣驼毛,束皮带,食蝗虫野蜜”之路进行评述时,引用了《庄子·胠箧》中的“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这一段话来解释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的心理动机,认为“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⑤事实上,老子认为人们只要抛弃现有文明,社会就进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境地。而托尔斯泰放弃土地所有权,放弃家产和版税,并身体力行,布衣素食,从事体力劳动等行为有鄙视贵族生活方式的诉求,但他更多的是求得良心上的自慰,是其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具体体现。从宗教层面来看,托尔斯泰鄙视奢侈糜烂的地主生活,是希望按照上帝主张的方式去生活。其倡导的是宗教意义上的有序。庄子则是抨击“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强盗逻辑,同时也批判了法律的局限性,其根本思想是对儒家圣人治国主张的否定,是要回到原始文明状态,其倡导的是一种原始性的无序。显然,寒泉子不仅混淆了托尔斯泰“回归上帝的自然”与庄子“回归原始的自然”两种思想的本质区别,也没有细察它们的出发点与归宿。
寒泉子在论及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中的“实行宗旨”时,再次对托尔斯泰躬行践履式的平民化之举进行了拔高,称之为“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而亦不失为世界之一伟人也”;其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伊尹的水准,“今世之人,非托尔斯泰其谁当此”。紧接着,作者在论及托尔斯泰宗教中的社会宗旨时指出,托尔斯泰“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代期之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行之席而入庄周之室矣”。⑥我们认为,托尔斯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平民化行事方式和淳古粗朴的社会宗旨,而在于其高超的艺术创作手法及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晚年的托尔斯泰的确在精神探索中有了觉悟之机,梦想摆脱世俗的“共同世界”,但他“又在这个‘共同的世界’卖劲地活着”,其平民化只是“通过放弃问题和回避任务,去战胜生活的谎言”(弗洛罗夫斯基 474)。从这一层面来说,托尔斯泰此举远未达到伊尹和许行的道德水准。此外,托尔斯泰藐视地主阶级的特权和谴责寄生生活,主要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按上帝的意旨生活。因为在他看来,“‘按照上帝的意旨生活’,这才是他的精神家园,才是他的理想的‘天国’”(任子峰 422)。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托尔斯泰确实追求精神生活,但是,他的追求被他强烈的唯理论思想引入歧途,并且夭折了”(弗洛罗夫斯基 470)。因此,从行为的结果层面来看,托尔斯泰与伊尹、许行的高尚情操及其精神水准相差甚远。
又如,1904年,王国维翻译了“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一文。这篇文章本身强调的是,不要迷信科学,因为科学并不能增进人生之幸福。王国维在译文前附了一则短评,介绍了原作者写作此文的宗旨:“盖伯爵欲令世人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⑦虽然王国维在这里并没有评说原作的“是非”,但其倾向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托尔斯泰虽重视道德完善,但并不排斥科学,晚年时他还专心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甚至还说过“科学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名言。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全盘接受“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原文作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典型的“误读性接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民初时期中国译者在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时,不太注重尽可能地保存和再现原作的风格和异国情调,在翻译人名与书名方面过分追求政论色彩。例如,在1907年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氏宗教小说》中,绝大部分小说名字被故意改动:“主与仆”被译成“主奴论”,“蜡烛”被译成“以善胜恶论”,“二老人”被译成“二老者论”,“人依何而生”被译成“人所凭生论”,“鸡蛋大的谷子”被译成“论蛋大之麦”,“教子”被译成“善担保论”等等。此外,译者随意在译本中塞进自己的评论,有意对原著的内容进行删减、改写,随意地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改成第三人称,将作品的章目改成章回体等等,都是当时通行且被普遍接受的翻译方法。上述做法导致研究者无法准确理解原作而出现了误读。类似这一类低层次的误读,我们必须及时加以纠正。
晚清民初我国对托尔斯泰的译介是中国接受俄国文学初期的特例,这为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开了个好头,为托尔斯泰作品在五四运动后大量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译介者在解读托尔斯泰方面出现了某些误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误读不仅为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我们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俄国文学的心理动机和期待视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注释:
①参见罗选民主编:《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236。
②郑振铎语。参见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的翻译》,钱钟书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58。
③参见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李大钊文集》第2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24-231。
④参见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72-479。
⑤⑥参见闽中寒泉子:“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陈建华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3,6-7。
⑦参见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16。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文学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战争与和平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复活论文; 王国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