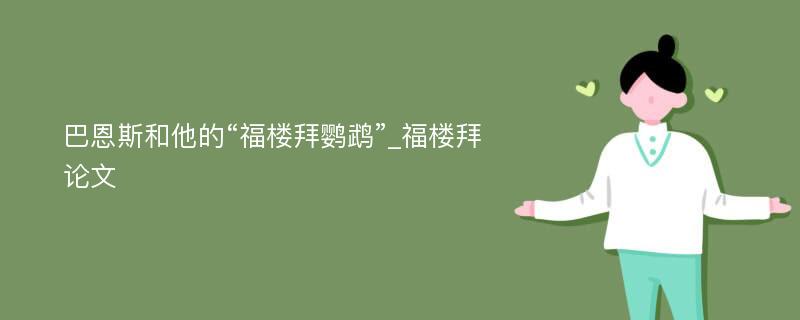
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楼拜论文,鹦鹉论文,巴恩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的英国文坛上活跃着一批新人。他们把“徘徊于十字路口”(大卫·洛奇语)的英国小说在非小说化的道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就是这批新人之一。他对英国小说的非小说化所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福楼拜的鹦鹉》都是一部新型作品。它不仅是一部有关福楼拜生平的准传记,而且包含有关福楼拜作品的大量批评文字;不仅有反映福楼拜一生不同侧面的风格迥异的三个“大事记”,而且有从福楼拜的角度讲述的动物寓言;不仅有以福楼拜为题的大学本科生考试试卷,而且有站在今人立场上对福楼拜时代所作的种种评论。有了这么多的创新,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成份自然只能占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了;《福楼拜的鹦鹉》引人注目,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
《福楼拜的鹦鹉》第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显然在于它手法上的别出心裁。这一点,除了它那主题性的而非小打小闹的“互文性”以外,除了以唯美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先驱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生平、他的几部名著、他的艺术观念和社会政治立场为作品主干以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读者可能发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部“小说”的准小说性或某种程度的非故事性。没有故事的小说意味着非小说,甚至不是小说(这里应当不涉及法国式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传统中那种以故事情节的淡化、连篇累牍的场景和景物描写,以及摄影般详尽的人物外貌和心理描写来制造的非故事性印象)。《福楼拜的鹦鹉》大概应算作不是小说的“小说”。它总共有15章,其中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篇幅被用来追述和评论福楼拜的一生、他与母亲、妹妹和几个女友的关系、他与几个男友的关系、他的艺术观念、他的社会政治立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看作一部颇具真实性的福楼拜传记。其余的篇幅被用来陈述“作者”—叙述者杰弗里·布雷斯韦特——的艺术信念和批评理论以及他寻觅“福楼拜的鹦鹉”的过程和对自己与不忠的妻子关系的思考。后两方面代表了《福楼拜的鹦鹉》仅存的一点“正统”意义上的故事性。或许正是由于还保留着这么一小点故事性,《福楼拜的鹦鹉》终究还能被称为“小说”。不过无论怎么讲,巴恩斯在小说的非故事化和准小说化道路上,比60年代的先贤们前进了一步。
这部小说的第二个特点似乎更具有技术性。这一特点不仅在于巴恩斯所使用的叙述视角的变动性,也在于这种视角的不明确性。他在这部作品中并非只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在有关福楼拜生平的三个版本的“年谱”中,他在最后一个版本里使用了福楼拜本人的视角,虽然只是摘录福楼拜的某些“日记”而已。当然也可能是他模仿福楼拜的口气杜撰了一些他的“日记”,但这需用一番考据的功夫加以证实。在“露易丝·科勒的说法”一章里,他又以福楼拜的情人、著名诗人露易丝·科勒的视角来讲福楼拜故事(变换视角的手法在巴恩斯的另一部小说《十章半的世界史》中的发挥可能过了头,已多少沦为一种为技巧而技巧的小把戏,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原创”,或“原创”与否至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变换视角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巴恩斯笔下的布雷斯韦特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等同于福楼拜的立场和态度这么一种倾向,他有时会批评福楼拜,有时又会显出一副与福楼拜若即若离的样子,有时还会摆出客观转述、不对转述内容负责的姿态。不用说,巴恩斯与布雷特韦特是有距离的,再加布雷特与福楼拜的明显距离,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这别出一格的三角关系自然为“解码”巴恩斯的新型小说增添了不小的麻烦。
论者觉察到的第三个特点与第二个特点密切相关。它在于这部混合文类的准小说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福楼拜的生平及文学理论和实践的评论。对这种半真半假的准文学评论(以及文学传记、文学理论)加以解读和评论有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是解读的解读,是评论的评论,是解连环套、套中套。当然,这样的麻烦从根本上说源于所谓“小说之死”,或更准确地讲,源于小说中叙述性成分的消亡、小说中的“故事之死”。故事既然已“死”,用文学传记和文学评论来填补身后虚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有意识标新立异?在这个崇尚“原创性”的时代,《福楼拜的鹦鹉》的手法所意味着的,恐怕只能是其故事性尚未“死”定的英国小说朝“小说之死”的末世景观挪近了一步。英国小说经历了激越、震荡的60年代,经历了张扬和实践“叙事已死”的极端者B.S.约翰逊时代[①],在“十字路口”犹豫了,徘徊了,但还是前进了。及至巴恩斯,它似乎又遇到了一个大“克星”。不过,他毕竟有比约翰逊聪明得多的中庸之道,虽然明显地在玩技巧,却并未使技巧压倒一切,虽然没有讲出一个正而八经的故事,但仍然在众多“非故事”因素中插进了一些故事性。
当然,巴恩斯的聪明更在于他自始至终都使《福楼拜的鹦鹉》这部似死未死、死而不僵的“小说”充满了救命的机智和诙谐。没有这种机智和诙谐,他这部作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它在英美文坛上可能也不会像目前这样大紫大红。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着巴恩斯式的机智和诙谐所树立的榜样,英国小说创作的前景将大为改观,那就是向法国型实验小说更加靠近,或进一步非小说化或非故事化。
二
《福楼拜的鹦鹉》的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摆出的那副不屑于显示哪怕一丁点社会关切的姿态(至于能否百分之百成功地排除社会关切,则另当别论),这自然与它总的唯美主义模样密切相关。
在这方面,巴恩斯又是以他极端崇拜的福楼拜为楷模的,至于福楼拜本人究竟愿意不愿意充当这一角色,那是另一回事。巴恩斯笔下的杰弗里·布雷斯韦特既然总是在引用福楼拜的名言,便自然不会忘记“不要带着寻求道德和社会药方的目的来写一本书”的主张,更不会忘记“我只是一只在美之伟大日光下晒太阳取暖的文学蜥蜴而已”,以及“真实、美、感觉和风格乃至高无上”的教导了。[②]其结果便是《福楼拜的鹦鹉》从书名到绝大部分内容的“互文性”;它的非故事性、准传记性;它的准文学理论、对文学评论的评论、视角的变换,以及在形式技巧与老老实实讲故事之间寻平衡、求中道的聪明做法。这一切都似乎非常有助于《福楼拜的鹦鹉》在英美文学批评界赢得近乎显学的地位。
但除了这些结果以外,还有另外的效果。譬如1846年福楼拜的妹妹卡罗琳死了,她丈夫自然痛不欲生,哥哥居斯塔夫冷眼旁观掘墓人将卡罗琳的棺材置入挖好的墓坑里,可是墓坑挖得太窄了一点,于是几个掘墓人对棺材又是推、又是搡、又是抖、又是敲,甚至还用铲子劈,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干脆一脚踏在那盒子上,恰好踏在卡罗琳的脸上,将它强行挤压到坟里”。[③]这显然是一副施虐—受虐的情景,只不过发生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历史喜欢重演,在福楼拜身上也不例外。1880年他本人死后,他和他的棺材的运气更不好。他也卡住了。这次棺材的宽度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它的长度。结果棺材既塞不下去,也拉不上来,几个掘墓人使尽全身解数也无能为力。几分钟后,吊唁者怏然而去,一代文豪被斜着塞挤在墓坑里。布雷斯韦特(拟或巴恩斯本人?)对此评论道,诺曼底人太小气,“厌恶多挖哪怕一小撮土”。[④]福楼拜和他妹妹的棺材的遭遇本身怎样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作者”—叙述者这种唯美主义的非道德腔调。是不是生活中充满了大意的讽刺、巧合和尴尬?福楼拜倡导作者应当做一个不动声色、超然在上地安排故事中事件的“上帝”,他因这样的艺术理论和实践出尽风头,但在死神面前也不过如此……甚至还被上帝小小捉弄一番?无论如何,福楼拜的妹妹和他本人棺材的不幸遭遇为巴恩斯“不是小说的小说”又赢了一分,为巴恩斯式的机智、幽默、“风格”及“感觉”又添了一个筹码。
巴恩斯的“风格和感觉”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对福楼拜与几个女友或情妇的关系兴致勃勃,着墨不可谓不多。除了为人熟知的福楼拜15岁时对比他大十几岁的已婚女士爱莉莎·施莱辛格的单相思以外,巴恩斯还着重讲述了福楼拜与露易丝·科勒的婚外恋情。[⑤]
但最好不要把科勒—福楼拜之恋过分浪漫化或抬得过高。这对20世纪中叶以后福楼拜所享有的巨大身后声誉未必是好事。在这位当时35岁的“美丽”女诗人所“征服”的一长串名人中,福楼拜只是一个姗姗来迟者,而且并非没有后继者。甚至科勒并“不需要居斯塔夫进入我的生活。”[⑥]巴恩斯是不是在告诉世纪末的读者,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性—婚实验”其实早在19世纪便在法国的文人圈子里实施过了?他是否在教导读者:婚姻是文学创造的敌人?他是否在指出,孕育出《包法利夫人》(1857)的福楼拜—科勒激情并非某种至纯至真的激情,而只是某种缺乏底气的伪激情?不过科勒半推半就地将福楼拜收编到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这一信息为《福楼拜的鹦鹉》又增添了一点非道德的“风格”和“感觉”,这一点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所谓“风格”和“感觉”的取得,显然用的是以私生活曝光把那位多种“主义”的神圣始祖加以非神圣化这样的手段。
巴恩斯自然也不会忘记对科勒与福楼拜母亲之间的微妙关系写上几笔;不会忘记点出福楼拜去埃及一趟,染上了梅毒,身体发福,从而引起母亲颇具醋意的怀疑。此外,巴恩斯—布雷斯韦特还近乎捕风捉影地拼凑出了另一幅艳情图,即福楼拜与他侄女的家庭教师朱丽叶·赫伯特的暖昧关系,但终因证据不足而作罢。这些只是福楼拜与女性的关系。巴恩斯对福楼拜与其男性朋友如杜康姆、阿尔弗里德·勒普瓦特万和路易·布耶等人的关系也着墨颇重,不过是以暗示为主,因为要把他们说成是同性恋,证据就更加稀少了。总而言之,在巴恩斯的笔下,福楼拜的私生活就好像福楼拜本人当年自称用手术刀无情解剖小说人物那样,被无情地解剖了。再加上有滋有味的细节,其结果就可想而知,那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世界级人物被几乎一丝不挂地呈现在公众眼前。这一切自然都成就了巴恩斯的新型“小说”。
三
不过,说巴恩斯全然不流露一丁点社会关怀似乎并不十分公平,因为毕竟他将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当做“小说”材料来使用了。他指出,福楼拜是“不相信进步”的,“尤其是不相信道德意义上的进步”,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而普法战争后的所谓“新时代”在福楼拜看来就“更加愚蠢”了,[⑦]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意义上的“进步”,都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进步,而资产阶级从来都是那么可鄙,那么猥琐,那么可气可恨。
这只是福楼拜对他的时代的看法。巴恩斯对他自己时代的看法似乎与福楼拜对他的时代的看法差不多。一百多年后巴恩斯笔下的布雷斯韦特携夫人来到了福楼拜的家乡,甚至进到一家药店为脚打了泡的夫人买了绷带。他觉察到药店主人对他夫人的脚表现出某种过分的热情,近乎恋物癖,简直就是非礼。同时他觉得,药店主人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跟《包法利夫人》里的药店主俄麦十分相似,因此得出了“俄麦精神仍大行其道”这一结论。那么什么是“俄麦精神”呢?那就是“进步、理性主义、科学、欺骗”,[⑧]或者说,就是资产阶级所崇尚和擅长的一切。布雷斯韦特因此想到,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包法利死后,有两个人守护她的尸体,一个是牧师布尔尼先,另一个是药剂师俄麦。牧师代表宗教正统,俄麦代表科学,爱玛·包法利则代表罪愆。这三种东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相互矛盾。不仅宗教正统观念和罪恶相抵牾,而且宗教与科学似乎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在《包法利夫人》的结尾处,布尔尼先和俄麦在就忏悔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时先后睡着了。在《福楼拜的鹦鹉》中,这两位守护尸体者不顾体面地“伏在尸体上”睡着了:“他们起初只是由于某种哲学错误而走到一起,但很快便在共同的鼾声中达到了深层次的统一。”[⑨]在这里,巴恩斯对福楼拜勾勒出的这一极富洞见的守灵场景的阐释是:宗教与科学一起保卫着罪恶,或者说,宗教与科学在罪恶面前勾结起来,与罪恶形成了某种可耻的三角关系。巴恩斯—布雷斯韦特显然在顺着福楼拜的思路发挥福楼拜的社会批判精神,在附和福楼拜,等同于福楼拜。那么这到底是在传达福楼拜的社会关切,还是在表现他自己的态度?权且算作两者都是吧。事实上,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里所表达的那种有限的社会批判精神,从来就是依傍在福楼拜的社会批判信息上的,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当然,如果将《福楼拜的鹦鹉》主题性的“互文性”加以考虑,则似乎巴恩斯—布雷斯韦特不得不这么做,因而大体上说就无可厚非了。
大约正是宗教与科学的那种“深层次统一”使“俄麦精神”或资产阶级的“臭德性”长存,甚至使它延展到俄麦的创造者福楼拜身上。福楼拜讥讽意味十足地塞进俄麦嘴里的话“我们应当同时代一起前进”被布雷斯韦特发挥成:俄麦“向着‘荣誉’勋章前进”(俄麦在《包法利夫人》里得过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福楼拜对此竭尽挖苦之能事);进而更被发挥成:福楼拜“这个头号反资产阶级者,这个刻毒仇恨政府者居然让政府把自己加封成‘荣誉勋位骑士’”。[⑩]布雷斯韦特因此用一种不褒不贬的口气宣布:“生活模仿了艺术”(11)。有充分理由相信,巴恩斯写《福楼拜的鹦鹉》前在福楼拜研究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因此福楼拜对俄麦的那种奚落终于在现实生活中返还到他自己头上这则轶事是可信的。于是,反资产阶级的文化英雄被非英雄化了,福楼拜头上的耀眼光环又被剥掉了一层。不仅福楼拜的私生活被强行挪用,强行曝光,而且就连他的社会政治态度也是难逃巴恩斯惠眼的。然而,福楼拜的尴尬并没有结束。
巴恩斯—布雷斯韦特在另一处还引用了福楼拜的另一句名言:“对资产阶级的仇视是一切德行的开端”,(12)紧接着马上披露:“但他死后却葬在鲁昂最富有的家族中间”(13)。这简直是在说:福楼拜这个“头号反资产阶级者 ”终究仍然是一个“头号资产阶级分子”。考虑到福楼拜去世时几乎已是一文不名,能葬在“最富有的家族”中间,显然是资产阶级政府给他的殊荣使然。不过,在法国,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时尚可谓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大革命以前。及至福楼拜,这种风气蔚然“积淀”成一个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的大传统了。但在法国这个非常重视文学、文人社会地位很高的国度,文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那里是相当受宠的。也就是说,文人们在资产阶级的国度里反对组成其读者群的资产阶级,只能是玩游戏。
这游戏在福楼拜之后仍然在“玩”着。福楼拜显然不是最后一个“头号反资产阶级者”。20世纪中叶的让—保罗·萨特无疑也是一名“头号反资产阶级者”。他“像一个身强力壮、急切万分的救生员,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捶他(福楼拜)的胸,对着他的嘴吹气;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想方设法使他醒过来,这样,就能让他坐在沙滩上,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如实告诉他。”(14)出于对反资产阶级的福楼拜的敬意,萨特写过一本研究福楼拜的书。这就是巴恩斯—布雷斯韦特所谓“捶胸吹气”使福楼拜活过来的根据吧。但巴恩斯想说的似乎也是,萨特的“捶胸吹气”是白费力了,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的福楼拜实际上不配当他的偶像。可是巴恩斯写《福楼拜的鹦鹉》又何尝不是“捶胸吹气”之举呢?他在反抗资产阶级方面能够做到比福楼拜和萨特更加彻底、更加不自相矛盾吗?作为一个其小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量颇大、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读者群的作家,他能成功地避免福楼拜所未能避免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命运吗?这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他做到了的,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加入那场由来已久的游戏,即资产阶级情调的文人英勇地反抗资产阶级,但终究逃脱不了被资产阶级收编的归宿;或者说,他试图把这种法国风味的游戏“风格”和“感觉”进一步移植到英国的文化氛围里。
当然,福楼拜的时代除了资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他们在向统治者要民主,甚至建立了巴黎公社。但在经巴恩斯—布雷斯韦特过滤了的福楼拜看来,“那整个民主梦不过是将无产阶级提升到资产阶级业已达到的愚蠢水平而已”。(15)福楼拜不光是讨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铁路出现后的第一代法国人,他还“痛恨”铁路,“痛恨它用进步的幻觉来讨好人们”:“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有何益?”,而“铁路只是让更多的人流动,使他们聚集在一起,愚蠢在一起”。那么用什么来抵制铁路,来反抗“工厂、药剂师和数学家”,来最终消解这铺天盖地的“愚蠢”呢?福楼拜的回答应当是不出乎意料的,那就是:艺术。因为“优越于一切的是艺术。一本诗集比铁路更可贵”。(16)对进步、铁路、资产阶级,乃至对无产阶级的仇恨导致了福楼拜那颇有名声的“仇恨人类”,(17)尽管他对具体的个人并非不怀有爱慕之心。其实,福楼拜所仇视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相联系的,还有无产阶级的崛起及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巴恩斯—布雷斯韦特对这些东西大体上也是不满的,而他不满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在于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大体上说,巴恩斯的文化政治立场是保守主义的。但他传达这种立场的方式既然是使用福楼拜这面透镜,读者得到的东西最多只是一种折射的印象。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取得福楼拜那种非道德模样的艺术效果,因此小心翼翼地在福楼拜的社会批判精神与他自己可能有的立场之间保持距离,排除可能显山露水的社会关怀,从而相当成功地保持了他那唯美主义的非道德模样。
四
最后必须讨论一下《福楼拜的鹦鹉》中的“鹦鹉”。所谓“福楼拜的鹦鹉”,指的是福楼拜写《淳朴的心》这一故事时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使用过的一只剥制的鹦鹉。《淳朴的心》的女主角全福出身卑贱,爱过一个举止粗野的未婚夫,后来当了仆人。她心地善良,一生任劳任怨,对女主人一家忠心耿耿,把感情寄托在女主人的孩子们、她的侄儿,以及一个臂膀上长有癌瘤的人身上。及至女主人去世,少爷小姐们当婚的婚,当嫁的嫁,她寄托感情的其他人也各奔东西,只得另寻精神寄托了。最后,她把她全部的爱倾注到一只有个可笑名字的鹦鹉“露露”身上。可是不久,它也死了。全福请人把“露露”剥制出来,当作宝物随身携带,甚至祷告时也将它放在自己面前。布雷斯韦特探求“圣杯”式地所企图找到的,就是“露露”的原型。在此过程中,他找到好几只据当地博物馆称是福楼拜用过的鹦鹉,甚至发现了几十只似乎具有同样悠久历史,而且种类和外貌与福楼拜的描写十分吻合的鹦鹉。布雷斯韦特最后醒悟到:要找到充当“露露”模特的那只鹦鹉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福楼拜的鹦鹉》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探寻、追问乃至最终觉悟的故事。它也包含了布雷斯韦特对自己与妻子关系的反省。在探究“露露”的下落和思考福楼拜的生活和艺术信念的过程中,布雷斯韦特逐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包法利夫人》里夏尔·包法利十分相似,他们两人的生活经历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吻合。布雷斯韦特觉得,既然自己性无能,作为作家也一事无成,因此就非常可能像夏尔·包法利那样,已在懵懵懂懂中被人戴了绿帽子(同夏尔·包法利相比,布雷斯韦特“进步”和“觉悟”的程度似乎高多了;前者在爱玛·包法利死后不久也郁郁寡欢地死去,但对妻子的不忠却至死也执迷不悟,最后一次迸发出强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即萌生出让她“穿上婚礼服和白色鞋子下葬,在她身边放上一个花环,她的头发应披在肩上”这一“浪漫念头”(18))。在焦虑和恐惧中,布雷斯韦特用纳伯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话,“通奸是超越平庸的最平庸的办法”(19)来安慰自己。他甚至不无自虐地自言自语,妻子是否知道纳伯科夫的这句话?当然,他妻子从来没有像爱玛·包法利那样替丈夫积下一大叠欠帐单这一类念头,这使布雷斯韦特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由于布雷斯韦特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那么不妨问这么一个问题:夏尔·包法利是不是布雷斯韦特自己生活经历的原因,或者说布雷斯韦特的可怜命运是不是夏尔·包法利这一不朽的文学形象的结果?在布雷斯韦特看来,生活和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生活可以是艺术的原因,也可以是艺术的结果。艺术可以模仿生活,生活也可以模仿艺术(在此不妨顺便问一问:是否仅仅是巴恩斯的艺术模仿了福楼拜的艺术?)。二者不仅互为因果,相互模仿,而且也是可以相互交叉、相互跨越的。甚至可以说,二者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在此需承认,实验主义的巴恩斯在消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与生活的二分法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二分法的消解归消解,可以肯定的一点则是,在巴恩斯心目中,人们永不可能像博物馆收藏鹦鹉那样彻底地把握生活和艺术的本质;这就像企图寻找充当“鹦鹉”模特的鹦鹉那样,终究是劳而无功的。
在此不难看出,《福楼拜的鹦鹉》在对所谓“福楼拜的鹦鹉”的性质的思考中,也包含了对所谓“生活的真实”的思考。既然文学以语言为媒介,那么这种思考也实际上就是对语言反映现实能力的思考。在这方面,巴恩斯—布雷斯韦特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两次引用了福楼拜的话:“语言就像一只有裂缝的壶,我们在它上面敲出曲子,让熊合着节拍跳舞,同时还老是指望感动天上的星辰。”(20)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福楼拜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就已用形象生动的话表达出来了。及至20世纪中叶以后,小说家们不仅不再相信语言与现实是对应和吻合的,他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是事物产生了词语,还是词语产生了事物”。(21)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既然已经不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后现代”的巴恩斯便只好求助于“福楼拜的鹦鹉”了。他求助于福楼拜的《淳朴的心》。在这个故事中,在全福死前的幻觉中,天堂的大门向她敞开着,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头上盘旋。在这里,鹦鹉代表圣灵,而按传统的说法,代表圣灵的应是鸽子。全福把自己的鹦鹉与圣灵联系起来的逻辑何在呢?回答是:“鹦鹉和圣灵能讲话,而鸽子却不能。”(22)一只剥制得十分粗糙、取了一个十分可笑名字的鹦鹉现在竟代表着神圣三位一体的“三分之一”,而福楼拜这样安排的用意“既不是讥讽,也不是感伤,更不是亵渎”。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23)
其实,这困难从根本上说产生于生活“真实”的难以把握,产生于文学作品和语言反映“真实”能力的有限性。20世纪中叶以来的“作者之死”、“小说在十字路口犹豫”,乃至“小说之死”这一切麻烦实际上都产生于人们对这一情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布雷斯韦特的思绪中,“露露”对于全福来说是“圣灵的一个怪诞而符合逻辑的变体,而对我来说,它却是作家声音的一个拍着翅膀、躲躲闪闪的象征”。(24) “作家的声音”就是文学形式和语言。巴恩斯想说的是,文学和语言反映现实的能力与鹦鹉学舌的能力差不多。这能力最多只能是“福楼拜的鹦鹉”,最多只达到了全福死前幻觉的水平,何况即便在这幻觉中,“露露”也仅代表了神圣三位一体的“三分之一”,即圣灵。也就是说,这种反映是不完整的。既然“真实”无法把握,那么巴恩斯的新型“小说”显然便师出有名了。
这种反映虽不完整,虽不可靠,却仍然在那种能指与所指的“后现代”合一中获得了某种本体论根据。这本体论根据不乏神圣意味(所谓“圣灵”是也)。在“后小说”时代,求新求异的“小说”家便是在这种貌似神圣的本体论根据上安身立命的。在巴恩斯看来,用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连贯一致的线性故事来反映现实的企图,最多不过是一种“福楼拜的鹦鹉”,不仅靠不住,而且从根本上不可把握、不可企及。小说家仍然能够做到的,只是用某种准故事的手法来讲“故事”,用某种准小说的形式来写“小说”,甚至走上一条探寻“福楼拜的鹦鹉”的道路,像萨特那样,“捶胸吹气”使福楼拜活过来,使俄麦、包法利夫妇、全福,乃至鹦鹉“露露”活过来,以便达到一种跨时空的大团圆,在这个大团圆中敷衍出一部不是小说的“小说”来。在使“福楼拜的鹦鹉”活过来的过程中,朱利安·巴恩斯给不死不活的英国小说又打了一剂强心针。他的强心针显然产生了一定的效力。不过这效力主要不是来自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故事性,而是来自《福楼拜的鹦鹉》主题性的互文性,形式与技巧的空前膨胀,以及连篇累牍的机智幽默。
注释:
① Malcolm Bradbury,The Modern British Novel,Penguin,1993,p.364.
② 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Reading,1985,p.33,p.134.
③ ④ ⑥ ⑦ ⑧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Flaubert's Parrot,p.72,pp.7273,p.137,p.85,p.64,p.68,p.185,p.185,p.185,p.86,p.85,p.100,p.128.
⑤ 露易丝·科勒在福楼拜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在西方国家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已是定论。恕笔者孤陋寡闻,我国80年代发表的有关福楼拜的文字材料中似乎找不到有关科勒的任何信息。
⑨ Flaubert's Parrot,p.85.在《包法利夫人》的英文版中,俄麦和布尔尼先是在尸体“旁边”睡着的。他们“面对面,挺着肚子,愁眉不展,一脸的浮肿和苦楚,在争论良久后,最终却在人类相同的弱点中联合起来。他们像身边的尸体那样一动不动,那尸体也像睡着了似的。”可是他们并没有“伏”在尸体上(over the body)睡觉。巴恩斯对这一场景显然作了发挥,但似乎并不过分,大体上符合《包法利夫人》总的精神。参见Gustave Flaubert,Madame Bovary,Bantam Classic Edition,1981,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Lowell Bair,p.88.
(18) (21) (22) (23) (24) Gustave Flaubert,Madame Bovary,p.284,p.88,p.17,p.17,pp.182-183.
(19) Flaubert's Parrot,p.91,p.164.
(20) Flaubert's Parrot,p.19,p.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