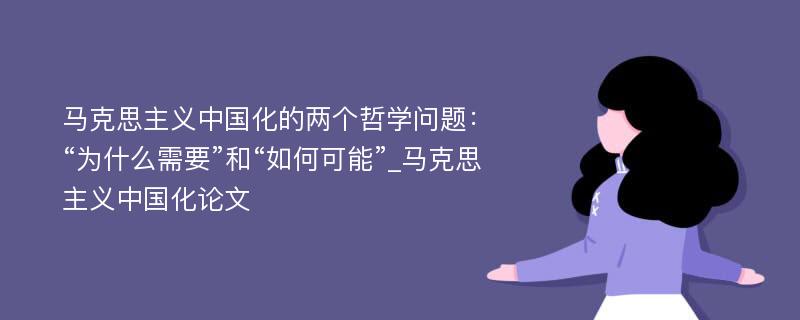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哲学追问——“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已经是一个勿需论证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视野追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然有追问的必要。这个追问就是:何以需要?何以可能?
一、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命题把两个事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从实践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生关系,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化”(改造)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实践的历史进程又表明,从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程”。解说这个“历程”,从理论上理解和深刻反思这个“历程”,就是我们的一种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
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需要解决两个前提性问题: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理论能否同东方的古老大国——中国及其具体环境相适应?2.即便以往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包括俄国)是真理,但它对于中国来说,肯定也是真理吗?
众所周知,理论是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如果脱离实践,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抽象命题,那么前面的第一个前提性问题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这个命题在每一个场合都需要实践的证明。没有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够超越“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原理。西方和俄国的实际当然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西方的近现代社会实际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便是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也无法完全照搬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来。这个普遍原理需要首先经过反复摸索,变成能够适应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理论。
只有在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第二个前提性问题才可能找到答案。
第二个前提性问题其实是认识论的问题:一种理论的真理性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时候,我们指的只是:以往的实践反复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指明一个方向。但是在每一个新的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的问题依然还会提出来,并要求我们给予回答。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不管它在欧洲、在俄国曾经怎样为那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或建设提供过指导,并且取得过怎样的胜利,它一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面对新的实际,就必然重新面对上面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具体国度,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而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凭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真理的信念而取消这个认识论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
总之,从理论是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的真理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历史的)这两个原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的需要。
二、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上面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何以需要”的问题。这里要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可能性首先表现在“结合”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
关于结合,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结合”不是机械的相加,这种“结合”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教条主义就是一种机械的结合。它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照搬过来,套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对原理不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这样的结合,当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说,光有结合,并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结合。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两件有着密切关联的事情,然而二者并非同一。有一个时候,由于某种政治原因,人们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后来,又重新恢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二者是完全同义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必须通过“结合”,但是光有“结合”——例如,机械的结合——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者不是完全同义,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是实现(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手段,而通过结合,在改造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目的。前面那种“结合”正因为无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的,所以“结合”(实际上是照搬、套用等等)只能是教条主义的。
再次,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总是在先的。因为结合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摸索、探求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在总体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具体地考察全部进程,我们必须承认,刚一开始,只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是人们通过反复的实践使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从而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在后的。它是成功结合的产物。这个摸索、探求的过程虽然是漫长的、艰苦的,但一旦成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一种贡献。
(二)“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来说,过程的全部要素中,核心或者实质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任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无从谈起。
结合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有差异或矛盾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作为旧世界改造者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格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改变本国、本民族的现状,如果这种理论指导是基于该民族的特点并结合了本国实际的,那么积极的结果就是:一方面使客观实际发生预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使原有理论(普遍真理)本身在内容上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化”为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真理,而是一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真理”。只有这种具体真理,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
在上述积极结果中,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后者,可以叫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二者都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过程:只有在漫长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摸索到如何按照中国特点来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理论中国化;只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化”中国。
根据结合的不同情况和问题,我们可以区分不同层次的结合。一种是浅层次的结合,即这种结合只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非本质方面的认同。比如说,把俄国人的“苏维埃”变为中国老百姓懂得的“人民政府”。另一种结合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本质方面的认同。为了达到对实际本质方面的认同,有许多途径和方法:
一是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比较中国实际与外国实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习惯做法加以变通,甚至可以是在形式上完全颠倒的结论。大家熟知的俄国人夺取政权走的是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而中国人则相反。两者都是对本国实际的本质的认同。
二是把实际看作利益差异的各种群体的矛盾统一体。结合能否达到对实际本质的认同,取决于对实际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冷静剖析。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的民主革命开始时期,做过中国革命的各阶级的分析,由此判定革命党依靠谁,联合谁,反对和打击谁。离开这些分析,就不可能有对实际的本质之认同。今天,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能否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问题上做到对中国实际的本质认同,同样需要这样的对各种利益群体的剖析。改革措施是首先顾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眼前和根本利益,还是照顾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总之,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都是发生在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实践之上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结合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但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实质和核心。
(三)“结合”的过程是通过“实事求是”解决矛盾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不是天然吻合的。这里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为了使二者有机结合,必须设法消除这些差异或矛盾,找到一条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道路——或者说,使二者有机结合的道路。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既存在着同一性(如果没有同一性,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和矛盾。
1.文化上的差异。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继承了19世纪之前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它不是专属于某个民族的文化产物。但是就其思想来源说,它主要发源于西欧。其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完全吸收和继承了19世纪西欧(英、法、德三国)的古典思想家和文化巨人的思想。因此马克思学说所体现的,主要是近现代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20世纪2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它只是作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尚未被中国化的一种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文化思想层面看,这种学说在长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实际面前,显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不首先克服存在于两种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2.价值观的区别。一种文化的核心是其文化价值观。作为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价值观属于近现代的观念,属于所谓“现代性”的范畴——虽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又是超越和批判根源于“资本”的现代性的。而旧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是前现代的。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反映着文化的时代性。就是说,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东方还处在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那些生活在旧中国环境里的先进的社会变革者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难免在思想深处存在着种种前现代的价值观的残余,这就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难度。
3.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一种经济-社会形态所允许的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未全部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一种比它更为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如果尚未具备它赖以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力——的时候,它一定会束缚、阻碍着现存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不可能长久存在。所以当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从来就没有把眼光注视到落后的东方(所谓通过19世纪初俄国的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只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例外)。然而,十月革命不但把政权交给了比西欧发达国家落后很多的俄国无产者,而且随后还把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东方的中国也卷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之中。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一度曾经获得过比较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也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也曾有过令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由于无视马克思所预期的生产力要求与现实中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大“落差”,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曾经一度忽视马克思学说中的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急于向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结合——例如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反之,当我们党积累了长期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只能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们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付出的代价就小得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变得异常的成功了。
4.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结合中出现的问题。当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有时候会要求反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是说,当从比较发达阶段引出的现存结论被应用到不发达的阶段时,理论(现存结论)与实际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同一个原理,应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结论不能照搬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度。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用新的结论取代曾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例如,在西方,革命夺取政权都是走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在旧中国,却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俄国,城市中心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的产物,在旧中国,反城市中心论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
总之,结合就是解决矛盾,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来求得结合。也就是说,成功的结合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现存的理论结论出发。当现存结论与中国实际发生巨大矛盾时,研究客观实际,根据现存的实际的客观规律去创造新的结论,从而获得理论与实际的新的“结合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成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