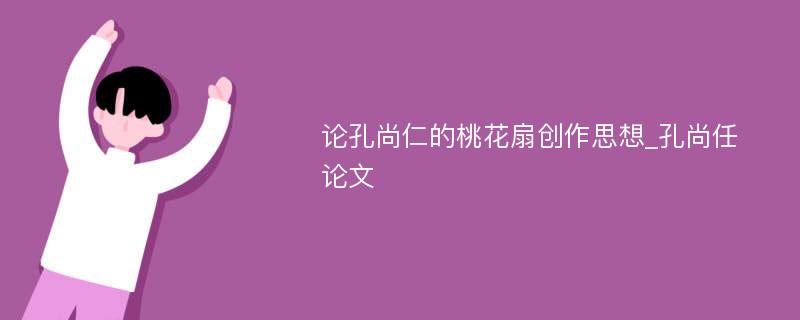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桃花扇论文,论孔尚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园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离合之情 兴亡之感 吊明 颂圣 民族意识
历史悲剧《桃花扇》是孔尚任精心结撰的戏曲名作,它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女李香君的悲欢故事为题材,结合政治风云和时代战乱来描绘,总结了南明弘光王朝必然败亡的历史教训,寓意深刻。关于《桃花扇》的主旨,作者在开场《先声》中说明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但在探讨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时,当代评论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尚任从爱国立场出发,剧中带有反清的民族情绪;另一种意见认为,孔尚任原是康熙皇帝提拔上来的,他创作的《桃花扇》是为满清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两种意见或誉或毁,各执一端;实情如何,有待商榷。
根据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自述,此剧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凡三易稿而书成”。我认为就从这三个阶段来考察孔尚任的思想面貌,必将有助于评析剧作的创意。
一
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号东塘,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他早年习攻科举之业,熟读四书五经,曾赴济南应试,未能中举。乃隐居石门山,结庐读书。石门山古称云山,所以又自号“云亭山人”。但他没有断绝功名之念,三十四岁那年,还用捐资的办法获得了一个“监生”(太学生)的头衔。在这个时期内,他想出山仕进,但科举之路不通,便只能消极隐退,过着“野鹤孤伴,山鹿群陪”的生活。[(1)]他的山居题为“孤云草堂”,“园花按时开放”,供其玩赏。他在《会心录》中,描写“买山而隐”、悠闲自得的情趣是:“芳草留春,翠茵堆锦,我当醉眠床席,歌咏畅怀,使花片历飞,满衣残香,隐隐扑鼻”。他“自少留意礼、乐、兵、农诸学”,[(2)]对于乐律深有造诣,对戏曲也颇感兴趣,于是便利用林间泉下空暇的时日,开始写起剧本来了。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说:“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足见他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隐居石门山以后开始动笔的。《桃花扇本末》又说: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
这说明他在没有出山以前只写了个草稿,因闻见有限,材料不够,便暂时搁置了。
那末,孔尚任怎么想起来要写这个剧本的呢?《桃花扇本末》自述其创作缘起说: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这里提及的“族兄方训公”,便是他的堂兄孔尚则(号方训),做过南明的刑部主事。秦光仪是他的岳父,曾到南京孔尚则处住过三年,所以得知弘光王朝的兴衰故事。孔尚任成年后从岳父那里听到二十多年前南明亡国的逸闻,觉得很有兴味。因他父亲孔贞璠原是崇祯六年的举人,明亡不仕,崇尚民族气节,曾亲自参加过抗清活动。[(3)]其父的挚友贾应宠(凫西)于明末在北京任刑部郎中,明亡后与抗清志士丁耀亢、阎尔梅等交往,编撰《木皮散人鼓词》,抒发了对人世的不满情绪。孔尚任童年时曾赴贾家作客,听讲《论语》数则,在思想意识上受过贾氏的影响;[(4)]后来创作《桃花扇·听稗》时,直接引用了贾氏的一段鼓词《太师挚适齐》。
从孔尚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来看,他写《桃花扇》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吊明之亡,是基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剧中褒忠斥奸,反对农民起义,而不是为清朝政府唱赞歌。
二
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岁,孔尚任已届三十七岁。这年冬季,有一件意想不到的宠遇,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那就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北返时到曲阜祭孔,衍圣公孔毓圻举荐他御前讲经,博得了皇上的赏识,“不拘定例,额外议用”,破格提拔他为“国子监博士”(最高学府的教授)。他在《出山异数记》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并感恩戴德地说:“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这便是他在修改《桃花扇》时添加颂扬圣朝的“试一出《先声》”的原因。他通过老赞礼之口说:“日丽唐虞世,花开甲子年,山中无寇盗,地上总神仙”,“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对康熙皇朝大大地歌颂了一番。这一出戏在石门山写的初稿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而是二稿或三稿中添加上去的。
孔尚任恪守儒家之道,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进京,入国子监开坛讲经,并随衍圣公孔毓圻上朝谢恩,再次晋见了皇上。二十五年(1686)七月,他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治河救灾。动身前又蒙皇上召见,“陛辞于乾清宫,天语劝劳”。[(5)]当时黄河夺淮后淮海一带水灾严重,朝廷在扬州设立“下河局”,督理河工疏浚淮河海口。孔尚任这次南下,深入生活打开了眼界,投身社会接触了现实;并广泛结交江南文化界人士,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为他写作《桃花扇》第二稿收集、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扬州本是淮南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戏剧艺术十分繁荣,昆曲演出甚为流行。孔尚任到扬州之初,地方官就招待他看戏。他写的《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诗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亦有侏儒嬉谐多,粉墨威仪博众喜”,生动地反映了扬州戏曲演出的盛况。康熙二十六年(1687),孔尚任到泰州一带视察河工,又多次观赏了昆班的演出,曾赋诗《元夕前一日……踏月观剧即席口号》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在这样浓郁的戏曲氛围中,的确引起了他重写《桃花扇》的兴趣。这时他结交了昆曲作家吴绮和徐旭旦等人,把自己创作《桃花扇》的情况告知徐旭旦,徐氏为他预拟了《桃花扇题辞》,他后来据此改成了《桃花扇小引》。在《桃花扇·寄扇》中,他借用了徐旭旦写的〔北新水令〕《冬闺寄情》套曲。[(6)]他还结交了精通昆曲艺术的泰州名士俞锦泉。俞氏能粉墨登场,亲自执教、培养了一个家庭昆班,伶人多达百数,全部是女演员,常在府中流香阁演出以佐客。孔尚任在《舞灯行留赠流香阁》诗中赞说“俞君声伎甲江南”,对俞班的演艺备极推崇。孔尚任到兴化时,俞氏还带了家班流动献艺。这样良好的艺术环境,促使他写《桃花扇》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为了拓宽《桃花扇》的剧情思路,孔尚任在大江南北广泛结客,访遗问老,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经常举行文酒之会,倾听前朝遗民痛诉明末遗恨,曾有“生平知已,半在维扬”之说。[(7)]在会见诸多的明末遗老中,重点人物有黄云(仙裳)、杜浚(于皇)、邓汉仪(孝威)、冒襄(辟疆)、余怀(淡心)、李沂(艾山)、李淦(若金)、石涛(朱若极)、龚贤(半千)和张怡(瑶星)等。这些人都是心怀明室、不忘故国的隐逸耆旧,其中与剧作直接关联的人物是如皋冒辟疆和南京张瑶星;而余怀叙写秦淮歌妓的《板桥杂记》,则是孔尚任汲取素材的重要文籍。
冒襄(1611—1694)是孔尚任采访的重点对象,康熙二十五年(1686)仲冬,孔尚任在扬州举行“广陵第一会”,即邀约冒襄与会,彼此“高宴清谈,连夕达曙”。[(8)]次年九月中,冒襄以七十七岁高龄,从如皋专程到兴化与孔尚任会晤,留住三十日之久,两人剪烛长谈,搜讨旧闻,畅叙弘光遗事。冒襄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并称“明末四公子”,都是复社名士,在揭发阮大铖是阉党余孽的《留都防乱揭帖》上曾联合署名。冒襄的父亲冒起宗曾任左良玉驻襄阳时的监军,与史可法又是“同年”好友,所以冒襄曾得到史可法的荐举,对左军和刘泽清等“江北四镇”的情况都很熟悉。另外,冒襄多次到南京参加乡试,不仅与侯方域过从甚密,而且还和李香君有直接的交谈,对侯、李的婚恋过程十分清楚。据《同人集》卷四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秋,冒襄在南京访晤侯、李,曾“与李香快谈”。[(9)]足见冒襄是侯、李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人,不仅能为孔尚任提供详尽的题材细节,而且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上也给孔尚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扬州和南京两地的察访,对剧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趁着留驻扬州的机缘,曾游览了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并重点凭吊了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这为剧中写“江北四镇”和史可法督师的《争位》、《和战》、《移防》、《誓师》四折戏奠定了基础。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孔尚任渡江到南京,对《桃花扇》剧情的发生地进行了为期二个月的实地考察。他寓居朝天宫冶城道院,邀约友人游秦淮、青溪,寻访旧院河房和长板桥遗迹,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足迹遍历虎踞关、鸡鸣寺、雨花台、莫愁湖、清凉山、牛首山、凤凰台等处。[(10)]又专门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张瑶星。《桃花扇》中把张瑶星写成收场结穴的关键人物,其创作构思无疑是从栖霞山的访晤中生发出来的。
江淮三年多的生活实践,使孔尚任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因督察河工到了射阳、盐城、高邮一带,亲眼看到穷乡僻壤中渔民和盐民的苦况,在《湖海集》中,他写下了一系列同情民生疾苦的诗文,如《登文游台》诗云:“但见流亡庐,荒础无人扫,何处问游踪,枯骨引鸦噪。”他所到之处,关心民瘼,自称“《湖海》一集,乃呻吟疾痛之声”(《与田纶霞抚军》第一书)。另一方面,由于河道总督与下河大僚之间在治河方案上意见分歧,引发了倾轧争斗,孙在丰等人被撤回京,他留守在冷署中,受到了宦海浮沉、人情冷暖的煎熬,终于觉察到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写于扬州的《待漏馆晓莺堂记》中说:
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处所!而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冤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与予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独立予呻吟病饿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盖有似乎迁客羁臣!
此文抒发了他心灰意冷的苦闷情绪。现实的悲凉生活,打破了他拯饥济溺、报效圣主的幻梦。他既不能回京,又不能归家,穷饿困顿,竟至向俞锦泉借粮度日(《湖海集》卷三《乞米行》)。他已失去了眷顾宠臣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成了被贬的迁客。因此,即使康熙二十八年三月皇上第二次南巡过扬州时“蒙召登舟,赐御宴一合”。[(11)]也没有激起他多大的心潮。这与《出山异数记》的境况相比,他的颂圣热情已大为减退。正如邓孝威评论说:“公淡泊敛退,绝无矜张之容。”[(12)]这决定他在《桃花扇》第二稿中,虽有“颂圣”的意向,“吊明”的创作思想仍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三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孔尚任回到北京,仍任国子监博士。这时候,他结识了诗人王士祯,又和词家顾贞观、曲家顾彩等文士交往。王士祯给他海波巷的书斋题名为“岸堂”,他便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由于三年多淮扬生活的曲折经历,再加回京后一直处于闲曹冷官的境地,他对朝廷已经失望,利禄之心也就日渐淡薄,甚至还产生了辞官归隐的念头。他在《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诗中说:“吾将拂袖归,期翁同登岱。”《和林桐叔归石岳诗》更声称:“鸡肋何足贪,儒冠将弃溺!”表示了抑郁不满和厌绝功名的思想情绪。这期间,他在古玩市场买到了汉玉羌笛、唐制羯鼓、南宋内府琵琶“大海潮”和明宫琵琶“小蝉吟”等。康熙三十年(1691)秋,他“典衣”购得了一把唐朝的古琴“小忽雷”,欣赏之余,便和曲友顾彩在康熙三十三年创作了《小忽雷》传奇。他在剧本卷首的题辞《博古闲情》中说:
〔逍遥乐〕侨寓在海波巷里,扫净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窗外儿竹影萝阴,浓翠如滴,偏映着潇洒葛裙白纻衣。雨歇后,湘帘卷起,受用些清风到枕,凉月当阶,花气喷鼻。
〔梧叶儿〕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大海潮,南宋器;甘黄玉,汉羌笛;唐羯鼓,断漆奇;又收得小忽雷,焦桐旧尾。
可见他的寓所是简陋清冷的:月俸不够用,生活凄苦困窘,惟有寄情于书卷文物中,与乐器古董为伴。
到了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下旬,他升任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具体职务是宝泉局监铸,成为正六吕的京官。宝泉局是铸钱的机构,他做了监督,“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其实,他清廉自守,“寒如故也”。[(13)]他给张潮的信中说:“今年在铜臭中,不为所染,自觉潇洒,而长官僚友多不相信(张潮《友声后集》)。由于他的监铸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便获得皇上的敕令嘉奖,表扬他“经画多才,恪勤奉职,出纳裕公私之积,权衡佐军国之需,劳积有成,新纶宜沛”,并赠衔为“承德郎”。[(14)]
这期间,他又酝酿着写《桃花扇》第三稿。对于南京访问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他要慢慢消化。其中包括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以及剧情细节的增减,都是颇费心思的。为此,他返京后经常出入戏园,观摩昆班新戏,以资借鉴。他在康熙三十三年写的《燕台杂兴四十首》之八说:“太平园里闲萧管,演到新词第九回。”注云:“太平园,今之梨园部也,每闻时事,即谱新声。”这座京中新开的著名戏园,被孔尚任写进了《桃花扇》“先声”和“孤吟”中,作者借老赞礼之口说:“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这“太平园”的名目,在石门山和淮扬期间写的稿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肯定是第三次在京中定稿时写进去的。据孔尚任在《博古闲情》的跋语中记载,当时京中“三家老手鼎足时名”的昆班是聚和班、一也班和可娱班。此外,他还看过景云班、南雅小班、兰红小部的演出。他又结交剧作家,互通声气,如《扬州梦传奇》作者岳端(红兰主人)、《琼花梦传奇》作者龙燮(改庵)。他和顾彩在康熙三十三年合作《小忽雷传奇》,可以说是在《桃花扇》定稿前的试笔。这一成功的尝试,对《桃花扇》的定稿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
《小忽雷》也是借儿女之情写朝政得失的历史剧,剧中以“小忽雷”这把古琴为引线,通过梁厚本和郑盈盈的爱情故事,反映唐宪宗、文宗年间权奸当道、忠良受害的政局变乱,抨击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剧中的阉宦头目仇士良是祸国殃民的元凶,他不仅抢夺小忽雷,争琴起衅,而且还狠毒地屠戮反对他的文武官员。剧中以“甘露之变”前后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把朝臣权德舆、裴度、李训、郑注和文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都穿插在戏剧矛盾中。孔尚任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试笔,是跟他创作《桃花扇》的主题互相呼应的,其反权奸的构思是完全一致的。
促使《桃花扇》早日问世的另一因素,是淮扬旧交田雯的一再催索。《桃花扇本末》说:
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
田雯字纶霞,山东德州人,康熙二十六年八月任江苏巡抚时与孔尚任在淮扬结交,后调任贵州巡抚,从此天各一方。康熙三十三年正月,田雯入京,升任刑部侍郎,两人又得以聚会。田雯每次见到孔尚任时,都要紧握他的手,索览他的秘宝《桃花扇》。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挑灯夜战,加快创作进度。正巧他在友人岳端家里认识了从苏州来的老曲师王寿熙,给他提供了优伶常唱的曲谱范本;他每写一曲,王寿熙必击拍歌唱,如有音律不谐之处,即时改正,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关于这一情况,《桃花扇本末》中有记载说:
适吴人王寿熙者,丁继之友也,赴红兰主人招,留滞京邸。朝夕过从,示余以曲本套数,时优熟解者,遂依谱填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故通本无聱牙之病。
丁继之(1585—1675)是南京的昆曲串客(业余演员),住在秦淮河与青溪交汇处的丁氏河房内。据《板桥杂记》说,丁继之和张燕筑、柳敬亭等人常会集在李贞丽、李香君和顾媚等名妓家,客串演戏。王寿熙早年曾在秦淮河房为诸伶拍曲,与丁继之相交甚厚。所以王寿熙不仅在昆曲的音律方面对孔尚任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为《桃花扇·眠香·闹榭、栖真、入道》写进丁继之的形象提供了活材料。
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完成了《桃花扇》全部的定稿工作。此剧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艺林纷纷传抄,产生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消息传到宫内,连康熙皇帝也大感兴趣,派内侍急急地向孔尚任本人索取剧本。康熙三十九年元宵节,金斗班就首先把《桃花扇》搬上舞台。此后,各戏班争相上演,“岁无虚日”。当年三月初,孔尚任又获得升官的机会,晋升为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但刚刚上任十多天,到三月中旬就无缘无故地被罢了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因史无明文,成了一件疑案。至于是否与《桃花扇》有关,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四
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从康熙十八年进石门山开始动笔,在淮扬、京华之间多次改稿,断断续续,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最终完成,前后共经历了整整二十个年头。真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创作态度是十分慎重严谨的。
从《桃花扇》创作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他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对康熙皇帝感恩图报,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当今圣主的构思。但由于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和京中闲官冷宦的刺激,他重新审视了从扬州、南京访问得来的大量素材,深化了对南明史料的认识,使吊明之亡的意蕴愈来愈浓,颂扬圣朝的情绪越来越淡。从最后定稿的《桃花扇》作品来看,流露出来的民族意识相当强烈,但并无反清悖逆之词;开场对康熙圣朝歌功颂德的表白是明显的,但并无为满清统治集团效忠邀赏的意图。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特别是晚清以来民主革命兴起后的读者)对颂圣的开场已毫无兴趣,受到艺术感染的全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
孔尚任“吊明”的创作手法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实际上就是借情言政:侯、李之情是表象,政治主题是实质。换句话说:写情只是手段,写政才是目的。关于“兴亡之感”这一政治主题的具体含义,作者曾明确地宣示: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
孔尚任抱着儒家救世之心,总结南明败亡的原因是“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15)]作者认为祸根是权奸当道,昏君误国,在《桃花扇小识》中曾说:“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帝基者也!”这是指阉党余孽阮大铖与马士英互相勾结,迎立酒色之主福王,把持朝政,大肆迫害主持正义的东林、复社人士,毁掉了明朝三百年的基业。正如作者友人陈于王《桃花扇题辞》所言:“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消得东林多少恨,梨园吹断白牙箫。”而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国家民族的危亡造成的。作者把离合之情贯穿在国家兴亡之中来写,这种构思无疑是十分高明的。侯、李身逢末世,空有忠肝义胆,实无力铲除奸恶、挽回世道人心的颓丧,最后只能在栖霞山双双入道。这是作者救世不成而消极遁世的一种思想表现。
南京的栖霞山是佛教圣地,并非道家渊薮。山中的栖霞寺创建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历史悠久,发展到唐代,已成为全国“四大丛林”之一。孔尚任在康熙二十八年亲至栖霞山实地考察,曾赋《游栖霞寺》五律二首。但他在剧中写侯、李上山不是皈依佛门,而是栖真入道。这表面上是因为张瑶星道士隐居在白云庵中,[(16)]但实质上深层的因素是由孔尚任本人崇尚道家老庄的思想所决定的。孔尚任早年就受到其父执贾凫西“道似老庄,亦婚亦官”(《木皮散客传》)的思想影响,他科举失意后曾隐居于石门山中。这种作风是历来隐逸文人共通的心理意念。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得志于时而谋天,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17)]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孔尚任也是这样。作为正统的儒士,他大有出仕救世之志,但在遭遇挫折时,便转向道家,追求老庄超凡脱俗的意境,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这种儒道对立而互补的人生观,救世与遁世相矛盾又统一的人生态度,便是孔尚任到南京时,住进冶城道院,以及在《桃花扇》中写“道”而不写“佛”的思想文化根源。他对栖霞山的佛寺环境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却另辟蹊径,在剧本中创造了浓郁的道院气氛,虚构了李香君随卞玉京入葆真庵,侯方域随丁继之入采真观各自修道的情节,而且还称许卞玉京和丁继之是隐居乐道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骂筵》眉批)。孔尚任从第二十四出写到第四十出,先后上栖霞山隐居入道的共七人:卞玉京、丁继之、张薇(瑶星)、蔡益所、蓝瑛(田叔),而苏昆生是第六号,柳敬亭是第七号(《余韵》眉批)。孔尚任写他们在明亡后都找到了最理想的归宿,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为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指点迷津,树立榜样。所以侯、李的双双入道,是孔尚任创作思想和形象发展的必然结果。
按史实,侯方域在明亡后回归商丘老家,在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曾被迫参加河南乡试,中了副榜举人,但没有出仕。至顺治十一年(1654)忧郁病逝,年仅三十七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把侯方域处理成上山入道,目的是为了保持其艺术形象的完整和人格的独立,以便充分肯定复社文人反权奸的爱国志节。对于明末的党祸,孔尚任痛恨阉党,竭力推崇东林人士,剧中借李香君之口说:“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骂筵》)而复社是继承东林遗志而组成的进步的文学社团,所以孔尚任在剧中重点突出了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等复社名士,把他们作为正义的化身来刻划。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人士曾得到江南市民阶层的广泛支持,清初李玉的剧作《清忠谱》传奇已反映了这种情况。孔尚任在戏曲界继承《清忠谱》的传统创作《桃花扇》,进一步反映了市民阶层支持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的斗争,塑造了秦淮歌女李香君有胆有识的闪光形象。侯方域是复社的代表人物,他不是士大夫,只是一个尚未入仕的儒生,在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中,他得到了李香君、卞玉京、苏昆生、柳敬亭、丁继之等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侯、李之情,是在与阉党余孽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生一旦,侯、李并重,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表彰李香君就必须维护侯方域。以入道作为悲剧的结局,便是对侯方域正面形象的肯定。这也是作者潜在的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隐”与“道”的结合,原是元明戏曲创作的主题之一,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曾分杂剧为十二科,第一是神仙道化,第二就是隐居乐道,又名“林泉丘壑”。朱权又厘定戏剧十五体,其中“草堂体”的特点是“志在泉石”。孔尚任继承元明以来戏曲文化中的这一传统,用文艺笔法把佛家的栖霞山写成“修仙有分”的道家福地,[(18)]借“林泉丘壑”的传统意境为《桃花扇》的政治主题服务,创造性地在第四十出《入道》以后又增写了“续四十出《余韵》”。巧妙地通过“山林隐逸”的描绘,大发故国之思。
在《余韵》中,作者写南明覆亡之后,苏昆生、柳敬亭和老赞礼都坚持民族气节,隐于山林之间。他们面对剩水残山,触景生情,共叙兴亡之感。老赞礼唱巫歌〔问苍天〕,是愤慨于世道人心的乱离与不平,柳敬亭唱弹词〔秣陵秋〕是悲叹弘光朝昏君乱臣倒行逆施,导致了国破家亡。苏昆生唱北曲套数〔哀江南〕则感伤明亡后金陵的败坏凄凉景象,泼洒了深沉的民族血泪。这套北曲七支是抒发亡国之痛的主题曲,第七支〔离亭宴带歇指煞〕云: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跟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不仅诉说了舆图变色、江山易主的痛楚,而且宣泄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关于《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主要是通过斥奸骂谗和褒扬忠烈的情节表现出来的。剧中在揭露昏君乱臣腐朽暴戾的丑恶面目时,通过《誓师》和《沉江》两出,重点歌颂了抗清殉难的民族英雄史可法。而《余韵》这一出,则集中地寄寓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在《余韵》的后半部分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徐青君投降清朝后到栖霞山“访拿山林隐逸”的情节,辛辣地讽刺了投降变节的南明旧臣。徐青君本是明朝元老重臣的后裔,明亡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走卒和帮凶,作者用“开国元勋留狗尾”一句台词,就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位降官的丑态,与苏昆生、柳敬亭、老赞礼形成鲜明的对照。三位“山林隐逸”坚持民族气节,抗拒清廷公差的访拿,“登涯涉涧,竟各逃走无踪”。作者在这里一贬一褒,毫不掩饰地显露了贬斥降清褒扬抗清的感情。
总的说来,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思想感情是复杂的。他一直处在儒与道、仕与隐、颂圣与吊明、忠清与宗汉、救世与遁世的矛盾中。但他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见,有惊人的魄力,终于突破了矛盾和禁区,以现实主义的大手笔,出色地构思了亡明痛史中爱情纠葛与政治浪潮相互交织的剧作,展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内容,使《桃花扇》成了一部不朽的悲剧名著。
注释:
(1)孔尚任《石门山集·买山卷》及下述《会心录》诸文,均见于宫衍兴编《孔尚任佚文遗墨》(1994年济宁市新闻出版局批准自费铅印本)。
(2)见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大学辩业题辞》(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3)清刻本《阙里新志》卷二十三《史传·孔贞番墓志》。
(4)见《孔尚任诗文集》卷六《木皮散客传》。
(5)见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待漏馆晓莺堂记》(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康熙刻本排印)。
(6)见谢伯阳《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徐旭旦作品》(《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7)见《湖海集》卷十一《答张谐石》(第二书)
(8)见《孔尚任诗文集》卷七《与冒辟疆先生》(第一书)
(9)见顾启《冒襄研究》第198页(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本),据《同人集》卷四陈则梁致冒辟疆信:“明早乞同去侯朝老处,与李香快谈。”
(10)见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咏南京诸诗。
(11)(12)见《湖海集》卷六《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谢用前韵》。邓孝威评语见《送驾至淮上恭赋》诗注。
(13)见《孔尚任诗文集》卷四《燕台杂兴三十首》第十七首自注。
(14)见徐振贵《孔尚任评传》第一章《孔尚任传略》(1991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封赠孔尚任为承德郎的诏书,原件藏曲阜孔府。
(15)见《桃花扇·先声》〔满庭芳〕唱词。
(16)据明万历时盛时泰《栖霞小志》和清乾隆时陈毅《摄山(栖霞山古名)志》记载,白云庵是佛寺,并非道教宫观。张道士是个人寄宿在白云庵中,所以方苞《白云先生传》说他“独身寄摄山僧舍,不入城市,乡人称白云先生(《望溪先生文集》卷八)”。可见孔尚任把白云庵改写成道院是从道家思想出发的艺术虚构。
(17)见王夫之《诗广传·大雅四十八论》,中华书局1964年排印本第135页。
(18)见《桃花扇·入道》张薇的说白:“贫道张瑶星,挂冠归山,便住这白云庵里,修仙有分,涉世无缘。”按:张薇的真名是张怡,字瑶星,号璞生,又号薇庵,孔尚任把他写进剧中时易名为张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