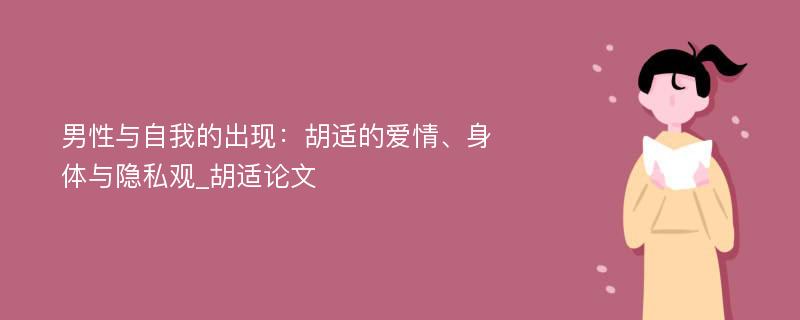
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扮相论文,躯体论文,隐私论文,男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1891-1962)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同时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从1917年他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1948年他赴美的三十年间,他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学者以及教育家。他在这些年间扮演了的多重角色,包括中国驻美的大使(1938-1942)。他的盛名与地位固然使他时时处在众目睽睽之下。然而,他自己也煽引了人们对他的好奇心。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传资料产量最丰富的人。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他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诚然是一个自传的档案。然而,他这个自传档案其实没有多少可以说是真正的私密意义下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要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密——不管窥淫与否——的隐私,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
胡适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自传档案,当然是研究胡适及其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资料。但是,本文既把胡适的自传档案当成是研究胡适的资料的宝藏,也把它当成是“文物”(cultural artifacts)的宝藏。我在本文里援引了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演伸的“扮相”(performativity)的观念,也参考了女性主义的自传和传记研究、男性研究的成果。我的做法是把胡适放在论述的脉络下来分析胡适的“自我”观,以及分析他在对自己的隐私的掩与彰之间的拿捏。我引用了巴特勒的理论,认为胡适的“自我”观以及他在自叙、自传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属于扮相式的。这所谓扮相的意思,是指这些行为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扮演,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意义符号的重演和再体验”。①
其次,我在本文里对“自我”的了解,和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对“自我”的了解有所不同。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自我”观,是把“自我”当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它的原貌是可以透过细密、忠于史料的传记研究来还原的。胡适自己和历来所有为胡适立传的人,他们所接受的都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对“自我”的观念。我则认为“自我”在被描绘、扮演和型塑以前,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果“自我”是“扮相”式的演练的结果,自传里的“自我”更是如此。自传里的“自我”除了是“扮相”式的以外,还必须透过其所在的文化里,站在宰制地位的叙述模式来展现的。②
胡适在自叙、自传方面的所作所为,是承袭了中国文人“知识男性的自我观”悠久的传统。他在自传的书写和保存方面所下的功夫,等于是他在“知识男性的唱和圈”里的耕耘。③ 在他的一生当中,除了两位女性——陈衡哲和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以在思想上与胡适平起平坐的身份,挤身进入他的唱和圈以外,他的自传园地,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世界。这个“知识男性的唱和圈”的观念虽然是我向崔芙·柏络顿那儿挪借过来的,不管是从其精神、实践、甚至从用词上来说,它可以说是完全捕捉住了传统中国士人以诗文来唱和的传统。④
本文以上述的理论作基础,提出以下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胡适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是了解胡适如何拿捏他的公私之间的分际的关键。我的论点是:胡适对公与私的分际,不仅仅有其社会和历史的缘由。他这个知识男性的唱和圈跟他的“自我”观还是相生相济的。这一方面让胡适划下了他的公开领域的界域;在另一方面,让胡适能有把他的一些隐私,嵌入公开领域的余地,也因而让他能够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语只字。这些片语只字,对那些在胡适“知识男性的唱和圈”里的朋友,可以引来会心的一笑。可是,对他圈外的人来说,胡适等于是有意让这些同样的片语只字,成为只能臆测,不得其详的断简残篇。胡适维护他的隐私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回忆胡适的传记文学的出现,而更重要的,是他与他的美国朋友兼情人韦莲司来往信件的公布。⑤
本文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胡适对自己的躯体,关注到已经近于偏执的地步。虽然胡适谨守其恋情的秘密。相对而言,他对公开暴露自己的躯体却不甚介意。我认为胡适可以那么坦然地公开暴露自己的躯体,其反映的是他那个时代氛围,亦即,当时人对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我在作这项分析的时候,选了三个胡适同时代的人来作比较。其中,最特别的是吴宓。胡适最令人回味的地方,在于他毫不腼腆把自己痔疮的毛病一五一十地说给别人听。我引用后现代主义对弗洛伊德肛门偏执的演绎,用胡适对肛门的偏执来解释他写作的焦虑。
本文的第三个主要的论点是:胡适在公私领域里的扮相,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最特别的视野去分析胡适如何扮演丈夫、男性、以及思想界领袖的角色。历来,有多少人费尽了笔墨去分析胡适的矛盾。他们都说他作为一个打倒中国传统的领袖,却矛盾地听从他母亲媒妁之言的安排而娶了一个裹小脚、没受过正式教育的江冬秀为妻。由于人们认定他婚姻不美满,那捕风捉影、色淫淫地窥伺他的婚外情之风,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⑥ 这种窥淫风下的作品,把胡适的公与私的领域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而把他的婚姻看成是纯然属于个人或者私领域的行为。
我在本文里则强调胡适在他的婚姻里的男性的扮相,与他在公领域里的扮相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我们分析胡适在公与私的领域里的扮相,可以帮助我们修正目前胡适研究的一些错误,并且可以让我们对胡适有更细致的了解。这种分析不但可以证明为什么历来大家说胡适反对参与政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分析可以提出另一个更可让人信服的解释。更有甚者,当我们特别把胡适自诩的骑士、君子之风在胡适的性别论述里凸显出来的时候,这种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这个近代中国为妇女争自由与独立最铿锵有力的辩护者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
知识男性的唱和圈与公私的分际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描述一下胡适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的大略。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及白话文所衍生的文学革命。⑦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术领袖、作家、评论家、发行人和主编,他是当时中国文学界与好几个学术领域的把关权威。作为学术领袖,他订定了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⑧ 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他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⑨ 除了文艺创作的领域很快地就有女性作家崛起以外,所有其它学术机构以及出版界在当时都属于男性的世界。胡适的影响所及,不只在学术机构或出版界。由于他勤于写信,又是近代中国人人都想跟他通信的名人,他所留下来的卷帙浩瀚的书信,也是他知识男性的唱和圈的一部分,是他与友朋、各路方家谈学、论史、酬答诗文的唱和圈。同样地,就像我在下文会详细分析的,他的日记也属于他唱和圈的一环。
胡适这个知识男性的唱和圈有其男女有别的空间的面向。就像大学和基金会是男性的世界一样,他所进出的公共场所也泰半是男性的世界。由于中国并没有类似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ian)所描述的那种绅士会所或咖啡馆的公共领域,⑩ 北京的高级餐厅就等于是胡适所处的时代的公共领域。胡适在日记里记他在餐馆宴客开会的次数不胜枚举。这种聚会的成员都是男性,少数的特例多半是以太太的身份参加,而且也多半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女性。(11) 当胡适及其朋友——不管是作东还是作客——与外国朋友夫妇聚餐的时候,他们多半都是不携伴而单独出席的。
连胡适家居生活的空间都是男女有别的。虽然他一辈子都没置产,他一向住的都是相当大的四合院。他1918年所租的最小,也有十七间;他1948年共产党进城以前所放弃的四合院最大,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东厂胡同的所在地。(12) 就像维多利亚以及北美殖民时期的宅邸,让男主人能够在他的城堡里划分出男女、公私有别的空间一样,(13) 胡适在他四合院的宅邸里,也有他公私有别的空间。他真的是他自家城堡里的主人,因为即使他是在跟江冬秀讲话,他都习惯称呼他们的家为“我家”。(14) 虽然胡适不常在家宴客,他的家在周日是对外开放的。他周日的访客固然偶尔会有女性,他的客厅基本是他在北大以及餐馆的男性世界的延伸。就像维多利亚以及北美殖民时期的宅邸里的书房,胡适的书房是他男性的世界,是他的沉思的世界(vita contemplativa)。他的书房远离妻小、仆佣的喧嚣,据说是他消磨一天最多时间的地方。(15) 书房是胡适看书、沉思、写作、处理来往信件、写日记,以及编辑刊物的所在。
如果不是因为胡适一生有写日记的习惯;如果不是因为他刻意地保存他来往的信件,甚至留下他所写的信的底稿;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夫人江冬秀忠心耿耿的协助之下,费尽苦心地把他最重要的文稿、日记、信件辗转搬运到安全的所在,我们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可资运用的胡适传记资料。早在1933年,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在塘沽协定签订前后,胡适就已经把他的一些重要文稿存入银行的保险库。(16) 1937年,在日本占领北京不久,胡适已经赴美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江冬秀托人把胡适七十大箱的书籍、文稿、和他所搜集的自传档案先搬到天津,然后再搬到上海。等到他在美国接到江冬秀寄给他的清单,他在选了又选以后,要江冬秀把他和他父亲的日记和文稿,以及十五箱书寄到美国。最后,他把他和他父亲的日记和文稿寄存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17) 1948年12月,他离开了北京。匆促离开的他留下了一百多箱的书,其中包括了他所有的来往书信、文稿以及部分的日记——原稿或者抄本。(18)
虽然胡适大部分的日记是在他过世以后才出版的,我们不能忘记他写日记的初衷就是要让大家看的。光是从他在保存他的日记上所用的苦心,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要把它们公开的——不管是在生前或死后公开,或者是公开多少。他的留学日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他留美的初期,他每写完一本日记,就寄给在他在国内的朋友许怡荪。并且,他还让许怡荪把一些日记的片段在《新青年》上发表。1933年,胡适请住在他家的助手章希吕帮他重抄、整理他的留学日记,另加条目。根据胡适自己说法,他在1939年初版的留学日记,“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19)
胡适的日记从来就不是要秘而不宣的。1913年4月,当他还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时候,他用中国历史上自传作者经常使用的套语,来为他为什么要写日记作辩护:“自传则吾岂敢,亦以备他日昆弟友朋省览焉耳。”(20) 等他成名以后,他就不再用这种自谦或自贬的套语来形容他自己的日记的价值。1921年4月,当他在日记中断以后又再次下决心要持之以恒的时候,他说:“我这三四年来,也不知被我的懒笔断送了多少很可有结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损失了多少可以供将来的人做参考资料的事实。”(21)
胡适的日记公开的程度,远远超乎琳·卜伦(Lynn Bloom)一针见血的针砭。她说:“专业作家没有下班的时候。”(22) 胡适的日记,就像他来往的书信、新诗以及他的学术著作一样,是必须放在他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里来看待的。胡适的日记里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记载,因为家庭生活是私事,不在他的唱和圈的范围内。他在日记里所记载的,是友朋的往来、记游、寻访图书、病恙、臧否人物、匡时论政、论学、谈诗、读书札记、发信存本、剪报、写下自诩的洞见,以及完稿成书时的喜悦。他—直让朋友借阅他的日记,偶尔还主动出示。总之,他的日记所记载的,与其说是他的私密生活,不如说是他和友朋之间的唱和。
胡适的日记是写给人看的。这充分地表现在他日记里的两个做法。第一,他在日记里会加上注解和作参照。更有意味的是,他会回头去念他的日记,并附加注解。在他留美以前,1910年的日记里,就已经有加注解的例子。他留学以后更是如此。比如说,他在1911年6月18日,记他在美国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Pocono Pines)基督教夏令营差一点成为基督徒。他在1919年10月回过头去看这一条,觉得当时的记载太过简略。于是,他把当年给章希吕和许怡荪的信附钞于后。然后,又加了一个很长的注解,解释他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恨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信教:“后来我细想此事,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23)
附加注解与作参照,是帮忙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这跟真正私密性质的日记是不同的。与之相反的,就是胡适的第二个做法,亦即隐讳。胡适在日记里隐讳的作法有几种。其作法包括隐去人名,用□□取代,或者用英文缩写,或者删削附载的文字。有些英文缩写并不难猜,比如说,C.W.(韦莲司)和S.H.C.(陈衡哲)。胡适一向在日记里称陈衡哲为莎菲,或干脆直接用英文Sophia。但是,他在1937年3月21日一条,由于所记给陈衡哲的英文信话说得相当难堪,他只附了原信的一段:“You are hopelessly unintelligent! You can neverdistinguish between the flatterer's gossip and the sincere advice and the sound judgment of a lifelong friend.”(“你真是笨得可以!你连阿谀者的奉承,跟一生的挚友给你的真心劝告都分不清楚。”)同时,他也只注明这是“给S.H.C.之信”(letter to S.H.C.)”(24) 这封信以及日记所引的片段都是英文,这除了可以使责骂的语气稍显缓和以外,其用意可能也在于把伤害陈衡哲的程度减低到只有看得懂英文的人才会知道的范围之内。
对于除了是哲学家以外,又以历史家自居的胡适来说,日记、自传是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界领袖对历史应有的回馈。他认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许多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可以为历史留下珍贵的资料。在1921到1922年之间,胡适读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录了李慈铭三十多年的生活。李慈铭在日记里不只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以及国家大事。他也记录了他读经的注疏、历史研究、读书札记、人物的臧否,还有他的诗文。事实上,胡适自己说:阅读《越缦堂日记》,是让他在1921年“重提起做日记的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25)
作为一个勤读日记的人,胡适在自传上的所作所为是“扮相”式的:不仅只是其体例,连他所记录的题材以及他所赋予它们的历史意义,都是他以及传统中国士人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演练其所在的文化里,约定俗成的体例及叙述模式——这就是“扮相”式的意思。胡适在1920年代初期读了李慈铭的日记以后,他所写的日记根本是师法李慈铭。和李慈铭一样,胡适在他的日记里记他的朋友圈;他谈诗、论时事;作读书札记、以及黏贴上李慈铭那个时代所没有的剪报。胡适有意师法李慈铭,他要让他的日记成为历史资料的典藏。用胡适戏题《越缦堂日记》的六言诗来形容,他自己的日记除了要“写出先生性情”以外,“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26)
胡适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就是他公与私、掩与彰之间的分界点;只要他是在这个唱和圈里,他可以无须掩饰;反之,他一旦离开了这个唱和圈,他就会坚持保有他的隐私权。反映这一点最为透彻的,莫若他在日记里,关于他和曹诚英的恋情的记载。1923年夏天,胡适在表妹曹诚英的陪伴之下到杭州的烟霞洞养病。在烟霞洞,他和曹诚英有了一段恋情。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他结婚时候的伴娘之一。由于曹诚英的先生娶了妾,他们关系失和,她去了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念书。(27) 1923年,曹诚英21岁,胡适32岁。六十年之中,没有人知道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一直要到1980年代末期,拜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传记、回忆文学盛行之赐,这段恋情才广为人所知。台北的远流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胡适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日记,可以用来证实他这段恋情。(2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他的日记里,完全没有留下流露出他和曹诚英坠入爱河的痕迹。
胡适从九月到十月的日记里,每天都写了他和曹诚英形影不离的情形。他们一起下棋、爬山、看桂花、赏月。他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可是,他就硬是不愿意留下只字片语说他们相爱着。他在日记里的描述简略已极,完全没流露出一丝丝柔情与蜜意。他在离开杭州烟霞洞前一晚的日记里,留下了一段颇为委婉的话: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我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悽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29)
但是,他并没有明说这“神仙生活”指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文字里,不但“神仙生活”黯然失色地被前后笼罩在“残月”、“悽惨”、“黯然神伤”这样惆怅、悲凄的字眼之间,而且,他很矜持地不愿意说出曹诚英就是那个让他过了一生中最快活日子的神仙伴侣。
胡适的许多朋友目睹了他在烟霞洞的“神仙生活”。例如:任鸿雋、陈衡哲以及徐志摩。只有徐志摩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两段颇有弦外之音的话。10月11日:“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顾忌。”(30) 10月13日:“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31) 然而,浪漫、奔放如徐志摩,还是为“有所顾忌”的胡适作了保留。
然而,一个以历史家自居的人,不把他与曹诚英的恋情写出来,似乎总是有点说不过去。于是,胡适就在日记里留下了些许片语只字。这样,无论是要“写出先生性情”,或者是要“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他都可以算是有了交代。对他唱和圈里的朋友来说,他们根本就不须要看他的日记才会知道他的恋情;他们当中有好几位,例如徐志摩,甚至还跟他们一起游西湖,得以亲睹胡适的“神仙生活”呢!
但是,胡适仿佛是故意要吊人胃口,或是要考验日后要为他立传的后人,他埋下了一些伏笔。比如说,1926年7月24日,他经由满洲穿越西伯利亚赴欧。7月24日,阴历六月十五,他到了贝加尔湖边的伊尔库次克。当晚,他在日记上写著:“今日为十五日,下午骤冷,有云,竟不见日光。几年来,每年六月十五夜的月是我最不能忘记的。今天待至10时,尚不见月,惆怅而卧。”(32) 由于我们现在从1980年代以来的传记文学知道他跟曹诚英有过一段情,这一则扑朔迷离的日记就得以迎刃而解了。我们知道曹诚英和胡适1923年7月29日(农历六月十五夜)清晨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五个月以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他踌躇良久不敢写下来的一首诗。这首《暂时的安慰》启始说:
自从南高峰上那夜以后,五个月不曾经验过这样神秘的境界了,月光浸没著孤寂的我,转温润了我孤寂的心。(33)
胡适1926年7月24日的这一则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解密的线索。他说:“每年六月十五夜的月是我最不能忘记的。”现在,我们可以精确地判定胡适与曹诚英订情之夜其实是在1923年7月28日(阴历六月十五),也就是他们上南高峰上看日出的前一个月圆之夜。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已经从传记文学里知道了他与曹诚英有过一段恋情,这一则谜样的日记,对胡适唱和圈里的朋友来说,可以引来他们会心一笑;然而,对于身处他的唱和圈外的我们而言,这只是一个挑逗得我们心痒难耐而不得其解的断简残篇。胡适这一着棋的微妙,与其说是在其隐,毋宁说是在其彰。崔芙·柏络顿在研究雷司立史帝分的书里,提到了史帝分在《坟书》(Mausoleum Book)里露了一招跟胡适几乎完全雷同的作法,亦即,既然都已经“隐”了,却偏偏故意要撂下一句话说:“此地有隐”——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意思。问题是别人根本挖不到银子,因为他已经把它隐去了。柏络顿评史帝分的那句话,用来形容胡适,同样是再贴切也不过了。她说:“这种把自传/记的隐与彰之际弄得那么有居心的复杂的作法,如果称之为勒索(blackmail),是有点用词过当;但如果称之为挑逗(flirtation),又未免有点太宽恕了他一点。”(34)
躯体的暴露与写作的焦虑
胡适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胡适的“自我”观、他的公与私的分际,以及他的隐与彰的分界。这个观念同样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对他自己躯体的偏执。胡适会在日记里描述他的身体,多半是他生病的时候。然而,最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他描述得最仔细,而且最锲而不舍的,不是他的心脏病或是纠缠他多年的脚气病,而是他的痔疾。我们要了解胡适对他的痔疾——或者更确切地说,肛门——的偏执,就必须先把它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的脉络里,一个对自我或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的时代脉络里。
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对躯体的暴露不甚介意,这当然是一个必须从当时人所写的日记、年谱、自传入手去系统研究的问题。然而,即使只是粗疏地俯瞰,就已经可以让人若有所得。比如说,胡适的好友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在他的英文自传里提到他青春期自慰的习惯——他用的字眼是“adolescence self-indulgences”(青春期的恣纵)和“self-abuses”(手淫)。(35) 郁达夫(1896-1945)在日记里写他狎妓并与妓女一起吸鸦片已经是相当特别了。(36) 然而,最奇特坦然的恐怕还是吴宓(1894-1978)。
吴宓有名的,因为他离婚后因为单恋而死缠狂追毛彦文(1898生)。然而,言传还远不如吴宓自己在日记里所作的描述。吴宓的日记所显露的,不但是他对女人的情痴,而且是他对女体的偏执。比如说,在他1936到1937年间的日记里,他每次都详细地记K(学生高棣华)来宿舍找他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他写K“丰腴”、“丰艳”、“润腴”;他更记下她来的时候偶尔“不袜”、“裸足”、“裸胫”、“裸腿”;或者偶尔K来的时候,他自己正沐浴完毕,或正披著浴衣。(37)
吴宓对女体的迷恋或偏执,还有他潜意识里的虐待狂的倾向;或者,用弗洛伊德的“反动机制”(reaction formation)的观念来说,是用看似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的举措,来取代或隐藏他自己所压抑下来的虐待狂的冲动。他在他晚年所作的《吴宓自编年谱》里,有一段描写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祖母虐惩比他大三岁的婢女翠屏的故事。翠屏“貌甚美秀,性亦聪敏”。吴宓祖母作六十岁寿宴的当天,由于吴宓口渴要喝水,翠屏水上得太慢,而且吴宓嫌水太烫,他祖母大怒。立刻把水碗从吴宓手中夺过,把碗向翠屏的头上掷去。同时,她命翠屏在院中铺一张芦席,坐在上面待命。等他祖母匆匆食毕,女客辞去以后,他祖母
即往芦席上坐,喝命翠屏将全身衣服脱光(旋经杨妗婆、姑母等再三请求,使留短裤),杨太淑人用尽气力,打击翠屏,并拧(撕、扭)其肌肉。翠屏大声呼痛,发披,血流,气喘、汗出。——久久,气竭,声嘶。(38)
吴宓在此处所用的语言令人联想到的是性高潮到来、激情亢奋之后的虚脱。其结果是:那原本是体罚的行为,微妙地转化成虐待狂的行为。表面上看来,吴宓是在谴责他祖母“性情反常之表现”。然而,其背后所呼之欲出的,是一种观看着一个赤裸的女体被凌虐那种暧昧的虐待狂的快感。
吴宓在窥视女体以及在满足他那被压抑的凌虐女体的虐待狂——即使是旁观者式的虐待狂——的时候,他还不太敢太放肆。然而,当对象是母骡的时候,吴宓的描述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在他的《吴宓自编年谱》里娓娓地描写他幼年、青春期的时候,对母骡的恋癖。他从小就爱观察骡马,特别是母骡;他陶醉地、巨细无遗地描绘他幼年时与之厮磨的母骡的性器官:“宓与骡马狎,注意其动作(宓幼时之男女性知识,全得之于骡马)。”他十五岁那年暑假乘骡车返家,半路上休息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车上,连车夫也不在。吴宓已经观察那匹青栗色的母骡许久,于是他
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骡用力,以其紧硬之尾骨与肌掩覆肛门。宓用左手握骡尾之中段,向上擎起,得窥见骡之阴部,自肛门下至尿孔,阴毛盛长,谛视甚详。(39)
吴宓迷恋母骡,他在1950年1、2月间,一口气写了六十几首用七律为体裁的《悯骡诗》。这六十几首诗,现仅五首留存。其吟咏的是母骡之美,特别是母骡排泄时的娇羞之美。这几首诗十足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上所说的《恋粪癖》(coprophilia)和《恋尿癖》(urophilia)。但这不是本文处理的重点。与本文的主旨切题的,是其中一首。其所描述的是1910年,他16岁时,一件让他四十年以后还难忘的母骡惊艳的往事。当时新年刚过,吴宓与表兄弟分坐两辆骡车回家。其中一车的“美骡”因右轮陷入石缝中,几乎倾倒。母骡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骡夫的鞭笞即将加身。惊惶失措之下,母骡肛门的刮约肌失控。骡尾上举,大量粪水喷射出来,喷在大表兄的锦袍上。
大祸临身惧犯干,直前力曳岂容啴。黄流下泻阴唇闭,翠点翻飞股露溥。谁取柔巾拭妙处,更因磨摆染鞦鞶。锦袍污损性欣笑,回首方知主厚宽。
吴宓在四十年以后回首这匹母骡“黄流下泻阴唇闭”的事件,他一边遐想那“谁取柔巾拭妙处”的乐趣,一边想像那匹母骡在“锦袍污损惟欣笑”的主人的温柔揩拭之下,必定“回首方知主厚宽。”
吴宓笔下的母骡,就像那可怜的婢女翠屏所代表的所有的赤裸、无助的女体,是被车夫鞭笞、被骡店的公骡性侵犯的对象。虽然他多处描写载重、拖曳的母骡和公骡。然而,在他笔下,被车夫蛮横地鞭笞、落泪,以至于折磨得精疲力尽的都是母骡。于是,母骡等于是吴宓意淫之下的赤裸的女体——“此骡亦美女子身”(40) ——是被男性窥淫、性虐待的受害者。他对母骡的窥视、对其私处栩栩如生的描绘,乃至于对之意淫与爱抚,是一种取代;吴宓对母骡的情痴,看似变态,其实是一种掩饰。换句话说,吴宓其实是用母骡为晃,而肆意地去满足他对赤裸裸的女体及其私处的窥伺、意淫,以及施以性虐待的快感。
与上文提到的三个人相比,胡适在躯体暴露的方面要算是最保守的了。他连赵元任点到为止的暴露都不愿为,更何况是郁达夫或吴宓那种暴露狂了。然而,与胡适对他恋情的隐私守口如瓶的矜持相比,他在躯体的暴露方面就显得放松多了。比如说,他的留学日记在出版的时候,删去了十条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删去他梦遗的一条。他1911年,2月20日的日记写着:“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W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41) 在他后来的日记或书信里,他偶尔也会记下了他其他的病状。比如说,“颈上长小核”、“左脚踝略肿”。他也会作切片式精确地报道的。比如,他晚年写给杨莲升的信里的粉瘤手术:“我背上左上角生了一个粉瘤,已有十年的历史……在台大医院请高天成先生根治,挖出了7.7cm×7.7cm一块肉,可以说是除根了”。(42)
胡适会在他的日记和书信里记载他的身体状况,这可以说是他像李慈铭一样,要“写出先生性情”。同时,我也认为胡适会作出像“挖出了7.7cm×7.7cm一块肉”那样切片式精确的报道,是因为他要科学地、信实地写下人与事发生、发展的经过。最值得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对他的痔疾详尽的报道。在1922、1923年之间,胡适在他的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的痔疾。他报道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所做的诊断和手术;他描写他的脓肿的大小、数目、部位;如何发生、发脓、肿胀、出血的经过;他的粪便的形状、恶臭;以及他所看过的大夫、敷或吃的中药。(43)
胡适不只在日记里写他的痔疾。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会一五一十地也都说给韦莲司听。他跟韦莲司的友谊和恋情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道尽的。(44) 他们在1920年代很少通信,稀疏到了一年只有一两封的程度。他俩的关系一直要到了1930年代初期才发展成为恋人的关系。然而,胡适却能够把一般人可能说不出口的毛病毫不保留地说给她听。他在1923年5月18日给韦莲司的信里,告诉她说他“有两颗名为‘ischio rectal abscess’[肛门脓肿]的脓包。脓包现已破,仍然折磨着我。”(45) 1926年,他的肛门脓肿演变成肛门瘘管,即肛门腺到皮肤之间长出了脓肿发出来的瘘管。他写信告诉韦莲司,说他“刚作了一个手术,把那纠缠了他三年半的肛门瘘管给割除了。”(46)
由于胡适的日记和来往信件都属于公开的领域,他能如此毫不害臊地谈论他的痔疾等于是一种暴露狂。一个最最谨守自己隐私的人,却又能如此毫不遮拦地暴露自己。这个矛盾的理由无它,就在于那是一个对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的时代。这也就是说,胡适这种暴露狂是扮相式的,亦即,他只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演练、重复那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作为一个名人,胡适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包括他生的病。不管是不是他自己主动透露的,他的病情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他1920年患肾炎,由陆仲安中医医好。据说,陆仲安也因此而享大名。(47) 1930年,当郁达夫为痔疾所苦的时候,还特别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告诉他他看的医生的地址。(48) 姑不论郁达夫知道胡适得过痔疾,是胡适亲口告诉他的——胡适1923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之前曾见过郁达夫——还是他听来的,其所反映的事实是,胡适的痔疾不但是广为人所知,也不是他所讳言的。
胡适不只是好谈他肛门的毛病,他根本是对他的肛门有偏执狂。我们如果只念他的《南中日记》,我们就不会知道他除了痔疾以外,还深受脚肿之累。他在这个日记里,只有一、两次轻描淡写的提起他脚肿的情形。与之相对,他在《南中日记》、《山中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和痔疾奋斗的经过。事实上,在他给韦莲司,告诉她他的痔疾的同一封信里,他说:“在这整个月(从四月二十一日到现在)南游途中,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从我一到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被我的脚肿折磨着。”(49)
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胡适对他的肛门的偏执呢?现在胡适档案开放了,我们有机会利用它所提供的大量的资料来从事心理分析。他对他三岁时所失去的父亲恋物癖式的崇拜、他对他母亲的爱与罪恶感——或者其实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反应机制”,亦即反叛与怨怼的潜藏心理假借爱与罪恶感的保护色来呈现——以及他跟江冬秀由媒妁之言所订定的婚姻的天长地久,这些都在在地是典型的心理分析的上好题材。他的肛门偏执也更是典型的弗洛伊德的题材。在本文里,我要采取一个稍稍不同的分析策略。我不要用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而是要试图探讨胡适的肛门偏执跟他的写作焦虑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是从压抑的角度来分析写作的焦虑。根据他的说法,写作的焦虑产生的缘由,是因为写作的器官——即手指——被过度赋予性欲的象征。弗洛伊德用男女交媾来作比喻:“当写作的动作——墨汁从笔管里流泄到白纸上——被赋予男女交媾的意涵的时候……写作……就被打住了,因为它形同于在进行一个禁忌的性行为。”(50)
由于肛门并不是写作的器官,肛门似乎应该不是一个会引起神经性写作焦虑的所在。然而,弗洛伊德对肛门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道,来分析肛门与神经病理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理论把黄金和粪便、金钱与排便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和行为连结在一起。(51) 毫无疑问地,弗洛伊德在此处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肛门型的人具有有条不紊、节俭、固执的性格特色。然而,我们可以引申弗洛伊德把肛门视为性区(erogenous zone)的理论,借以发展一种身体(somatic)经济学。(52) 于是,忍便就意味着储存、节俭、积攒;而排便意味着花钱、卖出、甚或是损失。与本文主旨最为攸关的是:排便的行为,可以被我们的下意识诠释为损失或盈利——亦即,生产以及创作。(53)
这种与创作攸关的肛门身体经济学,会因为本能、矛盾以及“反应机制”等等因素而浮动。我认为我们如果不但把身体视为一个被本身就不稳定的语言系统所型塑的场域,而且也是一个被语言所挪用的场域,一个“作为文字的接受、再生产、再现的肉身脉络(corporeal matrix)的出入口(openings)”的场域,我们就可以想象一种创作的焦虑,那是来自于“所有身体的机能——排便、排尿、精液、月经、声门音、舌音——都混然成为一个浑沌、低迷的汇流(undifferentiated and abject flux)”。(54) 因此,朱丽娅·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会说:“我把我自己排出来、吐出来;我在说我立己的同时也沮(abject)己。”(55) 拉冈(Jacques Lacan)说得更有意味。他说:“那白纸的晕眩……对某人来说,就好像是阻挡所有走向他者之路的障碍物。如果他那排山倒海似的思绪,碰到了白纸却倏然终止,那是因为在他看来,那张白纸根本就是一张厕所纸。”(56)
我们有证据说胡适是属于肛门性格的人。他巨细无遗地搜集、孜孜不倦地保存他的自传档案,特别是保留别人所给他的信件,这些都是典型的特征。他规划每天作息的偏执,在在地表现他为自己所设计的日程表上。这个日程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以一个小时为单位。每一个小时又划有两栏:一栏是“预算”栏;另一栏为“实行”栏。从1919到1920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恒心地在“预算”栏里填写他的计划,如果实行了,他就会在“实行”栏里打勾。(57) 同样有意味的,是他为克己所下的工夫。有关这点,我将在下一节详细分析,但我用的不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比较有揣测性质的,是我对他的写作焦虑的假定。然而,我有理由相信胡适一生未能免于写作的焦虑。大家都知道,《中国哲学史》中下卷,他始终未能完成,那失败的阴影他一直未能摆脱。最有意味的是,他写作的焦虑最强烈的时候,就正是他对他的肛门最有偏执狂的时候。
1921年,商务印书馆希望他能辞去北大教职,而去商务办编辑部。虽然他相信他如果主持商务,他所能造成的影响力会超过他在北大教书,但他还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作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58) 他所谓的自己的事业为何?他在1922年2月23日的日记就提供了答案: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门罗邀请我教授两科,一为中国哲学,一为中国文学。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颇费踌躇。我已决记明年不教书,以全年著书。若去美国,《哲学史》中下卷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学史》罢了。拟辞不去。(59)
胡适是否在次年找到时间写他的哲学史,他在日记里没说——当然没有,因为次年就是他跟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三个月的“神仙生活”的一年。他的日记所透露的,是他对他的肛门脓肿的偏执。
男性的自律、政治与性别关系
如果胡适在自传自述上的作为是源自于中国传统士人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演练出来的约定俗成的传统,其背后的男性观则是中西范畴糅合、反覆演练出来的结果(performative accomplishment)。到了1910年他赴美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九年的私塾教育、四年的初、高中的西式教育。作为一个报坛新秀,他一生所服膺的许多基本人生观已经形成。无怪乎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他那本见解深刻的胡适传里,会说胡适在美国所接受的观念,都是他早期的教育已经为他奠基了的。贾祖麟认为改变了胡适的,并不是新的观念,而是胡适称之为“天生乐观、快乐”的美国民风。乐天的美国民风变化了他的气质,也影响了他引申他的观念的表达方式。(60)
贾祖麟有他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也说美国进步主义的思潮深深地影响了胡适。(61) 同时,贾祖麟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缺点。那就是在他的笔下,胡适仿佛变成了一个静态的人物。事实上,胡适留美时期的变化,以及他回国以后传奇式地崛起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领袖。要了解这一切,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去分析他的男性的扮相。这是因为留美的胡适,他所受到的影响不只是新观念。他的举止、视野甚至他的整个人,跟他的思想观念绝对不只有边缘的关系,而实际上是他的思想与为人所彰显的主要所在。他的男性观不仅是中西糅合的产物,而且是一个持续演进的演练过程。其所反映的,是他在1917年回国以后,中西文化里不同的规约机制(regulatory practices),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牵扯、拉引的矛盾。
最近几年来,学界有一个甚嚣尘上的说法,就是谈论近代中国的男性危机。这所谓的男性的危机有许多不同的根源:传统父权至上的思想和制度死掐着年轻男女不放、传统男性文学的式微,以及那展现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及其化身——摩登女郎身上——的西方的魅力。(62) 由于胡适在他男性的扮相上是如此的平稳和顺遂,我认为这个所谓的男性的危机完全不适用在胡适身上。盛名以及成就,让胡适得以释放出一种悠然自得的自适感,那在近代中国是少见的。
胡适一生中最重要而且也是他最能持之以恒的中西糅合之下的男性理念是克己:禁戒与修身。克己是儒家传统里一个重要的德行。这个德行,胡适得之于他的传统教育,也得之于那克己的典范——他年轻就守寡的母亲。(63) 然而,克己的德行,并没能使传统中国的士人谢绝冶游青楼。青楼艳妓不但是士人宴饮的玩伴,而且是士人赋诗的灵感。才貌双全的艳妓,更是士人用诗文让她们永垂青史的对象。(64) 胡适留学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有过他自称为荒唐的一段。他与友朋们喝酒、赌博、看戏、逛青楼,以至于有一天酒醉殴打警察被捕入狱。(65) 他在留美时期接触到了的进步主义时期的道德运动、19世纪易卜生(Henrik Ibsen)、赫仆特满(Gerhardt Hauptmann),以及白里而(Eugène Brieux)的“问题剧”,使胡适接受到新的克己的道德制约。
这整个过程是渐进的。他那一夜的牢狱经验,除了刺激了他的羞耻之心,使他发奋读书考取了庚款留美以外,还使他很自然地就能接受禁酒的理念。由于他自己已经戒酒,他很快地就变成美国“基督妇女禁酒同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支持者。赫仆特满在《东方未明》(Before Dawn)一剧里所描述的酗酒之害,更使胡适坚定他禁酒的信念。(66) 虽然胡适在回国以后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他在留美时期始终滴酒不沾。他在留美的时候也以不该恣纵的理由而作到了不打牌。(67) 只是,他回国以后又开始打了牌。他留美的时候想戒、可是始终就是戒不掉的,就是抽烟。这—方面反映了美国当时没有什么禁烟的运动。另—方面,这也反映了烟草与男性气概不可分割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校园里男性喜欢举办“烟集”(“smoker”)的作法。胡适一生一再地想戒烟,可是从来就没成功过。
胡适在克己方面作得最为成功的地方是禁嫖。一直到1911年9月,他在美国看到上海的报刊登载了他当年的旧识成为名妓的照片。他当时还显露出缅怀不舍之情。(68) 然而,就在同一个月的月底(69),他就在日记里记他去听了一个有关性病的演讲。(70) 到了1914年初,他已经读到了易卜生的《鬼》(Ghosts)剧以及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这两出剧都生动地描写了梅毒在遗传以及社会上所能造成的可怕的影响。胡适在惊骇之余,在日记里说梅毒:“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71)
在胡适禁嫖思想的巅峰,他发誓他要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他说,只要从禁嫖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中上阶级的道德要远超过中国。(72) 这是他后来中国不如现代西方的理论的滥觞。然而,我必须指出胡适在回国以后,他禁嫖的立场显然松动了许多。不管是因为他好奇还是因为他从众如流,他去一家新开的妓院去探访一个住在那儿的哈佛留学回来的同事唐钺;去逛红灯区;跟几个妓女合照;带一个美国朋友去拜访两个妓女。(73)
胡适能够如此从容自适地来回于两个不同文化的规约机制。这除了证明了文化有惊人规约个人行为的力量以外,也同时显示了胡适在处世方面能把握大处、不拘末微的圆通高明的所在。就以喝酒为例,像胡适这样一位知名的思想界领袖,一定是所有饭局、集会所争相邀请的对象。在这种场合里,喝酒一定是不可免的。胡适回国以后又开始喝酒,江冬秀不喜欢。江冬秀的机智,最痛快淋漓地展现在她与胡适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的一场斗智角力赛之上。那个场合是发生在胡适四十岁的寿辰。胡适的一群朋友假定江冬秀一定狠不下心、不让胡适在寿辰当天喝酒。他们写了一幅典雅的寿辞,描写了一幅美酒如流的宴会图。然而,他们低估了江冬秀的坚毅与机智。在关键时刻,江冬秀出示了她送给胡适的生日礼物。那是一颗刻有“止酒”二字的戒指。江冬秀最高段的地方,在于她把写那幅寿辞的钱玄同派为“证戒人”。(74) 这个“止酒”的戒指固然没有使胡适从此戒酒。然而,胡适后来在不想喝酒的时候,就每每把它祭出来作挡箭牌,帮了他不少的忙。(75)
如果胡适在回国以后,能重新拾起那在克制恣纵方面比较不严格的规约机制,他在品格的锻炼上则毫不放松。他留学当初在日记里所流露出来的在修身方面的焦虑,逐渐转变成为品格的锻炼。品格的锻炼涵蕴了克制恣纵的锻炼。同时,这种更新、更宽广的视野,意味着胡适对品格锻炼有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亦即,公私领域的行为有其相互重叠的所在,不是截然可分的。如果他在这以前的修身的工夫是被动的(reactive),亦即,有了恣纵的行为,才施以克制的功夫。他现在所从事的,则是锻炼他的品格以为公益。同时,这品格又作为他所服膺的理念的基础。以下,我将集中讨论他在品格锻炼上所反映出来的两个最重要的男性理念:修身以及性别关系上的“君子”之风。
作为胡适男性观的基础,克己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如果不是因为他把克己的美德也运用在公的领域上,他这个克己的观念不足为奇了。如果一个人恣纵、不知收束,会捣乱一个人的生活。胡适相信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个人所属的团体里,不管是社会、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就以民族主义为例。虽然胡适承认人们偏爱自己的国家是很自然的,他认为狂热的爱国主义是国际纠纷的根源。(76) 胡适之所以会从1912年到1916年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运动,并不是像历来的研究所说的,是一种徒劳无功(quixotic)、注定是会被国际的现实所粉碎的理想。(77) 其所反映的,是他的一个信念,一个要用理性与道德来规范国际关系的信念。由于历来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不但根本地误解了胡适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态度,他们而且完全不知道他所反对的不是参与政治,而是莽撞无序的政治行为。
胡适从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一个无论如何都拒绝使用武力的人,转变成为一个主张依靠国际组织,用法律、仲裁与武力去维持世界和平的人。这并不像是历来的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转变,而毋宁是他的国际主义观点必然的逻辑结论(78)。(79) 即使在他和平主义的巅峰、根本地反对使用任何武力,即使是自卫,(80) 他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用他喜欢的话来说,道义抵抗主义,仍然包含着权变的因素在内。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跟卢森堡不同的遭遇作为例证。他说,比利时由于抵抗,而惨遭德国的攻击而残破,卢森堡则因为投降而得以瓦全。(81)
1915年1月,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以后,胡适写了那篇受到不公平的奚落的公开投书《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他在那篇投书里的主旨并不是不抵抗,而毋宁是“我们必须要严肃、心如止水、坚定不移地求学。我们必须要卧薪尝胆,以求振兴祖国——如果它能安然渡过这个危机的话。当然,我深信它一定能够;而即令祖国这次不幸而覆亡,我们也要让它从死里复活!”(82) 他在报上读到抵制日货的报道,觉得“可喜”:“吾所谓道义的抵抗之一种也。”(83) 他的和平主义所反对的,不是抵抗,而是武力。对他而言,不抵抗是意味着要卧薪尝胆以振兴中国。
胡适之所以能够超越了他对道义的抵抗的执着,是拜他在1915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跟他学习的杜威之赐。(84) 杜威在《力量与制裁》(Force and Coercion)一文里说:力量“所意味的,不外乎是让我们达成目的的诸条件的总和。任何政治或法律的理论,如果因为力量是残暴的、不道德的,就拒绝去处理它,就会落入了感情用事、冥想的窠臼”。(85)他说:“由于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用力量来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任何在政治、国际、法律、经济上借助力量来达成目的政策或行动……衡量这些行动的标准,在于这些工具在达成目的的效率及其所用的力量的多寡。”(86)
胡适对杜威五体投地地佩服。这一点在在地显示在他1916年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的征文比赛的得奖论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我们只要引胡适在这篇论文里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如何挪用杜威的观点:“解决问题之道,在于统合各国的力量,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87) 于是,杜威的一个假设,到了胡适手里,变成了一个公理。经济与效力,是杜威用来认可使用武力的标准。到了胡适手上,它们变成了各国的力量如果统合起来就可以达到的理想情况。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胡适所希冀的,是一个能够仲裁纠纷、用武力制裁的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不但是一个维持和平的工具,而且还是一个培养超越国界的国际公民观的媒介。
跟本文的主旨更切题的,是胡适把国家的行为与个人的行为类比,而且,两者都必须接受法治的看法。他认为国际社会可以从人类演化的历史学到教训:“从野蛮无序的状况演进到文明法治的政府。”法治的做法应该同样地运用到国际事务上,以便使各国的行为都有“必须遵循的义务,尊重他国的权利。这可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因为这同样也会克制他国侵略之心”。(88) 胡适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尊重法律。他征引杜威,说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89)
胡适的国际法治观念,反映的就是他理性与道德必须胜过狂热与暴力的信念,亦即,把克己的德行扩大运用到国际社会。历来的学者之所以会根本地误解胡适对政治参与的看法,就在于他们没有把握住胡适的克己的概念。(90) 胡适绝对不反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最好的例证,就是胡适认为美国的世界学生会应该投身参与国际和平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学生会里,胡适是属于他名之为“前进派”的领袖。前进派力战那认为世界和平属于政治问题、而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的保守派。这个保守派虽然是少数派,但声量不小。胡适说世界学生联合会1915年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召开年会,他在该年会上的致辞,是他对“非政治派”所下的一份“哀的米敦书”,即最后通牒。他在日记里踌躇满志地说,他以议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打败了保守派,让前进派所提出的议案一一通过。(91)
胡适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历来的学者说胡适看到他的老师杜威去参加争取妇女参政权的示威活动,大不以为然。其实,那是误解了胡适的意思。胡适在感动之余,明明是在《留学日记》里说:“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92) 他们却把这个感叹句错读成批判句,变成了:“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93)
胡适所反对的,不是政治参与,而是参与政治的方式。就以他对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为例。1915年10月23日,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团体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游行让他看得肃然起敬。他在日记里慨叹,说那是:“千古未有之大盛举”,“秩序之整肃”,“与游之人,固属少年男女居多(西人四十以下皆为少年),而中年以上妇女亦不少。头发全白者亦有之,望之真令人肃然起敬。”(94) 与之对比的,他在回国以后讲演美国妇女的一个演讲里,就叱责中国争取妇女参政权者的做法。他说她们东施效颦,学英国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暴力、令人齿冷的行径。(95)
历来学者说胡适反对学生运动的说法也同样是错误的。(96) 他所反对的与其说是他们干预政治,不如说是他们的行为缺乏秩序。毫无疑问地,胡适认为学生的责任是在读书。这是他从留学时期就已经有了的立场。然而,我们从他自己参与国际和平主义运动,以及他对杜威参与美国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的感佩,就可以知道他绝对不反对为政治理想而奋斗。1921年,胡适在安庆的第一师范演讲。他在表明他的遗憾,说“在变态的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他接着立下了他的理想的罢课行动纲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用代表制来代群众运动,且须用轮任法,代表每月改选五分之二,以均劳逸,且可多练人才。(97) 胡适的精英主义暂且不论,这个罢课行动纲领所在在显示的,是胡适坚持学生运动必须是由理性与秩序来领导的。就正因为狂热与暴力是他厌恶群众运动的所在,他才会要用代表制把参与的人数减到最低,以避免他们产生团队精神。
与胡适克己的观念息息相关的,是他在性别关系里的“君子”之风的理念。这是胡适男性观的核心,是最不为人们所了解的。“gentleman”(君子),这个字眼是胡适自己用的。君子的行为表现在他对女性的态度,特别是他对待他已聘的女子的态度上。他跟江冬秀的婚姻就是他这个男性理想最可堪玩味的一个例子。江冬秀没受过正式的教育,一直到20岁才放足。在我们分析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以前,我们先讨论他对三个婚姻的看法。那可以更凸显出问题的核心。
胡适所讨论的第一个婚姻是罗素。罗素是胡适留美时期,和平主义信仰最坚强的时候所崇拜的一个人。然而,到了罗素在1921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胡适对他的观感已经大为改观。胡适对罗素的观感改变,这跟罗素批判西方文明、建议中国采行国家社会主义有关。(98) 然而,这也跟他觉得罗素对他的妻子不能有君子之风是有关的。罗素到中国来旅行的时候,陪伴着他的是朵拉·勃拉克(Dora Black)。当时,罗素在名义上还跟爱丽司·史密斯(Alys Smith)还是夫妻。胡适1921年6月30日的日记,明显地是在批评罗素:
罗素先生前娶之夫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美国女子,罗素二十年前著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时,于序中极夸许他,又附录他的一篇文章。现在罗素把他丢了,此次与勃拉克女士同出游,实行同居的生活。他的夫人在英国法庭起诉,请求离婚,上月已判决离异了。(99)
同样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对康乃尔大学铁道工程教授克蓝德尔(Charles Crandall,1850-1917)的婚姻的评论。1923年5月底,他在杭州养病的时候,接到了陈衡哲的一封信。陈衡哲在信里,提起她作了一篇小说,用的材料是瓦莎学院(Vassar College)的娃须本教授(Margaret Washburn,1871-1939)和康乃尔大学的提区纳教授(Edward Tichener,1867-1927)之间的恋爱故事。这就是陈衡哲1928年发表的那篇《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的由来。陈衡哲在信上说:“你何不也用这个题目作一篇呢?我的题目是Prof.Tichener[提区纳教授]and Prof.Washburn[娃须本教授]的事。事情的大纲属于他们,但细目尽可自由创造。我的主旨是妇女的出身问题。你如能做一篇,狠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一样的材料的不同用法,这是很有趣的。”胡适的答复可能是陈衡哲所意想不到的:
我也想试做一篇,但拟用他们二人之外,还加入Cornell[康乃尔]的Prof.Crandall[克蓝德尔教授]的事。此君订婚之后,尚未结婚,而女子病了,病中把双目都瞎了。伊就请求他解除婚约。他坚持不肯;他们竞结婚了。这位夫人虽是瞎子,但绮色佳的人没有人不敬爱伊。他们生的子女也都很好。(100)
胡适第一次听到克蓝德尔的故事是1915年他还在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他在日记里称之为:“西方之信义也。以其可风。故记之。”(101) 他所要表彰克蓝德尔教授的地方,显然在于他在他的未婚妻失明以后,他还能坚持信守他的婚约。
最后一个例子是胡适对威尔逊总统第二个婚姻的评论。这充分地显示出胡适认为对婚姻的信守,可以是公德与私德相交的环节。1916年美国总统威尔逊竞选连任的时候,有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投威尔逊的票。他们的理由是,威尔逊总统在他妻子过世四个月就再婚。胡适是威尔逊的支持者,他听不进人们说威尔逊沉溺于女色的批评。他说这种思想是狭陋的清教徒主义。他说:
余非谓政治公仆不当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别。如贪赃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恶,国人所当疾视者也。又如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倖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国人鄙之可也。至于妻死再娶之迟早,则非他人所当问也。(102)
这段引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适把君子对婚约的信守当成公德的一部分。他1915年10月3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也表现了这一点。他在这封家信里,首先澄清了他已经在美国跟别人结了婚的谣言。他说他“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他说:
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103)
胡适对他的婚约要信守,这除了是因为他要考虑到社会的制裁以外,还更因为那违背了他男性的君子、骑士之风。1921年8月30日的一则日记,是胡适对他的婚姻所作的一个最详尽的反省。在这则日记里,胡适描述了他跟江冬秀结婚以前的一个危机。那个危机能得以化解,完全是因为他所具有的男性的美德。1917年8月,在他们结婚之前的四个月前,胡适要求到江村和江冬秀见个面。没想到虽然江家的人都已经同意了,等胡适到了江家,江冬秀却躲到床上,连床帐都放了下来。就在江冬秀的姑婆要出手强拉开床帐的时候,胡适摇手阻住,退了出来。过后,胡适不但若无其事地留在江家过夜,而且在第二天临走以前写了一封信给江冬秀,说强迫和她见面是他的错。事后,胡适庆幸他当时还够机敏。江冬秀不得不拒不见面,那是传统约定俗成的礼俗使她必须作出的女性的扮相。胡适的结论是:
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gentleman[君子]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104)
姑不论胡适说:“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这是不是指他在此以前,对他的婚约曾有过无意“矜持”的时候。重点是:他在此处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君子”宽大体谅未婚妻的形象。殊不知他当时所作的要求,如果她照做了,会为她招惹来不要脸的罪名。
胡适的婚姻一直是人们窥伺和尖酸刻薄揣测的题材。他们完全不能体会胡适之所以决定信守他的婚姻,是因为那跟他的男性观的理想是息息相关的。历来论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的人,多半为胡适惋惜。夏志清甚至用“悲剧”这两个字来形容,说江冬秀“没有现代医药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105) 周质平也用相当重的话来形容胡适的婚姻,说他常“觉得胡适成婚那一刻的心情,与其说是洞房花烛的喜悦,不如说是烈士就义之前一种成仁的悲壮情怀”。他认为胡适对他的婚姻,是经过了一番自我说服的功夫,而达到了“近乎自我欺瞒的境界”。(106)
这些自命为是替胡适打抱不平的人,他们的共同点还不只在于男性同仇敌忾式地、忿忿然为胡适是鲜花插牛粪的颠倒版的牺牲者而感到不平。他们还同时把胡适的公与私的领域判然划分成二,而把胡适的婚姻放在他的私的领域。在这种理论框架之下,由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她所赐予的”(107) 的亏欠的心理——胡适就仿佛像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样,他在他的私的领域里所甘心匍匐的传统,就正是他在公的领域里号召全国的青年人去打倒的。
这些胡适的恻隐者完全弄错了胡适挣扎的所在。胡适要不要信守他的婚约,症结点在于他的男性气概,他的君子之风的维持。这点他们完全没把握到。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公与私的二分法之下,他们把胡适的这个挣扎放在他的私领域里,仿佛这与他在公领域的行为是毫不相干的一样。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去揣度别人婚姻的品质。也许胡适心灵的伴侣确实不是他的妻子。然而,胡适在他的婚姻里所欠缺的,他在婚外情里得到了补偿。这些婚外情,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两个,(108) 他跟韦莲司在1930年代的远距恋情虽然对韦莲司来说是翻天覆地、刻骨铭心的,却从没真正触及胡适罗曼蒂克的心髓。他1923年跟曹诚英的恋情则显然不同。他因为爱曹诚英而想跟江冬秀离婚。然而,他很快地就死了这条心。据说他那精悍的妻子拿起菜刀威胁要把两个儿子跟自己杀掉。(109)
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的婚姻远比外人想象的要满意,而且有意味。当然,胡适在演练他的男性的君子、骑士的理想的过程当中,不是不可能对他媒妁之言的婚姻有过踌躇、失望甚至拒斥。他1918年5月2日,也就是他结婚不到五个月以后,写给他极亲近的叔叔胡祥木的一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这封信他要他的叔叔看过以后烧掉,可是他的叔叔没照做。这是所有认为胡适婚姻不美满的人一定会征引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胡适把他对他的婚事的苦水全都给吐露出来了: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110)
然而,这并不表示胡适不可能跟他的妻子产生亲密的关系。他在新婚燕尔两个月以后写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胡适用了传统旧诗里宫女倚栏盼君的意象,来比喻江冬秀等待郎君回国跟她结婚的心情。然而,胡适这首诗里的意象有一个不同的转折。传统旧诗里的宫女的命运常是成为白头宫女,只能落得回首诉说前朝往事的命运。他的未婚妻则终于盼到郎君回国跟她成婚。胡适与江冬秀固然等了十年才成婚。然而,他们这一对年岁稍长了的新郎、新娘,却像陈年的爆竹,“越陈偏越响”。这首引人遐想的诗云: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呵,
越陈偏越响!(111)
胡适深得品诗的三昧。他对中、英诗的写作与品评都游刃有余。隐语、暗示和双关语是他精擅之所在。“爆竹”的“响”、“烈”、火花与神魂荡漾,其所描述的是他新婚燕尔的欢愉。胡适在这首诗里其实是在试探、挑拨他的读者。他装佯故作不知他爆竹“越陈偏越响”的情色挑逗意味(eroticism)。熟知胡适的徐志摩说:“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112) 胡适在这首诗前加了一个序:“吾本不欲用爆竹,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不忍不用之。”(113) 俗话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信然。
新婚以后单独住在北京的胡适相思想念他的新娘子。胡适听说江冬秀的哥哥五月要去北京,就希望她能跟着去北京和他团圆。等到他知道他母亲有点为难以后,胡适明白地告诉他母亲他的失望:“我在外面独立了十几年了,难道不能再耐几个月无家的生活吗?”(114) 后来他知道他母亲改变了主意,他很高兴地回信说:“我岂不知吾母此时病体不应令冬秀远离,但我在此亦很寂寞,极想冬秀能来。此亦人情之常,想吾母定不怪我不孝也。至于他人说长说短,我是不管的。”(115) 这种想要跟他的新娘子团圆的渴望,跟他写给叔叔胡祥木的那封信形成强烈的对比。更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他写给他叔叔、大家都说是道尽心底话的那封信的前五天,他写了一封以胡适的风格来说,相当缠绵的信给江冬秀:
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农历],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道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
……
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116)
这封信有隐语、有暗示,有只有胡适和江冬秀知道的亲密的纪念和回忆;不像是一个奉母命结婚,而对妻子没有一丝爱意的人写的一封信。五天之间写出两封如此迥异的信,是颇令人惊讶的。其所反映的,是胡适媒妁之言的婚姻所带给他的痛苦、矛盾与挣扎。然而,除非他言不由衷,新婚甫四个月的他,对江冬秀有他的相思,对他们新婚之夜有他的纪念与眷恋。6月11日,江冬秀抵北京。一个半月以后,她就怀孕了。
不管胡适对他的新娘子感觉如何,他已经是接受了与她结婚的事实。他老早就已经说服自己,说婚姻就意味着妥协。他在1914年的一则日记有一段他跟康乃尔大学一个房友的谈话,历历地表达了他对女性、择伴和婚姻的看法:
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不勉强迁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谓此邦女子至是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偶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偶,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D.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为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117)
表面上看来,胡适仿佛在寻找心灵的伴侣方面是把妻子放在朋友之前,但实际的次序其实可能刚好是相反的。我认为即使胡适娶的妻子不是江冬秀,他知识上的伴侣还主要还会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由于胡适受到了美国19世纪“纯美的女性”崇拜(cult of true womanhood)的影响,他认为女性应有其特有的温婉、柔顺与纯洁美德。他在1914年6月8日的日记里就勉励自己:“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118
尽管胡适会使用“纯美的女性”的陈词套语,“女性”也同时是他用来作比喻,形容没人要、既势利又没种、或咬舌撞墙式的人或做法。比如说,他在1921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丁文江在北京饭店和威廉·克娄杰(William Crozier)将军的一段话:
Crozier责怪我们知识阶级的人何以不鼓吹舆论,使政府不能不利用新银行团来筑造铁路。我们把现在的情形告诉他,并说,政府决不肯向银行团借这种于他们无利益的款,即使政府肯做,国民也要反对。现在银行团若希望政府来提议,我们可以断定银行团决无事可做,譬如待嫁女子,无人求婚,终必作“老女”以死。我又说,新银行团若不求作“老女”,只有一条路:须先使中国资本家组织铁路公司,向银行团借款,承认他们的条件,如公共监督用途之类。若无这样一个有信用的求婚者,银行团必不能免“终身老女”的命运。(119)
同年6月,北京各大学代表因政府积欠教育经费请愿,被卫兵刺伤。几天以后,他和蒋梦麟有这么一段对话:
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120)
当胡适听说受伤的北大教授马叙伦在医院里绝食的时候,他说:
其实这是无益之举。当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实行示威时,英国政府也用严厉手段对付他们,逮捕多人入狱,入狱之女子多实行绝粒,谓之Hunger Strike[绝食],政府大窘。大战之后,各国政府作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妇人的把戏了,故去年爱尔兰革命领袖有绝粒而竟死于狱中者,英国政府亦因此少减其严厉手段。何况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呢?(121)
胡适会把“女性”作为没人要、既势利又没种、或咬舌撞墙式的人或做法的比喻,其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套用俗话的问题。在这些传神妙喻的背后所层层积累的,是一些几乎天经地义的对女性的看法。胡适在1914年6月20日的日记里,记他第一次参观美国的婚礼。他叙述到牧师带领新郎朗诵他的誓词的时候,他说:“牧师以环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为妻,誓爱之养之(to love and cherish)’。”(122) 胡适把“to cherish”翻成“养之”,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翻译失当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以“养之”来和“爱之”对称。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美国这两个同样地认定男人的责任在养家,而女人的天职在持家的经济、文化体系里成长、受教育、从事男性的扮相的胡适,会用“养之”来翻译新郎对新娘的誓词。更重要的,是新郎对新娘“爱之养之”,在在体现了胡适的男性的扮相的理想,亦即,男性对女性应有的骑士、君子之风。可惜胡适在叙述新娘朗诵她的誓词的时候,并没有重复这一段誓词,他只说新娘的誓词,“其词略同上”。我们因此不知道胡适会用哪一个字,来翻译新娘对新郎所说的“to cherish”;然而,根据我们对胡适的男性的扮相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他会用“养之”这个字眼。
女性不但应该是被有君子、骑士之风的男性“养之”的对象,她们还注定要被生理的缺陷所局限。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同年,她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并和任鸿隽结婚。陈衡哲任教北大不久,就因为怀孕而辞职。1921年9月,胡适去探望产后的陈衡哲,他在日记里写着:
去看莎菲,见着他的女儿,名荷儿。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123)
胡适会把女性会怀孕的事实看成是“天然的一种缺陷”,自然是相当令人惊异的论断。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认为女性的缺陷,不只在于会怀孕,而且还及于心智,也就是说,在心智上比男性差。1922年4月19日,他在北大替美国节育运动专家山格(Margaret Sanger)夫人作翻译。当晚,他在日记里说:
下午,山格夫人(Mrs.Sanger)在大学讲演“生育裁制”,我替他译述,听者约二千人,他的演说力甚好。女子演说甚少他这样的有条理层次。(124)
胡适用他那宽广仁慈的男性观,来对女性不幸被她的心理、生理与智力所局限表达他同情的时候,他的态度诚然是居高临下的(condescension)。然而,在近代中国,对女性的解放、平等与教育的鼓吹,他可以算是第一人。从他在日记以及在这方面所发表的文字来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心。(125)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表面来看胡适的性别论述。就像周明之所指出的,在胡适有关婚姻——希望与牢笼——的作品里,所有的女主角最终都获得“自由”,不管是用“出走”私奔的方式,还是以死作为解脱。相对的,婚姻对男人来说却永远是一个死牢(death trap)。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单身的自由,也不能狠下心来用私奔、离婚、或遗弃的方式来了之”。(126)
对周明之来说,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的过度补偿机制(overcompensation)与投射(projection),虽然周明之并没用这些字眼。然而,我认为这一切所显示的,不外乎是胡适君子、骑士之风的男性的扮相。男女因应他们的命运的方式,因其性别而有别。女性如果觉得她的婚姻不理想,她大可以找出口逃生。然而,像胡适这样一个君子、骑士,他的命运就必须是与他的婚姻与共。如果他那艘婚姻之船沉了,他也就必须像船长一样,与之共沉海底。这是因为胡适是男性,而那是男性的责任去引领一个最好的世界,以便女性和孩童们都能被“爱之养之”。胡适对他一个美国朋友说过一段话。其辞极其壮烈与悲怆:
如果我们要领导,我们就必须匍匐于传统。我们属于一个过渡的世代,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父母和下一代牺牲。除非我们想失去所有的影响力,我们就必须听从父母之命,跟他们所替我们所选、我们前所未见的女子结婚。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去创造一个比较快乐、健康的社会。那就是我们的补偿、我们的慰藉。(127)
三十多年前,贾祖麟出版了他那本杰出的《胡适传》。在该书的结尾,他作了一个沉思。他说如果有人能把胡适和他生命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拿来作心理分析,一定可以得出一些挑拨人的结论。(128) 然而,他自己却裹足不前。理由是没有“足够透露真情”的资料。然而,贾祖麟所担心的,与其说是资料不够,不如说是他在方法论与客观性方面的顾虑。他唯恐如果他“进入了主人翁内心最深的世界”,他就可能太与主人翁认同而变得不客观了。(129) 贾祖麟最后还是讨论了胡适生命中的女性,但他把他的想法放在附录里。这种做法,是把公与私当成两个判然若分的领域。这种做法,就是把胡适的私生活放在一个“私密的领域”(sequestered realm),与他在思想与政治上的扮相没有丝毫的关联。贾祖麟当初叹惋资料不够,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1980年代晚期以后,中国内地和台湾内地所出版的有关胡适的传记资料有如雨后春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42册的《胡适遗稿和密藏书信》。三十多年前,贾祖麟踌躇不前,不敢走进胡适的内心世界。要打破这个顾忌,此其时也!贾祖麟把胡适公与私的领域截然划分成二。打破这个二分法,此其时也!
眼前浩瀚的胡适传记资料对胡适传的撰写提供了机会和挑战。本文只不过是我望洋兴叹之下的腼腆一试。我在本文里强调胡适的举手投足(manner)、他的视野、他的整个人格的流露(persona),都是他的整个思想特质彰显的场域。胡适如何演练他男性的扮相,胡适如何在他“知识男性的场合圈”里拿捏他公与私的分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角度来观察他如何作为丈夫、男人以及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巨星。我们不了解他在私领域的为人,就不可能了解他在公领域的为人。他那理性、克己、公平的男性理想表现在他处理婚姻的态度,也同样地表现在他在公领域的所作所为。我在本文分析胡适的男性的扮相,不但可以纠正历来认为胡适厌恶政治的误解,也可以提供一个更宽广、更细致的分析工具来探讨他的自由主义与性别哲学的局限和矛盾。
茱蒂司·卫尔特(Judith Wilt)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批判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见与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130) 胡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就是说,性别平等云云的说法大可以是建立在男性中心(phallocentric)论之上。最后,我们研究胡适的“知识男性的唱和圈”——他如何经营、成员为何、成员的变化——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资料,去了解他一生中所提出、奠定的研究议题、方法论以及文风。
作者注:本文原发表于美国《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3.2,May 2004:p.305-332。我翻译这篇英文旧作,有两点与原文稍有不同。第一,有几段引文,我在英文版里是用译述的方式,现在就把原文全部引出。第二,我撰写英文版的时候,《胡适全集》以及联经版的《胡适日记全集》都尚未出版。现在,为了读者征引查对的方便,都一律把注释里相关的出处改用这两个全集。
注释:
① Juda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Routledge,1990,p.140.
② Sidonie Smith,"Performativity,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Resistance," a/b:Auto/Biography Studies,10:1,1995,p.17-21.
③ 本文“知识男性的唱和圈”的概念是来自于崔芙·柏络顿(Trey Broughton)。请参阅Trey Broughton,"Men of Letters,Writing Lives: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Routledge,1999,p.21.
④ 比如说,余英时就曾用唱和这个观念来描述胡适与杨联升之间的来往关系。
⑤ 韦莲司与胡适的来往信件分别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韦莲司给胡适的信则藏在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由于叶维丽(Weili Ye)没有机会利用这两个档案馆所藏的信件,她对胡适与韦莲司的恋情的描述虽然颇为得体,但仍有许多错误。比如说,胡适留美归国以后再与韦莲司重逢的时间以及他俩之间关系的演变。请参阅她的"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82-90。又请参阅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中文这方面的文献不胜枚举。具有代表性的有《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0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202页;郭宛(沈卫威):《胡适:灵与肉之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周质平:《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丛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7-184页、《吹不散的心头人影——记胡适与曹佩声的一段恋情》,《胡适丛论》,第231-251页、《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最近的一篇是云之(耿云志):《恋情与理性读徐芳给胡适的信》,《近代中国》,2002年2月25日第147期,第128-157页.
⑦ Jerome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⑧ C.T.Hsia,"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Laurence 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lfornia Press,1971; 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⑨ 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⑩ Steve Dillon,"Victorian Interior,"MLQ: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2.2(June,2001),p.83-115;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1),p.32-33.
(11) 任鸿雋的太太陈衡哲以及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是最明显的例子。
(12) 胡适致江冬秀,1918年3月13日,《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3页。
(13) Jessica Kross,"Mansions,Men,Women,and the Creation of Multiple Publ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North America."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33,1999.2:385-408.
(14) 胡适致江冬秀,《胡适全集》第23卷,第493、564、569页。
(15)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101页。
(16) 章希吕:《章希吕日记》,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8页。
(17) 请参阅下列胡适给江冬秀的信,《胡适全集》,1937年11月29日,第367-368页;1939年4月23日,第437-439页;1939年6月25日,第3450-3452页;以及1940年7月30日,第519-520页。
(18) 这就是今天保存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
(19) 胡适:《重印自序》;《自序》,《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11页。
(20)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237页。
(21)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3页。
(22) Lynn Bloom,"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in Suzanne Bunkers and Cynthia Huff,eds.,"Inscribing The Daily: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6,p.25.
(23)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154-157页。
(24) 《胡适日记全集》第7卷,第397页。
(25)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5页。
(26)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674页。
(27) 我现在的解释与此不同,参见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28)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90年版。
(29) 《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第111页。
(30)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第4册,《日记·书信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31)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第4册,《日记·书信集》,第17页。
(32) 《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第329页。
(33) 《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第209页。
(34) Trev Broughton,"Men of Letters,Writing Lives: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p.61.
(35) Yuen Ren Chao,"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First 30 Years,1892-1921",in Vol.2,"Life with Chaos: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Ithaca,N.Y.:Spoken.Language Services,Inc.,1975,p.59,68.
(36) 郁达夫:《郁达夫日记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37) 《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1999年版,第1页开始,多页。
(38)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页。
(39)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80页。
(40)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56页。
(41)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121页。
(42) 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43) 记载的日记条目不胜枚举,请参阅《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668-702页;第4卷,第41-58页,第92-93页。
(44) 有关胡适与韦莲司的恋情,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45) 胡适致韦莲司,1923年5月18日,《胡适全集》第40卷,第220页。
(46) 胡适致韦莲司,1926年4月17日,《胡适全集》第40卷,第228页。
(47) 罗尔纲:《名医陆仲安》,《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3-110页。
(48) 郁达夫:《郁达夫日记集》,第256页。
(49) 胡适致韦莲司,1923年5月18日,《胡适全集》第40卷,第220页。
(50) Sigmund Freud,"Inhibitions,Symptoms and Anxie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et al.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9,p.20:90.
(51) Sigmund Freud,"Inhibitions,Symptoms and Anxie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9:167-75.
(52) Ernest Bornemann,"Introduction: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edited by Ernest Bornemann,New York:Urizen Books,1976,p.31-44.
(53) Ernest Bornemann,"Introduction: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p.41.
(54) Calvin Thomas,Male Matters:Masculinity,Anxiety,and the Male Body on the Line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6,p.29-30,32.
(55) Calvin Thomas,Male Matters,p.33; Julia Kristeva,Powers of Horror:An Essay on Abjection,translated by Leon S.Roudiez,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3.
(56) Calvin Thomas,Male Matters,p.33,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NewYork:Norton,1978,p.268-69.
(57)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549-760页。
(58)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4页。
(59)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445页。
(60)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44.
(61)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43.
(62) Ching-kiu Stephen Chan,"The Language of Despair: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ew Woman' by May Fourth Writers,"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edited by Tani Barlow,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3-32; Shu-mei Shih,"Gender,Race,and Semicolonialism:Liu Na'ou's Urban Shanghai Landscap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1996,p.934-956; Wendy Larson,"The Self Loving the Self:Men and Connoisseurship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A Reader,edited by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Wasserstro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75-193.
(63)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8-16; Hu Shih,"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Vol.II,compiled by Chou Chih-p'ing (Taipei:Yuanliu).
(64) Timothy 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29-31.
(65)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34.
(66)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410、492页。
(67)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177页。
(68)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176页。
(69) 注:误。是1912年的9月29日
(70)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200页。有关美国的社会卫生运动,请参阅John 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4,March,1973.
(71)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279-281页。
(72)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344-345页。
(73) 《胡适日记全集》第6卷,第304-305、647、864页;Ming-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236-82.
(74) 杨天石:《钱玄同与胡适》,李又宁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89页。
(75) 《胡适日记全集》第6卷,第474页。
(76)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521-522页。
(77)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52-71; Ming-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p.83-106.
(78) 请注意:我现在认同胡适以及这些学者的看法,认为这确实是一个转变。请参见拙著《舍我其谁:胡适》第l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428-433页。
(79)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59-60 and Ming-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92.胡适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种转变。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63页。
(80) Suh Hu,"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0.7,April,1915,p.425-426.
(81)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524-525页。
(82) Suh Hu,"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0.7,April,1915,p.425.
(83)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97页。
(84) 我现在要加上安吉尔(Norman Angell),参见拙著《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428-433页。
(85) John Dewey,"Force and Coerc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26.3,April,1916,p.361.
(86) John Dewey,"Force and Coercion," p.364.
(87) Sub Hu,"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Vol.I,compiled by Chou Chih-p' ing ,Taipei:Yuanliu.
(88) Suh Hu,"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67-68. (89) Suh Hu,"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67.
(90)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p.53-54; Ming-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107-09.
(91)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7-9页。
(92)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247页。
(93)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54; 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108.
(94)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245-246页。
(95) 胡适:《美国的妇人》,《胡适文存》第4册,第50页。
(96)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54,249-50,255-57; 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138-42.
(97)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56页。
(98)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The Century Co.,1922; Suzanne Ogden,“The Sage in the Inkpot: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6.4,1982,p.529-600.
(99)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100) 本段有关陈衡哲和胡适的信件来往,都引自《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第55-56页。
(101) 《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第162页。
(102) 《胡适日记全集》第12卷,第444-445页。
(103) 胡适禀母亲,1915年10月3151,《胡适全集》第23卷,第91-92页。
(104)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98-299页。
(105) 《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0页。
(106) 周质平,《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丛论》,第168-170页。
(107) 胡适致韦莲司,1914年11月2日,《胡适全集》第40卷,第5页。
(108) 其实更多,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
(109)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38-40,49页;郭宛:《胡适:灵与肉之间》,第241-243页。
(110) 胡适致胡近仁,1918年5月2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203页。
(111) 胡适:《新婚杂诗》,《胡适全集》第10卷,第79页。
(112)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第4册,《日记书信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13) 胡适:《新婚杂诗》,《胡适全集》第10卷,第78页。
(114) 胡适禀母亲,1918年4月3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91页。
(115) 胡适禀母亲,1918年4月13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98-199页。
(116) 胡适致江冬秀,1918年3月17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845页。
(117)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552页。
(118)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330页。
(119)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55页。
(120)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106页。
(121)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107-108页。
(122)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341页。
(123)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310-311页。
(124)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523页。
(125) 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65,74-76.
(126) 同上,第76页。
(127) quoted in 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80.
(128) 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p.351.
(129) C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ix.
(130) Judith Wilt,"Recent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 Nineteenth Century 35.4,Autumn,1995,p.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