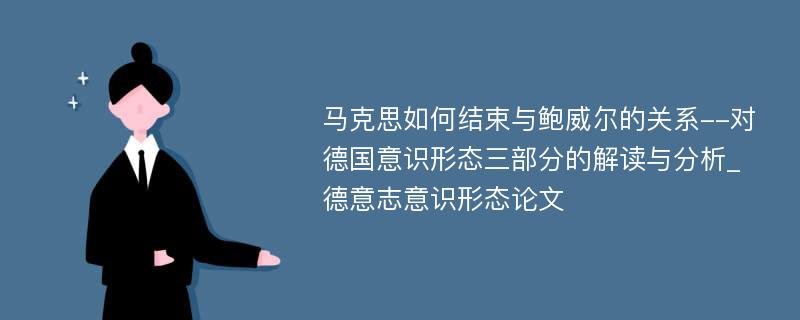
马克思是怎样了断与鲍威尔的思想关系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三个片段的解读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鲍威尔论文,德意志论文,马克思论文,是怎样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7)03—0044—05
本文撷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了断他与布鲁诺·鲍威尔思想关系的三个片段。即作为这一著述“先行稿”的《对布鲁诺-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统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两章的《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和归属《圣布鲁诺》章的《与“莫·赫斯”的诀别》① 进行解读和分析,意在甄别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问题的逻辑和方式,把握其进行思想论战的特征和思路。
一、鲍威尔的反批评依据的是什么材料
《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回应《维干德季刊》(Wigandl's Vierteliahrssehift)②第3期上鲍威尔所写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原先并没有写作大部头著作的设想,因此只写了一篇短评作,这就是后来刊登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第2卷第7期上的《对布鲁诺·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这可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写作之前的“先行稿”,它没有被收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通行本中,但马克思后来写作的批判鲍威尔的部分(《圣布鲁诺》)并不能替代这一短评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它作为马克思了断与鲍威尔关系的组成部分首先进行解读和分析。
这篇短评,对鲍威尔所写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涉及《神圣家族》的有关论述的反驳,主要集中在揭露其所引证的材料的不实上。
从马克思、恩格斯首度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问世,到同年10月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作出回应,这期间只有5月出版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月刊上匿名发表的一篇评论和6月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期上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等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观点的文章涉及到《神圣家族》。也就是说,在这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并没有引起鲍威尔等人对自己原有观点的反思。因此,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鲍威尔声称恩格斯和马克思对他不理解,特别是认为《神圣家族》中的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不明白他提出的诸如“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等警句和论断的真正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短评中集中指出,鲍威尔回答的症结在于他“不以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而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5月号第208页及以下各页)所载的对这本书的平庸而混乱的评论作为他感叹和引证的对象”[1]364。这使得他的回应不仅“结结巴巴”,而且相当荒唐。
具体说来,鲍威尔的做法是先“把(《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编造的东西抄下来”,把它们作为《神圣家族》中的主要思想,“强加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然后据此作出自己的评论和回应。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的文章只是“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1]365。这表明,鲍威尔用以反批评的基础和依据本身就是错误的、不靠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逐字逐句”比较了三组材料。
第一组材料指出,《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用极为简单的语言概括了《神圣家族》对鲍威尔的指责,但这些概括都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始思想。比如,认为为了消灭犹太人,鲍威尔把马克思等人变成“神学家”,还认为鲍威尔把政治解放的问题变成了人类解放的问题;为了消除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他又用作为其学生的老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辛利克斯的思想解释黑格尔:“为了摆脱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费尔巴哈”这些世俗事件、事物和思想,鲍威尔一再申讨和指责群众;为了赞美精神,就把群众钉在十字架上,还认为真正的精神就是鲍威尔自己的批判,就是绝对观念在其身上的真实体现,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地列出他们在《神圣家族》中论述这些问题的出处,对比之后就可以看出,“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给这些论述作了一个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概括”。而鲍威尔对此全然没有判断,在回应文章中“一整段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逐字逐句抄来了”这些“在《神圣家族》中根本找不到的话”,用“建设和破坏”的巧妙手法强加于原著。[1]365—366
第二组材料谈到的是在《神圣家族》中曾有一节内容专门论及鲍威尔的“自我申辩”③,《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说鲍威尔打算用庸俗的自我礼赞来证明,凡是在他过去受群众的偏见束缚的地方,这种束缚都只不过是批判所必需的外表,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对鲍威尔的这种说法,马克思答应写“烦琐的论文”《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玛利亚怀了孕?》来予以回答。循此,鲍威尔在回应文章中就相信马克思是愿写此文“来回答这种庸俗的自我礼赞”的。但是,只要查阅一下《神圣家族》中的那一节,就会发现“在那里烦琐的论文连影子都没有,因此根本谈不上象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所臆想的那样,用它去回答布鲁诺·鲍威尔的”,而鲍威尔却把这些当作《神圣家族》中的论述抄下来,甚至把有些话加上了引号。实际上,这一论文是在另外一节中而且是在联系到别的问题时才提到的④。《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和鲍威尔没有认真阅读原文就妄下判断,完全是对原文语境和意思的歪曲。
第三组材料引述了《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的话:“世界历史性的戏剧不需要许多技巧就变成了最滑稽的喜剧。”鲍威尔在回应文章中也沿用这一表述,认为“这些东西⑤ 当然驳得布鲁诺·鲍威尔哑口无言,并使批判恢复了理智。相反,马克思却为我们演了一出戏。他自己最后扮演了滑稽的喜剧演员。”[1]367 如果说上述两组材料是鲍威尔引证《威斯特伐里亚汽船》评论员对《神圣家族》的错误概括和指认作为其立论的依据的话。那么这里他是转换甚至直接移植、照搬评论员的说法来对马克思进行判决了。
上面三组材料表明,尽管回应《神圣家族》的批评本来是鲍威尔正当的权利,但他却征引了别人对《神圣家族》的概括来陈述《神圣家族》的观点,这就使得他的反批评很难服人,甚至有些荒诞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讥讽说,他“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1]367。
二、“莱比锡宗教会议”场景中的鲍威尔
如果说上面这篇短评不过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鲍威尔的一个实验,那么接下来序幕就正式开启了。长期浸润在欧洲人文经典、宗教氛围的熏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大量的比喻来铺叙、陈述和表达他们对论争对手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他们使用了“莱比锡宗教会议”这个词来讽喻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宗教会议本来是天主教为了审判异教徒和斥责异端邪说而召开的高级僧侣会议,作者把在这一卷上发表的鲍威尔和施蒂纳反驳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比喻为高级僧侣在宗教会议上对异教徒的审判,可谓匠心独运,切中肯綮。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维干德季刊》第3期中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两篇文章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好像真是发生了当时颇为轰动的画家考尔巴赫描绘过的“匈奴人之战”⑥:“阵亡者死有余恨,亡灵在空中喧嚣和号叫,恍如战斗的轰响,厮杀的叫喊,剑、盾、战车的铿锵。”[2]88 然而,究其实这不过是思想者在纯粹观念领域中的自我纷扰,并不是对现实问题的真正探讨,甚至根本没有触及那个时代迫切的实际问题,即“不是为了关税、宪法、马铃薯病,不是为了银行事务和铁路”[2]88,而是为了精神的“最神圣的利益”。为了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和范畴⑦ 进行的无谓的争论。
为了批判得透彻和形象,马克思、恩格斯设置了一幕宗教会议的场景。两个审判者是鲍威尔和施蒂纳,异教徒则是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审判者的形象稍有差别。被称作“圣布鲁诺”的鲍威尔头上罩着“纯粹批判”的灵光,披着“自我意识”的法衣,睥睨世界的万物,俨然是创造一切的上帝,他本身既无父也无母,他就是“他自己的创造物,他自己的制品”。一言以蔽之,他把自己视为精神领域的“拿破仑”。在鲍威尔的思想结构中,最高范畴是“自我意识”,“实体”概念不过是“自我意识”可以肆意摆布的东西,“实体”所代表的宗教现状、国家形态和群众力量,在他的理解中要么可以随意被“摧残”,成为废墟和“残骸”,要么像灰尘一样微不足道。这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的精神修炼就是经常不断地“倾听自己,而这种自我倾听又推动他达到自我规定”。当然,例外的情形偶尔也会发生,有时他不仅“倾听”自己,而且还得“倾听”《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的声音,上面那篇短评就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个审判者是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作“圣麦克斯”的施蒂纳。他的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其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用了将近600页的篇幅来确证自我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证明唯一者不是随便什么人,不是“张三或李四”,正是“我”施蒂纳自己!而别的东西只是“他⑧ 的对象,因而也就是他的财产”,它们是“唯一的”和“无与伦比的”和“无可名状的”。唯一者既是“词句”,又是“词句的所有者”。和鲍威尔稍有不同的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施蒂纳“苦修苦炼的是对无思想进行痛苦的思想,对无可怀疑进行连篇累牍的怀疑,把毫不神圣的说成是神圣的”[2]89。他总是习惯地说:我就是一切,而且是高于一切的某物。我是这种无的一切,也是这种一切的无。
鲍威尔和施蒂纳都对费尔巴哈提出批评。鲍威尔看出,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无定形的本原物质(hvle)、实体是其哲学的基点,其基础地位不可动摇,那么鲍威尔最为珍视的“我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就不能在费尔巴哈那里得以充分展示其功能和价值。“自我意识必须像怪影一般地游荡,直到它把导源于它而又汇集于它的万物全部吸回本身为止”;而今自我意识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吞没了,没有吞没的就只有这个物质、这个实体,它被费尔巴哈牢牢地锁藏着,怎么也不肯交出来。而施蒂纳则认为,“凡是人就不会缺少哪怕是最微小的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甚至对于“任何一只鹅、任何一条狗、任何一匹马说来也是如此”⑨,费尔巴哈对他的这一看法持质疑和批评态度,施蒂纳就根据其“唯一者”的理论“控诉”费尔巴哈,提出反质疑和反批评。
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文章除了批评费尔巴哈而外,对赫斯和作为《神圣家族》一书作者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批评。但由于马克思已经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忙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调查、赫斯正在推广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因此没有马上作出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诙谐地说:“他们没有出席圣宫(santa casa)受审,结果他们就被缺席判决:他们在整个尘世生活期间永远被驱逐出精神的王国。”[2]90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到,鲍威尔和施蒂纳两人的思想其实也有些差别,因此在对其他人物的评论中,也看出他们“彼此之间又制造出一些奇异的阴谋而互相倾轧”[2]90。
《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的原始手稿中原来还有一段话:“在舞台深处出现了格拉齐安诺博士(Dottore Grazianno)或称作‘非常机智而有政治头脑的人’的阿尔诺德·卢格(《维干德》第192页)。”[2]90这表明《莱比锡宗教会议》原计划包括《圣布鲁诺》、《圣麦克斯》、《“格拉齐安诺博士”》、《费尔巴哈》四个部分,其中《“格拉齐安诺博士”》章由赫斯写成,后来马克思在修改时把这段话删掉了,赫斯已经写出的稿子就不再被纳入《莱比锡宗教会议》,进而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三、鲍威尔怎样与“莫·赫斯”诀别
按照鲍威尔的界定,费尔巴哈的同党除了《神圣家族》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外,剩下的就是赫斯了。因此,为了彻底清算这一派别,需要与“莫·赫斯”做最后的诀别。在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文正式写作的《圣布鲁诺》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按照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赫斯这样的顺序来叙述鲍威尔的观点并进行批判的。笔者在《“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中已经解读并分析过鲍威尔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现在我们看他是如何与“莫·赫斯”诀别的。
关于赫斯的思想。鲍威尔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推断的:先问,赫斯在费尔巴哈派别中的意义何在?就在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尚未完成的东西,莫·赫斯正在完成”;再问,“恩格斯和马克思尚未完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对施蒂纳的批判:最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为什么“尚未”批判施蒂纳呢?因为当他们写《神圣家族》的时候施蒂纳的书尚未问世。
鲍威尔的上述推论可以说把他理论思考的特点“暴露无遗”了,他把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与费尔巴哈之间复杂的思想关联,把《神圣家族》写作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出版时间,无原则地组合在一起。并且臆造出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或先后顺序,以“思辨的戏法”“任意虚构一切,使最不相干的东西带上莫须有的因果联系”。其实,就当时思想倾向看,尽管还可以笼而统之地把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等归入青年黑格尔派,甚至又“派中有派”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归入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与赫斯还是与费尔巴哈思想之间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分野,前三人与费尔巴哈的思想之间绝不是像鲍威尔所拟喻的“器皿与窑匠”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他们的思想无原则地扯在一起、又主观臆造地认为在费尔巴哈派别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尚未完成的东西,莫·赫斯正在完成”呢?再者,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其思想独立发展是他们长期艰辛的理论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过程中对施蒂纳的评论诚然也构成了一个环节,然而就其实质性而言,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环节提升到其思想成熟的标志的地步:鲍威尔在这里对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分量的估计显然是非常不适当的。最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尚未问世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本书第二章的研究表明,施蒂纳写作这本书的时间是在1843~1844年,书写完之后,他将书稿送给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全书排出校样还未正式出版时,维干德就给恩格斯寄去一份,让他先睹为快。该书正式出版的时间是1844年10月,而《神圣家族》确切的写作时间是1844年9月至11月间,也就是说,当《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已经正式出版的时候,《神圣家族》还没有写完,更何况在出版之前,恩格斯已经看过此书的校样了。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作出马克思、恩格斯写《神圣家族》的时候施蒂纳的书尚未问世的判断呢?凡此种种表明,鲍威尔无视事实,仅凭自己的印象和思辨处理一切!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无偏激地说,这些做法“在他那里达到了最荒唐无稽的地步并堕落为一种小丑的行径”[2]112。
接下来,我们看鲍威尔是如何批判赫斯的。他先是摘引了赫斯《晚近的哲学家》中的大段论述,遇到赫斯思想与费尔巴哈不一致或者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他就点评说:赫斯“没有了解费尔巴哈,或者是器皿想反抗窑匠”。在完成了对赫斯著述的征引之后,他注意到赫斯特别喜欢使用诸如“联合的”和“发展”这两个字眼。我们知道,黑格尔也使用过这些词汇,于是鲍威尔得出结论说,赫斯抄袭黑格尔。这真有点让人哑然失笑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以及此前一再用事实证明:“我们在圣布鲁诺那里发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对黑格尔的经常的依赖。”[2]95 现在他却在指责赫斯抄袭黑格尔!赫斯不过是使用了“联合的”和“发展”这些并不是黑格尔哲学最重要、为其所独有的字眼;如果这样竟然被指责为抄袭,那么鲍威尔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马克思、恩格斯顺手引证了《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1O页上的一段话,在那里鲍威尔写道:“自然和历史中的〈1〉矛盾的〈2〉真的〈3〉解决〈4〉,彼此分隔的诸关系的〈5〉真的统一〈6〉,宗教的真理性的〈7〉基础〈8〉和无底的深渊〈9〉——真正无限的〈10〉、无法抗拒的、自我创造的〈11〉个性〈12〉——尚未发现。”[2]113 〈〉里的序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这段话表明,在短短三行文字中出现的不是两个似是而非的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如像在赫斯那里一样),而是整整一打!如果说赫斯是在抄袭黑格尔,那与鲍威尔相比,他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看到,鲍威尔在对费尔巴哈派别的分析中,从费尔巴哈出发,然后利用“恩格斯和马克思”做过渡,最后到赫斯这里;现在,可以说,赫斯成了他最终将费尔巴哈同他关于施蒂纳、关于《神圣家族》以及关于《晚近的哲学家》的等的评论串联起来、具有了因果联系的工具、线索和归结。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在这里费尔巴哈“哲学不能不虔诚地完结”了。但是,上述分析表明,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为过渡、把赫斯的思想视为费尔巴哈思想的完结,是一种多么荒唐的指认和主观臆造!退一步说,关于费尔巴哈哲学有一种完结、哲学有一种完结这样的想法和表述,其实也不是鲍威尔的创造,乃是他从赫斯在《晚近的哲学家》的序言中反对他的一段话中抄来的,这段话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最近的后裔别无他法,不得不如此向世界诀别。”[2]114
布鲁诺·鲍威尔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主将之一。他生于1809年,比马克思年长9岁,在思想上更是早慧,1836年他开始任柏林大学副教授的时候,马克思才由波恩大学转入该校,因此应该不折不扣地说他是马克思的老师。次年他们相识,马克思开始听鲍威尔的讲座,受到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1839年马克思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鲍威尔思想的痕迹更是非常明显。1841年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合作,先是合写了《论基督教的艺术》(后改名为《论宗教和艺术》),后来又一起酝酿筹办《无神论文库》。1842年鲍威尔因激进的宗教观点和政治言论被解除教职,当时身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撰写了《再谈谈奥·弗·格鲁培的小册子》为其辩护。但到第二年,他们之间的思想出现了裂痕,在鲍威尔发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后,马克思写了反驳其观点的《论犹太人问题》;其后鲍威尔又写了关于同一议题的《被揭穿的基督教》、《18世纪的政治、文化和启蒙史》,其弟埃德加·鲍威尔发表了《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论争》。1844年8月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征询其对进一步批判鲍威尔的意见,9~11月,他与恩格斯第一次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对结集在鲍威尔周围的《文学总汇报》上的论者及其作品、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不无偏激和过火的批判。之后鲍威尔于1845年10月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费尔巴哈学派的成员一一进行了回应,为此马克思等人又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进行反批评。本文解读的这些部分表明,至此他们的关系彻底了断了。
这样,从师生到论敌,从深受影响到彻底决裂,时间不过1O年,这里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源于观照、理解和把握世界方式的巨大差别:是从观念、精神和自我出发还是根源于现实、感性和实践?
注释:
① 对这一章其他部分的解读请参看拙文《“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② 《维干德季刊》是当时一本引人注目的哲学杂志,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参与该杂志工作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
③ 即《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中的“(a)绝对批判的自我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7—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④ 即在《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中的“(b)犹太人问题,第三号”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准备写一篇烦琐的短论来阐明……‘现代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⑤ 指鲍威尔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摘抄下来并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引证。
⑥ 匈奴人之战(Battle of the Huns)是考尔巴赫于1834—1837年所作的一幅著名的画。画中描写了许多阵亡战士的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空中进行的。
⑦ 诸如“实体”、“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和“真正的人”等等。
⑧ 指“唯一者”。
⑨ 另一种表述是:“任何一只鹩,任何一条狗,任何一匹马”都是“完善的人,甚至是——如果有人喜欢听最高级形容词的话——最完善的人”。
标签: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鲍威尔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