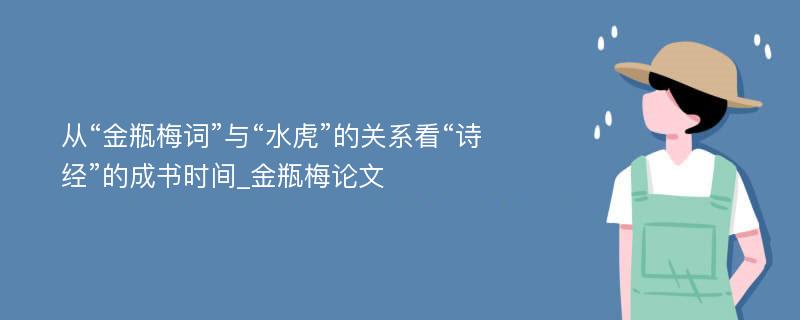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金瓶梅论文,成书论文,水浒论文,看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瓶梅》)的部分故事是从《水浒传》生发出来的。《金瓶梅》的男主人公西门庆和作为女主人公之一的潘金莲都是《水浒》中原有的人物,他们两人发生私情并因而害死潘金莲的丈夫武大的情节,以及武大的弟弟武松这个人物也都是《水浒》中原来所有的。《金瓶梅》的开头五回所写的武松与潘金莲等人的故事,与《水浒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回不但有不少类似的情节,文字也颇有相同或联系密切之处。但是,《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既有繁本和简本之别,繁本与繁本之间、简本与简本之间又不尽相同。那么,《金瓶梅》这些内容所依据的到底是《水浒传》的繁本还是简本?又是怎样的繁本或简本?对此,虽有学者曾加以注意,但似尚有进一步考辨的必要,因为这一问题不仅牵涉到《金瓶梅》与《水浒传》之间的版本关系,并进而影响到我们对《金瓶梅》成书时间的判断。故特撰此文略加论述,并以求正于方家。
(一)
据我所知,目前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金瓶梅》所根据的是繁本《水浒传》。①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金瓶梅》中与《水浒传》情节有关的文字尽管并不都与《水浒》一样,有些并很有差别,但其第五回写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与天都外臣序本或容与堂本一类的繁本《水浒传》却多类似,有的段落甚至一字不差,②由此而认为《金瓶梅》作者(或其写定者,下同③)根据的是繁本《水浒传》,其与繁本《水浒传》相异之处则是该书作者在繁本《水浒传》的基础上有所删改,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假如我们对同样出自《水浒传》的《金瓶梅》第一回中武松打虎的文字细加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判断尚可进一步推敲。
为了说明问题,现先引《金瓶梅》第一回中的一段文字如下:
……原来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皆落黄叶,刷刷的响,扑地一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来,犹如牛来大。武松见了,叫声阿呀时,从青石上翻身下来,便提稍棒在手,闪在青石背后。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个欢翅,将那条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个焦霹雳,满山满岭,尽皆振响。这武松被那一惊,把肚中酒都变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猛虎项短,回头看人教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一伸,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侧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了一声,把山岗也振动。武松却又闪过一边。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力已自没了一半。武松见虎没力,翻身回来,双手轮起稍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枝带叶打将下来。原来不曾打着大虫,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只拿一半在手里。这武松心中也有几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发,剪尾弄风起来,向武松又只一扑,扑将来……④
再把此跟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的相关文字比勘一下(一般认为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较容与堂本为早,但该本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当于另文讨论;故本文引繁本《水浒传》均据容与堂本):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右手里,闪在青石边。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往上一扑,从半空里窜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拆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⑤
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老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这句话是两本都有的,但容与堂本此句之前的“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这句话,在《金瓶梅》中是没有的。所以,在容与堂本中,老虎伤人的“一扑、一掀、一剪”的三个过程是清清楚楚的,但在《金瓶梅》中,“一剪”的过程却没有了,致使《金瓶梅》中的“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这句话变得难以理解:读者不知道老虎伤人的三大手段中的“一剪”是怎么回事。当然,《金瓶梅》在写“大虫扑来”时,曾有“将那条尾剪了又剪”之语,在写老虎再次向武松扑来时,又有“剪尾弄风”四字(皆为容与堂本所无),但那样的“剪尾”都只是它在扑人之前的一个附带的动作,对人并无杀伤力(能杀伤人的是它的“扑”),显然不配成为老虎伤人的三大手段之一;何况那既是其扑人的先行动作,自应包括在“一扑”之中,不应成为与“一扑”并列的另一个“伤人”的主要手段——“一剪”。所以,《金瓶梅》尽管为老虎在扑人前加了这一类描写,但仍然不能阐明老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的真实含义。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金瓶梅》作者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繁本《水浒传》中写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扑、一掀、一剪”改得如此含糊不清,以致上下文缺乏应有的联系呢?从《金瓶梅》的整体艺术水平来看,其作者绝不会如此低能。而且,他这样改的动机是什么呢?如说是为求文字的简略,那么,删去了“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十五个字,却又加上了“将那条尾剪了又剪”和“剪尾弄风”十二个字,也不过只少了三个字,如将“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句中的“这铁棒也似”五个字删去,虽不如《水浒》原句的传神,但却比现在这种删改要多省掉两个字,又不致丧失“一剪”的原意;难道《金瓶梅》的作者竟然低能到连这也想不到?
为了对上述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只能舍弃《金瓶梅》作者在写此段时是在繁本《水浒传》的基础上删改的假设,而寻找另外的前提。据马幼垣先生的《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⑥,现存的保存着武松打虎一回的《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写武松与老虎的搏斗过程,皆删去了老虎伤人的“一剪”动作,但又均有“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望(按,当为“掀”字之误)、一剪”之语。所以,上述的现象只能解释为《金瓶梅》作者在写此回时所依据的也是一种简本《水浒》,⑦这种本子已经没有了老虎对武松的“一剪”,但却还保留着“……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之语,《金瓶梅》作者意识到了这样的描写中缺少了“一剪”的过程,但却不知道这“一剪”是怎么“剪”的,只好凭自己的想象来补充。但究竟只是凭想象,想不到这一剪乃是“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所以只好想些“将那条尾剪了又剪”一类的描写来凑合。
关于《金瓶梅》作者看到过插增本简本《水浒》的事有一个确切的证据,那就是该书第一回所说的“……那四大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⑧因为在繁本《水浒传》(后出的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传》除外)中,皆无田虎、王庆“僭称王号”之事,只有插增本简本才有(至于宋江,《金瓶梅》显然不把他包括在“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之列,所以在那以后紧接着就是“惟有宋江”云云)。
(二)
在《金瓶梅》的第一回中,除了此段文字以外,还有一段也很能显示出其出于简本《水浒》: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方。那时山东界上有一座景阳岗,山中有一只吊睛白额虎,食得路绝人稀,官司杖限猎户擒捉此虎。岗子路上,两边都有榜文,可教过往经商结伙成群,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岗,其余不许过岗。这武松听了,呵呵大笑,就在路旁酒店内吃了几碗酒,壮着胆,横拖着防身稍棒,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⑨
从这一段中的“这武松听了,呵呵大笑”之语,可知在这之前一定是有人在对武松说话,以致引起了武松“呵呵大笑”的后果。但就这一段文字来看,在此句以前并没有人向武松说过什么话,那么,这两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来的呢?
如与繁本《水浒传》相对照,就可以知道:《金瓶梅》此段中的“(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方”,在繁本《水浒传》中乃是“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至于上引“那时山东界上”直至“其余不许过岗”的一段叙述,在繁本《水浒传》中是没有的。繁本《水浒传》于“来到阳谷县地面”后,即叙其到一酒店中喝酒,在临离开酒店时,酒家对他说:“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官司如今杖限打猎捕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两边人民都有榜文,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余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务要等伴结伙而过。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我见你走,都不问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间歇了,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冈子。”紧接着就写:“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⑩所以,《金瓶梅》中的“那时山东界上……”云云,乃是据繁本《水浒传》中酒家对武松所说的那段话改写而成,不过把酒家与武松的对话变成了作者的叙述;至于“这武松听了,呵呵大笑”则是据繁本中“武松听了笑道……”删改而成。但因为原先酒家对武松所说的话已被改成了作者的叙述,而“武松听了笑道……”中的“武松听了”四字却没有作相应的修改,以致这整段文字变成了前言不搭后语。
假如把繁本《水浒传》中的上引叙述改成《金瓶梅》中的那种写法,是出于《金瓶梅》作者所为,那么,从《金瓶梅》的高度艺术水平来说,其作者实不应如此低能、拙劣。何况此段文字还留有出于简本的明显痕迹,那就是“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这一句。按,“浪浪沧沧”,繁本作“浪浪跄跄”,见于武松已经上冈以后、即将遇到老虎之前:“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浪浪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把“浪浪跄跄”作为武松由山下上冈时的表现则出于简本系统,《新刊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写武松从酒店出来,即有“武松正走,日色渐坠,沧沧浪浪,奔上冈来”之语。(11)故《金瓶梅》的“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之句显然源于简本;倘据繁本改写,则繁本这样的描写并无不妥之处,《金瓶梅》作者何以要将“浪浪沧沧”改为武松上冈时的表现,与上述简本相符,何况繁本的“跄跄”在《金瓶梅》和《水浒》简本中都误成了“沧沧”?
既然《金瓶梅》的“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是源于简本《水浒》,那么,把“武松听了,呵呵大笑”这样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理解为《金瓶梅》作者的低能、拙劣所导致,实不如视为也是因袭简本而来;因为正如马幼垣先生所指出的,“各种简本都是漏字盈篇,文意文法不断遭践踏的所谓作品。任谁也写不出那些乱七八糟,句不成句的句子。……那些糟透的所谓句子只会是盲目乱删一顿的产品……”。(12)
(三)
我的上述推论很可能会招致如下的质疑:假如《金瓶梅》第一回关于武松部分的描写,是以《水浒》简本为依据的,那么,作为其依据的这种简本在哪里呢?迄今所见的各种《水浒》简本没有一种是符合被《金瓶梅》作者作为其写作第一回依据的简本的条件的。例如,《金瓶梅》是写了老虎对武松“一掀”的动作的,但却根本没有武松与酒家在酒店中的对话。现存的简本有哪一种是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第一,当时的简本很多,光在万历十七年以前的简本就有好多种,但目前已发现的简本属于万历十七年以前的至多只有两种,也许一种都没有(说见下)。第二,如上所述,以《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才能,他在写第一回时如是以繁本《水浒传》为依据,绝不会出现上述那样的败笔。第三,在第一回中确有《金瓶梅》作者看到过插增本简本《金瓶梅》及其某种描写(即关于武松出了酒店后“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的那句话)出自简本的痕迹。那么,把《金瓶梅》第一回的上述毛病视为其所依据的简本原有的缺陷,作者一时没有发现(如“武松听了”之与上文不相衔接)或虽然发现了但却无法弥补得天衣无缝(如老虎的“一剪”)的结果,岂不是更合理吗?怎能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或许已永远无法发现)其所依据的简本而否定此一推断呢?
现在,对于上述第一点略加阐释。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有一段记载: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13)
《庄岳委谈》作于万历十七年(据《庄岳委谈》卷首《小引》的自署),所以,从这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获知这样一些信息:第一,胡应麟在万历十七年(1589)的二十年前——即隆庆(1567-1572)年间——所见到的“《水浒传》本”就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本子了,因为文中有“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的话,这意味着《水浒》初出时比其当时所见到的此种本子要好得多,可惜他已无法看到(或无法完整地看到);只不过这种本子删节很少,所以“尚极足寻味”。第二,对《水浒》简本的删改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少持续了二十年(删节本至迟出现于隆庆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水浒》已经越删越简、越删越糟,(14)成了“几不堪覆瓿”的本子。由此可知,从隆庆到万历十七年之间,闽中坊贾出过好些简本,并呈现出水平日益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目前虽还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水浒》简本,但据马幼垣先生考证,现存的绝大多数简本都后于万历二十二年所出的《忠义水浒志传评林》(15),大致在《评林》之前的只有两种简本(即他的所谓“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而这两种本子只能断定其出于万历时期,也即从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二年之间。(16)
也正因此,现存的简本中出现于万历十七年之前的至多只有两种,也许连一种都没有。
(四)
在论证了《金瓶梅》第一回所依据的《水浒》乃是简本之后,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金瓶梅》第五回写潘金莲在王婆协助下毒杀武大的一段所依据的明明是繁本,那么,为什么《金瓶梅》作者写第一回时要以简本为依据呢?
对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金瓶梅》作者得到过《水浒》繁本的一种残本,这种残本中虽有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及毒杀武大等事,但却没有武松打虎这一回,所以他在写《金瓶梅》第一回时只能以简本为依据了。
还应补充的是:《金瓶梅》作者所得到的繁本不仅是残本,而且中间还有缺页。例如,自潘金莲在收帘子时失手打了西门庆后,直到王婆说十条挨光计之前,《金瓶梅》所依据的都是繁本,只不过在这基础上有时又增加若干或略作修改(17),但在写十条挨光计时,不但文字又颇有省略,而且有的明显不通。如以下一段,《水浒传》繁本是这样的:
……我便请他家来做,他若说“将来我家里做”,不肯过来,此事便休了。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来做,就替你裁”,这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来我这里做时,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第一日你也不要来。第二日他若说不便当时,定要将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这光便有三分了。这一日你也不要来。到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18)
但在《金瓶梅词话》中,这段却是如此:
……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请得他来做,就替我裁,这便二分了。他若来做时,午间我却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吃,他若说不便当,定要将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语吃了时,这光便有三分了。这一日你也莫来。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19)
两相对照,二者不但有繁简之别,而且《金瓶梅》由于省去了“第一日你也不要来,第二日”十二个字,上下文就联系不起来了。因为潘金莲第一日既然肯到王婆家来做了,在她家吃点点心乃是正常之事,而且第一日吃了点心,并不等于第二日她还肯继续来做,何以吃了点心就意味着“这光便有三分了”,以致西门庆第三日就可以在王婆家来会潘金莲?《金瓶梅》作者在从西门庆与潘金莲见面起到“挨光计”之前为止,不仅以繁本为依据,而且把繁本原有的描写润色得更精彩(20);此处不应改得如此拙劣。故其所依据,当是简本。换言之,其所依据的残本繁本此处又有缺页,所以只能以简本来补。这也就意味着,他所得到的繁本不仅是残本,而且残缺得相当厉害。
学术界一般认为天都外臣序本刊行于万历十七年,如果此说可以信据,那么《金瓶梅词话》的写作若在万历十七年之后,则要找到一个完整的繁本并非难事,怎会以如此残损的繁本为依据,以致在好些地方只能依据简本?因此,《金瓶梅词话》的写作当在万历十七年之前,而其所依据的残缺的《水浒传》繁本必然是天都外臣序刊本以前的本子。如此说不尽可据,那么,《金瓶梅词话》的写作也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因为袁宏道在这一年至少已看到过《金瓶梅》的上半。(21)
不过,胡应麟在隆庆年间所看的简本《水浒》还是“尚极足寻味”的,是在他写《庄岳委谈》的万历十七年以前开始的“十数载来”,《水浒》简本才被越改越坏以致“几不堪覆瓿”的;而《金瓶梅词话》作者所据的《水浒》简本,在武松打虎的描写中已经把老虎“一剪”的动作也删去了,以致紧接着的“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之语没了着落,显然已远不是隆庆时的“尚极足寻味”之本,而当是万历时的越删越糟的本子。倘若《金瓶梅词话》写于隆庆时,大概还找不到这样的本子。由此言之,《金瓶梅词话》的写作也不可能早于隆庆时。
最后,顺便说一说,胡应麟显然认为他在隆庆时看到的“尚极足寻味”之本已是简本而非原本,所以有“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之语。然而,他既没有看到过原本,而那些“尚极足寻味”的简本又绝不会自己标明为简本,胡应麟又怎么知道那些是简本而非原本的呢?想来,胡应麟大概也像《金瓶梅词话》作者那样看到过原本的残本,虽则分量很少,只能“窥豹一斑”,但却已使他明白那些“尚极足寻味”之本并非原本,并进而产生“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的感慨了。
*本文的基本观点曾发表于2008年7月28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第四届东亚出版文化國際學術會議”,此次成文,已对初稿有所修改,特此说明。
注释:
①如日本上野惠司、大内田三郎教授均认为《金瓶梅》作者所据为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见上野惠司:《“水滸伝”から“金瓶梅”へ——重複部分のことぱの比較·付書き換之語句索引》(《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1970年3月第3号,第119—140页)、大内田三郎:《“水滸伝”と“金瓶梅”》(《天理大学学報》1973年3月卷24第5期,第90—107页)。
②如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金瓶梅词话》卷五自第八页B面第四行“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起至第九页A面第五行“假哭起养家人来”一段273字,即同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卷二十五第九页A面第三行至B面第四行相对应的文字全部一样。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金瓶梅词话》(原藏北京图书馆的《金瓶梅词话》本同)与容与堂本相比虽有两个字的异文,但其有异文的一页显系后刻(如该页中的“说”字皆刻作“說”,与其前后诸页的刻作“說”有别,而毛利家藏本此页的“说”字均刻作“說”,与其前后诸页一致)。
③《金瓶梅词话》是个人创作抑或由一人最后写定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在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本文对此问题不拟涉及,故两说并存。
④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第五页A—B面。
⑤见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第八页A面—第九页A面。
⑥按,马幼垣先生此书分上、下两册,仅见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4年12月试行本。
⑦据马幼垣先生研究,在《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之前应该还有较此本删节少的简本(见其《两种插增本〈水浒传〉研究——兼据辑校插增本所获的新知去探讨〈水浒传〉的演化过程》,载《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上册,第40—44页),所说甚是。关于此点,我在下文还将论及。
⑧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第三页B面。
⑨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第四页A—B面。
⑩见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第六页A-B面。
(11)按,繁本的“浪浪跄跄”本为“踉踉跄跄”之误(“浪”与“踉”为校勘学上所说的以形近致误),“踉踉跄跄”为行路不稳的样子(参见《辞海》“踉跄”条),这是武松“酒力发作”所导致的;而把繁本的“跄跄”写成“沧沧”乃是进一步的错误。
(12)马幼垣:《两种插增本〈水浒传〉研究——兼据辑校插增本所获的新知去探讨〈水浒传〉的演化过程》,见《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上册,第60页。
(13)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72页。
(14)这不仅从文中“尚极足寻味”到“几不堪覆瓿”到“将永废矣”这样的用词可以推知,在上举马幼垣先生的论文中也有大量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15)(16)见《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载马幼垣:《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86页、87—88页。
(17)请对照《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第二回第四页B面—第十一页B面与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第十五页B面—第二十一页B面。因原文颇长,不予引录,以省篇幅。
(18)见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第二十二页A—B面。
(19)见《金瓶梅词话》第三回第二页B面。
(20)如西门庆在见到潘金莲后的第二天,又到王婆处来吃茶,容与堂本《水浒传》是:“西门庆道:‘干娘相陪我吃个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门庆也笑了一回,问道:‘干娘,间壁卖甚么?’王婆道:‘他家卖柂蒸河漏子,热汤温和大辣酥。’西门庆笑道:‘你看这婆子,只是风。’王婆笑道:‘我不风,他家自有亲老公。’”《金瓶梅词话》则作:“西门庆道:‘干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缘何陪着你吃茶?’西门庆也笑了一会,便问:‘干娘,间壁卖的是甚么?’王婆道:‘他家卖的,拖煎河漏子,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饺窝窝蛤蜊面,热汤温和大辣酥。’西门庆笑道:‘你看这风婆子,只是风。’王婆笑道:‘我不是风,他家自有亲老公。’”相比之下,《金瓶梅词话》增了好些字句,并显然比原有的描写更生动传神。
(21)见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