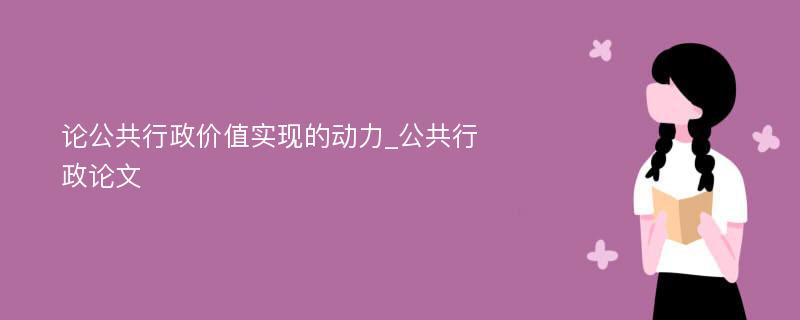
论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行政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6]02—0013—03
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是指它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如果没有动力因素的作用,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公共行政价值关系的框架内来分析,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的动力:人类社会对混乱的恐惧,对秩序的渴求,对效率的关注,对公平的期待,对社会和谐的期盼以及对自身全面发展的不懈奋斗等,都在时刻地鼓舞和激励着他们为达致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另一方面是来自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动力: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是一个“人造物”,人类社会创设“国家”之时,就已经赋予了它一定的价值设定或价值期望。此外,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国家是一个有着紧密结构和功能齐全的公共行政系统,它内部也蕴涵着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动力机制。
一、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主体动力
(一)人类社会的理性之光
理性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这也是人类比其它任何动物更高级的重要方面,由此也决定了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灵”的地位。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说法,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通过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地转让给“主权者”,这个“主权者”就是国家。国家像其他任何社会组织一样,都是人类行动和理性选择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无论是“社会契约说”,还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二者都蕴涵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因素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以理性创设了国家,其最终的目的是以国家为工具,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国家和社会二者的关系中,国家是手段,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是当今时代所强调的“服务行政”的理论根源。在如何运用国家这一工具服务于人类社会方面,依靠自身的理性,人类社会因应历史发展和公共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探寻着与之相适合的公共行政模式。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的增长,其驾驭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运行的能力也在提高。虽然,辩证地看,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时常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扰攘,理性因素也并不像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就是绝对真理,不可移易。尤其是在自然与社会的交相关系中,人的理性因素往往不是独尊的。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往往会让理性出卖自己。在历史领域中,理性决不像在自然领域中那样坚强无比,它甚至依赖成性,最终总是屈从于人性的其他因素。”[1]
从最终结果上来看,人类社会的理性作用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并不妨碍对人类社会的理性这一命题的判断。人类社会以理性创设了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朝向进步与发展的希望之门;人类社会又在以自身的理性驾驭着国家,为追求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而不懈奋斗。可以说,人类社会正是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对于无序与失范的戒备,对于秩序与和谐的向往,才最终找到了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权力这一惩恶扬善的“利器”,并以高超的艺术控制着它,为达致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而发挥作用。
(二)人类社会的理想之欲
人类社会凭借自己的理性创设了国家,希冀通过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的运行,实现追求公共行政价值的理想,虽然这是一个艰辛和漫长的过程,但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正是在这种美好理想的向往和感召之下,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人类社会一步步地朝向这种理想迈进。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完全和真正实现,也就是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和描绘的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国家消亡了,公共行政活动也将不再存在,人类社会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达致共产主义,实现公共行政价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人类社会的持续努力。人类社会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理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绝不是无序和随意的,缘于人类社会的理性设定,它们内在地体现为一个具有逻辑层次关系的价值体系。从人类社会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理想设定上来看,在工具性价值意义的层次上,人类社会企求通过公共行政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可这又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二者的冲突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就会造成社会的失序和混乱状态,从而回到了社会契约论者所称之为的“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或“每个人反对所有人”(each against all)的“自然状态”。因此, 人类社会中公共行政的生成和运行,其最基础和根本的价值追求就是秩序。这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它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绝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2]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只有在秩序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注意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存和发展当中去,也就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一方面妥善地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保障,促进人性的自我完善。就公共行政的最高价值的“善”的意义上而言,可以说,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性的完善,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社会)两个方面,给予公共行政的神圣使命以恰切的诠释。从总体和本原的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创设国家,启动公共行政运行的初衷也就是为了这两个方面,它们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在此,笔者不赞成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将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仅归结为人的全面完善与发展上面。因为从更为广阔和宏观的视野上的主体——客体二分观点去看的话,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也处于主体——客体关系的框架之内,在这一框架之中,人(或者说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立足于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社会)两个方面,去探究公共行政之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实质上就是在方法论上坚持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那种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公共行政视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维向度,其实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后现代性的主体——客体二分消解的思想。在笔者看来,后现代性的这一消解主体——客体二分关系的思维模式,主张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固然能在某种程度上从理论上解释危及现代社会发展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但其在实质上却是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反动,因为一旦消解了主体——客体关系,其实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地位也不复存在了,也就更谈不上公共行政为人而设、而行的意义了。
如果从反面的经验层面上来分析的话,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对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公共行政对此方面的无视和忽视所致,它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了人性的完善。当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人与自然关系之紧张,主要是由于现实的人类出于对眼前利益的竞争,而采取的一种反道德的对自然的索取方式。如果这种行为还单单伤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它并不足以让人类对此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方式会渗透到人与人(社会)的界域中来,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实社会中的损人利己、以强凌弱、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这个社会,人为物役的现象遮蔽了人之为人的实质和意义,人性完善的实现也终将是一句空话。这些都从反面说明了理性的人类创设国家的目的,就是希冀通过公共行政的运行,处理好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现实生活中,这两方面关系的紧张,更说明了人类关于公共行政的希冀和理想之实现的不易,但人类的理想之欲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二、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客体动力
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一经产生便在与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的互动中,不断地释放着自身的力量,从而推动着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居于客体地位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在运行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正方向的力量。如果公共行政价值主体对其的驾驭不当,它也会产生巨大的反方向的破坏力量,从而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起到一种阻碍作用,延缓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进程。霍布斯曾以“利维坦”(Leviathan);喻意权力巨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对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权力的不恰当的运行,会产生的巨大的破坏性的担忧。从理论上来说,国家只是实现人类社会的目的的一个工具。作为公共行政价值的客体,它的动力之源主要来自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来说,作为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的人类社会对其的理性把握和设定;二是从内部来说,由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国家的内在结构组合与功能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动力机制系统。来自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外部的推力和内部的聚力两种力量,在共同的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统摄下,汇合成了一股朝向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客体动力。
从外部的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动力来源上看,国家是理性的人类社会人为创设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承载着人类社会对它的价值期望。这正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状况,是与客体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凡是客体为自然物(人类未施加影响的自然物)的,其价值是其属性决定的,而不是由主体赋予的。凡是客体为人为物(包括人改造的自然物)的,其价值,有的是客体出现后人为赋予的;有的则是由人事先赋予和确定的。”[3] 因为“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沉的呼唤。”[4] 国家的出现本身就蕴涵和寄托着人类社会对公共行政的理想价值的索求。人类社会的这种希冀和期待折射到现实的公共行政之中,便体现为从内心深处对公共行政的自觉参与、服从和信任。无疑,这种自觉的参与、服从和信任其实就是体现了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认可,它在与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的互动关系中转化为一种推动公共行政价值客体以自身属性运行的动力。这种动力是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客体动力之一。
从内部的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动力来源上看,作为人类社会理性产物的公共行政权力运行载体的国家,其内部有着严格的对公共行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结构,不同的结构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对公共行政权力的属性和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的提高,作为其载体的国家的内部的结构的配置会更加合理,其功能也会更加优化。在这种动态的演进中,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国家,其实就“物化”为一个内部充满活力、协调统一、运行规范的,由不同的“结构——功能”板块所组成的,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内部动力机制的系统。在与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的互动并朝向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它源源不断地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构——功能”板块失衡、塌陷或脱落,或者各个不同的“结构——功能”板块之间发生交叠、碰撞和挤压,这一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动力机制系统就会发生故障,从而影响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
当然,在相对稳定的公共行政生态环境下,这一动力机制系统一般来说能保持着正常的运行。一旦公共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动力机制系统就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从而导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对其的变革与改造。从动态的视角看,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国家的动力机制系统与其所处的公共行政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正是在这种矛盾关系的斗争中,促使公共行政价值主体通过不断地改造客体,从而保证了其满足主体需要的能力。“不变的是变革”,这句广为人知的话语,也许能从经验层面的意义上,为我们理解作为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国家,在面临不断变化着的公共行政生态环境下,为保持其自身动力机制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不断地被改造、变革的现象。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内部的动力机制系统,一刻也不能停止运行,它是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又一动力。
以上所说的关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的来自外部的动力和来自内部的动力,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来自外部的动力以来自内部的动力为根据,来自内部的动力以来自外部的动力为条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而融会成朝向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强大的客体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