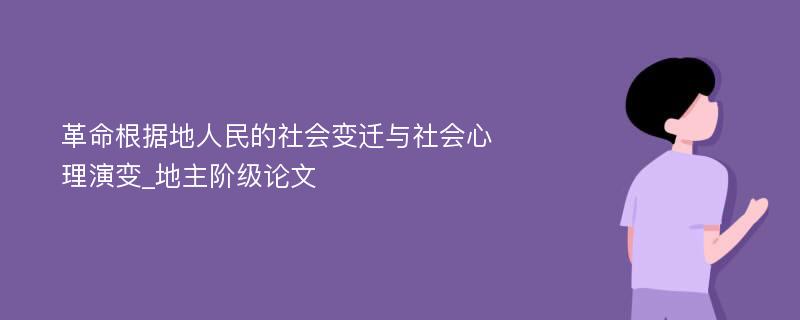
革命根据地社会变动与民众社会心理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根据地论文,社会心理论文,民众论文,变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6)06-0054-09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在一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中广泛的、共同的、典型的社会精神现象或社会精神状态。它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较为直接的反映形式,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环节。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伴随着乡村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对中国革命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关革命根据地社会变动与民众社会心理变迁问题的探讨尚属薄弱。本文谨就所见史料,对其略陈管见。
一、土地革命与中共土地政策对根据地民众社会心理嬗变的影响
任何社会心理及其嬗变,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和演化的。鉴于中国革命根据地处于广大农村,因此研究根据地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就不能不首先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农民对中共发动的土地革命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的心理反应。
众所周知,旧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作过论述。他写道:“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① 土地革命前赣西南、闽西的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的状况亦十分突出。据毛泽东1930年5月、10月先后在寻乌和兴国的调查统计,在寻乌县,占人口总数88%以上的贫农和中农仅占有全县30%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7.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70%的土地②。在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地主和富农仅占人口总数的6%,但占有全区80%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80%的贫农、中农仅占有全区20%的土地③。另据有关文献记载,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6县“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④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力图改变土地所有权时,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
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根据地农民实现了千百年来获得土地的梦想,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民间歌谣源于生活,是劳动人民的心声,苏区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愉悦心态可以从民歌中得到印证:“荷树叶子笑呵呵,红军帮我打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一人分到六担多。今个世界大吾同,贫苦雇农有田种;这个田地自家的,自种自收无人动。”⑤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有了自家的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因此,尽管在反“围剿”战争紧张局势下,革命根据地的农业仍获得丰收。1934年1月24日和25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指出:“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战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虽然不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租佃关系,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减租减息并不是一开始就得以顺利进行,起初根据地农民在心理上是有所顾忌的。例如,在晋察冀边区,“有不少农民在依法公开减租减息之后,又偷偷把已减的租息照原数退回”。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贫农、雇农、中农等逐渐积极起来,拥护减租减息。“于是,黑压压一大片农民,排成队伍,一组一组、一队一队,打着小旗,敲着锣鼓,领着儿童团,闺女、老婆婆也坐上大车,到地主家或者到大会场、小会场上去算帐。”⑦ 当地主向农民发难时,农民们便团结一致讲道理,讲法令,人多气壮,使地主威风扫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土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贯彻《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地方出现“左”的偏差,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这对农民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如在晋绥边区,“有的人实在小心,怕上升富农就变了质”⑧,“甚至有些人认为‘穷比富好’”。所谓“房住小,地种少,留个老牛慢慢搞”,是当时不少怕冒富的农民普遍的心态。1947年冬至1948年初春,在平分土地的高潮中,过去没有引起重视的“左”的倾向继续发展,达到了比较普遍和比较严重的程度。在侵犯中农利益方面,“动中农面太宽,动中农土地太多,引起中农阶层很大不满”⑨,以至在一段时间里普遍发生了中农对发家致富有所顾虑,拼命吃喝浪费等现象。另外,对一些地主富农处以极刑,乱打乱杀的现象十分严重,使一些农村中弥漫着恐怖气氛,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生产受到影响。据晋绥解放区一个分区代表团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左”的错误,造成一些地区“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⑩ 1948年1月,习仲勋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称:葭县乱搞不及5天,竟一塌糊涂,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11)。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偏差给农民的心理笼罩了一层难以消除的阴影。直到1949年3月,“农民对我党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政策还有各种顾虑”,如“土地以后分不分?劳动致富会不会再受打击?出租土地以后会不会定为地富成分?雇人种地会不会当作地富斗争?借贷会不会成了高利贷?”(12) 等等,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农民中形成了“穷光荣,富危险”的社会心理。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迅速纠正了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使土地改革回到正确轨道继续向前运行。
山东解放区是较早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一个省份。1947年2月22日,上海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美国女新闻记者贝蒂·葛兰恒(Betty Graham)写的《共产党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作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报道了山东土地改革的情况:农民中一部分人“害怕国民党会夺回这个地区,并让地主重新掌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领导开展了深入的教育运动,使农民相信自己组织起来将成为强大的力量,他们自己就能阻止国民党重返这个地区。”“土改运动在全省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表明了农民接受这种观点的程度。我向五十个农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也证明了这一点。”“我问他们:‘你难道不怕万一国民党夺回这个地区,你会因为刚得到了土地而受惩罚吗?’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不相信国民党还能回到这儿来,因为我们得到自己军队的保护。即使他们真的回来了,我们也不怕。我们会尽量战斗下去’”(13)。由此可见,获得土地的农民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他们已下定决心,要保卫刚刚得到的土地,抵抗任何强迫他们退回到封建时代的企图。
从社会心理层面上看,需要和利益是构成态度的最主要因素。中国革命固然不能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组织系统乃至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需要一种认同革命、支持革命、参与革命的社会心理取向,而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废除了农村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农民的物质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乡村民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
二、革命根据地民众政治心理变迁的多重表征
根据地广大民众之所以拥护并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经济因素外,还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心理动因。所谓政治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它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态度、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的论述占有显要地位,强调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是重要的社会集团,因此阶级心理构成了社会心理的内容之一。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阶级心理决定于特殊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它是某一阶级社会境遇的体验之结果。
阶级需要是构成阶级心理的首要因素,又是特定社会群体行动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谋求社会公正合理,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是根据地民众投身革命的直接政治心理动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区域,工农大众政治意识之强可谓前所未有,阶级心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年歌、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所表达的内容。“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14) 闽西永定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地区之一,永定县溪南和金丰农民在敌对势力的烧杀中惨遭损失,饱受痛苦。但乡村“民众普遍表现出对豪绅地主阶级的仇恨”,对于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而遭到挫折,“他们不曾懊悔,一无怨党及农会”(15)。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剧烈的农村大变动中,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鼓动下,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大为增强,通过参加实际斗争,阶级情感和阶级心理特征进一步凸显。对中国革命的心理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民众意志转化为共同行动的心理机制,也是根据地社会力量形成合力的关键环节。
阶级的情感是构成阶级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阶级的情感与阶级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及个体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在同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同一阶级不同成员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心理表征。譬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的农民虽然在思想感情上倾向和欢迎革命,但对敌对势力的阶级报复具有恐惧感,担心遭致杀头烧屋,因此不免产生“等待红军打平天下后,再来安做苏维埃老百姓的心理”(16),因而“大半依赖红军,自己怕斗争”或“不愿意斗争”,有的甚至不敢要分到的土地和财物,或请求共产党组织“停止斗争”(17),甚至要求与敌人“讲和”。这里所谓的“讲和”有其特定的含义,它实际上是当时根据地内一部分农民为缓和阶级冲突,避免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骚扰,而采取的一种调和策略,即主动清还一部分租谷给地主。一些农民说:“我们目前无力抵抗他们,只好与他们讲和,我们才能收禾过冬,同时我们外面虽然挂白,暗中可以做我们红的工作,一待我们力量强大之后,再来斗争。”(18) 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军的“围剿”和地主武装的烧杀,对根据地内部分农民确实产生了威慑作用。当然,具有这种心态的以老年农民和经济比较富裕的中年农民为主,青年贫苦农民则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不愿调和”(19)。此外,一些民众政治判别能力欠缺,在他们看来,“国民革命军也好,工农革命军也好,横直老百姓吃苦”(2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民众政治心理变化的最重要体现莫过于与日俱增的政治参与意识。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广大民众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治事务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参与主要包括政治选举和政治表达等活动。
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中国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只能企盼“为民作主”的明君和“为民请命”的“清官”来保护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轻徭薄赋,社会安定成了他们普遍的心理诉求。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参政意识日益增强。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开代表会议,决定工农本身一切问题”(21)。在赣西苏区,除地主豪绅富农外,16岁以上均有选举权,以乡为基础,农民50人推选代表1人,工人10人推选代表1人,“自由职业者并合于农民内”,少数工厂直接派代表参加,组织乡苏维埃政府,推举7人为委员。在区一级,“农民百人选代表一人,工人二十人选代表一人,工厂仍直接派代表组织区苏维埃,推举十三人为委员,七人为常委”(22)。
随着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苏区普通民众政治表达的积极性逐步高涨。如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每当开会时,“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情形便与这完全不同。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23)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初创阶段,除了游民之外,中农、贫农、乡村工人及一切贫苦群众未完全脱离地主和富农的控制与影响,尽管他们拥护抗日民主政权,但大多数人的政治心态表现出患得患失。这一点在晋察冀边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除一部分积极分子外,许多人“在瞻前顾后地观望形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现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有不少农民在依法公开减租减息之后,又偷偷把已减的租息照原数退回,此即所谓‘明减暗不减’。有的工人在增加工资之后,又暗与雇主约定‘明加暗不加’。有的工人、贫农已经当选村长了,但凡事又偷偷去请示地主、士绅或雇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于“惧怕地主、雇主报复,由于思想上的蒙昧,经验上的缺乏,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和独立性,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力量。”(2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其核心是民选政府。在此问题上,根据地民众的心态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对于村基层工作人员的变换态度颇为冷淡,认为这无非是“从前那一批人得势,今天是这一批人得势”(25),他们如台下看客,冷眼观看着政治舞台上你下我上的场面,这种心态显然不利于中共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抗战的政略之实现。这也从一个方面促使中共认识到要使自己最大限度地取信于民,就必须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立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之上。因此在农村实行普选,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开展了第一次村选,选举出一批新村长,撤换了那些原先横行乡里、鱼肉村民的旧村长。在陕甘宁边区,行政村的主任和自然村的村长也经过村民的选举而产生,民众选举了那些能为自己办事而且公道精干的人担任村主任或村长。1940年7月至10月,晋察冀边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全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在区、县和边区三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区选、县选和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分别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86.3%、91.1%,有的区村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值得一提的是,女议员在晋察冀边区全部议员中占了1/5,一些优秀的女干部脱颖而出,担任了县长、区长和县议会负责人(26)。
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再向下移动,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根据地民众对基层民主选举的态度。村选之日简直成了一个盛大节日,村庄里贴满了各色标语,四处喜气洋洋。“有的村庄还高搭彩牌坊。全村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佩带着红花。”“在选举大会上首先由旧村长报告一年来的村政工作。村民有不清楚的地方或其他的意见,当场提出质问。旧的村长、副村长和村政委员会的委员负责答复。”当新村长选出后,选民们就高呼口号:“解决村长的困难,拥护新村长!”“在选举中还有这样动人的故事,一位老太太病倒在床上了。但是在选举的那一天还让她的老伴扶了她出来,亲自投她那应有的一票。晋察冀的人民对选举是这样的讲:‘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决不放弃!’”(27)
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其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还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民参政议政的情况作了描述。他写道:“在晋察冀就是一位老乡,当他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讲:‘开个会讨论讨论。’”“晋察冀边区从成立那天起,所有困难问题的解决,一切优良的设施,多是利用民主的方式,开会讨论的结果。由于人民政治认识的提高,在一个村子里,最高政权机关已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而是全村的村民大会了。在区里则是区代表大会。还有军政民共同召开的区政会议,就象是各县皆有的县政会议一样。”正是由于通过行之有效的会议制度和工作落实制度,使边区的政权运作顺畅,“一道一道的法令实施下去,一件一件的工作跻于完成,一个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新建设出现在边区各地。”(28)
根据地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组织。苏区时期,“赣西有组织的群众,已达三四十万,赣南也有二三十万”,“赤色区域的群众,无论男女老幼,都参加他们自己的组织。”(29) 在苏区内,除老弱及部分富农外,都是农会会员。“农协的男性会员四十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上,都参加赤卫队的组织,二十一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都参加少年先锋队的组织。”(30)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3年时间里,仅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参军的农民就多达207万。此外,各地农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随军行动,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民兵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参政参军的政治意识外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群体行为,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总之,经过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尤其是通过参与政权建设,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政治热情高涨,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充分显示了其政治心理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持续转变的态势。
三、革命根据地民众道德心理变迁的新趋向
道德心理,是以舆论、榜样、教育等方式来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准则与规范在观念上的反映,它与政治心理一样也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心理领域的反映。
中国2000多年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伦理工具是“尊卑”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主奴”道德观。这种旧的封建观念浸润于中国普通百姓的道德意识之中,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就是认为纳税、服役、唯命是从是天经地义的。此外,中国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通过对三纲的神圣化、孝道的政治化和贞洁的非人化,导致伦常关系的异化,使封建道德伦理成为束缚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31) 因此,打破封建旧道德规范,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民众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随着苏维埃运动在革命根据地的推进,那里的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了以往所不曾有过的权利和地位。江西兴国县高兴区上村乡青年女工刘长凤的一番话颇能反映革命前后苏区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她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却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都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的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兴国就有很多妇女当乡苏主席和委员。”(32) 这表明,在苏区内从前妇女唯男子之命是从的旧情形已被男女平等、妇女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新景象所取代。革命根据地妇女翻身解放与参政议政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封建道德反叛的一个突出表现。
此外,根据地民众树立新的家庭道德和婚姻观念也从另外两个层面体现了人们道德心理的变迁。纵观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和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伦理道德就是在三纲五伦的基础上展开的。“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规范的是家庭内部关系,要求子女和妻子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和丈夫,而“五伦”中的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调节家庭伦常关系的。在旧家庭伦理道德支配下,人性被严重扭曲,尤其是广大妇女更是深受其害。当年闽西流传的一首《妇女苦情歌》真切地反映了女子悲苦的命运和不幸的遭遇:“荷树叶子叶连连,想起妇女真可怜,一周三岁拿来卖,当猪当狗卖给人。荷树叶子叶青青,细生妹子唔当人,家娘家官常打骂,拳打脚踏不留情。”(33) 而这些悲惨的境况又是与旧的婚姻制度和家庭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废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革命根据地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体现于:在党的代表会议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改革旧婚姻家庭制度的纲领;根据地的立法机关加强家庭婚姻立法,制定的婚姻法均以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为宗旨。如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中提出,彻底地摧毁半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引导妇女群众走上解放道路。“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反对买卖妇女”(34)。又如1931年7月,湘赣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条例》规定:废除一切包办、买卖、欺骗式婚姻制;禁止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婢蓄妾;打破守节制度,禁止童养媳。同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章“原则”也明确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这些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推动根据地婚姻家庭制度的破旧立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地民众的家庭道德发生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往昔受封建礼教束缚而带来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三从四德、守节等陈腐观念和愚昧陋习已被人们所逐渐抛弃。当时的一首《结婚歌》反映了这一方面的变化。歌中唱道:“婚姻从来是包办,男歹女好真可叹”;“买卖婚姻最害人,不是配偶硬对亲,巫顾那男女终身”;“于今婚姻不须忧,男欢女爱真可逑,结婚呵有了自由”;“从前嫁出哀哀叫,今下结婚哈哈笑,自由权岂不重要”;“两情欢恰叶无连,一生到老巫闲言,恋爱呵实在值钱”;“还有离婚也要讲,总爱理由来正当,不管他谁人阻挡”;“离婚结婚莫传人,自己目标要认真,方免得贻误害终身”(35)。另据1933年1月《湘赣苏区团省委青妇部报告》,在永新、莲花、茶陵、安福、吉安各地,大多数的翁姑已不欺负媳妇,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和入校读书等成为苏区的新景象。但在这一些地方仍存在虐待妇女、包办婚姻的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又先后颁布了一些婚姻条例,作为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实行变革的法律依据。如《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等。随着这些婚姻法的实施,根据地的不少男女青年开始意识到婚姻大事与自己的生活幸福紧密相联。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宣传鼓动下,婚姻自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家长不征求子女的意见而随意拉郎配的做法受到青年人的抵制和反对。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不平等的色彩十分浓厚。尽管如此,但乡村家庭中离婚现象并不多见。在中共组织和民主政府的宣传引导下,根据地妇女焕发出与旧传统、旧道德决裂的叛逆精神,她们不再忍声吞气,逆来顺受,一些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妇女开始主动大胆地到民主政府部门提出离婚请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对此用了一定笔墨加以叙述:“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36) 另据晋冀鲁豫边区1947至1948年的统计,涉及夫妻关系不和的婚姻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70%到97%,这些案件也大多是女方提出的。此外,据山西省平顺县1948年的统计,在140件要求解除婚姻的民事纠纷中,女方提出的竟达112件之多(37)。以往只有丈夫休妻的权利,如今女方对不满意的婚姻主动提出离婚,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夫权的式微。
根据地民众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还反映在新道德观念的逐步树立,新的价值观促使人们淡化个人利益,慷慨奉献。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为和睦相处,生产互助,新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
翻阅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苏区民众积极纳税和要求增税,超额购买公债甚至自动退还公债票(即不要政府偿还)等感人事迹频频映入眼帘。如为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行公债,原定龙岩县推销8000元,结果该县群众踊跃购买,共认购13000多元,超过原定计划5000多元,其认购数量在福建苏区中名列第一。此外,该县农民还用现金缴纳农业税,一些不满二石谷田按规定可以不缴纳农业税的贫苦农民也自动要求不免税(38)。1933年2月,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人员将按有关规定红利所得的10%的酬金仅留下200元作为生活费外,其余1114.43元全部捐给苏维埃政府作为革命战争经费(39)。
革命根据地经济基本上属农业经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农忙季节不少农户因缺少人手和畜力常常误工违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根据地人民政府积极倡导组织劳动互助,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就建立了不少耕田队、割禾队,帮助红军家属从事生产劳动,拥军优属、互助友爱蔚然成风。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农民的劳动互助形式主要是“变工”和“扎工”。所谓“变工”即换工,是指在不改变土地、作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或人工换人工,或牛工换牛工,或人工换牛工等,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少出的农户以工钱补偿给多出的农户。“扎工”,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户组成一个劳动集体,除相互变工互助外,也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劳动互助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据米脂县有关资料记载,一些变工队主动给病人代耕,尽义务,不用还工。“不能个人主义”已经成了变工队的口头禅(40)。上述这些事例表明,纯粹义务帮工行为对于改变小生产者自私自利观念,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根据地民众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还适时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开展表彰劳动模范先进事迹的活动,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边区社会的主体精神,人们普遍确立了“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艰苦奋斗光荣,怕苦怕累可耻”的荣辱观。尊重劳动英雄,努力增产,成了边区民众的主流意识和行为准则。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8页。
②③(3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99~200、178页。
④《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⑤武平民歌,转引自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⑥《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⑦作者佚名,丁一岚、王必胜校订,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第18辑),1982年铅印本(内部发行),第19页。
⑧张稼夫:《晋绥边区生产会议总结》,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3页。
⑨中共晋绥分局:《关于1948年分配土地问题的参考材料》,1948年7月27日。
⑩(晋绥)《五分区代表团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
(11)习仲勋:《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
(12)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篇),第815页。
(13)[美]葛兰恒等著,麦少楣、叶至美译,陈秀霞编:《解放区见闻》,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14)《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15)(18)(19)《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参考资料》编辑组:《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1981年铅印本,第319页。
(16)《江西省委转录赣西特委第七号报告与赣西特委对省委去信的意见和执行的决定》(1929年6月28日)。
(17)《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3日)。
(20)《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4页。
(21)定龙:《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1930年2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版,第58页。
(22)(30)克珍:《赣西苏维埃区域的现状》,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版,第79、77页。
(23)代英:《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1930年3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版,第72页。
(24)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25)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26)谢忠厚、居之芬、李铁虎:《晋察冀抗日政权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27)(28)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1~92、96~97页。
(29)《赤光普照的赣西南》,《中国苏维埃》,1957年版,第81页。
(31)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7~178页。
(32)刘长凤:《苏维埃女工的话》,《红色中华》1934年3月8日,第6版。
(33)细生妹子,指童养媳;家娘家官,即婆婆和公公。见谢济堂编:《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3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8页。
(35)巫:客家方言,意为不、没有。见万平近主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37)傅建成:《20世纪上半期华北乡村家庭关系实态与变迁分析》,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38)《龙岩群众热烈购买公债与纳税》,《红色中华》1932年9月6日,第6版。
(39)《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人员捐助巨款给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2月22日,第3版。
(40)《米脂县1944年春耕变工总结报告》(1944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