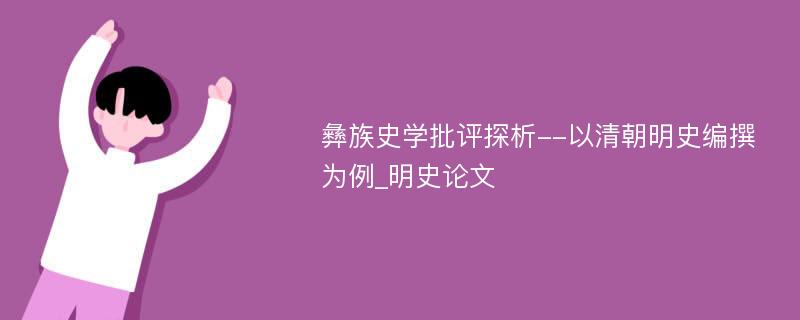
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以清朝《明史》修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史学论文,为例论文,清朝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08)06-0050-04
我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官修《明史》便是易代修史的产物。清朝《明史》修纂断续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4朝,至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成书,历时大约为95年,前后参与人数达190余人。乔治忠先生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中将清朝《明史》修纂大体分为4个阶段:顺治二年至康熙六年,《明史》纂修的准备阶段;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八年,《明史》纂修的奠基阶段;康熙四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废弛与中辍;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明史》纂修的完成阶段。[1]4阶段的划分符合清朝《明史》修纂的实际情况。《明史》修纂先由众多纂修人员分题并拟成史稿,然后总裁在其所拟史稿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修订、增补、润色、综合而成。康熙朝,《明史》修纂形成了两个综合性史稿,即416卷本《明史稿》[2]和310卷本王鸿绪《明史稿》[3],殿本《明史》[4]在这两个综合性稿本及纂修官所拟史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严格地审定,在体例、传目、质量等方面远远高于前两个综合性史稿,它凝聚了监修、总裁和众多纂修官的心血与智慧。通过详细考察《明史》修纂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监修、总裁和纂修人员不仅发表对明代历史的看法和评价,还注意将史学批评与修史实践相结合,对《明史》修纂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积极发表评论。
一、追求信史,秉笔直书
面对明清易代的历史事实,清初士人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明朝灭亡的原因遂成为清初士人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从批判明代空疏学风入手,深刻反省明代灭亡的原因。他们极力提倡“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这有力地促进了清初学术风气向实学思潮的转变。清修《明史》无疑也受到这股实学思潮的影响。如,康熙帝多次强调《明史》修纂应核实史料、考辨史事、以《实录》为据、纠《实录》记载过当或失实之处、追求信史,强调史书“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5](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三年,史馆订立指导《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其中亦指出:“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彰,先人无善而他人带为谀语,均不可也。今日仕宦诸君先世多有显达,若私滥立传,能无秽史之讥?愿秉公心共成直道。”[6](卷二)在《明史》修纂的全过程中,监修、总裁和纂修官屡次强调修史应追求信史和秉笔直书,并将其贯彻到修史实践中。如,潘耒在《修明史议》中强调修史应“秉笔欲直,持论欲平”,表达了“国不可一日无史,史不可难而弗为”的思想。[7](卷四)他还在《国史考异序》中强调直书的重要性。“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8](卷六)朱彝尊在史馆7次上书总裁,阐明信史思想,认为修史应客观地定是非,别黑白,不应先存门户之见。他说:“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9](卷三十二)康熙二十七年,毛奇龄在《奉史馆总裁札子》中对先前所撰《梁储传》作进一步辨证,他认为《通纪》、《藏书》及诸野史记载梁储有“草制”、“草敕”、“沮居守”、“斥护卫”四大事,实际上是野史的附会,提出“捏造非史”的主张。[10](卷十一)纂修人员追求信史,孜孜不倦地考辨史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殿本《明史》记载史事的客观性。
二、对明代史料的考辨
在《明史》修纂的过程中,史馆汇集的资料非常宏富,利于纂修人员在史馆对明代史料进行考辨。他们考证明代《实录》和野史的不足与失实之处,广泛搜资料并与《实录》相互考核。众多纂修官在史馆多次上书请求广泛搜集明代史料。顺治十二年,汤斌提出修史要以《实录》为据,建议及时搜集野史及郡县志乘,重视搜集明末抗节死事诸臣事迹,主张褒扬忠义之士。[11](卷二)康熙十九年,施闰章上《修史议》,提出《明史》修纂“考据”、“核实”之难,主张凡所见、所闻、所传闻均为异词者则存疑。[12](卷二十五)崇祯朝无《实录》,给修史带来了很大困难。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七书》中认为《明史》成书尤其难于万历之后,各种稗官野史参差不齐,是非难辨,主张编纂《崇祯长编》时不宜只据十七朝邸报,而应将史馆四方所上之书凡涉及崇祯朝的史事者一一贯穿,并分年录写,并提出对明末死事诸臣的言论辨而核的主张。[13](卷三十二)康熙十九年,史馆接受汪楫的建议,万言、汪懋麟、汪霖等人根据崇祯朝邸报及相关资料,编成《崇祯长编》,以备修史参稽。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中认为修史必先聚书籍,认为一代之史不可只据《实录》而成,应搜集馆中没有的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以备修史之用。[14](卷三十二)。汪由敦提出辨别史料真伪之方法,即根据立言之人的心性及所处之地进行判断。他还强调了《实录》的重要性,认为《实录》虽有曲笔之处,但不像野史一样凿空无稽,主张修史以《实录》为主,采用野史和《实录》互参的方法。主张在录用大臣奏疏时注意保存大体及史事原委,认为有数人共事且有数谏者,录其犹当者存之。[15](卷二十三)。在《明史》修纂过程中,纂修官修史主要取材于《实录》,并与其他明代资料,相互考索,辨别异同。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有力地辩证了明代史事不可信者十余事。杨椿认为,永乐初明成祖朱棣实际上没有革除建文年号,而是当时钦天监在《日历》中因避讳而不敢直书建文年号而改之为洪武,明成祖朱棣对此未加禁止,于是诸臣上书相继沿袭,改为洪武三十二年、洪武三十五年。而到了万历年间,王祖嫡请求复建文年号时,大学士申时行以《成祖实录》中还书有元年、二年、三年来回答。[16](卷二)杨椿由此根据《实录》记载纠正了野史的错误。
此外,雍正、乾隆两朝《明史》修纂工作主要是在王《稿》的基础上进行考辨史事、增补史料、润色词章等工作,订正了不少王《稿》的错误,考证成果大多已被《明史》采纳。
三、明清历史断限问题的转变
明清易代之际,清朝统治者将明代灭亡时间定为崇祯十六年,不承认南明的历史地位,认为是僭伪政权。顺治二年,清廷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急忙宣布诏修《明史》,这一举措无疑意在表明明朝国祚已终。但徐乾学在《条陈明史事宜疏》中认为,福王、唐王、桂王之历史为明朝之延续,虽大势已去,但一代历史之始终不可不详,故建议仿照《宋史·瀛国公纪》以列传附益、卫二王事迹之例,将福、唐、桂三王事迹附于《崇祯本纪》后,并削去“僭伪”之号,存留三王事迹,表明明朝历史之始终。后《修史条议》中也说:“《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17](卷二)显然是沿用了徐乾学的主张。但由于清初政治斗争复杂,明清历史的断限问题又是清初较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清朝官方迟迟不承认南明政权的合法性。乾隆四年,张廷玉曾在《进呈明史表》中再次强调宜于崇祯十七年后附载福王史事,于顺治二年后续载唐王、桂王事迹,但清朝官方仍然没有采取他的意见。最终,《明史》作为清代的官修史书,在明清历史断限问题上与官方意见保持了一致,仍以崇祯十六年作为明代历史的终结,于《崇祯本纪》后未附三王事迹。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很多“殉节”人物,如何对待和评价“殉节”人物也是清初较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朱端强先生在《布衣史官万斯同传》中将“殉节”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殉国”和“殉节”人物;另一类则是清初反抗清朝而为明朝“殉国”、“殉节”的人物,而这一问题实际上又与明清两朝时间断限问题密切相关。[18]由于清初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所以清廷认同和褒扬的只是第一类“殉节”人物,而不承认在清初反抗清朝而为明朝“殉国”、“殉节”的人物。《明史》亦然。乾隆二十四年,官修《御批通鉴辑览》时,清朝官方才在这明清历史断限问题上有所松动。乾隆命在顺治元年用大书注明福王元年,1645年之后还附唐王、桂王事迹。顺治二年福王被执,遂成为明朝历史终结的标志,而清廷官方至此才对明朝灭亡的时间作了定案。乾隆时期,随着清朝政局的稳固,乾隆帝对明末清初反清的“殉节”人物和投降清朝的人物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如,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下令集议谥明靖难殉节诸臣和表彰明末清初抗清人物。同年十二月,下令将清初降清人物如洪承畴、冯铨、钱谦益等编入国史《贰臣转》。乔治忠先生认为,清朝官方对明代灭亡的时间和明代正统转移等重大问题上的界定,其目的是为表彰明末抗节的忠义之士及事迹扫清障碍,这是表彰明末抗节人臣的先奏。[19]显然一语中的。
四、对体例方面的商榷
清官修《明史》的过程中,纂修官对体例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在史馆考察历代史书体例的得失,并就《明史》体例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殿本《明史》大多采纳。
(一)建议《明史》不设《道学传》。《修史条议》主张《明史》仿《宋史》例,设立《道学传》,把王守仁归入《名卿列传》,王派弟子则归《儒林传》。可见,将王守仁排挤出《儒林传》和《道学传》之外。《修史条议》关于设立《道学传》的建议及对明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在朝野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除彭孙通等少数人赞同外,汤斌介于可立可不立之间。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从不同角度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史馆最后决定《明史》不设《道学传》,只列《儒林传》,但仍坚持《修史条议》中将王守仁归入大传的决定。这是清朝遵奉程朱理学、排挤王学、立门户之见在《明史》编纂中的反映。史馆的最后定论实际上也间接地平息了这场激烈的争论,反对者对王守仁不入《儒林传》比较满意,宗奉者对王守仁入大传也心服口服。徐乾学等人能改变自己的主张,广纳朝野学者的建议是难能可贵的。[20]
(二)主张《明史》设立《土司传》。朱彝尊主张《明史》设立《土司传》。他在《土官底簿跋》中说:“予在史馆,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毛检讨大可是予言,撰《蛮司合志》,因以是编资其采择焉。”殿本《明史》采纳了朱氏的建议,这也就成为它在体例方面的创新之一。
(三)其他有关体例问题的见解。汤斌在《明史凡例议》中集中体现了他对《明史》体例问题的相关见解:其一,认为明太祖四代考妣应只于《本纪》内载明,不必另作附纪。殿本《明史》采纳。其二,主张兴宗当称懿文太子,睿宗当称为兴献王,不入《本纪》,列于《诸王传》之下。殿本《明史》亦采纳,将二人单独立传。康熙二十年,姜宸英入史馆,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姜宸英根据明代特有的酷刑,于《刑法志》中创设了《廷杖》、《厂卫》、《诏狱》专目。殿本《明史·刑法志三》中有专门论述。尤侗编纂《明艺文志》5卷(已佚),其体例只著录明人著述,后来黄虞稷撰《明史艺文志》4卷时采纳,经王鸿绪《明史稿》稍加审定后采入。而殿本《明史·艺文志》直接采纳王《稿》。《艺文志》只录明人著述,这也是殿本《明史》在体例方面的创新之一。王源认为王越不宜与李孜省、继晓同传,徐元文采纳其建议,但又将王越与陈汝言、陈越、戴晋归入同传。王源认为不妥,特上《与徐立斋论王威宁书》,进一步阐释王越与陈汝言、陈越、戴晋实非同类,不应归入同传,主张将王越与杨善、王骥归入同传。殿本《明史》将王越、王骥、杨善归入同传,采纳了王源的建议。
五、对明代史事的评价
清修《明史》时,对明代某些重大问题众说纷纭。如,建文帝下落、靖难之役、英宗复辟、大礼议等。建文帝下落是史实无征而带来的裁决困难,靖难之役、英宗复辟、大礼议则是虽有史实记载,但评价困难。纂修官在探讨明代史事时,以《春秋》大义、名教大防作为他们发表评论的立足点。从纂修官的言论看来,《春秋》义理、名教、惩劝等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纂修官对史事的裁决,有些评论或争论的结果也直接影响了殿本《明史》的定论。
关于建文帝下落问题,无论主“崩死宫中”,还是主“逊国”,其实背后均暗含着对明成祖朱棣取得地位的谴责或宽容。朱彝尊、陆葇、陆奎勋、杨椿主张建文帝“崩死宫中”。徐嘉炎、邵远平、尤侗等人则主张建文帝“逊国”。徐嘉炎分撰《建文帝本纪》时,主建文帝“逊国”之说,陆葇审稿时,可能受朱彝尊辩证建文帝“逊国”不足信的影响,又削去了“逊国”之说[21](卷四十五)。《修史条议》则说:“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据。其尤诞妄者,史氏《奇忠志》、《忠贤奇祕录》二书是也。史贵阙疑,姑著其说,而尽削其从亡姓名,不以稗官混入正史可耳!”[22](卷二)但邵远平仍然主张建文帝“逊国出亡”之说,他特撰《建文帝后纪》和《逊国人臣传》,激烈反对《修史条议》的看法。[23]王鸿绪《明史稿》则曰:“帝崩于火。”又说:“阖宫自焚,以死殉国,建文之正也。后人不见正史,妄相附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损,故诡言刘基之祕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24](卷二)但陆奎勋则力主建文帝“崩死宫中”,他说:“金川之变,《实录》称:‘建文帝阖宫自焚,中使出其尸于火,越七日备礼葬之。’夫国君死社稷,义也。据《实录》所载,纤毫无损于建文。”[25](卷十一)这也表明陆氏在评论史事时深受《春秋》义理的影响。杨椿也主建文帝“崩死宫中”,并在《孟鄰堂文钞》卷三《惠帝论一》、《惠帝论二》、《惠帝论三》[26]中更详尽地加以考辨。如,他在《惠帝论三》中考辨《实录》记载不当之处,认为燕王中使迫使建文帝自焚,或建文帝自尽后,被燕王中使所焚。殿本《明史》则云:“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显然存其说而不加评论,没有过多地谴责明成祖之意。
关于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事,纂修官多持批评态度。朱彝尊主张应以《实录》为据。他说:“世之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录》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27](卷三十二)陆奎勋认为“靖难”之役只是燕王篡夺皇位的借口。燕王自称按照《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藩王就可以举兵以“清君侧之恶”,但燕王的行动与《祖训》并不相符,他援引《祖训》不过是断章取义,举兵理由也并不充分。杨椿在《惠帝论》中也认为“靖难之役”与汉“清君侧”表面相类而其实不同。七国之乱源于削地,当时诸侯没有军队和虎符,故起兵不易。而明靖难则源于夺取帝位,其封地内有军队,而“清君侧”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从而贬低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诡诈方式夺取帝位。他说:“古之得天下者,有正有谲。正者,仁义;谲者,假仁假义者也。燕王则仁义不施,而诈谖权变之术胜,固不可谓之正,并不可谓之谲……”[28](卷二)蓝千秋也认为靖难诸臣是“乱臣贼子”,激烈反对将邱福列入《功臣表》。[29](卷十八)对此,殿本《明史》没有采纳。
关于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位之事,纂修官多有评论。《修史条议》中说:“夺门之事,当以为罪,而不以为功,如以徐、石为是,则景帝之勒死何辜?”[30](卷二)雍正年间,陆奎勋则根据《春秋》义理思想来贬低“英宗复辟”,认为是历史上“千古仅见之事”。他认为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已是最大的耻辱,他侥幸生还,假使明景帝“晏驾”,群臣奉迎他为皇帝也应当极力推辞,更何况发动“夺门之变”来夺取皇位呢?陆氏认为明英宗失地辱国,是不能再入主皇位的[31](卷十一)。检《明史·英宗纪》赞语中亦未提及“夺门之变”。
关于嘉靖初年“大礼议”问题,纂修官中多有论述者。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不仅在明代争论得非常激烈,而且在清修《明史》过程中亦引起很大争议。“大礼议”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与宗法制的紧密关联,即皇帝生为帝统,死为庙统,强调皇位继承之间的统系分明。嘉靖皇帝以宗藩入继,必然会带来“继统”与“继嗣”的争论。施闰章在史馆反对门户之见。他说:“议礼则予张、桂,而绌杨、罗;讲学则祢紫阳,而祧新建。百喙争鸣,几成聚讼。尤可异者杨、左、崔、郑,黑白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论之难也。”[32]施闰章对议礼则偏向“继统”反对“继嗣”;对讲学则推崇朱熹,而贬低王守仁;“三案”旋定旋翻,提出批评。汤斌则主张兴宗应称懿文太子,睿宗应称为兴献王,不入《本纪》,仿“《汉书》定陶共王例”,列于《诸王传》之下,认为“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统系分明耳”!徐乾学《修史条议》赞成“继嗣”,反对“继统”。“张、桂之议礼,祗以献谀,何曾知礼,惟富贵之是图,遂名教之不顾,诚小人之魁,士林之贼。”[33]毛奇龄折中“继统”与“继嗣”,毛氏主张明世宗可以为明武宗后,目的在于强调嘉靖帝得帝位之正,但仍主张其所生父母亦不改称。[34]陆氏虽赞同“大礼议”中的“继统”,但反对明世宗将其父兴献王“称宗入庙”之举。陆奎勋认为明世宗继位是“兄终弟及”,不应以“汉定陶王”、“宋濮王”为例,认为张璁上“继统不继嗣”之疏,本意为了迎合明世宗,但“其说近正”,故认为明世宗立世庙祭祀其父,以孝宗为“皇伯考”是合情合理的。但他极力反对嘉靖十七年明世宗追尊其父为睿宗,并衬祭于太庙之举,谴责天启时礼官把明宪宗神位迁入祧庙。[35](卷十一)汪由敦也反对将懿文太子和兴献帝合传,认为兴宗、睿宗只是尊称之辞,与身为皇帝者有异,如果入传,则紊乱帝系。
综上,纂修官围绕《明史》修纂而展开的史学批评,对《明史》的成书和质量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此,希望通过对《明史》修纂中上述几个问题的深入论述,能对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的探索有所助益。
标签:明史论文; 明朝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春秋论文; 明史稿论文; 康熙论文; 崇祯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元史论文; 宋史论文; 东周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