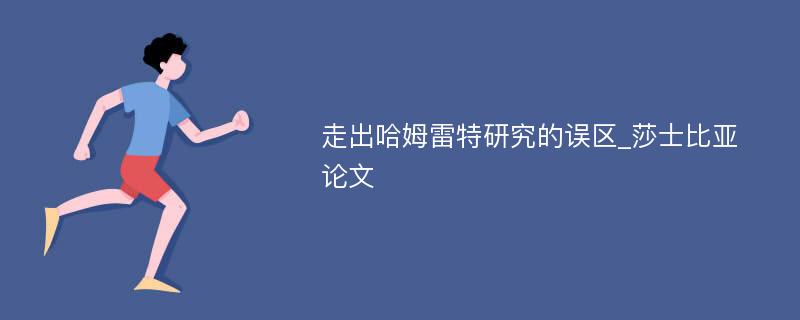
走出《哈姆莱特》研究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特论文,误区论文,哈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长期以来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研究中存在的因袭陈说、主观片面、脱离实际(时代、作家和作品的实际)、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等谬误和弊端,指出其原因在于对前苏联莎评无批判的吸收和外国文学评论界的积重难返。文章对整个莎士比亚研究也多所涉及。
关键词 弊端与谬误 前苏联莎评 正视与反省 实事求是 走出误区
多年来,我国对《哈姆莱特》及其作者的研究总是在同一误区里徘徊,虽然有时也吹起一陈陈清风,但始终未能走出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杨周翰先生曾经指出的前苏联莎评的误区。80年代伊始,杨先生在《二十世纪莎评》中介绍和评价过前苏联莎评的特点:
……1)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2)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他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3)强调莎氏之人民性;4)与以上诸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5)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往往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氏文过饰非,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但明明也有藐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但苏联学者多避而不谈,相反,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的思想意识的倾向。帝王将相的品德在他们笔下也说成是非帝王将相所独有。莎氏在写悲剧时明明已堕入悲观的深渊,他们必定要说并不悲观。这种一味肯定,同传统的浪漫派莎评如出一辙。他们强调现实主义也有片面或表面性,突出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忽略人物是莎氏思想的传声筒,忽视莎氏的主观意图的一面。而且分析的公式化,使读者很难看到评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的看法。[①]
杨先生的介评是实事求是的,只是在谬误几乎淹没了优点的情况下还肯定其基本正确,未免欠妥,而且也不宜将这样的莎评称为“马克思主义莎评”,因为“缺乏辩证观点”的莎评,算不得马克思主义莎评。
由于对苏联莎评照搬,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既有苏联莎评值得怀疑的优点(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未必真能贯彻,把莎作都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未必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也承袭了它的缺点。对此,不少学者早有清醒的认识。卞之琳先生指出过无中生有大肆发挥莎士比亚“平等”观念和断言哈姆莱特爱人民也受人民爱戴的谬误,并且还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之类的悲剧进行分析,在它们的社会反映和社会意义上,可能拍合得太‘巧’了,也就是机械了,简单化了,而在艺术分析上又说得太天花乱坠。”[②]几乎同时,陈嘉先生也发表过几乎相同的意见:“对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的高度推崇,是西方文艺评论界几乎一致的态度。苏联评论家更进一步,把他捧上了天,使他几乎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至少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者。十多年前我本人曾追随后一种看法。现在看来,未免过火了,带有片面性。”[③]
上述三位著名学者的洞见,应能振聋发聩,但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并未因此走出误区。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上述正确观点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杨先生是在介绍二十世纪国外莎评中介评苏联莎评的,许多人不能或不愿看到中国莎评与苏联莎评的师承关系,因而不能反躬自省,而且杨先生虽然指出了苏联莎评的得失,但他与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仍沿袭了苏联莎评(而没有考虑到60年代起苏联人如阿尼克斯特等观点的改变),这就抵销了对其错误的正确批评。卞先生与陈先生的观点可惜都未展开作具体、全面、深入的论述,而且令人遗憾,正确意见未能一以贯之。陈先生指出丹麦王子关于“改造社会”的言语的实质,却又象不少论者一样将哈姆莱特“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那番话截头去尾,认为是“对于人类怀着崇高信念的语词”,具体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所在”。[④]卞先生批评有人曲解戏文而随意发挥,但先生也同样曲解了戏文而不恰当地发挥。如谓“(哈姆莱特)接受报仇任务,从一开始,就联系了整个社会的斗争任务”,在“追问自己‘活下去还是不活’的时候,并不想到自己个人的不幸,而只想到社会的不平”。[⑤]
第二个原因是外国文学评论界的反应。这里有一个避难趋易和积重难返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但因过于迅速,许多人便走了捷径。如果接受上述的正确观点,就得一切从头做起,从我做起,这太难了,远不如照搬《欧洲文学史》和孙家琇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类的来得容易。在我国,某种已被接受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正确而稳妥的观点,50年代从苏联搬过来的观点和方法,不知不觉已被视为国货,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清醒者的呼吁被当成了耳旁风,少数人要改变局面的努力,被习惯势力的大海淹没而成为徒劳。
笔者深感彻底反省改弦易辙的必要,特就《哈姆莱特》的研究作一番深入的探讨,找一找弊端和谬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如能使人走出误区,共同去开辟新的天地,笔者则不胜欣幸。
概括地说,过去的研究,总偏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面,而疏于文学和美学的方面;对莎作,总是从编造的莎士比亚神话出发,不是评价其优劣,而是证明其如何高妙,如果批评,至多千篇一律地指出所谓朝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往往以未加证明的前提,推论出牵强附会的结论,因而陷入逻辑的怪圈;总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而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采用的观点和方法往往倒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时,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甚至指鹿为马;分析人物形象时,总象小孩子看电视,只会将人物分好坏,贴标签,而根本不顾人的复杂性……
以上弊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许多论者都喜欢强调这一点,潜在的意思是莎士比亚处处进步,一切正确。似乎这一来,莎士比亚创作必然遵循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其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必定跟他一样是人文主义者;剧中正反两面人物的冲突,必定代表先进阶级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至于艺术表现,必定尽善尽美,无懈可击。这种对莎士比亚的潜在的美化是主观主义的。且不说“文艺复兴”有其深刻的局限,人文主义并非完整的体系,人文主义者五花八门并非个个代表进步,我们只消来看一看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安东尼·吉伯斯在其《莎士比亚》的开头就说:“莎士比亚在戏中说了许多反对追逐功名利禄的话,但这只是戏,只是供人们打发三两个无聊时辰的娱乐,不是作者深思熟虑之后表达自己信念的严肃声明。关于这个手套工匠、剧作家、诗人、演员和乡绅的人品,我们知之甚微;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一点就是,他热衷于功名利禄。”“对于他,能买下休·克洛普顿爵士留在斯特拉福镇的那所房子,并在那里扮演他最后一个角色,即充当退隐的普通乡绅,这已经是心满意足的了。”[⑥]这实在有损于许多人在我们心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但我们有谁能象莎士比亚的同胞而且是专门研究其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同胞吉伯斯那样了解他呢?没有光环的莎士比亚不过是出卖演技、剧本和兼任剧团股东的商人,“对于自己的私事比对于公众的事务更有兴趣”。[⑦]这样一个莎士比亚,会象我们按某种框框设想的那样去写作吗?有人总想在莎剧中寻找反映阶级斗争的光辉思想、微言大义,读读吉伯斯的大实话,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在意识形态上,有人甚至认为莎士比亚坚持的是中世纪的传统。美国评论家哈里·布拉迈尔斯在其《美国文学简史》中论及《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时指出:“这三大悲剧探讨了个人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宇宙内部蔓延的紊乱。莎士比亚和许多在这方面坚持中世纪传统的人是一致的……这些一致之处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的尤利西斯关于‘秩序’的著名演说中,作了概括性的说明”[⑧]。这样看来,有什么必要强调“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呢?
第二,关于“人文主义的典型”。除少数人曾著文表示不同意见外——如陈绍棠《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吗?》[⑨]——外,这几乎成了《哈姆莱特》研究的定论。这是仍然包含着潜在的推论:人文主义者是进步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更是进步的,因此,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斗争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不过,所谓“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的论据并不可靠,论证也不合逻辑。论者说,哈姆莱特在人文主义的堡垒威登堡大学读书,所以是人文主义者。在此,威登堡大学之为人文主义堡垒未经证明,即使确为堡垒,也不能断言哈姆莱特就是人文主义者,正如在我国高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按论者的逻辑,甚至可以证明雷欧提斯是人文主义者,因为他在信奉新教的法国留学,而新教是文艺复兴的另一形式宗教改革的产物。至于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既与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同学,其为人文主义者更是无疑。论者又以哈姆莱特对世界抱有美好看法作为论据,而这一论据的论据则是哈姆莱特那段“我近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的对话。那番话中,装疯的哈姆莱特禁不住表露了真情:过去认为世界很美好,人很伟大,现在却认为世界非常丑恶,人非常渺小,因此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变化的原因哈姆莱特推说不知道,其实很明白,那就是父亲被人谋杀,母亲被人淫辱,自己失去了王位。这一段反映哈姆莱特情随事迁的话竟被论者截头去尾,任意拼凑。如果可以如此,不是可以另行拼凑成“大地是一个不毛的荒岬,世界是一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不过是由泥土塑成的不值钱的生命”,从而证明哈姆莱特是一个对世界怀着阴暗的看法的反动人物吗?论据之三是奥菲莉娅对哈姆莱特的赞美。“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目的一朵娇花;时流的名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⑩]不仅证明哈姆莱特是当之无愧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甚至被当成是对恩格斯关于“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11)的诗的表达。我们不必象吉伯斯那样把“对于辞令、诡辩和俏皮话的癖好”看成莎士比亚的弱点,(12)也不必根据“情人眼里出西施”怀颖奥菲莉娅是否有溢美之嫌,笔者只想指出,如仅凭他人的赞美来判定一个人,雷欧提斯也堪称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五幕二场有一段哈姆莱特热情称赞雷欧提斯的话,那番称赞不亚于奥菲莉娅对哈姆莱特的赞美。有人甚至将莎士比亚把哈姆莱特作传声筒大谈戏剧的话(见二幕二场),通通当作哈姆莱特卓越品质的表现,说他“趣味高尚、喜爱文艺,尤其是戏剧……能即兴背诵戏文,编写台词,品评剧作”,说他“对演戏目的和表演艺术的理解,表现他头脑敏捷,充满睿智,显然能够领会伟大文艺复兴的卓越性质”,(13)真是极尽了歌颂美化之能事!这种生硬联系必然导致荒谬:波洛涅斯也演过戏——扮演过裘力斯·凯撒,而且也精通戏剧,长于品评(见二幕二场),波洛涅斯不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者吗?
第三是关于“重整乾坤”。“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这是哈姆莱特见过鬼魂,得知父王被害、王位被夺之后说的话,含义非常明确:克劳狄斯谮越了臣下的本份,用谋杀的手段窃取王位,就是“颠倒混乱”;君臣易位乃乾坤颠倒,把被颠倒的乾坤重新颠倒过来,便是“重整乾坤”;除掉克劳狄斯夺回王位责任过于重大,而他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深感倒霉。不少论者硬是牵强附会地说“颠倒混乱”指的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黑暗现实,“重整乾坤”则是指按人文主义理想改造社会,这一来竟把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说成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的较量。为了解释“进步力量”的失败,又不惜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地引用恩格斯的名言。他们说,哈姆莱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所处的朝代还缺乏先进分子必然胜利的条件。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谈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4)乍看之下,人们以为恩格斯的话是针对哈姆莱特的悲剧而言,然而一查出处却发现恩格斯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指的是济金根领导的骑士起义要求贵族与农民的联合,所谓“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指的是贵族与农民对立而不能联合,这对置于二者之间的济皇根是一个悲剧性的矛盾。(15)恩格斯的话跟哈姆莱特的悲剧,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重振乾坤”,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田民在《论哈姆莱特性格的模糊性》中指出,“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始积累)所带来的‘时代脱节’(旧秩序的大破坏)无疑是历史上的一次飞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哈姆雷特的只身‘重整乾坤’反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这一点来看,哈姆雷特倒有点象堂·吉诃德)”。(16)田民过于紧扣社会发展史,未免偏离文学批评,但他不事美化哈姆莱特,确实值得肯定。
第四是关于“世界是一所牢狱”。许多论者把“牢狱”之说说成是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对当时英国黑暗现实的揭露,采用的仍然是断章取义,任意解释的办法。记得二幕二场哈姆莱特与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对话的读者应该懂得,哈姆莱特的话,是疯话,也是真话。一个失去王位,生命危在旦夕的王子,忧郁、恐惧,把自己所处的宫中(“这儿”)、丹麦和世界看成束缚自己的牢狱,是最自然不过的,不必去找什么微言大义、潜台词。而且他也说得明白,天堂地狱因人而异,善恶也由不同的人所分别(由此我们应能看出莎士比亚的善恶是非观)。罗森格兰兹最后的话颇有道理:牢狱就是自己的野心。哈姆莱特不想当王,牢狱将不复存在。
第五,关于复仇和延宕。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哈姆莱特信仰上帝,本能地厌恶个人复仇,并认为个人复仇会遭天谴,故一再推迟行动。一种认为,哈姆莱特从接受复仇任务开始,就把它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深知关系重大,未敢贸然行动。第一种说法显然不通。莎士比亚在写作《哈姆莱特》之前,已写过几部表现个人复仇的历史剧,因而不会将反对个人复仇的观念加于哈姆莱特;老王也信仰上帝,他的鬼魂要求哈姆莱特为他复仇,可见复仇与否与信仰无关;哈姆莱特并未表现出对复仇的厌恶,他倒是念念不忘,不断责备自己,多次表示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去完成复仇大愿,他在克劳狄斯祈祷时放弃了杀掉仇人的机会,是为了“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说到“天谴”,哈姆莱特怕的不是复仇要遭天谴,而是不复仇要遭天谴,所以他说,“如果我不去翦除这一个残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至于第二种说法的谬误,上文在“人文主义者的典型”部分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第六是关于哈姆莱特的世界。《哈姆莱特》中描绘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或真实世界如实的反映呢,还是虚构的、幻想的世界?有人把作者借哈姆莱特之口说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当作莎士比亚创作的原则,著文《哈姆莱特的世界》,(17)把它当作真人真事的搬演,认为剧中描写的一切都可以从伊丽莎白末年的英国现实中找到印证。其实这种意见非常牵强。比如该文将“女性的堕落和淫欲横流”也纳入哈姆莱特的世界就违背事实,失之公允。在莎士比亚所处的英国社会中确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女性的堕落和淫欲横流”决不是成为问题的现实,剧中出现的两位女性,严格说都是受害者。王后的被夸大了的“堕落”是受了男人的诱惑,奥菲莉娅则完全是被人利用,谈不上“堕落”,更没有什么横流的“淫欲”。哈姆莱特指责母亲的乱伦和奥菲莉娅的背叛,实际反映了他(和他的创造者莎士比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由于把戏剧虚构的世界当成现实的世界从而把哈姆莱特之类的人物当成现实世界中实有的其人,作者遇到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难题。如作者为了美化哈姆莱特,说“哈姆莱特形象的人民性特征,更至于他那植根于民间文艺的风趣的语言特色”而又自觉不妥,不得不说“如果拿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一位王子尽用老百姓的用语或比喻,可能是个问题”,但最终仍不愿正视困境,竟以“莎翁所构思的,首先是他当代人文主义者的代表,而那些人文主义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们确是熟悉民间生活和各色人物的”这样想当然的理由来进行辩解,使读者实在不能信服。
文学作品的世界必定是想象的世界(虽然它有现实世界的某些影子),这应当视为常识。所以,上述《哈姆莱特的世界》的作者所否定的麦克·梅那德的意见倒是正确的。梅那德认为,哈姆莱特的世界不是丹麦,也不是伊丽莎白的英国,而只是“悲剧让我们进入的想象的环境”。(18)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开启《哈姆莱特》之门的钥匙。有两位英国人正是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哈姆莱特》的大门,解决了一直困扰人们的一大奥秘。
艾弗·埃文斯指出:“《哈姆莱特》对于那些爱好通俗情节剧的人们是一个谋杀、自杀、疯狂的故事;但是对于其他的人则是一次最精巧的人物性格的分析,又是一出诗句运用得十分巧妙的戏剧。”(19)
安东尼·吉伯斯谈到哈姆莱特那段“活下去,还是不活”的独白引起的困惑时说,“一些较为幼稚的观众会皱眉蹙额表示不解。因为这个人物明明已经证明,而且是通过自己父亲的亡灵证明,天堂与炼狱是存在的,却还想知道人死之后是否还会有什么,想知道‘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王国’。但是,一些比较聪明的观众懂得,这出新《哈姆莱特》其实是两出戏:一出是基德写的石老的复仇悲剧,有真正的地狱,复仇者可以将他杀死的恶棍投入其中;另一出则深入地探索了一个现代不可知论者的思想。这两出戏真能达到浑然一体吗?”(20)
这两位英国人意见的共同之处是,《哈姆莱特》是两出戏,讲两个故事,描绘两个世界。这样的两个世界必然是想象中的,而且难以浑然融为一体(如吉伯斯所担心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世界看成真实的,并且看成是一个,那么,剧中的许多问题,如“复仇”、“重整乾坤”、“延宕”等等,将永远是不可回答的“司芬克斯之谜”。
注释:
①见《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⑤见卞之琳《关于我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无书有序》,《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③ ④见陈嘉《〈哈姆莱特〉剧中两个问题的商榷》,《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
⑥ ⑦ (12) (20)见安东尼·吉伯斯《莎士比亚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⑧见哈里·布拉迈尔斯《英国文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版。
⑨见《惠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⑩见朱森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本文引剧中语皆同此。
(11)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3) (17) (18)见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4)见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6月版。
(15)参见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一书前附恩格斯致拉萨尔信,人民文学出版1976年1月版。
(16)见《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
(19)见艾弗·埃文斯《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