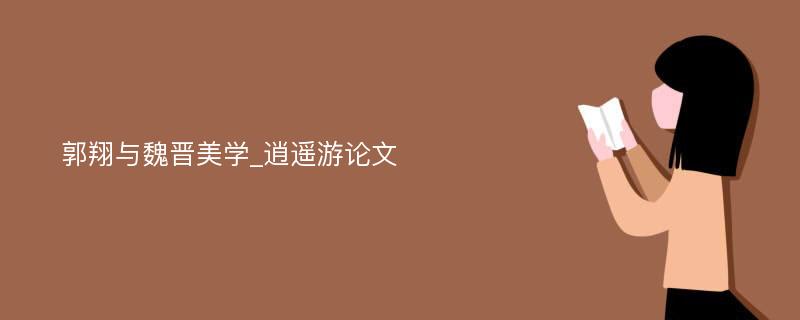
郭象与魏晋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4)04-0018-08
郭象(约252-312年),是魏晋时代紧随王弼之后以注《庄子》而出名的玄学家。郭象玄学是王弼玄学向两晋思想转折的关捩,也是玄学美学向中国大乘佛教的现象学美学(例如即色宗与禅宗的美学)演化的中介。有意思的是,魏时王弼在注《老子》、《周易》和《论语》时,运用高超的解释经典的智慧,创建了玄学贵无论。过了几十年后,郭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六经注我”式的阐释,对于王弼的贵无论进行消解,使玄学更趋圆融,同时消泯了其中的风骨,标志着两晋南朝人格精神的转型。魏晋美学的灵魂是人格精神,因此,人格精神的研究是我们分析魏晋美学变化的内在依据。正是基于此,本文拟就郭象美学中表现出来的魏晋美学变化的内在原因作一些分析。
一、“万物万情,趣舍不同”
魏正始年间产生的王弼玄学是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它以玄学思辨的形式,将建安风骨慷慨悲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情结向上提升,深化为远大玄淼的思理。在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高蹈云天、鄙弃尘俗的理想主义,故而当时的嵇康与后来的陶渊明很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这种形而上精神追求的实践者,嵇康为此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玄学的生命精神即是那个卓然标举的“无”、“大”、“道”等概念。这些精神性的概念是人格与宇宙精神合一的理念。王弼用本与末,母与子,有与无,一与多,自然与名教等对立统一的范畴来说明这些精神概念,旨在宣明这种理想的高尚。正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对于王弼玄学所追求的总体性和谐即理想境界所作的评价:“这是玄学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为人们所点燃的一盏理想之光,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1](P224)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这种理念又明显地带有调和自然与名教、精神与世俗的关系,它是当时士族心态的表现,士族的高蹈意识与世俗情结在王弼玄学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清楚,向秀本人就是一名与嵇康同属“竹林名士”的人物,尽管与嵇康私交甚笃,但是在思想旨趣上却相差很大,曾就“养生”问题与嵇康展开过论战。嵇康的《养生论》宗旨是宣扬洁身自好,远离世俗;而向秀则在《难养生论》中鼓吹“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将当下性的情欲作为人生的最高存在,是不可加以室抑的。向秀注解《庄子》,实际上是借此宣传自己的人生哲学,且勿论他与嵇康孰是孰非,单从其所论即可知正始名士内部的人生追求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分裂。《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嵇康被冤杀后,向秀被迫入洛做司马氏的官,虽然心里是不情愿的,观其所作《思旧赋》可见一斑,然而他经过这次惨案的刺激,再加上原先即存在的随顺时流的念头,因此,他入洛做官后应答司马昭的这番话,未尝没有真实想法在里头。意为嵇康效法古代高士的人格志向虽然为“隽介之士”,但不足多慕,做人应审时度势。这不应看做是向秀个人的意志问题,而是整个士人精神志向的转变。大厦将倾,其一绳所维?因此,随着士族发展到了西晋后期,由于命运的转折,理想的失落,士人精神走向世俗,乃是有其必然性因素在内的,是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的。郭象与向秀注解的庄子一书的关系,以往大多说他是剽窃。其实不然,里面更多的是思想的传导,精神的共通,表现出从魏正始到西晋年间士人思想的演进,并且在美学精神与文学创作上清晰地显示出来。
郭象对于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的解构,首先是从“有无相生“的论题作出自己的解答。在王弼看来,“无”是人格精神的表征。为了突出这一宗旨,王弼大力宣扬无的本体意义,它是寂然不变,应对万物的。而郭象则提出,既然有之为有,恃无以生,那么在无之前又是什么事物呢?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推理下去,势必会推导出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而无法自拔。另外,王弼哲学将无说成万物的宗统,而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独断论的成份,无法从逻辑上说清楚,故而王弼的贵无论具有审美的理想色彩而缺少推理,更没有实证上的支撑,王弼哲学确实也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与漏洞,因此,它被后人修正也是势所必然的。魏晋玄学的向前推进,必然意味着要对这些缺漏进行弥补。梁启超指出:“《庄子》郭注,剽自向秀,实两晋玄谈之渊薮,后此治此者罕能加其上。”[2](P68)这是很有见地的。郭象哲学既是对于王弼哲学的庸俗化,也是对于其缺漏进行修正的表现。郭象看到王弼贵无论在生成论上的不足之处,在《庄子·知北游》注中首先就此问题提出:“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郭象明确提出,“有”作为一种现象与存在,固然不能从自身获得自证,但是它更不可能从“无”之中而产生,因为一旦要从“无”产生,势必要关涉“无”又缘何而生,“无”又是什么物事。他认为“有”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自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这种变化是无从知晓,倏忽自变的,是为独化。而独化的依据即是事物自身之理。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必然的,它不会无缘无故而产生,而消失。郭象将这种自生自灭叫做“玄冥”。所谓“玄冥”是一种神秘的演化与动作。后来《列子》一书的作者将这一概念与《周易》解释万物演化的动因“阴阳不测之谓神”相挂钩,将其互释,《周易》将“神”说成是万物之身的各种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变化动因,它是神秘而不知的,故而只能通过占卜的神秘方式来把握。王弼和东晋的韩康伯在注《周易》时,尽量将“神”这一概念与道相联系,力图使这一古老的神秘概念与玄学的理性精神相联系,以消除其中的神秘的非理性成份。(注:如韩康伯注《周易·系辞上》中“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时云:“夫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可见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思想,以自然之道释“神”这一概念。见《王弼集校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0页。)王弼的思想表现了正始年代的士人精神的自信与向上,而处于西晋年间的士人面对的是另一种表面承平而内里凶险的局面,对于前途早已茫茫然,于是当下性的冥数成为精神信念。这不能不说是精神人格的逆转,表现了士人对于命运的忧恐心态。在西晋“八王之乱”与紧随而来的“永嘉之乱”中,许多士族文人尽管有着高贵的门第和良好的文化修养,但是在横暴的权臣和军阀面前,无法实现自己的尊严与选择。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起正始年代的嵇康阮籍等人更惨,更缺少人格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在无可奈何下,只好向无法掌握的命运俯首称臣,将人生追求进一步当下化,将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变成形而下的个体欲望的满足,以自我麻醉,自我逃循。晋末的士风放荡与魏时名士竹林名士的放逸相比,格调更为低下,徒得其形似而已,这一点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过。兹不复论。西晋末年美学精神的世俗化,实已开齐梁文风之先河,东晋年间虽有一些振兴,然终不能挽其颓势。
郭象对于王弼贵无论的消解,是从各个范畴上着眼的。如果说王弼强调“自然”这一范畴的本体论意义,郭象则竭力消解其中的本体意义。《庄子·齐物论》中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联。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郭象在注解时发挥道: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郭象与庄子思想相比,突出了道体自然,非有所待的意思在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郭象也汲取了老子与王弼的思想,认为事物是由真宰发起的,它自身并不能完全设定自身。因为将事物说成完全是由自身设定的,就无法解释事物的变化与运动,而处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年代中,要否定变化是不可能,也无法满足哲学对于现实人生的解答,因此,郭象作为一名当时周旋于政治与社会中间的人物,必定要对于事物的运动与变化作出应答。郭象认为事物的存在与运化是由背后的真宰推动的,然而,他又将种本质性的概念悬挂起来,强调它只是一种逻辑的存在,至于到底是一种什么概念,郭象采用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方法。强调这种真宰并不存在,而是事物自身的变化使然,郭象有意识地要纠正王弼将一切现象世界的变化与发展归纳为无的精神本体的观点与做法。认为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就是自身,这种自身背后的动因是一种无从认识的玄冥与独化。就这一点而言,郭象的哲学也是充满着矛盾的。他也知道有不能说明有,因此,无的概念是不能完全否定的。郭象认为万物有一个自在之理,但理不是本质与抽象的概念物,而是随缘的事物自身。郭象认为“理”与“无”,只是一种想象与逻辑的概念,不能构成实体。事物的终极即在于本身,现象即为实体,实体即为个体。如果说王弼强调的是共性化的精神实体,而郭象则用个性化的变化概念消解与代替了王弼的这种“无”和“道”的概念。
郭象在注《庄子·齐物论》中著名的“罔两待景”的寓言时,发挥了这一思想。《庄子·齐物论》中云“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则寓言通过罔两(影外微影)责问景(阴影)为何忽行忽止,无有特操,使自己无所适从?而景物则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所以行止不定,完全是形物所使,而形物则又有所待,则所待为何物?这种原因之外的原因究竟能否认识?庄子的这则寓言,旨在说明事物的变化并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是受偶然性与个体性所支配的,事物的原委与是非很难辨清。郭象对此发挥道:“言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郭象依据自己的独化论对此大加演绎,认为这则寓言正好说明万物自生自动,非有定规,是天机自动,所谓天机,是由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然之理所造成的,它是不可知的,因此可以称作独化之迹。郭象强调一定要去追问它是什么推动的,最后的结论依然是无待的原因造成的,不可能寻找出可以说明其变化的内在推动力。精神价值被融解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之中,他的这种思想真有点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意思在内。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曾说;“物无妄然,必由此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无”的本体来解释。王弼主张用整体的精神和谐说明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寻的,至于“无”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先天设定的概念,故而王弼从来不去多加说明,他还不像老子与两汉的思想家,用阴阳二气的宇宙生成论去加以实证性的说明,只是将“无”说成宗统一切的本体。郭象则认为既然“无”是不可证明的,那么可以证明的只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个体存在才是可以把握的,而“无”则是一种无从证明的妄想。郭象是主张类似现象学的结论的,他主张将事物本质加以悬置或者干脆加以否定,强调精神的意义在于个体化的运动与变化之中。郭象对于“罔两待景”的寓言大加发挥道: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郭象强调,世人大抵将罔两待景,景待形,而形又待造物主这几者的关系,说成是因果关系,这是大错特错了。郭象认为,“罔两待景”这样的现象既不可能从“无”,也不可能从“有”之中产生。“无”不能生“有”;“有”亦不能造有。在这一点上,郭象不同于当时的崇有论者,但他也不同意王弼的贵无论,而是主张在玄冥中来看待事物的自生自化,所谓玄冥即是一种超越有与无的境界,是对本质进行解构之后的一种超验的实体,它只能自证自感,而不能被本质所设定,后来的佛教哲学学对于现象世界的解构,禅宗美学鼓吹的自证,都同这种哲学有着直接的关系。郭象提出,既然万物独化,非有所待,其中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王弼所说的举本统末的那个“本”即“无”,本是子虚乌有的,因此,苦苦地将那个臆构的理想之物作为追求目标,那样岂非水中捞月般地徒劳无益?明白了这一点,岂非应当任从命运的安排,随遇而安,“故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这就是郭象进行自我解脱,自我解构的理论凭据。据《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嵇绍之父嵇康本为司马氏所诛,嵇绍为报父仇,本不应去当司马氏的官。这样的举动也为士人所不齿,有背于乃父生前的人格理想。然而,处于西晋与郭象差不多同时的嵇康的旧友山涛却从“天地四时,犹有消息”的理由出发,诱导嵇绍出仕,嵇绍后来却成了司马氏的忠臣,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条中斥之为:“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与时俱进”,正是以郭象所代表的士人精神世俗化的真实写照。
二、“各当其分,逍遥一也”
郭象消解了统一的终极的精神之境与人格之境,将精神的价值定位于个体的和谐,自主的和谐。由此而将人格理想加以彻底消解。因为既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自我高于一切,所谓人格境界也就失去了形而上的依据。而没有人格境界,自汉魏以来所追求的美学精神的超越也就丧失了灵魂。
然而,这种理论毕竟与中国传统的人格思想相左,与魏晋以来的思想解放与个性精神不相一致,在理论上也存在着难以自圆的地方。因为真正的人格精神从来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结合,光有个体性而没有共通的价值观念,人的类属性就无从谈起,就会变成动物一般的适应性,只是在感官的层面上认同自我,而不能将自我化入精神高尚之境之中。人的个体性毕竟与动物的个体性不同,它要承担作为类属性的道德责任与人的尊严。《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也是看到人的存在价值毕竟不同于动物以个体存在为至高原则的道理。事实上,真正具有个性的人物并不是用自私自利来消泯共性,相反,而是通过自我的努力来确证自我完善,将个性融入共同性之中,使自己的个性尊严具有形而上的动力与本体论的支撑,个体性若无整体性的道德作为精神信仰,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个体性,这是人的个体性与动物个体性不同的地方。魏晋时真正的个性鲜明的名士,正是用自身不同于流俗的举动来确证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所谓求仁得仁,蹈仁就义都是指这种气节。六朝时颜延之在《五君咏》中对于嵇康的赞美;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郭象对于整体性的消解,力主个体性便是自适其性,不必对于整体负责,对于西晋士大夫人格精神的影响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循此而看待西晋文学精神与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相比,滑向世俗与低调,便是必然现象。后人对此多加以批评,也是顺理成章的。(注:如《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云:“建安风骨,晋宋莫传。”李白《古风》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郭象的这一思想在注释《庄子·逍遥游》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庄子》书中,逍遥游的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对于人生精神自由的追求,主张超越一切有待之境,入于自由自在的消遥之境,这种精神自由之境又与人生的自由无待相融合,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境界。魏晋以来主张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人士大都以此作为谈资。比如阮籍的《达庄论》便是经典。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的名士常在白马寺讨论《逍遥游》。(注:《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可见这篇庄子的经典是士大夫人生理想与人格精神的理论依据。郭象要消解魏时王弼嵇康一振的人生超越哲学,当然要先拿《逍遥游》开刀了。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从阐释学的角度将庄子的逍遥游思想阉割成犬儒主义,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也就没有了依托,很容易倒向混世主义。庄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本来是很明白的,这便是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作为对立统一的世界,从众生之有待向无待之境汇融。在思想方法上便是将个性融入共性之中,追求的是一种共同性、本质性的生活理想,在美的形态上是以整体理想的人格作为众生看齐的目标。尽管庄子思想也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其中不乏相对主义和混世的因素,但从总体来说,是追求无待即理想世界,以精神世界为至贵至尊的。在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中,所谓大鹏也好,斥鴳也好,尽管各得其所,但能未达逍遥游的境地,因此庄子提倡“逍遥游”乃是倡立一种无待的精神境界。郭象对于庄子的思想与历代知识分子的解释,自然是很明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要竭力通过重新解释《庄子》,消解这种以大压小,以小羡大,以共同性来消泯个别性的思想,从而使精神价值从“逍遥游”下放到尘世中来,它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精神乌托邦,而是各得其所,无分大小的自足自乐。郭象在《庄子·逍遥游》的题解中申明: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郭象直捷了当地指出,大小虽殊,但是只要放任情性便可达到逍遥的境地。在他看来,人们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固执于一种既有的尺度,只会从差异中看待事物,总是以小羡大,因而不能自我解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郭象显然是借注解庄子来树立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他那个年代,士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人生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对于是是非非早已不存什么标准,而是希望在有限的年头抓住瞬间即逝的时光来享受,满足自己的人生欲望。这不仅是郭象等人的想法,也是许多士人的想法。据《世说新语》和《晋书·庾敳传》记载:当时的名士庾敳也有如此心理:
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着《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服鸟》也。其词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天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摇玄旷之域兮,深漠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这一段记录非常真切地描述出当时的名士内心的痛苦与幻灭。他们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生与死,存与亡似乎没有甚么规律可循。类似王弼在注《周易》、《老子》时洋溢着的理性精神,早已荡然无存。过去与未来俱已消逝,在这里只剩下了当下性。这种情绪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中,尤以思想界最为明显。从《晋书·本传》来看,郭象的人生与性格也是充满着矛盾。郭象本来也并不是一个厚颜之徒。然而一旦成为任势专权、当道走红的人物之后,郭象也就面临着从心理上自我解脱的的问题。郭象既要任势专权,又要心安理得,无愧怍之态,为自己也为整个士族官僚寻找行为的精神依据,就要彻底消灭是非界限与价值判断尺度。因为这些固定的尺度犹如人生与历史的一面镜子,会照出各自的颜面真相,这就使中国古代素以好面子著称的士人多少有一些不好意思。而如果去掉了这面镜子,消除人的自尊,使自己的行为不但不是羞愧的,而且可以罩上一层逍遥的光环,岂非一举而得?郭象注解庄子,大衍发微,就是想完成这项任务,其深层心理原因盖缘于此。
对于儒家和道家,以及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那些精神高尚的理想人物,郭象自知这是传统文化塑造的人物形象,凝聚着厚重的历史与道德的力量,凭他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推翻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勇气远远不如东晋《列子》书中的《杨朱篇》作者那么大胆,但郭象的却有着超人的理论智慧,他发挥偷梁换柱、鱼目混珠的本领,竭力加以重释。比如经常为后人诟病的那段对于庄子所说“神人”概念的重释便是证明。《庄子·逍遥游》原文是“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出现在庄子中的“神人“是一位理想的自由无待的人物,庄子为此赋予他以美丽的容貌与超人的气质。郭象既不否定这位神人的存在,又将他俗化,从天上拉到人间,重新装扮一番。他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郭象指出神人与世俗化的圣人是一致的。对于庄子中的神人郭象不便加以否定,但是他强调圣人也好,神人也好,都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顺从自然,只要自足其性,便能够达到精神的至境。他在注“圣人无名”时提出:“圣人者,物得性之名耳,为足以名其所以得也。”郭象据此认为,圣人即神人,神人即圣人,其特征是自足其性,而不是凌超万物,睥睨一切。至于精神的内敛与扩张,郭象是这样看的,只要自足其性,即使是闲坐屋里也无妨神游四方。郭象在注《逍遥游》中“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时提出:
夫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虽静默闲堂之里,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两仪而御六弃,同人群而驱万物。苟无物而不顺,则浮云斯乘矣;无形而不载,则飞龙斯御矣。遗身而自得,虽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事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则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齐其所见而断之,岂尝信此哉!
郭象强调对于那些体居闲堂中人,照样可以得到玄同四海的精神境界,其前提是自足其性。神凝与否不是外在的精神状态,而是精神的自足自得。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郭象与王弼嵇康等正始时期的思想家相比,更加强调的是作为审美与观察对象的事物的个体性,与这种个体性概念相适应与配套的则是他的物各任其性的审美观念。如果说王弼与嵇康推崇的是个体性背后的那个神圣至一的精神人格境界,追求的是整体性的和谐与超越,并将其作为审美与文艺的终极意义,如嵇康在诗中咏叹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此中‘太玄”即为玄学心仪的至一境界,也是人格境界的形而上的精神支柱。玄学祟本息末或举本统末的观念,也反映在它对于精神意蕴的赞扬和对于世俗事物的鄙俗,以及对于现象世界的弃置。这种精神人格当然有着抗拒世俗与权势的积极意义。不过另一方面,在审美观念上也存在着对于现象世界丰富性的遗缺,《文心雕龙·时序》中就说;“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明诗》中亦批评玄学诗风:“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至于东晋时代产生的玄言诗在审美观念与方法论上,也存在着对于概念精神的抽象演绎以及对于丰富的个体性重视不够的弊病。就这一点而言,郭象的思想倡导对于丰富的现象世界与个体性的关照,应当说对于文学创作与美学观念的更新,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郭象在注《逍遥游》中的天籁概念时申论:“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声虽万殊,而所禀之度一也,然则优劣无所错其闲矣。况之风物,异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则天地之籁见矣。”这一段话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之曲度,节操同检,至于引气不同,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有相同之处,不过曹丕的个性论并没有否定共性的存在,所谓“文本同而末异”,而郭象的个性论是建立在玄冥与独化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对于这种个体性与现象世界完全是无条件的加以赞同,并以此作为否定共同性的理由。在郭象看来,声音没有优劣之分而只有自然与否,所谓天籁就是物各任其性,完全的自足其性,这就是美,就是善,而互校短长的尺度是根本不存在的。郭象在注《道遥游》中“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时提出:“大块者,无物也。夫噫气者,岂有物哉?气块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则块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块为名。”郭象提出,“大块”作为浑沌一体,与天籁之美与自然之道相通的概念,其价值在于块然自生,无有所使。庄子曾指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也就是在绝对的道之中,一切界限都不存在,庄子用超越是非差别的道来消解美丑善恶的相对标准,主张主体回归到道之中,这种道是一种整体性的和谐。郭象则将这种个性体的统一尺度还原为自身,也就是说,物之所以美在于物自身,现象与个体循着自身的尺度而运作与评判。他提出:
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
这就消解与否定了以统一的尺度产生出好美厌丑的常人心态。郭象狡黠地将“道通为一”的概念作了偷换,在他的哲学中,“道”不再是统率个性的概念,而是不离个体与现象世界的概念,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精神性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显现和描述。郭象通过夸张和放大个体化与现象世界的自足性,将个体的意志现象成了一种最高的尺度,这样,作为类属性的人的精神意蕴不复存在,终极意义也没有必要再关注,剩余的只是各足其性,意志欲望的充分释放,不必再为公共伦理承担责任,普适性的道德也就不存在了。郭象为了给自己的这套理论寻找依据,也没有公开否定共同性,而是一再强调公同性不能脱离自足性,还是那个思路与逻辑,任从个体也就是任从共性,当下性即是共同性。至于王弼所说的举本统末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庄子·德充符》中假托孔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庄子的意思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用道的统一性来消解万物的差异性,宣扬他的相对主义。当然他的相对主义与郭象是不同的。郭象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
虽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则万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则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异而异之,则天下莫不异。而浩然大观者,官天地,府万物,知异之不足异,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则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无而无之,则是非美恶,莫不皆无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恶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虫,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尔。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无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无非;无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无是。无是无非,混而为一,故能乘变任化,迕物而不慑。
这里明显地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对于庄子的思想作了重释。郭象这里提出了一个审美评判的标准问题,即各美其美,这就是万物的尺度,如果从固定的统一的尺度出发,则必然会生出许多差异的问题,自人类至于动物界大抵所持的标准是以己之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事物,这就难免会产生偏至,这才是未能适性,造成各种各样弊端的原委。而玄通泯合之人则不然,他们懂得尊重万物之个性,不用统一的固定的标准去进行评判,这样的审美是真正的智慧,心灵建构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之上,自然也就会解脱了,自由了。物我两泯,大彻大悟。郭象的解脱方法与庄子相比,显然是一种甚为庸俗的自足其性,和光同尘的混世哲学。郭象的哲学与庄子的哲学固然有一些相通,但是庄子逍遥游的超越精神却被他全然消解了,“故放心于道德之闲,荡然无不当,而旷然无不适也。”在魏晋玄学的王弼与嵇康等人看来,美是善的升华,是人格精神的升华,而在郭象看来,人生的自由恰恰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对于道德的忘却与放弃。引伸到极处,不能不说是一种很自私的道德观念。
郭象的这一道德标准影响到他对于儒家道德思想的消解。《庄子·德充符》假托孔子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庄子中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止水”即停止不动的水面,惟有平静不动的止水才可以作为镜子来鉴人。庄子提出“水静犹明,而况精神”,水如果是流动不息的,也就不可能作为镜子来照人。同样,道德标准好像镜子一样,必须是一种固定的标准,统一的标准,不然就无法起到照烛世人的作用了。郭象对于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但他同样明白的是要消除这一标准,不能让它成为世人的镜子。郭象在《庄子·德充符注》中提出:“夫止水之致鉴者,非为止以求鉴也。故王骀之聚众,众自归之,岂引物使从己耶!”也就是说,止水所以能够鉴照万物,并非自己故意为之,而是众物自然从之,是各自欲鉴照自身,就像庄子书中道德高尚的丑人王骀吸引众人,是由于众人从善如流,而不是王骀故意为之,如果王骀刻意为之,就失去了其价值。同样,松柏所以能够成为众木之榜样,所谓“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并不是松柏故意想成为众木之榜样,而是由于它自身的资材与特性使然。故其《庄子·德充符注》指出:
夫松柏特禀自然之钟(五)气,故能为众木之杰耳,非能为而得之也。言特受自然之正气者至希也,下首则唯有松柏,上首则唯有圣人,故凡不正者皆来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则无贵于松柏;人各自正,则无羡于大圣而趣之。
郭象深知孔孟的道德毕竟是难以否定的,如同王弼一样,他对于孔子的圣人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还要承认的,因此,他对于孔孟圣人的道德标准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地位不可移易,不过他又巧妙地置换概念,认为众木以松柏为正,众人所以以圣人为正,也是众庶之性所然。这样就相对消减了圣人与松柏的榜样作用,而突出了物各任其性,非有统一价值标准的思想。郭象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消解统一的价值标准,消解道德的公共性,消除崇高感,毫无疑问是当时精神人格濒于崩溃的西晋末年的士大夫形象的写照。三国时刘桢在《赠从弟三首》中勉励从弟在乱世中要学习松柏,坚守素志:“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而这种风骨到了西晋则很难见到。大行其道的是郭象的犬儒主义人格志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人格也是一种人格类型,它说明当时的士人仍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人格理由,只不过不再是魏时王弼嵇康所坚持的人格理想罢了。
郭象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也是在充满动荡的年代中形成了分裂痛苦的性格。据《晋书》本传记载,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着碑论十二篇。”从这些记载看来,郭象生活在一个动乱而不幸的年头,他本是一位哲学天才,好老庄,能清言,以至于王衍这样的玄学人物都对之倍加欣赏,郭象早年也是服膺老庄,效法嵇康,闲居以文自娱。然而在当时的激烈的司马氏集团的宗室之争中,许多士人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陆机、陆云兄弟,还有潘岳、张华等文士都是如此。处于这种年代,知识分子投入时流,投靠权势者实在是太普通的事了。而一旦进入此中,就会导致整个人生观的改变。而擅长将思想学说作为吃饭家伙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会对于自己的行为从理论上重新进行解释,在阐释中实践新的人生追求。当时的另一名士庾敳与郭象曾经就此进行过激烈的人生交锋,从中亦可看到郭象与另一些知识分子在人生炼狱中的煎熬。据《晋书·庾敳传》,庾敳本是一位名士,“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但他的人生理想以及对于老庄的理解与郭象不同,他是用老庄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名士追求,而郭象则早已世俗化了,官僚化了,所以后来庾敳也不得不折服他的精于世故,投靠权贵。《晋书·庾敳传》记载:
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隽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这段记载可谓说明白了当时郭象为代表的士人状态早已完成了转变,而另一些原先有气节的名士不得不慨叹郭象这类人是“当世大才”,自己不如郭象的当下追求,所谓“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士人精神的消退,自然而然地会引起美学精神的全面世俗化与转向。这是我们了解正始之音向着两晋南朝美学精神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关捩。
标签:逍遥游论文; 美学论文; 庄子名言论文; 郭象论文; 魏晋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易经论文; 庄子论文; 玄学论文; 王弼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