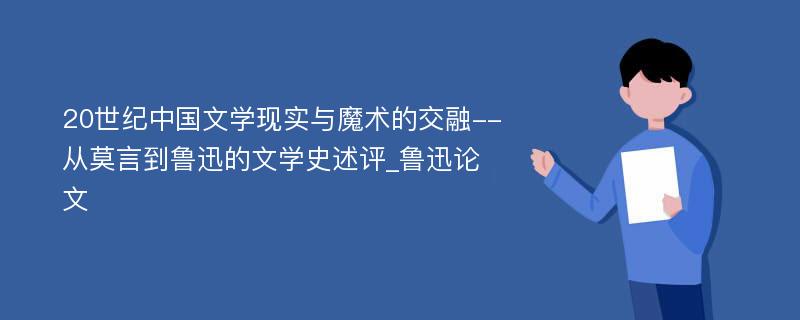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与魔幻的交融——从莫言到鲁迅的文学史回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现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3)01-0018-07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莫言的授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刚刚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无论是他自身的作品创作,还是当时的文学思潮,都表现出魔幻与现实交融的趋向和特征。20世纪末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极大冲击,对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其中就包括莫言,莫言自己也并不讳言这一点,承认自己从马尔克斯、福克纳那里吸收了很多灵感;但是莫言也曾经表示过,自己有意识地逃避这种来自西方的影响,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炙热的高峰”[1],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另一股文学热潮——寻根文学中,和许多寻根文学作家一样,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用强烈的现实精神,表现了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民间文学。
学界对于这两种文学思潮的研究,更多的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认为寻根文学思潮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寻根小说作品源自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甚至是模仿。但是单就莫言而言,其创作的许多因子,更多的是传承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包括《聊斋志异》,包括鲁迅。如果仔细回溯中国文学史的进程,文学当中的魔幻手法运用,在中国文学当中是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到当代文坛莫言等人的创作,都表现出了揭露现实和重构历史的双重取向,以及对于魔幻、想像等文学表现手法的多种探索,这一精神取向和艺术探索有着清晰可溯的历史脉络,伴随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
一、魔幻与现实的文学史追溯
中国小说的发展演进,很早就表现出魔幻和现实之间的双重趋向。在中国小说文体发展演进的早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其各自创作背后代表着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风格萌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虽然《汉书·艺文志》对于小说家做出了较早较为明确的定义,但是街头巷语不过是传播的方式,中国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的源头,实际上是早期的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头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2]19
在这些早期具有志怪小说雏形的神话传说当中,鲁迅首推对自己影响甚大的、也是收集各类神话传说故事最多的《山海经》。鲁迅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这些神话传说故事的浓厚兴趣,他在《阿长与〈山海经〉》当中回忆起自己看见远房的一位叔祖的藏书时,表现出的渴慕,这其中就有一本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3]而正是后来长妈妈留心为鲁迅买来的《山海经》,培养了鲁迅从小对于文学、小说的兴趣。
王富仁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中指出“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总源头。”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是一样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这诸多神话传说,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原始初民对客观世界的想象,也是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4]所以王富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即使把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神话传说称为中国最早的历史小说也并无不可。
明清之际,这两种趋向随着文学的发展逐渐分化明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两股潮流。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三国演义》树立起了“三分虚构,七分真实”的标尺,极大程度上模糊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划分,《聊斋志异》则通过奇谲诡秘的想像力和情节,表现了一个虚幻的狐鬼花妖的世界。这两种创作趋向,是中国注重伦常道德的史官文化和注重神力崇拜的巫官文化的影响结果,而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领域逐步获得主流地位,前一种创作倾向毫无疑问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文学中的浪漫文风、奇谲的想像长期被压抑,“载道”、“言志”、“宗经”、“崇实”的观念一直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流。而小说在古代的地位则更为低下,面对来自正统经史的巨大压力,小说的创作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就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描述的那样,许多的小说虽说是小说,件件却都要从经传上来,纵使明代曾经出现过《平妖传》《西游记》《封神传》这样的充满想像力的神魔小说,但是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往往被归结于“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2]160,即三教之争尚未解决、社会思潮处于混乱时期的产物,一旦儒家思想重新成为社会的正统,这样的文学形态则会受到挤压和压制。另一方面,明清之际虽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开始摆脱历史的束缚,运用了更多的虚构,但是这类叙事文体的小说亦常常受到来自历史的压力,在文学观念上都是主张按经史书记载的事实编写故事,不主张想像和虚构。
近代中国发生的小说界革命,是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同样也是对于传统史学观的一次反叛。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5]同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并创作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创作上都对于小说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革新,但是他的创作实践更多是从文学功利主义作用的角度出发,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未来记》以及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只是传统讲史、演义的延续和他自身对政治观念的图解。
或许恰恰是长期游离于中国古代诗文“言志”、“载道”的文学主流传统之外,小说在民间获得了较为宽广的生命力和生长空间,那些带有传奇色彩和想像力的小说,往往更为普通百姓民众所接受。也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像资源和能量。
二、莫言对魔幻与现实的经典性呈现
和鲁迅一样,莫言在回忆起自己幼时的文学启蒙时,也谈到了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民间传说、神话、鬼怪故事对于自己的影响,他在文章《好谈鬼怪神魔》中回忆:
从我的故乡西行数百里,便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先生的故乡淄川,都是山东人,出省之后便算同乡。有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同乡真令我感到自豪。在漫长的科举取士的社会中山东考中的进士车载斗量,被钦点了状元的也有十数之多,他们当年的荣耀连蒲松龄也眼热过。时过境迁,人们早已忘了他们,但在当时穷困潦倒、靠编织鬼魅狐妖故事以寄托心中情感的蒲松龄却流芳至今并且肯定还将流传下去。近年来,有一些评论家在评论我的小说时,总是忘不了提起我这位光荣的乡亲,并从他那里找到了我的小说的源头。这令我不胜荣幸至极。[6]
儿时听村里的大人给他讲蒲松龄笔下各种鬼怪、狐妖故事的经历,对莫言的创作影响很大。蒲松龄笔下魔幻的风格、奇特的人物、充满想像力的情节,经常能够看到蒲松龄的神韵。这个基本事实表明魔幻、想像的因子虽然长期受到主流文学思潮、话语的压抑,但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本身是存在的,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我们无法去步马尔克斯的后尘,但向老祖父蒲松龄学点什么却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6]各种魔幻的因素中,莫言特意提到了与蒲松龄创作心理相近的“鬼气”,称自己的创作“鬼气”渐重,其原因是“因为都市生活中的喧嚣、肤浅、虚伪、肉麻令我厌烦,便躲进想象中的纯净世界去遨游。这种创作的心理动机与蒲氏当年的心态也许有共通之处。”[6]
这种“鬼气”在同样喜欢听神话传说、鬼怪故事的鲁迅身上出现过,鲁迅在给北大学生李秉中的信中曾经提到:“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却不能”[7],尤其是在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时,往往会联想到地狱、鬼魂。杂文《“碰壁”之后》中,鲁迅这样表述自己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感知:“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不堪闻见。”[8]这种需要直面中国现实世界时,灵魂内心受的挣扎苦痛,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里的梦境与幻想、影与火、秋叶和坟地、地狱和鬼魂当中,有着集中体现,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就曾经指出,作为“五四”启蒙思想家的鲁迅,追求的是魔鬼统治之下使人觉醒的光,将“鬼”变为“人”的过程,但是到了《野草》创作的时期,他笔下描绘的这幅中国的现实图景完全变形:“‘人类’取代了‘魔鬼’在地狱的统治权,但使‘地狱’更为整饬,更为严酷。”[9]
可以对比来看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开头所描写的阎罗地府世界,相比于主人公西门闹之后在六道轮回的现实世界里见识的荒诞闹剧、苦难悲剧,小说开头的地府、阎王褪去了狰狞恐怖的面容,反而呈现出一副明晓事理、清明的人的姿态:
在我连珠炮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继续喊叫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说:
“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10]
这个开头可以视为一个由地狱中的“鬼”重返人间的隐喻:将“鬼”变成“人”,是鲁迅以来中国思想启蒙的核心话题,然而却逐渐发现,恰恰是现实中的人,将现实世界变得比地狱更为可怖,使得早期的启蒙愿景和期望轰然崩塌。在这一点上,莫言表现出了与鲁迅一样的深刻,他将自己与蒲松龄笔下塑造的、在外人看来恢诡谲怪、狐鬼花妖的魔幻世界,称之为一个可以遨游的纯净世界,相反将外部世界看作是一个肮脏、虚妄、喧嚣的对照。历史、现实较为虚拟的小说而言更为魔幻,因此小说的魔幻手法,可以视为莫言在直面中国苦难历史、残酷现实的过程中,自己精神世界的外化,是他灵魂挣扎、苦痛的反映。和蒲松龄一样,曾经生活于农村、民间底层的现实经验,给了莫言的写作以深刻体悟和写作素材,所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不是向着西方有关魔幻与现实的评判标准的趋近,而是在中国民间文学语境和现实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是真实的中国本土经验的表达。
莫言将魔幻手法与现实精神结合,一方面能够直面现实当中的残酷与虚妄,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于正史的解构,使得小说艺术能够从作为“经典附庸”、“正史之补”的传统小说观念中解放出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曾经提出过事实和虚构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有人说对于《伊利亚特》,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11]这就构成了对于历史真实的质疑,以及对通常人们对于历史理解的一种反思,对于历史本体(历史本来面目)的解构。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往往被要求要忠实于正史,满足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和叙述逻辑,即使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名著在虚构上做出了一些突破,突破了“信史”的局限,但是这中间反映出的“尊刘反曹”、“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思想观念,依然不能摆脱经史叙述中儒家正统的历史局限。莫言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他对历史真实的认知: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故事的人,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弄到后来,一切都被拔高了。我死活也不相信历史上真有过像《史记》中所写的那样一个楚霸王……[12]
莫言善于以宏大历史叙事作为他人物塑造、故事展开的背景,《红高粱》里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檀香刑》的背景是山东半岛的义和团运动,而《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直到《蛙》,更是表现了横跨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历史画面。莫言有一种对历史、对现实表达的诉求在作品中,但是他的这种表达早已不是作为“正史之补”、经典附庸的文学表达,在这一点上他和鲁迅一样,更关心的是历史车轮轰隆碾过之下,作为个体人的命运。在小说《檀香刑》中的主人公孙丙,是一个油滑、粗鄙、身上带有各种缺陷的普通农民,他的另一身份则是义和团的拳民。无论是过去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当中,还是在当前历史理性思考的研究框架里,这一历史存在早已经被贴上野蛮、残忍、愚昧的标签,而相比之下,细细品读莫言的描写,特别是最后对酷刑的描写,作者没有站在价值评定、道德审判的高位来审视这个普通的人,他努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拥有着各种劣根性但是又闪出人性光芒的个人,真实地表现出文明冲突之下一个普通人所应具有的情感和生存状态。
莫言小说创作当中,魔幻与现实、想像与历史的结合在《蛙》中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主人公姑姑经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计生历史,一方面作为乡村医生,同时又曾当过计划生育的干部;带有守护和结束生命的双重角色。而“蛙”与“娃”的谐音隐喻也给了莫言魔幻手法发挥的空间,在小说中,莫言用精神幻象来表现姑姑内心的苦痛与挣扎:
姑姑沿着那条泥泞的小路,想逃离娃声的包围。但哪里能逃脱?无论她跑多快,那些哇——哇——哇的凄凉而怨恨的哭叫声,都从四面八方纠缠着她。……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有的大如电熨斗,有的小如枣核,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13]
在这里,莫言透过了表层的魔幻手法和宏大的历史叙述,通过魔幻的视角达到了历史背景之下个体生命的真实内心世界,这样的心理分析和刻画让人联想到鲁迅在小说《白光》当中对陈士成的幻觉和惶恐内心的表现。虽然在小说《蛙》中莫言稍稍偏离之前自己的语言风格,“放弃了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14]他甚至超越了之前启蒙话语/反殖民话语、知识分子/民间这些鲜明的立场划分。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在平白、写实的小说以及最后的戏剧部分当中,莫言没有放弃用魔幻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命运和挣扎。相对于《檀香刑》中表现的义和团历史,《红高粱》里的抗日中国,以及《生死疲劳》等小说中展现的“大跃进”、“文革”,作为莫言最近创作的一部长篇作品,《蛙》一直写到了21世纪的当代中国,小说中作者多了更加直白的写实和历史展现,但是依然坚持将魔幻的表现手法交融在自己的现实精神当中,来探索对当代中国人生命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呈现。
三、鲁迅对魔幻与现实的历史性建构
孙郁在《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中总结道:“鲁迅走进莫言的视野,是在七十年代。那些暗含的精神对他的辐射是潜在的。近五十年的文学缺乏的是个人精神,莫言那代人缺少的便是这些。我以为他的真正理解鲁迅还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一段特殊的体验使其对自己的周边环境有了鲁迅式的看法,或者说开始呼应了鲁迅式主题。”[15]孙郁认为这些主题的呼应,就包括《欢乐》中散出《白光》的意象,《十三步》的笔法有着《故事新编》的痕迹,而小说《酒国》则是把中国文学中已经中断的流脉给衔接上了。
莫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与鲁迅笔下的鲁镇一样,都是对于中国农村、土地和民众的展现,都表现出强烈的疑古精神和国民性批判,都有对中国历史中“吃人”、“杀人”和看客主题的描写和揭露,莫言创作的小说《酒国》《生死疲劳》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食婴”、“吃人”这样的情节。但是还应该注意一点,作为这些主题的呈现方式,莫言小说魔幻与现实交融的艺术表现,是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开拓、建构起来的,而在莫言更加夸张、奇诡的魔幻表现背后,一方面是五四作家相同的反思和现实精神在延续,同时在此基础上有着新的思考。
如同《聊斋志异》对于莫言的影响一样,因为童年时期对于《山海经》为代表的民间神话传说、鬼怪故事的喜爱,鲁迅对于带有魔幻题材性质的古典小说也始终保持着关注。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清代张南庄的小说《何典》,鲁迅在为其撰写的题记当中就谈到这种鬼怪魔幻题材小说的现实意义:“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16]鲁迅本身对于儒家正统文学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怀疑和反叛,使他注重民间更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和想像力的文学资源,同时也让他的小说创作能够突破之前史官文化传统影响的藩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透过一个狂人的视角来重新观察历史和世界,于是小说中的现实世界和中国历史也随之变得带有些癫狂和魔幻的色彩。狂人所表现出的疑古精神,不仅对于中国儒家正统的伦常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在一种“疯言疯语”的虚构叙事模式之下,对于中国社会“礼教吃人”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犀利的批判。《狂人日记》的第六部分只有两句话,但是对于整部小说的氛围烘托有重要作用: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17]
狗的叫声、青面獠牙的面孔、时隐时现的月光、黑暗的村子和房屋,以及“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传说,都增添了整部小说鬼魅、魔幻的气氛。《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就具有相当“魔幻”的色彩,是意味深长的,学界公认鲁迅对于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创作手法是有吸取借鉴的,但是细读这些带有魔幻性质的心理与意象当中,联系鲁迅从小所受到的民间传说故事的熏陶影响,依然可以发现来自中国本土社会的现实资源和基础,这与后来的莫言的创作是一致的。
而在鲁迅具有实验性质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鲁迅借助了许多带有魔幻和神话色彩的中国传统故事原型,更为清晰系统地表现了对所谓历史真实及其背后权力话语的质疑,如在小说《起死》中,让庄子与复活的骷髅鬼魂对话辩论,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手法,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文化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解构。而在小说《铸剑》的最后,鲁迅借用了古代复仇故事《列异传》超现实的、魔幻的结尾: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18]
鲁迅让复仇者和统治者的头颅纠缠在一起鏖战、最后一起被放在一个金棺里埋葬,享受着国中百姓的跪拜和几名义士的忠愤泪水,对专制历史的残暴和被奴役人民的麻木,都有深刻的揭示。与鲁迅一样,同样用带有实验意义的文学想像、魔幻手法来反思中国现实和国民性主题的,还有“五四”新文学另外两位小说大家,老舍和沈从文早期创作的《猫城记》和《阿丽思中国游记》,两人在创作生涯的早期,都已经能够用一种更加现代、开放、充满想像力的创作模式,来营构自己的小说世界,反映出当时中国作家在现实与想像之中,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以及对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老舍的《猫城记》与晚清许多幻想题材的小说类似,是一部政治讽寓小说,借虚构想像出的火星上的猫人国,通过荒诞离奇猫人国的隐喻,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弱点有穷形尽相的揭露和批判;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则借英国小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蓝本,将儿童幻想视角移至作为殖民场所的中国,以西方外来者的视角来看现代中国,并对当时中国人的习俗、文化、思想乃至文坛的一些弊病,都有影射、批判与嘲讽。
由鲁迅、老舍、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开创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使得小说创作不再是作为经典历史的附庸,或者是政治观念的图解,而是运用文学的表达方式,倚靠着中国的现实进行的创作,这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小说艺术当中现实和魔幻如何融合的探索和建构。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同是他们进行创作、想像的现实资源与基础,在这一点上,莫言笔下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也一样:无论莫言笔下的人物如何怪诞、情节如何虚妄、如何魔幻、匪夷所思,莫言的文学表现指向,还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经受的生活、精神的变迁与苦难,都还具有民间野蛮的、原始的生命力。
在处理魔幻与现实的问题上,莫言的小说与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精神内核上是相同的:将超越具体真实、充满想像力的艺术表现方式,与直逼历史、社会现实的思想指向相结合。国民性问题和看客心理,在莫言笔下的魔幻世界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他自己谈到国民性这一主题时,也承认启蒙的艰难与历史的荒诞:“鲁迅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国民性的丑陋、黑暗的现象,再过去一百年、二百年,人性中阴暗面还是不会消亡,永远会有,与生俱来”[19]。毫无疑问,鲁迅关于魔幻与现实的历史性建构在莫言笔下得以继承:他的一些魔幻手法,充满想像力的语言、描写、情节,在对历史、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最大真实地折射出生活真实的本质;而现实当中的丑陋、怪诞和扭曲,用文学艺术的夸张手法表现出来,都极具冲击和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小说的魔幻元素更为大胆、诡谲,对民间土地的描述更为开放、直白,这与莫言对于传统儒家主流文学观念的绝决反叛不无关系。同时,也和莫言在延续“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关于“礼教杀人”的批判精神之外,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性也保持警觉有关,他在一次论坛的发言谈到自己与鲁迅一代人的差异:
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写的也是乡土,但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20]
莫言不只一次强调自己创作的民间立场,包括他对于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一种警惕和拒斥。这与古代老庄思想、民间巫文化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对儒家载道文学思想的反叛何其相似,这或许可以解释在莫言的作品中,那些过于放纵自由的情节、残酷裸露的画面,与狂欢化、色彩丰富的语言。但是莫言毕竟与时下的一些完全背离现实,只为魔幻而魔幻的小说创作不同,那些作品往往是“非道德化,无价值性,不问是非,不管善恶。只求绚烂,只求痛快。”[21]莫言尽管对于庙堂、精英、主流话语有排斥,但并不代表莫言的作品魔幻背后没有现世价值信仰的支撑,在他的作品中和他本人身上,其实还保持着中国民间所保有的朴素良知、信仰和道德操守,使得他在魔幻与现实中依旧保持着一种度;对于古典小说包括新文学的资源进行反思的同时也有继承,这让他的小说呈现出生气淋漓的气息和场面,又能让人感受到同鲁迅一样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觉与自省,这一点,往往是作为历史中间物、带有某种“鬼气”的作家自身难以意识到的。
标签:鲁迅论文; 莫言论文; 文学论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山海经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生死疲劳论文; 檀香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