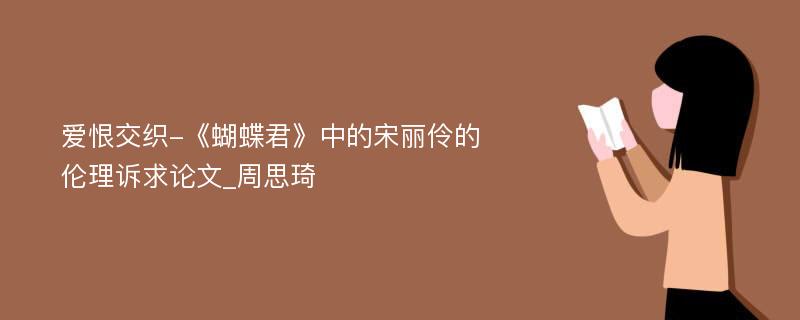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围绕东西方的权利关系及同性恋间的爱与恨这一伦理主线,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在其代表作《蝴蝶君》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东方人对西方人的爱慕,另一方面又塑造出一个挣扎于东西方权利关系的压迫与同性恋不被理解的主人公宋丽伶。宋丽伶其东方人的身份及京剧旦角的职业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对伽里玛的爱,然而回到当时文革特殊的伦理环境,东方长期受西方的支配与统治,宋丽伶对伽里玛代表的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与性别之恨。
关键词:《蝴蝶君》,文学伦理学,东西方
引言
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是20世纪杰出的美国华裔剧作家,其代表作《蝴蝶君》于1988年在百老汇的尤金?奥尼尔剧场公演并获得巨大成功。《蝴蝶君》中宋丽玲通过爱与恨的纠结传达了不同的伦理诉求,并最终演绎了一场道德意义上的悲剧。作为男旦的戏剧演员,宋丽玲因其特殊职业、民族、生理等身份对伽利玛产生强烈固执的同性之爱。然而,面对中国数百年来受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在文革期间的宋丽伶对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之恨。
一、爱的伦理诉求
“性别本身是一种社会构建,指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属性,一个人的生理性格不会改变,但是他的性别角色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黄,p99)。“舞台后部,穿着传统中国服装的宋丽伶,以一个漂亮女人的面目出现了,她舞蹈着,表演着京剧的一个传统段落。”(p03)。宋丽玲第一次认识伽里玛时便是“以一个漂亮女人的面目”,潜意识里设定了宋丽伶在伽里玛心中的女性身份,“中国服装、中国音乐”无不宣释着宋丽伶的东方人身份,而京剧的表演在开场便告诉读者宋丽伶是一名戏子,一名京剧旦角。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黄哲伦把宋置于京剧中性别模糊的旦角。以唱念打为核心的京剧作为中国文化的国粹,京剧中的旦角表演时透露的是隐忍与柔弱,被西方视为中国阴性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此外,“‘艺术是为了大众’是让艺术家们保持贫穷的一个低劣的托辞”(p35)。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戏子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伽里玛这个西方男人的出现及其对宋丽伶的欣赏与爱护,让宋丽伶感受到了其身份的存在意义。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宋丽伶说“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小小的咖啡馆,可以坐在里面”(p35)。宋对比中国先进发达、自由开放的西方有着一种向往,由此也延伸了伽里玛身上的男性魅力。当宋不顾世俗偏见邀请伽里玛到她家时,宋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对他的爱以渗入心灵。“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了”(p49)。宋丽伶想变得现代,想要突破扎根于两千年的过去的中国道德伦理,然而,她失败了,“一颗小小的、受了惊吓的心跳得这么快,把我暴露了”(p35)。宋丽伶用女性的身份去走向伽利马,当伽里马对她的一切言听计从后,宋丽伶的同性之爱演变成了更多的欲求,她不能接受自己永远是伽利马的一个东方幻象。最后,她坦诚自己的身份,导致了伽里玛如蝴蝶夫人的悲剧。
宋丽伶扮演着“蝴蝶夫人”这个受西方霸权迫害的东方柔弱女性的角色。在和服的遮掩下宋丽伶能征服伽里玛坚信她的女性身份,一方面不得不归功于伽利玛内心对温顺柔美的东方女人的渴望,而最根本的力量则正如宋所说:“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从来不可能完全是个男人”(P130)。宋丽玲游离于两种性别,对伽里玛的同性之爱欲盖弥彰,无疑破坏了伦理秩序,并最终导致其选择颠覆东西方权利关系,报复西方对东方的种种压迫。
二、恨的伦理诉求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该作品的情节发上在现在巴黎的一所监狱,而在回忆中,是从1960年到1970年期间的北京。回顾中国百年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首先,作为中国人,宋丽伶深谙中华民族遭列强践踏的屈辱史,骨子里怀着对帝国主义强烈的仇恨。宋丽伶嘲讽地用“顺从的东方女人”“残酷的白种女人”“帝国主义”“强大的西方人”等鲜明而激烈的词语和伽利玛对话。第一次舞台后部的对话,伽里玛夸赞宋丽玲“一个漂亮的演出”,宋丽伶坚决地回答“请别这么说”、并表达了对蝴蝶夫人的看法是“很荒谬”。如宋丽伶所说“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是的”,这是个美丽的故事。宋丽伶讽刺地反问伽里玛,如果是金发碧眼的女王爱上矮小的日本商人是精神错乱了吧?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美尚未建交,根源于他的民族意识,宋丽玲勇敢地愿意牺牲自己去做间谍,即使到了不受约束的法国也尽力收集情报。无论何时、何种场景宋丽玲始终铭记“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作为“情人”利用与伽利玛之间的爱情为民族大义服务。作为一名东方人,宋丽伶无意识地把伽利玛想象成西方霸权主义的代表,落后的东方遭受着西方霸权主义的欺压和凌辱。宋丽伶的民族伦理诉求支撑着其对伽里玛的恨,甚至是反抗。宋丽伶恨的伦理诉求在表达东方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刻板印象不满的同时,也宣泄了美籍华裔对于美国社会对于少数族裔歧视的愤恨。恨的伦理诉求也驱使宋丽伶提供假情报导致了伽里玛遭解雇被遣送回巴黎。赛义德认为,在东西方的权力关系中,东方始终处于沉默无声的地位,而所谓的“东方”只是西方的一种言说,“东方是西方的一个发明”, 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一个他者。此外,作品中多次提及伽里玛与越战的关系,也证明西方文化从来不真正真实地接纳东方本身的文化,而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而东方人总是顺从西方的霸权文化。
结语:
《蝴蝶君》中宋丽玲在爱与恨的纠结之中传达了不同的伦理诉求,并最终演绎了一场道德意义上的悲剧。作为男旦的戏剧演员,宋丽玲因其特殊职业、民族、生理等身份对伽利玛产生不可避免的同性之爱。又回顾中国百年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并结合宋丽玲生活的时代背景,宋丽伶对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之恨。
参考书目:
Hwang, David Henry. M. Butterfl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Said, E.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antage, 1994.
黄哲伦.蝴蝶君.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O1)。
论文作者:周思琦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7
标签:伦理论文; 中国论文; 蝴蝶论文; 身份论文; 京剧论文; 旦角论文; 东方人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7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