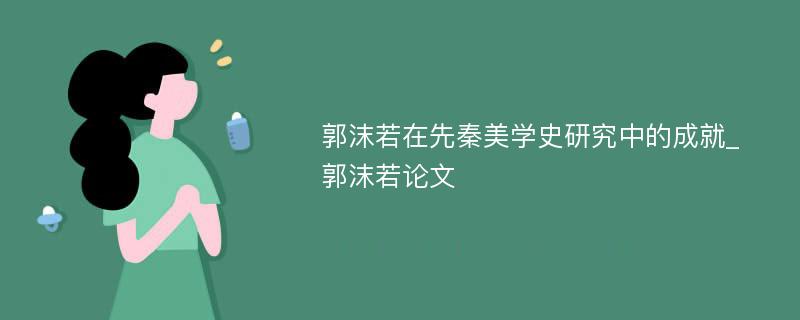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先秦论文,美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9)04-0001-08
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先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青铜时代》、《石鼓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时代》、《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集校《管子》。他侧重于社会史、思想史、文字史的开拓性研究,然而,又发挥了自身的学术优势,进行美学史研究。美学史既独立成体,又和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相交错沟通。郭沫若是文史哲之通家、大家,他充分利用通家、大家之才、之识,炬照美学史特别是先秦美学史,烛幽通隐、钩沉发微,遂使其研究成就别具一格,自成气象。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周代彝铭进化观》就曾直接运用了“审美意识”的概念。可见,美学已成为他的研究视域,美学史已成为他的研究领域。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又集中在青铜器的研究上。半个多世纪之前郭沫若对青铜器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和水平,至今还是人们研究的出发点。他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说:“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便是历代已出土的殷、周彝器的研究。”青铜时代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断代史上,而且在美学史、先秦美学史研究上由郭沫若打开了大门。
郭沫若杰出的学术贡献是确定青铜作为时代的概念存在。他在1946年《青铜器的波动》中认为:“跟着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便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既然相当于殷、周二代,而殷代有六百年之久,周代合东西二周共有八百多年,总共起来青铜器时代在中国是有一千多年历史,在殷以前,由于材料的欠缺我们尚不敢断言……惟殷代,则已经非常地明显,就是由青铜器进到铁器时代的界线。”郭沫若的这一界定十分重要,由此也奠定了他在青铜美学史和先秦美学史上的地位。
一、审美形式和社会史、美学史意识的融汇
郭沫若在先秦美学史研究上卓越地把审美形式和意识及其理性结论结合在一起,概括言之,是经验理性;具体言之,不是形而上地从抽象思辨层面上进行,而是从具体的器物切入。“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形下者为研究的起点,由形下及于形上,这是通过具体实例考察和抽绎出结论的科学研究途径。因此,他坚持以器物即广义的文本作为美学史的对象物。郭沫若在《青铜器的波动》中说: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约相当于三千年前的殷、周时代,那时的遗迹到今天也都有发现。自宋以来,收藏的古器不下一万件,保藏之久,数目之巨,实为中国的特色,可惜以往的都只把它们当作古董来收存,而没有当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实际上我们这些器物正是历史的最确实可恃的材料,在这些古器之上,我们可以发现三千年前手工业及一般社会状况与风俗习惯,因此,在今天好些古器都已被我们视作研究历史的学术资料了。
器物所发挥的作用是历史的资源、资料,犹如文献古籍一样,而不是古董收存。他着眼于历史的价值论体系,在《青铜器的波动》中说,由青铜器“使一切古器都有了历史的价值”,这是富有深刻意义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自汉以来所出土的殷、周彝器”,“即存世而有文字者亦在二三千具以上”,但它们并没有在史学包括美学史研究方面发挥应用的解读、抽绎作用。“此等古器历来只委之于古董家的抚摩嗜玩,其杰出者亦仅拘拘于文字结构之考释汇集而已”。郭沫若以拓荒者的眼光发现了“此等古器”的真正价值乃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因为它们保留了最原初的面貌和特征,“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因此“可单刀直入地便看完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这是实例性进而实行概括性的研究路向。在郭沫若看来,青铜器同时具备了社会史和艺术史的双重特征。就社会史而言,从青铜器“可以证明殷、周二代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形”——“在殷、周奴隶时代之后,中国出现行帮制的手工业时代,青铜器时代至此告终”;就艺术史而言,“青铜器的精巧技艺,却都移置他用了”。因此“不管研究艺术史或社会史都可以循着这些古器来作系统的研究”[1]171。
在确立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后,他又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青铜器皿上的器型、铭文和纹饰。
以文字而言,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被废弃,某一字的字形如何演变,可以探究“一字的社会背景和含义的演变”。他从审美上解读所施之文饰,其效用与花纹同。他认为,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钟鼎文与花纹等同,按照审美意识和方式所孕生,书法史纳入审美的方向就这么被确定了的。以花纹而言,“某一种花纹形式的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2]301。这样,就深入到美术史,也就深入到美学史层面上来了。这可以说是微观透现宏观式的研究。郭沫若上世纪30年代两次写给容庚的信中均表述了这一思想,1930年4月6日的信中说,青铜器“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而划定时代的界限又是重中之重;1931年7月17日的信中认为,“定时乃花纹研究之吃紧事”。郭沫若第一次原创性地运用青铜器花纹来解读和确定时代的界线、内涵和特征,在先秦美学史的研究上独具地位。
纹绘、纹样、纹饰都是形式,是经过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成线条和结构的有机组合和配置,但是,它包含着某种趣味。正因为它是有意味的,才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生机和表征着某种历史性的深刻内容和意韵。郭沫若从青铜鼎器的“厚重”形制中探发出“深刻”的意味。饕餮是传说中的食人猛兽,据此所塑造的形象本身就包含着先秦时代人的意识的对象化需要。然而,当它凝定起来,转而便又成为人们表达某种观念的具象体,用以显示自身的神秘、威严,因而它是历史力量的符号。郭沫若的贡献也就在于透过生动的形式探觅到生命的意味(即内涵),这样,便使他的美学史研究富于深度和学术厚重感,不同于一般性的现象、形态或范畴的罗列和陈述。他作为青铜器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成了青铜器美学史研究的开山祖。
郭沫若不仅从几何图案和抽象纹饰形式中把握历史的形态,而且观照历史的意脉,更把文字图形研究融入美学史研究之中,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之路。总的来说,就是充分利用了线条的艺术抽象形式(鼎器上的花纹和文字两种线条形式)。花纹和文字作为线条艺术的图饰,同时成熟。把握线条艺术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才算是把握了问题的基核,抓到中国美学史的最原初和最根本特征,这正是郭沫若美学史研究的杰出之处。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中认为:“彝铭之可贵在足以征史。”郭沫若的铭、史互证和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论,异曲同工,开辟了研究的新天地。那么,依靠什么来具体操作呢?“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他又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而为文饰。如钟鎛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郭沫若在这里视文饰(即文字图饰)与花纹同等效用,把它置于跟纹饰的同等地位上,这是对汉字特征的最根本揭示。汉字乃是象形字,是区别于拉丁文之所在。“象”表模仿、拟构、象征等功能,因而一方面是记录符号,结束了结绳以记事的原始阶段,另一方面在审美意识的支配下,充分利用汉字线条结构的特征,龙腾虎跃,出现曲直、构架、意兴,便进入审美,成为美的艺术。在该文中郭沫若所说“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是一个极有见地的见解,是他用审美眼光炬照中国美学史图式之范例。“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是郭沫若通过对钟鼎文之研究,对汉字之为艺术品的最基本确定,也是对书法艺术源流史的最原初确定。这种确定无疑具有美学史意义,万里征程就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只要看看钟鼎文的那些整饬而又灵动、俏健而又柔媚、古拙而又颖脱的字迹,就会印验郭沫若的书法美学起源论的正确了。
他还提出与古代美学史的创造者进行精神互动和心灵勾连,用他个性化的话语来说,就是谛听远古美学的“心音”。郭沫若生理的耳朵久已失聪,但他心理的“耳朵”却灵敏、发达,细致入微。《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认为“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一幅绘画”,“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的铅幕,我们听出了古代画工的搏动着的心音”。他对远古的谛听,听到了美学史最原初的声音,也形成了研究主体与远古美学“心音”的对话和交流。他“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的铅幕”,其历史目光和审美目光是何等深邃而犀利!
二、“标准器论”、“波动论”的发明
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先秦美学史的研究上“凿穿了”“混沌”,乃是因为他“颇有创获”地发明了核心论——“标准器论”。他不止一次地申述了这一理论:“先选定了彝铭中已经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为标准器或联络站,其次就这些彝铭里面的人名事迹以为线索,再参证以文辞的体裁,文字的风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纹形制,由已知年的标准器便把许多未知年的贯串了起来。”[2]302既含有系统综合论,又含有已知进而未知的推导论。它不尚外证,完全从自身出发——“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采定见——“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另定规范——“不据外在之尺度”,靠的是内证。它从“标准器”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必不甚远”[3]307。他在历多年之后,经过检测、积淀,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仍坚守了他的“标准器”,前后表述保持了一致性。
“波动论”,或曰分期论、阶段论。时代性、时段性的划分、界定是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史、先秦史和先秦美学史最具根本性质的研究成就,王国维、罗振玉先生在这方面均未解决,视为笼统的时代观念存在,而郭沫若始作突破,厥功斯伟!
郭沫若创立了青铜器的“四个时期说”:“大体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2]302这一分期论最早见于1934年所撰《彝器形象学试探》:“第一,滥觞期——大率当于殷商前期。第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第三,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1945年,他在《青铜器时代》中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他把古代史研究、古文字研究、古纹饰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导入美学史研究。到1946年,他在《青铜器的波动》中重申了“四个时期说”并进一步确定它的具体阶段和时限。第一期“殷代+西周前半”,第二期“西周后半+春秋时代”,第三期“战国时代”,第四期“战国末年+后来”。四个时期的变化、演进,是在花纹、模样、铭文等无一例外地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尽管某些具体提法和时期的界定有些不一致)。它不仅有史学的分期意义,而且有美学史的历程轨迹。第一时期因脱胎于石器时代,前后相距时间较短,因此带有石器时代的特征和遗韵。到了第二个时期逐渐脱离了原始风味,第三个时期呈现精巧气象,第四个时期花纹几乎褪废。花纹是殷周青铜器最显著、最外在的感性表征,具有浓烈的美学情味。它的变化显示出审美特征的变化,进而显示出审美理想的变化。
郭沫若所考察的殷、周青铜器主要是鼎。他本人在《彝器形象学试探》中也说:“其器多鼎。”鼎在初期出现包含着实用性、功利性、审美性的三重功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用性让位于功利性和审美性;在郭沫若的美学史研究视野内,重视审美性又超过了功利性。《左传·宣公三年》载:“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这段记载中,鼎作为盛物器皿的实用功能弱化了,而作为王权象征的功利主义特征则被强化了。这才有楚王问鼎的狂妄举动,也才形成“问鼎中原”的历史成语。这番记载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铸鼎象物”,鼎上物象或花纹不是孤立、绝缘的存在,而是用以“象物”的。郭沫若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中对上引的《左传》中的一段话,做了这样的解释:“这说的虽然是夏代的事,但其实道破了古代彝器著象的真实用意。”此可谓是精辟之论。殷、周鼎器从一开始铸造就有不同于陶鼎器所具有的盛物实用功能的倾向,它不再具纯实用性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器物存在,而是用以“象物”。象,即表征、象征。这样,它就被编入艺术的符码,具备了审美的因子。这正成为郭沫若把握殷、周青铜器进而研究先秦美学史的绝好契机。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说:“铸器之意本在服用,其或施以文镂,巧其形制,以求美观,在作器者庸或于潜意识之下,自发挥其爱美之本能。”这是彝鼎器初起时,在增强“服用”即实用功能时,巧作形制,施用文饰,目的是“以求美观”。这样,审美的表层线条、色彩特征便孕育出来了。从“作器者”来考察,郭沫若认为他们在潜意识中,有“发挥其爱美之本能”。这里借用了心理学的原理,为青铜器装饰美的形成寻找到了原因。郭沫若以历史美学的眼光探发出殷、周青铜器表象所蕴涵的深层意识。他说:
(青铜器)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绘者,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纹,夔凤,夔龙,象纹等次之。大抵以雷纹、饕餮为纹绘之领导。雷纹者……盖脱胎于指纹……饕餮、夔龙、夔凤,均想象中之奇异动物……然彝器上之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4]313
青铜器皿特别是彝器上多饰以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云雷纹。郭沫若通过对纹样、纹饰的分析,作出了重要揭示:审美不是写实。形体是具象的,具象化的形态是经过想象所获得;而“彝器”之“象纹”,又是经过了“幻想化”。无论是具象的形体,还是抽象的纹样,都不是实物写照,乃是观念的对象化,表现殷、周青铜器深沉的历史力量。“率经幻想化”的“象纹”是一种抽象性的线条。这种抽象是艺术家的幻想产物,凝聚着灵动的形式感,是中国艺术的伟大发展,体现了高度的审美抽象力。这种图案、纹样是那个时代美的表征,传送出的美的讯息被郭沫若首先感应、理解、把握、接受到了。
三、实证精神、方法论及其学术生态的合力
探究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具有实证的科学精神,运用先进的方法论,形成了优越的学术生态环境,进而从内外场域上凝聚成合力。
1936年的《我与考古学》集中表达了郭沫若的学术见解:“这种学问是要以纯粹的客观的态度,由地面或地底取出古人所遗下的物证来,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考察出人类的文化从古以来所历进着的过程。”他的地上和地下二重证据论显然受到了被他尊之为“新史学的开山”[5]6——王国维先生的直接影响,跟陈寅恪先生的互证法交相发明,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法论的创获。他重视实例、实物、实证,回归和还原历史现场,为之做了大量的扎实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他说:“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载祀八百,其绵延几与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统称曰周,实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录愈多,愈苦难于驾驭。寝馈于此者数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3]306他在实际上就是做的这些精密的整理工作。他认为,科学的结论是具有真实性品相和品格的实例、实物、实证的逻辑概括和提升,以此作为坚实基础。
不断补充和丰富新的实证资源。郭沫若还从后代的史料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隋书》,开皇十一年正月丁亥,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靖康北徙,器亦并迁,金汴季年,钟鼎为祟,宫殿之玩。悉毁无馀。”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4]314这样便从“骇怪”的“形象”中推寻出深沉犷怖的历史力量,在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双重运动中产生了研究的深度。
实证研究又建筑在证伪的基础之上。郭沫若在《〈甲骨文辨证〉序》中说:“怀疑辨伪乃为学之基阶,为学与其失之过信,宁取乎多疑;子舆氏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终古不刊之论也。鼎彝甲骨诚多赝品,然而疑之有方,辨之有术,富有经验之士于其真伪之间几于一目可以辨白。所贵于学者即养畜自己之目力,先期鉴别之精审,更进而求其高深。”研究者养成眼力和学识,“观千剑而后识器”,一眼便能洞穿真伪。《“汤盘”“孔鼎”之扬榷》综合运用金文和文献资料,加以证伪。他写有《正考父鼎铭辨伪》,用有力的内证和外证,得出结论,说:“可知鼎铭全不足信。其文仅寥寥数语,前半抄袭而错误,后半摹仿而欠通……盖文之饤饾一至于此,其恶劣可谓登峰造极。”他推论造假之原因:“知《正考父鼎铭》为伪托,则知孟僖子之预言亦必为伪托。盖后之儒者推崇其先师,欲为之争门望,故托为此言以示光宠。”他寄希望“彝器铭文及形象等系统之学,方有成立之一日”,而他正是建立这一系统学的奠基人。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不是纯美学研究,而是以时代内容为核心的历史学、社会学和美学的互构性、交叉性研究。《“毛公鼎”之年代》是以铭辞来判断和界定时代之杰出范式:
本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犹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代为宜。
本铭之王自命不凡,辞气之间大有欲振兴周室,追踪文、武之概,此于宣王之为人为宜。
本铭中针砭时弊之语,于宣王时之史事尤相契合。
郭沫若于1942年5月15日《说文月刊》发表的《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对其中的“梁其器”考释,表达了和上述见解颇为相似的看法:“器出扶风,又花纹同毛公鼎,亦为西周末年器之一证。毛公鼎已经余考定,乃宣王时代之物也。”
划分时代的阶段性质,以此确定其内涵。史是由一个个时代连续和组合而成的。郭沫若反对“时代不分,一体浑沌”,因为时代性是具体的,不是混沌一片,乱成一团的,其阶段性鲜明而各有特征。《“毛公鼎”之年代》认为:“以周而言,有周一代载祀八百,其绵延直等于宋、元、明、清四代,而统称之曰周,此甚含混,不直是纸上之杂货店耶!”这和上引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他反复主张对某一大的时代区段要加以细分,经细分后时代的阶段性质、特征才得以彰显。然而,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照点和方式,即从烙有时代印记的实物、实器入手去探发各别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审美理想。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这些东西差不多是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的。譬如拿瓷器来讲,宋瓷和明瓷不同,明瓷和清瓷不同,而清瓷中有康熙瓷、雍正瓷、乾隆瓷等,花纹、形态、体质、色泽等都有不同。”[2]299时代具体论、区分论、特征论,是郭沫若历史观、美学史观的重要内容,和王国维的文体时代划分论一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然而,郭沫若的论述是着眼于审美形象、审美理想,特别是从美学的具象、形象中去揭示其审美理想及其审美理想的时代性、时代具体特征,因而更接近于科学的结论和史的实际。
在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宏深背景下考察美学现象的变化,反转过来,美学现象又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生动表征,双向互流的结构,使郭沫若的美学史研究获得了厚重的历史感。《彝器形象学试探》指出:“开放期之器物……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绘者,刻镂较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则不免粗率。”这里包含着纵向性比较:“前期”与“本期”,从而显示出美学史的阶段性差异色彩。盛极一时的雷纹,几乎绝迹;饕餮纹沦为附庸;夔龙夔凤亦已变相和变态;整个纹饰趋于肤浅粗陋,郭沫若由此揭示道:“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这为美学史演变现象提供了结论,神话时代宣告结束。饕餮的威慑,借助于恐怖色彩和纹饰来显示社会的力和威。这带有浓重的原始意识和神话思维色彩。它的淡化,显示出原始神话思维的弱化,社会历史的进化使得先民得以摆脱原始神话思维,产生实践理性思维(用郭沫若的概念来说,叫做“理智”),从而标识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郭沫若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中关于夔的演变有过专门的论述:“夔的形象在殷、周彝器的花纹和玉器的形制中极多见”;“夔,本是古人所幻想出的动物,就和凤一样,并不是真正地存在。所以在战国时代的人,理智渐渐发展了,对于‘夔一足’便采取了合理化甚至否认的说法”。这是对夔的存在的怀疑,它再也不是威风凛凛和令人望而生畏了。“权威”失却,大国降为“附庸”,于是思维投射到存在上,夔纹失落了。这种失落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的空谷足音。在这个层面上,是说青铜器饰映射出时代的风气变化;在另一层面上,则又是时代历史意识和美学意识的变化(不可触),促成了青铜器饰之变化(可触),因而具有双向互因关系。这就使得郭沫若的美学史观闪烁着社会学史的光芒。
郭沫若在对感性的美学晶体加以阐释时,十分注重原社会生态和形态的复现和文化内涵的揭举。例如对“莲鹤方壶”的阐释: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6]509
当中国文明从神话和半神话中走出时,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理性意识。郭沫若从白鹤亮翅的雄姿中发现了它所透发出来的美的昂奋精神,这是感性层面的发现,属于第一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进而推导出精神的社会、文化涵值:“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从感性之现象抽绎出理性之结论。需要提出的是,他进行感性层面的描述有一个别人所未及之处,那就是包含着自身对于对象的感受:此壶“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这是他从“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中感受得来的。这在中国美学史家中是很有特点的。他摆脱了纯客观性的美学研究,渗透了研究主体的意识、感受,而这在美学研究中不是应该排斥,恰恰倒是需要提倡的,因为美学是在主体把握中进行的。郭沫若在阐释美学现象时既透入自身的主体感受,又进行着感性的描述,体现出他的审美感受力和穿透力。因而,他的美学史研究又具有经验美学的色彩。
郭沫若的美学史观焕发出史识的光芒。他对于美学史研究和美学现象阐释,总是那么不同凡响、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乃是因为他有深邃而锐利的识见。这样,他的美学史观就有光点、灵犀。
郭沫若的研究不仅还原和复现时代,而且把美学现象中的精神归结和提升为时代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例如,前引的他认为莲鹤方壶中那站立于莲瓣之中、展开双翅、“单其一足”、微微张嘴似乎要鸣叫的白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又例如,他对晚周帛画的阐释:
夔是死沓沓地绝望地拖垂着的,凤却矫健鹰扬地呈现着战胜者的神态。的确,这是善灵战胜了恶灵,生命战胜了死亡……这是生命胜利的歌颂。
画的构成很巧妙地把幻想与现实交织着,充分表现着战国时代的时代精神。
虽然规模有大小的不同,和屈原的《离骚》的构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起《离骚》来,意义却还要积极一些:因为这里有斗争,而且有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念。画家无疑是有意识地构成这个画面的,不仅布置匀称,而且意象轩昂。画家是站在时代的焦点上,牢守着现实的立场,虽然他为时代所限制,还没有可能脱尽古代的幻想。[7]436-437
把握了时代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美学现象和美学精神就有了总体格调和趋向,这正是把握美学史的需要。对于殷、周青铜器,他首先扣住的是花纹图案这一感性现象。《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要求人们“细玩”“图案”。他具体阐述道,即使器物上没有铭文,其“花纹图案”也能“显示其时代性”。“大凡殷、周古器中之花纹均偏重几何图案;其次的动物图案,大抵均原始想象中之怪兽形;动物形而用写实手法者甚罕见,其用植物为图案者,则可云绝无仅有”。《“毛公鼎”之年代》一文对上述文化、美学思想做了集中发挥。以花纹形式为对象去揭示时代文化特征、审美理想。他说:“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成,今时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之时代上占有极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据,有时过于铭文,在无铭文之器则直当以二者为考订时代之唯一线索。如有史以前尚无文字之石器时代,其石器陶器等,学者即专据其形式若花纹以判别其先后。其法已成专学,近世考古学大部分即属于先史时代者也。”他不满于“中国学者考订古器物,自来仅专靠铭文,而于花纹形式毫无系统之研究”,即使某些“稍完备者,虽亦图像与铭识并收”,但是“其图像多空存而无说。说之者又多本先入之见而妄事臆测,不知比验其异同,追踪其先后,于形式与花纹之中求出一历史系统”。他提出这样的研究构想:“余谓凡今后研究殷、周彝器,当以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而他,正是身体而力行之。
郭沫若对此的研究还有更深入之处,即以花纹图案为具体案例,界定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审美特征:“凡殷末周初之器有纹者,其纹至繁,每于全身极复杂之几何图案(如雷纹之类)中,施以幻想性之人面或兽面(如饕餮之类)中,其气韵至浓郁沉重,未脱神话时代之畛域。稍晚则多用简单之几何图案以为环带,曩之用不规则之工笔者,今则用极规则之粗笔,或则以粗笔之大画施诸全身,其气韵至清新醒目,因而于浓重之味亦远逊。更晚则几何图案之花纹复返诸工笔而极其规整细致,乃纯出于理智之产品,与殷末周初之深带神秘性质迥异矣。”这些分析体现了郭沫若所独有的学识、眼光、欣赏水平和判断能力,最具美学史深度。以具体的花纹图案的感性特征来界定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审美特征,由此来划分美学史、文化史的区段,这是独具特色的文化史、美学史研究。从这一论述系统和基本观点出发,郭沫若认为那只“毛公鼎”“绝非周初之器所宜有”,其依据是由花纹案来鉴别的,其“花纹仅由两种简单之几何图案,相互间插,联成环带,粗枝大叶”[8]672,乃非周初之形制。郭沫若的上述研究是真正的美学史研究,关键是他久已形成了深广的史学意识、观念和眼界、视域、方法、材料。可惜,至今出版的美学通史虽有几部,但没有继承和延续郭沫若所开拓的美学史研究之路,对于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成果更吸收得不够。
郭沫若的这种先进的方法论,还得益于国外的研究方法理论的借鉴。他曾翻译并出版了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又名《美术考古学发展史》),他从这本书中借鉴了方法论,并与先秦美学史研究相连接。他在译文序言中认为,该书从方法论上给他以直接的帮助,说:“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反之,“假如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推而广之,“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他十分赞扬道:“这书实在是一本好书,它把十九世纪欧洲方面的考古学上的发掘成绩,叙述得头头是道。”[9]392-393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成果是当时学术生态所孕生出来的。郭沫若研究先秦美学史的整体学术生态环境是优越的,相互切磋,资源共享,决不个人居为奇货,互相封锁。就莲鹤方壶,曾发生了一桩学术公案。对郭沫若的此器解读,著名文物考古学家马衡先生提出了疑义。1932年11月致信郭沫若,言“当出土之时”,“亲往参观”,亲眼见到“鹤者亦确有之”,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疑问:“不知应附丽于何器?”他发现“凡壶盖必却置,故其铭必倒刻。今缀一鹤则不能却置矣。故知其谬妄也”。郭沫若接受了这一见解,于1933年刊行的《古代铭刻汇考》中登载了马衡的这封信,曰:“莲鹤方壶之臆论……自承谬误。”后来,却又收到亲历发掘的郭宝钧先生的信,否定之否定,郭沫若的《新郑古器中“莲鹤方壶”的平反》谈及此事:“郭氏此信,实为我解决了一桩重要的公案。汲县壶之出土不仅足以证明新郑之壶之不孤。而‘鸟立板心,盖中透空,盖与板判然二物’,亦足破‘盖必却置’之反证”,“余因未见原物,故于己说无法坚持,于马说未免轻信。今既得确证,故得维持原说,而取消1933年的‘谬误’之自承。”他认为,马衡先生提出异见,“商讨学问,以求接近事实”。据此,他就形成了先秦文化史、美学史的两项基本的研究经验:“做学问必须多求实物的根据,审慎从事,而且也必须多向朋友请教,以资反复商讨。不然便会轻易判断,轻易置疑,轻易诬枉,而且轻易失掉自信了。”概乎言之:一是实物依据,二是学界商讨。郭沫若受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尤深,得容庚先生的学术帮助尤多。容庚编辑《金文编》,郭沫若以得读释金文之便捷。时郭、容素不相识,郭沫若亡命日本,闻容庚于古文字学有精深研究,求助于铭文的拓本、摹本等,总是有求必应,毫无保留。正因为容庚慷慨相助,郭沫若才得以根据拓本、摹本之实物加以解读、研究。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常见“铭据容庚摹本”句。郭、容之间建立的学术交谊,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佳话。
唐兰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所作的序,高度评价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的成就,说:“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郭沫若之所以在这方面取得后人难以逾越的成就,最根本的是有巨大的学术勇气和探求精神。《〈管子集校〉叙录》说:“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力,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金文丛考〉重印弁言》说:“人们可以有所恃而深入虎穴,亦有所恃而必得虎子。”他在该书标题页的背面,题句曰:“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感慨万端,深长系之,大有太史公《报任少卿》的情味。由此也就揭示出了他在先秦美学史研究上取得世纪性成就的答案。
收稿日期:2009—06—28
标签:郭沫若论文; 美学论文; 青铜器文化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论文; 考古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文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