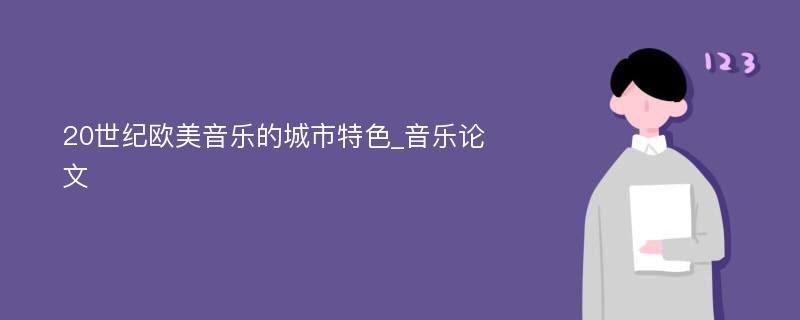
20世纪欧美音乐的都市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美音乐论文,特性论文,世纪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18、19世纪欧美的作曲家们通用共同的和声素材与处理手法,但踵至的20世纪欧美音乐却再未呈现出划一的图景。当代欧美音乐所标明的时代特征,正是艺术风格的纷然杂陈、多元并立。然而,在复杂的文化变异进程中,20世纪欧美音乐产生自一个相似的社会环境,即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折,这又使它们获得在某种维度上具有共性的外部条件。当代欧美的许多音乐作品具有“都市特性”,这一客观现象正是符合环境与文化变异之间辩证关系的一种结果。
19世纪后期,加速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欧美社会,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德国在统一前仅有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到1903年,这样的城市已有15个。柏林在1860年只是个50万人口的城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200万。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的人口由200万增至300万。伦敦在1880年已拥有500万人口,比1800年增长约四倍,而到1914年则成了有7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大都市的出现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它集中了庞大的人口,聚合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凝结了巨大的智能,成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心,人类世界为之改观。
如果说现代世界的面貌是科学技术所塑造的,那么都市机械文明,无疑对20世纪欧美音乐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体现机器支配力的都市景观,包括电影艺术、大众传播媒介、摩天大楼、工业机械、汽车运输、以及火车、飞机组成的市际交通等等,成为艺术家灵感的源泉。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曾这样写道:在欧洲农业占压倒优势的1850年,“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更不用说意大利人、教皇或西班牙人,都住在农村或小村镇里。四十年之后机器以及它绝对必要地把生产和生产过程集中,使人口失去平衡,倾向城镇。波德莱尔关于异化了的灵魂‘蝼蚁之城’的诗篇——‘蚂蚁密集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那里,光天化日之下幽灵拖曳你的衣袖’——开始排除田园的景象”,(注: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第4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而那种自然风光在J·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瓦格纳的歌剧、民族乐派作曲家和R·施特劳斯的交响诗中,就象在马内与雷诺阿的绘画作品中一样,达到了最后的顶峰。“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并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一种主动的适应,适应本身也就包含了改造。”(注:吕斌:《文化进化导论》第13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文化的发展加速了环境的变化,艺术家的观念也产生了剧变,他们开始认为“一辆奔驰的汽车就象一挺机关枪,它比萨莫斯雷斯胜利女神更加美丽。”(注: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第711页。)一位未来主义画家起草了关于“机械美学”的宣言,要颂扬齿轮、滑车、活塞、飞轮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品格。
1913年,意大利作曲家、未来主义运动的先驱路易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 1885~1947)为他的19件噪音乐器组成的乐队写了一部4乐章的组曲《噪音网》,其中第二乐章的标题为《汽车与飞机的集会》。在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成功第一架载人飞机10年之后,第一次在乐曲的标题中出现“飞机”的字样。到20年代,“机器音乐”大为膨胀。瑞士作曲家奥涅格写了一部久演不衰的管弦乐曲《太平洋231》(1924),这一标题暗示当时在美国问世的一种新型火车头,乐曲从模仿火车头排气、启动开始,以车轮滚动的轰鸣声和尖厉的汽笛声结束。美国作曲家埃默森·惠索思(Emerson Whithorne,1884~1958)取法鲁索洛,为管弦乐队写了《飞机》1926年)一曲。德裔美国作曲家、钢琴家乔治·安塞尔(George Antheil,1900~1959)创作的钢琴作品包括《飞机奏鸣曲》(1922),《小奏鸣曲“机器之死”》(1923)、《机械装置》(1924)等,他的舞剧《机械芭蕾》(1925)中用了8架钢琴、1架自动钢琴、8架木琴、2个门铃及飞机螺旋桨声,27年在纽约首演时用了真的螺旋桨并加入了汽车喇叭。美国作曲家J·A·卡彭特(J·A·Carpenter,1876~1951)的舞剧《摩天大楼》(1926)中,用加了班卓琴、萨克斯管的大型管弦乐队、复合的节奏、狐步舞节拍、地铁的律动、百老汇叙事曲的格调,表现了高楼林立、喷着烟的廉价汽车来回穿梭、匆忙的行人熙来攘往的美国都市纽约的生活场景。
声乐作品中也时常印染机械风采。德国作曲家库特·魏尔(Kurt Weill,1990~1950)与剧作家B·布莱希特合作创作了广播康塔塔《林德伯格的飞行》(1927),咏赞了美国飞行家林德伯格1927年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的创举。美国作曲家克热内克(Ernst Krenek,1900~1991)在他的爵士歌剧《容尼奏乐》(1926)中讴歌了工业技术的奇迹。奥地利作曲家马克斯·布兰德(Max Brand,1896~1980)则在三幕歌剧《机械师霍普金斯》(1929)中叙述了纽约工厂中发生的一起机器伤人的悲剧性事故。德国作曲家欣德米特的讽刺歌剧《当日新闻》(1929)中,一对夫妇唱着“憎恨二重唱”,合唱队唱起“离婚进行曲”,妻子裸露全身,坐在浴缸里唱咏叹调,一个侦探装扮成情人来查证一桩通奸案,打字机节奏怪诞地发出咔嗒声。这部被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破口大骂为“无调性作曲家的道德败坏”的歌剧,当然与表现天神、国王、公爵夫人的浪漫主义歌剧大相径庭。
在俄罗斯,都市特性音乐与“无产阶级音乐”并行不悖,如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舞剧《钢铁时代》(1925),肖斯塔科维奇用进工厂汽笛的第二交响曲等。莫索洛夫(A·Mossolov,1990~1973)根据自作的舞剧音乐改编成一部乐队组曲《铸铁厂》(1927),配器中放入一张钢板,模仿工厂机器发出的轰鸣。据说莫索洛夫以“结构主义音乐”之名提倡“苏维埃现实主义”,结果却在前苏联被批判为“颓废主义”。匈牙利作曲家尤金·扎多尔(Eugen Zador,1894~1977)写了一部描述现代工业的《技术交响曲》(1932),分为“桥梁”、“电线杆”、“供水系统”和“工厂”四个部分。墨西哥作曲家查维斯(C·Chavez,1899~1978)写了一部名为《马力》的舞剧,刻画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美国与贫困但充满原始活力的南美之间的鲜明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种夸张、写实的乐风不再时兴,但直到1964年,美国作曲家科普兰还写了一部描写纽约城市之声的乐队组曲《伟大城市的音乐》。科普兰的学生,西班牙作曲家L·巴拉达(Leonardo Balada,1933~ )根据访问美国钢铁中心匹兹堡炼钢厂后的印象,在1972年创作了一部单乐章的《钢铁交响曲》,1973年1月12日由D·约翰诺斯(Donald Johanos)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首演,并于1986年3月18日由马捷尔指挥该乐团在新世界唱片公司录制了CD。
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指出,引起艺术风格变化的主要力量有两种:“其一为技术改进;其二为社会竞争。”(注:E·H·贡布里希:《论风格》,见《艺术与人文科学》第89页。)都市机械文明对音乐艺术的浸染,当然可以用“技术进步影响着选择情境(choicesituation)”(注:E·H·贡布里希:《论风格》,见《艺术与人文科学》第89页。)来解释,但这种新的文化语境的产生,有着更为复杂的成因。当作曲家笔下的山峦瀑布、花鸟黄昏替之以发电机、涡轮机时,不论有意无意,他们从机器的轰鸣中感受到了一种既难于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力与能。机器生产物质财富,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注:马克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斯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第16页。)机器成为作曲家们顶礼膜拜的神明,也成为他们“非人性的艺术”的象证。
20世纪英国“概念小说”作家阿道斯·赫胥黎曾写过一本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1932),书中描绘在未来社会中,技术上所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范围日益扩大,进而能满足人们种种非物质的(如宗教性的、情感性的)要求。在生物工程学改变人类的基因与生理存在之前,其他的科技已能改变人类的“人性”存在。反乌托邦小说在幻想王国试图摇撼“人性”,而漫衍的机械音乐却在现实世界表露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无疑,机械音乐的作曲家在创作时,面临着敬仰科学和尊重基本的价值观之间的痛苦的抉择。20世纪的科学,正如法国还原论生物学家雅克·莫诺所说,其义无反顾的反人道主义倾向丝毫没有削弱的迹象,而且科学不能逃避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威胁的命运。他说:“在此,我不提及人口爆炸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甚至也不提及数量众多的百万吨级的核力量;我只想提一个更阴险和更深层的罪恶——一个围困着精神的东西。它是由思想发展的最关键的转折点而引起的。而且,这一发展还在同一方向上不断继续和加速,加剧着人们心灵上的痛苦。”(注: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纽约文特奇书店1972年版,第164页。)显然,作为无机的简单体和有机体奴仆的机械,在将效益和惊异带给世间的同时,已使有机体成了俯首贴耳的奴仆。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以大都市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电子技术以其综合性强、知识密集、投资效率高而位居高技术产业榜首,其迅速发展甚至导致拓建新型科技城(注:参见王洪濮:《20世纪科技史话》第八章。)。美国在西海岸集中了约800多家公司形成微电子工业生产中心,加州的硅谷,1977年产值为48亿美元,1981年上升为115亿美元。这种发展势头,是本世纪初兴起的汽车等工业难以企及的。电子技术业已成为任何一项新技术都离不开的基础,成为都市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当然也巨大地冲击了音乐,从感性材料、存在方式到传播媒介产生了一系列革命。
据美国音乐学家罗伯特·P·摩根的论著记述(注:参见R·P·摩根:《20世纪音乐》91年诺尔顿英文版第二十二章。),电子技术在其发展的初期就已引起音乐家的关注。他们尝试制作电子乐器,探求前所未有的新音源。1906年,撒迪厄斯·卡西尔(Thaddeus Cahill,1866~1934)设计了一台重达200吨运用电子发生器的电子风琴(Telharmonium);1920年,利夫·特尔门(Lev Termen,1896~ )创造了能够通过调节电子振荡器演奏单音和音高连续体的泰勒明电子琴(Theremin),瓦雷兹1934年为男低音与乐队写的《赤道》中采用了两架;1928莫利斯·玛特诺(Maurice Martenot,1897~1980)演示了他创制的玛特诺电子琴(Ondes Martenot),不仅可以奏音高连续体,而且可以在音质和音色上作更多的变化并可演奏复调,米约、梅西昂、若利韦、伊贝尔、奥涅格、弗洛朗·施米特等作曲家都曾采用过。1929年,路易斯·哈蒙(Louis Hammond,1895~1973)首创电子管风琴。(Hammond organ)。
二战后,声学技术专家、作曲家皮埃尔·舍菲尔(Pierre Schaeffer,1910~ )在巴黎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创始“具体音乐”,运用电子手段将乐音或其他自然音响变形后录在磁带上放送。1951年,他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第一个电子音乐工作室,GRMC(注:Groupe de Recherche de Music Concrete的缩写,即“具体音乐研究组”。),许多作曲家都曾在那创作“具体音乐”,包括梅西昂、瓦雷兹、布莱兹、斯托克豪森和泽那基斯。同年,生于中国的俄罗斯作曲家弗拉基米尔·乌萨切夫斯基(Vladimir Ussachevsky,1911~ )与美国作曲家奥托·吕宁(Otto Luening,1900~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电子音乐工作室,创作以“音乐的声音”(musical sounds)(注:例如,乌萨切夫斯基《声音的轮廓》(1952)基于钢琴的声音;吕宁《空间幻想曲》(1952)基于事先录好的长笛的声音。)为音源的磁带音乐。1952年德国作曲家赫伯特·艾默特(Herbert Eimert,1897~ )在科隆西德广播电台创办第一个完全用电子手段制作作曲素材的电子音乐工作室,而从巴黎回国的合作者斯托克豪森则既写纯电子音乐,也写与“具体的”声音结合的电子音乐(注:前者如他的练习曲Ⅰ号(1953)Ⅱ号(1954),后者如他的《青年之歌》(1956)、《远距音乐》(1966)。)。以后的作曲家多半对这两种作曲方法持开放的态度而不再作严格区分。50年代电子音乐工作室相继在米兰(1955)、华沙(1957)、伦敦(1958)、布鲁塞尔(1958)、斯德哥尔摩(1958)等城市建立,通常由国家广播电台出资。同时,在美国的安亚伯、旧金山、纽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等一些都市中,出现了许多隶属大学或私人设立的电子音乐工作室。
60年代,电子音乐广泛进入了广播、电视和影院、剧场,日趋商业化。音响合成器(Synthesizers)的出现大大简化了磁带拼接和音响合成的过程,作曲家可以在一个键盘上获得音高,用按钮控制泛音、波长、共鸣、声源位置,其意义是双重的:既压缩了电子音乐创作时间,又扩大了商业化运用的途径。最早成功的音响合成器是1955年在新泽西萨尔诺夫研究中心完成的RCA马克Ⅱ号,后给了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巴比特用马克Ⅱ号创作了不得《电子合成器曲》(1961)和著名的《夜莺》(1964)。美国发明家R·穆格(R·MOOg)和D·巴奇拉(D·Buchla)在60年代中期发明了更简便实用的电子合成器。80年代广泛传播的数码音响合成器能够产生更为复杂的音响而设备更轻便。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制成运行,而首次将电脑用于声音合成是在1957年,由美国电子工程师马克斯·V·马修斯(Max·V·Matthews)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完成。196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及稍后的斯坦福大学改进了马修斯的电脑程序设计。同年,在荷兰都市乌得勒支建立了欧洲最早一个电脑音乐工作室,并随之遍及欧美。电脑的使用使作曲家更自由地控制音高、音色、力度、节奏等参数,既可以通过电脑将音响合成器与其他电子设备相连接,使演奏程序实现更迅捷和自动化;又可以用来将事先录好的“自然的”声音进行变化,产生电脑制作的具体音乐;还可以用电脑实际写作乐曲,如美国作曲家利亚兰·希勒(Lejaren Hill)和伦纳德·伊萨克森(Leonard lsaacson)模拟独特的音乐风格(如巴赫、巴托克等),分别为各乐章设定作曲程序,用伊利亚克电脑为弦乐四重奏创作了《伊利亚克组曲》(1956),希腊作曲家泽那基斯用电脑为弦乐四重奏写了ST/4(1962)等。
事实上,一部计算机与一部机器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一部机器的各部件遵守力学定律,作用于这些部件的是外部力量。在计算机中,不过是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代替了螺母和螺栓。正如澳大利亚生物学教授查尔斯·伯奇所说:“螺母和螺栓不能够进化。它们只能被重新组合。”(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95年版,第91页。)“从任何意义上讲,计算机都没有什么进化,它只不过是由设计者改变了机器的外部设计。”(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95年版,第91页。)
电子技术影响音乐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使人类从人声与传统乐器的音响中解脱出来,开发亘古未有的音响媒体,为人类抒发情感发挥想象探求新的运作空间。作曲家不仅运用新的音源突破常规的音色、织体、曲式等表现因素,而且运用传统媒介去模仿非入声与传统乐器产生的音响,拓开了音乐形象的全新天地,使得科技日新、道统变异的20世纪都市,有了契合精神、适逢其会的时代之声。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是负荷着价值的,有着伦理与政治问题的含意。哈贝马斯甚至宣称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注:参见J·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68年版,第100-112页。)。电子音乐作曲家的探索,既反映了都市时代科技思维模式对艺术创作乃至社会生活和日常思维的浸渍,也表达了当代艺术家对技术社会中人的处境的深切关怀。
都市生活充满着运动、速度和竞争,而体育比赛正体现了这种特性,无怪20世纪欧美音乐中描述体育运动十分普遍。现代都市的体育运动并非养生之道,其文化实质是竞赛,所追求的东西正象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句口号那样,是“更快、更高、更强”,这显然意味着力量的对抗与搏击,折射出激烈的社会竞争。现代体育运动越来越专业化,因而对普通市民而言,体育竞赛已不是自己参与其间的运动,而已变成一种供观看的公众活动。看比赛成为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这时的竞赛也就具有“游戏”的意味。在西方,游戏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席勒甚至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注:席勒:《美育书简》第90页。)俄裔美国作曲家、音乐学家N·斯洛尼姆斯基在他编的《术语辞典》中有一个条目叫“游戏音乐”或译为“运动竞赛音乐”(Game Music),其中既包含了娱乐意义上的音乐游戏,也包含了描写真正的体育竞赛的乐典。(注:参见N·斯洛尼姆斯基:《1900年以来的音乐》1994年希尔默第五版第1134-1135页。)这些乐曲,往往体现出力与美的结合。
1912年德彪西写了舞剧音乐《游戏》,其中写了打网球,不过只是一种隐喻式的描绘:在球赛中网球弹离了草地球场,向前滚动,为一个小伙子提供了机缘,在追球的当儿追上了两个姑娘,表现了“人生就是游戏”的思想。瑞士作曲家奥涅格创作了舞剧《溜冰场》(1922)和为管弦乐队写的交响乐章《橄榄球》(1928)。捷克作曲家马蒂努(B·Martinu,1890~1959)用他的巴黎式享乐主义构成派风格写了管弦乐曲《半场》(1925),用乐器色彩描绘出观看足球赛的印象。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扑克游戏》(1936)中“打”了三局牌,演员均着扑克图案的服装,装扮成一张张扑克牌,其中一张飞牌(百搭)自信不可战胜,因为它可以变成任何点数连成同花顺。但最后飞牌搭成的黑桃同花顺被A打头的最强的一手红桃同花顺打败,裁判随后伸出大手将“牌”一一收回。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有奖竞赛》(1957)之名得自古希腊体育、音乐、诗歌比赛(Agon),用十二音作曲技法为12个舞蹈者写了12个乐章的舞曲。英国作曲家布利斯(A·Bliss,1891~1975)的舞剧《将死》(1937)描写了维也纳开局的国际象棋赛。在声乐方面,美国作曲家威廉·舒曼(W·H·Schuman,1910~ )写了“棒球歌剧”《非凡的凯西》(1953),并据此歌剧改编成“棒球康塔塔”《凯西当击手》(1976)。美国作曲家巴伯(S·Barber,1910~1981)为4个独唱者与室内乐队写了一部歌剧《一局桥牌》(1959)。意大利作曲家托萨蒂(Vieri Tosatti,1920~ )写了一部描写拳击运动的室内歌剧《拳击奖》(1953)。
当然,现代人对体育的兴趣不仅仅是娱乐或为某种冲动提供发泄的出路。都市的体育运动是一种被组织起来的事业,具有很大的群体向心力,当这种公众活动与某种精神联系在一起时,它甚至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注: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态》上海译文出版社97年版,第60页。)这也正是“运动音乐”附着的文化内涵。
显然,在深层次影响20世纪欧美音乐精神价值取向的是当代都市的文化倾向。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这一都市文化特性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这正说明,音乐文化不仅仅是由它自身的结构因素所组成,它还包括音乐创作者对其所处环境的反应,受到“工业与科技、政治和社会的倾向以及知识和哲学的氛围等等”(注:珍妮·鲍尔斯:《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的制约。也许,当21世纪形成信息化、超导化的城市,当未来海洋城市、宇宙城市的创建使陆地城市黯然失色,那时的音乐也将会呈现信息化、智能化、空间化的奇光异彩。然而,艺术的功用并非仅仅充当大千世界的一面镜子,艺术的价值在于对现时的超越。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更敢为者”、“贫乏时代的未来诗人”,就因为荷尔德林没有在一个世界失去平衡的时代里沉沦,而是用诗参与对时代的拯救。20世纪都市特性的西方音乐,是否揭示了未来的本质存在方式呢?是否展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历史”与“物质”之间的张力(注: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版,第183页。)呢?是否能引领人们步入未来呢?是否具有永久的价值呢?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时,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思索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