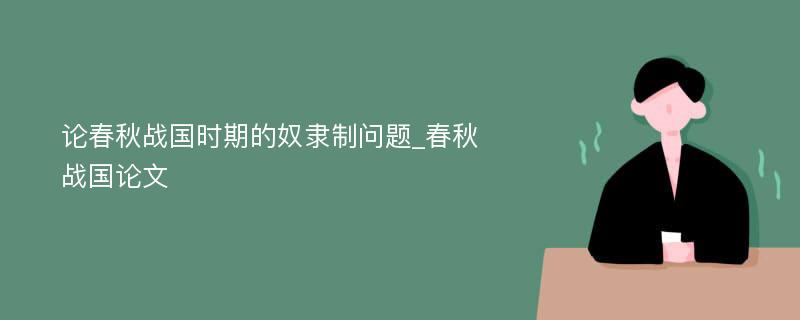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隶制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试论论文,春秋论文,战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是社会性质在由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浸透着宗法精神的奴隶制。从更大一些的范围看,奴隶制实际上存在于当时的宗族之中,如果说这是宗族奴隶制的残余,也应当是可以的。所谓宗族奴隶制,其基本特点是奴隶与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它是为我国古代宗族组织长期存在并且在社会上具有强大影响所决定的。奴隶身份方面存在的这种宗族性质,春秋时期比较明显,战国时期逐渐减弱,可是在许多方面仍然遗留有相当的影响。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但当时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封建生产关系,作为劳动者主体的、担负主要农业生产任务的还是庶人、自耕农民,不能因为奴隶制的存留而否定春秋战国时期所固有的封建社会性质。
在探讨古代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等重大问题时,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是颇受专家重视也颇多歧义的问题。我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是社会性质在由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浸透着宗法精神的奴隶制。今拟对于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为专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中,有各种不同名目、不同等级的奴隶。春秋后期,楚灵王建成章华宫的时候,曾经将逃亡的奴隶纳入其中服役,楚国担任芋尹的无宇,其“阍人”也逃奔章华宫,无宇到宫中将其抓获,章华宫的管理者不让无宇将“阍人”带走,无宇便振振有词地向楚灵王讲了一番道理:
《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左传》昭公七年)
在无宇所列的社会等级中,隶、僚、仆、台都是奴隶,专司放牧马牛的“圉”和“牧”也是奴隶。无宇举出周文王所制定的“有亡荒阅”的法令证明自己到章华宫中抓人的合理性,表明当时楚国依然有与此相类似的规定。所谓“有亡荒阅”,意谓有逃亡的奴隶,便大规模地搜索以将其抓获。“阍人”是守门之人,常以奴仆为之。无宇的阍人说是逃奔到王宫之中,依照规定也可以入宫抓获。无宇的这一段话十分有名,它的确反映了春秋时期奴录的多种名目和其间的等级。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的根本特点并不在乎此,而在于其间蕴含的宗族性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是社会性质在由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浸透着宗法精神的奴隶制。吴荣曾先生精辟地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家长奴隶制残余”[①a]。在这个论断的启发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存在于家庭里面的奴隶残余,从更大一些的范围看,实际上存在于当时的宗族之中,如果说这是宗族奴隶制的残余,也应当是可以的。所谓宗族奴隶制,其基本特点是奴隶与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它是为我国古代宗族组织长期存在并且在社会上具有强大影响所决定的。在春秋时期宗族组织盛行的时候,据一些文献记载,许多奴隶也属于宗族组织,并且其身份往往具有两面性,既是宗族成员,又是奴隶。春秋时人所谓“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士并不以一个普通贵族或家长的面貌出现,而是依靠宗族组织并且以宗子的身份来隶使子弟的。这些“子弟”作为宗族成员是无可怀疑的,不然的话不会称为“子弟”,但是其被隶使,则使其身份中又有了奴隶的性质。
春秋时期的“臣”往往具有宗族奴隶的性质。“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其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作为高级贵族的公卿贵族是君主的大臣,而作为宗族或家庭中的奴仆也常常称为臣。所以在谈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就春秋时期的情况而言,许多宗族奴隶是以臣相称的。春秋中期,鲁国三桓“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将鲁国的三军划归三桓分别掌管,“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襄公十一年)。季氏下属能够以自己的邑提供军赋者,应当多为士一级的贵族。孟氏让自己属下的贵族和平民的子弟入于军籍,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的奴隶身份。叔孙氏则不改变其属下的私乘的人的身份,仍属奴隶[②a]。可以推测,三桓属下的军乘之人原先尽皆具有本宗族的奴隶身份,只是在“三分公室”以后,才多少有所改变。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晋卿范献子聘鲁的时候,鲁国举行射礼,“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鼓父、党叔为一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些属于鲁国公室或私家的“臣”,有射艺,能够登大雅之堂,其身份显然具有双重性质,可以说与“三分公室”时孟氏的“半为臣”相近,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宗族组织之中,特别是称为“私臣”者,更是如此。鲁襄公十年(前563年)“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在攻城时“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坠),则又县(悬)之,苏而复上者三”(《左传》襄公十年),这是关于当时奴隶服役的一个宝贵记载。鲁国孟孙氏的家臣秦堇父拉着载有军需器物的车子前往服役的地点,他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勇敢。这是鲁国“三分公室”以前的事情,秦堇父的身份还是完全的“臣”。春秋前期,晋国的师服说:“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所谓“隶子弟”,即作为宗子的士隶役本宗族的子弟。这些“隶”,既是作为“子弟”的宗族成员,又有供宗子的役使的不自由的奴隶身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奴隶的多数应当属于这种情况。有些本非自己宗族的臣,也要通过“委质”的方式来效忠于宗族,即春秋时人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国语·晋语》九)。虽然,“委质”者非必为奴隶,并且有许多属于贵族中人,但是作为臣的奴隶要“委质”和效忠于主人,则无可疑。
奴隶身份方面存在的这种宗族性质,春秋时期比较明显,战国时期逐渐减弱,可是在许多方面仍然遗留有相当的影响。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对于诽谤其亲的行为十分痛恨。他说:“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韩非子·忠孝》)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孝的言论。那位能够“夜寝早起,强力生财”的某子之亲,很像是一位宗族的族长,其子孙臣妾都是其宗族之人,如果在这里姑且不谈谁养活了谁的问题,不去考究韩非子所谓的族长“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否合乎事实,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族长与臣妾实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云梦秦简载有一条《魏奔命律》谓:“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赘婿是社会上具有奴隶身份的一种人,实为卖给人家为奴之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赎出,过了一定期限遂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奴婢,《汉书·贾谊传》说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即此。依照《魏奔命律》所言,如果将赘婿杀掉,就会连累其“宗族昆弟”,可见这种奴隶存在于宗族之中。云梦秦简所载《魏户律》谓:“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世之后,欲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乃(仍)孙。”这些赘婿虽然依照魏国的法律不授于其田地和房屋,但是他们可以历代绵延,甚至子孙可以做官,可见他们有自己的产业。从《魏奔命律》所载“宗族昆弟”之说看,这些子孙做官的赘婿应当都有自己的宗族存在,所以在社会上可以产生一定影响。
二
与多数奴隶所具有的宗族性质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奴隶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私有财产。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刑法中有关于将犯罪的平民罚没为官奴婢的规定。湖北江陵张家山编号为M247号墓所出土的《奏谳书》载有鲁国的法律,谓“异时鲁法:盗一钱到廿,罚金二两;过百到二百,为白徒;过二百到千,完为倡。……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①b]。在鲁国的社会上,被官府判决为“白徒”者,其身份类似于战国时期秦律所谓的“隶臣妾”,即一种官府奴婢[①c]。被判处为“倡”者,则类于战国时期称为“城旦”的刑徒。被罚为官奴婢者,其本人身份虽然为奴隶,可是其家人依然是自由民,其家产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充公罚没,从原则上讲官奴婢对于其家产依然拥有一定的权力。当时常以“室”作为计算奴隶数量的单位,如晋景公曾经“赏桓子狄臣千室”(《左传》宣公十五年),所提到的“千室”,即具有奴隶身份的狄人1000家。这1000家,虽然身份为奴隶,但却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否则不会组成家庭。春秋中期,郑卿伯有作乱被杀,子产将其“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左传》襄公三十年)。伯有的“臣”有的居住于郑国都城市场的旁边,可见也有其自己的家庭存在。春秋中期,齐国崔氏之乱的时候,搜求崔杼的尸体,“崔氏之臣曰:‘与我拱璧,吾献其枢’”(《左传》公年二十八年),最后予崔氏之臣以拱璧,果然达到了目的。这位崔氏的奴隶,显然拥有自己的财产。
云梦秦简载被罚为官府奴隶的人,有些有自己的家室。《司空律》载“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②c]。依照秦律规定,被罚为官府奴隶的人,若有妻而且其妻是更隶妾或者自由人的,要由其妻负担所用衣服。其妻所供给的衣服的费用,依照《金布律》的规定是“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③c],显然有妻者要由其妻缴纳这些钱。秦律所载对于官府奴隶的处罚常常祸及其妻子。例如有一条关于“隶臣”的规定谓:“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怜,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也。”[④c]这条规定谓监管城旦的隶臣,如果城旦有逃亡,那么除了将这个隶臣处罚为城旦以外,还要将这个隶臣的妻、子罚没为官府奴隶并出卖。如果其子年幼,就“从母为收”。什么叫“从母为收”呢?那就是虽然人肯定要出卖,但是其子年幼,不能与其母分离,所以不要单卖孩子的母亲,而是将孩子和其母亲一起出卖。这是“隶臣”有其家庭的一个证据。依照秦律规定,“擅杀子,黥为城旦舂”[⑤c],一般的人擅自杀子,要处以黥为城旦舂的处罚,还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⑥c],私家奴隶若擅自杀其子,则按照城旦舂的样子施以黥刑,但是不罚没为官府奴隶,而是处刑以后交付其主人管理。另有一条规定谓“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枯死,黥颜口,畀主”[⑦c],私家的奴婢笞打自己的儿子,使儿子因此患病而死,依法律要在此奴婢额上刺墨,然后将此奴婢交付其主人管理。这条规定与关于“人奴擅杀子”的规定一样,都表明奴隶有自己的子女。云梦秦简所载《魏户律》规定“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如果从反面来理解,这正说明魏国赘婿这种具有奴隶身份的人,有许多是立户而被授于田地和房屋的。可以推测,在宗族组织比较盛行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家庭和私有财产一般都当在宗族保护伞之下,实际上是宗法封建制的一种补充。
三
在社会结构正在迅速地发生重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复杂情况一样,当时的奴隶制也是十分复杂的。当时私人所拥有的奴隶,存在着宗族成员身份和奴隶身份一身而二任的情况,其中有些地位较高的奴隶,其宗族成员身份的比重较强;反之,地位较低的奴隶,其奴隶身份的比重就强些,甚至完全失去了宗族成员的身份,而只存有其奴隶身份。如果说社会地位很低的奴隶与宗族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是属于某一宗族的奴隶,而其本身并不能算作宗族成员。
在浸透着宗法精神的各种名目的奴隶中,“圉”和“妾”的地位比较低下。晋公子夷吾生一男一女,卜人谓“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依照当时取名以厌不祥的惯例,应当给孩子起最差的名字,“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左传》僖公十七年),是可为证。直到春秋后期还有以“圉臣”(《左传》哀公三年)为谦称者,可见圉的地位确实低下。晋公子重耳在齐国时,其随从在桑树下密谋离齐时被“蚕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听到,她报告以后却被杀掉以灭口。从事蚕桑之事的“妾”的性命,在贵族眼中直如草芥一样。除了采桑以外,妾还从事其它劳作,史载鲁国大夫藏文仲的妾即“织蒲”(《左传》文公二年)以贩卖。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晋伐郑,“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国语·晋语》七),韦注引或说谓“女工,有伎巧者也”,说或近是,“女工妾”即有奴隶自份而又擅长女工——如刺绣、缝制之类——的“妾”[①d]。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妾被贵族作为玩物对待,所以屡有“贱妾”(《左传》宣公三年)、“嬖妾”(《左传》宣公十五年)之称。有些“妾”可以得到贵族的宠幸,例如卫献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左传》襄公十四年),就是一例。有些被贵族宠幸的“妾”,凭借权势作威作福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有的,齐国就有“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左传》昭公二十年)的现象。齐襄公的时候,“陈娄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国语·齐语》),给高级贵族直接服务的妾,其生活是相当优越的。有的妾还有机会被立为嫡妻,楚国的司马子期就曾经“欲以妾为内子”(《国语·楚语》上)。然而,就总的情况看,妾的社会地位不高仍可以肯定。晋国的魏武子病笃时遗命将其“嬖妾”“必以为殉”(《左传》宣公十五年)。作为贵族玩物的“妾”,虽然生活比较优裕,甚至可以“衣帛”[②d],但其社会地位不高,其性命之轻贱,于其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殉葬之事可以得见。战国中期,孟尝君赏赐某人以“良马固车二乘”、“千石之粟”、“五百金”、“宫人之美妾二十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妾的地位实与良车固车之类没有多大区别。妾在战国时期又称为“婢妾”(《韩非子·亡征》),可见有些妾已经与奴婢相同。齐威王骂人之语谓“而母婢也”(《战国策·赵策》三),“婢”在社会上应当是相当轻贱者。
奴隶买卖的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依然存在,社会上除了贵族以外,一般的平民也有不少拥有臣妾。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奴隶的买卖要受到宗法精神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志》书上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左传》昭公元年),《礼记·坊记》篇也说“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可见,身份地位低下的妾可以被买卖,但要问清楚其姓氏,如果不知,也要通过占卜来确定,以免与宗法原则抵牾。战国中期,术士陈轸说:“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战国策·秦策》一)可见同闾巷之人对于仆妾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良仆妾”才会顺利售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篇载: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买妾。”在向神灵的祈祷之辞里面,卫人之妻仅以“百束布”为希望,不敢奢望多有财富,原因在于如果财富稍多,其夫便要买妾。卫国的这对夫妻很可能是社会上一般的士甚至平民,可见买妾已是比较常见的社会现象。《庄子·则阳》篇载“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这位以卖浆者为邻的隐士,其生活条件不会太优裕,但却拥有臣妾。《庄子·渔父》篇讲到庶人的情况时谓:“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可见在战国时期社会上的庶上也有拥有“妾”者。云梦秦简载有一例“封守”爰书,仔细地列出了居住于某里的身份为士伍(爰书中称其为“甲”)的家庭人口和财产情况:“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①e]。从爰书所列该士伍的家庭人口和财产情况看,这是一个普通人家,其不动产主要是一栋房屋和十棵桑树,就是这样的人家却还拥有一臣、一妾。
奴隶的买卖不仅在普通人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普通人与官府之间进行。云梦秦简载有一个相当典型的例证:
某里士五(伍)甲缚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丙毋(无)病也。毋(无)它坐罪。”令令史某诊丙,不病。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丙中人,贾(价)若干钱[②e]。
这件题为“告臣”的爰书记载某里居住的士伍某人将其臣捆送官府,请求将其臣卖给官府,送去充当城旦。官府在依照市场价格买下这名臣之前,首先讯问各种情况,再讯问这名“臣”是否曾被其主人免除奴隶身份,还让有关人员检查这名臣是否有病,最后才让担任少内的职官及其佐助者按市场标准价格将这名臣买下。
春秋时期有以侍妾或奴婢殉葬之例,其中以楚墓较多,河南固始白狮子地1号墓殉人数量达13人之多[③e],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墓主为大夫级别的人物,其足下和南侧有5个陪葬棺,据鉴定,陪葬者均为青少年女性,年龄在14岁~24岁之间[①f]。除了这两座楚墓以外,考古发现所见殉人的春秋时期的楚墓还有湖北鄂城百子畈的3座,以及湖南浏城桥的1号墓,河南淅川下寺的2号墓等。这些都表明奴隶的社会地位在春秋时期还是很低的。70年代初期发现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②f],墓主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在主墓的顶部发现6名殉人,无葬具,分为上下两层,直接埋入填土之中。两层相距1.3米,中国有隔板,从残骸姿态看,这些人是被处死之后殉入的,也有的可能是被活埋于墓中者。在主墓周围有17个陪葬坑。这些陪葬者各有墓穴和棺椁,井然有序地埋在主人椁室周围。这些陪葬者有相当丰富的随葬品,包括仿铜礼器而制的陶器、贵重的佩饰,有的还随葬有陶俑,有两座陪葬墓还有殉人。这些陪葬者和前面所提到的殉人,大部分为20岁左右的女性,也有15~17岁者,最大者仅30岁。有些具有奴隶身份者,虽然可以近侍贵族,而且自己生活也相当优裕,但其地位依然轻贱。春秋时期晋国的骊姬将毒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左传》僖公四年)。这位“小臣”尽管有可能是近侍君主者,但在贵族看来,其生命的价值却与“犬”无甚差别。一般而言,战国时期殉人现象趋于减少,但有些地区依然有较多的存在。70年代后期江苏淮阴高庄发现战国中期墓葬[③f],其墓主为卿大夫一级的人物,墓内发现14具殉人骨骸,椁内11人,椁外3人。高庄地处苏北,历史上为东夷族活动较多的地区,大量殉人的出现或许与东夷族的习俗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大部分从事君主宫庭或贵族家庭内部的服务性劳务,如“仆人巡宫”(《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之类。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子产参加晋国召集的盟会,“命外仆速张于除”(《左传》昭公十三年),负责除地为坛的“外仆”即随从子产参加盟会的郑国主管官府奴隶的职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龁人,使者不敢往”,被派前往买酒的“仆”就是家庭中使唤的奴隶。除了家务之外,也有的私家奴隶被用于田间劳作。云梦秦简有一件“告臣”的爰书记载某人将其“臣”送诣官府的事情,原因在于其“臣”“桥(骄)悍,不田作”[④f],可见“田作”也是臣的职责。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作虽然有奴隶参加,但并不占主要地位,作为农业主力的依然是庶人。
四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私人所拥有的奴隶,具有较多的宗族奴隶性质的话,那么官府奴隶虽然多来源于宗族成员,但其被罚没为奴隶以后,则游离于宗族之外,形成颇有特色的一个社会群体。官府奴隶在春秋时期还比较少,到了战国中后期则比春秋时期大为增加,这反映了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的增强和宗族影响的减弱。
官府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战争中虏获的俘虏;二是触犯刑法者;三是官府奴隶的子女。《墨子·天志》下篇讲当时的战争,攻入敌国的时候,“民之格者,则刭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①g]。所谓“仆圉胥靡”、“舂酋”,都是官府奴隶。战国时期在频繁的战争中,许多贵族和民众“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战争使“臣妾”的数量大为增加,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事实。《吕氏春秋·精通》篇载有击磬而悲哀者,自述其悲哀的原因:“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子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其父杀人被刑杀,其母和他本人都被罚为官府奴隶,其身躯都是“公家之财”,所以没有能力出钱赎还平民身份。除了这两种来源之外,官府奴隶的子女似乎也继承了官府奴隶的身份,并且不能轻易改变,若私自改变,便要受到法律处罚。云梦秦简载有一条规定谓“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别)其子,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论可(何)也?或黥颜口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也”[②g]。依照规定,隶臣之妻在隶臣死后,若将其子从家中分出,作为非隶臣子,那么该隶臣之妻就应当被处以完刑。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一种合理的解释,便是隶臣之子其身份还是隶臣,属于官府奴隶,如果因为隶臣死去而改变了其身份,那就减少了官府奴隶数量,所以要对私自改变身份者进行较重的处罚。
战国时期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变化,特别是将平民罚没为官府奴隶,有些是由于国家干预或刑法酷烈的结果。战国时期,有些平民由于触犯刑律而被降为官府奴隶。80年代中期,内蒙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哈什拉村牛家渠发现一件战国后期秦国上郡地方所铸之戈[③g],铭文记载戈为秦昭王十五年(前292年)命令秦国上郡守向寿所监造,具体铸造者为“冶工隶臣奇”[④g]。这位名奇者为冶铸工匠,但其身份则是隶臣。作为官府奴隶的“隶臣”,其身份是不自由的,依照《汉书·刑法志》关于“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的记载,隶臣在其身份满一年之后才可以被免为庶人。这位名奇者本是一位有铸造技艺的工匠,另有戈铭载“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乘,工更长奇”,可见他在秦昭王十二年(前295年)的时候,其身份还是“更长”。秦汉时期,以轮番力役为“更”,服役者称为“更卒”。《汉书·食货志》上载“(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注谓“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其实,更卒未必只服役一月,到远处服役可能是一年为期的。《汉书·盖宽饶传》载“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注谓“更,犹今言上番也”。据十二年上郡守寿戈所载,名奇者当时还是更卒之长,故称“更长”,然而不知何种原因,在三年以后,他的身份却变成了“隶臣”。秦国徭役繁重,许多正常服役者可能被无端地变为隶臣以延长其服役期限,名奇者身份的变化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从云梦秦律里面可以看到的许多作为官府奴隶的“隶臣”、“隶妾”,其身份与一般的刑徒有所区别。刑徒是被判处服劳役的罪犯,在服役期满之后便恢复其自由身份;而“隶臣”、“隶妾”则是没有期限的官府奴隶,其身份世代相传,除非通过一定的方式免除了这种身份[①h]。“隶臣”“隶妾”的衣食一般由官府供给,有的还有自己的私有财产。社会上的官府和私家奴隶占有一定的数量,是当时社会各个等级中地位很低者。奴隶身份的免除,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经过赎免。春秋中期晋国栾氏之乱的时候,晋国官府奴隶名斐豹者就因为立有功劳而被免除奴隶身份。史载:
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盖因为犯罪而被罚没为官府奴隶者,罚没的时候写有“丹书”为证,有“丹书”在,其奴隶身份就不可更改。晋卿范宣子答应若斐豹能杀掉栾氏的勇力之臣督戎,就焚毁丹书而恢复斐豹原来的身份。可是焚毁丹书之事,必须“请于君”,得到晋国君主的批准。可见奴隶身份的赎免是相当慎重的事情。春秋末年赵简子所悬赏格中有“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一项,可见奴隶立有军功,确曾可以免除奴隶身份。云梦秦简所载一件题为“告臣”的爰书,记载官府讯问之辞,确认某人的奴隶确曾“未赏(尝)身免”[②h]。可见主人有权将自己的奴隶免去奴隶身份。鲁国曾经有可以取官府的资财赎免在其它国家为奴隶的鲁人,“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得赎人矣’”(《吕氏春秋·察微》)。这个记载反映了春秋末年国家对于赎免奴隶之事干预的增强。另有晏子赎免在晋为奴隶的齐人一事。《吕氏春秋·观世》篇载:“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赘)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吕氏春秋·观世》篇所载“齐人,累之”的累,陈奇猷先生释为“赘之假字”,谓:“累、赘乃一声之转。《释名·释疾病》:‘赘,属也。’……故今以‘累赘’为叠韵语。《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引如淳云:‘淮南俗卖子与为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此文‘文人累之’,犹言赘于齐人为奴耳,正与《晏子》云‘为人臣仆’义同。”(《吕氏春秋校释》卷二六)按,此说甚是。战国秦汉间的赘婿多有奴隶身份,所以《观世》篇所载才会有赎免之说。齐人越石父在晋国为赘婿,实际上与奴隶没有多大区别,晏子“左骖以赎之”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奴隶只与一匹马的价值相当,而只是说明赘婿只具有轻微的奴隶身份,所以一匹马即可赎免。
战国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社会上影响的减弱,国家对于私家奴隶的干涉增强,私人间的奴隶交易和对于私家奴隶的处罚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都有权进行干涉。湖北江陵张家山编号为M247号墓所出土的《奏谳书》载有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发生的一件行凶抢劫案的侦破情况,因为作案的现场发现有贾人所用的荆券,所以狱吏便“收讯人竖子及贾市者、舍人、人臣仆、仆隶臣、贵大人臣不敬德,它县来乘庸疑为盗贼者”[①i]。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属于私家奴隶,他们因为到市场上交易而被怀疑作案。在一般情况下,春秋战国时期主人对于自己拥有奴隶的生杀予夺之权表现得不太明显,对于奴隶的处置似乎要经过官府批准才能进行。云梦秦简里面一件题为“黥妾”的爰书载:
某里公士甲缚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也。乙使甲曰:‘丙悍,谒黥劓丙。’”讯丙,辞曰:“乙妾也,毋(无)它坐。”丞某告某乡主: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甲诣乙妾丙,曰:“乙令曰谒黥劓丙。”其问如言不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或覆问毋(无)有,以书言[②i]。有五大夫爵位的某人,命令自己的私家之吏,将自己的一名妾送到官府,请求官府将其处以黥刑,官府不仅要进行讯问,而且要由县丞调查妾的姓名、身份、籍贯,以及这名妾是否犯过罪等,由五大夫所在乡的负责人将情况向县汇报,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这个记载表明,对于私家奴隶的处置,官府有权干涉并且作出决定。
综上所述,可以说春秋时期社会还存留着宗族性质很强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在当时的社会上只是一种残余形态,只是宗法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补充。到了战国中后期,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耕农大量涌现,奴隶制的宗族性质也趋于减弱,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私家奴隶的干预强化。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存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并且无论是官府奴隶抑或是私家奴隶,都从事着比较广泛的劳作事务,但就整体情况看,当时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却是封建生产关系,作为劳动者主体的、担负主要农业生产任务的还是庶人、自耕农民,不能因为奴隶制的存留而否定春秋战国时期所固有的封建社会性质。
注释:
①a 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9页。
②a 《左传》昭公五年亦提及鲁国“三分公室”之事,谓“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又申述了其义。关于鲁国“三分公室”的具体内容,前人多有歧义。杨伯峻先生说:“季氏于其属邑奴隶尽释为自由民。”孟孙氏“其入军籍皆年轻力壮,或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弟,而皆以奴隶待之,其父兄则为自由民”。“叔孙氏则仍实行奴隶制,凡其私乘,其皆奴隶,今补入其军中者皆奴隶。”(《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87页)。杨先生的说法很有可取之处,然而释“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为自由民子弟为奴隶而其父兄为自由民,似乎不如释为其军乘之人具有奴隶和自由民双重身份较妥。另外,季氏只是区分为“无征”与“倍征”,对于私乘所属者的奴隶身份并没有改变,似不可以说季氏将奴隶“尽释为自由民”。
①b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①c 关于“白徒”的身份,专家曾经指出文献所载者即“军中未经训练装备的徒兵”,这与《奏谳书》所载鲁国的“白徒”是不相合的(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下),《文物》1995年第3期)。《管子·乘马》篇载:“白徒三十人奉车两(辆)”;《管子·七法》篇载:“以教卒练士击殴众白徒”,尹注“白徒,谓不练之卒,无武艺”。是皆以“白徒”为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卒。但是古人还有一种说法,谓“白徒”为穿白衣者,《吕氏春秋·决胜》篇载:“厮舆白徒”,高注“厮,役。舆,众,白衣之徒”。盖在春秋时期,鲁国确曾以“白徒”为刑徒之名,这种刑徒以穿白衣为标识。后世渐以“白徒”为白丁,其义已非其溯。
②c③c④c⑤c⑥c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第67页,第201页,第181页,第183页。
⑦c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条简文里面的“枯”字,原为从肉从古之字,读为枯,今迳写作枯。第183页。
①d 关于郑国赂晋之事,《左传》襄公十一年仅提到“女乐二八”,与《国语》所载稍异。《国语·晋语》八韦注将“女工妾”分为三类人,谓“女,美女也。工,乐师也。……妾,给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按,韦注此说疑误。“女工妾”即为“妾”的女工,因为郑国赠送者还有“女乐二八”,若将“女工妾”分为三类人,便与“女乐”重复,故而此释不可取。
②d 《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当时称赞鲁国季孙氏的懿德善行之一是“妾不衣帛”。季文子死的时候,“无衣帛之妾”(《左传》襄公五年)亦是其德操美善之证。墨子主张国家的君主应当节俭,“婢妾不衣帛”(《墨子·七患》)就是其中的一项。就社会一般情况看,贵族嬖妾“衣帛”应当是通例,所以季孙之举才被视为非同寻常。
①e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9页。
②e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
③e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白狮子地1号和2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①f 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
②f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③f 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④f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
①g 《墨子·天志》下篇所载“刭杀”,原文作“刭拔”,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疑‘刭杀’之误”,并引毕沅说谓劲,即刭。今从之而迳写作“刭杀”。
②g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5页。
③g 陈平、杨震:《内蒙伊盟新出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铭考》,《考古》1990年第6期。
④g 十五年上郡守寿戈和十二年上郡守寿戈,两戈铭文中的“奇”字,其右原来均有“牙”字偏旁,今为方便计而写作奇。
①h 关于“隶臣”“隶妾”身份的豁免,《云梦秦律·仓律》载“隶臣欲以人丁龄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龄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隶臣。女子操文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两名壮年男子可以赎免一名隶臣的身份,从事文绣女红的隶妾则不准赎免。隶臣的原籍在边县的,赎免之后要迁往边县。这是用人顶替而赎免的办法。《云梦秦律·军爵律》载“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这是以军爵赎免的办法。《云梦秦律·司空律》载“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内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如果百姓有其毋或亲姐妹为隶妾,基本人没有流放罪而自愿戌边五年(这五年不算作其应当服役的时间),可以赎免隶妾一人为庶人。这是以戌边服役而赎免的办法。这些规定表明,秦国官府对于“隶臣”“隶妾”的身份控制甚严,赎免后官府所控制的“隶臣”“隶妾”的数量并没有怎么减少,官府所控制的戌边者还会增多。这反映了秦国官府直接控制民力的措施是相当严格的。
②h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
①i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②i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