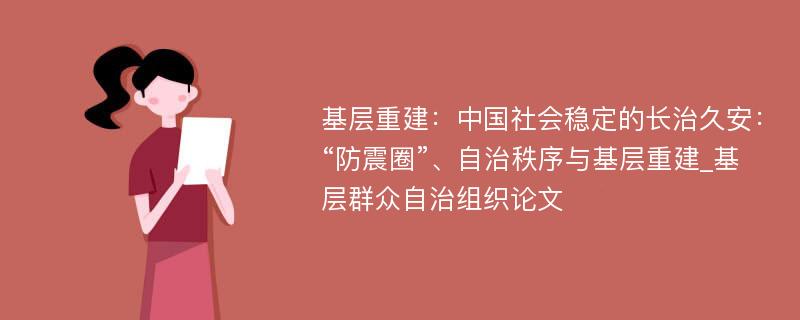
基层重建:中国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防震圈”、自治秩序与基层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长久之计论文,社会稳定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历史与现实,无论对于国家治理还是个人日常生活来说,基层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基层稳,则人心稳、社会稳、国家稳。中国的改革,起于基层,而基层亦受到改革开放最为猛烈的冲击。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型与阵痛,目前正处在失序和重建的过程中。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不进则退的深水区。在未来的社会政治改革中,基层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它事关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上层改革暂时难以启动的情况下,基层重建也许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继续深入的一个突破口。
今年3月,日本发生千年一遇的大地震。这次大地震有两点给世人以深刻印象:一是大地震没有造成楼房的大坍塌;二是大地震没有引起社会的大恐慌。前者得力于日本建筑物下面有一层橡胶垫圈,可以防震,在地震时起缓冲作用。后者得力于国民在长期自治秩序下形成的有序心理。强固基础,着力基层,是日本大地震给人的重要启示,也是我国现阶段要高度重视的基层重建的重要内容。
在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的重要基础就是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有一个“乡绅阶层”。在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看来,这一阶层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一植根于基层的阶层,实际上是国家统治的缓冲地带。政府通过他们,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有效治理社会的目的。大量的社会管理依靠的是以乡绅阶层为主导的社会自我管理,并由此建构起一套自治秩序。近代以来的革命和乡村改造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乡绅阶层的消失,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社会,甚至“进村入户”。人民公社时期达到极致。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乡政村治”,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具有鲜明的政府推动性,国家权力仍然顽强地向下延伸和无处不在地渗透,即使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具有突出的行政主导色彩。
现代化就是国家权力不断向下延伸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权力的全覆盖和强控制,社会自治的空间极小,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取决于政府;一是在国家权力延伸的过程中使社会保留相当的自治空间,除了服从政府意志外,人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服从内生和内在的自治秩序。我国是通过革命和改造建构起一个新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延伸更多的是前者。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迅速建构起一个新社会,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面对面”的直接权力关系。政府面对民众直接施政,民众面对政府直接受治。在这种格局下,政府需要不断地给民众以“好处”,才能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巩固执政基础。这正是学界谈论较多的“政绩合法性”。但是,我国30多年的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并没有使社会获得理想中的平稳。我国现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除了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以外,我国政府与民众“面对面”的直接权力关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矛盾正是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造成的,如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征地拆迁。与此同时,大量的社会矛盾缺乏一个过渡层或者中间层加以消化,而直接诉诸政府,如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在“瓮安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基层自治组织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缓冲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国经济可以无需政府介入而自运行。政府的重要职能除了经济规划以外,就是加强社会建设,使社会成为一个有序管理的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以往政府强力主导甚至直接控制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政府主导下高度自治的社会,是一个需要重建的社会。
重建社会需要从基层着力。这是因为,基层是民众的生活领域和世界,与民众的利益和幸福生活密切相关。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其后果是民众的生活改善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不同步,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为政府所掌控。政府层级越高,掌握的资源和财富愈多。这正是人们纷纷向首都和省城集中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愈是层级低的地方,特别是基层,其掌握的资源和财富愈少。这种资源和财富层级不均和过分集中的格局,使得地方和基层政府愈加看重经济发展而不是改善民生,甚至以牺牲民生为代价发展经济。如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大量发生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所以,从基层着力重建社会,首先需要在资源和财富分配上更多向基层供给。基层财力不足,必然造成执政基础不牢。国家“十二五”规划将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也有一个“调结构”的问题。这就是改革现行的财政税收结构,让更多的财力留在基层、流向基层,以惠及民生、恩及民众。如果基层组织连一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连日常开支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去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地带”呢?
基层重建,要着力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复归和功能复位。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大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际上是政府的“一条腿”,其主要功能是完成自上而下的政府任务。随着税费改革,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任务压力有所减轻。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大政府”理念并没有消失。在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建设的进程中,政府再次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新农村建设只见“政府主导”,未见“农民主体”。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政府建设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功能被替代,甚至被取代。政府虽然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基层,但如果由政府包办,就有可能进一步弱化基层群众自治能力。事实上,政府包办不了,也包办不好基层社会的所有事务。一旦政府在某一事上未满足民众的期待,就很容易发生因为信任和信用而引起的“危机”。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民众“疯狂抢盐”事件。
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功能,还需要制度创新。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四大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制度原有的基础是社会不流动,不同的人群在各自的村落区域里自我管理。而现在的制度基础却是一个流动性社会。大量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村民自治的主体“消失”了。以往少数民族群体居住生活在自己的区域,与其他民族人群是“背靠背”,相安无事。如今随着人口的流动,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处于“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之中,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了。而流入地的自治组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却处于制度“真空”之中。流动性带来的是“秩序空间”的转换。当流动人口缺乏自治组织的依托和归属时,就会陷于无序之中。现阶段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如何建构一个适应流动性社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基层制度创新的重要任务。
在基层重建中,还需要推动社会组织的发育。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毕竟具有公共管理功能,其自治作用相对有限。改革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的利益性愈来愈强,而组织化程度愈来愈低。大量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是以个体而不是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政府面对的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除了“交易成本”高昂以外,还蕴含着相当大的社会风险。无组织的个体是极其软弱的,政府可以借助公共权力随意征地拆迁;无组织的个体同时又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很可能以生命为代价表达其诉求,如“自焚”、“跳楼”、暴力对抗等。20世纪以来的革命和改造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农民组织,政府不放心;政府组织,农民不安心。当今要建构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社会组织建设,重构政府与民众的组织关系。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组织,让民众安心;社会组织依法组织民众和自我管理,让政府放心。在社会组织建设中,要注意发挥组织精英的作用。他们生活于基层或者民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要引导他们在自治活动中服务于法治秩序。这些人有可能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乡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扮演起“中间人”的缓冲作用。
标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