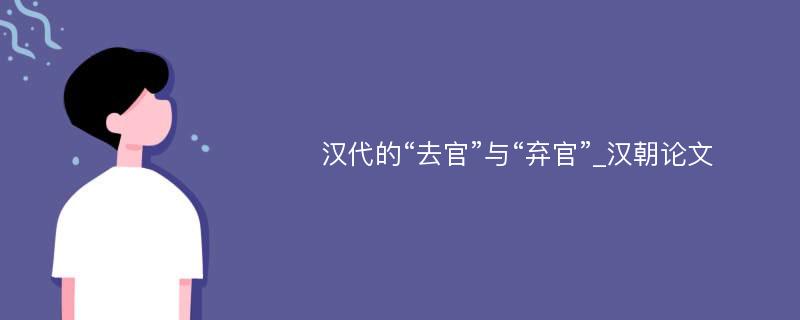
汉代的“去官”与“弃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弃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的“去官”是法律许可的一种退免方式,“弃官”则是一种法外行为。“去官”不同于国家的强制罢免,也与正常的休吏制度有别;“弃官”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习惯法倾向,它出现于春秋战国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是士人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产物,秦汉专制君主制建立后,它又蜕变为各级官吏沽名钓誉、逃避罪责的一种手段。我们探讨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不仅有助于把汉代人事管理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还可加深对古代政府官员习惯法特权的危害性的认识。
一
去官与弃官的“去”与“弃”,在秦汉法律用语中含义基本相同。如婚姻法中“出妻”之“出”,为两汉以后的法律用语,秦简中称“弃”,《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引律文曰:“弃妻不书,赀二甲”;文献中称“去”,《大戴礼记·本命》称“妇有七去”。用字不同,取义一也。
“去”与“弃”在汉代表示官吏主动解职时,用意大体一致,但由于“去”与“弃”的具体行为在性质上不同,因而使用时又存在明显差别。一般而言,表示因病、因丧而主动辞职称“去官”;表示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逃避罪责而自行放弃官职称“弃官”。这种区别在西汉史籍的行文中尚不明显,而在东汉史籍的笔法中已十分严格。
“去官”的特点即自免。官吏因种种原因主动辞职,一般需要得到朝廷批准,如乐恢为尚书仆射,以窦氏专权,遂称疾乞骸骨,如此者再,“诏听上印绶,乃归乡里”(注:《后汉书·乐恢列传》。)。西汉初年以秦法为治,官吏法禁尚严,即使意有不合,亦不得擅自去官。秦简中虽无“去官”、“弃官”之名,但律文严禁官吏未经许可而擅离职守,擅自离开岗位,称“去署”或“窦署”(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要追究法律责任。汉代沿袭此制,“去署”之名常见于汉简,如:
迫有行塞者,未敢去署。(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95.4A;3.28,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吏毋得离署(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95.4A;3.28,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违者往往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简文有:
隧长侯仓、候长樊隆皆私去署,诚教敕吏,毋状,罪当死,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注:《居延新简》简424,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从文献记载来看,汉初亦无自解印绶付吏而去的事例,意有不合,也要托故辞职。如吕后欲王诸吕,陆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注:《汉书·陆贾传》。);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枚乘因不乐郡吏,遂“以病去官”(注:《汉书·枚乘传》。)。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官吏主动解职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如自解印绶而去便属违法,这同擅离职守罪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西汉虽无具体事例可证,但求之东汉史事,仍有线索可寻。如杨伦为清河王傅,会安帝崩,“伦辄弃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注:《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可见官吏专擅去职,即使在崇尚名节的东汉时代,国家仍可依律予以制裁。
“弃官”之名始见于王莽篡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学的独尊,儒家思想成为辅助官吏法律规范官吏思想与行为的主要价值取向,士人风尚为之一变,由当初的任侠渐趋守文,所谓“自武帝以后,崇尚经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守文之徒,盛于时矣”(注:《后汉书·党锢列传》。)。与此同时,随着“以经治国”路线的深入贯彻,国家对士人的仕与不仕,法禁渐宽,儒家提倡的“从道不从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等思想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也不断为社会所认同。昭帝时,魏相为河南太守,所属洛阳武库令因父亲车千秋死,“而(魏)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注:《汉书·魏相传》。)千秋子的“自免去”显然属于自解印绶,没有得到魏相的同意,魏相除了发点牢骚,别无奈何。元帝时,萧育(望之子)为茂陵令,考课第六,却为殿最的漆令求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并在罢府后召萧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萧育径自出曹,按佩剑对赶来劝阻的书佐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师古注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须召我诣曹乎?”(注:《汉书·萧望之传》。)这段对白一语道破了汉代官吏可以任意“自免”而去的奥秘,那就是披挂印绶则为官,解脱印绶则为民,对一白衣男子,天子也不能屈。如汉成帝与成公的一段对话就形象地表明了这个道理,史载成帝对隐士成公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注:皇甫谧:《高士传》卷中。)成帝一时被驳得无言以对。应当说,千秋之子、萧育的自免、欲自免,尽管仍称“去官”,但已实开汉末“弃官”之渐。
王莽代汉,从深层文化底蕴言之,得益于西汉儒生主要是把通经作为汲汲求利的途径,而没有把孔孟之道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价值选择,正如顾炎武指出的那样:“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注:《日知录·两汉风俗》。)但王莽禅汉,毕竟与孔子的“正名”主张格格不入,也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去甚远,因此仍然引起一些官僚士人的公开反抗和非暴力不合作斗争。以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来说,许多气节之士纷纷“弃官”,走上隐逸之旅。如谯玄于平帝元始四年,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会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美阳令王皓、郎官王嘉以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沮阳令刘茂也愤然“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注:《后汉书·独行列传》。);等等。正是,“汉室中微,王莽篡汉,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注:《后汉书·逸民列传》。)此为汉世官吏弃官抗争时政之第一次高峰,撇开封建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它无疑表现了士人群体大义凛然的精神和不向强权低头的共同心态。
按范晔的说法,“弃官”的特征就是自解印绶,毁服去冠,对当政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此风一开,而光武又刻意“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注:《日知录·两汉风俗》。),以至“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注:《后汉书·党锢列传》。)。
二
从现存汉代律文及相关事例来看,“去官”是退免制度许可的一种主动辞职形式,“弃官”则是一种自行解职的法外行为。去官不同于休吏,弃官也不同于隐逸。依据官吏去官与弃官的动机、目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之大体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为讨论起见,兹分论如次:
(一)以公事去官。以公事去官在《隶释》所载碑文中常见,亦称“以公去官”(见《车骑将军冯绲碑》)。去官的具体原因不明,是犯有“私罪”被免官,而在碑铭中以“公事”二字掩恶扬善;还是因种种“公罪”被迫去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今已很难分辨清楚。但根据现今尚能索骥到的几条记载分析,似乎因“公罪”被迫辞职的可能性更大。如鲁峻为九江太守,行循吏之道,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寻“以公事去官”(注:见《隶释·司隶校尉鲁峻碑》。);虞诩在顺帝永和初,“迁尚书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复征之,会卒”(注:《后汉书·虞诩列传》。);冯绲“迁犍为武阳令,诛疾强豪,以公去官”等等。上述诸公在以“公事”去官前的行政,或为循吏,或为能臣,行文但云“去官”而不书“免”、“策免”、“下狱”,显然不是因为“私罪”被罢官,否则朝廷不会“思其忠”而复征之。如“公事”罪重,则称“坐事免”、“公事免”,可证以“公事”去官所犯过失尚构不成被免官的条件,而由当事者本人主动提出辞职。
(二)以病去官。汉代休吏制度有病休的规定,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注:一说为百日,见《风俗通义·过誉篇》、《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汉书音义》。),否则即行免官。官吏因病请假,在己称“告”或“取告”,在官称“予(与)告”,已经休假称“休告”。居延汉简中有对军官和士卒的病休事宜进行具体管理所使用的帐簿,分别称为《吏病及视事书卷》和《病卒名籍》,从有关病休与视事的大量简文看,休假均在三个月以内,且病假期满要归署视事,这在简文中记录的极为详备(注:参见赵沛、 王宝萍《西汉居延边塞休吏制度》, 《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另外,对二千石以上官吏, 天子往往以“赐告”的方式特别恩准给予长期休假,或“使带印绶将官属归家养疾”,或“居官不视事”。当然,二千石官吏也有未得赐告直接依律免官的,如山阳太守朱博、京北尹隽不疑等均以“病免官”、“以病免”。依此论之,在汉代病满三月免官是通例,“赐告”则为特例。
“以病去官”(注:史载中又称“以病自退”、“移病免归”、“谢病免”、“称病去”、“辞疾而去”等等。参见黄留珠《汉代退免制度探讨》,《秦汉史论丛》第4辑。)与上述“病休”、 “病免”不同(不含因病致仕),它是官吏因病或托“病”而主动辞官的一种习惯表达方式。首先,以病去官不同于“病休”,病休指因病休假,暂时不省官事,病愈后即回原岗位视事。以病去官的“去官”指的不是带官衔临时离岗,而是辞去官职,以后欲再仕要通过察举征辟等正常选举途径重新起用。如王吉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注:《汉书·王吉传》。);张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注:《后汉书·张奂列传》。)。其次,以病去官也不同于“病免”,病免指病满三月免官,不论官吏本人主观意愿如何,都要按制度执行。以病去官指官吏因“病”主动辞职,它体现了官吏或因厌倦仕途而求退、或托“病”以自引高等不同心态,尽管也要履行合法的手续,但毕竟是官吏个人意志的实现。
(三)以丧去官。汉代休吏制度之一曰“宁”,即奔丧。从官吏申请奔丧言之,称“取宁”,从官府批准奔丧言之,称“予宁”(注:见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7 章《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丧假的法定期限自文帝遗诏提倡丧制从简之后,大体实行三十六日释服之制。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三十六日,即除服起视事。论者或谓西汉也实行过“予宁”三年的制度,根据有三:一是公孙弘为内史期间,“后母卒,服丧三年”(注:《汉书·公孙弘传》。),然传文未说明是“予宁”三年抑或“去官”行丧三年,故不能作为西汉准许大臣行丧三年的根据。二是哀帝初即位,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注:《汉书·哀帝纪》。),但此令仅适用于博士弟子,而并非在职官吏。三是《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此律的出处或许就是安帝元初年间,邓太后所下诏令,曰“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注:《后汉书·刘恺列传》。),若是,则不能印证前汉事。设若应劭所引汉律始于西汉,也指未仕之人,所以何焯才不无遗憾地说:“哀帝既许博士弟子予宁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注:《汉书·哀帝纪》王先谦补注引何焯曰。)《后汉书·刘恺传》也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此乃西汉不准已仕官吏行丧三年之明证。
东汉一朝,朝廷对大臣是否行丧三年,或许或禁。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临政,曾准许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丧三年,但建光元年安帝亲政后,认为不便而中止。桓帝永兴二年初,也听任刺史二千石行丧三年,而到延熹二年又禁,故赵翼总结说:“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注:《陔余丛考》卷一六《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唯其如此,而文帝以来三十六日释服的惯例又相沿成俗,演为汉家故事,因此才有“以丧去官”和“以丧弃官”之分别。
汉以孝治天下,大力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把孝纳入选举制度之中,在察举征辟的诸科中,“孝廉”一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孝成为国家对入仕之人基本的道德要求(注:参见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孝亲与事君从理论上说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同一性,而从政治实践上讲两者又是矛盾的。就本文讨论的行丧与否而论,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儒家一方面主张以忠制孝,另一方面又提倡为父母行丧三年,汉政府在两难的选择中,总体上讲是把事君摆在孝亲之前,而无“必当行丧之制”(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问题是,汉代选举重“孝廉”科目的结果,对社会习尚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即人们对“孝”的过分追求,孝成为一个人社会评价的重要依据,士大夫能持服三年者,身价倍增。如铫期为父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如果遇丧不奔,往往身败名裂,如元帝时陈汤“父死不奔丧”,为司隶校尉弹劾而下狱。更有甚者,人们为追逐名誉,不惜采用卑鄙手段,借以立名,如青州民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居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然其五子皆服中所生,欺世盗名之迹可见一斑。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引导下,许多官吏争相慕效,宁过无不及。他们得以实现持丧的途径有三(安帝元初三年至建光元年及恒帝永兴二年至延熹二年间,不在论列):
一为“带职”行服,即朝廷大臣自愿持服者,可上书自乞,天子如果准奏,通常免去原职,特别恩准使带闲散官衔行服,类似病休制度中的“赐告”。如太仆邓彪遭母忧乞身,诏以光禄大夫行服;越骑校尉桓郁以母忧乞身,诏听以侍中行服;太傅桓焉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等等。
二为“去官”行服,地方官及朝廷属吏无“带职”行服的殊荣,欲为亲持服者需上书辞职。从官吏主动申请言之,称“上书求归”,如金城太守霍谞、辽东太守崔寔并以母忧,上书求归葬行服;从史家客观叙事角度言之,称“去官”或“去职”。如太常丞谯玄“以弟服去职”;扬州牧鲍永“会曹母忧,去官”;闻喜令陈寔 “以朞丧去官”(注:以上均见两汉书各本传。);上虞长度尚“以从父忧去官”(注:《隶释》卷七《荆州刺史度尚碑》。)等等。从官吏“去官”行服的对象来看,当时不仅为父母、祖母(见《宋均传》)、兄(见《韦义传》)、姊(见《陈重传》)、弟(见《谯玄传》)丧去官,而且也有为伯父(见《戴封传》)、伯母、叔父,从兄(注:见《隶释》卷一六《北海相景君碑阴》洪氏跋。)解官的。总体上讲,官吏“合法”去官行服的对象基本以“五服”亲属为准,如遇“齐衰三月”、“缌麻”之丧则“取宁”即可,无需“去官”。
去官行丧之风,自汉安帝以后愈演愈烈,致使各级封建官署往往因之严重减员,“缺动百数”。这不仅极大地影响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而且“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故左雄曾建议:“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此议是想通过立法严厉限制官吏因丧去官的范围(包括因丧或其他理由“弃官”),但因宦官从中抵制,“终不能用”(注:《后汉书·左雄列传》。)。
三为“弃官”行服,即不经许可就自解印绶而去。东汉时代私学昌盛,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师生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恩义”联系。同时,察举征辟之选至东汉中后期不重才学唯重族望门第的结果,也使举主、府主与门生、故吏之间的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种条件下,师长、举主去世后,门生、故吏往往也要奔丧成服。但门生、故吏为师长、举主服丧,既不合于“五服”从而不能“取宁”,又不具备申请“去官”的“合法”理由,所以只能“弃官”。如延笃、孔昱“以师丧弃官”,傅燮为举主,桓典、桓鸾为郡将“弃官”竟服(注:以上均见两汉书各本传。),等等。由于汉代“本未有不许行丧之令”(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所以一般情况下也不因此而罪之。
(四)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而“弃官”。汉代的“弃官”最早源于隐。隐与仕相对,即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与当权的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高敏先生在《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一文中,曾把古代隐士阶层区分为五种类型:一曰抗议型隐士,或曰不合作型隐士;二曰淡泊型隐士;三曰老庄型隐士;四曰清高型隐士;五曰虚伪型隐士(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而隐士实现隐逸的途径则有二条,一是终生不仕,不慕功名利禄,无意于升官发财,二是仕而后隐或以隐为诱饵,“假岩穴以钓名”。仕而后隐或假隐的表现形式当时主要就是弃官。如前所述,王莽篡汉,引起许多士人“弃官”归隐山林,以避王莽政权的征辟。此举深得刘秀称誉,东汉初,太原周党被征召,表示不欲仕宦,“愿守所志”,博士范升上奏诋毁周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其“不以礼屈,伏而不谒”的行为乃“大不敬”之罪。刘秀下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注:《后汉书·逸民列传》。)这个诏书实际上肯定了士人“隐”的权力,即政府的权力不得干涉“不宾之士”的不合作,而士人政治自由权利的确立,其外延顺理成章扩大为官吏的“弃官”也被确定为权利,被国家习惯上认可为一种“合法”行为。
我们讨论的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而“弃官”,自然不局限于隐。一般而言,由“弃官”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大都发生在朝政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它使一些人在无法直接抗争的情形下,转而采取消极遁世的态度,弃官退隐。如新莽时期,大批士人“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江河日下,许多士人在严酷的现实斗争面前,被迫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注:《后汉书·逸民列传》。)。正如司马光所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注:《资治通鉴》卷五一。)
由此弃官的另一种情况是抗议直接上司的“无道”。或因上司轻慢无礼,不能礼贤下士,有损于士人的名誉,侵害了士人的应有权利等。如前引萧育的“欲去官”,即因当众为扶风所辱;另据《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为河南令,“以职事为府君所责,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桥玄为洛阳左尉,而梁不疑为河南尹,“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耻为所辱,弃官还乡里”(注:《后汉书·桥玄列传》。);范滂为光禄勋主事,以光禄勋陈蕃不能礼遇,“遂投版弃官而去”。或因上司贪赃、受贿,而“士子羞与为伍”,如宗慈为脩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注:《后汉书·党锢列传》。);陈寔为太丘长,“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注:《后汉书·陈寔列传》。)。这种形式的弃官显然不是把“隐”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终归宿,而是以弃官为抗争手段,借以在舆论上抨击时政,贬抑邪恶。应当说,不论其弃官的主观动机如何,都是对士人人格独立和政治自由权力的维护,而此种权力的确立本身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些“抗愤而不顾”的士人尽管抗争的手段是消极的,但他们“大都具有不为富贵所淫和不为威武所屈的傲骨,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品德。他们往往鄙视权贵,反对暴政;仇恨贪鄙,清廉自律”(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 期。)。因此,在社会风气败坏,儒家道德沦丧的情况下,也有益于激扬正气,荡涤污浊。
(五)为逃避罪责而弃官。弃官既然被认定为习惯上的“合法”,那它就不会停留在归隐或抗争等动机和目的之上,大量事实说明,这种由隐派生出的“弃官”形式,在汉代主要蜕变为官吏逃避罪责的一种“权利”。即官吏有罪借故去官特别是弃官,可以不受法律追究(注:唐宋法律对前代官吏“在官犯罪,去官勿论”在罪行属性上作了明确限定,《唐律疏议·名例律》有“去官法”,规定“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宋刑统·名例律》因之。),而且不影响日后重新仕官。官吏的这种“权利”虽不似“上请”、“爵减”、“赎”等特权有律文可征,但西汉成帝时左冯翊薛宣对管内高陵令杨湛、栎阳令谢游的处理方式仍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依据。《薛宣传》载:杨湛、谢游“皆贪猾不逊”,薛宣暗中查访,具得其“罪臧”,以杨湛“有改节敬宣之效,乃手自牒书,条其奸臧封与湛曰:‘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即无其事,复封还记,得为君分明之。’(杨)湛自知罪臧皆应记……即时解印绶付吏”。而谢游自以大儒有名,轻慢薛宣,“宣独移书显责之曰:‘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谪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镌令……令详思之,方调守’”。谢游“亦解印绶去”。
这段记载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属官有罪,长官不加考案,当时竟传为美谈。请注意,这段文字是作为薛宣“良二千石”的政绩记录下来的。那么,薛宣的作法是否有法可依呢?否。汉律有“见知故纵”之法,明文规定:“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注:《晋书·刑法志》。)嗣后,桓帝建和元年,“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注:《后汉书·孝桓帝纪》。)。前引杨湛所犯“臧罪”,明言“疑为主守盗”,“又念十金法重”,而汉法主守盗十金是要以“弃市”论处的(注:《汉书·陈万年传》如淳注。);文中所列谢游的三条罪状,虽然不能与现存汉律律条一一对号入座,但亦属“擅兴徭役”、“恐猲受财”、“平价坐赃”的范围,数罪并罚,恐怕就不是仅仅免官的问题了。然而薛宣仅仅令其“弃官”,其所犯“罪臧”就一笔勾销了。依据安在?原来它源于当时的一种政风。宣帝时,丙吉为丞相,“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即“长给休假,令其去职也”。丙吉不案验属吏的“罪臧”,亦属失职,却美其名曰“吾窃陋焉”,于是“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注:《汉书·丙吉传》并师古注。)。上行下效,由此形成一代政风,薛宣之举又何“罪”之有?
其次,官吏“弃官”不仅可以逃罪,而且不影响日后的仕途,正如薛宣在牒书中对杨湛所说:“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换句话说,官吏因罪“弃官”,在法律程序上等于代替了行政处罚,这不仅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还可以为以后的乡举里选在舆论上搭就跳板。如西汉一代名儒戴圣任九江太守期间,“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何武迁扬州刺史,“使从事廉得其罪”,戴圣恐为所举劾,遂“自免”(注:《汉书·何武传》。),寻即征为博士。此例一开,遂相沿成俗,演及东汉,“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不仅舍生取义得名,弃官抗争、归隐、假隐、奔丧得名,而且弃官逃罪同样可以欺世盗名,恰如左雄揭示的那样,“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这就使弃官逃罪的现象日益普遍,欲禁不能。
我们把汉代的“去官”和“弃官”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目的在于分辨官吏主动辞职和自行解职的各种动因,借以剖析它对汉代人事管理制度及汉政得失的影响。从整体上考察,去官和弃官可划分为主观(隐、抗争、逃罪等)和客观(病、丧等)两大类。古人编纂史书虽然注重春秋笔法,刻意一字褒贬,但在具体述史的过程中也难免有用字混淆的地方,因此上述分类只能是举其大端而已。一般来讲,客观促成的“去官”除了造成人事管理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外,对实现政治的好坏并无太大的损伤;主观促成的“弃官”最初是对士人不合作行为的肯定,后来却成为官吏逃避罪责的手段,影响极其深远,也是我们准备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三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列有“擅去官者无禁”条,认为汉代“平时朝廷无禁人擅去官(实即本文讨论的弃官——笔者按)之令,听其自来自去而不追问也”。赵氏仅仅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不知“弃官”已经事实上成了封建官吏的法外特权。
前已述及,秦汉时期对官吏的控制很严,法律规定官吏不得“擅去职”,大庭脩先生亦指出:“从列传中所记载的官吏罢免情况来看,几乎不可能见到有罪免与病免以外的理由,所以,一旦当了官,要随便辞职是困难的。”(注:见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7章《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那么,王莽篡汉以后,官吏弃官归隐,弃官奔丧,特别是弃官逃罪的现象又何以日趋普遍呢?我们认为,在汉代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完备的条件下,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为意识形态导向与君主专制制度二律背反所致。汉代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武帝以后日趋完备,专制皇权的无限膨胀,必然排斥士人的政治自由与人格独立,任何反对现行制度与政策、追求个体身心自由的言行,按君主专制的“排他律”都属违法。另一方面,汉政府为使臣民绝对效忠汉室,以孝治天下。东汉伊始又褒奖隐士,提倡名节,从而使士人的“去就”被肯定为一种“权利”,这种不合作权利的确立本质上是与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自由律”。君主专制的“排他律”与士人追求政治自由的“自由律”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既对立又统一,它不仅为各种类型的隐士建构起“合法”的避风港,而且也为汉代官吏弃官逃罪提供了“二律背反”之间的法律空隙以及舆论上、习惯上的“合法”依据。
二由汉代官吏法尚不健全所使然。近几年,有关秦汉官吏法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对官吏的任用、法律责任、考核、赏功、罚罪法的讨论已然赅详(注:见安作璋《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王清云《汉唐文官法律责任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唯退免法中之“去官”、“弃官”等问题尚不清晰。如前所述,弃官逃罪问题自西汉后期不断严重,这就促使汉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予以限制。安帝永初元年,邓太后下诏规定:“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注:《后汉书·孝安帝纪》。)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禁止官吏“弃官”逃罪,尽管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有罪案发,被考未决者),但仍对官吏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因为士人仕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权势与富贵,袁安说的好:“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注:《后汉书·袁安列传》。)为此,任何官吏也不想冒被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的风险,于是乎,官吏有罪,只要嗅觉风声有变,不待被案验即“弃官”而去,这既可逃避法律的追究,又能因此钓取高名,左雄所谓“或因罪而引高”,通鉴胡注说得更明白:“因有罪而先自弃官以为高。”(注:《资治通鉴》卷五一。)及安帝崩,阎太后以杨伦“弃官奔丧”为“专擅去职”而罪之,有把禁断“弃官”的适用范围扩大的意图,遗憾的是没能成为汉家故事。顺帝初左雄所上“请限去官之令”,是在对弃官造成的人事管理制度日益混乱、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的认识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在排斥“父母丧”之外一切“轻忽去就”行为的制度上的可能性和习惯上的可行性,并以禁锢终身的厉禁加以保证。它不仅表现了一代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反证出当时弃官逃罪现象的严重。此议被搁置后,终汉一朝再不见有禁断法令出台,从而使弃官逃罪成为官吏事实上的“法外”特权。
三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而加剧。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形成了外戚、宦官两种邪恶势力,他们在经济上强取豪夺,通商致利,索贿受赂,“一书出门,便获千金”(注:《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在政治上操纵皇权,干乱选举,父子兄弟并据州郡,枝叶宾客布列职署,“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注:《后汉书·杨秉列传》。)。面对东汉政权危在累卵的局势,一部分刚直不阿的士大夫和广大太学生徒以天下为己任,坚持同外戚、宦官展开了殊死搏斗。但这种正义斗争或因外戚、宦官控制皇权,而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或因外戚、宦官操纵选举,而难以剪其党羽。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 年),朝廷遣杜乔、周举等八人分行州郡,“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注:《后汉书·周举列传》。),八使所劾奏最初就因梁冀和宦官居中阻挠而寝遏,后来在种皓、吴雄、顾固等公卿大臣的强烈呼吁下,才促使顺帝“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注:《后汉书·李固列传》。)。这次大规模查办赃罪的举动在东汉中后期实属罕见,因此范晔才不惜笔墨,将之分叙于《后汉书》数篇之中。这自然使人们想到,在当时朝政极度腐败的情况下,少数廉洁耿直之臣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反腐败斗争,必然总是受到外戚、宦官的顽固抵制而难收实效,也使弃官逃罪问题不可能立法解决。事实上,外戚、宦官的党羽即使被举奏、免官,甚至禁锢,也不会影响他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注:《后汉书·左雄列传》。),正所谓“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注:《后汉书·第五伦列传》。),这就必然“使奸猾枉滥,轻乎去就”(注:《后汉书·左雄列传》。),于是“弃官”成了赃官贪吏在外戚、宦官掩护下,反“反腐败”的得力盾牌和惯用伎俩,每当一些身怀“澄清天下之志”的官僚士大夫出任州郡或出巡地方,赃官污吏纷纷“弃官”而亡,使反腐败之剑如同挥向棉絮,无法露其锋芒。诸如“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弃官奔走者数十人”、“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注:分见《后汉书》:《扬雄列传》、《朱穆列传》、《第五伦列传》、《党锢列传》等。)等记载,自安帝以后便史不绝书。悲矣乎!东汉王朝本于激励名节的对“隐”的肯定,竟异化为官吏逃避罪罚的法外特权,真乃作茧自缚。
“弃官”逃罪之“罪”无疑以赃罪居多,前引杨湛之罪,疑为主守盗;谢游则“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顺帝时左雄上“请限去官之令”,王先谦《集解》曰:“汉世臧污吏往往恐劾奏,辄自引去”;范滂为清诏使冀州,“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官吏犯赃,汉代本来是予以重治的。文帝规定:“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注:《汉书·贡禹传》。)即官吏犯他罪免官或服刑期满,仍可再仕,而一旦坐赃免官则终身禁锢。此令除景帝时一度废止,西汉一朝一直令行禁止。东汉时期为禁止官员犯赃,更实行赃吏“增锢二世”(《后汉书·刘恺传》)、“臧吏三世禁锢”(《后汉书·陈忠传》)等严惩措施。在赃罪的量行界限上,“臧二百五十以上”即行起诉,“臧五百以上”就要免官,“臧十金以上”弃市,罪无赦。由此可见,汉代惩赃之法不可谓不严,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强,可官吏犯赃又何以屡禁不止,这除了封建制度下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合二为一、法律特权的庇护以及官吏受财产欲、权力欲的驱使等主客观因素外,“弃官”可以逃罪也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
本来惩治赃罪的法令在执行中已大打折扣,或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注:《汉书·贡禹传》贡禹曾上书建议:“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或以上请、爵减、赎等法律特权避重就轻,而“弃官”更为赃吏逃脱法律制裁提供了一种法外保护。弃官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弃官可以逃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注:《后汉书·左雄列传》。)。它已经从一种习惯、世风嬗变为事实上的法外特权,它不仅加深了汉代的政治腐败,更为官吏犯赃提供了某种安全感,何乐而不为。仅此而论,官吏的习惯性特权比法律特权危害更大,辐射面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