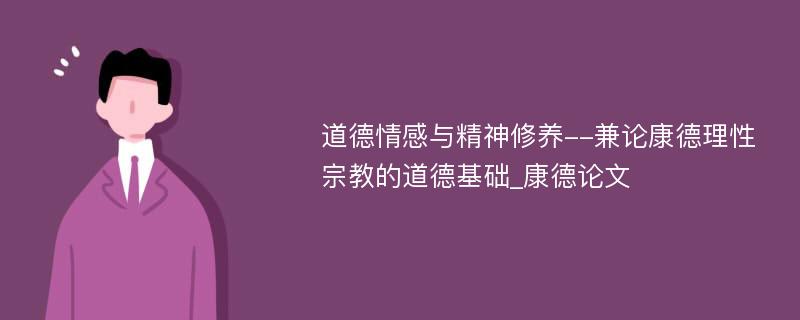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道德论文,理性论文,宗教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康德坚定不移地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成功地证成宗教是道德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而完成了单纯地将宗教建立在人类的自然理性基础之上的“理神论”理想。根据这个理想,康德将“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视作他的理性宗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培育人的道德情感,实现人的心灵改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途径。
一、康德界定的“道德情感”
康德对理性的实践能力所进行的批判,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行为全部道德价值的本质性东西取决于如下一点:道德法则直接地决定意志。”①意志所开启的是理智世界自由行为者的行动的因果序列。由于这个序列依然是一个有着因果联结形式的意志与行为的关系序列,即使它没有自然世界因果序列所具有的那种铁的强制性,也应当具有服从规律所造就的那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只能来自意志出于责任②而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一切依赖于其他动机的意志决定,行为可以是合乎责任的,但只是一种没有道德性的合法行为。这样,康德就将道德行为与纯粹善良的意志、出于责任的行为以及对道德法则的尊重等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命令。道德的绝对命令所以可能的根据,关键在于必须存在一个将行为者的主观准则与客观的道德法则“先验综合”于一体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即自由概念,它也被解释为意志自律。康德说:“我们必须也把自由的理念赋予每一个具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它仅仅按照这个理念去行动。”③又说:“如果我们设想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就把自己作为成员置入知性世界,并认识到意志的自律连同其结果,亦即道德性。”④由此可见,在康德这里,纯粹自由意志不是与感觉世界相联系的、具有认知性质的确定性意识,而是隶属于作为理智世界存在者的人的一种自律意志。这种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受制于作为自由因的绝对意识,由此决定人的实践行为既不受行为者主观偏好也不受行为欲求对象的福利支配,它完全出自绝对的善良意志。
在康德看来,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所确立的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是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在实践领域的必然结果。正如理论理性通过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划分使得对自然界的必然性因果联系成为可能,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将世界区分为现象世界和理智世界,从而将人二分化为既属于感性世界又属于理智世界的双重存在者,使得关于意志的自由因成为可能。康德成功证明了自由是道德的存在根据,而道德是自由的认识根据,从而证成了这样一种理性推理关系:人必然能理性地存在,因此人本质上有自由,如果人没有这种理性自由,道德也就不存在。如此一来,康德以自由与道德的不可分离性既证成了自由的本体性地位,也通过道德法则这一纯粹实践理性的事实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由于康德确认了自由的实在性,人摆脱感性的束缚,克服主观偏好的支配和对象福利的诱惑而让自己的行为服从和遵守纯粹的理性道德法则就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应当上,它必须落实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先天综合地将道德法则与经验的实践行为结合起来,即让理性的道德法则渗入经验,对感性世界施加影响,实现纯粹意志对行为所遵循准则的规则规定。在这一过程或者行动中,依照康德的观点,道德法则本身就是规则地规定行为的动力,因为在内在意识的绝对性被觉识到之后,意志绝对不能采纳其他的动机作为决定行为的准则,而只能是道德法则,但是,我们却需要“谨慎地决定,在什么方式之下,道德法则成为动力,以及因为动力是法则,那么什么东西将作为那种决定根据对人类欲求能力的作用发生于这种能力之前”⑤。康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如同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觉识到的自由意志是如何可能的一样,我们同样无法理解道德法则这样的东西如何能够直接性地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但是我们却知道,这种东西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了某种影响,使得我们心中产生出一种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由此觉知到自由意志,为道德法则的存在及作用提供理性证明。职是之故,康德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为论说道德情感,解释道德法则如何对人的心灵施以作用。
何谓康德意下的道德情感?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形式主义义务论的典范,他直接批判的对象是实质性的、经验的幸福论道德哲学。因此可以断定,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绝不是产生于人们的道德心理活动及其过程中的一般感性的或本能的情感。事实上,康德正是通过批判经验主义的道德情感,诠释对道德情感的纯粹理性理解。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一卷第三章中,康德指出,一切以特殊禀好作为动机的行为都可以在人这里产生一种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实质性经验的,是以自爱的幸福作为行动准则的利己主义所共有的。他指出:“一切禀好共同(它们也能够归入尚可容忍的体系,而它们的满足便称作幸福)构成利己主义(solipsismus)。这种利己主义或者是自爱的利己主义,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度的钟爱(philautia),或者是对自己惬意(arrogantia)的利己主义。前者特别称为自私,后者特别地称为自负。”⑥与这种经验的道德情感相反对,一切通过道德法则的意志决定的行为的本质性特征,正在于行为本身无须任何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必须拒绝所有的这种冲动,因为受道德法则所支配的行为仅仅是出于责任的行为,它不以任何感性的要素作为依据。因此,行为者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为了成就德行,就必须从善良意志出发,出于责任而行动,由此势必要求行为者必须贬损或者抑制任何一种以特殊禀好作为动机行为所产生出来的感性情感(“因为一切禀好和每一种感觉冲动都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⑦),将自己的意志置于道德法则规定之下,让意志所决定的行为依照道德法则而发出。这样的意志才是纯粹实践的理性意志,这样的行为才是充满道德感的行为,有限理性的个人也因此而现实地承担起理性存在者的职责。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先天地洞见到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道德法则,并且同时在贬损和抑制感性情感及欲望过程中,先天地认识到道德情感,即从概念出发先天地规定认识与快乐或不快的关系⑧。当然,道德情感在纯粹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过程,自然伴随着感性上因为平伏自爱、瓦解自负而产生出的痛苦情感,但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借助理性对意志的规定而进入经验,支配感性世界而渗入行为者的心灵之中,结果使得行为者在自己的心灵中产生出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作为道德情感尊重的对象是一种自在的肯定性的东西,不仅能够平伏和瓦解感性情感,而且作为自由的因果性形式,能够帮助道德情感摆脱经验他律的约束。道德情感因此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它服从并听命于理性。通过道德情感,行为者能够真切地在心灵中体察到道德法则的威严和壮丽,因此,道德法则必定是最大的敬重对象,道德情感必然是最伟大的感情。
综合上论,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对康德相关思想的理解:第一,由于人事实性地以自爱作为意志决定的根据,我们的心灵主观上被一种情感占据着,现在由于唯一真正的客观法则在我们的判断中瓦解这些东西,它要使自爱不再参与最高的立法,因而就必定能对情感产生一种否定性的作用。第二,人们是在比较道德法则与自爱准则过程中,发现自爱以及自负等情感遭到道德法则的贬损,而贬损之所以得以圆成恰恰借助了对道德法则本身的某种表象,因而那种关于道德法则的表象就是意志的决定性根据,就此而言,是表象本身唤起了对它自身的敬重,由此进一步推论,可以说,道德法则就是人主观上产生敬重的根据。第三,对道德法则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情感发生。由于道德法则消除掉了人主观的反抗,依据理性的判断,这种消除障碍就等同于因果性的肯定式促进,因此缘故,可以将这种理性的情感称之为出于道德法则对自身产生的敬重情感,而在主体之中并无先行与道德相称的情感,因而,道德感情作为一种理性情感,是道德法则渗入理性存在者(人)之心灵之中而在心灵引发的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感,它虽然不是先行存在于道德主体之内,但却是能够被道德主体先天认识的唯一的理性情感,它臣服于理性,执行理性的绝对命令,以打动心灵的情感方式贬损和抑制行为者的种种禀好和感性欲望。
通过这样的论证,康德断定,出于道德法则而对道德法则敬重的道德情感乃是在“主观”上被认定的作为时间中无限趋向于善的德性,因为实践理性本身乃是要展开于时间之中的,这种展开恰恰就是通过排除掉一切以自爱作为最高原则的意志决定,从而使得人走向无限趋近圣洁的道路。这一点是由人的根本有限性决定的。康德指出:“……敬重是施于理性存在者的情感之上的作用,从而是施于理性存在者的感性之上的作用,它以道德法则让其承担敬重的这种存在者的感性,从而以这种存在者的有限性为前提;于是,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不能赋予一个至上的或超脱一切感性的存在者,感性对于它不可能成为实践理性的障碍。”⑨依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乃是人这样的理性存在者所特有的一种东西,由于这样的存在者本质性地有一个身体的规定,感性要素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因而他应该超出于一切必然性的规定而听从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因而,道德法则直接性地决定规定其意志的决定必定是要克服掉那个感性要素的规定,而后者乃是出于自爱满足后的一种快乐情感,因而,道德法则是通过对行为主体的感性情感加以影响而成为实践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这种根据行为基于准则形成从感性意义上影响意志的情感。这一切的论证都是建立在康德对于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深深理解之上的。因而,似乎粗略看起来,康德对于道德情感的界定充满了种种的矛盾,这里说道德情感本身不存在,那里又说产生了这样一种情感,其实这是由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人的存在特征(双重存在)本身决定的⑩。
由此可见,“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置疑的道德动力,并且这种情感除了仅仅出于这个根据的客体之外就不能指向任何客体”(11)。因此,在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法则通过贬损自负而消除禀好障碍的影响而仅仅指向以法则为根据的客体,从而敬重也必须被看作活动的主观根据,即被看作是人之遵守法则的动力及选择适合法则生活的根据。如此一来,“从动力概念生发出了一个关切概念,关切决不被授予具备理性的存在者之外的存在者,并且在动力是由理性表象出来的范围之内,关切意谓着意志的一个动力”(12)。这就是说,关切从属于理性表象的范围之内,因而是一个纯粹的非感性的关切,与道德情感乃是与道德法则贬损感性动机相伴随相比,这个关切概念乃是与将道德法则纳为准则的意志相伴随,因而,如果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真的,我们还需要在这两个概念上建立准则的概念。“因此只有当这个准则依赖于人们对于遵守道德法则的单纯关切时,它才在道德上是真的。”(13)到这里,康德要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三个概念(动力—关切—准则)就全部给出来了。可将这三个概念之间关系作一大致梳理:因为作为以身体方式存在的理性存在者有感性的规定,康德将与之伴随的东西称作本能,因而,恶作为一种事实性而存在;在绝对的内在意识得到觉识之后,与将道德法则作为意志决定的根据相比,以自爱的幸福作为准则的意志决定得到抑制,从而道德法则本身就对自爱产生的快乐情感加以贬损,同时,在理性判断看来,贬损之际道德法则自身产生出理性的敬重情感,因而,道德情感本身就可以作为人决断行为的主观根据,从而被看作遵守法则的动力;这个动力本身就会产生对于将道德法则纳为根据的意志的关切,因而,关切乃是作为意志的动力存在的,并且仅仅是道德的关切;由于在此基础上,意志的一切决定都是仅仅出于遵守法则的单纯关切,道德法则也就作为意志决定的唯一准则,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之行为才会成为道德上的真。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三个连贯一致的概念就会发现,康德之所以要给出这样三个概念来解决向善的问题,乃是在于人意愿的主观性质并不是自发性地符合实践理性的客观法则的,否则的话,这样的概念就会成为不必要。所以,“它们一概以存在者本性的局限性为先决条件”(14),因而,也是在这里,康德明明白白地说,“一种单纯理智的理念(道德——引者注)对于情感的这种影响是无法为思辨理性所解释的”(15)。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这乃是由人这种存在者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作为有限存在者,人不得不仅仅满足于只能先天地洞察到道德情感与道德法则之表象在自身中的联结,对于这样一种仅仅出自实践理性、非本能性的情感何以能够贬抑掉本能性的情感,以及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力作用,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我们也不应当试图去知,只能对之表示深深的敬畏,理解为意志对道德法则的单纯关切。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逾越我们所当处的位置。康德的后继者们最不满意康德的就是这一点。然而,那些不满者所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比如休谟诉诸一种道德情感(与康德的不同)、谢林诉诸于理智直观、黑格尔诉诸于绝对精神、还有道德直觉等,其在思想史上的命运并不比康德的好到哪里去。或许后续的思想家依然会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康德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二、“责任”与“神圣性”
按照康德,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并非先行就存在于道德主体之内的情感,主要体现为对道德法则的敬重。道德践行者通过贬损或者抑制自己作为感性存在物所必然具有的种种禀赋与好恶,内心油然而生对森严道德律令的敬畏情感,让自己的意志接受道德法则的规定,做出出于责任的行动。可见,道德情感对道德法则的尊重也就是对责任的尊重,依据道德法则采取的行为就是责任行为。在康德看来,道德行为肯定是一种责任行为,但责任行为并不一定是道德行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是康德所说的道德行为,合乎责任的行为则不属于道德行为。因为,合乎责任的行为,仅仅是偶然与道德法则相符合。做出合乎责任行为的根据不是意志的理性规定,而是满足行为者主观偏好及对象欲求的感性规定。就此而言,合乎责任的行为无异受本能式感性情感的支配,无法摆脱来自感性利好所产生的必然诱使。出于责任的行为则通过实践理性而超克了人的本性及感性诱使,从而使人作为有限存在者能够将意志与法则联结在一起,贯通感性界和理智界,将人作为理智存在者所具有的伟大人格、绝对价值、崇高尊荣鲜明地彰显出来,成为自由的真正主体,拒斥感性规定,关切道德法则,发自内心地敬重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据此可知,“义务概念在客观上要求行动与法则一致,但在主观上则要求行动的准则对法则的敬重,作为法则对意志的唯一规定方式”(16)。就第一点,责任排除掉了恶的行为;就第二点,责任排除掉了合法但却不合道德的行为,这一点对于康德尤其重要。因为,趋向某个行为的“意向”是道德立法的核心所在。康德说:“这样,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才被安置在行为出于职责和出于对法则的敬重必然性之中,而不是安置在行为出于对行为可能产生的东西的热爱和倾心的必然性之中。”(17)
如此看来,康德是将自己有关行为道德性的论证落脚在“责任”概念上。所有道德的行为都出于责任,也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其余的一切行为统统不具有道德性。当然,只是对于人而言是这样,因为对于纯粹的理性存在者而言,道德法则同时就是客观根据而不存在面对感性要素的主观性根据这样的问题。因而,康德说:“道德法则对于绝对完满的存在者的意志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则是一条职责法则,一条道德强制性的法则,一条通过对法则的敬重以及出于对其职责的敬畏而决定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行为的法则。”(18)这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于理性保留的克制,尽管他彻底觉识到绝对意识的深邃性,觉识到自由的崇高价值之所在,但是在绝对面前,他还是保持了人性所特有以及应有的一种节制和谦卑,并且在一切准则之中记住并持守住这种节制和谦卑。后康德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们就没有像康德一样守住这个底线,在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争论中(19),我们可以深深地领会到这一点。康德如是说:“唯有职责和本分是我们必须赋予我们与道德法则的关系的名称。我们虽然是那个因自由而可能、因实践理性而向我们呈现为敬重的德性王国的立法成员,但同时也是其臣民,而非其统治者;并且误解我们作为创造物的低下等级,由自负而否认神圣法则的威望,已经是从精神上背叛了那个法则,即使这个法则的条文得到了实现。”(20)这句话,康德是说给狂热的宗教徒以及在道德上狂妄的人们的,它表明,现实中的人绝无可能实现圣洁,圣洁只是人要无限趋近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自由的王国里面,人不过是作为造物存在的有限存在者,而绝非圣洁的绝对者。对于那些道德狂妄以及宗教热狂者而言,那种完全纯洁的圣洁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安守住自己的本分,出于责任来决断自己的行为。在这个层面上,康德展开了对于基督教爱的诫命和道德狂妄的批评。
基督教有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圣经·马可福音》12:29-30);“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马可福音》12:31)。在康德看来,就其是“以爱命令人”而非随意对待别人而言,这两条诫命在形式上与法则一致;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因为上帝并非感觉对象,要我们对上帝爱(是禀好)是不可能的(21),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爱施予人是可能的,但是爱却不可被命令,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一个人被命令去爱是怎么回事。因而,康德认为,我们只能从实践的层面理解这两条诫命。这样,康德就将基督教最核心的主题纳入到理性的层面来思考(22)。我们来看康德的分析。
既然只能从实践层面理解爱的命令,那么,“爱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意谓着乐意执行它的命令;爱邻人意谓着乐意对他履行所有职责”(23),由于“乐意”是奠定在主观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具有无限种阶梯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强制性的乐意,也可能是完全的乐意。而在康德看来,“‘喜欢(乐意——引者注)’是一个理想,我们应该在一个经常而无止境的接近它的过程中奋力去实现”,“因为一个人总是要求‘自我强制,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受到驱使去做他并不乐意的事——但一个受造之物绝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道德水平’”(24),而且,“如果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某一天达到了能够完全乐意去执行一切道德法则的层次,这无非就意指:在他心中,甚至连存在着引诱他去偏离这些道德法则的欲望的可能性都没有”(25)。但是人却恰恰不是这样的存在者,就他总是要为了满足自己状况的需要而欲求着什么而言,他恰好是不自足的,因而,他绝无可能完全祛除掉欲望以及禀好。因而,在这样一种根本的有限性面前,所谓的“乐意”根本不是完全的乐意,而是带有一种强制性的乐意,因而这完全就是一种合乎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就命令本身而言,也是有问题的,由于遵循法则而做出合乎道德性的行为最核心的是要出于意向的,而意向恰恰是不能够被命令的,在此命令的含义就变成了人应该努力去追求它,而命令别人有乐意去做好事的意向本身就是矛盾的。因而,《福音书》中所描述的最完满的道德意向只是人在无限的过程之中逐渐接近的。(26)但是,在奥古斯丁之后的路德看来,因为这两条爱的命令“是上帝对人清楚明白的诫命”,它并非“作为一个我们必须经常奋力去达到、但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来命令我们做的”,“因为这与上帝的绝对性不相符合”,“毋宁说它是作为我们就在此时此地应该做到的来命令我们做的。理想是可以等待的,但命令是不可以等待的”,(27)因而,上帝本来就是要我们现在来爱,即使我们没有一个人事实上做到了,但是这却毫不损害命令本身的真理性和神圣性。这里我们看到康德与路德的差异,他们都要求行为本身的纯洁性,但是康德看到了人这种理性存在者的有限性,而路德看到了上帝这样纯粹理性存在者的绝对性,从而,无论人事实上做到与否,这丝毫没有触及到上帝诫命的神圣性,至于事实上究竟有无人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值得认真争辩的问题(28)。康德根本性地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在于由于取消掉了上帝的恩典,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就只能诉诸于人本身,但是人恰恰是具有根本的局限性。康德用简短的一句话揭示出了他论证的这种出发点以及最终落脚点,他指出:“……对于《福音书》中的道德学说,我们可以毫不虚伪、实事求是地照样说,它首先凭借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但同时凭借道德原则与有限存在者的局限相切合的性质,让人类的一切善行都委制于那放在他们眼前的职责的管教,这种职责不允许人们热衷于虚幻的道德完满性;它同时为喜欢无视自己界限的自负和自爱设立了谦卑的限制(亦即自知之明)。”(29)
从康德对基督教中道德诫命的解释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能够时时居于其中的道德状态,乃是德行,亦即处于斗争之中的道德意向,而不是在臆想拥有的意志意向的完全纯粹性之中的神圣性”(30),因而,一切不是出于责任,只是将道德的完满作为纯粹的功业来期待的就是道德狂热;将《福音书》中爱的诫命作为人之本身就拥有的德性意向证明,从而可以完成爱的诫命的就是宗教热狂。我们应该根本性地弃绝这种东西,从而仅仅在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界限之内做出于责任的行为,将行为的道德动力置于法则本身之中而非置于别处。这是康德对于宗教热狂和道德狂热的根本批判。
接受康德对宗教热狂和道德狂热的批判,就意味着承认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这是一个道德宗教问题而不是宗教道德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解决的问题。康德如是说:
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力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无非就是纯粹道德法则自身,只要后者让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超感性存在的崇高性,并且从主观方面在人之中产生了对于人自己高级天职的敬重,而这些人同时意识到他们感性的此在,意识到与之连结在一起的对于他们那易受本能刺激的本性的依赖性。(31)
三、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康德,道德宗教作为植根于道德的信仰体系,首先要体认到的原则是,由于意志接受道德法则的规定而在人心中产生对绝对律令的敬重,才使人在主观方面所具有的真正重要的道德情感,人拥有这种道德感情,就必然只关切道德法则,从而拥有弃恶向善的动力,纯然理性的宗教就必然有理据地提出“善的原则”统治“地上王国”的世俗化要求,促使人走出伦理的“自然状态”而成为“伦理共同体”一个成员。这样,如同康德对认识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考察,康德在这里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终将宗教信仰问题纳入启蒙视域接受理性化洗礼,用道德化宗教方式将宗教奠基在自然理性基础之上,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理性基础。
注释:
①[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7页。
②“责任”,德文为“Pflicht”,英文一般翻译为“duty”,中文除了翻译为“责任”,其他常见的翻译还有“义务”(如李秋零、邓晓芒)、“职责”(如韩水法)等。本文采用“责任”译法。
③[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
④[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461页。
⑤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78页。
⑥[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79页。
⑦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79页。
⑧康德的原文如下:“……我们能够先天地洞见到: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道德法则,由于抑制了我们的一切禀好,必定导致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名之为痛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从概念出发先天地规定认识(这里便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认识)与快乐或不快的关系。”(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79页。)
⑨[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2页。
⑩康德的后继者不满足于康德的解决方式,要求采取彻底的理智直观解决这个问题。在逻辑上,这样处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总归是人而不是纯粹的理性。而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康德,他从现象学角度对康德的道德情感说进行了分析。
(1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5页。
(1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6页。
(13)[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6页。
(14)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6页。
(15)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6页。
(1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韩水法的译文为“职责概念对于行为要求它与法则的客观一致,对于行为的准则却要求对法则的主观敬重,作为由法则决定意志的唯一方式”。(见韩译《实践理性批判》,第88页。)此处经比较,作者决定采用李秋零的翻译。
(1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8页。
(1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9页。
(19)1929年,在瑞士达沃斯,海德格尔与卡西尔进行了一场论辩,对“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主题。其中,卡西尔谈到无限性不仅仅是作为对于有限性褫夺的规定性,而且它还是某种本己的领域,并且当有限性使自身得到充实完成之际,它也就迈进了无限性,这些说法是完全背离于康德的,对此,海德格尔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具体参见[德]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附录二”,第273-275页。
(2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89-90页。
(21)爱是非常难的一个主题,就一般层面的爱,即世俗层面的爱来说,康德这样的界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作为一个感性情感的爱只能施于一个感性的对象;但是,基督教真正要说的是一种远远超出于感性层面的“圣爱”,这有点儿类似于康德界定的敬重概念,对于这种圣爱,数千年来,人们言说不断,但是却又总是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作者认为,康德之所以在这里故意不谈圣爱是出于批判的要求,对于在思辨理性层面无法解释的基督教概念干脆就忽略,因为也实在没什么好谈的,也不可能在逻辑层面谈清楚。对于这个主题,20世纪的舍勒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将这种神圣性的爱直接等同于人格性的存在,但这又何尝不是从人格的角度谈论神圣的东西呢。
(22)如此一来基督教所有重要学说都被康德批判分析了。康德对基督教主要学说的分析、批判、吸收、改造在他的“批判哲学”以及后期由关于信仰、历史、法权(权利与义务)、人类学等哲学思考所构成的“希望哲学”中随处可见,康德哲学甚至可以看做是对基督教传统的启蒙理性式系统重构。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论述重点,故仅仅指出这一点,存而不论。
(23)[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0页。
(24)[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25)[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1页。
(26)年轻时代的黑格尔对于康德如此分析基督教“爱”的学说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意,在黑格尔看来,耶稣基督教导的爱根本就不是权利和义务性的东西,根本不是概念统一性的东西,而是超出于一切权利、义务、概念的精神、神性的统一性,因而爱是道德的补充,在爱之中,道德的一切片面性和相互冲突都被扬弃掉了;另一方面,把义务作为乐意去做的理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义务必定设定一种对立(理性与情欲),而乐意去做却不设定对立,康德虽然认为人之有限不能达到理想,但是这个矛盾却是无法化解的,等。具体参见[德]黑格尔:《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8-313、341-345页。
(27)[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第132页。
(28)奥古斯丁在致马色林的信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具体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圣灵与仪文》,周伟驰译,章1、3、64、65、66。
(29)[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3-94页。
(30)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2页。
(3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6页。
标签:康德论文; 康德著作全集论文; 绝对命令论文; 道德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