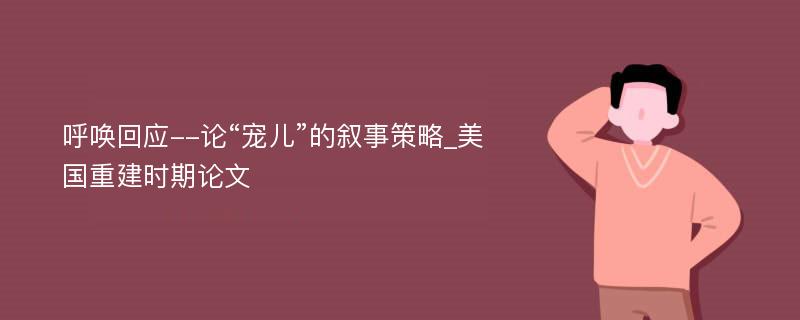
召唤应答——谈《宠儿》的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宠儿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4-0085-05
美国作家莫里森的第七部小说《宠儿》讲述了南方重建时期,已成为自由人的黑奴重建自我身份的故事。重建时期的南方社会虽然经历了体制上的更迭和进步,蓄奴制时代的种族暴行却依然盛行。故事中一个发人深省的场景——老黑人斯坦普·沛德偶然发现被杀黑人小姑娘的红发带,就发生在重建时期的南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把小说设置在这样的背景中,不仅使它承载了巨大的叙事张力,也使“重建”一词成为叙事的灵魂。小说有着与莫里森其他作品一脉相承的使命——重建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
《宠儿》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与故事发生的19世纪70年代相距一百多年。可是在莫里森看来,“当时(重建时期)的情况与今天美国黑人所面临的情况并无实质上的区别”[1]89。重建时期的南方黑人大多从事着身为奴隶时的工作,生活贫苦不堪。他们受歧视、被隔离,还时时遭受白人的私刑威胁。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里根政府带有倾向性的政治、经济政策不仅使黑人沦为政治上的弃儿,还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差距。这一时期的黑人失业率急剧上升,整体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黑人家庭和社区结构还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与现实的偶合促发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如果说作品的生成源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召唤应答”(call and response),那么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其实“召唤应答”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框架线索,是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
“召唤应答”源于非洲,是非洲口头文学和民族音乐特有的艺术形式,表现为召唤者和应答者双方的即兴创作。它在蓄奴制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常常是一名黑奴以劳动号子或圣歌起头,其余黑奴则纷纷回应他的呼唤。这种黑人自创的艺术形式往往能激发被压抑的人性,通过情感的宣泄和交流,创造力的自由表达,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正因如此,它在黑人中很盛行。无论是在家人叙旧的私人空间,还是在布道演说的公共场所,召唤与应答的双方“进行双向交流,一同分享生活感受与体验,这种群体创作特征使其成为黑人民族疗治伤痛、谋求生存发展的有意识文化行为”[2]117-124。小说中,莫里森充分运用了“召唤应答”这一本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重要文化密码,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凸显了作者重建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努力。一方面,小说基于声音的叙事特点最直观地道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小说通过“重复”这一叙事手法,扩展了“召唤应答”在叙事层面的应用,使之成为构筑情节的工具;同时,借助其强大的召唤功能,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也可看作是“召唤应答”在文本之外的延伸。对莫里森而言,“召唤应答”不仅是美国黑人重建其个体身份、家庭和群体关系的纽带,更是回归黑人文化之根的重要桥梁。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1855年,从肯塔基州的种植园“甜蜜之家”出逃到俄亥俄州的女黑奴塞丝面对前来抓捕的白人,为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奴隶的悲惨命运,亲手杀死不到两岁的女儿,出狱后让人在女儿的墓碑上刻上“宠儿”二字。18年后,一个自称名叫宠儿的年轻女子走进了塞丝的生活,从此一切都改变了……
引人注意的是书中彼此交织、前后呼应的各种声音,正是它们组成了“召唤应答”的主旋律。小说基于声音和听觉的叙事特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在小说起始的寥寥数页里,第三人称叙事人的叙事声音就已不露痕迹地迅速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推上了前台。如果说叙事声音在编织情节的过程中将不同的身份赋予人物,那么人物形象的逐渐丰满乃至呼之欲出,则应归功于书中出现的其他种种声音:人物的对话、内心独白、歌谣、布道、多声部的合唱等。它们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成为黑人重建自我、缔结家庭纽带关系、从群体中汲取力量的重要手段。
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生前常在“林间空地”布道,作为“一位不入教的牧师,走上讲坛,把她伟大的心灵向那些需要的人们打开”[3]103。伴随着她的一声声召唤,人们欢笑、舞蹈、哭泣,为她朴实而充满激情的布道伴奏。“悠长的曲调持续着,直到四部和声完美得足以同他们深爱的肉体相匹配。”[3]105布道的主旨很简单——“爱自己”。在一声声穿透灵魂的呼唤和应答声中,黑人渐渐找回了在蓄奴制下所丧失的人格尊严。
声音在塞丝与宠儿母女相认的情节中成了开启记忆的锁钥。塞丝、宠儿和塞丝的小女儿丹芙从河边溜冰回来后,宠儿不经意间哼唱了一首塞丝自己编的,只有她和她的孩子才会唱的歌。歌声让塞丝“回想起那一声咔嗒——让那些信息的碎片依原样各就各位的声音”[3]209。刹那间,种种回忆奔涌而来:婆婆说起不可能认出被卖女儿时的伤心模样;塞丝的母亲指着身上的记号,教她日后如何认出自己的画面……歌声唤出了记忆,唤醒了塞丝,对此的应答是她后来作为补偿所付出的加倍的母爱。
多重声音的交融则有力地传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对亲情的渴望。小说的多声部特征在第二部分尤为明显。这里,相当长的篇幅被用来记录塞丝、宠儿和丹芙的意识流动。第三人称叙事声音完全退出,我们听到的是交替响起的三个女人的声音,最终融汇成“召唤应答”的三重奏,“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3]259。
声音也是黑人个体,乃至黑人民族获取力量的源泉。小说结尾处一群黑人妇女为驱逐侵犯生者的宠儿,来到塞丝门前,祈祷、吼叫、歌唱:
对塞丝来说,仿佛是“林间空地”来到了她身边,带着它全部的热量和渐渐滚沸的树叶;女人们的歌声则在寻觅着恰切的和声,那个基调,那个密码,那种打破语义的声音。一声压过一声,她们最终找到的声音,声波壮阔得足以深入水底,或者打落栗树的荚果。它震撼了塞丝,她像受洗者接受洗礼那样颤抖起来[3]311。
声音几乎成了书中的一个主要角色,通灵般地在人物间往返穿梭。如果说文本内的声音是解读小说的一条主线,那么文本外的声音则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作品的互文性特点使它成为一个无限的开放体。正如福科所言,“书本的疆界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不能用标题,最先数行,最后的句号来界定它,也不能用它的内在结构和独立形式来界定它,它陷在一个涉及其他书本,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的体系中;它只是网络中的一个节。”[4]23
“甜蜜之家”显然影射了伊甸园,黑奴的逃亡则是对《失乐园》的戏仿。不同之处在于,“甜蜜之家”并不是黑奴的天堂,离开它是对命运的反抗,而不是伊甸园中人类始祖对命运的屈从。在小说中,《失乐园》的回声隐约可辨,它撞击在《宠儿》这面现实的镜子上,却折射出人间地狱的图景。
作品一开始就以“凶宅闹鬼”的情节牢牢抓住了读者,把哥特式小说元素放在这部取材于真人真事的故事中,其颠覆意味跃然纸上。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鬼视为被排斥、被压制、被放逐的对象,而宠儿这个冤鬼却能肉身还魂,回到人间,不断地向母亲索爱。她是过去的化身,却冲破时空的阻力,走进不属于她的现在,诉说满腔怨恨和冤屈。与宠儿相比,真正可怕的是蓄奴制。尽管已被废除,蓄奴制的余响依然如鬼魅般如影随形,是黑人心中不可触及的伤痕。
“召唤应答”还体现在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上。重复是莫里森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她擅长让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述同一事件,互为补充,彼此呼应。小说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不是在同一时间里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呈碎片状的叙述提供了一鳞半爪的线索,只有读完大半部小说,读者才能了解到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不同叙述声音的此起彼伏不断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小说的中心事件——杀婴,分别从前来追捕的白人的视角,斯坦普·沛德的视角,以及塞丝本人的视角来讲述。这种由远及近的视角上的推移使读者一步步接近真相。首先是白人对此的困惑,“她干嘛逃走,还这样做?”[3]179接着是斯坦普·沛德尝试性的解释,在他的描述中,塞丝杀婴更像是一种护犊的行为。他回想着“她怎样飞起来,像翱翔的老鹰一样掠走她自己的孩子们”[3]188。而塞丝的讲述则充分解释了她的行为,在她看来,杀死孩子是“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母爱,而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谓的黑人与生俱来的“兽性”,引发了主人公的极端行为。除了这一中心事件外,如丹芙降生;塞丝以肉体作为交换,为死去的小女婴墓碑刻字;塞丝的丈夫黑尔目睹妻子受辱后精神失常等事件,都是经过数次重复,借助叙述视角的转换和叙述声音的变化呼应来完成的。
如果说重复是莫里森构筑情节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故事真正完整地呈现则有赖于读者的参与。罗兰·巴尔特认为,文本统一性的达成不在其起源,而在其终点[5]33。这里的终点指的正是读者。莫里森的叙事往往能引发强烈的阅读期待。她在书中零星散落的条条线索,留下了一处处空白,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和经验来填补。这使文本具有了强大的召唤力,从而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交流的关系。文本的召唤功能还表现在作品的共时性上。小说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和线形叙事,将过去的点点滴滴穿插到现在的时间层面上,不仅使得故事的进展十分缓慢,而且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界限,使二者浑然一体。作品的共时性特征模糊了事件向前发展的历时性,造成时间的停滞和空间的无限拓展,“读者在空间的召唤下不得不参加情节和细节的组织。”[6]36-39
此外,作者对黑人口语体的大量运用更是给小说抹上了一层群体创作的色彩。“莫里森的艺术成就之一,是她在小说中成功地吸取和发扬了黑人文化传统中独特的魅力,把从黑奴时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7]445作品多处采用口吻亲切,如同唠家常一般的口语体,字里行间透露出听者和说者双方的默契。种种停顿、省略、欲言又止、言外之音,只有深谙黑人传统和说话方式的人才能毫不困难地听懂,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回应、补充和阐发。谈到《宠儿》的创作,莫里森曾说起过小说的“听觉”特性。在她看来,写作似乎是捕捉并记录头脑里的声音而不是文字,书写的是各种声音的组合,节奏和表达方式。“关键是不需要副词来说明它如何发声,只需在句中有它的声音即可。如果需要大量脚注、编者按或描述语来解释一通的话,那就有问题了。”[8]296从这个角度看,“召唤应答”强化了黑人的语言特色,它指向了美国黑人共同的文化之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书中涉及非洲文化的内容不作注解。当塞丝身怀六甲,拼死逃出“甜蜜之家”时,腹中胎儿在她的心目中,是一只小羚羊的形象。从未见过羚羊的她依稀记得年幼时黑人们跳过的羚羊舞。要揭示表层叙述结构的谜底,就只能借助于深层的象征结构。这样的文化解码足以激起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事实上,莫里森“所追求的是一种表现力。它的达成有赖于对黑人文化中的种种密码的充分理解,从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一种直接而亲密的共谋关系,并使复杂丰富的美国黑人文化以一种与之相配的语言被表达出来。”[9]76
“召唤应答”便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密码,透过它我们可以察觉到莫里森对本民族文化的痴迷,以及她重新建构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努力。事实上,从她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到最新作品《悲悯》(2008),保留黑人自己的文化一直都是莫里森作品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
尽管小说采取了流行于18世纪末的奴隶叙事(slave narrative)体裁,二者之间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传统的奴隶叙事以废奴为最终目的,主要阅读对象为白人,为了获得白人读者的认可,不得不隐去任何可能引起白人反感的内容。它往往只讲述个人的外在经历,而不触及内心情感。其代表作为道格拉斯的《一个黑人奴隶的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1845)。不可否认,这种早期的黑人文学形式鼓舞了奴隶们对自由的追求,但也常常拘泥“在奴隶叙事的修辞目标之内”[10]355。而《宠儿》则不同,它意在描述蓄奴制对已成为自由人的黑奴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因而人物的内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此外,奴隶叙事大多叙述黑奴离开家庭和黑人群体,只身逃往自由的北方。而《宠儿》则着重表现黑人通过重新记忆(rememory)走出过去,与家人和群体融为一体。这一主题流露了莫里森对黑人自我、家庭和群体的深切关注。蓄奴制在本质上剥夺了黑人的人格以及他们与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纽带关系,并在这一非人化过程中抹杀黑人的自我身份、语言和文化,如书中塞丝忘记了生母曾使用过的语言;非洲人特有的文化只在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中隐约可辨。更为可悲的是,蓄奴制下的黑人没有自我。“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了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3]299
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召唤应答”,踏上了一条回归黑人自我,捍卫黑人主体性和尊严的道路;而小说作者则借助于同样的文化密码,开始了她回归非洲传统文化的征程。无论是在语言运用上还是在叙事技巧上,都可以看到莫里森与黑人本土文化的契合点,而本民族的文化意识更是植入了她灵魂深处。首先,小说明显带有非洲传统的宗教观和生死观的印记。相信、接受、容忍鬼魂的存在,甚至与之交流的情形,在书中随处可见。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明确表示她相信鬼魂的存在。对这一主题的渲染其实反衬出她“所倡导的黑人民族传统对现代文明既定秩序的有力反拨”[1]Ⅺ。其次,小说也着力表现了黑人对祖先的崇敬。宠儿究竟是人是鬼?在这一点上莫里森以其叙事特有的含混性提供了两种可能的阐释。一是宠儿是鬼,是塞丝死去女儿的冤魂;二是宠儿是人,她是贩奴船上的幸存者。她对从前非洲生活只言片语的回忆,充满了黑人祖先自由自在的身影;她梦呓般的意识流动再现了被掳掠的恐怖经历,回荡着黑人祖先沦为奴隶后的叹息呼号,更是与开卷题词“六千万,甚至更多”的死于贩奴船上和种植园里的黑奴亡灵遥相呼应。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宠儿的出现看作是回应祖先亡魂的召唤。对黑人而言,祖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代们从先人那里得到的是文化和成长的信息,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我们的祖先是整个生命圈的一部分。”[12]268敬祖这一主题在莫里森其他作品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罗门之歌》(1977),主人公的寻根之路便是一首对黑人祖先的赞美诗。
当我们把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我们会看到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召唤应答”。“作为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其作品)回应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文学先辈在文字及口头上的召唤;与此同时,她对他们的应答转而变成她对我们(后辈作家)的召唤。”[13]25正如莫里森自己所言,“故事不应该因为情节的结束而结束,这一故事应该在人们的心头萦绕并得以流传下去。”[12]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