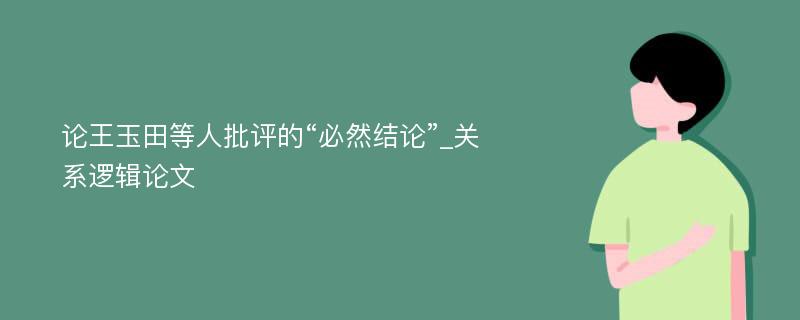
再论“必然地得出”——回答王雨田等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人论文,批评论文,再论论文,王雨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著作《逻辑的观念》和文章《论我国的逻辑教学》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包括一些批评。我欢迎批评,也仔细阅读了这些批评。我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批评做出回答。(注:由于主要回答王雨田先生在本刊文章中的批评,因此对其他人的观点只进行概述,不予引证。)
一、关于“必然地得出”
《逻辑的观念》一书的核心是“必然地得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也是我理解和总结出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本质,我还认为现代逻辑不仅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更清楚明确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我称“必然地得出”是逻辑的内在机制。根据这一思想,我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同样是根据这一思想,我对国内普通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史、逻辑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一些看法,还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把“必然地得出”看作是逻辑的内在机制,不仅是我的研究结果,也成为我一切相关分析论证的基础。因此批评我的观点,不仅无法回避而且也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批评是无法令人同意的。
王雨田先生认为,“必然地得出”是我“特别突出地加以使用的,而在通常的逻辑学学术交流中都是很少如此使用的”(王雨田,2001年,第131页);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过逻辑的本质就是“必然地得出”,这是我从亚里士多德的两段话中“引申出来的”,“事实是,亚氏当时没有使用‘逻辑’这个术语,更没有给逻辑(或‘工具’)下过定义。这样的前提不过是著者对亚氏文本的解读,其真假有待验证和进一步的剖析。由此‘必然地得出’之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同上,2002年,第74页)。
这一批评有几个明显的问题。其一,没有人说“必然地得出”,大概不能作为批评我不能这样说的理由。说出前人所没有说的东西,而且说得有道理,正是学术研究的进步。其二,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过“逻辑”这一术语,我在著作中已经说明。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强调他对“必然地得出”的说明。因为,如果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过逻辑是什么,我们就用不着在他的思想中寻找分析他关于逻辑的说明了。因此,我不明白对亚里士多德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引申”。其三,我在著作中用一章(第2章,第21-47页)详细论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引用了他谈到“必然地得出”的两段原话,探讨了他与这两段话相关的两个理论,即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并试图通过分析从四谓词理论到三段论的发展来说明什么叫“必然地得出”。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论证,我提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核心思想是“必然地得出”。王先生既然说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的“真假有待验证和进一步的剖析”,就应该验证和剖析我的工作。但是,他对我的这些分析论证不仅没有进行验证剖析,而且还断定“由此‘必然地得出’之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想,这一批评不仅十分武断,而且也太随意了,因为实在看不出这个“由此”是从哪里来的。此外,王先生虽然承认“必然地得出”的作用,但是认为我“显然忽略了,‘必然地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其赋值是什么,是否正确有效”,因为“‘必然地得出’的未必一定正确、有效和保真”(王雨田,2002年,第74页)。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怎样才叫说明了“必然地得出”?按照王先生的说法,似乎既然谈到“得出”,就必须说明结论如何,否则对“必然地得出”的说明就是无效的。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的分析,我明确指出,所谓“必然地得出”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含有前提和结论的推理形式,即A├B”(王路,2000年,第42页);“‘必然地得出’刻画的是一种基本的推理结构,同时它也是推理所具有的一种性质,因此逻辑是关于推理的学科,并且是关于必然的推理的科学,特别是这种推理的必然性不是由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形式决定的”(同上,第45页)。按照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研究,我明确地说:“只要符合三段论体系这样的形式,从真的前提必然得出真的结论”(同上,第43页)。通过对现代逻辑的分析(第3章,第48-75页),我进一步明确地说:“‘得出’,具体地说,从A得出B,显然是一种转换,既然要求这种转换具有‘必然性’,那么这种转换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无法做到‘必然’,也就是说,这种必然性不能是思辨的,而必须是能行的,可以一步一步实现的”(同上,第68页);“现代逻辑凭借形式化的方法达到了建立逻辑演算的结果,而且形成了元逻辑的研究,从而达到了从句法和语义方面对‘必然地得出’的精确刻画和说明”(同上,第74-75页)。在《逻辑的观念》中不仅可以看到以上这些结论,还可以看到对它们的具体的详细的论证。这里,我之所以不惜重复再次阐述它们,只是为了表明,“必然地得出”对所谓结论是有说明的。但是,由于是对推理的刻画,因此它对结论的说明总是在一个推理的框架内,结合着前提一起说的。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必然地得出”(参见同上,第21页),到建立三段论,再到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形成,始终没有变化。因此,不是我忽略了结论如何,而是“必然地得出”对结论的考虑只能是这样。换句话说,逻辑自诞生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常识:不考虑前提和结论怎样,而考虑含有前提和结论的推理的有效性;逻辑所做的是提供一套方法,它们保证人们从真的前提必然得出真的结论。因此,“必然地得出”不仅不考虑结论本身怎样,而且它考虑结论的这种方式恰恰体现了逻辑的性质。从事归纳和辩证逻辑研究的人,由于其学科的特点,大概习惯于对结论有专门的考虑,因此会有上述质疑。问题是,这种理解与“必然地得出”是明显相悖的。
二、关于“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
根据“必然地得出”这一思想,我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并在书中进行了专门的论证。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很自然的。对于批评者的意见,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探讨什么是逻辑、什么不是逻辑,乃是逻辑学内十分正常的学术和学理的讨论。比如,有人认为,只有一阶逻辑是逻辑,集合论和高阶逻辑不是逻辑,甚至模态逻辑也不是逻辑。奎因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们批评奎因所代表的观点,同时探讨为什么二阶逻辑是逻辑,模态逻辑是逻辑。他们通过具体的讨论,根据现代逻辑的性质来论证,比如,奎因对高阶逻辑的批评是不是“足以使它们没有资格作为逻辑系统”(Boolos,p.45)。这样的讨论不仅使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的区别更加清楚,而且明确了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自身的一些性质,比如它们的表达能力、限度以及一些弱点。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像王先生那样质问:“逻辑学中怎能没有高阶逻辑?”或“逻辑学中怎能没有模态逻辑?”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逻辑的讨论相比(参见同上;另见Gabby),我觉得批评者似乎缺乏一种学理上的平和心态。
其次,说归纳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是一回事,否定归纳和辩证逻辑则是另一回事,二者根本不同。我在书中明确地说,归纳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因为它们不具有“必然地得出”的性质。我所做的是揭示并指出逻辑与归纳和辩证逻辑的区别。但是我并没有说不能进行归纳和辩证逻辑的研究,更没有说归纳和辩证逻辑本身的研究没有意义。我甚至明确地说,“我们可以利用逻辑方法来研究归纳”(王路,2000年,第154页);“辩证逻辑不是逻辑,但是辩证逻辑仍然是可以研究的”(同上,第192页)。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批评者非常强烈地指责我否定归纳推理和辩证逻辑。这大概同样体现了一种情绪和心态上的东西。
第三,王先生指责我宣扬“唯演绎主义、唯形式化的逻辑观”,而“唯演绎主义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背离时代要求的”(王雨田,2002年,第72页)。他有许多论据,比如恩格斯的话:“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同上)又比如,“演绎与归纳都是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同上,第75页)。再比如,演绎和归纳是“逻辑中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正符合奎因的整体知识观”(同上,第76页)。还有,“归纳和演绎的相互联系互补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识”(同上),等等。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什么是宣扬唯演绎主义?其二,说归纳不是逻辑是不是就是否认演绎与归纳的联系?
“必然地得出”刻画的是演绎,因此逻辑是沿着这一方向建立和发展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如此,现代逻辑也是这样。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符合“必然地得出”的。而从目前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我也看不出今后会背离“必然地得出”这一特征。探讨逻辑的时候,每个人无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说什么是逻辑。因此我也可以根据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来谈论什么是逻辑。正是根据这一点,如上所述,我得出归纳不是逻辑乃是自然的。如果说这是唯演绎主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这背离时代要求,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
我在著作中分析论证了归纳不是逻辑,但是我绝没有说归纳和演绎没有联系。问题是,王先生所说的联系是什么意义上的东西?尤其是,这样的联系是不是足以表明归纳是逻辑?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演绎和归纳都是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使它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归纳法的创始人培根建立了归纳法,使它也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培根甚至明确地说,他“完全是一个开荒者,既无他人的轨迹可循,也未得到任何人参加商讨”(参见王路,2000年,第128页)。我的问题是:演绎和归纳都是科学方法,但是它们是不是都是逻辑?引申一步,逻辑与科学方法是不是一回事?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说逻辑与科学方法是一回事。因为科学方法涵盖的范围比逻辑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问:可以同样成为科学方法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同样成为逻辑?与此相似,说演绎和归纳是奎因整体知识观中的组成部分,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整体知识观比逻辑的范围肯定要大得多。实际上,在奎因的整体知识观中,逻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但是若说归纳是奎因逻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需要好好看看奎因的著作,认真论证一下才行。因为直观上说,奎因甚至认为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都不是逻辑,他怎么会认为归纳是逻辑、甚至是逻辑的基本组成部分呢?有了以上讨论,实际上也就说明,归纳与演绎的联系即使是科学和哲学的共识,也不足以说明归纳是逻辑。至于说应该把演绎和归纳用到该用的地方,则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倒是认为,明确了演绎与归纳的不同,不仅有助于它们自身的研究,而且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应用。因此这种关于归纳是不是逻辑的探讨,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褒一方而贬另一方的问题。
此外,王先生强调推理的大前提,认为推理的“初始的大前提归根到底仍是由归纳给出的”,由此认为归纳与演绎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因此认为否定归纳“实则危及演绎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否定归纳,也就否定了演绎”。(王雨田,2002年,第76页)我认为,这些论述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讲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从探讨“是不是逻辑”的角度说,则没有什么意义。如前所述,逻辑是在推理的框架内考虑前提和结论,因此它不会专门考虑结论如何,也不会考虑大前提是怎么得来的。
三、关于逻辑教学
王先生认为我所主张的在哲学系开一阶逻辑作为必修课“是有道理的”,而在教学中“否定作为教材的‘普通逻辑’,则是没有道理的”(王雨田,2001年,第138页)。对于王先生的支持,我表示感谢!对于他的批评,我想扩大一些,即针对一般批评者的意见谈三个问题: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问题;逻辑与哲学的问题;有用没有用的问题。
1978年以后,我国逻辑学界提出逻辑要现代化的口号,因此涉及到逻辑教学的改革,存在所谓吸收论和取代论等不同观点的讨论。吸收论的观念是主张以传统逻辑为主,在此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成果,而取代论主张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我认为,如果仅仅是由于师资水平问题而无法教现代逻辑,那么暂时先教普通逻辑,或者说,先以传统逻辑为主,吸收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作为过渡,同时争取尽早或逐步实现现代逻辑的教学,毫无疑问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吸收论者不是这样。他们不仅坚持教传统逻辑,而且要搞一套普通逻辑,还要“论证建立普通逻辑教学体系的问题,并且认为普通逻辑不仅是教学体系,而且是科学体系”(王路 ,2000年,第195页),并且进行了许多这样的论证。因此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问题,而是涉及到逻辑观。我认为,吸收论者所谓建立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在《逻辑的观念》第7章第1节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此前我把其中一部分内容以“论我国的逻辑教学”为题发表出来。限于论文篇幅,我做了大量删节,特别是删掉了吸收论者关于建立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一些原话,如建立普通逻辑的教学体系,“不仅对于搞好普通逻辑的教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它将有助于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形成”;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王路,2000年,第195页)但是在文章讨论的一开始,我还是提出,“普通逻辑究竟是在传统逻辑基础上建立的科学体系,还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的产物?”(同上,1999年,第41页);在文章的最后,我也批评说,对于普通逻辑,“吸收论者还在孜孜不倦地论证它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同上,第45页)。也就是说,我的论述并不是仅仅在主张取代论,反对吸收论;也不是单纯地提倡进行现代逻辑的教学,反对普通逻辑的教学,而是、而且更主要地是批评吸收论所说的建立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正是针对这种所谓的科学体系,我在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懂现代逻辑,那么就应该认真学习。像普通逻辑那样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搞,因为这是不值得的”(同上)。但是,所有对我的批评,都停留在要不要取代传统逻辑、传统逻辑有没有用这样的层面上,而没有涉及关于普通逻辑的所谓科学体系的问题。不是说这样的批评讨论不可以进行,但是我认为,我之所以坚决反对吸收论,认为并指出它表面上不反对现代逻辑,实质上仍然是反对现代逻辑,就是因为它主张建立所谓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因为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永远也不搞现代逻辑。
自弗雷格建立第一个初步自足的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逻辑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它不仅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成为公认的基础学科。所谓现代逻辑,正是指这种独立的科学和这种公认的基础学科。因此,我从逻辑自身的科学性出发,反对建立所谓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反复强调和论证要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教给学生,就是说,要教给学生完整的逻辑理论,比如一阶逻辑、模态逻辑(参见同上,2000年;2002年)。当然,逻辑教学涉及的面比较广,有些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除了逻辑观的问题以外,还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我在阐述取代论的时候,主要讲的是在我国高校哲学系中这样做(参见同上,1999年;2000年)。也就是说,我没有说在所有学科的逻辑教学中都讲现代逻辑。特别是,我在书中和文章中明确地说,普通逻辑盛行了20年,“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培养出来一个逻辑学家了吗?……此外,我们使用这样的教材为现代哲学研究、尤其是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又培养了多少人才呢?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可以不再进行哲学研究,但是应该具备进行哲学研究的素质。如果说逻辑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逻辑素质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普通逻辑又有多少帮助呢?……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到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实践问题”(王路,1999年,第45页)。我想,这里的论述应该是清楚无误的。它说明普通逻辑培养不出逻辑学家,即对逻辑本身的研究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而更主要的在于指出,普通逻辑对我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有的批评者却指责我错误地把逻辑教学理解为培养逻辑学家,以培养逻辑学家为衡量教学的标准,并认为我的说法武断、不负责、不公平。我想,这样的批评未免有些不负责任。
就王先生的批评而言,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教学”是不是专指哲学系。逻辑与哲学的关系、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我在许多论著中已经做过专门论述。我不主张再讲普通逻辑那样的东西,主要是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考虑的。对于非哲学专业,我不太懂,也缺少教学实践。因此虽然我相信学习现代逻辑肯定有好处,但是我的观点只针对哲学系。我认为,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应该是严肃的,具体的教材改革应该是慎重的。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我国哲学系的逻辑教学,确实不应该再讲传统逻辑了。
普通逻辑有用,是批评者反对取代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根据。我不知道王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思。在我看来,“有用”、“有好处”绝不能成为高校教学的充分条件。但是,这个问题虽然明显,却不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传统逻辑没有用的时候,并不是就事论事,单指它本身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现代逻辑来说的。具体一些说,传统逻辑的核心内容是命题推理和三段论,当然是有用的。学比不学肯定也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有了现代逻辑,它不仅比命题推理和三段论更好,而且完全能够取而代之,因此我们说传统逻辑没有用了。(参见王路,2000年,第202-205页)
顺便说一下,批评者总认为传统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基础,学习传统逻辑有助于现代逻辑的学习;他们认为否认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完全割断逻辑科学发展的历史,甚至批评别人这样做是为了根本否定传统逻辑。我认为,现代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传统逻辑(命题推理和三段论)在“必然地得出”这一点上一脉相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传统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基础,学习现代逻辑非要先学习传统逻辑不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最初在构造逻辑系统的时候,因循传统逻辑的方法,结果没有成功,后来他抛弃这种方法,引入数学方法和函数的观念,结果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参见王路,1996年)翻一翻现代逻辑的导论性著作,常常会看到作者在序中声明,该书内容不预设任何知识。因此,学习现代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不预设任何传统逻辑的知识,乃是一个常识。不能区别这两件事情至少是理论混乱的表现,而“为了根本否定”之批评则更是凭空猜测。
逻辑的本质是“必然地得出”。因循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创建了逻辑这门学科,使它有一些独特的内容,但是与哲学融为一体。同样是因循这一思想,经过现代逻辑的发展,逻辑终于成为一门科学,并且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今天,逻辑不仅作为科学在进行研究,而且也作为学科在进行教学。然而,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对于逻辑的理解都应该从逻辑这门科学出发。因此,对现代逻辑的理解和把握,乃是逻辑讨论的共同基础。国际学术界是如此,在国内无疑也应该是这样。
标签: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辩证逻辑论文; 归纳演绎论文; 普通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奎因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