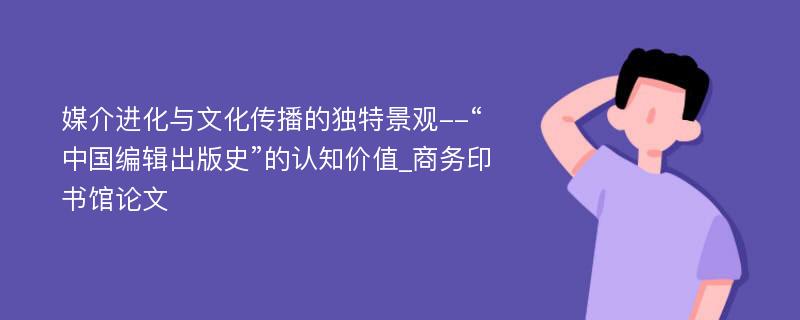
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文化传播论文,中国论文,景观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1-0180-05
相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电子媒介而言,以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已经变成了旧媒介。但“新媒介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与旧媒介不同,它改变了依赖于早期传播手段的那些社会方面”。[1](P65)因而新旧媒介的比较,为书籍史、媒介技术史、文化传播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现实意义,正如《书籍的历史》作者所指出的:“很久以来,我们就已经告别了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但这一现象才刚刚被更好地理解和研究。”[2](P423)中国作为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国家,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媒介文献和研究成果,其数千年的书籍编辑出版史,更是具有重新理解和研究的独特价值。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中国编辑出版活动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梳理其中所显现的媒介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一、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
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复制技术的改进过程为线索,出版传播可分为手工出版传播、机械出版传播和数字出版传播等阶段。手工出版传播又包括手工抄写和手工印刷两种方式。中国在古代主要处于手工出版传播阶段,在近代进入了机械出版传播阶段,在当代则进入了数字出版传播阶段。
中国是最早发明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国家,从汉魏以来纸张逐渐成为图书的主要载体,到唐五代雕版图书逐渐普及,再到近代引进西方石印技术和机械印刷技术,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改进,都推动了书籍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的繁荣。西方传播学者伊尼斯、麦克卢汉等人在研究传播史时,特别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对于社会性质以及人类感官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伊尼斯认为“根据传播媒介允许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倾向,它们成为‘有偏向的’”。[3](P512)如果具体分析中国的情况,古代以竹简、碑石为载体的图书,偏重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传之后世);以纸为载体的图书,更有利于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中国图书的载体形式也影响了文字内容和语言风格,造成了文、言长期分离的特征,还影响了文人著述讲究言外之意的思维方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分析道:“中国古代用以写书之竹简,极为夯重。因竹简之夯重,故著书立言,务求简短,往往反将其结论写出。及此方法,成为风尚,后之作者,虽已不受此文章的限制,而亦因仍不改,此亦可备一说。”[4](P9)而近代机械化大规模印刷的报纸的出现,必然引起语言文字的重大改革,出现更适宜向大众传播的白话文和“报章体”。
中国是以印刷媒介占压倒优势的,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5](P488)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6](P331)与此相印证的是,麦克卢汉也指出:“文献学的一条重要定律在谷登堡之前的雕版印刷中发挥了作用:文献生产越多,保存下来的越少。”[7](P203)在近代,西方石印技术的使用,催生了大众喜爱的时事娱乐性画报;西方高效率的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则带来了新式报刊的繁荣,从而改变了中国印刷出版物以书籍为主体的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复制技术的发展也受到出版传播环境的制约。中国书籍出版物以传播儒家文化占绝对优势,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字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阻滞了印刷机械化的进程。钱存训曾经分析道:“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相似,但其影响和作用则并不相同。”印刷术“不仅帮助中国文字的延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儒家典籍和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印刷,当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此,印刷术乃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一个基础工具。总的说来,印刷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所促成;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印刷术本身发展的趋向。因此,印刷术在社会上的功能是相互影响,并不完全是印刷术影响社会变革,各种社会因素也是促使印刷术发展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8](P270)
二、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建构
书籍既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媒介,又是可以营销流通的物质产品。书籍作为编辑出版物,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环境诸多因素的制约;而编辑出版物也具有文化建构的功能,或者说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特征和流通比例等,也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知识结构体系和文化传统。西方史学的年鉴学派关注印刷出版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其研究题目有《十八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等,通过对印刷出版物可计量因素的分析,研究其与文化传播、社会变革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状态史。[9](P414)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编辑出版物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先秦时代曾有过诸子并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元典产生的时代。冯天瑜指出:“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初步定型。这种典籍便可以称之‘文化元典’。”[10](P14)但是,先秦诸子具有原创性的文化典籍,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受到了很大限制,只有儒家经典获得了“经”的地位。蒋伯潜指出:“古以竹简丝编成册,故称曰经……所谓‘经’者,本书籍之通称;后世尊经,乃特成一专门部类之名称也。”[11](P2)在官方图书目录中经孔子整理而一脉相承的儒家经典被列在首位“经部”,诸子的著述则被列在“子部”,佛教图书和道家图书也附录在“子部”。从古代书目的分类标准和收录数量可以看出:以儒家典籍为主体,以史、子、集等部书籍配经而行,以释、道典籍为辅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体系。这反映了官方以“文治”、“教化”为主导的编辑出版理念,这也制约了传统出版物的总体特色和分布比例,对建构和维护中国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之际,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图书也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文人认识世界文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大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析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12](P3)利玛窦等人“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小。”[12](P10-11)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多种著作甚至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则收录了明末清初(1584-约1766)近200年来西方传教士在华著译出版的部分书籍。[13]这些西学出版物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知识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读书人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他们开始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大量翻译和编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书籍,而中国传统典籍作为不同于西学(新学)的国学(旧学)不断受到强烈的冲击。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也动摇了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这促使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例如,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了从接触西学书籍到反思“中学”甚至与“中学”决裂,接受西学的蜕变过程。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分析道:“1840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化中包括了大量从西方引进的文化要素。……在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起了选择的作用。……由于中西文化系统很不相同,中国人要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要素也是很不容易的。开始时差不多总是离不开中国固有文化这个拐杖,它虽然往往容易引起误解,但没有这个拐杖是不行的。”[14](P191)经过中西文化的多次激烈论争以后,国学出版物虽然命脉未断,其所占份额与西学出版物相比却逐渐减少了,其在当时的影响也远远不如西学出版物。1896年梁启超所编《西学书目表》在时务报馆石印出版,梁启超进行了统计:“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他感慨道:“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5](P141)显然,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物种类和比例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体系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新式传播媒介与社会变革
从传播学角度看,出版机构也是传播媒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我们要特别提到,近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以及新式报、刊的繁荣,改变了中国古代印刷出版事业的传统格局,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向近代化的进程。
1.新式出版机构推动文化事业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官方大规模兴办书局,大量刊印传统经史典籍,以恢复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受到重创的图书出版业,维持“文教”的传统。例如“左宗棠设局宁波刊经书,是为了使‘经史赖以不坠’”。而“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出现了变化,即由为刊刻经史读本之类而设置转向为译刻西学书籍而设置”。在经营方面,“书局全凭主要来源于公款之经费维持其活动。经费充裕,刻书亦多”,虽然设有售书门市部,却售价低廉,不追求赢利。所以,“官书局作为出版机构,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6](P366)这一时期的官书局已经将编译、刻印、发行等部门统筹起来,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从而与以往的官方编辑刻印图书的活动有了区别。
受到西方机械印刷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影响,中国新式民营出版机构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已经不同于传统书坊。李泽彰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1期统计,仅入会的出版机构已有22家。“又据光绪三十二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审定的教科书共计102册,由民营出版业发行的计85册,占全体五分之四以上”。这说明“出版业的重心已由教会和官书局移到民营的出版业了”。[17](P392)而商务印书馆就是当时民营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也是中国近代出版机构的典型。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最初以经营印刷业务为主,1903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自己的编译所,健全了以编辑部门为中心,编辑、出版、发行综合运作的体制,成为当时规模很大的新式出版机构。张元济作为编译所所长,既有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文化眼光,又有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的有效手段,在他的主持策划下,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大量新式图书,其中包括新式教科书系列、新式工具书和翻译西方名著等,这不仅推动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当时图书市场中占有了很大的份额。蔡元培曾如此评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其为商务印书馆。……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18](P58)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八种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外国小说,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和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都是古代以翻印科举应试书、《三字经》之类童蒙书来赢利的民间书坊根本无法相比的。王云五《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一文,详细列举了商务印书馆的各类新式出版物,明确强调“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进。而对此改进之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最力者,其唯我商务印书馆乎”。[19](P284)
2.新式报纸期刊改变传播格局
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除了图书出版系统以外,也有报纸系统,如官方的邸报系统。“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在此时期内,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綦严,无人民论政之机会”,因而是官报独占时期。[20](P29)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方公文,例如用木活字排印的《京报》:“所载无非上谕、奏折、官吏升迁、某官谢恩、某官请假等,只供统治阶级内部参考,发行数量不大。其形式是书本式小册子,薄薄的竹纸每日二三页,多或六七页,字体不大,大小不一,行字歪斜,墨色浓淡不匀,鱼鲁亥豕,几乎每页均有。外里黄色薄纸,盖有朱印木戳‘京报’二字,及某某报房字样。现在所见较早的也只是同治《京报》了。”[21](P77)
关于中国近代报纸的兴起,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纸,“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故称之为创始时期。在此时期,报纸之目的,有传教与经商之殊,其文字有华文与外国文之别”。[20](P29)而在西方报纸和新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自办报纸,“迨中日战争之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出,始开人民论政之端。此后上海、香港、日本,乃成民报产生之三大区域。其性质又有君宪、民主、国粹及迎合时代之多种,故称之为勃兴时期,而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基于此”。[20](P30)这已经指出新式报纸成为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主要传播工具,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报纸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有着不同的读者定位。其中既有以宣传政治主张为主的同仁政党报纸,也有面向大众的商业经营性质的报纸。例如,《申报》作为商业经营性质的报纸,强调其刊载内容的广泛:“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22]此外,《申报》还有小说故事连载、商业广告等内容。关于近代报纸与古代图书的明显区别,《申江新报缘起》曾比较说:“书册之兴,所以记事述言,因其意以传之世者也。……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23]报纸成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这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事业与世界隔绝的封闭格局,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和文化控制。上述比较可以为西方传播学学者对媒介分析的观点提供例证,“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7](P256)“作为形态,作为媒介,书籍和报纸在各种媒介中似乎是最不可调和的”。[7](P270)或者说“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24](P12)
报纸之外,各种期刊也相继编辑出版。其中专业的学术刊物(包括科学期刊)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戈公振所评价的“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20](P217)。还有多种大众化的娱乐杂志和画报,例如,《点石斋画报》以石印技术,采用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及时报道各种新闻时事、西学新知以及平民趣味,“因点石斋画报之起,上海画报日趋繁多,然清末数十年,绝无能与之抗衡的”[25](P99)。而大量新式文学期刊的出现,以及报刊连载小说形式与稿酬制度的建立,培养了职业的报人和作家,改变了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传播关系,促进了近代新文学的发展。一些出版社也同时经营多种印刷媒介,如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辑出版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杂志,与图书出版相互补充,扩大了经营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
总之,图书、报纸和期刊,虽然都是印刷媒介,却各具特色。从一个出版机构的经营来说,三者相互补充,整体运作,可以得到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古代出版机构不可能具有的经营模式。从整个传播环境来说,三者有不同的读者定位(服务对象),不同的编辑知识信息的方式和出版时效,又相互补充,从而改变了印刷媒介的比例、分布和传播格局。戴元光等人《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曾指出:“我们提出一个自认为很重要的观点:文化的特征,主要决定于在该文化中,偏重使用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人的比例。”[26](P242)这一观点可以借助近代编辑出版活动得到验证:多种印刷媒介并存的传播格局,特别是使用报刊媒介的人口比例的增加,不仅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对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知识视野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曾说明,他“最初关注的事情,是探索传播媒介如何改变了上一个半世纪美国的环境。新的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闲暇和消费的实质、社会化的进程,以及思想风气?它们实际上为何对美国日常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27](前言)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变化同样有助于探讨这些有规律性的变化现象。而这对于认识当今中国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激烈竞争又相互兼容的传播格局,考察不同媒介使用者的比例变化,及其对大众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演进的影响,也是很有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5-09-10
